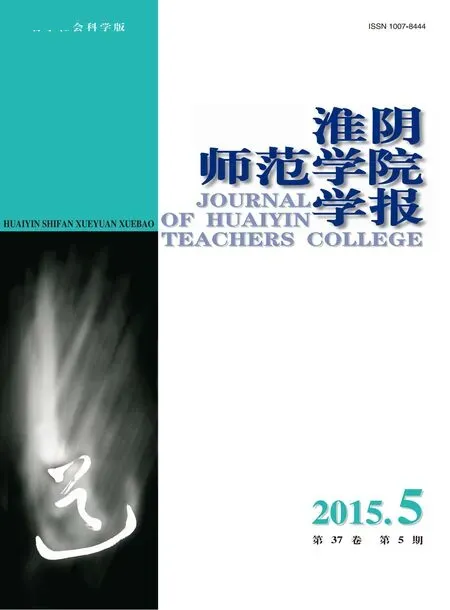“投石的诉说”:新世纪以来张承志精神世界的文学书写
文 娟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浙江宁波315100)
引言
著名学者黄子平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一时代的文学风貌,与一时代知识分子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直观密切。”[1]据此可知,文学作品可谓作家精神世界的征象,借助文字去体悟作家关于其生活语境的观察思考是有据有理的合法路径。对于张承志这样的文学知识分子而言,探查其精神世界的暗流与幽光自然最好深入他的文学作品。
在对哲合忍耶的皈依中,张承志对伊斯兰民族的文化品格有了深入的体悟和认同,但天生的“在路上”气质以及文学知识分子的理性召唤着他穿越哲合忍耶,吸收更多样的文化样态。他将受难的弱势群体扩展到了整个的第三世界,“投石的诉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永恒构件。“投石的诉说”源自张承志的散文名篇《投石的诉说》,文本中刻写了一个图画般的形象: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少年站在瓦砾堆上,面对隆隆驶来的坦克勇敢而又悲愤地拾起石块,套上投石索,拼尽全力向坦克掷去。瘦弱的少年和普通的石块当然不是抵抗战争的利器,但是此形象传达的是弱者的一种反抗情绪,是被压迫民众正义抗争精神的流露。“巴勒斯坦人用这样的语言,呼喊公正,呼喊着最古典和最低限的良心。投石的语言是神奇的;它超越了障壁唤起了良知和同情,也为非武装的民众反抗,做了痛苦而警醒的定义。”[2]259虽然此文的重心是巴勒斯坦民众面对新帝国主义战争所作的绝望抗争,但笔者更愿意将它视作张承志精神世界的一个面影。因为,在他的心灵中,一切的弱者,不管是中国的伊斯兰、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抑或其他的山区民众,还是亚洲地区甚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底层民众,都是他关心、挚爱和帮扶的对象。与他们站在一起,抵抗一切有形无形的压迫与侵略,维护生命与文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是他人生的目标和理想。在此,笔者扩大了原文本意蕴,将“投石”置换为一切的弱者,坦克隐喻着庞大的外在压制力量,譬如新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战略和“新十字军东征”等,从而将其视作张承志精神世界的永恒构件。所谓“投石的诉说”指代的是站在弱者的队列,以弱者的权利和利益为出发点,抵抗各种各样的文化或战争压迫,这种反抗虽然微弱而又无力,但是“它唤起的是良知,它种下的希望,会在下一个时代从废墟中发芽生长”[2]265。换言之,“投石的诉说”是文学知识分子张承志应对全球化语境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挑战而建构的精神策略,其表达的是个体的抗议之声,是知识分子社会良知和文化自觉的投影,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反抗的政治:立场、话语与行动
与第三世界被侵略和压迫的广大民众站于一列,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是张承志新世纪以来精神世界的政治诉求。张承志对于近些年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2001年的911事件并不是国际形势的断代标志,而应该朝前推移至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亵渎阿克萨清真寺、激化巴勒斯坦地区局势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迫使巴勒斯坦民众开始了弱者抵抗的“投石起义”,然而弱者的绝望抗争收效甚微,感到走投无路的民众将“投石的诉说”转换为绝望的自杀式袭击。而最为极端的反击,便是911事件。他认为:
9·11事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起因。
把它说成起因,是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宣传。它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真正的起因是列强和国际秩序对巴勒斯坦以及穆斯林世界施行的侵犯和榨取。国际舆论每天在上演着指鹿为马。当被侵害者用石块和生命送来语言时,这语言被下流地污蔑和误导,世界蔓延着丑化悲愤、践踏正义的劣行。我以为,每一个作家和每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说每一个穆斯林,都应该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扪心自问:你是否站在真实、良心和正义的一方?[3]
911事件被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势力刻意歪曲,“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主流的新闻媒体频繁征用。尤为夸张的是在西方强势话语的渲染篡改下,伊斯兰教竟成了“恐怖主义”的代称。自此之后,国际形势更为险恶。新帝国主义以911事件为借口,打着“反恐”旗号,开始推行新一轮的全球扩张战略。其目标不仅仅是穆斯林世界,它还包括中国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重新瓜分世界、统治世界、榨取世界是帝国主义势力的终极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在乎反恐、安全秩序、国际规则之类理论自身的悖论和荒诞,发动着一场又一场的“新十字军”进攻战。
因得对国际形势的理性洞察,再加上文学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张承志不仅以笔墨为武器揭露、控诉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侵略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的不义战争,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全世界平民为反抗不义战争而发动的大游行。在《2002年3月25日的小报》一文中,他怀着悲愤、绝望的情感,犀利地揭露美、英等国的军队利用先进核武器对阿富汗平民进行的大肆屠杀,抨击此种“非对称”的不平等交战态势给无辜平民造成的身心毁灭,这完全是强权对弱者的不义侵略。沉痛地拷问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在大屠杀面前的沉默,“人类的良知和最低限的正义,莫名其妙地究竟哪里去了?”[4]此种不义和沉默足以让良知尚存的他感到窒息和绝望,弱者的“投石起义”成为他心中的悲壮画面。
然而,真正的勇士在现实中并不虚无和绝望。在《投石的诉说》中,他在勾勒投石的意象与战斗之时,还表达了自己对未来胜利充满希望的战斗激情。那一个个瘦弱的巴勒斯坦少年掷向坦克的石块之声固然微弱,但他们的呼喊之声还是被一些失聪于强权话语的耳朵所捕捉,如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90岁的老妇杉原幸子、病弱的萨义德等,他们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守护人。他们的践行如同少年们的投石诉说,尽管微弱而又无力,但他们的形象是高尚的代言,他们的语言是神性的呼喊,那些沉睡的人类良知可能因此而苏醒。相信良知与理想的力量的张承志也加入到了“投石”的行列,他用文字传达自己对如此不义之世界的抗争。他坚信投石的时代中“投石的语言”不会泯灭,它所表征的超越种族与宗教的关于公正和大同的梦想,会有被更多人所理解追求的一天:“等到毒火如洪水退去的时候,鸽子会再一次衔着橄榄枝飞来,像古老的《圣经》故事一样。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会在和平中再生,以摧人肺腑的声音,唤醒死去了的希望。”[2]266
此外,张承志还参加了西班牙民众于2003年2月15日发动的大游行。美英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前夜,张承志正在西班牙旅行。出于对美英的强盗逻辑和强势媒体推波助澜的愤慨,他主动地打探西班牙的反战游行信息,并以一己之身投入其中,尽情宣泄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反战情绪。在拥挤的人流中,他高声地呼喊着“No a la guerra(不许战争)!”而这几乎是他学会的第一句西班牙语。游行队列中“战争是真正的恐怖主义”“美国就是恐怖主义”“让我们制止反伊拉克的战争(Paremos la Guerra contra Iraq)!”等标语震撼着他的心灵。对于战争的抗议、对于和平的向往是所有平民的心愿,他与所有的抗议者达成共识:“没有一个人相信所谓的反恐,没有一个人相信伊拉克要大规模地杀伤人类,没有一个人支持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5]由此可见,张承志反抗新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和行动是多么地坚定和自觉,这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追求。正因为这追求,才有了《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黑夜的凝视》以及《游击时代》等篇目的接连涌现。
二、建构的文化:“文明内部的发言”
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政治的抗争仅是公民意识的一部分。更为内在的身份认同,则源自个体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洞察、抗争和知识叙述。张承志对此有着自觉的反省和建构,在他看来人类的优秀文化应该:坚守民族内部文明的主体地位,既反对西方的新殖民话语又抨击国内汉文化主流的话语霸权,提倡“文明内部的发言”。张承志是一个崇尚自由、独立的思想者,他反对一切的外在压迫。因得文学知识分子的敏锐、理性以及长时间的国内、国外游历,他对世界范围内不同种类文明的质地与地位有了清晰认知。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歧视、压迫和侵略令他倍感心痛和愤怒。他站在弱者的立场,呼吁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明主体们挺直脊梁,以“文明内部的发言”范式来表达、审视和提升自我,从而有效抵抗和消解西方殖民话语或者本国内部主流话语的知识论述。
早在1989—1992年间游历加拿大、日本之时,张承志就觉察到了西方世界(包括日本)新殖民主义战略的“火药味”。新殖民主义的核心战略为“文化征服”和“经济侵略”,但并不排除军事手段的使用。强大的西方凭借其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实力,意图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进行“东方主义”建构,推行充满歧视与侵略色彩的文明“新体制”。面对此种压迫,张承志以笔为旗进行着坚决的抗争,《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真正的人是X》等文是他射向新殖民主义话语的有力子弹。
坚守中国本土文化,抵制日本“文化侵略”是张承志批判新殖民主义策略最为激烈的体现。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一个“全球化后殖民时代”日益逼近。在此语境下,由于羁旅日本时的切身体验以及日本侵华的惨痛铭刻,张承志将“日本文化”视作中国文化最为危险的敌人,常以高度警惕的态度审视之。即便是对待自己最为喜欢的日本歌手冈林信康,他也未曾麻痹。他写下了如此的检讨句子:“他是决心尝试以日本秧歌充亚洲文化的代表了,我不愿再为他写。”[6]对冈林信康艺术中凸显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满怀戒备。针对日本媒体丑化中国文化征象丝绸之路、黄河和长城的殖民化改写行为,他的揭露和批判则更为激烈。他说:
在日本的电视机上流过的黄河,像一个褴褛的母亲。也许,有很多儿女听见了她喊不出的嗓音?也许,她正在被她的儿女们贱卖?中国为什么不制定限制日本人拍摄黄河的方针,哪怕学韩国人限制日本文化活动政策的十分之一呢?……跨过黄河,跨过长城,这些矮腿的经济动物在中国的胸脯上持之以恒地寻找着侵略的论据。[7]
张承志在揭露日本“文化侵略”中国的图谋之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文化抵抗”策略。譬如上述引文中已涉及的希望政府方面出台文化“限制”政策;再如提倡写中文的美文,用母语大规模地书写国人自己心目中的黄河、长江等文化形象,捍卫“中国文明”的纯粹与独立。这两种方式都具有被动应战的意味,乃治标之技,他还提出了旨在治本的主动出击之术:重建中国文化。在他看来,唯有文明主体自身精神肌体强健,才有能力抗衡“他者”霸权的改写和形塑。而且文化重建的根本方法在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复活,而非一味地学习西方。其散文名篇《清洁的精神》,对此作了详细阐释。借着对许由洗耳,曹沫、豫让、聂政、荆轲等行刺,屈原投江等古代传说的讲述,礼赞中国古代文化中义、信、孝、耻、殉的清洁精神,从而树立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并期待这一遥远的高贵文化种子在当下的中国人心中发芽成长。
然而,张承志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者,在抨击西方殖民话语之时,他也理性地审视着国内的文明样态:
我们把剖析的矛,首先对准自己。我们给自己设置了禁忌与原则。如果说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学术的癌症在于,它曲解和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阐释权,那么时光在百年之后,地点在国门之内,我们自己对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少数民族、文明主体的发言,是否就不存在话语的霸道、文化的歧视和片面的胡说呢?[8]
由是,他站位于底层无声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倚靠少数民族文化质疑汉文化的主流话语,反对民族内部压迫。《心灵史》中,他对中国伊斯兰历史与价值的描述是此思想的见证。更为重要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借助自己的表述来呈现中国伊斯兰的历史与价值,尤其是将其作为一门学问加以阐释推广的时候,尽管他在描述之时已尽可能地引用了穆斯林表述自己的第一手史料,他还是期待着“泥足者”的本人能够入住学术的大雅之堂,因为“感悟他们遭受过的苦难,这一事业不该是名利之饵”[9]。他的任务只能是秘书或助手,尽力帮助“文明”的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内部的发言”。然而,他同样清楚实现此种愿望甚为艰难,因为“民众知而不言。他们不习惯发言,羞于解释常识,没有头头是道的口才,尤其是没有书写的能力。他们还没有对文化的主权意识;对知识分子的洋洋洒洒,和也许已经离谱的解释,他们的态度毕恭毕敬”[8]。为此,他投入大量精力去帮助民众跨进学术殿堂。譬如:他在清真寺内开办“泥足者的课堂”,用通俗散谈的语言给他们讲述“寺里的学术”;将美国学者弗莱彻研究哲合忍耶的英文原著《中国西北的乃格什板顶耶》(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Joseph Fletcher)介绍给清真寺;在网络上动员全国穆斯林介入苏菲起源问题研究;组织不同教派的伊斯兰青年学者共同整理出版阿汉合璧的《曼丹叶合》,等等。概而言之,他用“知行合一”推动着“文明内部的发言”朝实现的路途上步步迈进,这是其反对民族内部压迫思想的实践表达。
三、知识的抗争:抨“媚西”呼“自强”
在张承志看来,当下的中国文明重构势必勘破明末清初以来知识界广为流布的“媚西”倾向,在中华民族内部寻找第三种参照系。张承志认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布的“新体制”是一种歧视和压制穷国、用穷国的穷去保障富国的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且此种认知在许多国家已是常识,全世界进步的、正义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在对此问题进行揭露、批判和讨论,并寻找有效的抵抗方略。然而中国的右派“智识阶级”却置此全球性的文化现实于不顾,不遗余力地为“新体制”的所谓民主、普世价值和人道主义摇旗呐喊。就此而言,中国的右派“智识阶级”在文化姿态上的“全盘西化”,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他们全面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在文化源流上西方文明就优胜于中国文明。此与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完全无法勾连,实为堕落的“媚西”姿态,与本真的“现代化”追求也背道而驰。“现代化”不是彻底的“西方化”,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转型是其重要指标。事实上,他们已间接沦为传递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工具,可谓新帝国主义的帮凶。此种“媚西”倾向为张承志所深恶痛绝,一直以来他都以“侧着身子战斗”的姿态同其作着决绝斗争。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撕了你的签证回家》《无援的思想》到近些年来的《四十年的卢沟桥》《聋子的耳朵》等文章,他一直用犀利的语言抨击着“媚西”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尽管“媚西”的“智识阶级”现在占据主流,但是他们的学术依然意义鲜少。因为他们的学术一味尾随西方,从来没有同“泥足者”的人道主义结合过,缺乏正义的真知和力量。他们最终会被中国正义的知识分子击败。在激烈的批判之时,张承志对主流的“媚西”倾向亦有理性的深入研究。他既在历史、文化的源流中挖掘其形成的内在文化心理,又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切身境遇中剖析其主观动因,呼吁知识分子走出昔日“阴影”,在更为阔大的范围内追寻文化参照,做健全文明的“儿子”。
在张承志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英美文明,也就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式思想。其成因在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因得中国近现代史上长期的屈辱和失败,在文化心理上所积淀下的深重民族自卑感[10]。此种自卑其来有自,历史悠久,危害亦严重。百年前,确切地说,甲午海战失败后,整个民族心理完全处于自卑之中,以至于从权势者到普通知识分子开始了“全盘西化”的跟风式学习。在此西化过程中,曾经以求知为本的学习心理大多被异化为奴才心理,完全以西方马首是瞻,凡西方的皆好,凡中国的皆坏。此风自19世纪末始,一直漫漶至当下,虽然间或有中断,但主流基本如此。在《波斯的礼物》一文中,他借着探寻中国史学界关于波斯史料的研究历程,学术化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思想。他说:
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一个介绍、追撵,甚至取悦西方的过程。欧洲在一种仰视的目光里被中国人琢磨。欧洲列强的思想、方法论、世界观,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圣经,刻苦攻读,咀嚼再三。欧洲的东方学,在被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得博大,也日益富于优越感。[11]
此外,张承志在一次访谈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媚西”原因作了别种层面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境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以切身理解为基准,作了如下论述:
中国知识界普遍出现这种“媚西”倾向,实际上与长期以来“左倾”的恐怖历史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生怕再现那段不人道的、文化专制的历史。因为记忆太恐怖,所以在现实中就片面地强调向西方学习。不能否认这种心有余悸是真实的,这里可能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他父母妻儿的遭遇。但是,我希望这样的知识分子有更广阔的思考,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中肩负着一柄双刃的宝剑:一方面,如果你忘记过去,昨天高唱某种理想的人可能再用专制的思想来压制你;另一方面如果你矫枉过正,又可能招来一个帝国主义的阴魂。我在写那些文章时,知道别人会把我说成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其实,正是在“文革”时我反对过“极左”。正是我们知道“文革”时的残酷,才渴望铲除那罪恶的土壤。哪怕背负误解和咒骂,思想仍然必须讲出它要讲出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要面临的悲剧性命运,鲁迅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被多少知识分子嘲笑?他也和知识分子整体翻了脸,但他坚持自己的道路,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我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双刃剑的命运面前,做出正义的选择。不要因过去确实曾有过的一部分个人遭遇,而丧失分析今天和今后形势的能力。[12]
鉴于对中国知识界“媚西”之现状、原因以及危害的全面认知,张承志提倡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华民族内部寻找第三种思想参照系,一种有别于中华文明和英美文明的参照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参照系”》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英美文明中包含着太多不义的殖民思想,它的主导地位是由其一百年来的强权政治铺就的,不能作为其自身优越性之证明。中国知识界应该以分析和研究的态度对待它,学习之时亦要批判。对于真正追求学问、文化以及内心丰富的年轻人而言,世界上可供学习的参照系是复数的,譬如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自尊思想、非洲文明、阿拉伯文明、伊朗文明等都值得学习。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只要愿意求知,接近这些文明并不是难事。具体到中国,他重点推荐的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倡导没有止步于概念化的说教,他鼓励年轻人在学习某种参照系之时,还要从自己的生活实感出发,去发现感悟更多的文明,用多维的视野去思考和生活,把握好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做一个尊重“他者尊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当然,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其精神世界中的三块大陆自不必说,1999年至2003年间的异国游历可谓追寻更多文明参照系的又一例证。期间,他两次自费远渡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安达卢斯旧地,在那里实施共计6个月的文明寻访。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每一个安达卢斯的历史遗址,行踪广涉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三国。游历时收集的异质文化风俗资料以及自己的诸多感受,全部写入了《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一书。此书以地中海以西的世界为叙述中心,西班牙的自然、历史与人文有着更为鲜活的书写,但它依然不是坊间游记,而是张承志关于文明之沉思的载体,因为他的游历本就是“为了突破狭窄知识的牢笼”“追求——求知的震撼和愉悦”[13]。
结语
在消费社会的当下,不管是知识界自身还是社会语境不断将知识分子的“神圣性”和“抗争性”祛魅,大多的知识分子已沦为媒体时代中的“名流”。作为“名流”的知识分子在与大众媒体的“互惠”中不断地攫取更多的文化资本和“影响的权力”,已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以致整体的社会现状如同法国学者德布雷曾认为的那样: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也不过是说他们的形象和声音留存于公众之中而已。通过各种媒介来获取资本和名声是确保知识分子存在的手段。在这一意义上,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反对人民利益最危险的因素。[14]在此氛围下,张承志的精神探索及其文学便有了异端的色彩,他的平民性、抗争性、民族性以及建构性既洗涤着当今所谓知识界的“名流”污垢,亦呼应着鲁迅先生上个世纪初询唤“精神界战士”的五四命题。其不仅为当下积弱的文学知识界提供了健康清朗的文学知识分子标杆,亦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立了存照。
张承志曾将自己的此种精神认同称为五彩炸弹。社会主义革命的红色、伊斯兰哲合忍耶的绿色、内蒙古草原的黄色、新疆天山的蓝色,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分别展现,而这每一种颜色都是对某种压制性话语的反抗。它们是他精神清洁、独立、自由的标志,他“不追求任何一种颜色的体制”“宁愿对每一种乖顺的颜色都是异端”[15]。他不在乎被批评、被封锁,不留退路地坚决反击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不公、不义,他用文字将红绿黄蓝调色成黑色的炸弹,投向这个日渐无耻的世界,高调地为“精神界战士”们提供话语支撑和行动援助。
[1] 黄子平.小引[M]//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6.
[2] 张承志.投石的诉说[M]//张承志.张承志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张承志.讲演河州城[M]//张承志.你的微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76.
[4] 张承志.2002年3月25日的小报[J].天涯,2002(3).
[5] 张承志.热情的行踪[M]//张承志.饮虎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95.
[6] 张承志.艺术即规避[M]//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276.
[7] 张承志.无援的思想[M]//张承志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41.
[8] 张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J].天涯,1998(5).
[9] 张承志.为泥足者序[M]//张承志.你的微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94.
[10] 张承志.中国知识分子的参照系[J].东方艺术,1996(1).
[11] 张承志.波斯的礼物[M]//张承志.饮虎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02.
[12] 邵燕君.我被选择做一个“信仰的中国人”——专访回民作家张承志[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56/2007/0109/1286.html.
[13] 张承志.毗邻的古代[M]//张承志.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41.
[14] 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M]//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4.
[15] 张承志.怒向五彩觅炸弹[M]//张承志.你的微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132.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