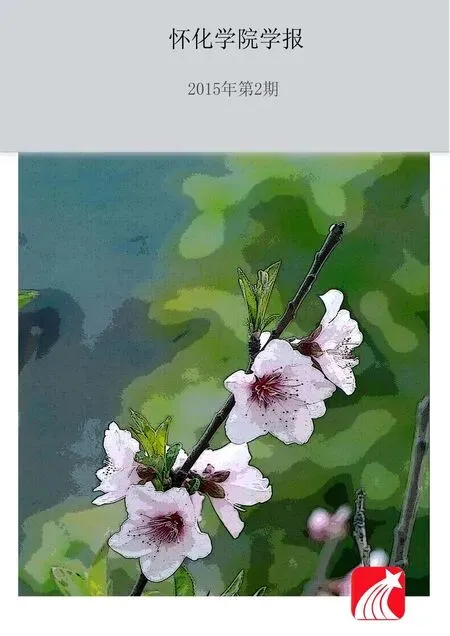论雅斯贝尔斯悲剧理论的独特品格
杨水远
论雅斯贝尔斯悲剧理论的独特品格
杨水远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悲剧理论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生存哲学的视角对“临界境况”中人的生存悲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阐明了悲剧与“生存”、“密码”、“真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悲剧是生存的基本底色,悲剧诞生于悲剧主人公追寻真理的失败,从而把悲剧艺术阐释为领悟“大全”的重要“密码”。其悲剧理论综合地继承成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文本阐释和尼采等人的生存论分析,具有独特的理论品格。
雅斯贝尔斯;悲剧理论;生存;真理;密码
随着理性精神的失落和上帝的死亡,西方哲学史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继承克尔凯郭尔开创的生存哲学传统,不再建构无所不包的概念体系,也不再仰望万能的上帝,而是高扬人的存在,把人的在世生存作为哲学的主要运思对象,其哲学因而与传统形而上学具有很大的区别,其“生存哲学”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孕育于其生存哲学体系内部的艺术观念特别是其悲剧理论也与传统哲学家的艺术观念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
一、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独特性①
雅斯贝尔斯的全部哲学几乎建立在“生存”、“密码”和“大全”这三个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展开的基础上,可以说这三个概念构成了雅斯贝尔斯哲学底座的三角支架,而对雅斯贝尔斯的任何言说,都必须从这三个概念开始。简而言之,“大全”(或称为“超越存在”)来自雅氏对康德“物自体”的改造,用来意指那个无所不包,无法言说却又真实存在的“至大无外的空间”,“它(大全——引者注)从来不成为对象。它是那样一种东西,它自身并不显现,而一切别的东西都在它里面对我们显现出来。”[1]4可见“大全”是非对象性的存在,无法以知性的有规定性的逻辑概念加以把握,它相当于上帝(这也是雅氏被认为是有神论存在论的重要原因)但又不是上帝,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人内心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某种主观力量,是某种内在于人自身而又超越于人,从而使人超越的东西。”[2]429与康德不同,雅氏的“大全”不是一个超验的根本无法用知性认识的“物自体”,而是一种与人本身相关的精神力量。据此,雅斯贝尔斯把人的存在状态区分为两种,一为实存(Dasein或译为实在,此在),一为“生存”(Existenz),处在“实存”状态之中的人以实用主义和自我保存、扩展为标准,在乎自己当下的利害,可以说是人的沉沦状态。处于“生存”状态的人却不一样,它完全剥离了外在的利害关系,是一种领悟到我是我自己的状态[1]27-29。“生存”概念来自于黑格尔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者:克尔凯郭尔。雅氏认为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生存使那些与一切确定知识无缘的东西表现出无限的深度。”[3]49这些与知识无缘的具有无限深度的东西乃传统哲学遗忘的部分,那就是人的存在,主要包括人的内在的精神以及非理性、欲望、情绪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氏把生存与人的本真存在深刻的联系在一起。
这样,人的“生存”和宇宙“大全”之间就有了某种相通性,雅氏说“生存乃是自身存在,它跟它自身发生关系并在其自身中与超越存在(大全)发生关系,它知道它自己是由超越存在(大全)所给予,并且以超越存在(大全)为根据。”[1]8这种相通性正是作为“生存”的人认识最高“大全”的基本路向,也使对“大全”的认识成为可能。然而“大全”并不自我言说,只是透露出某些本身的消息,这些消息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实际的生活世界,处于“实存”状态下的人永远也把握不到这些消息,只有处在“生存”状态下的人才能感悟并解读这些消息,这些消息,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密码”。密码语言有不同的存在状态,在雅氏看来,可以分为三种,即“超越的直接语言”、“在传达中变得一般的语言”和“思辨语言”[4]675-682。“生存”把握“密码”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超越”的过程,是“生存”在解读“密码”中向“大全”的超越过程。以上是雅氏哲学的基本轮廓。
艺术哲学在生存哲学中起着独特的作用,雅氏宣称在艺术中思考而不是思考艺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很少言说艺术,在言说艺术的时候,艺术也只是证明其哲学意图的工具,是哲学的“器官”而不是哲学本身,悲剧理论作为雅氏“唯一的艺术专论”也充当着这样的功能。总体而言,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以其对人的生存的强调而区别于传统的概念形而上学,悲剧与人的生存最为切近,因而成为雅氏关注的重要对象。在其哲学中,雅氏创造性地把悲剧与“生存”“密码”和“真理”联系在一起。
二、悲剧与“生存”
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只见概念而不见人,黑格尔的概念体系有着自己本身的演绎规律而外在于人,就是黑格尔本人,也是绝对理念演绎选择的一个传声者而已,其悲剧理论对“冲突”与“和解”的分析也有类似的特点。雅斯贝尔斯则把悲剧和人的生存结合起来,从而把对悲剧的讨论与人的生存困境深刻地勾连在一起。
对人生基本困境的认识,雅氏用“境况”与“临界境况”这一对概念来加以把握。雅氏认为,人生在世,就必然地存在于某种境况(Situation或译为境遇)之中,境况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主、客观现实,包括物理、心理空间,文化环境等现实条件,境况对于人而言,是被给予的,人不可能脱离境况而存在,但人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改变当前的一般境况而进入下一个境况。虽然如此,人生当中有诸多的境况却是无法改变的,它如影随形,始终与生存同在,甚至是领悟生存的最佳场所,雅氏把这种境况叫做“临界境况”,雅氏说“临界境况是不变的,它只是在显现中发生变化。对于我们的此在,它是最终的。它不会一览无余,在我们的此在中,我们看不到临界境况后面的任何东西。它犹如一堵令我们碰壁、失败的墙。我们不可能改变它,只能使它清晰;我们不可能根据他物来解释它,引申它,它与此在本身同在。”[5]637雅氏认为最适宜说明“临界境况”是“死”,因为人不可能对死亡获得任何的经验,死亡来临,此在也就消失。作为“实存”,根本无法领会死亡的意义,他们选择规避或者遗忘死亡。而“生存”则坦诚地面对死亡,并在对终结的忍受中领悟到无限,从而向自己的生存生成,所以雅氏说“对临界境况的经验和生存是同一个东西。”[5]638“临界境况”是阐明生存的重要场所。
雅氏对“临界境况”进行了分类,其中最重要也最关涉人的生存的是“个别临界境况”,个别临界境况包括“死”、“苦”、“斗”、“罪”四种。“死”和“苦”是没有我的介入而形成的无法改变的“临界境况”,而“斗”与“罪”则是“由于我的介入而造成的,他们是我积极所干的事。”[6]658在生存哲学体系内,作为“临界境况”的“斗”与“罪”与悲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雅氏把生存与悲剧联系起来。
首先是“斗”,人普遍地处在于“斗”之中,正如人的存在分为“实存”和“生存”两个层面,“斗”也相应地区分为“为实存而进行的暴力的斗”和“在爱之中为了生存而斗”(或译为“爱的搏斗”)。在悲剧中,“斗”表现为因悲剧冲突而产生的斗争,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身的争斗。这在悲剧作品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个别与一般的斗争,历史的生存原理之间的斗争,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的斗争等。其中在个别与一般的斗争中诞生了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诞生于个别与社会普遍性(如对现行权利、地位、秩序的不满)之间的斗争,性格悲剧诞生于个人力量与浓聚于人物性格内部的普遍性格之间的斗争。而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的斗争则更多的是人与人或者人与自身之间斗争的象征形态。
雅氏关于“历史的生存原理之间的斗争”的悲剧观念则主要继承和发扬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雅氏认为新旧社会的“过渡是悲剧产生的地点……他们(历史英雄—引者注)所带来的东西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注意,直到旧事物朦胧地感到了危险,便聚集起全部力量来,打击新事物最强有力的代表,消灭新事物。”[7]455可以说,这一观念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传统。黑格尔认为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总是悲剧的形象,马克思认为革命是最适合于悲剧的题材,恩格斯在评价拉萨尔的《济金根》时也说悲剧表现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8]560美国学者大卫·尼科尔斯(David Nichols)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重视悲剧的斗争传统,他说:“两位哲学家都诉诸悲剧性的语言去理解迷狂的人类在历史中的争斗。”[9]28可见,雅氏对这一传统是自觉地加以继承的,不同的是,雅氏的悲剧论述始终是与人的本真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生存原理之间的斗争也只是其悲剧斗争中的一种形态。
其次是“罪”。作为一种“临界境况”,“罪”主要体现在人的行动中,人无论选择行动还是不行动都是有罪的,如果选择行动,则必然会伤害到别人的生存,如果选择不行动,不行动本身却形成一种放弃的行动,而绝对的不行动必然导致迅速的没落,是一种自杀的方式。所以“无论我行动还是不行动,两种都有其后果,我不可避免地有罪。”[6]673而“罪”之所以成为“临界境况”,乃在于对“罪”的一力承担,负责意味着随时准备对罪责负有责任,“生存”就在罪责的不可消除的压力之下呈现出来。
在悲剧中,“罪”区分为广义的生存之罪和狭义的行动之罪两种。前者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深广的传统,从阿那克西曼德那里就开始宣称人最大的罪乃是降生于世。人的降生和生存势必会因为自己的生存而危及到别人或者别的生物的生存,这本身就是一种罪,只要人诞生就无法逃避。另外一种是我是有罪的祖先的后代,因而我的罪与生俱来。悲剧《安提戈涅》的主人公安提戈涅就是生存之罪的重要代表,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和他母亲乱伦的产物,她的生存之罪是与生俱来的,她的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而在国王禁令和亲情之间,安提戈涅选择了对禁令的无视,她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始终与自己内心保持一致,她的悲剧是生存悲剧。第二类是行动之罪,雅氏规定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行动,然而失败却诞生于起源于自由的行动,人本来是正当地真实地行动,但罪总是不可避免,雅氏认为罪本身就具有无辜的特点,但是人承担、践履自己的责任,在自由行动不可避免的失败中坚守,从而见证了生存的伟大,见证了人之为人的伟大。
三、悲剧与“密码”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研究悲剧的《诗学》是其各种学科分类中的一门,在黑格尔那里,研究悲剧的美学是作为艺术哲学而存在的,是主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雅斯贝尔斯这里,艺术(包括悲剧)则是作为哲学思考的器官,是领悟哲学“大全”境界的重要中介、“枢机”和“密码”。悲剧作为“密码”之一种,在其哲学框架中具有别具一格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文我们对雅斯贝尔斯整个哲学框架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密码”在雅斯贝尔斯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密码”沟通了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和作为超越存在的“大全”,使不可认识的“大全”在“生存”对“密码”的解读中得到领悟,完成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雅斯贝尔斯在《哲学》第二卷中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性被称作密码,因为它并非作为它本身、而是作为其语言才是超越。它根本不是为意识所理解的语言,或者仅仅为意识所听说,而是它的如何反应的方式为了可能的生存而存在。”[4]674雅氏这句话对“密码”做了必要的规定和描述,也就是说“密码”是“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是“大全”透露出来的“关于它自身消息”[1]4,是指向“大全”的可以领悟的语言。这种语言不能为作为“实存”的一般意识所理解,只有当人作为可能的生存时,才能接近这种语言。雅斯贝尔斯所区分的三种“密码”语言,第一种“密码”语言(超越的直接语言)作为形而上学的经验是不可把握和言传的,透露着部分“大全”的信息;第二种“密码”语言(在传达中变得一般的语言)则以直观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包括史诗、神话、悲剧、绘画等等;第三种“密码”语言(思辨)则表现为概念哲学对“大全”的阐释。孙秀昌认为这三种语言可以当做“密码”的三个层级,“由前至后,距作为根源的‘生存’愈来愈远,与此同时,与作为依据的‘超越存在’的显现愈来愈间接。”[10]168所以艺术语言理应成为最为合适的领悟“大全”的“密码”,除此,第一种语言太过玄奥,第三种又过于理性,处于二者之间的艺术却具有二者的长处而扬弃了其缺点。
虽然在阐释第二种“密码”语言的过程中,雅斯贝尔斯所使用的主要例子是“神话”而不是“悲剧”,但他认为“悲剧”与“神话”、“绘画”共同属于第二种密码语言,它们具有一样的地位。我们认为,“悲剧”作为直观的艺术语言通过“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情境”以及所营构的“悲剧氛围”,让主人公和观众在面对“临界境况”时体会不可避免的失败而领悟到“大全”的意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阐明。
首先,雅斯贝尔斯认为“在有限的毁灭中人看到无限的现实和真理”[7]477。“无限的现实和真理”就是对“大全”的一种表述,也就是说人在悲剧的毁灭中领悟到了“大全”的某些信息。舍勒曾说,悲剧一旦发生,价值的毁灭就不可避免。但是悲剧之所以为悲剧,不在于毁灭本身有多么的凄惨和悲壮,乃在于人们在经历悲剧的时候,不仅仅看到毁灭本身,而是透过毁灭看到人在价值毁灭中面对毁灭的抗争和力量,即使是失败了,也能在失败中领悟到人的本质力量最大化的美。
其次,从悲剧欣赏来看,欣赏者在悲剧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从而在面对自己的人生困境时,拥有了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坚执。雅斯贝尔斯在“悲剧中的解救”中明确说道:“那主要不再是爱看热闹、破坏的要求、寻求刺激的渴望,而是比所有这些都更深刻的东西在悲剧面前征服了他:他的兴奋过程,由观剧中增长的知识所引导,使他与存在相接处,由此使他的伦理道德在真实生活中获得了意义和动力。”[7]476观众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总是把自己想象为悲剧主人公,与他们同时历经一场场人生选择和悲剧命运,从而学会了面对人生普遍困境的智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哈姆雷特那里学会了如何在“沉默中面对自己的命运”,从俄狄浦斯那里学会一切都需要命运自承。
四、悲剧与“真理”
把悲剧与对真理的追求结合起来,在以往哲学家那里,虽然也偶有涉及,但是却没有把悲剧和真理、知识直接地挂起钩来。而雅氏的悲剧论却处于其重要著作《真理论:哲学逻辑学(第一卷)》中。“悲剧知识”被雅氏作为阐释“真理完成”的一个具体例子,成为雅斯贝尔斯最为重要的艺术专论。
早在1937年,雅斯贝尔斯就在《生存哲学》一书中探讨了真理问题,并把真理区分为“真本身”(Wahrsein)和“某个特定的真理”[1]23,前者是生存所掌握的真理,这种“真理”只存在于“大全”之中,而后者则为“意识一般”所掌握的真理,是真理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整全真理”②作为真理超越性存在的最高的形态,是“生存”永不停息趋附的一个终极目标。在经验世界,“整全真理”分裂为不同的多样性的真理,其中包括“实存的,精神的、生存的种种真理”[1]27。雅斯贝尔斯曾言“在完整状态中的单一的真理(即真本身,整全真理—引者注)是不可能有的,有的毋宁是在历史的形式中遇到的多重真理。”[11]89这些真理形式各具片面性,但是每种真理的代表力量却永远相信其所坚守的真理的永恒性,于是当不同的“真理”力量代表发生冲突时,悲剧就会产生。“悲剧发生在互相冲突的力量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真实的分裂或真理的不统一是悲剧知识的一个基本判据。”[7]460而这种冲突却是主人公追寻真理,走向“整全真理”的必由之路,对真理追寻的悲剧性乃在于:人作为真理的探寻者,却不可避免的面对失败,“整全真理”无法拥有。可以说,雅斯贝尔斯利用对悲剧的诠释来探究真理问题,这是雅氏“在艺术中思考而非思考艺术”这一原则的贯彻。在雅氏看来,悲剧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传统悲剧理论所说的命运或者对不可改变之物的承受,而是悲剧行动者对真理的探求,悲剧主人公的悲剧性在于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本身并坚持下去。在艺术中则表现为互不关涉的真实力量,各自以为自己是唯一准确的整全真理,从而产生无可救药的相互冲突,最后走向毁灭。
从这个角度来观照悲剧,雅斯贝尔斯认为有两种悲剧类型。一种是对“整全真理”的追问中暴露出真理的局限以及在一切事物中的不公正,在这个过程中每一行动者都展示出某些个别的真理,与此相应,也暴露了真理的局限,从而必然走向毁灭。第二种是悲剧作品中悲剧主人公本身对真理的探求和追问,他们探寻真理的可能性、意义和后果并在探讨真理的过程中毁灭了自己,从而完成向“整全真理”的超越。雅斯贝尔斯重点阐释的是第二种悲剧,并以《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两剧为例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阐释为“恋母情结”的原型,有的学者则认为俄狄浦斯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的悲剧。雅斯贝尔斯则别开生面,他认为俄狄浦斯的悲剧乃在于俄狄浦斯明晰的理性力量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此类似,一般学者往往把哈姆雷特的悲剧归结于其延宕不果敢的性格,雅斯贝尔斯则从真理的角度作出了另一种解释。由于雅氏对二者的阐释基本类似,我们选《哈姆雷特》作为例子来说明雅氏对悲剧与真理关系的探讨。
雅氏认为《哈姆雷特》“全剧就是哈姆雷特探索事实真相(真理)的过程”[7]464,然而造成哈姆雷特悲剧的是哈姆雷特需要去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指证一桩无法指证的谋杀案,去向人们证明一个无法证实的真相,而且这桩谋杀案与自己的父亲、母亲有关。哈姆雷特是真理的拥有者,因为老哈姆雷特的阴魂把一切的真相都告诉了他,并且作为一个儿子理应为自己屈死的父亲报仇雪恨,然而这种知情却让哈姆雷特陷入悲剧情境,他没有证人证物可以向世人证明罪恶曾经发生。杀死一个罪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哈姆雷特是有机会杀死自己的杀父仇人的,但是这样做便不能把真相公布于天下,让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即使自己在复仇之战中死了,他也要求他的朋友霍旭拉忍着人世的苦痛把真相公诸于世。
哈姆雷特一方面洞悉罪恶,另一方面需要在无法摆脱的命运陷阱和虚假的世界上“重整乾坤”。雅斯贝尔斯认为:“哈姆雷特必须担任一个实际的角色,一个在不真实的世界上探索真理的角色和对所发生的罪行报仇雪恨的角色”[7]465。而这个角色给哈姆雷特所带来的是他必须承受他的性格和分配给他的角色之间对立所产生的痛苦和扭曲,因此一般学者认为的哈姆雷特的“延宕”性格也就可以从其内心的痛苦而得到应有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是哈姆雷特性格的怯懦和优柔寡断,反而证明了他想要行动而未能找到合适时机来行动的紧迫感和自我反省。
《哈姆雷特》的悲剧在于主人公对真理的追求以及整个剧本结局的恐怖性,主人公没有任何自我实现的机会,即便把真相公布于众都需要他的朋友霍拉旭来帮他完成。“哈姆雷特的真理(或译为真实)之路没有指出解救”[7]471。这正是这部悲剧的悲之所在。所以哈姆雷特悲剧指向了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和解答:真理找得到吗?有可能与真理一起生活吗?
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人的境况之中,“生命的力量产生于盲目之中,产生于神话及其臆想认识的代用品中,产生于无疑问之中,产生于非限制的非真实中。在人的境遇中探寻真理提出了一项无法解决的任务。”[7]473人的境遇是有限的,因而谬误往往是必然的,“整全真理”却是无限的“大全”,追求绝对的“整全真理”预示了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的必然失败,然而在必然的失败中留下了哈姆雷特超人而不是非人的伟大印象。
五、结语
只有把雅氏悲剧观念放到其生存哲学的整体框架中,阐明悲剧与生存哲学基本概念“生存”、“密码”以及“真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把握雅氏悲剧理论的全部意蕴。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一直立足于悲剧戏剧文本的研究,这种研究试图对悲剧文本、悲剧创作、悲剧演出做出面面俱到的探讨。那么从叔本华开始,悲剧的研究就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向,这个转向超出悲剧文本的束缚,直接面向人的悲剧性存在,这个转向是由尼采来完成的。雅氏正是在综合前面两者的基础上,把悲剧理论纳入其生存哲学的框架中。在雅氏那里,悲剧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不仅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状态,而是作为生存哲学始终氤氲着的基本氛围,难能可贵的是雅氏与叔本华的悲观不同,雅氏的悲剧始终充满了进取和超越的元素,也许大全、成功、真理无法拥有和把握,而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却恰好在于向无限的趋近和挑战,在触摸无限的过程中,有限的肉身随时都有可能毁灭,但是人的精神却可以长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雅氏是深谙悲剧精神之三昧的。
注释:
①本文所选雅斯贝尔斯悲剧理论的译文均出自吴裕康译的《悲剧知识》(载1994年上海知识出版社《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一书),雅斯贝尔斯论悲剧的译文在国内已有五个译本,包括1970年台湾叶颂姿译《悲剧之超越》,1988年亦春译《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余灵灵等译《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以及1994年吴裕康《悲剧知识》和2003年朱更生译《卡尔·雅斯尔斯文集》本,可见国内对雅斯贝尔斯悲剧理论的重视。除了吴裕康、朱更生本译自德文原文,其余皆自英译本Tragedy is not enough转译。朱更生译本略显生硬,故本文选吴裕康译本。雅氏哲学译文除了为数不多的几部外,多以节译的面貌散落在不同选辑中,就是对Jaspers这个名字的翻译也很多,同一译者前后使用译名也并不一致,比较混乱,本文除了注释一律采用“雅斯贝尔斯”这个译名,期待国内翻译学界对雅氏哲学的进一步译介。
②在雅斯贝尔斯哲学文本中,“大全”有着不同的别名,在真理领域作“整全真理”或“真本身”,有时又作“超越存在”或者“超越”,这是雅氏哲学本身的述说方式及中文翻译所造成的。
[1]卡尔·雅斯贝斯.生存哲学[M].王玖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王玖兴.雅斯贝尔斯[M]//王玖兴.王玖兴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3]Karl Jaspers.Reason and Existenz—Five Lectures by Jaspers[M].translated byWilliam Earle,New York:Noonday Press,1955.
[4]卡尔·雅斯贝尔斯.密码的本质[G].韩水法,译//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卡尔·雅斯贝尔斯.临界境况[G].张继武,译//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卡尔·雅斯贝尔斯.个别临界境况[G].张继武,译//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卡尔·雅斯贝斯.悲剧知识[G].吴裕康,译//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
[8]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M]//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David Nichols.Heidegger and Jaspers on the Tragic[J].Existen: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 Philosophy,Religion,Politics,and the Arts,2009,(4).
[10]孙秀昌.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1]卡尔·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M].王立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On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Jaspers'Tragic Theory
YANG Shui-yuan
(Departmentof Chines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
Jaspers'tragic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Jaspers ha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human's tragedy in“Limit-situations”.At the same time he illustrates the inherent association between tragedy and“Existence”,“Cipher”,“Truth”.He believes that tragedy is the basic background of existence,born in the tragic hero who failed in pursuing the truth,So he believes that the art of tragedy is the important“Cipher”to comprehend“the Encompassing”.According to integrating Aristotle's text interpretation with Nietzsche's 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Jaspers'tragic theory has a unique theoretical character.
Jaspers;tragic theory;Existence;Truth;Cipher
B086
A
1671-9743(2015)02-0069-05
2015-01-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论与“去黑格尔化”研究”(13BZW00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萨义德批评理论研究及其中国化应用”(GD14CZW01)。
杨水远,1986年生,男,湖南新化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