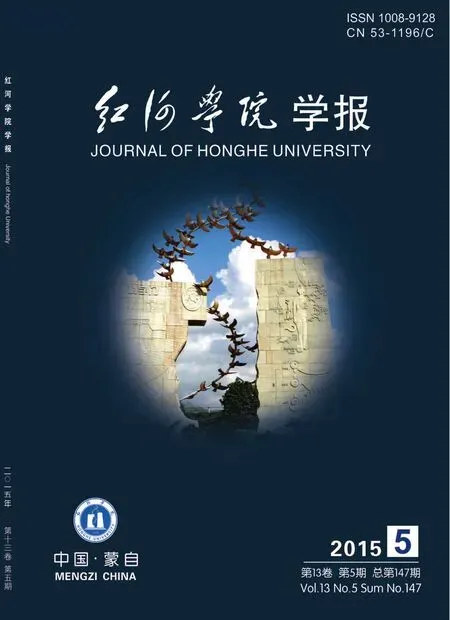以阿盖公主的诗歌解读“孔雀胆”传说
胡静
(西安理工大学,西安710127)
以阿盖公主的诗歌解读“孔雀胆”传说
胡静
(西安理工大学,西安710127)
“孔雀胆”传说是发生在元末明初时期云南的一段爱情悲剧,传说是依托“孔雀胆”事件而来。关于这段历史,正史中没有完整的叙述,所以经过历代演绎,有诸多异文。正史和异文中都有阿盖公主两首诗歌的记载,这两首诗歌也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一个参照。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以此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是研究“孔雀胆”事件,都绕不开阿盖公主的诗歌。文章通过这两首诗歌,用“以诗证史”、“史诗互证”的研究方法读解那段历史。
以诗证史;“孔雀胆”;元代;云南省
正史和异文中记载,“孔雀胆”事件后共有十首诗歌和一首词①流传于世,而这些诗词只有阿盖公主的《金指环歌》和《愁愤诗》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所有的史书中,其他诗词时有时无,而且会有多个版本。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以此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是研究“孔雀胆”事件,都绕不开阿盖公主的这两首诗歌,因此我们用“以诗证史”、“史诗互证”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两首诗歌来了解那段历史。
一 “孔雀胆”传说和后世演绎
传说中的“孔雀胆”是一种毒药,由昆虫虫体研磨而成,呈铜绿色,有剧毒。真实的孔雀胆类似大部分鸟类与哺乳类动物的胆部,具备平肝利胆、镇痉明目等功效;非但无毒,反而可以抑菌抗炎、清热解毒。
“孔雀胆”传说是流传于云南民间的一段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阿盖公主和大理总管段功,所以此传说又被叫作“段功与阿盖”传说。故事发生在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明玉珍进攻云南,云南梁王②与行中书省官员不是对手,只能望风而逃,大理总管段功出兵相救,赶走明军。梁王为表感谢和拉拢段功,先是奏拜段功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后将女儿阿盖许配给段功。婚后,段功留在昆明竭力效忠梁王,因权高位重,惹来杀身之祸。梁王听信谗言,认为段功有谋反之心,于是,他命阿盖用孔雀胆毒杀段功,阿盖不从,让段功逃回大理,段功不听,并执意向梁王表明自己没有贰心,最终还是被杀害。阿盖悲痛不已,服孔雀胆自杀。这是“孔雀胆”传说的始末,在当地影响深远,广为流传。
“孔雀胆”传说是根据历史事件而来,有史为据。记载于明初《元史·顺帝纪》、明阮元声的《南诏野史》(原书散失,现有明代杨慎整理本和清代王崧校理本)、明杨慎《滇载记》、明蔣彬《南诏源流纪要》、明刘毅安《脉望斋诗草》、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明史·巴匝拉瓦尔密传》、《新元史·梁王传》及《新元史·明玉珍传》等史籍篇章中。在专门的蒙古史书及云南地方志等书中也有这个事件或详或略的记载。在正史记载中,以《元史》、《明史》、《新元史》最权威,史籍中的记载是通过人物传记,而不是完整叙事形式的记录,所以完整的情节是通过相关传记拼合而成。“孔雀胆”事件距今已有700多年,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异文,但其传说主体是不变的。在异文中,以《南诏野史》的记载最为完整,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其文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其中有别于正史中的情节,有待于进一步地考辨。
“孔雀胆”事件发生在元末明初的云南,这里政治环境险恶,政权关系复杂。云南在西汉的时候称为滇国,唐朝时改叫南诏,宋朝的时候又叫大理。元朝开始设云南行省,一方面分封蒙古贵族为梁王,统治这里;另一方面设置大理都元帅府,把大理世家段家提任为总管。自大理国灭亡以后,大理虽设段姓总管,但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大理的控制,另派蒙古官员监察。这样在云南就存在着三股势力,直属于中央管辖的蒙古贵族,游离于中央的云南梁王和一直想分化出去的大理段氏家族。只要存在权力的分化,就存在着权力的此消彼长,也就存在着斗争。元朝统治云南之初,“采用分化、招抚、任用归附土官为之长的新制度”[1]13,忽必烈征云南和兀良合台镇云南时,主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但同时,
也没有忘记“分化、招抚”的办法,如忽必烈征大理时,就曾事先“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谕大理。”[2]59至于任用归附之人,亦不乏其人,以大理国的后人信苴日最有名。《元史·信苴日传》六百余字,无不描述了其归附元之后如何建功立业,如何受奖赏,“……乙卯,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十八年,信苴日喻其子阿庆复入觐,帝嘉其忠勤,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留阿庆宿卫东宫,及陛辞,复拜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2]910可见,元朝在统治云南之初,对原“大理”的统治者“分化、招抚”,拜官封爵,很快确立了对云南的统治,但这也为元末云南权力的争斗埋下了隐患。我们也就理解了段功虽为梁王的女婿,但还是免不了政治阴谋。当段氏势力由滇西发展到滇东,足以威胁梁王的统治地位时,梁王只有密谋杀死段功才能稳固自己的权位。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必当在一个时候以某种方式爆发,“孔雀胆”事件只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
从故事发生到今天已有700多年,“孔雀胆”传说在云南家喻户晓,并为古今文人所记,成为文人创作的素材。明清以来的诗人写诗作文歌颂阿盖公主、段功,表达惋惜、敬仰之情,如明末楚雄诗人刘联声的《阿盖妃》;清乾隆年间钱南园的《阿姑祠》;清乾隆时李作舟的《阿盖庙》;还有赵文哲、陈文述、宋嘉俊等人以《阿盖庙》为题写的叙事长诗等。近代以来,文人又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1931年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阿盖公主》(收录于《将军底头》),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塑造了阿盖、梁王、段功等生动的人物形象,探究了阿盖和段功爱情悲剧的成因,使观众从社会的、伦理的、人性的、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历史故事。1942年,郭沫若以阿盖公主为题材创作出历史悲剧《孔雀胆》,随后被席明真改编成川剧搬上舞台,一时间“孔雀胆”传说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此时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创作的需要,作者改编了某些情节,虽然有违历史事实,但作者坚持“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3]501的创作原则,他在《孔雀胆》后有7篇附录,详细说明创作过程、史实考证、创作心得等。《孔雀胆》是以阿盖与车力特穆儿的矛盾展开情节,表现主题的。就像郭沫若所说的,他是“借史事的影子来,表现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4]23二十世纪90年代,赵建华的剧作《阿盖公主》,后被苏保昆、李琼芬导演为白剧搬上舞台,本剧立足于白族文化,创作反映白族历史与现代生活中的典型形象。此剧离郭沫若创作的话剧有40年时间,题材虽然相同,但剧作者以“蒙古姑娘阿盖是我们白族的好儿媳”为情感主线,用白族的戏剧形式,重新讲述这一历史故事,最后将段功之死引申到“民族一定要团结”的高度上。2010年当代作家吴蔚以此题材创作出长篇故事小说《孔雀胆》一书等,也是以这一传说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可见,关于这一题材改编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很多。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对同一历史题材做出新的解释,演绎改编成具有各个时代审美意趣和思想意识的作品。可见,“孔雀胆”传说是蒙古族、白族和汉族文化交流的结晶,作为一份文学遗产,它留给后人太多创作灵感和内心触动。
二 以阿盖公主的两首诗歌解读“孔雀胆”传说
阿盖,蒙古族,生卒年不详,元后期云南行省梁王之女,大理总管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段功之妻。“阿盖”蒙古语称“押不芦花”③。《新元史·阿盖公主》上记载:
“梁王女阿盖公主,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袭为蒙化知府。明玉珍自蜀分兵攻云南,梁王及云南行省官皆走。功独进兵败之。梁王深德功,以公主妻之,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功自是不肯归。或语之梁王曰:‘段平章心叵测,盍早图之。’梁王密诏公主谓曰:‘功志不灭我不巳,今付汝孔雀胆,乘便可毒之。’主潸然,私与功曰:‘我父忌阿奴,愿与阿奴西归。’因出毒示之。功不听。明日邀功东寺演梵,阴令番将格杀之。公主闻变,大哭欲自尽。王防卫甚密。因悲愤作诗云云……竟死。”[7]466
史书中关于阿盖公主的记载不多,我们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大概勾勒出她的形象:美丽善良、能歌善舞、果敢决绝、忠贞爱情。她也被认为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存诗两首。这两首诗歌创作于不同的时期,《金指环歌》创作于父亲的谢功宴上,《悲愤诗》(又称《愁愤诗》)创作于段功被父亲杀害之后。不同时期,不同的际遇,有不同的心态,抒发了不同的情感。下面具体分析之。
首先,读解阿盖公主的《金指环歌》,感受阿段二人的“旷世绝恋”。这首诗歌创作于庆功宴上的:“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灵辉彻南北东西,皓皓中天光映月。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8]363这是阿盖为段功做的一首诗,这首诗一方面盛赞段功的英武及对梁王的忠心,另一方面表露了阿盖对段功的倾慕、对美满婚姻的期望。她在诗歌中讴歌段功为“将星挺生扶宝阙”,“豪杰长作擎天手”,对段功的欣赏和爱慕溢于言表。阿盖把和段功的结合,写成“犹唐贵主结配偶”,以唐代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自喻,可以看出她博大的胸怀及宽广的视野。
阿盖以“父母之命”嫁给有房室的段功,二人
非常恩爱,夫唱妇随,但毕竟是一场政治婚姻,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到:“在封建社会里,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婚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9]74虽然是一场政治联姻,但阿盖忠贞于自己的丈夫,并以死抗争梁王的决断。蒙古族女性身上的那股刚毅精神在阿盖身上体现出来,蒙古族女性具有积极主动的主体意识,这与她们的生活习性有关。蒙古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开放、流动的,蒙古族女性在这样的游牧生活中,具备了主体意识萌发与建立的宽松的氛围。《蒙古秘史》中就记载有阿兰豁阿、诃额仑、孛尔贴、也隧四位女性,通过她们的事迹,我们了解到蒙古族女性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她们在政治舞台上行使了决策、指挥、参与的权力,在男性独领天下的古代蒙古社会,蒙古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弘扬。并且在以体能衡量人的生存状态的时代,蒙古族女性以主体的姿态去面对外部世界,凸现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蒙古族女性更加意识到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并激发起自身蕴藏的更大的主体能量。”[10]218相比较她们,阿盖身上多了中原女子温柔的一面,因为自幼随父阔别大草原来到云南,汉人“男尊女卑”的观念侵染了她的心灵,她逐渐被“汉化”,如郭沫若所说:“照阿盖故事看来,阿盖这位女性是充分汉化了的,她能有那样贞烈,并且能够做诗,便是绝好的证明。”[5]390所谓汉化,就是他们性格中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阿盖和段功都不是汉族,但是却恪守着合理的传统道德和伦理原则。阿盖弱小的身躯终究没有敌过父王的铁骑,终成封建社会“和亲”的牺牲品,她和段功的爱情只不过是男权社会中的祭祀品。
其次,欣赏阿盖公主的第二首诗歌《愁愤诗》,领教她不凡的“语言混搭”技巧。梁王阴谋杀害段功之后,阿盖公主非常悲愤,写了这首诗歌表示抗议和哀悼,而后殉情。这首诗的争议比较大,在《滇载记》和《南诏野史》两书中,所记载的内容略有不同,注释也有差异。《滇载记》所载之文为: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路里彩(原注,以下同:棉被名也)。吐噜吐噜段阿奴(吐噜,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云片波潾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押不芦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独坐细思量(肉屏,骆驼背也),西山铁力霜潇洒(铁力,松林也)。”[11]756
《南诏野史》所载之文为: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黄嵩历乱苍山秋,误我一生踏里彩(华语棉被也)。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潾不见人,押不芦花(华语起死灵草也)颜色改。肉屏(华语骆驼也)独坐细思量,西山铁力(华语松林也)风潇洒。”[8]363
两文的主要差别在第五句;第六句第五字一作“路”,一作“踏”;末句第五字一作“霜”,一作“风”。方国瑜先生整理《云南史料丛刊》时,将上面几处不同考证为:第五句为“黄嵩历乱苍山秋”,“误我一生踏里彩”,“西山铁力霜潇洒”。虽有词语上的不同,但其表达的意思和主题思想都相同。笔者认为,两书中的不一致的记载,很可能是两书在流传过程中,是那些对白语和白族文化并无多少了解的人所为。因为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有时甚至歪曲、捏造历史,所以历史在流传中总会多少变异。诗歌的前两句交代了阿盖的身世,叙述她老家在雁门以北,后随父来到昆明滇海,嫁于段功。诗中“闲云”活用了宋玉《高唐赋序》的典故,指阿盖自己,“闲云到滇海”意指与段功结为夫妻。三四句写得比较含蓄,“心悬明月”意指段功对梁王忠心耿耿,但梁王依旧怀疑段功有“吞金马,嚥碧鸡”之心。五六句写段功轻信梁王,终致遭害。七八句叹息政治斗争带来的屠戮。九十句阿盖忆起当初夫妻同游的地方,只有云片、波粼不见人。最后两句写作者的哀伤,独坐骆驼背上思量夫君,悲痛莫名。这首诗歌杂用几种民族语言,情切意真,形象鲜明,凄婉哀怨,感天动地。该诗在以后的700余年间广泛流传于西南广大地区,成为一首有名的爱情悲歌。
这首诗歌出现了“语言混搭”,诗中兼有汉语和“夷语”,这里“夷语”可能是蒙古语,也可能是白语。近代学者对这些“夷语”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有不同的见解,莫衷一是。1980年蒙古籍学者方龄贵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考证了阿盖公主的这首诗歌,用元明以来的字书证明诗中六个“夷语”(踏里彩、吐鲁、歹、押不芦、肉屏、铁立)是否是蒙古语,一一辨析,最终指出:“传世所谓阿盖公主诗中的几个‘夷语’,可说无一是蒙古语,此中或不无待发之复。姑设此说,以质诸世之究心大元史事及滇云掌故者。”[12]60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怀疑这首诗歌是否是阿盖公主所作,如学者王敬骝就指出:“此两书中所述的阿盖公主诗,并非阿盖本人所作,而是当地述蒙、段史事的白人‘讲史’者所作;此诗中用汉字写的‘夷语’,不是‘蒙古语’,而是白语。”[13]74他从考证这首诗歌最早出处的《滇载记》和《南诏野史》出发,分析它们的成书体裁,认为这两书更像是“讲史”。王敬骝以郭沫若的“按《野史》实系一种小说,其中事实多出虚构”[5]389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又拿王实甫的《西厢记》作比,“把段功、阿盖……等都认作诗人……。这就像我们根据元代大剧作家王实甫所写《西厢记》中的唱词,把剧中一些人物,包括和尚、强盗等都认作词人一
样,岂不叫人感到好笑?”[13]74笔者以为,这种揣测值得商榷,“孔雀胆”事件中出现的十余首诗词,不排除有些是后人添加或修改的,但不能否认当时蒙古族贵族和白族贵族的汉文化水平。在蒙古族文学史中,阿盖公主的汉文化造诣是被公认的。虽然一些白族文学史或文化史的著作中,也有对《滇载记》和《南诏野史》中所载史事的质疑,但是我们不能全然否定这两书的史学价值,也不能因此认定《愁愤诗》的作者是一些“讲史”人所作,目前还没有其它新材料佐证这一看法。本文依从大众之说,姑且认定这首诗歌的作者是阿盖公主。阿盖公主的成长环境,使她具备掌握多种民族语言的可能:其一,阿盖是蒙古族,母语是蒙古语,即使幼时随父来到云南,她也会说蒙古语,识蒙古文;其二,从《金指环歌》来看,阿盖公主可以用汉语创作诗歌,推测她汉语水平应该很高;其三,这是一首为悼念丈夫而写的挽歌,段功是大理白族人,阿盖嫁给他之后,他们用哪种语言进行交流,或许是通用汉语,或是蒙古语,或是白语,已无从考证,但语言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诗中六处“夷语”是哪种语言,方龄贵、王敬骝分别从蒙古语、白语的词汇发展演变出发,指出一二,研究比较专业,考证也比较详细,在此不赘述。笔者以为,不能单纯去从词汇、语法的角度考虑,也要考虑作者的人为因素。阿盖写这首诗歌是哀悼段功,表达自己对丈夫的思念,有可能在诗歌词汇的选择上会更倾向于白语。白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绝大多数使用汉字书写,元明时期曾使用过“焚文”(白文),即所谓“汉字白读”。所以,阿盖有可能用“汉字白读”的形式创作了这首诗歌。总之,阿盖公主在这首诗歌的创作中融入了多种民族语言,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她巧妙地将汉语的音韵美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铿锵美融合在一起,别具一番风味。从这种多民族语言混搭的现象中,可以看出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已经互相影响,这是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例证,这种交融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之间的矛盾。
总之,阿盖公主的这两首诗歌各具特色,是云南地方文学不可多得的佳作。我们不仅在《金指环》中感受了被阿盖和段功的“旷世绝恋”、欣赏了当时的人文自然景观④;而且学习了《愁愤诗》中“语言混搭”技巧。通过对阿盖公主两首诗歌的解读,用“以诗证史”和“史诗互证”的方法来挖掘诗歌和史事的契合点。从《金指环歌》的美好憧憬,到《愁愤诗》的无助呐喊,阿盖公主通过诗歌将自己复杂的心情和同样复杂的历史交相映照。
注释:
①这十一首诗词分别是:阿盖的《金指环歌》、《悲愤诗》,高蓬的《答梁王》,杨渊海的《劝段功诗》、《题壁》,高氏的《玉娇枝》,梁王巴匝剌瓦尔密的《奔威楚道中》,段功的《无题》,段宝的《答梁王借兵》以及段僧奴的《寄兄诗》。
②历史记载不是很确定,《云南史料丛刊》卷二记载是把匝拉瓦尔密,《明实录·洪武朝》记载的是孛罗。后来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多将梁王记作巴匝拉瓦尔密。
③意即能起死回生的美丽仙草。宋代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押不芦》有记载。
④诗歌中,“碧鸡”一词在元代就广泛使用,并且逐渐成为云南昆明的明信片。
[1]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2][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M]//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郭沫若.郭沫若剧作全集(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6]余秋雨.戏剧审美心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柯劭忞.新元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8][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连新.对古代蒙古族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地位之关系初探[J].前沿,2006(6).
[1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四[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2]方龄贵.阿盖公主诗中夷语非蒙古语说[J].思想战线,1980(4).
[13]王敬骝.《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诗考释[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5).
[责任编辑贺良林]
Interpreting the Legend of“Kongque dan”from the Prospective of Agay Princess
HU Jing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127,China)
“Kongque dan”legend was a love tragedy which occurred in Yunnan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the legend based on“Kongque dan”event.The official history has not a complete description about this history,so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exts after successive interpretation.The two poetries from Agay princess all appear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different text which become a reference about the special history.Regardless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in this theme,or study of“Kongque dan”event,we need to study Agay Princess poetry.Through these two poems,we use two methods to interpret the history,one is the“to prove history with poetry”,and the other is“history and poetry prove each other”.
proof the history through poetry;"Kongquedan"legend;Yuan Dynasty;Yunnan province
I206.2
A
1008-9128(2015)05-0097-04
2014-09-30
胡静(1984—),女,安徽宿州人,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