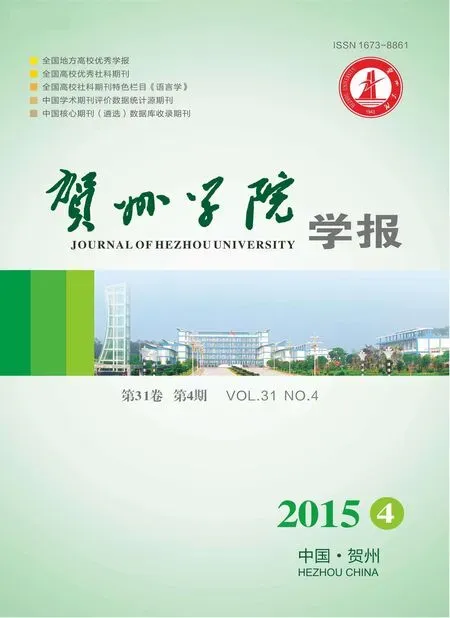《吉尔尕朗河两岸》散文文体认同探析
刘弟娥
(贺州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吉尔尕朗河两岸》散文文体认同探析
刘弟娥
(贺州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广西籍作家梁晓阳的大西北书写《吉尔尕朗河两岸》以散文文体面貌出现,既具有散文文体的特点,也体现了当代散文写作的新变;但对潜在读者定位的模糊。大西北的风情与思想者的探寻在某些方面并未能完美结合,使得此散文文本瑕瑜互现。
散文文体;思想者;潜在读者
一、源 起
梁晓阳的《吉尔尕朗河两岸》(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初版)于2014年再版,由初版的27万字增至30万字,命之为长篇散文。在这纯文学发展不景气的时节,写作散文,特别是写作长篇散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关于《吉尔尕朗河两岸》出版的艰辛,作者本人已多次讲述,在此不再赘述。该书初版业界知之不多,《吉尔尕朗河两岸》此书能被业界知晓并再版,得益于广西北流籍作家林白的推掖。在新浪微博上关注林白的粉丝当有记忆,认证名为“作家林白”并加V的新浪微博于2013年11月18日发表了一段文字,“未在主流杂志发表,亦无评论和推广,一本好书遇不上它的读者。痛心!《吉尔尕朗河两岸》,梁晓阳著。关于新疆的十年,关于伊犁。清澈、朴素、动人,富有生命感。谨荐。”①在近一年后,林白再发博文,“看来呼吁是有效的,祝贺《吉尔尕朗河两岸》再版。”②相信很多似笔者之类的林白微博粉丝通过她的第一条微博知晓了《吉尔尕朗河两岸》此书,并由此关注作者梁晓阳的微博,其后由此成为该书再版的最先一批读者。通过梁晓阳本人的新浪博客,笔者还了解到有浙江某高校的毕业生打算选择他的《吉尔尕朗河两岸》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研究对象[1]。实际上,此书的再版,推荐者的队伍已经比较豪华,如由林白与王克楠作序,评论家谢有顺、散文家祝勇等也有书面文字的介绍,并于同年被推荐角逐当年的“鲁迅文学奖”。
《吉尔尕朗河两岸》书名与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有点类似,自然也引得好奇网友的询问,“跟《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什么关系?”,关于此问题,梁晓阳声明,“额尔古纳河是长篇小说,吉尔尕朗河两岸是长篇散文,额是写东北,吉是写西北,额的作者是大作家,吉的作者是无名氏③。自此,对此书不熟悉的读者对该书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就是该书作为长篇散文,在纯文学不景气的当下,特别是作为非中心文体的散文,非名人的写作,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但是在读书界毫无反响,几有覆瓿之虞,幸得林白等人的力荐,从而再版。《吉尔尕朗河两岸》作为散文的文体性质一再被作者本人以及推荐者所强化,在这种强化的话语背景下,实际上是对散文文体的一种认同,令笔者感兴趣的是,这种强化的文体认同是否与散文的文体规范相一致?
众所知之,我国曾作为诗歌与散文大国,盛产文学。士人日常交往习惯用诗歌表达感情,经济文章则用散文,所谓高头讲章是也。发展至“五四”,一切传统被视为腐朽,传统的文学规范被鄙弃,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被视之为文学的正宗,散文居之为末流。尽管由于写作传统的惯性,“五四”前后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散文家,但延至20世纪,小说成为文学当然的主角,散文写作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因“文化散文”的出现而风行一时,流风余绪延至今天,但是,散文成为小众文体已为文界公认。
追溯现代白话散文的源头,其文体体例当是以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等第一代散文家开创的。虽然,作为文学创作者,很多时候强调文无定法,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也承认,文体规范“定法则无,大体须有”(王若虚语)。因此,当作者本人一再指认此文本为散文写作的时候,读者在其阅读的过程中当会一再在文本中寻找这种散文的文体认同。在此需要确认的是,作为前代散文写作者为散文确立了哪些文体规范?《吉尔尕朗河两岸》此文本在哪些方面与前代人的散文写作有着契合?
二、作为上帝的“我”与作为叙述者的“我”
关于鲁迅的写作,多有论者论及其作品中凸显的“看”与“被看”的视角[2]与其“改造国民性”的写作态度。在鲁迅的时代以及其后的时代,即有人指出这种悲天悯人俯瞰众生的写作为“散文笔法”④,作为叙述者的“我”以上帝的姿态存在于小说中,可能令人诟病,但是,在散文中,写作者作为绝对的上帝具有主动权,这种态度与视角,适合于写作者发抒感触,为读者指点迷津,有利于写作者的思想表达。
《吉尔尕朗河两岸》一书的作者梁晓阳,以散文写作作为自己的职志,自命为文学青年,因此,选择散文这种在当代文学界比较冷门的文体作为自己的特定写作文体,当与自己对文学的追求以及文体的认识有关,同时也有文学青年天生就有的殉道者的精神追求有关。以这样的写作信念,选择散文作为写作文本,以“我”作为写作的叙述者,更便于思想的表述。
梁晓阳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作为自己的写作范本,同时也期盼能将大西北的人文景观展示在读者眼前,在另一方面,也期盼能以思想者的姿态被读者所认同。因此,这一类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多以散文写作为多。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考察此文本,当有四个层面的写作:第一层面为大西北广袤大地的风景描写,如开篇的雾松;第二层面当为对大西北的民俗风情描绘,如对姑娘追这种活动的原生态展示,惋惜很多时候的商业化演出,其中重要的写作以人为活动中心;第三个层面为自己家庭生活的描写,外在的有岳母岳父一家艰难的“创业史”,内在的有我们小家庭的由南到北候鸟般的迁徙生活;第四层次,则为“我”的精神生活,亦为文本中最为作者所看重的写作。这是作为此散文文本的总体结构。
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塞外大西北是一个异样的存在,其浓郁的塞外风情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是值得书写的。文艺青年因为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从此与遥远的大西北结缘,在大西北生活的过程中,喜欢上了这里广袤的土地与淳朴的人情,遂着意将之形之笔墨。梁晓阳来自广西的某一城市,为当地的公职人员,从事秘书相关工作,但是,平时颇为厌倦这种捉刀人的工作,也厌倦这样的八股文字。吉尔尕朗河两岸景观,加乌拉尔牧场,无不给予“我”新鲜的人生感受,也涤荡“我”的心灵。在此,笔者感兴趣的是,对于这样的写作,读者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阅读方式来打开这本书:文学青年的异域采风还是思想者的孤独吟唱?是接受写作者上帝般的思想熏陶还是平面真实的风情叙述?
作者本来的意图,显然,希望此书能作为思想者孤独探索的文本存在于读者的阅读体验中。这一点在他的写作中也数次得以强调,这种写作态度不单纯体现在写作者面对异域风情的叙少论多的表达方式,更直接体现为一个思想者的孤独探求:即便是生活在心息相通的家人中,“我”也与家人的生活有着显明的距离,“我”习惯早起,更习惯独自阅读,这一点,虽然得到家人的体谅,但是,实际上,与家人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孤独的思考,也是“我”自身的一种追求,在诅咒自己曾经的文字工作是一种“掏空灵魂的工作”之时,“想到之前在南方工作的岁月,在经常利用周末和假日加班加点忙于活动忙于应酬中,我什么时候有过现在这样对辽远时间和空间的寂然凝思呢?真的没有过。现在,我在这里已经有幸成为了一位难得思考时空与众生、过去与将来的思想者。”[3]25对于自己这种两栖生活的矛盾心态,“我”并没有回避掩饰,“我也常常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矛盾,我爱这里的自然,我甚至愿意在较长的时间内和这片自然一起生活,渴望看到天空的颜色,听到野花开放的声音,甚至想把自己融为这片自然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想啜饮世俗甘醇的美酒,倾听都市舞蹈的律动,乘坐一辆现代气派的小汽车,酣睡在一张高级销魂的软榻上。”[6]66颇具有思想者的自剖精神。更为显明的是,作者在遥远的大西北,时常阅读的《瓦尔登湖》,数度的阅读,让“我”更迷恋自己在吉尔尕朗河生活的岁月。实际上,也的确有论者将该书与《瓦尔登湖》进行对照(如王克楠的《自然人文写作的探索文本》序二)。美国作家查尔斯·弗雷泽尔在《寒山》这部小说中描写了英曼这样一个人物,他冒着生命危险逃离战地医院,只为了“回到家后,在寒山上为自己建一个小木屋……远离尘嚣,没有人,只有从秋天的云中飞过的夜莺能听得见他的悲泣。生活在如此宁静的环境中,他将再也用不着听觉。”[4]275-276这样一个向往荒野,追求宁静的主人公,携带着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踏上了漫长的返乡之路,如果《旅行笔记》对于英曼有类似于“镇静剂”的作用,那么,《瓦尔登湖》对于梁晓阳来说,也差可类之,甚至,以自己的笔写出一部《瓦尔登湖》似的传世之作,也是梁晓阳本人的夙愿。
以此,《吉尔尕朗河两岸》自然不属于单纯的采风类地域风情的写作,尽管在文本中出现大量对少数民族生活与民俗的描写,即便是在热闹的场景背后,作者仍旧保有一颗冷静的心态,但是,超脱呢?却也未必。“我发觉大部分时光独处,实在是妙不可言。有人陪伴,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很快就会厌倦,曾经共处的快乐一去不复返。我从来没有发现比孤独更好的伴侣了。”[5]150享受孤独,甚至制造孤独,这一点阅读梭罗《瓦尔登湖》的作者当能感受得到。同时,以悲悯的姿态俯瞰众生,不带乡愿,有着智者的优越,也是这一类写作的独特之处。对于外在的景物,“‘那些无形之物’是能够激起我们的情感、关系到我们的幸福与满足、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4]1内心的精神体验与外界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与人对话,与自己对话,与心中的神灵对话,或者与一种无法企及的精神对话,在任何的场域中的行走,都是思想者的孤独之旅。
如作者所认同的《抵达之谜》也即如此。行文至此,尽管作者说,“我刚收到《抵达之迷(原文如此,应为谜——笔者注)》,非常喜欢,我没想到我这本《吉尔尕朗河两岸》风格有抵达之迷(同上)影子,可之前我一直没看过他的这本书。”⑤但是,作为读者,笔者对两书的阅读体验并非如此,《吉尔尕朗河两岸》更欣喜于异域风情的写作,没有让读者感受到思想者的力量,“我”作为行走者,叙述者,其姿态融入到风情叙述中,更类似于采风的写作,而非思想者的独吟。
三、潜在读者
作为散文文体,第一代散文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读者有着清醒的认知,如鲁迅,立意于醒世;周作人,精心于知识的串接;冰心与朱自清清新的风格,更适合“小读者”。读者群的定位,从语言方面规定了其风格,要求语言与潜在读者的阅读趣味相近,如鲁迅的文章针对青年激进者,所以其笔峻急;周作人的文章面向具有一定修养的知识分子,所以其文温雅;朱自清与冰心的读者群当为阅世未深的青年学子,所以其文清新雅洁。该书作者视之为精神导师的梭罗在写作《瓦尔登湖》是,则开章明义地指出,“我的文字更适合那些贫寒的学生阅读,至于其他读者,完全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我明白不可削足适履的道理,因为衣服只有穿在适合它的人身上,才能发挥好的作用。”[5]2以此,梭罗明确自己作品的读者群,也从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庸众所接受。
来自南方的文学青年梁晓阳,在大西北,显然也能感觉到梭罗般的孤独,明白自己的不被理解,“他们不责怪我们这些无病呻吟无事生非的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最大的宽容了。但是,我已经在这儿住居了许多岁月,也慢慢习惯了这些寂寞的日子,所以我也是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些草原上的人们的,我的心里有平静或者不平静的想法只有我知道,如今我默默地栖居在马场上,埋头敲打我的键盘,是因为我要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作为我的纪念。”[3]11显然,在作者的心目中,他所认为的潜在读者,并非这些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或新疆人。但是,在另一方面,尽管作者这样说,“我也不奢望这儿的人们对我有什么赞誉”[3]6,“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新疆的,也不是每一本写新疆的书都可以出版,哪里有太多的东西要把握,太多敏感的关系要区辨,写新疆,首要的是爱中国,爱新疆,爱新疆人,尤其对各族人要有真挚的爱情。所以,当30万字《吉尔尕朗河两岸》一版和再版后,我觉得自己不是自负,而是有些了不起了。”⑥这不单纯是作者所说的一种自负,乃是作者从内心深处,渴望自己所写作的对象,无论是哈萨克,还是新疆人,甚至是这一片土地,能够认同自己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又间接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同性阅读。
作者面对这一认同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作者希望自己的辛苦写作,对于这里的人们以至这块土地都能有所裨益;但是,在另一方面,作者显然明白,作为游牧民族,现在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所改变,聚族而居的生活也有利于他们接受相对稳定的文化教育,但是,其文化水平显然还不足以欣赏他的这一类写作,如他曾描写了一位当地的少女,“你(帕提曼)曾经是刚刚从校园里出来涉足社会的少女,到现在还热爱看那些《女报》《知音》类刊物,听图尔干大叔说,你也曾经发奋自学准备2004年的应考,可如今你已经是一位仅仅喜欢消遣阅读正在孜孜追求故事情节的牧区少妇。”[3]111在作者的价值判断中,“追求故事情节”的阅读自然是等而下之了,那么,这一类读者对于《吉尔尕朗河两岸》一书的观感也是可以想见的。正因为对故事情节的拒斥,《吉尔尕朗河两岸》选择了散文文体,叙民族风情与地域特色,议自己的心得感受,这是典型的散文写作。虽然世人以为宋人以议论为诗,陷第二流,尽管是一种偏见,但是也说明读者对文学作品中大量议论性写作的态度。章太炎曾问众学生文、学之别,周豫才对曰:“学以启人思,文以增人感”。正因为议论的出现,研究者往往将如《围城》这类好发议论,逞才使学的小说名之为“学者小说”,视之为第二流。这一点,在《吉尔尕朗河两岸》一书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作者以思想者好议论的面具出现,似乎其读者面似乎又是知识分子。对读者群期待的不确定性,导致《吉尔尕朗河两岸》行文的犹疑,既渴望成为孤独的精神探索者,也希望成为普罗大众的消费文本,这种乡愿的写作态度,不但导致其行文风格的不统一,也失去其可能的读者群。
四、结 语
白话散文发展至今日,已再难寻觅昔日的光华,随着第一代接受古典教育的白话散文作家先后离世,现代作者对散文写作已殊难坚持。《吉尔尕朗河两岸》的写作,其巨大的勇气以及可以预见的冷遇让读者与评论者都可能心生怜惜。但是,其并非不可以再议:让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散文,这不但是读者的修为,也同样需要作者本身对散文文体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注释:
①引自作家林白(林白)2013年11月18日16∶24发布的微博。
②引自作家林白(林白)2014年8月3日15∶28发布的微博。
③引自梁晓阳的马场(梁晓阳)2013年11月19日18∶24发布的微博。
④参见天用(朱湘)《〈呐喊〉桌话之六》、部元宝《小说模样的文章》、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杭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等文中的相关论述。
⑤引自梁晓阳的马场(梁晓阳)2014年9月2日17∶13发布的微博。
⑥引自梁晓阳的马场(梁晓阳)2014年7月29日17∶12发布的微博。
[1]梁晓阳.答浙江某大学毕业生的问卷[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4ef6bba10102w0ny.html.2015-05-17.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梁晓阳.吉尔尕朗河两岸[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4]程虹.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梭罗.瓦尔登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On the Prose Stylistic Features of Both banks of ER Gu lang river
LIU Di-e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f Hezhou University,Hezhou Guangxi 542899)
Liang Xiao-yang came from Guangxi.He created Both banks of ER Gu lang river,a book about The Great Northwest in China in the form of prose.This book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the traditional prose style and the contemporary style.At the same time,the book has some imperfect aspects:vague awareness of potential readers,the in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writing about The Great Northwest in China and the inquiry of thinkers.
prose style;thinker;potential readers
I226.9
A
1673—8861(2015)04—0087—04
[责任编辑]肖 晶
2015-10-23
刘弟娥(1977-),女,湖南衡南人,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贺州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HZUBS201306)、2014年广西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YB2014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