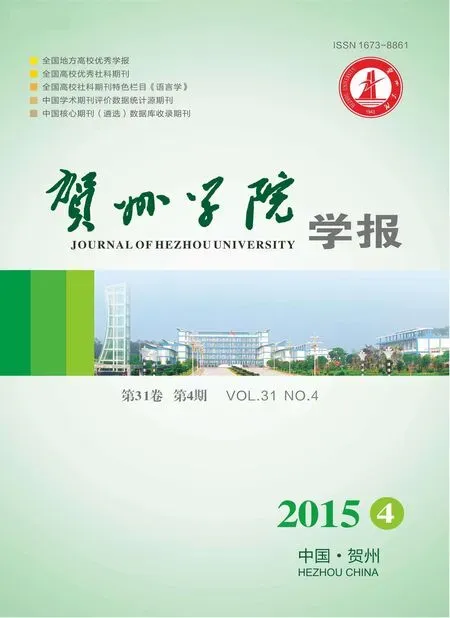廉州话性别范畴的表达方式友其文化内涵
王英远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廉州话性别范畴的表达方式友其文化内涵
王英远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性别作为人类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体现出各自不同的造词理念和文化色彩。廉州话性别范畴主要是以词汇的手段来表达。通过对性别语义范畴表达方式的描写分析,了解廉州话性别表达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廉州话;性别范畴;文化内涵
范畴(category)是指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形式和工具。[1]117可以说范畴是对人类认知对象的分类概括。人们对世间万事万物进行着不同层次的分类,有多少种分类就有多少个范畴。
性别作为人类认识自身、认知世界的重要范畴,几乎是所有语言都共有的范畴。同一范畴,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以词汇手段反映而有些以语法手段反映。不同语言对“性别”的认知不一样,印欧语系里的一些语言具有性的语法范畴。如:德语与俄语的名词和形容词就可分为中性、阴性和阳性三种。这里的“性”虽然只是一个语法上的概念,与生物学上的性别概念不能完全一致,但这一语法现象也反映了持这些语言的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知。当这种认知反映在语言里,并以语法的形式体现出来时就有了“性”的语法范畴。而汉藏语系语言里没有性的语法范畴,表达“性别”的范畴多是用词汇的手段来表现,体现了一种性别的语义范畴。
廉州话属于粤语钦廉片代表音,地处广西南部边境区域,包括北海、钦州、防城港和玉林部分地区。在反映性别这一范畴上,和大部分汉语方言一样,主要是以词汇的方式来承担,但也有不同于其他方言的特色之处及不一样的方言文化色彩。
一、性别范畴的表达方式
性别范畴里有雌雄、男女两性的区别,可以分为“阳性、阴性”次范畴。廉州话里主要以词汇的手段来表示性别的范畴。表“阳性”类的性别范畴。如:公、佬、牯、男、郎等词,这些词都是在[+阳性]这个语义范畴内下;表“阴性”类的性别范畴。如:母、婆、牸、乸、女、娘等词,这些词都具有[+阴性]的语义。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类范畴的表达方式及分布情况。
(一)“阳性”类性别范畴
廉州话里表“阳性”类性别语义范畴的特色词语主要有“公、佬、牯”等,虽然这些词可能在其他汉语方言也有,但在使用上存在不同。
1.“公”类词的使用
“公”在廉州话中广泛参与构词,使用语域较宽。
(1)构成表人称谓名词,表示男性
公祖(曾祖父)、啊公(祖父)、外公(外祖父)、叔公(父亲的弟弟)、舅公(母亲的兄弟)、新郎公(新郎)。
在廉州话中,“公”用在表亲属称谓上的情况较多,多位于亲属词后面,还含有[+年长]、[+尊敬]的语义,往往指比父母辈分高的人,而“叔公、舅公”是和父母平辈的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词里“公”不承担词的主要意义,只是一个意义虚化的词尾,“新郎公”这个词就是很好的佐证,所以“公”在廉州话里出现了语法化的现象。“公”用在亲属称谓上时,一般与“妈”“婆”相对,“比父母辈分高”的用“妈”配对。如“阿公—阿妈(奶奶)”;与“父母同辈”的用“婆”配对。如“舅公—妗婆”等。
(2)构成表神明或具有神力的事物,指代男性
祖公(家族的先贤)、社王公(社神)、天公(天神)、雷公(雷)、日头公(太阳)。
其中“祖公”是切切实实存在过的真实男性祖先,归到神明这一类,是因为在廉州地区,认为祖先已是具有神力的人物,祖先崇拜意识强烈。虽然“天公、雷公、日头公”没有实实在在的性别之分,但是人们主观上认为有性别的区分,具有象征性的性别意义。“雷公”,被拟作男性神灵,与普通话不同的是,没有“电母”与其配对,而是用“火蛇”或“闪电”表示。“日头公”指太阳,与月亮对举,所以月亮又被称为“月亮娘娘”。
(3)构成表动物的名词,表示雄性
“公”在表动物雄性名词时,可用于禽兽类动物,但会根据体型的大小有不同的区分。用在体型较小家禽类动物时,“公”后置。如:鸡公(公鸡);鸭公(公鸭)等,而体型较大的畜类动物,包括家养和野生的动物,是畜类雄性动物的总称,组词时“公”要前置。如:公狗、公猪、公蛇、公虎等。可见,“公”词缀在表示雄性动物范畴时,出现了“禽类兽类”“体型小体型大”的对立。
(4)构成表植物的名词,表示雄性
“公”表示雄性植物时,一般是不结果的。如:木瓜公(公木瓜树,即不结果的木瓜树)、公菠萝(不结果的木菠萝树)、公花(雄花)等。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也用“公”表示,但不表性别之意。如公绿豆(体型比一般绿豆小,质地很硬,很难煮熟的绿豆),但没有“母绿豆”与之对应。
2.“佬”类词的使用
“佬”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示男性范畴的性别词缀,一般指成年男性。“佬”放在某事物或某种工作名词的后面,表示从事该工作的成年男性。如:卖菜佬(卖菜的男人)、劏猪佬或猪肉佬(卖猪肉的男商贩)等。当放在某些形容词或名词后面时,有时候表示一种轻蔑的色彩。如:癫佬、白拈佬(小偷)、捞佬(当地称外地人)、麻疯佬等。“佬”和“婆”对举。如:癫佬—癫婆、贼佬—贼婆等。本来“佬”和“婆”构成“成年男人”和“成年女人”对立,但这两词缀所组成的词倾向于带有“贬义、轻视、嘲笑”的意味,而且倾向于泛指一切带有某些特征或从事某些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即不区分年龄,也可以指未成年的男性和女性。如:“官佬”(对当官的人的称呼,带有一种仇官情绪)、大肚婆、肥婆。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军佬”(军人)就不含贬义。
3.“牯”类词的使用
“牯”作性别词尾,用在动物名词后面,表雄性动物,而且一般是生性较猛、体型较大的家畜类动物才用“牯”,此外还带有[+做父本]的语义特征,仅限于“牛和马”的使用。这就和“公”表示一般雄性动物区别开来。如:牛牯(大公牛)、马牯(大公马)、水牯(公水牛)、沙牯(公黄牛)。如果要表示年幼的公牛时,一般在名词前加上“nε33小”,如:nε33水牯(小公水牛)、nε33沙牯(小公黄牛)。有“马牯”(公马)的说法,但因为马是不多见的,所以不强调用“牯”,也不见用在其他动物身上。有同音的“羖”,如“羊羖(没被阉割的公羊)。这两个词同音往往被混用。也有用“哥、郎”表示雄性动物的,一般专指“用来配种的公猪”如“猪哥、猪郎”。“公、牯、羖、哥、郎”等的使用也表示了不同动物或同一动物不同特征的对立。
(二)“阴性”类性别范畴
和“阳性”类性别范畴对举的是“阴性”类性别范畴。廉州话里表阴性类性别语义范畴的特色词语主要有“婆、乸、牸、项”等。
1.“婆”类词使用情况
在廉州话中“婆”也是构词能力较强的性别词。一般构成表人名词,指的是女性亲属称谓或某类女性。如:姨婆(母亲的妹妹)、阿婆(父亲的妹妹)、贼婆(女性小偷)、卖鞋婆(卖鞋的女商贩)、接生婆等。表亲属称谓时,还含有[+长辈]的语义,不含[+年长]的语义。如:“姨婆”“阿婆”可以是年轻的、甚至是年幼的,主要是辈分上的区分。而在表示某类女性时,即从事某一职业的女性或具有某一特征的女性,其中一般指年长的女性,与“妹”(年轻女性)相对。但也有例外,像“贼婆、白拈婆(女扒手)、大肚婆、肥婆”这些带有贬义意味的词语就不分年龄,因为与“婆”相对的“妹”没有相应的组词,所以“婆”的范围就扩大化,占据了“妹”的一部分。根据同场同模式或类推的语言机制,“婆”和“妹”作为一对在表女性范畴里的对立的义位,二者的引申应该是同步的。但是二者在使用频率和分布上存在不平衡性,所以也会出现这种不保持同步发展的现象。
2.“乸”类词使用情况
“乸”在廉州话里加在表人名词的后面,表示女性亲属称谓。如:老乸(母亲,引称)、姑乸(父亲的姐姐)、姨乸(母亲的姐姐)、亲家乸(亲家母)等;“乸”除了表女性亲属称谓时带有[+尊敬]之义,其他用来指女性时,一般在“乸”前加上动物名词,借用动物的习性来比喻女性性格或体态等,带有贬斥和不友好的意味。如:鸡乸(凶恶的女性)、肥猪乸(很胖的女性)等,而且一般用常见的“母鸡和母猪”来作比喻,态度极不友好。现代的许多壮侗语中,把母亲、岳母、姨母、婆婆等称作meh。现代粤语也把母、姨母等称作“乸”的,meh和乸音义相通,二者关系密切。
“乸”除了用来指人之外,还可以用来指已生育的雌性动物,位于动物名词的后面。如:猪乸(母猪)、鸡乸(母鸡)、鸭乸(母鸭)、牛乸(母牛)、老虎乸(母老虎)、蛇乸(母蛇)、老鼠乸(母老鼠)、雀儿乸(小鸟妈妈)等,可见“乸”可以指一切已经生育了的家养禽类、畜类或野生类动物,构词方式相对开放,相应的其构词能力也比较强。
除了“乸”可以表示雌性类动物以外,“母”“牸”“项”等也是用来表示雌性动物的。但它们的构词方式和语义存在一定的差异。“母”是一般雌性动物的总称,位于动物名词的前面。如“母鸡”。“牸”跟“牯”形成对称,专门用来指未生育的雌性动物“牛”,置于动物名词的后面。如:水牸(水牛)、沙牸(沙牛)。但没有“牛牸”的说法。“项”是专门用来指处于初成熟阶段的雌性家禽、家畜范畴,和“乸”相对。尤其是指“鸡、鸭”和“猪、牛”。如:项鸡、项鸭、项猪、项牛等。语序上和广州话的“鸡项”相反,范围上也比广州话的要大,广州话里“项”不指“家畜”类。可见,“乸”“母”“牸”“项”等在表雌性动物这一范畴里存在对立与分工。
从以上对阴性和阳性类性别语义范畴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表示雄性动物性别范畴的形式比较多,词语的位置不一。例如:公猪、鸡公、雄(雄鸡)、猪哥猪郎(配种的猪)、水牯等。表示雌性动物的用法就比较一致,无论禽畜、家养还是野生动物,都可以用“乸”来表示“已生育的动物”,而一般的雌性动物直接用“母”前置表示即可,如“母猫”。相对“婆”和“乸”来说,“母”和“女”是较书面的用语,属于文读音。同样,相对“公”和“佬”来说,“男”也是较书面的用语,属于文读音。一般“男、女”这两个词出现在一些较新兴的词中,如:女男老师、女男医生、女男歌手等。
还有一些词不属于性别语义范畴,但在使用上呈现了不一样的方言色彩。这些词含有性别语素但不表示性别概念,如:鹰婆(老鹰)、虾公(虾)、母虱(虱子)、石牯(石磨)、公瓦(覆盖在瓦槽上面的瓦片)、母瓦(形成瓦槽的瓦片)、鼻公(鼻子)、公绿豆等。这些词在某些特征上与“公、母”类特征相似引申而来。如:“虾公”指的是虾中个头比较大的,头部往往长有钳,常用钳咬人,这个特征显示了[+力量大][+个头大]的意思。而“公绿豆”虽然是绿豆中的个体较小的,但却是质地较硬,不易煮烂的那种,显示了[+强硬]的意味,而“鼻公”有学者认为是由形似男性的生殖器引申而来的,但在对性不开放的封建时代,这个引申或许太过于超前,不太可能。同其他词观察比对,我们发现,鼻子是人脸上最突出的一个部位,而且位置正中,这个位置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就是“主位”,“公”的说法正好显示了男权主义的权威。“公瓦”是指覆盖在瓦槽上面的瓦片,相对母瓦来说,能接收到更多的阳光,而“母瓦”指的是做瓦槽的瓦片,除了接收的阳光较“公瓦”少以外,还要作为雨水的引流之处,这在传统文化上就属于阴性较强的一面。传统上认为,阳性代表的是刚强、强劲有力的意思,可见这几个词的特点跟“公”或“阳性”的语义特征很相似。“母虱”因其繁殖能力很强,联系到母性的生殖能力,所以也由其引申而来。可见这些词的引申跟传统文化不无关系。
二、性别范畴体现的文化内涵
从前文对阳性和阴性性别范畴表达方式、使用情况的描写分析,我们发现,在廉州话中表阳性和阴性的性别范畴大体上形成对称,但也有一些不对称的现象。如:表神灵或具有神力事物的称谓和对人的称谓中表尊敬义的则是“阳性”类词的使用较多,“阴性”类词使用较少,而且阴性的“乸”在用于称呼人时(亲属称谓除外),借助动物的特性蔑称女性,几乎不带尊敬义而是含有嘲讽、不友好的意味。这些语言现象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的。
语言是人类思维表达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廉州话是粤语文化的特有的形式载体,要理解上述的语言现象还需从文化层面去解读。
(一)性别二元对立观念在语言中的反映
客观世界里有生命的物体存在两性繁殖的现象。生命的产生与繁衍都离不开两性繁殖。有两性繁殖就会存在两性的二元对立现象,如人有男女的二元对立,动物、植物有雌雄的二元对立,这些现象在多数语言里都有反映。中国古代的阴阳观也包括性别的二元对立。古代的阴阳观,一直存留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阴阳观起于何时,或许早在人类认识到男女有别就已经存在了。最早在《易经》里就把世间万事万物,不管它们有生命与否一律都被归入阴、阳两大范畴。比如,火为阳,水为阴;天为阳,地位阴;日为阳,月为阴……这种阴阳观的对立体现在廉州话性别范畴里就是“阴性和阳性”的二元对立。在廉州话里,性别二元对立的观念由有生命的人和动物,推及到无生命的物体,体现了类推的思维方式。将本不存在性别的物体也赋予其象征性的性别内涵,如:公瓦和母瓦、公橹和母橹(学名叫橹罟叶,当地用来包粽子,包粽子时要把叶子上的刺去掉。公橹的叶子比较小,质地比较脆、硬,母橹的叶子较阔大,质地软,一般包粽子用母橹)。这种性别的二元对立观念深深根植于当地人的思想中,把世界看成是一分为二的,并在性别词汇中体现出来。由类推思维的作用,这些词汇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说明了性别作为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范畴。
(二)男性地位显赫,女性地位受到限制
在廉州地区,男权中心主义比较明显。儒家思想里“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成为廉州地区根深蒂固的理念。男性在家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女性往往受到限制,属于从属的地位。反映在性别词汇。如:祖公(家族的先贤,是整个家族里的最先的男主人,辈分很高,可以上溯至爷爷的父亲的父亲),祖公的妻子称为“老祖”。祖公所在处称为“祖公屋”,就相当于祠堂,旧时村里建房子不可高过祖公屋的。而“老祖”的房子是一座小小的屋子,只能在“祖公屋”的左边。每逢节日祭祀活动只能先祖公后老祖,甚至有些时候可以不祭拜老祖。“祖公屋”的建立和拜祭习俗显示了男权的重要地位,宗主的权威。即使“老祖”在宗族繁衍后代中也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女性的地位不可改变的属于从属地位。“公”获得了显赫的社会地位,并承担了具有神秘力量的神灵角色。如“雷公、社王公、拦门公、土地公”等神灵。而表女性的神灵则比较少,而且祭拜活动往往都是由男人来主持,女人只是帮忙打理、备餐等。在家族里,男主人的地位往往比女主人高,家里的财产也是传男不传女。
(三)巫风迷信影响下的性别观在语言中的反映
北海廉州地区很多风俗习惯都与巫风迷信有关,据梁鸿勋《北海杂录》载:“迷信神权,中国通病,而北海土人迷信颇深。埠上有三婆、三王、文武帝、龙王、华光、普度震宫等庙,外沙有龙母庙。”[2]可以说北海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红白喜丧之事都离不开“神明”,连生病也请神来看,所以在农村地区有很多化身为宣称“能与神鬼沟通”的土巫。一般是上了年纪的男女从事该行业,男的称为“问花公”,女的称为“问花婆”。至此,北海也有“饿死医生,饱死巫人”之说。可见巫风迷信影响深远,性别亲属称谓中存在着的一些偏称现象,比如把自己的父亲称作“阿哥(大哥)”或“阿伯”,把母亲称作“阿嫂(大嫂)”等。这是由于听信了土巫说孩子与父母命里相克,要避免相克的灾难,就要避讳父母的称谓,而改称其他造成的。这种观念深受巫风迷信的影响,在当地社会大量存在。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性别作为一种重要认知,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粤语廉州语性别范畴的表达主要采用词汇的方式,分为阴性和阳性性别范畴。廉州话里对性别的区分并不是随意的,既有阴性和阳性的对立,也人和动物、植物等非人范畴的对应。这既与廉州话的语言便用特点有关,也与廉州地区社会文化背景、人文风俗习惯紧密相连。
[1]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梁鸿勋.北海杂录[M].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1905.
The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ender Category in Lianzhou Dialect
WANG Ying-y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Guangxi 530006)
Gender is an important cognitive way for human being recognizing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Each language has a its own expressive way which reflects its unique idea of word creation and its cultural pattern.gender category in Lianzhou dialect mainly embodies in vocabulary expression.By analyzing expression and description of gender semantic category,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ender expression in Lianzhou dialect
Lianzhou dialect;gender category;cultural connotation
H218
A
1673—8861(2015)04—0059—04
[责任编辑]肖 晶
2015-08-30
王英远(1990-),女,广西北海人,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壮侗语汉语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