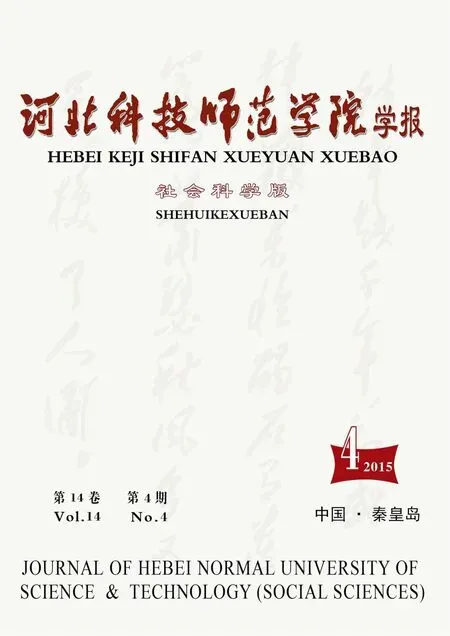《笑忘录》中的隐喻与政治书写
王宝迪
(山东大学(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笑忘录》中的隐喻与政治书写
王宝迪
(山东大学(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有丰富的隐喻,除了传统写作中建立在单个意象上的隐喻,米兰·昆德拉更是追求一种建构于小说内容与篇章结构间的整体性隐喻,这种隐喻手法的使用为阐述小说主题构造出一个“隐喻的森林”。以《笑忘录》为例,分析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对隐喻手法的使用,在此基础上讨论隐喻手法与政治书写的关系,作为一种认识的可能,理解作者在政治情节的设置之外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
《笑忘录》;隐喻;政治书写;存在
法籍捷裔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且在小说艺术形式上具有革新性。复调艺术、音乐结构、幽默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他的作品所具有的隐喻性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无论是在小说理论方面还是在小说创作方面,都能发现米兰·昆德拉对隐喻的重视,隐喻是昆德拉的小说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充满诗性智慧的叙述方式,对隐喻的使用体现着他的生存智慧和人生态度。
一、隐喻——米兰·昆德拉笔下的政治书写
(一)隐喻
隐喻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隐喻研究初期,它仅仅被看作是一种修辞现象。随着人类语言、思维和认知的发展,隐喻也逐渐从最为传统的修辞学概念发展为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出现在人们每时每刻的交流与思考中,语言因其所具有的隐喻功能使其在话语使用中创造出超越于语言的内容,并且使人类在思维认知过程中思考那超越于思维的存在。
1.隐喻的理解模式
在对隐喻意义的辨认中,存在着两种较为典型的理解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理解模式,即听话者(或读者)对隐喻产生的语境非常熟悉,听话者依据对说话者本人以及话语内容的了解,能够判断出该隐喻将要表达的大致含义。笔者对于《笑忘录》中的隐喻使用的分析主要运用这种模式。另一种理解模式是听话者(或读者)对隐喻使用的语境并不熟悉,对说话者本人和话语内容的了解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话语内容的理解主要依靠对实际话语中所具有的隐喻性信息的解读,这种隐喻理解过程被称为是“自下而上”的模式[1]193-194。
2.对隐喻的识别
当今学界存在着两种隐喻识别的方法。一种是通过对话语中出现的比较明确的隐喻信号进行识别,这类隐喻信号主要有元语言信号、领域转移信号或话题转移标志、明喻的直接使用等;另一种识别方式则需要分析话语使用中言语变异的性质。即从逻辑认知的角度,分析话语使用过程中所构成的逻辑错误,对其中所传达出的隐喻信息进行识别。
3.对隐喻意义的判断
识别出话语中所用的隐喻现象后,就需要听话者(或读者)推断说话者运用隐喻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约翰·塞尔*隐喻研究学家,在《表达和意义》(Expression and Meaning)一文中关注了隐喻意义,认为隐喻研究的主要问题应该在于说话者的意义如何被听话者所理解和接受。从语用学角度提供了理解隐喻的有效方式。塞尔认为,一旦确认应该从隐喻角度来理解话语意义,那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何在正常表述下出现的S is P在实际理解中却表示S is R?(S代表本体,P代表喻体,R是相似点)塞尔通过系统研究总结出了通过P而获得R值的一些原则,笔者主要应用的原则有:
原则1:P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R。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R特征是P事物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主要特征。
原则2:P事物经常被说成或被认为是R,尽管说话者和听话者可能知道这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可能是文化渊源使然。
4.语境知识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
隐喻理解过程离不开听话者(或读者)对语境意义的考察。束定芳将理解隐喻的语境背景知识划分为三类:其一为“话语同显”,即听话者(或读者)在话语接受过程中,将上文中出现的话语作为理解这句话所需的语境背景知识;其二为“物理同显”,即听话者(或读者)从人的客观经历角度出发,结合说话者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事情对话语本意进行解读;其三为团体成员的身份,即特指从属于某一特定团体内的成员所普遍认同的信息。[1]209
笔者在解读《笑忘录》中的隐喻艺术时主要运用了以上理论。
(二)作品客观存在着的政治性
“政治”是研究米兰·昆德拉小说世界的两个入口之一[2]代序。米兰·昆德拉作为一个经历过政治同时又进行着政治性思考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对政治有着大量的表现和书写,他自己也曾说:“我喜欢时不时地直接介入,作为作者,作为我自己。”[3]100这或许与米兰·昆德拉自身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有关。
结合对昆德拉人生经历的基本了解可知,因为昆德拉本人真真切切地经历了政治,并且在政治的帷幕之后展开深邃的人生思考,所以在他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浓郁的“政治底色”。政治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除了在小说中直接或间接地呈现相关的历史事件外,昆德拉更是运用隐喻的方式,从对小说内容与结构的深层建构中展开对政治问题的书写,并在书写中思考人的存在问题。
二、“隐喻的森林”*论文用此词揭示《笑忘录》中隐喻用法的多样化以形成一种立体的隐喻效果。——建构立体的隐喻世界
隐喻的智慧闪现在《笑忘录》的字里行间,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笑忘录》的主题,笔者选择从统括全书七部分内容于一的文化学隐喻入手,结合作品在章节设置上的对位,分析隐喻在《笑忘录》中的独特使用。
(一)意象隐喻——七部分的章节设置
1.《笑忘录》对七个部分的安排
《笑忘录》小说共分为七个部分,七部分内容在情节上并不具有连贯性。从传统的小说写作上来看,作品更像是“系列小说”,而非长篇。正如克里斯蒂安·萨尔蒙在与米兰·昆德拉就小说结构艺术进行谈话时讲到,“《笑忘录》由七个部分组成。如果您不是那样简约地去写,您可以写出七部不同的长篇小说。”[3]90
的确,小说七个部分之间在情节上没有了传统小说记叙上的连贯和情节统一。小说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同名“失落的信”,第二部分名为“妈妈”,第三部分和第六部分同名为“天使们”,第五部分名为“力脱思特”,第七部分名为“边界”。在七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之下,米兰·昆德拉又将各个部分分成若干章节,并用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记,在各个章节内书写并不连贯的内容。根据论文上一部分对隐喻理论的分析,在此主要按照“自上而下”的思维模式对构成小说整体性隐喻的各个独立性隐喻进行简单梳理。
2.对七个部分内关键隐喻的识别
根据对于隐喻的理解,只要在一定的语境中,用某一类事物来谈论另一类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从而使所用语言在字面意义上与语境发生了某种冲突就构成了隐喻。结合隐喻识别的具体理论,将《笑忘录》中七个部分内所涉及到的关键性隐喻列举如下:
第一部分名为“失落的信”。一个较为连贯的情节是米雷克寻找他20多年前的情人要回他在青年时代为她所写的情书,颇具隐喻意味的一句话:“我说,你怎么能跟这么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上床?”[4]19
疑问句突出“奇丑无比”这一信息,在语境内造成一种认识上的反差,促使我们对文本进行深入阅读和思考,为何米雷克会在青年时代找这样一个形象令周围人都感到诧异的情人?根据小说内容得知,米雷克很早就开始追逐自己“先前的事业”,而他的情人则是一直对“夜莺歌唱的花园”忠贞不渝的人。同时,他的情人是最近这段时间内、兴高采烈地欢迎俄国坦克到来的全国百分之二的人之一。这样,就将米雷克对于情人的追求与他“先前”所热爱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这个女人、这个事业也即他对捷克共产党的归属。
第二部分名为“妈妈”。具有超验感的一句话为,“实际上妈妈是对的:‘坦克是易朽的,而梨子是永恒的。’”[4]49
按照第二种隐喻识别的方式,用“易朽”修饰“坦克”,“永恒”修饰“梨子”,这种表述方式在逻辑上明显构成了一种语义及语用层面上的冲突。“坦克”是固体的、坚硬的,却用修饰容易腐败、变质的“易朽”来形容;而“梨子”是容易腐烂、变质的,却用代表长久的“永恒”修饰,其中明显存在着的认知冲突促使我们从隐喻角度对作者的说话意图进行猜测和判断。
第三部分名为“天使们”。关键词有“犀牛”、“两种笑”、“圆圈舞”。
“犀牛”来自于欧仁·尤奈斯库的一部剧作,作者讲到剧作主旨是剧中的人物为了趋同而纷纷变身为犀牛。那么,作为当时“被排斥”的米兰·昆德拉,作为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信念而选择从众“变身”的人,他只能用离开的方式远离这个他已格格不入的环境。小说在这里用一部剧作所阐发的意义来概括个人的类似经历,这是从领域信号和话题标志的转移方面识别出的隐喻。
“两种笑”,即天使的笑和魔鬼的笑。考察发出“笑”这个动作的主体就能感受到其与日常逻辑上的不一致。首先,“天使”和“魔鬼”在现实生活中本就是不存在的。其次,既然发出“笑”这个动作的主体都不存在,那么又怎么能够实施这种“笑”的行为。而小说不仅讲到了两个主体所发出的“笑”,并且对这两种“笑”的来历做了细致的分析:魔鬼的笑在先,指向事物的荒谬;天使的笑在后,是仿效魔鬼的笑而发出的带有欺骗性和强制性的笑。这样,从语义和语用线索方面就识别出“两种笑”所存在的隐喻性。
“圆圈舞”是艺术类词汇。文中作者却在艺术之外,将“圆圈舞”描写为代表某个政治圈子的小集体,并将个人经历加入其中。“圆圈舞”这一中心词的意义从艺术领域转而修饰个人的政治遭遇,因而辨别出这一词汇的使用具有一种隐喻性。
第四部分名为“失落的信”。这部分内容主要讲述非法逃离了波西米亚的塔米娜在异乡为找回过去的记忆而努力,然而脑海中的记忆却在她的刻意寻找中愈加模糊的经历。
结合语境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依据“话语同显”的原则,可知塔米娜这个人物俨然就是那个身在异乡的作者的化身。因而,这一部分对于塔米娜对抗自然遗忘的描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相互映衬,作者借塔米娜的经历进行着自我书写,其间存在着一定的隐喻性。
第五部分名为“力脱思特”,介绍捷克词语——力脱思特(Litost)。“那么,什么是力脱思特呢?力脱思特是突然发现我们自身的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4]187
同样,根据“话语同显”和“物理同显”的隐喻理解原则,“力脱思特”这个捷克词语的意义与作者笔下对于捷克共产党在政治上表现出的特点有相似之处。用这样一个原本修饰个人性格特点的词汇来修饰一个政党的作为,之间形成一种隐喻的话语信号,传达出中心词在意义上的转移。
第六部分名为“天使们”,继续写塔米娜为寻找记忆所做的努力,她来到了儿童岛,却被所谓理想化的世界逼迫而死。
作者在这一部分内容中,向我们细致地描绘了理想中的“儿童岛”,它想来美好,看似有秩序,实则充斥着强制性和控制欲。而这个“儿童岛”正是那些忠于捷克共产党的“天使们”引渡世人所去的“田园牧歌”般境地。因而笔端下存在着的“儿童岛”实际上是对某种政治理念的实施效果的形象性隐喻。
第七部分名为“边界”。关于“边界”,《笑忘录》中这样讲到,“人的生命的所有秘密就在于,一切都发生在离这条边界非常近甚至有直接接触的地方,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以公里计,而是以毫米计的。”[4]323
“边界”原是指反映在地图上的一条分界线,而在文中的叙述中,它则代表着在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表现着个体置身于陌生环境中所能体会到的一种疏离感。在这里,“边界”这一中心词的意义从地理方面转移到了人的心理、情感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从隐喻角度理解话语内涵的线索。
(二)政治书写——依托于同名章节间的对位
1.小说两大主题性线索
第二部分“妈妈”与第五部分“力脱思特”可以说构成了小说隐喻性叙述的两条主线,其他各章作为对这两章内容的平行性书写而存在。
第二部分名为“妈妈”。分析这一部分中具有隐喻性的内容,按照“自上而下”的隐喻理解模式以及“话语同显”、“物理同显”的语境背景知识,对于一个流亡在外的作家来说,“妈妈”其实是对祖国母亲的一种隐喻。这种隐喻方式的使用与塞尔提出的对隐喻意义的判断理论中的第二条原则相契合。“祖国”像“妈妈”一样生育了作为子民的我们,因而在日常表达中习惯于用“妈妈”来指代“祖国”。而妈妈的话“坦克是易朽的,梨子是永恒的”,表达着古老而沧桑的波西米亚在战乱与变革中看到的子民之生存繁衍的永恒性。政治上的变动或许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地此起彼伏,但是生命的延续却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母亲是对的:坦克必朽,梨子永生。
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窥见作者在人的记忆问题上的思考:人们能够长久地记住的,总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与人的生命本身有着恒常的重要性的东西。“坦克”只代表一时的历史事件,它总会成为过去。相比之下,梨子却与人们的生活有着更为根本的联系,所以梨子永远不会消失[5]。
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了一种心理——“力脱思特”。这种心理是“突然发现我们自身的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4]187,“自我折磨之后产生的是报复的欲望”,“因而特属于初出茅庐的年龄,它是青春的点缀。”[4]188按照塞尔隐喻意义的判断理论中的第一条来分析,与饱经沧桑的母亲——波西米亚相比,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应该就是作者对于捷克共产党的一种隐喻,因为年少且“缺乏经验”同样也是当时的捷克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他(捷克共产党)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但另一方面他更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自己。作者将“缺乏经验”看作是人类生存处境的性质之一。正是因为客观存在着这样一种生存困境,掌权者才会强制性地组织人们对不堪的历史进行有步骤有计划地遗忘;才会身处于大国和各种强势的挤压之下,只拥有“选择不同形式的失败”的自由;才会使其统治下的波西米亚变身为依附于苏联的“小女人”,听从“大丈夫”的安排,在自己的境地内成全玩弄自己的侵犯者,从而使自己无休止地扮演着荒谬的角色。
“妈妈”——波西米亚和“力脱思特”——捷克共产党,是纠缠在昆德拉复杂情感中的两极。对祖国,他百般地关切与思念,而对于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狂热追求过的捷克共产党,他在真正经历过之后,则表现出一种疏离、一种同情。
2.遗忘——主动遗忘与抗拒遗忘的人生困境
从隐喻的视角分析同名为“失落的信”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发现两部分内容都与“遗忘”有关,但一个是选择主动遗忘,一个是对抗人的自然遗忘。在对于两种遗忘的书写中传达出作者关于人的存在处境的思考。
第一部分以米雷克主动寻找记忆并试图毁灭记忆为喻,指出存在于个体生命中的有选择性的主动遗忘。有政治见解的知识分子米雷克毫不在乎随时被捕入狱的危险,决议要找回透露着他青春时代的政治狂热的信件并进行销毁,他不喜欢自己青年时代的一段过去,“他当时所热衷的正是他今天不计一切所反对的。”[2]122面对着少数知情者的打趣,“我说,你怎么能跟这么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上床?”成熟的米雷克对青年时代由于缺乏经验的狂热行为更是感到不堪回首,于是选择主动去遗忘那段曾经选错对象的过去。这个对象,正是那个对党忠贞不渝的“奇丑无比”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同时也是对捷克共产党的一种隐喻。
将这种主动性的遗忘从个体上升到政党,这种遗忘行为恰与捷克共产党统治下强制人们进行的“有组织的遗忘”具有相似内涵。捷克共产党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忘记那段在他统治下的不光彩的历史,而它统治下的人们也强制自己遗忘自己曾经忠于捷克共产党的过去。在揭示个体生命中所普遍存在着的主动性遗忘之外,同时展开了作者对于存在于政党中的遗忘行为的一种揭示与讽刺。
第四部分的内容则是以流亡在外的塔米娜苦苦寻找对祖国及过去的记忆为喻,借塔米娜的经历来说明人在刻意选择保存某段记忆时,遗忘的不可抗拒,这是自然状态下人与遗忘的抗争。在政治性的隐喻下,塔米娜是同样流亡在外的昆德拉的一个化身。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塔米娜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让他牵挂的女人,塔米娜和她的丈夫在“布拉格之春”后逃离捷克。在他乡,塔米娜的记忆越来越苍白,过去也渐去渐远,于是她开始有所作为,渴望得到出国前遗留在婆婆家的私人信件和十一个笔记本,她调动起所有的才智来达到找回她的过去的目的。从中可以体会到个人在抗击自然遗忘时的无力以及流亡在外之人在个人身份认同上的飘忽感。
同时,按照隐喻理解的思维模式和原则,塔米娜这一女性角色对往昔记忆的追寻同时也隐喻着祖国波西米亚对待捷克共产党的一种矛盾感情。为了找回对自己所珍视的那段生命经历的回忆,她竭尽所能,并将肉体交与他人蹂躏,正如波西米亚一度相信捷克共产党,在它任性的挣扎下将自己沧桑的历史交与苏联,最终却带着期望在所谓理想的境地中挣扎死去。其间表达着作者对于捷克共产党统治下的祖国波折命运的同情与怜惜。
3.嘲讽——“理想国”的可笑
同名为“天使们”的第三部分和第六部分内容表达着远离祖国的作者对自身遭遇的隐喻性书写以及对捷克共产党所谓的“田园牧歌”的否定。作者先是在第三部分的叙述中揭开所谓“天使们”的真实面目,而后在第六部分中更加深入地剖析了“天使们”憧憬中的“田园牧歌”的可笑。
在第三部分的内容中,作者审视并探询着同一个主题,即,“天使是什么?”[3]95作者通过对两种笑的分析认为,人们在习惯性认知中把魔鬼构想成恶的信徒,把天使构想为善的战士的思维方式是接受了“天使们”蛊惑人心的宣传后的结果,而现实中关于“天使”和“魔鬼”形象的定位及善恶的分析远非如此简单。
这部分内容以欧仁·尤奈斯库的话剧《犀牛》为喻,里面的人物,出于让彼此相近相似的意愿,纷纷变为了犀牛。而小说中的“我”——米兰·昆德拉,成为那最可贵的一个拒绝变形的人。于是在天使们那看似名正言顺实则充满强权与霸道的笑声中,“我”被赶到了圆圈之外。小说运用话剧《犀牛》的象征性隐喻,表达出作者对于自身被逐遭遇的荒谬性的无奈。通过对天使和魔鬼的笑的分析辨认出所谓“天使”的真实形象,即“他们(天使们)通过语义假冒欺骗了我们。”[4]95
第六部分的内容则主要揭示“天使们”对我们的欺骗,同时表达了作者对“理想国”,即捷克共产党向大家鼓吹的“田园牧歌”的否定。作者在文中尝试性地建构了一个牧歌般的存在——儿童岛。在那样一个想象中的世外桃源里,由孩子掌权,符合共产党人为大家建构的一个“夜莺歌唱的田园”。然而,作者让塔米娜身在其中,却发现表象理想的世界,竟让她无法忍耐以致多次逃离未果后,在孩童纯真眼眸的注视下溺死水中,这也体现了“孩子掌权”的残酷性。昆德拉在《六十七个词》中认为“孩子掌权”意味着将儿童时代的理想强加于人类,这个儿童时代的理想恰好与那个被捷克共产党美化了的“理想王国”、那个所谓的“夜莺歌唱的田园”相契合。作者让塔米娜在小说建构的理想化世界中进行尝试,发现所谓的“田园牧歌”非但没有给塔米娜带来她所憧憬的快乐,相反却造成了她的不幸。这种儿童时代的理想,这种“田园牧歌”,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制性和控制欲。
在同名的第三部分与第六部分内容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联性线索——拉斐尔夫妇,他们在小说中都是作为引渡人而存在。拉斐尔夫人在第三部分中出现,作为学生加百列与米迦勒的引领老师,憧憬着“圆圈舞”,在欢笑声中同她的追随者向天堂飞升。拉斐尔则出现在第六部分中,是他将塔米娜引领到充满欢声笑语的儿童岛,也是一个理想国的追随者。拉斐尔和拉斐尔夫人这两个人物的设置是作者有意为之,他们两人都负责把人们引渡到快乐的“理想国”中去,都是制造天使般的欢笑声的导师。同时,他们的名字也具有一定的指涉性。
考察“拉斐尔”这个名字,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三杰”中那位擅长于绘制圣母像的著名画家之外,在《圣经》和《古兰经》中,也都有拉斐尔这个天使长。因而更容易理解作者在《笑忘录》中,将拉斐尔夫妇分别安排在同名为“天使们”的第三部分和第六部分,并且让他们以具有引渡人职责的“天使们”的形象存在于人间的意图。他们憧憬着天堂,制造着“天使们”强制性的笑,负责引渡缺乏坚定信仰者走向他们的“上帝”为他们承诺中的理想之地,然而理想之地究竟怎么样呢?在作者的分析下,只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乌托邦。
4.边界——政党不等同于祖国
我们不能忽视米兰·昆德拉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已经流亡法国的写作背景,他是带着对于祖国的思念和对于捷克共产党的不满,在陌生的语言和环境中进行自我书写的。远在法国的昆德拉面对着他那“忧郁的波西米亚”,同样遭受着“力脱思特”情结的折磨,一方面他思念着保存有自己生命之根的祖国而且抵抗着对其的自然遗忘,另一方面又嘲笑着“缺乏经验”的、尚处于“青年阶段”的捷克共产党,并渴求着对青年时期自己的荒谬归属进行主动性地遗忘,但在遗忘的过程中对祖国的关注一直存在。这里讲到的“边界”,不仅仅是指有形的地域边界,它还涉及无形的语言、文化、信仰与整体氛围的临界。虽然反映在地图上只有毫米的距离,然而其隔阂感却横亘在每一个心系祖国的流亡者心中,虽然被逐但仍与自己的祖国惺惺相惜。
(三)整体隐喻——对存在问题的揭示与思考
综合以上对依托于小说章节的对位之中包含着的隐喻内容的分析,小说先是在第二部分“妈妈”和第五部分“力脱思特”中分别推出饱经沧桑的祖国与“缺乏经验”的捷克共产党的形象,祖国母亲与她的子民携手走过沧桑历史,彼此之间荣辱与共,而作为年轻政党存在的捷克共产党却因为“力脱思特”情结在祖国的怀抱中折磨着自己和他人,这些无不都在牵动着作者的内心。于是抽离出政治“圆圈”之外的昆德拉在认识到自己年轻阶段的政治狂热与缺乏经验之后,想要竭力遗忘自己对青年阶段的记忆,同时流亡在外的他又努力抗拒着对于祖国的遗忘。为了更加形象地让读者感受这种生存处境,作者在同名为“失落的信”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推出米雷克和塔米娜这两个人物形象,让他们作为自己这种特定情感的化身带领读者游走于对于祖国和政党的复杂而纠结的感情之中,由此揭示出个人因为遗忘所带来的存在问题上的尴尬局面。在以上几部分内容的铺垫之下,作者又将自身的部分经历加入其中。于是在同名为“天使们”的第三部分和第六部分中讲述了作者本人身在他乡的环境中对祖国的回忆以及对捷克共产党的认识:一方面书写自己类似于“犀牛”般的处境而被政党驱逐出祖国的遭遇,另一方面又用“儿童岛”的隐喻表达对于捷克共产党所鼓吹的虚伪的政治牧歌的讽刺。最后,在小说第七部分“边界”中进一步揭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就是这样纠缠于由波西米亚和捷克共产党所形成的边界之间。
《笑忘录》就是这样在对“政党不等同于祖国”的认识之中展开详细且有层次的叙述,表达着肉体存在于边界之外而情感横亘在祖国和政党之间的流亡者们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生存感受。
三、“对存在的诗意沉思”
尽管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存在着客观的政治性,但他却不接受学者对其作品的政治性解读。在他看来,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也非预言家,他只是存在的探究者。因而,对于客观存在于他的文本中的政治因素,从小处着眼,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或感受到的一种人生境遇。从大处着眼,则是他思考人类存在问题的一个平台。而后者才是他真正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而且俨然已成为小说之所以存在的根本。
昆德拉在分析《笑忘录》时谈到,这部小说是建立在“遗忘、笑、天使、力脱思特、边界”这五个主要词语之上的,“这五个主要词语在小说进程中被分析、研究、定义、再定义,并因此转化为存在的范畴。”[3]106例如,他在小说中揭示出“遗忘”是个体生命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境况,并且是先于政治问题而最早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的。诚然如此,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带着前世积累的经验在此生万无一失地生存,必然会因为年少时期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而做出一些令今后的自己遗憾的选择,那么面对这种遗憾,个人便会进行主动性地遗忘,以求在心理上“解救”自己;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所珍视的记忆,却因为自然规律中客观存在着的遗忘让个体无力抵抗,这是个体乃至上升到更大范畴的政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样,对于“笑”、“天使”、“力脱思特”等出现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的问题,他也进行着睿智的思考。因此,整个《笑忘录》在隐喻性地进行着政治书写的基础上,更是依托这种情景的设置深入地思考着人的存在,这才是米兰·昆德拉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6]。
“西方哲学传统中,人与世界是对立的,人以征服各种对象为乐。这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遮蔽了人在世界中的本真生存。”[7]昆德拉的系列小说则体现着他“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意思考”[3]45。而对于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政治问题,昆德拉曾这样阐述在小说中处理此类问题时所需注意的原则,“历史本身必须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来分析。”[3]48当他谈及在小说《笑忘录》中设置“布拉格之春”这个历史事件时,也并没有将其限制在表面化的政治和社会范畴,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展现人的根本生存处境来进行描绘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出现在昆德拉作品中的政治性描写做扩大化地解读,不能把他看作是个政治学家,把他的作品看作是对自己坎坷经历的一种个人发泄,而应该从更高层次的存在角度认识他在作品中所谈及的政治话题,从文学与哲学角度体会他在其中展开的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
结 语
对于克里斯蒂安·萨尔蒙向米兰·昆德拉提出的关于《笑忘录》的七个部分可以写出七部不同的长篇小说的问题,昆德拉如此作答:“假如我写出七部独立的小说,我就无法奢望通过一部书来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3]90在情节联系并不紧密的七个部分之间,昆德拉像谱写奏鸣曲一般通过整体性隐喻从宏观角度建构了一个“隐喻的森林”,复杂的故事在叙述中展开,散而不乱,因为主题唯一。《笑忘录》正是通过对隐喻手法的巧妙使用为小说在内容上建构起一个立体的空间,让我们从处于边界两端的祖国和政党入手,游走其中。在“笑”与“忘”中获得特殊的情感体认,在感受昆德拉的小说所具有的创新性的同时,领会他在其中对人的存在问题的睿智思考。
[1]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仵从巨.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米兰·昆德拉.笑忘录[M].王东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艾晓明.昆德拉对存在疑问的深思[M]//李凤亮.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318.
[6]仵从巨.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4):120-129.
[7]董惠芳.从思维方式看现象学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 [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4):65-71.
(责任编辑:刘 燕)
The Metaphors and Political Writings inTheBookofLaughterandForgetting
Wang Baodi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China)
There a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metaphors in Milan Kundera’s novels. In addition to the metaphors based on single image 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writing, Milan Kundera tends to pursuit holistic metaphors which are constructed between the content and chapter structure in his creation. The utilization of holistic metaphors creates a forest of metaphors in illustrating the novel’s theme. The paper setsTheBookofLaughterandForgetting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abundant usages of metaphors in Milan Kundera’s novel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al usage of metaphors an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As a feasible way to cognize, we can obtain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human’s existence beyon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in this novel.
TheBookofLaughterandForgetting; metaphor; political writing; being
10.3969/j.issn.1672-7991.2015.04.012
2015-10-26;
2015-11-16
王宝迪(1992-),女,山东省济南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I106.4
A
1672-7991(2015)04-00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