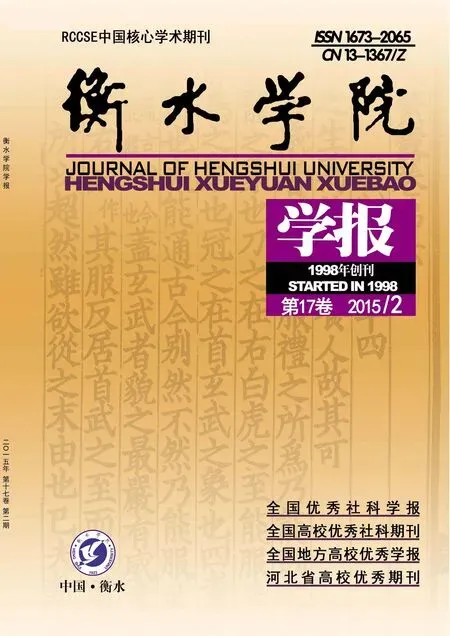《董仲舒与儒学研究》栏目特约主持人按语:
中国的政治,一向有“儒表法里”“阳儒阴法”之说,虽未必完全正确,但儒法兼采、两相资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儒、法之间的勾连与纠结便一再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话题。吴光教授一文把董仲舒在“表章六经,推明孔氏”、阐发《春秋》“微言大义”名义下所创立的“德主刑辅”王道论理解成一种以“《春秋》公羊学”形态出现的“政治经学”,可谓新颖独到之见地。这种“政治经学”不但开创儒家藉经议政、托孔改制之学风,而且还催生出今文经学与谶纬学。董仲舒创建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也为历代今文经学家提供了一套“托天论道、托孔改制”的经学思维模式,他所提出的“三纲五常”一度成为自汉至清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阐述精当,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董仲舒的“德主刑辅”在李俊芝、朱冰清、朱云鹏、宋风轩的论文中则被表述为“德本法助”,并被从天道、人性、政史三个角度予以初步论证。
黄玉顺教授的演讲虽疏于学理论证和逻辑推演,但把董仲舒看做儒家与政治权力实现真正双向互动之肇始,董子之前,诸子百家只有思想贡献,董子之后才落实、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指认作为御前会议纪要的《白虎通义》是整个帝国时代的“基本法”、“大宪章”,因其使“三纲六纪”成为两千年帝国制度最核心的伦理规范;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代化其实并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内生现代性”,这个转换过程最早发轫于宋代,而成为中华帝国“下行”的一个转折点;中国思想观念的二次大转型都与公羊学的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董仲舒所强调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种威权主义,“屈民而伸君”是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屈君而伸天”则是制度设计的形上根据,所述所发,启示良多,催人深省。
曾振宇教授一文凸显阳气之重要,视仁德为阳气本质属性之彰显,颇得董学之精义。在孟子以心性论善基础上,董仲舒以气论善,从阴阳气论高度论证善之缘起与仁观念存在之正当性,使得儒家仁学跃上一座新的形上“山峰”。透过包括天人同质、天人同构、天人互渗、天人同德之内容的“天人合一”命题可以看出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天并不是最高范畴,“气”才是“最顶层设计”的哲学概念。这就一举推翻了前人,属于别出心裁之见解。其虽言董子天论与气论密不可分,但二者内在关联仍遮蔽犹深,令人生疑。从当代学术史的层面来总结与评议前辈专家之成就,则是常会营研究员文章之亮点,他详尽追溯周桂钿先生四十年治董生涯,历数并厘定周先生的学术贡献:考订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8年,即高祖九年,死于公元前107年到104年之间,寿曰93 岁。三次定性董仲舒治学术:从唯心主义,到“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再到“求善的政治哲学”,而“定性的变化,说明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提高”。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说、“独尊儒术”皆为“周先生对于董仲舒的理论贡献”。充分肯定周先生“对学术的极度专注与认真执着”以及“对人类、国家、社会、生活、自然乃至宇宙的持续不断的思考和判断分析”。这些都将成为董学后来者的宝贵财富。
金春峰编审的文章考证出《礼运》并非孔子及其弟子论礼之言,而出于西汉儒者之手,其第二部分天地阴阳、天人同类之大礼乐观,以阴阳五行论礼,这是汉人释《春秋》,释《易》,释《尚书》的思想范式,而不可能出自孔子和先秦阴阳家。第三部分礼与阴阳、五行及太乙、仁义之关系,则采自先秦文献。大同、小康之说是儒家思想,但非孔子之言。这些虽能成一家之言,但于逻辑环节、文献支撑仍有待加强。儒学史上,程门弟子杨时一生历经两宋七朝,只专注于扬洛学、为贤臣两事,“以身殉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义。”刘京菊教授一文评议杨时之生平与学术,将“内外合一”当作学者“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人之境,也是平治天下的王道理想,检讨王道之“正心以知人”入门路径,值得一读。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子学院、董子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余治平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