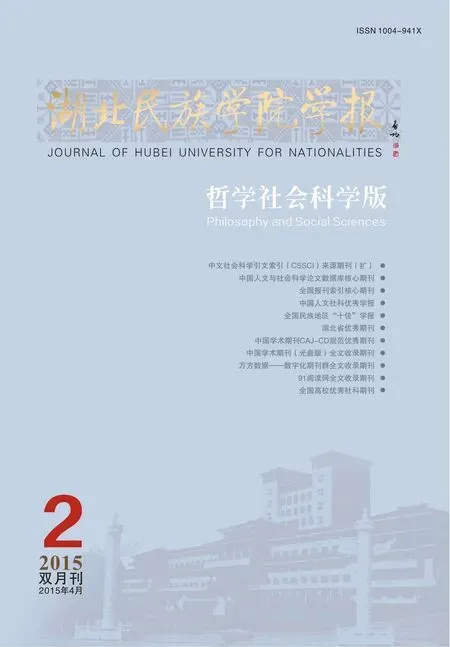重述法律推理
朱 政
(湖北民族学院 法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重述法律推理
朱 政
(湖北民族学院 法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主体。在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双重视角下,可将其刻画为:通过论证(论辩)获得推理的前提——规范与事实,并最终从前提到结果的推导过程。基于此,法律推理的理论模型可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一是“推理核”;二是“论辩层”。“推理核”关心法律推理的起点和基本形式结构;“论辩层”则拓展了论辩对话的具体方法、程序性规则和评价标准。至此,可对法律推理展开分析和重构。
法律推理;法律论辩;推理核;论辩层
一、如何看待法律推理
(一)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主体
讨论法律方法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学者们对其存有不同理解,亦即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各种方法的地位与运用相差甚远。看似同样谈论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其实往往“鸡同鸭讲”,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本文中,法律推理被认为是法律适用的主体。其他方法则为推理过程中,遇到特殊问题的具体“解决”。事实上,这种看法也是学界的主流意见。解兴权曾指出,“法律推理应当包括以上四个方面的要素,即法律理由、推导与论证、权威性以及证成方法,因此,法律推理就是特定法律工作者利用法律理由,权威性地推导和论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或方法)”[1]25。伯顿更简洁地指出,“法律推理就是在法律争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2]1。当然,除非给出理由,否则单纯援引学界前辈的意见不能算作真正的“论证”。
(二)法律推理与法律方法体系
不论学者如何争论,很少有人认为法律方法杂乱无章,各行其是。相反,法律方法应当以体系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各种方法之间协调、配合,共同贡献于法律适用。陈金钊教授指出,法律方法的体系有着不同的表达,至少有三条路径:⑴以法律发现建构法律方法体系;⑵以法律解释作为法律方法的体系;⑶以法律推理为最高方法的概念,用推理涵盖所有方法。陈教授主张“在发现的逻辑下建构体系”,“这就是以法律发现作为司法首要使用的方法,以法律推理为最后要使用的方法。中间的包括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利益衡量(价值衡量),漏洞补充、法律分析等方法”[3]191。
这里无意去比较上述方案。重要的是指出,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难言“中立”。还以陈教授为例,他钟情于“在发现的逻辑下建构体系”,是因为“强调了发现的逻辑,而否定了司法中的创造”[3]186。这与他重视“形式”方法论的一贯主张相契合。毫无疑问,法律方法体系建构的背后有支撑其发展的“裁判理念”(ideology of the judicial decision)——“裁判理念澄清了和最终证成了法院应该如何适用法律。它定义了法院适用法律的总体方向和态度”①Jerzy Wróblewski,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law, edited by Zenon Bankowski and Neil MacCormick,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p.266.。这意味着,不同方案的取舍,最终取决于立场的选择。
在卢勃列夫斯基那里,“裁判理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严格裁判理念(ideology of the bound judicial decision),自由裁判理念(ideology of the free judicial decision),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裁判理念(ideology of the legal and rational judicial decision)。显而易见,这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在司法裁判领域上演的“变脸”戏法。因而,我们无法脱离现实的“法治”语境展开讨论。法律方法论研究,应当有这样的坦白。
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对中国法治充满信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实给了法学界很大的信心。诚如徐显明教授在2014年法理学年会上所言:“中国法治的春天,来了。”,对中国司法抱有期待,那么,“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裁判理念”就更值得追求。因为,它代表了“精致司法”的样态,一方面,避免脱离法律展开司法的“非理性的谬误”(irrationalistic fallacy),另一方面,避免形式逻辑僵化运用的“过度理性谬误”(ultra-rationalistic fallacy)。在“兼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裁判理念”观照下,以法律推理为主体是建构法律方法体系的不错选择。
二、如何刻画法律推理
(一)研究路径
一般来说,法律方法论研究有两个基本路径(basic approaches):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描述性维度,致力于对法律适用的过程进行整理;规范性维度,则要求对法律适用进行内部评价(internal evaluation)和外部评价(external evaluation)。所谓内部评价是指从法律体系内部展开,强调司法裁判与法律规范的一致性(consisitency);而外部评价则以法外的价值体系(axiological systems)为视角,关注司法裁判的政治功能、道德评价和工具性价值等诸多方面*See Jerzy Wróblewski,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law, edited by Zenon Bankowski and Neil MacCormick,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62-64.。
简单地说,描述性研究以法庭辩论为原型,将法律推理刻画为当事人共同参与的,相互承认、质疑、诘问、辩论的过程,最终由法官采信,“从无到有”的形成推理的前提集——事实与规范,并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规范性研究重构法律推理的链条,对其展开评估,一是,评估推理是否成立,二是,比较多个推理方案的优劣。不难想见,法律推理的理论重述,应当在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双重视角下展开。
(二)法规范的适用与证立
法律发现与证立的两分是法律论证理论的重要前提,“前者关涉到发现并作出判决的过程,后者涉及对判决及其评价标准的确证”[1]。然而,法律推理是一个“夹叙夹议”的过程——在适用中论证,在论证中适用。
恰如哲学中多数两分法的命运,从法律发现与证立的两分到截然两分,就从真理走向了谬误。事实上,规范的适用与证立是融为一体的,亦即因证立而能正确适用。关于这一主题,可以从阿列克西和京特(K. Günther)的争论中得见。
京特认为,在一条规范的证立与适用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一条规范的证立涉及的是它的效力,而适用涉及的是它的适当性(Angemessenheit)[2]43。简单地说,规范的适用与规范的证立展开的前提是不同的,规范的适用面对的是一个特定的情景,它要在“顾及到某个情景的所有特征”的情况下,指出什么是适当的解决办法;而规范的证立面对的是人为简单化了的标准情形,它负责决定哪个普遍的规范是正确的。前者可称为真实适用情境(genuin situationen),后者为假设情境(hypothetischen situationen)或范例情境(beispielsituationen)。这样,证立性商谈就成为独立于情境的规范判断。由于商谈者的认知有限性和情境的变动性,因此它呈现出初显性特征(prima facie)。阿列克西总结道:在京特眼中“证立性商谈和情境间的联系与适用性商谈和情境间的联系方式并不相同”[2]58。
在京特看来,在法律适用中,面对相互竞争的N1和N2规范,借助法律规范的融贯性,可以获得最终适用的具体化的规范N1k。或者说,如果N1k可以被证明为法律融贯体系的要素,那么它就无需证立。对此,阿列克西表示不能同意。如果,证立性商谈的对象是初显性规范N1、N2的有效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碰撞。这无疑降低了证立性商谈的地位,“它就只能成为适用性商谈的一般论据和标准情形的拳头规则(faustregeln)的产品。随着适用性商谈上升为融贯性商谈,证立性商谈也就沦落为了论题商谈(topoidiskurs)”[2]。另一方面,证立性商谈并不如京特所言,情境描述可被限制为不变的,实际上它同样依赖于情境的多样性。在商谈规则中也没有禁止参与人构想出复杂情境并予以追问的规则。这样,阿列克西认为,适用性商谈与证立性商谈虽然面对不同的情境,但商谈展开后,将遇到相同的问题,并且两者皆以同样的论证形式并依据同样的论证规则。同时,具体的适用的情境拥有现实的商谈理论意义,在其中法规范的精确化、改变、摒弃和新创不仅是允许的、可错的,而且还积极地体现“固有的历史性”的可能的新情境。当然,它们都可以被证立,也需要被证立。
其实,融贯性是法律论证的标准之一,是正确性的一种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西班牙法学家Leonor Moral Soriano指出,法律领域存在两类融贯论,其一是法律体系的融贯(coherence of the legal system),其二是法律推理的融贯(coherence in the legal reasoning)*Leonor Moral Soriano, A Modest Notion of Coherence in Legal Reasoning: A Model for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Ratio Juris 16,2003,第296-323页.。前者是法律体系的一种特征,后者则关注理由链(网络)的建构和证据的收集及推论。法律推理的融贯对于法律命题来说,形成了一种“积极关联”,而促成这类“积极关联”的关系正是“证立关系”。所以说,在规范冲突中,只有通过证立才能获得融贯的法律规范,相反,通过预设法律体系的融贯性来获得个案规范是错误的思路。
法律推理就是通过论证获得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范和法律事实等各类前提,并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诚如阿列克西所言,“每个适用性商谈必然包含一个证立性商谈(适用性商谈的结果依赖于证立性商谈),这一事实禁止我们将适用性商谈与证立性商谈视为两种独立的商谈形式来相互对立”[2]62。
(三)模式建构
一如上述,法律推理是从前提到结论的一个正向推导,以及在具体争点上展开论证的过程。基于此,法律推理的理论模型可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一是“推理核”;二是,“论辩层”。它们共同构成了法律推理之“理性”。下面,分而述之。
“推理核”关乎推理的前提和推理形式结构两面方内容。或许,我们能立刻联想到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结构和非形式逻辑中的推论结构。然而,由于法律推理是在现行法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规范性推理,因而它又不同于逻辑学的研究。正如季卫东教授所言,“法的推论是实践性议论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类型”[3]。具体说来,其一,法律推理的规范性,要求以法律规范为起点进行法律推理。现代法学理论,普遍认同法律规范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这使得,我们不仅要研究法律规则与原则有怎样的区别,还得关注他们的适用方式、推理的形式和如何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寻找它们。其二,法律推理基本的形式结构问题。雷磊认为,“法律推理的正当性取决于它的理性,而它的理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当然绝非全部)由它的结构决定。如果对法律推理的结构分析,揭示出法律推理不外乎是推理者的意志决断,那么法律适用的理性及其正当性就都是成问题的;相反,如果法律推理仅仅被化约为单一的形式(如三段论),而将理性的内涵与外延限定于演绎逻辑之上,那就有意忽略了法律推理或者说理性本身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同样是不理性与不正当的。无论如何,法律推理的结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法律推理理论的核心”[4]。的确如此,某种程度上,法律推理的基本形式,决定了推理是如何进行的,推理的前提(理由)是如何支持结论的,这最终将关系到推理的理性程度。
另一方面,是关于“论辩层”。法律推理是在对话中运用理由的过程。加拿大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R. H. Johnson),提出论证需要一个“论辩性外层”(dialectical tier)的思想。“一个论证是一种论辩实践的讨论或文本‘蒸馏’,论辩者通过产生支持它的理由来说服他人一个论点是真的。除了这个推理核,论证还有一个论证层,论证者在其中履行其论证义务。”这样,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将其扩展为一种二维结构,亦即推理结构和论辩性义务。其中,论辩义务代表一种“理性要求”——“如果论证者没有处理反对意见和批评,……其论证就将不能满足理性要求(the dictates of rational)”*Ralph H. Johnson,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0年。。显然,“论辩层”为法律推理拓展了动态对话的具体方法、规范和评价标准。它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一方面,它利用了非形式逻辑关于“抗辩”、“攻击”、“辩驳”和“击败”等概念,分析论辩的阶段、具体方式和谬误判断。正如沃尔顿的新论辩术(new dialectic)和阿姆斯特丹学派“语用论辩术”(pragma-dialectics)所作的工作。另一方面,它关系到一套程序性的论辩规则,以规范论证主体如何提出命题、应对挑战和结束对话。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在“论辩规则”问题上,本文利用的理论资源来自于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行文之便,法律论辩规则与形式的标注,也遵循阿列克西的方式。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69-373页。,属于这方面的理论高峰。
三、推理核
(一)推理的起点
法律推理须由法律规范为出发点,但“法律规范的含义是所有法理学最基础的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歧义丛出的概念”*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Julian Riv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第19页.。在当代法理学中,法规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律原则问题和法律多元论上。
关于法律原则的理论,主要由三个相关部分组成:规范属性理论、区分理论和适用理论。规范属性理论争论的是法律原则是否存在;区分问题关心法律原则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法规范;适用问题意在探讨法律原则如何适用。前两个问题是法律原则适用的前提性问题。对于规范属性理论存在两种立场——肯定和否性,否定法律原则存在主要在规范性层面上提出异议,如亚历山大和克雷斯就认为法律原则既无存在必要,逻辑上也不可能存在[5]。关于区分理论,存在三种立场:强分离立场、弱分离立场和一致性立场。强分离立场认为法律原则和规则之间是逻辑上的、结构性差别,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德沃金和阿列克西;弱分离立场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原则的一般性更高,而规则的一般性较低,这种观点以拉兹、摩尔为代表;一致性立场主张两者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支持这种观点的有阿尔尼奥和绍尔。其实,“现今大多数法理论家即除了极端的法实证主义者都接受了下列观点即法律并不仅仅由法律规则组成,也包括法律原则”*Peczenik,Jumps and Logic in the law, in Logical Mode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Edited by Henry Prakke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7,第298页。。
另一方面,在法人类学和法社会学那里,“法律多元在当代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6]2。站在法官法源的立场,道德律、民俗习惯、法学理论等皆被认为的非正式法源。这要求,法律推理需要一个前置程序,亦即对诉讼参与人提出的推理之大前提进行甄别,验证其正当性(实质正义)、合法律性(合乎制定法的精神)和规范性(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无疑,关于这些问题,也会遭遇当事人双方的分歧,并展开辩论。法官需要对论辩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值得为了推理目的而被采纳”[7]390。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这是法律发现的方法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法律发现为法律推理提供“适格”的法规范;其二,“适格”的非正式法源,在法律推理中也必须遵循推理的基本形式。
(二)推理的基本形式
德沃金和阿列克西在大量的论著中明确指出法律规则的适用方式是涵摄,法律原则的适用方式是权衡。此外,阿列克西在《两种或是三种模式?》(Two or Three?)一文中,又提出了第三种法律适用的基本形式:类比推理(Analogy、Analogie),适用于案件间的类比(analogy between or a comparison of cases)。
第一,涵摄。传统司法三段论中的涵摄,不仅具有形式性,而且是真值保持的,亦即联接具有真值的大、小前提,推导出同样具有真值的裁判结果。这显然超出了形式逻辑的能力范围。阿列克西指出,“将涵摄的形式结构与实质的演绎推理区分开来,是一个显著的进展”*Robert Alexy, On Balancing and Subsumption———A Structural Comparison. Ratio Juris, Vol. 16 No.4, (December) 2003,第433-49页.。他将完整涵摄的形式结构刻画为:
(J.1.2) ⑴ (x)(Tx → ORx)
⑵ (x)(M1x → Tx)
⑶ (x)(M2x → M1x)
·
(n+2) (x)(Sx → Mnx)
(n+3) Sa
(n+4) ORa ⑴—(n+3)
第二,权衡。关于法律原则的适用,德沃金的观点是开创性的:法律原则和规则之间的区别是逻辑上的,规则是全有全无(all-or-nothing)的方式应用于个案的,而“原则具有规则所没有的深度——分量和重要性”[8]47。在个案中,法律原则适用是一个衡量分量或重要性的过程。阿列克西认为德沃金的理论过于简单,他将法律原则定义为“最佳化的命令”(optimizing commands):原则是基于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可能性,尽最大可能实现的规范。从而,原则不具有“确定性特征”(definite character),而具有初显性特征(the prima facie character)。事实上,在法律规则存在例外的时候,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一样具有初显性特征,因为此时需在支持法律规则的原则与支持例外情形的原则之间作权衡。这样,法律规则的适用也就可能牵涉到权衡。因此,可以认为权衡在法律适用中是无所不在的。
阿列克西通过极具数理化的推演,发展出“重力公式”(weight formula)来表达*用“I”(intensity)来表示原则的这种具体的受侵害或被满足的重要性程度;加入“R”以使得重力公式能够反映出“经验性假设的可靠性”(reliability of the empirical assumptions)。:
阿列克西自信地认为权衡具有一个形式结构。虽然,“涵摄公式是以逻辑规则为基础的框架,而权衡公式是以数学规则为基础的框架”*Robert Alexy, On Balancing and Subsumption———A Structural Comparison, Ratio Juris, Vol. 16 No.4 , December 2003,第433-449页。。但是,这种差别仅仅是推理形式结构而已,它们都为法律推理的理性化提供了形式基础。
第三,类比。类比是漏洞补充的最主要方法。阿列克西将它的基本形式描述如下:*Robert Alexy,Two or Three?,载http://www.steiner-verlag.de/uploads/tx_crondavtitel/datei-datei/9783515096089_p.pdf,2012年8月28日访。
A1:每个(待决)案件ci与(经典)案件cj。ci与cj在特征F1j,……Fnj上相似,因此,ci根据规则F1j,……Fnj→Q,与cj同等对待,获得法律效果Q。
A2:每个有A1论述的案件,可以提出两个反向的主张:
A2.1:如果ci与cj在特征F1i,……Fni上有别,根据规则F1i,……Fni→┓Q, ci与cj非同等对待,而不取得法律效果Q。
A2.2:如果ci与ck在特征F1k,……Fnk上相似,根据规则F1k,……Fnk→┓Q,ci与ck同等对待,而取得法律效果Q。
据阿列克西所述,他将类比与涵摄、权衡一样置为推理的基本形式之一,是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征:形式性(formal)、必要性(necessary)和特殊性(specific)。其实,从英美法系的先例传统来看,类比推理的重要性是一望而知的。诚如伯顿所言,“法律推理采取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类比推理,另一种是演绎推理。这两种形式具有重要的实际作用,因为对于组织大批法律材料来说,某种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可以帮助你认定推理的适当起点,找出相关的材料,明确表述争点以便集中思考”*[美]史蒂夫·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第30页。。
四、论辩层
(一)论证图示
动态的法律推理是通过不断平息“争点”得以推进的。或者可以说,法律推理就是一连串的法律辩论。沃尔顿“新论辩术”非常成功地刻画了“对话”的交互框架,并在一个“说服型对话”的主体中,区别出其他多种对话类型,容纳了多种论证形式、技术,并针对性地给出运用和评价的方法。他考察了法律论证的一般形式,称其为论证图式(argumentation schemes)——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论证的形式,另一部分是一组批判性问题。例如,诉诸专家意见论证[9],用来检验专家意见。
其实,佩雷尔曼、阿列克西、图尔敏等学者都讨论了论证图式,只是偏重不同的方面。在佩雷尔曼那里,“论式本身是关于论证的‘论题’,它们是将意见与凭借被公认和听众接受而获得力量的断言联系起来的不同方式。正是该形式本身的可辨认性赋予论证说服力”[10]。因而,是一种修辞技术。在阿列克西那里,论证图示是外部证成的方式,如法律解释。恰如卢勃列夫斯基将法律解释称为“操作解释”(operative interpretation),“‘操作解释’被嵌入法律论证,而作为一种实践推理的形式,目的是对法律裁决的证立”*Neil MacCormik and Robert Summers(eds.), Interpreting Sta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 Aldershot: Do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91,p.21.。
在描述性视角下,论证图示就是面向“争点”的论辩方式或技术。在规范性视角下,它的作用是联接、阐明或重构推理链条,完成佩岑尼克所言的跳跃(jump)*See Aleksander 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 Springer,2008,第96页.。萨尔托尔评论道:“它们允许佩岑尼克所谓的跳跃(jumps)或飞跃(leaps):当相信一个可废止图式的前提时,我们被引导支持图式的结论,即使我们的前提没有真值保持地蕴涵这些结论”*[意]乔瓦尼·萨尔托尔:《法律推理:法律的认知路径》,第68页。。
(二)论辩规则
埃默伦将批判性讨论划分为四个阶段:冲突阶段、开始阶段、论辩阶段和结束阶段。在冲突阶段,论辩双方确定他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在开始阶段,论辩双方分配角色:谁是正方,谁是反方,就讨论规则以及讨论的出发点达成一致;在论辩阶段,正方通过提出论证来应对反方的异议或打消反方的疑虑,为他的立场作辩护;在结束阶段,论辩双方评估意见分歧消除的程度,确定论辩结果支持哪一方[11]。在这个过程中,论辩规则为论辩者的行为准则——归结起来,共十条规则。
阿列克西在哈贝马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普通实践论辩的5组22项规则,
以及一套法律论辩的规则和形式。他认为,在论证的规则和形式两者间,前者是更为根本的。“商谈理论可以完全通过规则表述出来,因为这一理论并不包含对个体的特殊规定。出于简化的理由,在规则之外表述论述形式 (Argumentformen)是合乎目的的。将(论述)形式转换为规则(它允许或规定使用特定形式的论据)在技术上不会产生任何困难”[2]91。因而可以说,程序性论证理论旨在建构一套具有普遍理性的论证规则来规范法律适用(论证)活动。遵循规则,论辩者对规范性命题达成合意和共识就有了基本的保证。诚如颜厥安所言,“理性讨论的规则所涉及的,并不是语言陈述之逻辑关联而已,更指向于言说者之态度。因此理性讨论之规则是一种语用学之规则”[12]。
五、法律推理的分析与重构
(一)推理的步骤
图尔敏的论证图式*See Toulmin, S., R. Rieke, A. Janik, An introduction of reasoning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4,第49页。,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前提—结论”式的结构,影响深远。菲特丽丝认为,“图尔敏运用自己的论证模型,试图表明评价规范有些是普遍性的,用他的话说是场域永恒的(field-invariant),有的则是特定的,或者说场域依存的(field-dependent)”[13]38。“场域永恒”说明,主张(claim)的可接受性部分的依赖于法律程序。
当法律程序开启,控辩双方第一步是提出一个特定的主张(claim),第二步是提出主张的理由(grounds),作为该主张的基础而提出的理由就相当于法律中的证据,第三步是要给出一个保证(warrant):一个规则、原则或其推论出的准许(inference-licence)。第四步,在疑难案件中,保证会遭到质疑,譬如,“1.保证可靠吗?2.这个保证真的可以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案件中运用吗?”*Toulmin, S., R. Rieke, A. Janik, An introduction of reasoning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4,第62页。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出佐证(backing)。法律论辩由此展开。
图尔敏的论证图式,暗示了法律推理的步骤。可作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建构特定的论述阶段;第二,比较不同的论述阶段;第三,逻辑重构阶段[14]。简单地说,首先,提出方案,当事人双方分别提出“主张”、“理由”和“保证”;其次,方案比较,面对对方可能的质疑进行辩论,并提供进一步的“佐证”,直到优势方案胜出;最后,结果重构,将优胜方案以完整的逻辑形式呈现出来,形成判决。
(二)提出方案
双方当事人提出“主张”,须以法规范为起点,将其组织为符合形式逻辑的方式——涵摄(J.1.2)。这将会遇到三类情况。一是,以法律规则为起点。涵摄本身就是法律规则适用的方式,无须赘述。二是,以法律原则进行权利主张。然而,法律原则一般比较抽象、笼统,缺乏事实构成和法律效果。如果当事人提出以法律原则为依据,则不能径直将其与对方的主张进行“权衡”,而必须通过将法律原则具体化的方式,以符合演绎逻辑的形式提出。如拉伦茨所言,“法律原则并不是一种——一般性的案件事实可以涵摄其下的,同样——非常一般的规则。毋宁其无例外地须被具体化”[15]348。三是,规则漏洞的情况下,运用类比推理。根据类比推理的形式,在建构论述时,重在刻画与经典案例cj或者类比规则的相似性,最终类比推理的起点是经过“转化”的法律规则,是间接从法律规则出发的,亦即存在这样一个“转化”:(x)(Tx∨Tsimx → ORx)。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满足了法律推理在形式逻辑上的要求,其二,满足了法律论辩之可普遍化原则(J.2.1,J.2.2),“最重要的要求是,至少有一个前提必须是某个普遍规范的表述。这个要求大多情况下很容易理解,因为法律三段论首先是一种制定法适用的理论,而制定法通常是普遍的规范。但在没有制定法规范可用的情形下同样如此。理由在于,涉及命令、禁止或允许的判决必须基于一条普遍的规则作出”[2]。此外,涵摄须尽最大可能展示逻辑推导步骤(J.2.4,J.2.5),而当有人表示异议——针对逻辑推导步骤中插入的各类前提(J.2.3),遂进入相关的法律论辩。
(三)方案比较
广义的法律论辩(外部证成)的对象是逻辑推导步骤中插入的各类前提。阿列克西大致将其分为三类:“(1)实在法规则;(2)经验命题;(3)即非经验命题、亦非实在法规则的前提”[16]285。实在法规范的证立在于指出其符合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标准;经验命题的证立是对经验前提进行的;最后一类,则是法律论证的对象。这三类证立的程序之间存在着多重复杂的关系。因为,实在法规则的论证,譬如对非正式法源的运用与争论,则可能需要对某个法律秩序内界定有效标准的规则进行解释;经验事实的论证,也关系到证明负担规则及其解释。基于分析清晰性的考虑,阿列克西将它们相对剥离开,并主要对第三类前提进行了讨论。因而,我们应当留意,对于完整的法律推理,下面的分析也只是一种对其核心部分的展示,而远非全部内容。
以阿列克斯认为最重要的一组论证图示——解释规准——为例,展示法律论辩如何处理规范冲突。当遇到语义模糊的时候,由规范R和语用规则W,就得出“通过W对R的解释”的规范R’。在出现几种不同解释论述的时候,如何处理呢?一方面,只宣称解释与文义、立法者意图或规范的目的相一致,是不够的。根据饱和原则(J.6),一定形式的论述,只有当其包含所有属于该形式的前提条件时才是完全的。另一方面,权衡规则(J.8)指出,最终必须根据权衡轻重的规则来加以确定。
规范冲突可能出现下列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当事人双方指向不同的法律规则(并解释),那么最终将出现规则与规则抵触的状况。这时大抵有两种解决方式:⑴根据规则冲突法则处理,譬如上位法优先、新法优于旧法、特殊法优于普通法;⑵出现碰撞漏洞,亦即无法根据规则冲突法则解决的,就需要法官提出新的方案——法律续造,这就可能以某个法律原则为起点,或者根据类比推理重新开启论辩阶段。
第二种情况,如果当事人双方根据同一条法律规则给出不同的解释论述,或者得出不同法律效果,那么就需要权衡各自论述的分量。同一法律规则的解释出现多值,究其背后的“论据”,一般都可归因于法律原则P1、P2,譬如文义解释重视法律的确定性,目的解释强调某种法益,等等。当然,为了确保论辩首先受现行法之约束,法律的文义或立法者意图优位(J.7)。这样,根据原则的适用形式予以权衡:
第三种情况,如果双方当事人,一方提出法律规则的论述N1,另一方提出法律原则的论述P2,则会出现规则与原则冲突的情况。法律原则的适用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它也必须顾及与之冲突的其他原则和规则。如果规则N1背后的支持原则为Pn,更复杂的情况还要顾及N1背后可能出现的多个相矛盾的原则Pn1、Pn2(假设Pn1优于Pn2),以及N1规则安定性分量原则Pf。这样,得出权衡公式:
显然,面对当事人双方的分歧,主要运用权衡的重力公式来确定各类冲突的优先性关系。也就是说,通过比较相抵触的规范性论据之间的相对分量,来确定它们在个案中的优先性。
(四)结果重构
当最优方案出现,应当要求法官将其重构为符合形式逻辑的判决,使得裁判结果以合乎法律规范和演绎推理的样式呈现出来,以增强法律发挥作用的真实感和司法裁判的安定性。因为,“作为司法判决成功证立的最低要求,判决被要求这样重构:它可以从作为理由被引证的论断与作为先决条件的论断中一起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这些论断必须是相互不矛盾的(从互相矛盾的前提中可推出任何结论[ex falso quodlibet]”[2]7。
(五)法律论辩
法律论辩,就是在每一个争点展开对话或者论证。“我们把若干论证联结在一起构成的论证链叫做论辩(argumentation)。论辩是在对话中为了某个目的而将一些论证联结起来的动态过程”[17]39。这意味着,法官既要关注当事人双方的“局部交锋”,也要评估完整的论证链条。这当然不是容易事。面对某个争点,当事人可以选取多种论证方式,既可以诉诸法律解释,也可以同时诉诸判例、法教义学等等。这样就可能形成多项论证同时支持其主张的情形(当事人总希望提出多的论据支持其主张)。如此一来,双方论据的对抗就变得十分复杂,例如在复式型论辩,击败其中一个论据,并不意味着其主张不能成立;在协同型论辩中,首先需要确定对方多个论据各自的分量,以便对最重要的展开攻击[18]237。
[1] 焦宝乾.法的发现与证立[J].法学研究,2005(5).
[2] (德)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M].朱光,雷磊,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3] 季卫东.“应然”与“实然”的制度性结合[M]//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 雷磊.法律推理基本形式的结构分析[J].法学研究,2009(4).
[5] 拉里·亚历山大,肯尼斯·克雷斯.反对法律原则[M]//安德雷·马默.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张卓明,徐宗立,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 (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M].强世功,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7] (意)乔瓦尼·萨尔托尔.法律推理:法律的认知路径[M].汪习根,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8]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9] (加)道格拉斯·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M].梁庆寅,熊明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10] 武宏志.论式:法律逻辑研究的新方向[J].政法论丛,2011(6).
[11] (荷)弗兰斯·凡·爱默伦,斯诺克·汉克曼斯.论辩:通向批判性思维之路[M].熊明辉,赵艺,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
[12] 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3] (荷)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张其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 雷磊.法律推理基本形式的结构分析[J].法学研究,2009(4).
[15]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6]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7] 武宏志,周建武.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8] 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胡 晓
2015-01-10
2014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项目编号:14HBZ008)。
朱政(1980- ),男,江苏南京人,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方法论、法社会学。
D910.1
A
1004-941(2015)02-007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