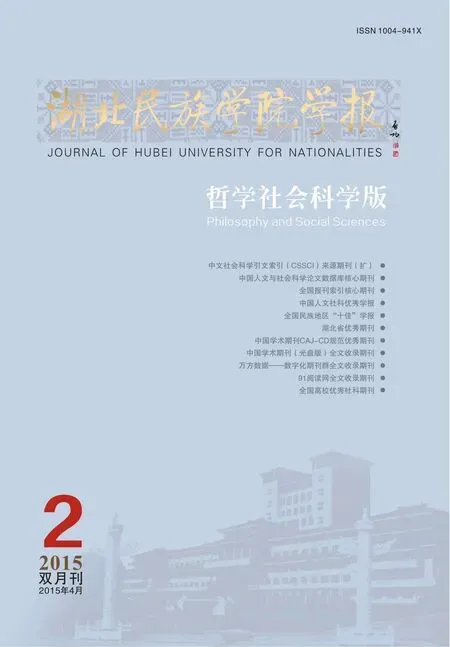土家族神歌的宗教功能流变刍议
陈宇京
(1.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北京 100031)
土家族神歌的宗教功能流变刍议
陈宇京1,2
(1.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北京 100031)
土家族神歌是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事象之一,原初的土家族神歌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极强的宗教功能,随着人文历史的衍进发展,土家族神歌的文化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土家族巫傩神歌的个案解析,可以发现土家族神歌的文化功能,有着从族体神灵祭祀到与宗室家先祭拜并行、从合族禳灾祈福的神圣宇宙普泛到日常劳动生产空间等具体流变过程。
土家族;神歌;文化功能
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神歌”,有狭义和广义两类。就“神歌”的狭义而言,最初专指川南“巫门起教”①巫门起教:川南地区巫教门派之一。在所设“还愿”、“陪神”等武坛法事活动中的专用歌、乐、鼓、舞等综合艺术表现形式,因当地人称其为“神歌”而得名。就“神歌”的广义而言,则主要是指各种神灵祭祀类传统文化活动中,以歌、乐、鼓、舞等为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浓郁宗教色彩和祭祀功能倾向的歌舞等具体文化事象及其综合表现形式。
古往今来,土家族神歌承载了众多神灵信仰的实质性内容,并因而成为了土家族民族精神的生发元点之一。由此可见,神歌既是土家族宗教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文化事象,又是土家人藉此以达天庭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历时传承久远、地域跨度广阔的特征,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专题。
一、土家族神歌的宗教功能
土家族宗教文化中,作为传统乐舞文化事象的“神歌”,具有形态芜杂的特征。根据其具体艺术外化形式,土家族神歌具有专指和泛指两个层面的概念内涵。就其专指意义而言,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土家族宗教文化活动中,单用人声演绎或阐释具有一定宗教意蕴的文辞内容的纯粹声乐形式;就其泛指意义而言,则是指那些根据宗教仪礼所需,将人声、器乐与肢体语言融于一体如麻舞歌、梯玛舞(或端公舞)等综合性较强的乐舞文化。由于分类依据不一样,因而土家族神歌的名称、种类也有差异,例如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身份,可以将其分为梯玛神歌、道师神歌、端公神歌等;根据不同的题材主旨,可以将其分为梯玛神歌、创世神歌等;根据不同的生发空间,可以将其分为巫傩神歌、农事神歌等。据此可以发现土家族神歌的普遍性特征,即说、歌、乐、舞等综合艺术表现形式耦合一体,巫、祀、仪、法等宗教仪礼场合为其文化宇宙。总体而言,土家族神歌的宗教功能可从讲说族源和劝世和谐的教义规约、天地神灵与普通百姓间的交通媒介等两个方面略窥一斑。
(一)族源讲说和劝世和睦的教义规约
土家族的创世神歌,是指以梯玛类职业巫觋为传承主体、以口耳相传为主要手段、以讲述天地山川等客观世界由来、人世男女脉系族源为主要内容的神歌。土家族创世神歌的文辞内容主题芜杂、形式多样。尽管如此,仔细考察所有讲述客观世界与人脉族源等土家族创世神歌的文辞内容,可以发现其中有两个重要命题,一是“鸿钧老祖传三教,盘古三皇还在后”的世界由来与人文渊源,可归纳整理为“天人之本”,二是“洪水泡天人世灭,夫妻本是同根生”的教义信条与劝世和睦的主旨规约,可概括总结为“为人之道”。
1.天人之本——世界由来和人文序列的述说
土家人有很多与创世神话相关的神歌,主要讲述的是天地山川等客观世界的由来,以及人文教化的渊源传承,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与重庆黔江区交接的小南海区域至今仍有传唱的《鸿钧老祖歌》:
(说)鸿钧(那个)老祖(他)传三(那个)教(啊),顿时(那个)一气化(呀么)化三青。盘古(那个)开天不(呀么)不记所(呀),鸿钧老祖还(呀)在先,后有(那个)盘古开天地(哟),才有(那)天地人三皇。*《鸿钧老祖歌》,讲唱人:张明祥(时年72岁),居住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小南海地区,田野调查时间:2006年7月,记录人:陈宇京。
这首《鸿钧老祖歌》传唱的是土家族的人类始源神话和文明始源。与汉族创世神话中的盘古开天辟地故事不一样,土家人认为鸿钧老祖才是打开混沌天地的第一人,人类的文明教化起始于鸿钧老祖传下的三教。
在湘西北保靖县,也留存着上述人物不同,但在创世方面内容大致相近的土家创世歌,例如湘西当地著名梯玛向宏清用土家语唱的一首神歌:
没有天,梦一般昏沉,[啊尼!]没有地啊,梦一般混沌。没有白天,梦一般什么也辨不明。没有夜晚啊,梦一般什么也分不清,[啊尼!]绕巴涅啊,他把树搬上肩,惹巴涅啊,她把竹扛上身。[那尼!]大树连蔸,[那尼!]大竹盘根。传说大鹰也来帮忙,传说大猫也来相助。大树飞起做支柱,大竹飞起把天撑,大鹰展翅横起身,大猫伸脚站的稳。[啊尼!]天开地也开啊,天成地也成。*董珞.巴风土韵——土家文化源流解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86-87.
仔细考察《鸿钧老祖歌》及这首湘西土家族创世神歌可以发现,在纵向的历时维度上,土家族创世神话中的鸿钧老祖,比汉族开天传说中的盘古及“天地人三皇”要早;而通过辛勤劳动达成“天开地也开,天成地也成”的绕巴涅与惹巴涅创世的神歌内容,在一定意义层面来看,也与汉族盘古开天的神话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此而言,土家族创世神歌中,不论是鸿钧老祖还是绕巴涅与惹巴涅的创世之举,其文化学意义在于讲述了土家人心目中天地山川等外部客观自然世界的由来,以及“鸿钧老祖”-“三教三青”-“盘古开天”-“天地人三皇”的时间序列。关于人类外部自然世界是否鸿钧老祖所创,以及天地之分是否源于绕巴涅与惹巴涅的辛勤劳动等宇宙起源问题,已有近现代天文、地理等自然学科的科学论断,此处毋庸妄言。尽管如此,土家族创世神歌中所蕴涵的人文信息,却必须引起包括民族音乐学在内的整个文化人类学界的重视,因为它至少向人们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支脉之一,在时间的纵向历时过程中,土家族的传统文化绝不比以汉族为创造主体的传统文化迟,于今天的文化人类学界而言,我们至多只能说,在空间的横向发展方位上,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即土家族传统文化是山地河谷文化,汉族文化是中原黄土文化。
2.为人之道——夫妻同根暨劝世和谐的要义
土家族宗教祭祀传统宇宙中,存在大量以洪水泡天、人类再造等为文辞内容主体的创世神歌,它们通过隐形于这一母题中的、或兄妹或姐弟间的通婚产诞行为,达成劝诫人世男女超脱血缘俗见、和谐共生共荣的教义目的。
土家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类初祖的神话故事,有很多种表述方式,所有这些表述方式下的故事梗概大同小异——洪水泡天之后,万物萧条,人类仅剩藏于巨型葫芦中的一对兄妹,为延续香火,有菩萨作合兄妹成婚,但兄妹碍于血缘系出一脉的人伦事实,不愿苟合,菩萨竭力撮合,并决定以两山头两块磨石分别滚下能否合成完整一付的方式决定是否联姻,在菩萨的法力作用下,两块磨石滚下山头,上下对合,天衣无缝。但兄妹二人仍觉与人伦之理不合,尚有心理障碍,为使二人完成延续人间烟火的大任,菩萨再次以天神形象出现,对二人进行说教,最后约定兄妹二人各据山头并焚香,若香烟于空中合成一股,便认可菩萨的说教,并结成婚配。当然,菩萨的能力是无限的,二人在山头点燃香火,袅袅细烟升空,弯曲之中,点燃了人类得以延续的烟火,两股香烟终于在空中交织在一起,合成人间情意最美丽的图画。经过种种天意注定、命中该合的赌注求证之后,兄妹二人终于成婚,并生子养女,人类也因此繁衍至今。
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与重庆黔江区交接的小南海区域,至今仍然流传的土家族神歌中,就有一首以此内容为主体的《初祖歌》:“天地相合生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蛇相交生金龙,兄妹相交生后人。”
结合前述土家族洪水泡天及人种再造的创世神话,考察这首《初祖歌》的歌词,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发现两个方面的信息。
首先,是人类初祖的同根性。不管这两首神歌道出了土家族口承文化中怎样的人类起源,即渝东北与鄂西的土家族认为人类始源为“兄妹相交生后人”,湘西土家族认为人类始源乃绕巴涅(弟)与惹巴涅(姐)所为。直至当下,土家族人口承文化中的人类初祖,应是同出一个母体的男女。
其次,是土家族宗教祭祀仪礼音声的多元性。上述土家族《初祖歌》歌词中“佛祖”、“老君”两个宗教人物形象的出现,说明了土家族原始宗教祭祀仪式歌乐已不单纯,而是掺合了佛祖、老君之后的多种外来人为宗教歌乐的混融形态,可见梯玛神歌具有主动吸纳、兼容并蓄的人文特质。
上述两例梯玛神歌中的土家族创世主角,是一母所生的兄妹(或姐弟)。将土家族的人类始源神歌,与西方基督教《圣经·创世纪》的人类始祖说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如下三种本质性区别。
第一,种族繁衍血脉分支关系不一。从人类生衍繁殖的原生系统而言,土家族的男女祖先源出一母,兄妹间有源于相同血脉的分支并置关系,既有先后之分的表征,也有血缘一脉的本质,因而有“男女关系生而平等”的内蕴。但西方基督教创世神话中的亚当夏娃,因为夏娃乃亚当肋骨所成,其血脉缘于亚当之体,因而,夏娃的一切都是亚当身体的衍生之物,他们血脉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分支所属关系,其内在意蕴可以定性定格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物。
第二,人种衍生意愿的原点不一。作为人类繁衍之源,土家族的祖先是一对亲生兄妹,兄妹之间的情感沟通,必须合乎正常的人伦规范,尽管有菩萨的姻缘撮合之举,但他们的本真心意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突破传统观念中的人伦道德樊篱。因此,土家祖先创世意愿的原点,并非土家兄妹的意识情感自觉,而是菩萨的权威强迫。与此相反,西方基督教的人类起源,是原本赤身裸体生活在无忧园(伊甸园)的亚当与夏娃,因夏娃听从了蛇的怂恿,吃了能知羞耻的禁果,以至于被罚出园,并与亚当结合,从此诞下人类。可见,西方基督教中人类初祖交媾产诞的意识原点,是人类在神或神物(如蛇)指引下的一种理性自觉。
第三,担任人类再创天职的具体人物不一。兄妹(或姐弟)作为土家族口承文化中的人类初祖,是大洪荒发生之后的人类仅存硕果,血源同母一体的男女结合,是为了大洪荒之后人间烟火的繁衍。西方《圣经》中洪水泡天之后,担任人类再创任务的是诺亚一家,既包括诺亚夫妇,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尽管也身负人种延续大任,但血源各有所属。
综上所述,土家族创世神歌中的“初祖”,与创世神话故事中洪水泡天后人种再造过程中的主角之间,虽有“兄妹说”和“姐弟说”之别,但二者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土家族创世神话故事中,人类初祖的血脉源出一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土家族的本族宗教仅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阶段,族体内部所有有形的人为宗教都是外来宗教本土化了的结果,但由于土家族《初祖歌》可以出现在各种宗教祭祀的特定宇宙之中,因而,土家族创世神歌中的兄妹(或姐弟)人类再造说,对土家族万世子孙的夫妻关系等日常人际交往而言,具有约定俗成的教义规约等宗法作用,例如:土家族的日常生活中,不论实际年龄,不论故交新识,土家男人都将已婚女性统称为“姐”,将未婚成年女性统称为“幺妹儿”,这种口称习俗的根源,便可以追溯到人类初祖的“兄妹说”和“姐弟说”。同时,这种口承习俗也向人们呈示了一个极具土家人文特质的人伦理论前提,即在土家人的眼中,夫妻本是姐与弟,百年前世一母生。夫妻间既然血源相同、连理同枝,在实际生活中,就应该生活情趣一致、价值取向一致,所谓“夫妻同心”。
(二)天地神灵与普通族民间的交通媒介
“梯玛”是截至当下所有土家族职业巫觋称名中历时最为久远、最具土家人文特色的称谓,因此,我们不妨将由梯玛、道师、端公等职业巫觋专司宗教祭祀仪礼的音声、乐舞等文化事象,统称为“梯玛神歌”。
总揽过去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结果可知,梯玛神歌“是最早产生的土家族歌谣的基本类型之一。在生存繁衍十分艰难的年代,土家族先民一方面认识到掌握劳动本领对于生存繁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从‘万物有灵’的观念出发,产生了原始巫术宗教观念,并试图沟通神灵,借助外在神秘力量来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也因此成为土家族先民谋求生存繁衍的一大途径。与此同时,作为具有与神灵沟通功能的一门特殊语言,梯玛祝福神歌也应运而生。……由于神歌是以神灵为吟唱对象,所以现实生活气息较少,极富浪漫色彩,想象丰富异常,格调神奇。”*陈素娥著.诗性的湘西[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52.由此可见,“梯玛神歌”是土家族传统宗教祭祀文化活动中的重要事象之一,其文化功能的主要表现,是通天告地、晓谕神灵,满足族体或族民祈福禳灾的生存目的等。
在土家族聚居区域内、以土家族民为主体的各族原著民中,“梯玛”又叫“土老司”,他们“是土家族民间的职业宗教者,也是土家族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播者,他们在民间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凡民间的各种巫祀活动均由他们主持,神歌便是他们沟通神灵的特殊媒介”。*陈素娥著.诗性的湘西[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52.
在各种土家族民间仪典、祭祀性质的社会活动场合之中,作为职业歌师代表的“梯玛”,起着至关重要的仪式组织和主持的作用。由于各地“梯玛”兼承采药行医的医者行当,其中也不乏行医高手,清朝乾隆《永顺府志·风俗志》卷十中就对此有过专门记载,说土家梯玛“师巫击鼓、摇铃、卜竹篙以祀,祷告土人猎鱼,病则无医,惟性中羊旺”。梯玛也因此成为了土家人眼中“上能通天,下能达地”、神-人-鬼之间的中介者。因此,梯玛既是人中神圣,又是天神在凡间的肉身显形。作为人中神圣,他们了解人类的酸甜苦辣;作为天神的凡间肉身,他们给予人类欢愉苦痛的精神解脱。于是,梯玛融神性与人格于一体,凡在他们应该出现的各种社会场合中,定会弃平日行装于它处。他们头戴凤冠,身着八幅罗裙,一手持八宝铜铃,一手拿九环法刀,脚登白底黑帮手纳布鞋,在纸糊篾扎的神坛之上,在香烟缭绕的氛围之中,在火烛明灭的意念之间,在芸芸众生俯首叩拜之时,在锣、鼓、唢呐、法螺等法器音乐伴奏之下,梯玛们口中念念有词、手头左右挥舞、身法进退自如,他们或望空长歌替众生祈祷,神态庄重、潜心礼神;或绕物徘徊仿效神迹,且歌且舞、喧念神谕。
我们说,土家族聚居地区多为喀斯特地形地貌的山地河谷,决定了土家族传统文化浓郁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人文特征。作为土家族原始宗教文化典型的“梯玛神歌”,具有驱傩迎神、敬天奉地、祭亡祀灵、请神还愿、跳神求雨、求福禳灾、祈祷六畜兴旺、歌赞五谷丰登、叩谢家业兴盛、祝诵人丁兴旺等诸多宗教功能。由此可以发现,梯玛神歌的本质是物我一体、万物有灵且同情、万物生命一体且互化等天人关系理念基础上的土家族宗教文化内涵,它是土家人精神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定位的综合性文化活动。根据原始宗教祭祀具有早期人类所有愿景综合的功利性质,我们可以说,梯玛神歌不仅在土家人的个体精神生活中具有引领导向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对土家人的族体意识形态产生提炼升华的动力性功能作用。因此,梯玛神歌的内涵不仅限于梯玛的巫傩法事行为模式,而且还应该包括土家人的族体语言模式和族体思想模式。所有这些族体模式均建立在土家人对于超人力范围物事的神秘性认知及经验性总结,并进而表现为对梯玛作为神灵代言人地位的绝对服从,以及对梯玛虔诚崇奉的族体信念。
梯玛神歌本体形式的种类很多,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可以分解为音乐、舞蹈、诗歌、仪典等多个组成部分,但在梯玛神歌中,音乐、舞蹈、诗歌、仪典等任何单一艺术本体的文化人类学特征,都不能完全替代梯玛神歌的整体。也就是说,梯玛神歌本身是一种集说、歌、舞、乐等艺术本体,以及巫、祀、仪、法等宗教文化质素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事象。因此,凡梯玛、土老司、端公、巫师等职业巫觋出现的各种重要社会仪礼场合中,宗教祭祀性质的神歌、神舞、神乐,以及与之相应的祭文献辞,便因其活动行为主体、活动功利目的、活动仪礼规范的需要,在应该出现的文化空间中得到适时运用。据此可知,梯玛神歌的具体形态,与土家族宗教祭祀活动的仪式环节及具体进程之间,是一种互相引领、互为依托的关系。
由此可见,土家族神歌是由梯玛组织、主持并表演,融说、歌、舞、乐等艺术形态于巫、祀、仪、礼等法事空间之中,综合性质极为明显的土家族宗教祭祀文化事象之一,其实质主要体现在土家族神歌的宗教功能价值或意义层面之上,而此实质又集中表现在梯玛类职业巫觋身份的双重性上。就梯玛类职业巫觋的身份双重性而言,一指作为普通族民代言人的梯玛,可以向上即向天地神灵呈传普通族民禳灾祈福的生活愿景;二指作为神灵鬼怪信使的梯玛,可以向下即向凡世肉身传递天地神灵护佑责罚的意旨。总之,土家族神歌的重要宗教功能之一,就在于它是神灵鬼怪与普通族民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媒介和通道,它所实现的目标是俗体肉身的生活愿景,解决的是普通族民最简单的生活质量问题。
二、土家族神歌的世俗化
就宗教祭祀文化的本质而言,是人们把“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种人世通则,用之于理想的神灵身上,表述“苦心付出之后,便应有良好回报”的心理愿景。这也是宗教祭祀的根本心理动因。所以,从本质上看,宗教祭祀是由诸多血肉之躯对于图腾或神灵的讨好与收买,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心理关系,由己及神,推广到人-神交流沟通过程中,认为神受人奉之后,必定回报人类欲求的活动。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功利心性的逐渐浮躁,在族体宗教祭祀宇宙中以求族体利益为本心的土家族神歌,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以及等级利益集团的出现,人们诉之于神的思想寄托或者其他功利性追求的教义宣喧,逐渐定型为巫觋称谓、宇宙质素、功利目的等渐次多元的世俗化格局。
(一)巫觋称谓的多元化
土家族聚居地区,各类神歌的人声行为主体均以梯玛为首。《论语》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送。”儒家称其术为异端,所以,明清以后,汉风渐长,人们也多将土家族梯玛、土老司或其他善操巫术之人,以汉家儒学正统为据,称之为“端公”。可见,“端公”是土家族梯玛、土老司等职业巫觋的局外他称而非土家族自称。
正如前述,土家族宗教文化中的“道师”、“端公”等称谓,实际上是土家族梯玛从族体精神领袖的神坛之主,降格到红尘俗世的宗教文化主体的世俗化表现。因此,随着“道师”、“端公”等世俗化了的巫觋出现在土家族宗教祭祀仪礼的过程中,梯玛、土老司、道师、端公等职业巫觋在土家族宗教文化中的角色,就不仅仅限于族体神灵祭祀仪礼的组织者与主持人了,他们还要在春祭禾苗灵怪、秋祭山川圣主、年祭社稷仙道、给人治病消灾等俗世斋拜傩仪中,担当起自己的巫傩使命。因此,他们不仅要为族体神灵唱诵圣歌,更要为宗室家先歌乐舞蹈。当他们为普通宗室神灵歌唱舞蹈时,原先仅用于族体神灵祭祀的神歌,便不可避免的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二)宇宙质素的多元化
当梯玛、土老司等职业歌师在宗室家先的祭祀仪礼场合现身后,他们所唱神歌的内容主题,又可分为“神曲”和“俗曲”两大类。“神曲”是梯玛们将用于族体神灵祭祀的歌乐,在宗室家先祭祀仪礼中的变通形式,而“俗曲”则是梯玛们吸纳和运用民间艺术,并用之于神灵祭祀仪礼的形式。“神曲”在族民宗室家先祭祀仪礼空间中的出现,是梯玛神歌世俗化的具体表现,而“俗曲”的出现,则进一步加快了梯玛神歌的世俗化进程。从此,梯玛们身穿法衣,手执八宝铜铃,脚踏九宫八卦,边念咒边施法,边歌唱边舞蹈,出现在各种层级的宗教祭祀仪礼场合之中,族体神灵与宗室神灵之间的界限也被进一步模糊。以往族体神灵祭祀仪礼场合中的专用歌唱形式如独唱、对唱、齐唱,也被广泛运用到了宗室家先的祭祀仪礼之中;梯玛们的神歌音乐因为对于民间艺术形式的有效吸纳,也使得旋律更显优美、节奏感更加规整强烈,与之相伴的舞蹈动作也更加粗犷豪放。
当族体神灵祭祀仪礼场合中的专用神歌世俗化为“神曲”和“俗曲”之后,土家族各巫傩教派也开始了设“坛”为普通族民酬神还愿、祈福禳灾的俗世之旅。世俗化了的巫傩活动多在秋后至岁末举行,有的还将其与相关内容的戏剧活动与法事活动融为一体。根据当时愿欠东家的不同家境以及家庭成员的意愿,梯玛、土老司、端公等掌坛法师在主持巫傩仪礼时,也开始了傩坛的文坛、武坛之分。
文坛、武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仪式音声结构以及是否运用舞蹈类肢体语言叙事这两个层面。文坛一般多用于酬神、还愿、祈福,因祭文献辞篇幅较长,故念诵花费时间较长,从祭祀仪式音声的结构层面来看,梯玛代“愿欠”主东还愿祈福的人声,在时间分配上占绝大比例,其他如鼓、锣、钵等器乐以及法螺、牛角等法器,都仅限于间或而为,较少用舞蹈类肢体语言叙事。与之相对,武坛多用于禳灾、驱鬼、逐疫,在土家人的观念中,灾祸疫病多为凶灵鬼怪所为,这类鬼怪脾气乖张、暴躁,梯玛驱鬼逐疫时,需要与这类冥界中的凶灵恶魂进行打斗,因而,从祭祀仪式音声的结构层面来看,鼓、锣、钵等器乐以及法螺、牛角等法器声音在时间分配上所占比例较大,多用舞蹈类肢体语言模拟与凶灵恶魂打斗之姿,因而,武坛的整体艺术形式粗犷彪悍、挥合有致,观赏性较强。总括而言,不论文坛还是武坛,在具体的法事活动中,都有“神歌”的人声演绎形式出现。
根据当下诸多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调查资料可知,世俗化了的神歌,已很少有人专门搭建巫傩礼台,转而多在普通族民的家院中举行。一般情况下,普通族民家中出了不吉利之事(如孩子不好带、家中人有病遇灾等),大多会请梯玛提前看好日期,以便杀牲祭祀。届时,梯玛(或土老司、道师、端公)等职业歌师很远就会吹起法器牛角,“愿欠”主东及家族人等定会闻声前往迎接。一旦梯玛进门,东家就会把事先准备用于祭祀的三牲(多为猪、牛、羊)牵到院坝之中,东家族人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朋好友将其团团围住,由梯玛向三牲神灵念诵祭文,并企望它们的恩准。祭文念完并火化为灰,梯玛便代三牲神灵发旨——因主东“愿欠”未了,鉴于“还愿”诚心,可将三牲用作牺牲。经此一轮仪式环节之后,东家及家族人等围观杀牲,并敬奉土王菩萨及众位家先。待牺牲做熟之后,还要用一桌十碗的排场再次敬奉列祖列宗、诸路神灵鬼怪。敬奉期间,梯玛必须念经,恭请各路神仙享用。此时梯玛做法,东家一应亲朋好友随之跪于诸位神灵的牌位前,梯玛则头戴五幅凤冠,身穿八幅罗裙、脚踏马蹄裟鞋,右手拿九环神刀四方玩转,左手执八宝铜铃上下摇晃,在堂屋里供奉的土王菩萨塑像及诸位先祖神灵牌位前,合着其他歌师们帮场锣鼓响器的节奏节拍,进退有方,边念边跳,等祭祀土王菩萨及家先的歌功颂德之词唱到一定时候之后,就开始了神歌的演唱。神歌的歌词内容,除用于供奉土王菩萨和家先的祭祀经文外,还可根据东家的愿欠内容、仪式的具体场合,以及东家欲求目的等,取庆贺丰收、发财致富、四季平安、逢凶化吉之意。
(三)功利目的的多元化
神歌世俗化的主要表现,除了族体专用神歌用于宗室家先神灵祭祀仪礼外,还有许多很重要的表现,如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大量接纳、俗世人情成为歌词内容主题等,这里以重庆市酉水流域内于土家人平日生活或者丧事闹夜中流传的一首神歌《郎打哨子应过沟》作例:
郎打哨子应过沟,娇妹妹站在炉灶烘背后。娇妹听得郎哨子,瓢儿刷把一起丢,娘问女儿你冒啥子火,湿柴不燃烟子鼽。
就这首《浪打哨子应过沟》神歌而言,其世俗化的表征有两点,一是神歌艺术表现形式中出现了日常生活中传递信息的“哨子”;二是歌词内容主题关于男女爱情的取向。这首神歌中有许多极富日常生活情趣且尽其形象生动的描写。土家人口中的“哨子”种类很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当地土著居民弯曲手指放于口中吹出的响声,此中能人高手,任意手指放于口中均能作声,只要是他所听过的任何动物声音,特别是各种鸟鸣,他都能运用他所掌握的这种吹奏本领,将其表现得惟妙惟肖。直至今天,在许多通讯工具不发达的偏远山区,仍有人用此类哨声作为彼此之间信号传递的常用手段,具有较强的话语功能;二为“打呜呼儿”,即利用嗓音发出音区极高、音响较强的人声。这种声音常常具备假声的高度和真声的威力,因其发生体的独特音色及各人爱好不一导致的个性而容易辨识,大多用于较远距离如山头、沟壑之间的呼唤和信息传递。土家族聚居区域内,这种“哨子”式的“打呜呼儿”,常被刚刚步入热恋殿堂的男性青年约会幺妹儿,因种种原因,暂时不愿意女方父母太早知道时广泛采用。同样,这种“哨子”因其邀约恋人的信号作用,具有传情达意等明显的话语功能。本歌曲中的“哨子”随取何意均可,因其具备的话语功能,也就具备了传递信息的作用。通过文辞可以发现:歌曲中的“郎”与“娇妹妹”之间,肯定已经有了心灵之约,否则,“娇妹妹”会与“娘”等局外人一样,单凭一声哨子是分辨不出谁是哨子的主人的。也正因为辨别出了哨声的主人,幺妹儿才会出乎娘意料的“瓢儿刷把一起丢”,以及不得不对娘作“湿柴不燃烟子鼽”的搪塞和遮掩。
其实,就这首神歌而言,只是土家族神歌功利目的多元化体系的一个代表。这类神歌在土家族中可以将其用“XX问XX你XXXX”格式化,例如在土家族聚居区域内广泛流传,且为音乐学界特别是民族声乐界广为人知的《高高山上一树槐》即是此类神歌的典型:“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你望啥子(唉),我望槐花几时开?”
由此不禁有问,既有土家族神歌功利目的多元化“XX问XX你XXXX”的格式化结果,其本真源自何处?是否有迹可寻?凡此种种,其实在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区,特别是酉水流域内的土家梯玛神歌中,都能找到形迹几近模糊但稍加甄别即可明了的原样。以下即笔者2008年暑期在湖南省保靖县田野调查时,酉水流域中段陡滩村梯玛向文德(时年75岁)讲唱的一首神歌(后文称“向氏神歌”):
隔山叫,隔水呜,千呼万呼鸿钧太上老祖,(急急如律令),奉请天上栽的桫椤树,再求天上住的雷公和电母。我问主东你着啥子忙,我望天神许百福。
据向文德老人解释,之所以“向氏神歌”文辞以祈祷祭告酉水河神,特别是包括主控陡滩水流等人世福祸灾变的鸿钧太上老祖、雷公、电母天神,只因酉水至此,水陡滩急,漩涡众多,暗流涌动,特别是夏天山洪暴发之际,情势更为险恶,以致常有人于此丧命。因此,旧时常有专门祭告天神平水、缓滩赐福的专门祭祀仪式,此神歌即这类仪式的主要曲目。
通过《郎打哨子应过沟》、《我望槐花几时开》以及“向氏神歌”的文辞结构比较,可以发现,三者间除“向氏神歌”多了“急急如律令”句外,其他几乎没有区别。若言三者差异,则在于“向氏神歌”的仪式专用性,与其他两首神歌的世俗普泛性的两分结果。与之相应,神歌在土家人族体生活中从神坛到红尘的功利目的多元化情势,也因此可见一斑。
除了上述实例以外,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境内还流传着另外一种世俗化了的神歌——“麻舞调”(也叫“火麻田”)。“麻舞”是职业巫觋应当地族民还求子愿的要求,在晚上演绎的一种集歌、乐、舞一体的综合仪礼形式。尽管麻舞的动作有着严格的程序:砍山-烧山-撒麻种-管理(打炮吓鸟兽)-刮麻-收捆背-煮麻-洗麻-破麻-接麻-织布-搭桥等,但因其内容的生活气息浓郁,因而,它的功利目的便已经未仅止于娱神这一纯粹目的,而是超越提升为神人共娱的文化事象了。
神歌的本初目的是陪神娱神,有把天地神灵甚而象征鬼神的“茅人”(茅草扎的草人)唱得“高兴”,以遂消灾弥祸本意的功利讲究。但是,世俗化后的神歌,其歌唱内容便不一定局限于“神”的赞誉了。一般情况下,除梯玛、土老司、道师、端公等职业巫觋担纲的“包头匠”*包头匠:在土家族句句区域内的神歌类具体演唱活动中,因其具有起头领唱定调的功能意义,因而,土家人也戏称其为“包头匠”。唱极少与神有关的内容以外,其余的神歌(包括陪坐在茅人周围的信众所唱的神歌等),则多以唱情逗趣或历史传说故事为主,其内容绝大部分均与“神”无关。后来,“神歌”这一音乐体裁形式被土家族聚居区域内各族人民广泛用于野外田间的劳动生活之中,内容更发生了向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变化和过渡,“神歌”也随之自然演化为类似汉族山歌的歌种之一。
当然,世俗化了的“神歌”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即在“神歌”专司神灵祭祀仪礼的功能基础上,同时还兼具了劳动过程中的解乏提神功能。例如重庆市大足县境内关于“平腔神歌”的一种流行解释,就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当地人称:过去工业不发达时,在大足县西山一带的土煤窑、土纸作坊和川南盛产夏布的隆昌麻布作坊,曾大量流传盛行过“神歌”,并主要将神歌演唱用于劳动过程之中,如“大足平腔神歌”多为土纸作坊的工人在室内劳动时所唱;“隆昌麻布神歌”则是麻布作坊工人在生产麻布时演唱的歌曲等等。这些工厂、作坊等劳动场合中的劳动条件异常艰苦,唱“神歌”的目的是为娱人,即“提神”,因而,当地人将这种歌曲也称之为“神歌”。
另外,土家人聚居的武陵山区,素有驱傩迎神、“信巫鬼,重淫祀”的人文传统。由此可以发现:在土家传统风俗中,土家人治病、消灾、求子、保寿都要请梯玛施法,如打扫屋子要请梯玛“跳神”,以保一年无灾无难、平安无事;无子的青壮年夫妇要请梯玛“冲傩”,许愿还愿以求生子;生了病要“冲傩消灾”,以求病愈;家里逢凶事要“开红山”,化凶为吉;老人生日要“冲寿傩”,祈求高寿;“干贵”小孩的人家,在孩子十二岁以前要打“十二太保”、“跳家关”、“保关煞”,以保小孩不受灾生病、易长成人。这些活动都与土家傩愿歌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神歌出现在非专门宗教祭祀宇宙而是纯粹劳动生产空间的情况,是神歌专用于祭祀仪礼空间这一崇高地位的完全降格和贬抑。这种降格和贬抑的过程,实际上是消解土家族神歌的神性,使凡间人性得到彻底关怀的世俗化过程。由此可见,无论何种形态的神歌,就其演唱形式而言,既可以是一人独唱,也可以是两人或多人对唱,更可以发展成为一领众和的重唱、合唱。就神歌的内容而言,随着氛围的渐趋热烈,神歌的主旨由“神性”、“鬼性”向“人性”渐变,直至最终达到凶灵恶神被逐、祖先圣灵附体、神-人共娱的狂欢高潮。就神歌内容的渐变思维空间而言,其变化途径为礼敬鬼神-请兵护坛-鬼神之舞-梯玛之舞-神灵附体-逐出凶灵(或神人沟通)-神人共欢。不管神歌以何种形式何种内容进行,也不管神歌内容所呈示的时空阴阳怎样变换,作为神-人-鬼中介的梯玛、土老司、端公等职业巫觋,始终承担着土家族祈福禳灾的心愿诉求重任,为创造土家人心中的美好生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精神引领作用。
三、结语
土家族的梯玛神歌,就是土家人面对万能的神灵,按照一定的仪礼规范,用实际行动向它致敬和献礼的综合文化事象。在这类对象具体、仪轨明晰的宗教祭祀文化活动中,人们以诚惶诚恐的心态向祭祀对象匍匐膜拜,他们借助梯玛、巫师、土老司、端公等职业巫觋已经掌握的相关仪典规范、行祭模式、祭文献词等,通过职业巫觋的祭辞文本、口头陈述、声乐器乐、肢体语言等具体诉求方式,使行祭之人的意愿上达神听,把俗世的愿景与神灵的意旨耦合,达成人心-神意终极吻合的境界,实现自然万物神灵均能给予人世凡间帮助的功利性目的,实现并满足凡夫俗子靠一己之力难以达成的终极愿望。
[1]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英)J·G·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3] (美)约翰·B·诺斯,等.人类的宗教[M].江熙泰,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4] 潘乃穆.潘光旦文集:第七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田青.中国宗教音乐[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6] 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4-09-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重大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项目编号:03JAZD760005);三峡大学求索基金重点项目“土家族传统乐舞文化美学研究”前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KJ2011EZ02)。
陈宇京(1970- ),男,土家族,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文化研究、少数民族乐舞文化美学。
J608
A
1004-941(2015)02-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