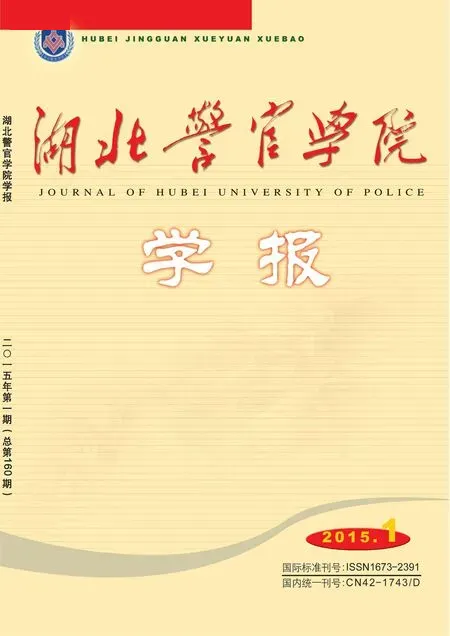民意“由刑制罪”之规范化探讨
民意“由刑制罪”之规范化探讨
王晓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在“以刑制罪”的理论框架下,民意经由规范化的转换,通过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的理论路径,对犯罪的认定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与制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化的民意在定罪体系中只能作补充性的、有限度的适用。
【关键词】民意规范化;以刑制罪;理论路径;有限适用
近年来,影响性诉讼案件不仅引起了刑法学研究者的争论,也引发了社会大众对于此问题的热议。此类案件最后的法律适用结论,大部分回应了社会舆论对其的质疑,甚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意味着“民意”通过某种理论进路对刑事法判案规则施加了某种微妙的影响,即民意通过规范化的理论通道影响或制约了犯罪的认定或刑罚的裁量。下面拟对这一法律现象进行探讨。
一、民意“由刑制罪”之可能性
刑事法中的影响性诉讼案件,一般是指,民众由于具体个案中所关涉的公共性、结构性的主题元素而对其加以特别关注的疑难案件。此时,对于某个或某类案件相同或相似的舆论倾向——民意,不是公民个体意见的简单累加,而是掺杂了伦理规范、公共秩序、法律见解等因素、变量的,经过提炼、加工甚或形塑的公众意见。“以刑制罪”,是在三个意义上来适用的:第一,以刑释罪。以刑释罪是指刑罚的严厉程度反过来制约构成要件的解释,它只适用于解释论层面,是作为刑法解释的指导规则而存在的。[1]第二,以刑定罪。犯罪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刑法既定的静态的刑罚体系和动态的刑罚适用及其实施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制约着司法者对具体危害行为性质的认定及其入罪与否的抉择。[2]第三,以(量)刑择罪。以(量)刑择罪是指从量刑的妥当性的基点出发,反过来考虑与裁量的相对妥当的刑罚相适应的构成要件是哪一个,从而反过头来考虑该定什么罪,这就是刑罚(量刑)对犯罪(定罪)的反向制约关系。[3]
有人认为,刑事司法的不可妥协性、刑事案件的专业化特征决定了民意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4]笔者认为,此论断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及立论基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首先,对于刑事司法的不可妥协性来说,该观点认为,既然作为“公意”的法律在立法环节已经给予了民众充分表达意愿的空间与强制性保障,那么在刑事司法中,就应严格照此执行,不可能、也不允许民意再侵蚀刑事法律历经法治洗礼所构建的权威,在此没有妥协的余地。然而,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是否如此呢?笔者认为非也。就近年来兴起并在司法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恢复性司法而言,作为其表征的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德国刑事协商制度、法国刑事和解制度等刑事理论、制度、程序,已经使刑事司法绝对不可妥协性的刚性规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赔偿及法官对处罚性要素的个案考量,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罪与刑、罪与罚的妥协甚至交换。也就是说,前述刑事司法的完全不可妥协性的理论前提已然立基不稳。
其次,对于刑事案件的专业化而言,法律事实的复杂化、案件判决的多元牵动性,决定了定罪量刑的专业化比单纯的民意裁决能够更全面、彻底地保障人权,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机能。但其绝对的、刚性的纯粹追求形式理性的特质,也可能造成个案的不公正或实质的不正义,这是由法律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刑事司法运作的过于封闭性引致的。对此,从司法系统之外吸纳非专业化的法律意见,来充实刑事法律过分专注形式理性而忽略实践理性的内核,就可以弱化刑事案件审理过度僵化的不足,其主要制度表现有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英国的治安法官制度、法国的参审制度、日本的裁判员制度等。这样,不仅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刑事法律的信赖及信仰,而且反驳了刑事司法黑箱运作的指责,实现了司法的民主化与职业化的精准对接。
如前所述,既然在刑法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上,民意可以影响、制约甚或决定刑事司法的特定走向及对个案的判定,那么就可以说,民意中可影响的“刑”的要素与以刑制罪中的“刑”存在某种规范性的交集。本来,刑法的社会防卫机能、刑罚目的之预防机能,就是法官定罪量刑时所参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犯罪的特征里面,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判定,也要考虑到民众对司法结论的理解能力及接受程度。从法治体系的宏观视野观察,国家凭借公权力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刑事制裁,正是对于民众呼唤良法美治所作出的法律回应与权力架构的调整。在司法机关、媒体、民意、当事人的两权(权利、权力)争夺影响与话语权的四方角力中,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及作为社会喉舌的媒体(包括自媒体形式)无疑更有优势,民意与当事人的权利诉求,只有通过上述两者发声与制度性的回应,才能对刑事司法的进程产生影响,其理论路径为当事人的权利诉求—媒体的推动—涉案民意的形成—公权力的司法回应。然而,公权力的司法回应,大部分是以对行为人的宣告刑为着力点的,因为民意质疑司法的原因之一,就是基于民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不信任,以及对于司法机关可能罪刑擅断的担忧。对行为人所判处的具体刑罚种类、刑罚幅度、刑罚执行方式,作为看得见的正义及体现刑罚报应性、预防性的主要表现形式,较之对罪行性质的认定,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此时,司法机关通过对所宣告刑罚的重新审视,在综合考量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目的、刑事个案具体犯罪构成的基础上,来实现对先前定罪或判罚的调整甚或修正。这样,民意通过刑罚的理论中介就与定罪体系联系在了一起。
二、民意“由刑制罪”之理论进路
依笔者愚见,民意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定罪机制,分别为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的规范解读。
(一)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
民意对特定疑难个案的评价实质上就是价值的衡量与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熔伦理、习俗、宗教、自由、正义、秩序等国家价值导向、社会价值理念于一炉,与刑事政策的内蕴价值具有重合性与相似性。例如,公众对于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重暴力侵犯人身及财产犯罪的强烈意愿,就与国家现时整顿食品安全生产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政策的关注重点相契合。同时,民意有时也会呈现出与当前刑事政策的侧重点相抵触的一面。例如,民众希望对某些金融犯罪行为(比如非法集资罪)非犯罪化,或细化兜底性经济犯罪的罪状描述(比如非法经营罪),使国家放松对经济的过分行政管制,以释放民间金融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力。民意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与制约并不是单向、不可逆的:一方面,民意推动刑事政策的生成并依照政策的精神与内涵而实施相关法律行为,也就是说,民意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诉求本身就是刑事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现阶段犯罪情势的正确判断,前瞻性地制定刑事政策,规划、引导民意,畅通民意的表达机制,完善民意合法、理性的评价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法律效能。
民意通过上述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其蕴涵与刑事政策的相契合性,增强了其规范性的法律特质,而民众对于某个或某类犯罪的价值倾向性的好恶,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民意对于此类案件的刑罚理念的选择。例如,对于严重食品安全犯罪、国家机关人员滥用权力案件,民众希望从重处理。相应地,司法机关在对这类案件进行定罪量刑时,对于作为刑事政策表现之一的民意的法理诉求,在犯罪性质的认定上,刑罚种类及强度的选定上,就会作出某种回应。从微观方面分析,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及刑法中概括性条款、规范性构成要件的存在,对于某个特定危害行为,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时,就会存在不同解读。同时,不同犯罪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外延上的交叉性与模糊性,也会使处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临界点的案件,在犯罪的定性方面存在偏差。此时,精细的刑法教义学本身不能证明自己分析案件的正确性,即使通过习惯法解释也不能完全消除定罪的歧义,况且刑法解释自身还存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但刑法的补充性又决定了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给出明确的司法结论。对于此两难困境,必须借助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在结合当前刑事政策的侧重点、主导价值追求与案件本身的性质、类型、情节的基础上,为犯罪构成的实体判断注入价值因素的考量。这样,就可大致选定符合政策要求与民意倾向的犯罪该当性内容。
(二)刑法解释的规范解读
有人认为,教义学本质上涉及的是价值判断的规范化问题,具有将价值判断问题转化为法解释技术问题的功能。[5]那么,当现时民意的价值取向及对个案的判决意见与依据专业判断得出的司法结论存在认识差异时,除了通过上述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协调两者的冲突外,还可以借助刑法解释的规范性方法,在犯罪构成要素的内部找出能够吸纳民意的理论通道,通过刑法解释来甄别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是否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又不能离开对于刑罚效果即刑罚目的及其机能的实现问题的考量。
是否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必要及其限度,是通过刑罚的类型、幅度及执行方式的轻重缓急体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当民意的价值判断经由刑法解释对犯罪的认定产生影响时,必须考虑刑罚的问题。亦即,民意在对特定疑难案件施加影响时,主要是通过影响行为人预防必要性的认定,具体来说,就是其人身危险性、罪犯改造的可能性,来间接地影响涉案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再通过对其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规范判断,以刑法分则相应犯罪的法定刑及其适用为基点,经由刑法解释的理论桥梁,最终对犯罪的认定形成反制。这实际上是刑法实质主义的当然逻辑。
民众对于争议案件已判罪名及刑罚的不理解甚至不满,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存在严重的罪责刑不适应的问题,这种情形不管是定罪方面还是量刑方面都有反映,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罪抑或量刑,不仅不能实现刑法的预防目的,而且会削弱民众对于现行司法制度的信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具有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功能,如果某个解释结论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的结果,则必须否定它的有效性。[6]当民意形成的主观倾向与价值取向被刑法解释注入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判定时,就必须重视因刑罚的分配不当而引发的犯罪控制的异己性(即法律自身制造出自己意图或本该遏制的行为的这种现象),此时,在犯罪认定时准确适用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就可以对这种偏离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
三、民意“由刑制罪”之司法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民意的“由刑制罪”的适用范围应限于司法疑难案件,“疑难”是指法律上的疑难而非事实上的疑难。疑难案件是指,根据形式逻辑,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没有明确的涵摄关系,无法直接适用三段论处理案件,需要通过复杂的法律推理或解释以及其他司法技巧才能解决的案件。[7]实际上,它是在判罚明显不当、罪刑不相均衡及缺失实质正义时,才确定适用的补充性的定罪机制,那么,其司法适用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考察其发挥机能的进路可知,“由刑制罪”属于定罪机制的逆向推理,即司法官首先依据其审判经验、司法前见及内心的确信形成一个先验性的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构成要件符合性进行内外部的司法证成,这样的逻辑进路很容易引致目的导向式的、社会危害性优先考量的“有罪推定”。由于对社会危害之规范意义的理解不同,加之刑法概括性要素的大量存在,使得在具体诠释犯罪构成要素的具体涵义时,过多的价值判断主导着犯罪认定的司法过程(这种情形多存在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难以区分时),某种程度上,这样就为类推解释、刑法的过度刑事政策化以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此时适用以刑制罪的方式认定犯罪,就会产生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的紧张甚至冲突。因此,在“以刑制罪、由罪至刑”之罪刑关系的基本框架下,民意对于定罪机制而言,应将其作为例外的、有限制的理论进路适用。
虽然适用“以刑制罪”理论处理疑难案件,存在一定的刑法风险,但这种风险是可控的。在审理特定个案时,当依据法律专业意见得出的法律结论与民众的司法感知与刑罚结果预判存在明显差距时,法官在结合当前刑事政策的关注重点、特定犯罪类型高发的特点、社会治安防控的热点的情况下,在犯罪该当性的框架范围内,通过刑法解释、法律推理等法学方法,在适当考虑民意所折射出的司法诉求的前提下,对疑难案件之被告人确定犯罪性质、选定罪名、判定刑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的,同时,也没有超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要限度。至于有学者担心的此间可能会造成类推解释、有罪推定司法的泛滥,笔者认为,此时应明确,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仍应遵循可预测的、不超出国民基本感知、良知的范围。民意之中蕴含的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论证的侵入,并不必然导致犯罪构成要素基本涵义的耗散或偏离。因为民意经由以刑制罪理论对定罪机制产生影响,其立意宗旨在于缓解甚或消解罪刑的不均衡及个案的实质不正义的情形,不管是立论的本意,还是司法适用的客观效果,民意的以刑制罪的机能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写、替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与认定犯罪的基本机制,它只不过为犯罪的认定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而已。另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中“价值判断规范化”的关键,在于其应与法律规则之间建立必要的规范性的、制度性的联系,即应利用刑法规则来解读、解决价值分歧,辨识法律价值优先度,将价值判断转化为刑法技术性问题,例如,刑法解释及对犯罪概括性要素、兜底性罪名内涵及外延的界定等。也就是说,民意中价值判断的嵌入只能存活于开放性的构成要件之中。
民意与以刑制罪理论形成互动并影响、制约犯罪认定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提炼规范化的民意。有人认为,民意是多变的、反复的、情绪化的,往往是可操纵的,有时甚至是虚假的,司法领域并不存在有效的民意收集机制和议事决策机构,经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渲染与剪裁的民意,代表性大可质疑。[8]笔者认为,民意虽然具有流变性与情绪化的特征,但其在案件基本事实清楚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社会舆论的自发、自觉浸染与演化,所表征出来的司法诉求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例如许霆案中,民意对于所判刑罚过重的质疑),即使对于法律专业性问题,民意中的理性分析也可为司法适用提供借鉴。须知,法律专业人士所提出的意见也是民意形成的助力之一(例如在“天价过路费”案件中,民意对于偷逃养路费金额计算方式及定罪依据的质疑)。民意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司法诉求并不一定必须要有专业、固定的、可见的收集程序及决策机构得出结论,民意自身的自发性、自觉性,及民意主体中专业机构、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使得民意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性的、规范性的主题意见,这一点已为大量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当然,如果能够建构一个集民意收集机制、民意筛选机制、民意规范机制、民意吸纳机制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评价体系,使之成为刑事法律科学体系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更能促进民意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民意收集与分析制度的构建,不一定完全委诸于司法机关的法制部门或政策研究部门,公民团体或具有基本法律素养的公民个人也可以作为民意反馈机制的组成部分,向司法机关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及建议,但民意评价体系的顺利运行及发展完善,必须以相关刑事实体法及刑事程序法为规范的支撑与保障,在这方面域外的法院之友制度、治安法官制度可资借鉴。
四、结语
以刑制罪理论的生成及兴起,是刑法实质主义思潮在犯罪认定机制方面的具体体现,而民意裹挟着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也对犯罪性质的确定及刑罚的确定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与制约,两者之间的结合正是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渗透甚至修正的典型诠释。基于此,对于刑事法学的研究必须秉持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与法学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刑事法学诸学科的学科整合与知识契合。
【参考文献】
[1]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4):40.
[2]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06(5):125,127,128.
[3]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8(4):160.
[4]孙万怀.论民意在刑事司法中的解构[J].中外法学,2011(1):149.
[5]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4):30.
[6]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4):40.
[7]赵运锋.刑罚反制机能的梳理与展开——基于传统罪刑关系的反思[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1):36.
[8]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J].政法论坛,2012(4):36.
收稿日期:2014-05-06责任编校:陶范
【文章编号】1673―2391(2015)01―0074―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