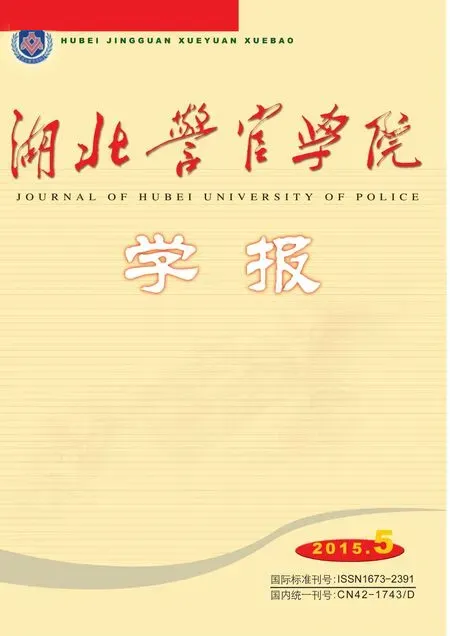刍议开放式罪刑规范的正当基础——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分析样本
韩玉刚
(太原工业学院 思政部与法学系,山西 太原030008)
我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文除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典型的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犯罪以外,又以兜底条款的方式——“以其他危险方法……”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罪名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犯罪构成客观行为方面的开放式规定。因为此,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本罪缺乏罪刑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明确性,是无所不包的“口袋罪”。[1]在司法层面,最近几年关于本罪名的一些司法适用案例,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2]其实,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现行《刑法》分则以兜底条款表述的罪名共有24个,涉及25个法律条文。此类罪名在客观行为方面似乎都有表述模糊的缺陷,与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化要求存在紧张关系。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代表的开放式罪刑规范到底有无正当基础?在当前政治社会条件下,罪刑法定主义的政治功能该如何定位?刑事立法的价值选择何去何从?本文即从上述两个维度展开,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分析样本,尝试论证开放式罪刑规范的正当基础。
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理正当性
(一)罪刑法定主义政治功能的历史考察
评价刑法兜底式罪刑规范的正当性问题,绕不开罪刑法定主义这一基本参照。因此,探究罪刑法定主义的制度价值或曰政治功能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研究罪刑法定主义的政治功能,必须从其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出依据。“他(孟德斯鸠)的原则是:‘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研究传统似乎是历史的事,但就法律文化这个题目来说,立足于当代也一定要抓住历史……总之,法律文化研究少不了要谈历史和传统,否则,就不能深入下去,终究只是现象的肤浅说明。”[3]通说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历史源头有两个:一是英国的大宪章,二是法国刑法典。[4]从这两大法律文件出台的历史背景中不难发现其在当时的实际功用,或者是限制(如英国大宪章)或者是反思(如法国刑法典)王权曾经在刑法司法领域的滥用。由此可见,罪刑法定主义最初的政治功能,在于限制王权,限制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罪刑擅断。在当前民主政治条件下,这一制度的历史背景显然已经不成立,但罪刑法定主义背后的制度逻辑——限权功能却不容否定。在坚持罪刑法定主义的前提下,我们所要追问的,是其现实的政治功能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十八世纪罪刑法定主义的提出,其政治功能是针对君主专制体制下国家刑罚权(其实是君主刑罚权)的恣意,从而保护普通民众的自由和人权,那么在今天民主政治体制下,罪刑法定主义的限权功能,无疑是指向了刑事司法权。作为罪刑法定主义基本要义的明确性要求,就是立法者应当给司法者确立相对明晰的入罪标准。理想的罪刑法定主义形态,其内在逻辑就是建立“自动贩售机式的司法”——立法确立严格入罪标准,司法则按图索骥。但罪刑法定主义的构想毕竟是一种理念式的追求,对此,我们必须以务实的态度去把握刑法的这一基本准则。尤其在社会转型期,我们不能以此苛求立法机关高屋建瓴,毕其功于一役。较为现实的一个选择是考虑从刑事司法上努力消化这一紧张关系。“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罪刑法定无疑是历史事实所明证的经验总结,但在今天,我们对其现实制度价值和政治功能定位,必须以今天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司法经验重构。同其他部门法一样,刑法也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为此,打破学究式的、固有观念上的藩篱就成为一个必要的理论前提。笔者以为,当前迫在眉睫的并不是在刑事立法上构建如何缜密的法网,而是在刑事司法领域,破除重刑主义的深刻影响,以谦抑性重塑刑事司法的品格。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罪刑法定主义在限制刑事司法权滥用上的内在局限性。如果把罪刑擅断的具体样态做一个细分,其在客观上无非有两种表现:一是随意出入人罪,二是量刑上的畸轻畸重。虽然罪刑法定主义在解决随意入罪和量刑畸重问题上能做到效如桴鼓,但在解决随意出罪和量刑畸轻的问题上,则明显超出了其制度意涵。
(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范性评价
刑法分则以兜底条款表述的罪名共有24个,涉及条文25条。从数量上看,兜底式罪刑规范仅占刑法分则条文总数(条)的6.7%、刑法分则罪名总数(541个)的5.32%。这一数据足以说明,立法者对兜底条款的应用是极其审慎的。就质的规定性看,兜底条款的主要表述方式为:“以其他方式……”、“以其他方法……”、“以其他手段……”(或表述为以其他……手段)、“其他……活动”、“其他……行为”。无论表述为方法、方式、手段,还是活动、行为,其实都是对犯罪客观方面行为方式的表述。表面上看,此类罪名在客观行为方式方面,外延宽泛,似乎无所不包,仔细推敲,则不难发现,相关条款所涉及的罪名在客观行为方式方面,受到了犯罪构成其他要素的严格限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在犯罪主观方面,本罪必须出于故意;在犯罪客体方面,以公共安全为本罪的侵害对象;在犯罪客观方面,本罪也以具有“相当危险性”作为行为性质上的限定。危险性,指行为侵害的客观可能性,相当一词的限定,则表明该危险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机率上较大的盖然性。何谓危险行为,基于人们共同生活准则,按社会一般观念即可判断,相当危险性则表明了行为人对该危险行为导致危害结果预测可能性的程度。而行为的预测可能性,恰恰是罪刑法定主义明确性要求的题中要义。至于本罪侵害的客体——公共安全,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上也早有明确的规定,即便是按照生活经验来判断,也有相对明确的外延界限。行为人基于故意的犯罪心态,以具有危险性质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基于这样一种犯罪构成的内在表达,本罪无论是其行为外延,还是行为本身的预测可能性,都是有迹可循的。因此,本罪留给司法自由裁量的余地并没有学界想象的那么大,称其为口袋罪,言过其实。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作为口袋罪的典型“流氓罪”,在犯罪构成方面,则无此明确的内在限定性,流氓行为,即便是按社会观念判断,本身也是极其模糊的。而危险方法(行为),基于社会共同生活准则,其判断标准要明确得多。作为一个正常理智人,在对自己行为是否有可能侵害公共安全的问题上并非难以做出预判,刑法对其相关注意义务的要求并不苛刻。综上所述,本罪在犯罪构成上的明确性或曰行为的预测可能性上表述明了。至于最近几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上出现的种种不端,笔者以为并非立法上的问题,而是由司法体制、职业水准和职业习惯等种种原因造成的。如果司法者有意或无意地曲解法律,再细致缜密的立法都是徒劳的。例如,最近几年发生的几起行为人因盗窃窨井盖而被司法机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案例中,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或者说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可能性持放任的心理状态,符合本罪的主观要件。但刑法理论告诉我们,间接故意犯罪,是以发生实害为成立要件的,相关判例并不符合这一基本要件。这些代表性案例足以说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并不在于立法上的缺漏,多数情况下是司法水平所致。
“(圣托马斯认为)法律在以下情况下可视为正当:其目标在于共同福利,其创设者没有越权;至于法律的形式应满足的条件是,它附加给公民的负担所分配的比例有利于促进共同福利。”[5]从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看,有些是从侵害法益(犯罪客体)的角度表述的,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有些是从行为方式(犯罪客观方面)的角度表述的,比如诈骗罪、盗窃罪等。其实,从犯罪的本质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来看,任何罪名都可以从结果意义上去表述。笔者并无以“严重社会危害性”代替犯罪概念的取向,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评价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尺,是毋庸置疑的。例如,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典型形态是爆炸、放火和投毒,出于司法便宜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将其表述为爆炸罪、放火罪、决水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但从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维度考察,四罪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正是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周延考量,立法者规定了备受争议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力图藉此编织一个相对严密的法网。另一个表述类似却评价迥异的例证是故意杀人罪。我们从来不质疑故意杀人罪在罪状表述上的正当性,因为,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立法者难以通过枚举的方式在刑法典罗列故意杀人的具体行为样态,比如“以刀捅的方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以绳勒的方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或“以下毒的方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故意杀人罪这一概括表述其实隐含了“以任何方法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这样的内容,就客观行为方式而言,故意杀人罪当然也是开放式的规定,并无明确的外延限定,难道我们会据此认为,故意杀人罪是一个口袋罪,有悖罪刑法定主义吗?故意杀人罪作为严重犯罪,可以从“犯罪侵益性”这一维度界定,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另一类性质严重的犯罪、涉及重大法益(公共安全,甚至包含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犯罪,从侵益性的角度概括表述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法理正当性不言而喻。笔者以为,最高人民法院不妨取消爆炸罪、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枚举表述,统一表述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罪名表述上的合并其实和故意杀人罪的概括表述并无二致。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把一个法律条文分解为相对独立的四个罪名本身就是有疑问的,《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从其措辞和逻辑看,更像是以“列举+兜底”的方式表述了一个罪名,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社会正当性
(一)刑事立法的社会基础问题
“作为耶林法律观中心的是如下思想:法律科学自身必须关注社会关系,以及规则背后的社会目标。在理想状态下,这一目标应是对‘利益’的保护。在此,他区分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立法者和法官的任务都在于调和这些利益——法官的途径是少凝视纯粹法律文本,多关注文本背后的社会目标。”[6]整体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目标及其变迁特征无疑是牵涉宏大的命题,要准确把握其规律性,更是困难重重,也绝非笔者学术能力和文本篇幅所能统摄。但从相对微观的角度观察当今中国社会,则不难发现,“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三个关键词可以作为其流变性的注脚。其实无论是城镇化、信息化,还是国际化,背后都有一个社会交涉性日益增强的显象。社会交涉性的增加,客观上有导致犯罪率升高、犯罪手段多样化、新类型犯罪(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凸显的可能。相对于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生活的这一深刻变化,给中国刑事立法的技术和价值选择提出了追问:到底是坚持刑法的稳定性、可预测性还是适当考虑其前瞻性?“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这一经典论述告诉我们,中国的刑事立法离不开“社会转型期”这一基本变量,刑法在追求人权价值的同时,不能偏废刑法的基本社会功能:社会安定性的价值诉求。面对一个价值多元、社会阶层分化、犯罪手段日益技术化的社会,刑法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适当的前瞻性和灵活性,是达致这一根本目标的必要前提——面对犯罪的恣意保护社会。就社会秩序而言,公共安全虽然不能涵盖其全部内容,但无疑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而成为刑法构建其秩序价值的一把“重剑无锋”的达摩克利斯剑。
(二)刑事立法的价值选择问题
从刑法的三大原则看,罪刑法定主义侧重于人权(自由)价值,罪责刑相适应和平等原则体现了公平和正义价值,从我国《刑法》第一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可以推导出我国刑法的秩序价值。这就提出一个刑事立法位阶及其选择的问题。笔者以为,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刑法的自由或人权价值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当时,刑法实际上成为议会限制君主滥用刑罚权的工具。笔者以为,刑事法治的初衷,无非是社会生活的安定性,对罪刑法定主义的现实定位必须置于这一根本目标之下。虽然罪刑法定主义在整个刑事立法上有顶层设计的意味,但罪刑法定主义绝不能涵盖或取代刑法的全部价值。刑法学界长期以来,更多强调刑法的人权价值,较少从秩序的维度去考虑刑法体系的建构。其实,就秩序价值所蕴含的“保护全社会共同福祉”而言,何尝不是指向大多数人的人权?因此,在刑事法治的构建上,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也要兼顾社会生活安定性的价值诉求。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实际情况看,不同的罪状表述,实际上也体现了立法者针对不同犯罪领域所做出的不同价值选择:在某些犯罪领域,立法者侧重法的秩序价值,在入罪标准上相对宽松,立法者或者采取概括式的表述,或者采取兜底式的表述——“针对犯罪的恣意保护社会”;在某些犯罪领域,立法者更侧重该领域社会活动的自由保障,对其入罪标准做了相对严格的限定,以穷尽式列举的方式对该类犯罪的行为外延做了严格限定——“针对司法的恣意保护个体”。
三、结语
中国最近十多年来在刑事法治领域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刑法》包括《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订也都突出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精细化和人性化的特点。凡此种种,既有和国际接轨的考量,多半也是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如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和重刑主义。可以说,在“去法律工具主义”的改革进路上,罪刑法定主义功不可没。罪刑法定主义作为现代刑法理论最重要的精髓之一,无论身处怎样的历史情境,我们都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但罪刑法定主义绝不是教条,有其特定的历史演进背景和制度内涵,既要从历史,也要从现实中找寻罪刑法定主义的依据,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罪刑法定主义。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践,则必须将其置于刑事法治的整个框架之下,服务于刑事法治的整体目标。笔者以为,社会生活的安定性,应该是刑法的终极价值诉求,刑法不是万能的,但刑法也决不可无为而治。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在坚持刑法谦抑性的大前提下构建“有为刑法”,服务和谐社会,就成为法律人探索的一个新的法学命题。
[1]陈兴良.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J].政治与法律,2013(3):2-13.
[2]孙万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J].现代法学,2010(5):70-81.
[3]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现在、过去和未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4.
[4]马克昌.罪刑法定主义比较研究[J].中外法学,1997(2):31-40.
[5][爱尔兰]凯利.西方法律简史[M].王笑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71.
[6][爱尔兰]凯利.西方法律简史[M].王笑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