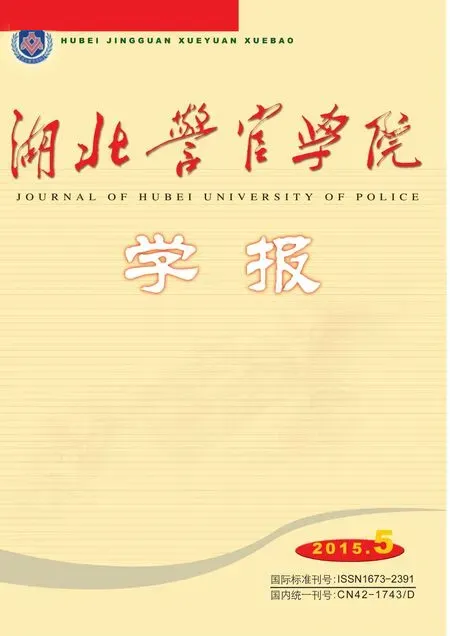当前我国突发事件政府话语权面临的困境
贾俊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政府是处置突发事件最重要的主体。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不仅要调动各类社会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紧急加以处置,同时还要及时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的目标[1]。要实现上述目标,就涉及到政府两个最重要的能力——行为能力和沟通能力,而话语权的控制即是沟通过程中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之一。在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新闻舆论的管控已经成为突发事件处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我国对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从国家立法、制度设计层面到地方预案制定、具体执行层面等多层次推进,为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突发事件政府话语权领域还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是政府自身话语权运用不当,在突发事件中“失语”或滥用话语权侵犯公众权益;另一方面则是突发事件另外两个重要的话语主体——媒介及公众话语权既存在缺乏保障、受到政府话语权挤压等情况,也存在违法违规、滥用话语权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对话语权的合理掌控,也不利于政府形象的建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形成,亟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研究改进。
一、政府话语权的缺位与越位
(一)突发事件后失语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扮演着突发事件话语的生产者、监督者和控制者等多重角色,把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信息当作“秘密”,担心公布信息会引起公众焦虑和恐慌,“公开越多,做事越难”一直是过去管制型政府的典型思维。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广大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往面对突发事件采取“鸵鸟式”的应对政策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要求。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对此并不适应,突发事件发生后失语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莫过于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吉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由于爆炸现场距离松花江仅500米,近百吨苯污染物泄露并流入江中。起初,吉林当地政府否认饮用水污染物超标108倍的事实,使污染危害到下游的哈尔滨,之后,黑龙江省继续隐瞒事实甚至谎称“地下供水管网维修停水”,直到11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水污染的情况,此时距13日的爆炸整整历时12天。再如,2012年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2]火灾发生后,天津媒体集体沉默。只有《今晚报》在7月4日第2版角落处发了一则简讯——《本市蓟县火灾事故医疗救治工作有序进行》,标题连正文170余字,性质为官方通稿。权威信息的缺失导致谣言四起,部分媒体及网民质疑火灾发生后,商场老板封锁大门导致大量人员被困、求救电话拨打25分钟后消防队才赶到、死亡人数甚至超过378人,舆论哗然。直到7月6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才发布消息,公布火灾事故伤亡人数和遇难者名单,但此时已没有人再相信官方公布的数字。对此,《中国青年报》刊发评论称:“面对互联网的汹汹议论,当地官方媒体普遍保持沉默,错失了释疑解惑、沟通民众的契机,值得反思。”[3]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传统社会对公众的治理模式,仿佛是古罗马人建造的监狱,看守们站在监室的最顶端,对所有犯人可以一览无余;而犯人则看不到看守的存在,因此一直有“被监视”的感觉。这样,即使看守们不在,犯人也不敢有所动作,因为他们不知道看守是否存在,从而自觉地规罚自己。这种通过彼此占有的信息不对等而实现的治理,被称为“超级全景监狱”。但在今天,信息的传播渠道和表达方式已经大大丰富,政府和民众处于相对平等且相互围观的状态下,希图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或信息不对等来实现政府的优势治理已经很难实现,相反,握有公权力的人往往处于被监督的中心位置。面对这种新挑战,部分领导干部从思想观念到能力素质都还不适应,重事件处置、轻舆论引导,不愿说、不敢说,往往被迫公布真相时又不会说、不善说,陷入了“事件发生—舆情高涨—被迫公布真相—再度炒热—事件升级扩大”的怪圈,致使失去第一时间抢占话语权、报道政府行动及处置工作的最佳时机,最终造成工作被动。[4]
(二)政府话语权滥用
哈贝马斯曾把公共空间中的行动者分为两类,“一种是从公众中间涌现出来的组织松散的行动者,一种是站在公众面前的、从一开始就拥有组织权力、资源和威胁潜力的行动者”。在突发事件话语权领域,政府由于其占有的权力资源、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势,实际上在各话语主体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如何慎用、善用政府话语权,从而达到有效配合突发事件处置,均衡话语空间的目的则还需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倚仗着手中掌握的信息资源和媒体公共平台,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草率发布、不当定性,动辄扣以“不明真相”、“别有用心”、“黑社会性质组织”、“破坏社会稳定”等大帽子,不仅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感情,客观上也没有收到引导舆论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引发“次生灾害”。2008年发生在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的群众聚集打砸烧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的严重群体性事件,起初只是源于一起简单的治安事件。6月22日,瓮安县三中初二学生李树芬在河边玩耍时突然自杀身亡,瓮安县和黔南州公安机关两次鉴定结果认定其为自行溺水,向死者家属说明不予立案。家属在向其他几名当事人索要50万元赔偿的要求遭拒后,以怀疑李树芬系被奸杀后投入河中为由,在亲属组织下于28日下午14时到县政府上访,游行至公安局门前被阻拦。如果当地政府能在此时放低姿态与家属沟通,并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引导舆论,可能事件就不会朝着迅速恶化的方向发展。可是,当地政府却始终未予回应。29日下午,在尚未展开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的新闻,引起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同样地,在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种“定性怪圈”。
政府话语权滥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以权压法,动用各种行政、司法资源打压媒介和公众话语权。2009年2月12日,河南灵宝籍青年王帅以“王二宝”的网名在天涯社区发表题为《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的帖子,举报灵宝市政府违法征地。帖文发表后,迅速被搜狐网、中华网、猫扑社区、凯迪社区等40余家网站、论坛转载。2月23日,灵宝市政府向灵宝市公安局报案,举报王帅发帖称500万元抗旱资金被贪污系捏造。2月25日,灵宝市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对王帅立案侦查。3月6日,灵宝市公安机关派人赴上海将王帅抓获。3月13日,公安机关对王帅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4月7日,王帅继续在网络发帖讲述自己被灵宝警方抓捕的经历,并向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反映问题。这两篇帖文发出后,受到网民的极大关注,传统媒体介入报道,河南三门峡警方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并认定王帅发帖不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向灵宝市公安局下达了《关于纠正灵宝市公安局办理“王帅案件”违法问题的通知书》。4月15日,灵宝市公安局作出决定,对王帅解除取保候审、撤销案件,并给予国家赔偿。作为近年来影响最大的跨省抓捕网民案件,王帅案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地政府在面对民众的网络批评时,不是反省自身有无错误,而是以诽谤为由对发帖者进行打击,滥用政府职权,其结果只能是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和质疑。同样的做法,在辽宁西丰警察到《法制日报》社抓捕记者、《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遭浙江遂昌警方网上通缉、陕西渭南警方进京抓走作家谢朝平等事件中屡屡上演,充分暴露了相关地方政府手中权力的傲慢。这种以权压法的做法不仅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此外,还有一种政府话语权滥用的形式,即替无良官员“背书”。背书源于我国古代官场,古代官员要保荐谁,就写在保荐书的背面,由此称为背书。今天所言的背书,实际上是指以政府的名义在政治上为当事人进行担保。在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中,此类例子也不少见。例如,2012年12月5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个人微博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结成官商同盟、包养情人等。12月6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作出回应,称“举报内容纯属污蔑造谣”,“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2013年8月8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称,刘铁男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坐实了此前媒体举报的内容。对此,《人民日报》微博发问:“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查,从被实名举报,到新闻办负责人否认严斥,再到证实接受调查,‘剧情’跌宕起伏。调动公权为个人背书,是否应反思道歉?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可以说,这种利用政府和组织的名义给个人背书的做法,是典型的“公器私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做法比前两种做法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
(三)话语方式失当
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其话语方式本应严谨、规范,符合法治要求,符合其自身身份,但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话语方式却走偏了,习惯于“文件式”的写作手法,官话、套话、空话等官僚语言一度盛行,殊不知这种高高在上且官僚气息浓重的官方口径早已引起公众的反感,更难堪澄清事实、疏导情绪的重任。更有甚者,一些官员信口开河,“雷人雷语”频出,不仅暴露出自身素质的低下,更凸显了这些话语背后权力的傲慢以及对广大群众知情权、监督权的侵犯。典型的例子如2009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就河南郑州市一起违规在经济适用房土地上建设别墅事件采访郑州市规划局。该局副局长逯军竟然拔掉了采访机话筒并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后,面对媒体的“围追堵截”,时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是个生命的奇迹”等话语来回答记者的提问,这种漠视生命的回答以及铁道部在事件处置中的救援不力受到媒体的普遍诟病和公众的强烈批评。类似的例子还有贵州毕节民警说“戴套不算强奸”、“五条禁令违法”;济南市天桥区文化局局长说“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湖北南漳县委宣传部长说“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等等。
2014年以来,政府话语失当又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即“自创新名词”。例如,2014年5月23日,有网民在天涯论坛发帖称,四川合江县交警大队某副大队长带女下属开房后,将随身携带的警用枪支丢失在宾馆的房间内。此文一出,立即引发大量网民围观。该县公安局相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称,当事人并不是“丢枪”,而是枪支“暂时失去控制”。此条“定性”回应曝出后,立即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的显著位置。有网民调侃道:“继‘和异性开房是谈工作’、‘保护性拆除’等词后,‘暂时性失控’在近日成为官方经典回应中的一员。”这种“狡辩式”的回应脱离了基本的认知常识,只会给公众以政府在推卸责任、弱化事态之感,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失范和失信,不仅不能有效“灭火”,还会引发舆情的二次灾害,令公众对官方回应失去信任。
二、媒介表达的僭越与异化
媒介是政府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媒介话语权一方面来源于政策和法律的授权,在政府的指导下承担着意识形态建构、信息传播、引导舆论等功能,同时又受公众话语权委托,客观上为公众自由表达愿望和利益需求提供平台。在我国,媒体的各项新闻报道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媒体既是党的喉舌,也是社会公众利益的守望者。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媒体却偏离了这一定位,造成对政府话语权的损害和对公众的误导。
(一)媒体报道的僭越
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信息发布和沟通最重要的渠道,媒体功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政府对话语权的掌控效果。而当下中国,媒体是兼具部分公共权力的舆论部门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单位,这种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双重取向,往往造成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扭曲和异化。
1.僭越法律法规。突发事件固有的冲突性、悲剧性和重大性等新闻价值,加之新闻报道讲求及时、快速等新闻属性,使得突发事件的报道尤其吸引公众眼球,拨动受众心弦。对于突发事件的媒体报道,国际上早有规范,如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不得侵害公共道德和个人隐私等。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也对“以人为本,减少危害”等基本原则作出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媒体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吸引公众眼球,提高发行量或点击率,奉行“坏事就是好新闻”的法则,对发生的突发事件特别是恶性刑事案件,不遗余力地展示犯罪过程、泄露侦查内幕、曝光当事人隐私,个别媒体还存在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信息,刊登“有偿新闻”,甚至收取“好处费”、“封口费”等现象。这些行为严重超出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界限,也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
2.僭越伦理道德。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不仅要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还要尊重公民的隐私权,不能忘记突发事件中对人的关怀。据有关研究表明,30%—58%的重大突发事件参与者、目击者会出现明显的心理不适;而对其他人来说,新闻报道的过度也会引起厌烦、不安等情绪,影响真正的传播内容。[5]比如,在2012年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新闻报道中,部分媒体得知犯罪嫌疑人周克华有一位68岁母亲的时候,便云集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二塘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一遍又一遍地要求老人讲述周克华的性格及成长历程,一遍又一遍地拍摄老人满是沧桑又稍显木讷的表情,甚至当重庆警方将周克华击毙后,媒体还要跟拍老人“得到警方允许给儿子收尸”的过程,完全不顾一个风烛残年老人的心理感受。再如,在2014年3月8日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中,最初也有部分媒体追逐围堵机上乘客的家属,在受到舆论指责后,才逐渐调整了报道角度。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不到媒体作为社会道德的引领者所应当具有的人文关怀,也看不到这些媒体的职业素养。
3.形成媒体审判。媒体审判一词源自美国,起因是在该国的一起诉讼案中,法庭认为用作诉讼证据的录像含有倾向性宣传内容,有违司法公平,因此推翻了此前的判决。在这之后,人们就把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干预和影响司法的新闻报道称为媒体审判。在我国,由媒体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的情况并不少见。2010年10月20日,年仅21岁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深夜驾车撞倒受害人张妙,因担心其看到车牌“以后找麻烦”,便持尖刀连刺张妙数刀,致其当场死亡。10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此案一经报道,立即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体在报道中不断披露药家鑫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的身份(后经证实均为不实报道),整个社会“喊杀声一片”。在这样的民意压力下,法院对药家鑫的审判仿佛变成了民众与社会不公的对决,如果不判处药家鑫死刑,就意味着放纵犯罪,也就意味着将从法律的笼子里放出更多“药家鑫”来。姑且不论药家鑫最终被判处死刑是否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单就这样一个“未审先判”的舆论环境,就不是成熟的法治社会应有的现象。媒体审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是媒体绕过司法程序,利用自身话语权伤害当事人感情、曝光当事人隐私,对当事人生活造成实质性影响的行为,如网络人肉搜索、网络言论暴力等。
(二)意见领袖的误导
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通过观察身边的选举现象发现,人们投票的决定很多时候都会受到身边亲戚朋友的影响,这些熟人所发挥的影响力要比报纸广播的影响大得多,为此,他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6]一般情况下,意见领袖比一般受众具有更强的交际活动能力和影响力,他们是大众传播中的评价员、转达者,经常通过自身的评论和意见影响他人。在社会生活中,意见领袖通常由专家学者、媒体和法律精英、商业领袖以及各个群体和阶层中“享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意见领袖的作用既有积极、建设性的一面,也有消极、破坏性的一面,我们这里研究的,是意见领袖的消极作用,即意见领袖误导舆论的情况。在近年来的诸多重大案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意见领袖扩散与传播负面信息,影响舆论走向的身影。例如,云南网民“边民”(真名董如彬)利用其在“躲猫猫”案件、云南小学女生卖淫案中获得的影响力,私下开设公司,介入热点事件或直接恶意造谣,误导社会舆论,从中谋取钱财,最终被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三)谣言充斥网络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特·希布塔尼等人认为,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即重要性和模糊性,谣言传播的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模糊性的变化而变化,重要性越强、事件的信息越含糊,则谣言传播的广度和强度越大。[7]突发事件因其发生的突然性与反常性,与公众利益的相关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特点,使得公众既想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但又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这种需求和矛盾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近年来,在我国历次重大突发事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谣言传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一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大型工程车压断脖颈,其因征地补偿问题长期上访等特殊背景而使事件迅速引发炒作。有网民宣称:“钱云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4个保安按住,让车轧过来”;有网民爆料“当地拆迁款达7亿元之多”;还有网民称“案件调查组组长自杀”……这些匪夷所思的谣言在官方公布“交通肇事”的定性后依然满天飞。谣言借着“为民请命”的“正义化”包装和极富悲情的“血腥”讲述,意图赋予负面的谣言以正面价值,由此生产出一套“正义谣言”的反权力话语,对政府话语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三、忽视公众话语权保障
(一)公众知情权的“被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受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惯性以及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权的管制模式的影响,在整个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官本位”思想,掌握着公共权力和信息资源的政府部门“往往把自己当作权力的所有者和社会的主人”。[8]在这种“官本位”政治思维的指导下,政府部门及其领导者往往以“父母官”的姿态对民众进行教化,认为民众的智慧和能力无法使其在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倾向于代替民众对突发事件信息做出筛选,按照自己的意愿呈现给公众以“真相”。于是,我们看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黑龙江省长面对此前“维修自来水管网”的质疑,微笑着回答“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们看到某省的一位政协官员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公示的提问时反问记者,“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我们看到湖北武汉上访人员在省委门口被打后,面对上访者由“普通人”到“厅官太太”的身份转变,当地公安分局负责人“没想到打了大领导夫人”的表态;我们看到山东东平多名初中女生疑遭性侵后,面对公众质问和“有领导打招呼”的质疑,当地官方迟迟未予回应,似乎认为没有倾听的必要,也没有向民众解释的必要。在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今天,许多领导干部的理念观念跟不上,在公共行政中竭力排斥民众的参与,殊不知这种“被选择”的知情权已经超越了政府应有的权限,民众对信息“选择的自由”才是知情权的真谛所在。
(二)相互隔绝的话语体系
在当前的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两套话语体系。一方面,“官方舆论场”利用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引导公众情绪,促使事件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解决;另一方面,人们依托于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在网络、微博、BBS上议论时事、针砭时弊,评论政府的公共管理,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传递着各式各样的信息,但内容却是真伪难辨。两个舆论场的传播基调、话语方式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不仅直接挑战政府话语权的权威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从近年来频发的各类突发事件中可以看到,两个舆论场各自封闭的状态,严重阻碍了政府和公众两个话语主体的理性沟通,这也使得双方在面对一些重复多次的冲突事件时,仍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如从福建厦门的PX事件开始,辽宁大连、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广东茂名等地皆因上马PX项目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尽管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官方媒体反复说明、论证PX项目的安全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无论如何“苦口婆心”,多数地方仍陷入“群众逢PX必抗议、政府逢抗议多让步”的“抵制怪圈”。究其原因,除了相关项目立项的前期过程多有纰漏,科普工作不重视,与周边居民协商不足等因素外,长期以来政府角色错位、环保机制架空、安全事故频发,特别是民众与官方的话语体系长期相互隔离,难以达成认同与共识,恐怕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对此,央视网提出建议:“‘邻避效应’①邻避效应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不可避免地存在,但它并非症结所在。真正值得思忖的,仍是在信息不对称、沟通失灵的议事框架下,几方诉求在博弈界面上铺开、衔接。”
(三)监督和追责缺位
尽管我国通过立法形式规定了信息公开工作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法定职责和义务,但在实践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前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信息的“公开”与“不公开”基本上是相关政府部门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换言之,如果没有监督和追责的存在,那么对某些政府官员而言,“不公开”或“晚公开”相对于“公开”或“及时公开”的成本要小。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很多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把本应该公开的信息在经过一系列“利益考虑”后演变为“集体性沉默”或“推诿”与“扯皮”。现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突发事件信息公开责任均有明确规定,但相关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明确细化的监督追责主体、程序及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束之高阁或大打折扣。近年来,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河北石家庄市原市委书记吴显被媒体发现悄然出现在河北党代会现场,曾质疑“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又回到工作单位担任原职,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在因“豪华游”被曝光免职后仅隔2个月就任省政协副秘书长,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县长“低调”复出……这些曾因突发事件被问责的官员的复出都会“不约而同”地引发媒体关注。这种儿戏般的问责,透支的是政府形象,挥霍的是信任资源,不仅失去了惩前毖后的警示作用,也无疑刺痛了公众的心。更有甚者,在经历了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封堵”和民意拷问后,竟能无碍仕途、照样升迁,集中暴露了政府监督追责的疲软,体现的是制度的漏洞和执行的无力。
此外,公众知情权在受到侵害后,有效的救济途径缺失。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公民渴望获得更多更详细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公布信息,或所公布的信息与事实出入较大、信息量较少时,公众很难获得有效的申诉和救济渠道,无法通过“投诉、举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司法部门对于因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诉讼也很多以“不受理”的方式进行处理。这种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知情权,恐怕只能停留在“被动”和“口头”的层面上。
四、结论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民主化大潮的冲击,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面临的舆情环境将日趋复杂。如何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兼顾政府执政和公众权益的双重目标,协调好政府、媒介、公众三者间的话语关系,合理掌握突发事件话语权,是政府部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梳理上述问题的目的,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找到改进突发事件政府话语权掌控的关键点,从而有的放矢地加以研究改进,以推动更合理有效的突发事件政府话语权构建。
[1]贾俊强.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话语权控制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83.
[2]贾俊强.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话语权控制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87.
[3]祝华新.天津媒体沉默应对蓟县火灾值得反思[EB/OL].http://ne ws.qq.com/20120709/000090.html,2012-07-09.
[4]贾俊强.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话语权控制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85.
[5]陈堂发.媒介话语权解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20-221.
[6]朱洁.中西方“意见领袖”理论研究综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6):34.
[7][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
[8]肖其明,梁莹.话语民主理论:渊源与发展[J].广西社会科学,2005(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