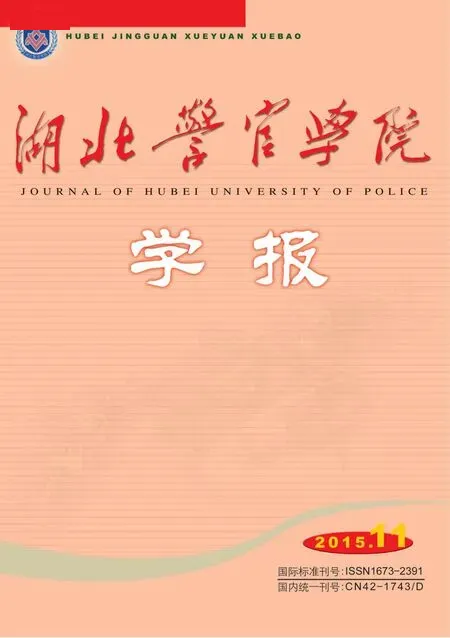论投资型保险契约保险人说明义务之规范
张晓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430073)
投资型保险乃兼具投资与保障功能之金融产品,其最大特征为在一般帐户之外设立分离帐户,并由投保人自担投资风险,故具有相当之复杂性与专业性,亦易产生纠纷。面对此种情形,我国《保险法》以第17 条为基本规范之说明义务能否妥善应对?保监会出台的相关规范又能否有效规制投资型保险契约之说明义务?2013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为金融消费者之保护提供了契机,又能否将投资型保险纳入保护范围,其保护又是否足够?下文将展开详尽分析,并对完善我国投资型保险契约说明义务之规范提出建议。
一、保险法上说明义务之规范
关于说明义务之涵义,现行法没有明文规定。其一般指有传送特定资讯于资讯需求者之法律上义务。而相关文献经常使用之语辞,如解明义务、告知义务、公示义务、资讯提供义务、解释义务、通知义务、指示义务、建议义务、开导义务、公开义务与说明义务在涵义上系指同一,仅说明义务最常被使用。[1]然于保险法而言,说明义务之目的在于创造契约双方当事人间资讯之对等。保险产品的设计与其内容涉及保险、精算及法律之专业知识,且此为保险人自行设计提供给有意愿缔结保险契约之人,亦唯有保险人提供必要且充足之资讯给有意愿缔结保险契约之人,后者才有足够之资讯去判断并决定何种保险商品最符合自己的需求。[2]故本文认为,保险人之说明义务乃保险人于缔约前之资讯提供义务,主要包括资讯披露义务、解释义务等。为了与从适合性原则发展出来的建议义务相区分,可将资讯披露义务、解释义务称作狭义说明义务(已为我国现行法所规定),而广义说明义务则包括狭义说明义务及适合性原则等。
(一)保险人之说明义务:基于我国《保险法》第17 条之分析
通说认为,《保险法》第17 条是保险人说明义务之法律依据,亦可谓是《合同法》第39 条之特别条款。其主要规范解释义务,亦有资讯披露之内容。然就资讯披露而言,保险人所披露之资讯仅是保险格式条款,且并未明确乃资讯披露,仅以“附”字聊以说明,可见此条仍囿于醒意义务①亦即解释义务,参见温世扬:《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之我见》,《法学杂志》2001 年第2 期,第16 页。之内涵。资讯披露依附于解释义务,未获得独立发展,故人们关注之焦点仅于解释义务。
而以解释说明义务之对象为中心解构此条款,其以一般条款与责任免除条款为界分,分别确立保险人说明与明确说明之义务,学者称之为“分别机制”,即对契约之内容进行说明,而对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应以提示并予以明确说明。保险法上之说明义务以说明对象为标准,对一般条款与责任免除条款分别科以不同程度之说明义务,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界定困难。《保险法》修订前采责任免除条款,而《保险法》修订后采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相较而言,后者之外延更为广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 条第1 款将此条款进行了细化,但未对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进行解释,仅采明确列举之形式,超出列举范围之条款是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仍有赖法院之判决。第二,说明与明确说明界分困难。关于说明义务履行之具体方式一直存有争议,更勿论说明与明确说明在具体履行方式上之差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和答复》曾就“明确说明”进行解释,但未指明具体判断之标准。第三,未尽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规范不足。就“分别机制”来看,保险人对责任免除条款未尽说明义务,则此条款不生效;而对一般条款未尽说明义务,则未规定法律效果。其实乃不完整之法律规范,因为其仅有行为模式,而未有法律后果。[3]对于一般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还有赖司法实践之补充解释。
(二)投资型保险契约适用保险法之困境
我国保险法上之说明义务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及于投资型保险契约之适用更是问题叠生。以说明义务之源起来看,就如被保险人必须向承保人(保险人)披露所知道的增加风险的一切资料一样,承保人必须向被保险人披露降低风险的一切资料[4]。换言之,保险人所披露之内容应是与投保人决定是否承保相关之一切资讯。然随情势之变化,尤其是保险商品之不断创新以及保护消费者理念之兴起,影响投保人作出是否投保之决定的显然不仅是保险格式条款。而且针对投资型保险产品之复杂性与风险性,现行保险法资讯披露之事项在时点、方式上之规范均有疏漏,不利于保护投保人之利益。而投资型保险适用解释说明义务时,其相关条款究竟属一般条款抑或责任免除条款尚有争议,如投资型保险契约中有关投资帐户之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之条款是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不明。
前已分析,我国现行法并未明确何为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又将此扩大解释为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之条款。但无论如何,适用此条款之前提是存在保险人所承担之责任。于保险契约中,投保人以投保单与保费为对价,换取保险人在保单规定之情况下支付保险金之允诺。[5]保险人通过担任承保人,预先确定并收取保险保障期间之保险费,于约定条件下承担支付保险金之责任。[6]然而,尽管投资型保险契约之保险部分如同传统保险契约一般,保险人负有给付保险金之责任,但投资部分却未曾得到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之允诺。其类似信托契约之运作,是以分离帐户之资金虽由保险人运作却独立于保险人之外,投保人自担此部分资金运作之风险,保险人仅有管理之责任而无固定给付保险金之责任。其不同于免赔额、免赔率等条款,因为免赔额等条款是本应由保险人承担责任而通过法定或约定的方式予以免除,而分离帐户资金运作之风险从来就不是保险人之责任,保险人仅须尽善良管理人之责任。是故投资型保险契约中有关投资帐户之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之条款并非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而仅是一种风险之提示。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为保护投保人之利益,法院往往将此条款认定为免除责任条款,而对保险人科以明确说明之义务。
进言之,《保险法》第17 条第2 款规定,未对责任免除条款尽明确说明义务者,该条款不生效力。依文义解释,所谓“不生效力”即否定免责条款之正当性,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仍应负保险给付责任,而法院亦作如此解释。①参见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 年第3 期。然此于投资型保险契约之投保人未必是最好之选择。因为实务中往往将投资型保险契约中责任自负之条款认定为责任免除条款,而对保险人科以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一旦未尽说明义务,投资帐户之资金发生亏损,所产生之法律效果即是保险人仍应负保险给付责任。此时,投保人不能就投资帐户之亏损要求保险人承担责任,亦不能要求解除保险契约而享有保险费之返还请求权,极不利于投保人权利之保护。②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南终字第214 号民事判决书,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编:《保险诉讼典型案例年度报告·第五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54-58 页。因此,投资型保险契约适用保险法上之说明义务面临两难困境:若适用一般条款,则因现行法未明确说明之具体方式及法律效果而无法保护投保人之利益;若适用责任免除条款,则有违责任免除条款之机理,未能真正理解投资型保险契约之本质,亦未给予投保人妥善之保护。
二、保监会对说明义务之规范
(一)投资型保险契约保险人之说明义务:基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之分析
我国《保险法》无法对投资型保险进行妥善规制,因而多依赖保监会之相关规定。2009 年《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第6 条以《保险法》第17 条为蓝本,但另行要求保险人向投保人出示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以及投保提示书,并要求投保人签字确认。其第18 条规定,产品说明书应包括风险提示、产品基本特征、投资帐户情况说明、利益演示与犹豫期及退保等内容。依我国《保险法》上之说明义务,资讯披露范围仅是保险契约之条款;而依《信息披露办法》,资讯披露之范围及于投资型保险产品之相关信息,包括风险、特征、投资帐户与可期待利益以及风险提示等。这无疑是对保险法上说明义务之扩张。且从该规范之名称来看,专门规范资讯披露使资讯披露义务得以独立发展。
保险人说明义务之内容经由保险契约法及授权主管机关制订之法规命令,可因个别险种之特性而进一步明确化。此等规范方式对于法律关系之明确性有相当之助益[7]。现代保险产品愈加多元化,未来投资型保险产品未必尽是此办法列举之几种,亦未必尽是人身保险,近年来新兴之投资型财产保险即是其例。是否待新兴产品成熟之后又另立相关规范?更为迫切的是,“办法”之立法形式的法律位阶相对较低,且因其着重对保险业之监管而将此视为一种保险人公法上之义务而非契约当事人间之私法义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投保人之需求。无法律效果之规制,其是否足以应对投资型保险契约?又是否足以保护投保人之利益?这些问题均需进一步反思。
(二)保监会之规范对投保人利益保护之不足
从《中国保监会关于2014 年上半年保险消费者投诉情况的通报》中《涉及保险消费者权益投诉情况统计表(按险种分)》来看,投资型保险占人身保险60.70%,而占所有保险37.42%。①此数据是根据《涉及保险消费者权益投诉情况统计表(按险种分)》计算所得。由此可知,投资型保险易产生纠纷之状况颇多。从根本上说,保险契约乃由复杂之契约条款及各项契约文件所构成,属“法律商品”之一种,其内容牵涉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颇为复杂之权利义务关系,若非具有一定之知识以及花费相当之时间,不易了解其重要内容。[8]若投保人在订约之前,未能获得充分之商品资讯即订立契约,则该保险不一定符合其需求或期待,日后易产生契约上之纠纷。兼涉投资功能之投资型保险契约还不仅如此,因为其突破了一般人对传统保险之认知,投保人即使获得相关资讯并得到保险人及其代理人之一定说明,亦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投保人往往只看到投资收益而忽略投资风险,而保险人为销售保险,更有意促使此种情况之发生,并善于利用保监会之规范,诱使投保人签字确认,以规避法律责任。
我国保监会对通过欺骗、隐瞒诱导等方式,对有关保险产品之情况作引人误解之宣传或说明的行为予以特别规制,规制对象以投资型保险为主。但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往往依据《信息披露办法》判断保险人是否已尽说明义务,即以投保人在相关文书上之签字认定其已明了保险条款之内容、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②参见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保险诉讼典型案例年度报告·第五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55 页;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16905 号民事判决书,载http://bjgy.chinacourt.org/paper/detail/2011/09/id/579627.shtml,2014 年9 月13 日访问。可见,实务中采形式标准,而非实质上确认投保人是否被误导。是故要求保险人为此种形式上之说明义务,恐不足以让投保人真正了解投资型保险之目的或避免产生误解,亦难以发挥保护投保人之作用。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说明义务之规范
(一)经营者之说明义务:基于《消法》之分析
消费者之资讯弱势地位亟待改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渐趋完善。消费者之知情权与经营者之说明义务就很好地体现了权利义务之对应。消费者之知情权乃指消费者依法所享有之了解与其购买、使用的商品和接受服务有关的真实情况之权利;经营者之说明义务即经营者须依法向消费者提供与其商品和服务有关之必要信息并保证其提供之资讯真实性之义务。[9]我国《消法》第8 条对消费者知悉之具体内容有明确规定;第20 条就经营者说明义务有详细之规定,并于2013 年修订后,就提供之资讯有明确之列举,强调资讯之真实与全面。
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之行为与普通消费者一样,本质上乃一种消费行为,因为投保人签订保险契约,以支付保费之形式购买保险产品与保险人之服务,用以换取保险人对风险之保障,所消费之保险产品与保险人之服务同样具有使用价值。[10]故投资型保险契约似可适用《消法》以完善其说明义务。《消法》第28 条就提供金融服务之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之资讯有详细、具体之规定,“风险警示、售后服务以及民事责任等信息”无不是对保险人说明义务范围之扩张。且在法律效果上,经营者违反说明义务或侵害消费者之知情权,其程度达致欺诈,消费者就可依《消法》第55 条要求惩罚性赔偿。此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保险人说明义务在法律效果上之漏洞。
(二)投资型保险契约适用《消法》之难题
《消法》第28 条有所谓“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亦应有与之对应的消费者,或称金融消费者。投保人即是其一,故可被称为“消费者”。然《消法》第2 条将消费者严格限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者,在字面上排除了“为生活消费以外的其他目的”而购买、使用或接受服务之情形,在解释习惯上亦排除了自然人以外的消费者主张适用《消法》之情形。[11]人们购买保险的目的主要在于避免损失,以实现人身或财产上之保障,此与生活消费似有些许联系;但投资型保险分离帐户下之投资部分由投保人自担风险,于保障目的之外兼具投资功能,则与生活消费之通常涵义相去甚远。《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使用了保险消费者概念,并提出推动完善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要求,且《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险消费办法》)第43 条第2 款界定了保险消费者的概念,但在法律解释上仍然存在疑义,即保险消费者是否为《消法》中的消费者,亦即《保险消费办法》与《消法》的效力冲突问题。因此,尽管出于保护金融消费者之需要,学界大多认为包括投保人在内的金融消费者应可适用《消法》,然对《消法》规定之理论分析无不存在矛盾之处,是故投保人等金融消费者究竟是仅适用《消法》第28 条抑或全盘适用《消法》亦成未解难题。
此问题如此重要,乃在于《消法》对经营者未尽说明义务或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之情形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应承担之法律责任,且一旦及于欺诈之程度,则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在2013 年《消法》修订之前,司法实践几乎均将投保人排除在消费者之外,亦否认保险契约可适用惩罚性赔偿。以白国梁诉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人身保险保险纠纷案为例,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尚未将商业保险行为归属于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这一范畴”,而二审法院亦认为“我国法律目前未明确规定保险合同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双倍赔偿规定(旧《消法》的惩罚性赔偿)”①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7254 号民事判决书,载http://bjgy.chinacourt.org/paper/detail/2009/06/id/4485 6.shtml,2014 年9 月13 日访问。。而《消法》修订之后,第28 条又再次引发争议。进言之,惩罚性赔偿以欺诈为适用前提,惟有在保险人乃故意时方得以适用。这无疑使得投保人之举证责任尤为困难,亦排除了保险人过失未履行说明义务之情形。是以尽管《消法》第28 条为金融消费者适用《消法》打开了缺口,但《消法》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有限的,且第28 条为新修订之规范,司法实践中亦少有案例可循,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之效果亦难以判断。
四、我国投资型保险契约说明义务之完善
(一)现行法上说明义务之补足
投资型保险契约为保险契约之特别形式,但其本质仍为保险,仍应受保险法之约束。我国投资型保险契约主要依据保监会之相关规范,此宜为过渡性选择。未来修订《保险法》时,还是应对投资型保险进行专章规范。故探讨投资型保险说明义务之完善仍应以《保险法》为主,其他法律规范为辅。
第一,修正《保险法》第17 条之“分别机制”。该条之规定,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之规定,乃受《合同法》第39 条之影响。须注意的是,《合同法》第39 条为规范格式条款,而保险法上之说明义务应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间之资讯关系,故应侧重对投保人之保护。其实,责任免除条款已要求保险人另行“提示”之义务,在措辞上无须加以“明确”二字。且责任免除条款未必比一般条款更为重要,说明与明确说明亦未必有严格区分之必要。[12]“分别机制”导致之另一弊端是将人们的目光都聚焦于责任免除条款与明确说明,而明确说明之标准本是保险人尽一般说明义务所应达至之标准,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保险人一般说明义务。以比较法之视域观之,此条规定可谓“独一无二”。故未来我国《保险法》修订之时,应统一说明义务之立法机制,不必作说明与明确说明之界分,仅对保险人科以说明义务,另对责任免除条款尽提示义务。
第二,补足未尽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一方面,保监会并未对此问题作出明确规范。保监会意在规范保险人之行为,进而维护保险市场有序进行,故其要求保险人对投资型保险而为之特殊说明,并非私法上保险契约间之说明义务,故未来亦不太可能对此规范相应之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就《消法》现行法律框架而言,其对投保人的保护极其有限,惟一可期待的即是扩大消费者之概念,使得投保人在受欺诈之情形下可请求双倍赔偿。由此观之,法律效果之补足仍需我国《保险法》之进一步完善。
承上述,现行《保险法》在“分别机制”下,对未尽说明义务未规定法律效果,对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规定不生效力之法律效果,均不利于对投保人之保护。对其补足则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基于保险契约乃最大善意契约,双方订立契约时必须真诚,不容有欺诈意念。虽一方无欺诈意念,倘有关重要之告知系错误时,或意于告知而成隐瞒之结果时,对方均得解除契约。[13]是故应在说明之“统一机制”下,就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之情形,赋予投保人解除权,或透过契约解释来保障投保人,而无须作不生效力之规范[14]。未来《保险法》修订之时,宜统一说明义务之立法机制,在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之情形下赋予投保人选择之权利,由其决定保险契约是否解除;而当下则宜将投资型保险契约之责任自负条款解释为免除责任条款,而将不产生效力作扩大解释,认为在此种情形下投保人享有解除权。二是投保人因保险人未对重要事项说明而订立保险契约,通常会主张若保险人尽说明义务,则自己不会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因此之损害赔偿即指恢复原状。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而投保人行使解除权,保险契约溯及失效,投保人得请求保险人退还已收取之保险费。而从实务来看,对于人身保险契约(包括投资型保险契约),法院往往依据《保险法》第47 条之规定,认为此情形下保险人应退还保单之现金价值。①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3〕秀民初字第949 号民事判决书。然投保人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享有之解除权与《保险法》第15 条规定之任意解除权并不相同,因为契约之解除往往具有溯及效力,而第47 条之规定显然向将来发生效力。故严格来说,第15 条之规定并非契约之解除,而是契约之终止,是以与投保人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所享有之解除权有所不同。于此种情形之下,可援引《合同法》第97 条,要求恢复原状,即退还已收取之保险费。
(二)适合性原则之引入
完善现行法上之说明义务,仍然会面临以下问题而不足以保护投保人:一方面,资讯披露之假设前提在于藉由资讯赋予,使投保人能积极作出投资决定,但实际上投保人未必是作成投资决定之人。其可能将权限授予投资顾问与保险业者,或者依赖投资顾问与保险业者之推荐,因而使投保人之投资决定实际上仍由保险业者所掌握②Peter J.Barack:The Random Road to a New Suitability,83 Yale L.J.,1527,1528,1974.。另一方面,投保人未必有足够能力作合理之投资决定。不论是其缺乏金融知识,缺少必要的时间分析资讯还是业者不当行销,资讯披露都未必足以保护投资人。相较欧美国家,受制于我国保险业之发展,投保人与保险人间资讯不对称之情形尤为严重。投保人之权益没有得到妥善保护,说明现有之说明义务仍然有所缺憾,因而有必要引入适合性原则来弥补其不足。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已将适合性原则引入金融业法,而德国则将适合性原则置于保险契约法中,说明此亦乃世界发展之趋势。
[1]向明恩.前契约说明义务之形塑与界限——评基隆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诉字第三四二号民事判决[J].月旦法学杂志,2011(90):174-175.
[2]廖伯钧.初探2008 年德国新保险契约法——以保险人咨询建议义务为中心[J].法学新论,2010(23):120.
[3]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7.
[4][英]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中译本)[M].何美欢,吴志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5.
[5][美]克劳福特.人寿与健康保险(中译本)[M].周伏平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7.
[6][美]道宾.美国保险法:第4 版(中译本)[M].梁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
[7]叶启洲.从德国保险人资讯义务规范论要保人之资讯权保障[J].政大法学评论,2012(126):295.
[8]叶启洲.台湾保险消费者之资讯权保护——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之说明义务规范为中心[J].月旦法学杂志,2013(214):46.
[9]金福海.消费者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1.
[10]郭丹.金融服务法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9.。
[11]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84-85.
[12]陈群峰.保险人说明义务之形式化危机与重构[J].现代法学,2013(6):186.
[13]魏文翰.海上保险学[M].上海:中华书局,1947:29.
[14]樊启荣.保险告知义务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