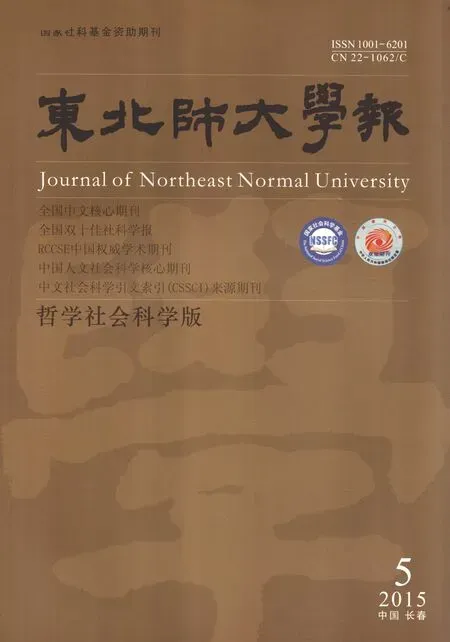论居住权的物权法保护
王明文
(1.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2.白城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吉林 白城13700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因居住权纠纷引发的案件屡屡见诸报端和网络媒体。
案例1:邱先生丧偶,有一女,后与林女士再婚。邱先生去世前留有遗嘱:自有房产一套由女儿继承,妻子林女士对该房屋拥有终身居住权。邱先生去世后,林女士与邱先生的女儿因房屋发生纠纷。其女认为自己对房屋享有所有权,因我国法律未规定居住权,故遗嘱关于居住权的部分应属无效,向法院起诉要求林女士迁出[1];
案例2:张某与张某某系父子,张某有商品房一套,后登记在张某某名下,房子由张某居住。2004年,张某给张某某出具“用此房抵偿欠款”的说明。2009年,张某某起诉要求张某腾房。法院判决:诉争房屋虽归张某某所有,但由于其未能就张某还有其他合法住房提供有效证明,基于当事人间特殊身份关系,暂不宜判决其腾房,遂驳回张某某诉讼请求。2010年,张某某将房卖给李某。李某主张张某腾出房屋,张某则以判决确认其有居住权为由,不同意腾房[2]65。
案例3:张伯和赵姨为夫妻。2005年,二位老人将房子赠予小儿子阿宏,约定有权继续在房屋内居住到百年归老。后阿宏将房子过户给妻子,后又将房子出售,仅保证老人两年的居住权。为此,老人将其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赠与。因未履行赠予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老人居住权的义务,2014年,广州中院裁定维持一审判决,撤销赠与合同,房屋返还老人[3]。
上述案例都是因居住权引发的典型法律纠纷。这些纠纷凸显了当今中国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无法保障“人人有住房”情况下,要实现“人人有房住”的目标,必然在居住权实现与房屋所有权人权利保障之间引发冲突与紧张。如何协调这种冲突和紧张,充分保护作为弱者权利的居住权?从司法实践看,由于物权法对居住权的规定尚付阙如,因此,如何在审判实务中裁判居住权纠纷,难免莫衷一是。在理论界,无论是《物权法》颁布前还是颁布后,对应否设立居住权的争论从未中断。本文拟结合上述典型案例,从学理上对居住权立法及其保护问题展开分析。
二、在当前我国立法未确定物权性居住权情形下,司法实践对居住权的保护及其不足
(一)我国居住权立法的现状
所谓居住权,是指非所有人因居住需要而对他人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排他性权利[4]。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未明确规定居住权,缺乏物权性的居住权保护制度。虽然我国《婚姻法》第42条及《〈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6条分别对离婚时弱势一方的房屋居住权、老年人居住权益的保护作出了规定。但严格地说,它们所规定的并非大陆法系民法上的物权性居住权。2005年公布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曾一度用12个条文规定了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的居住权,但由于争议较大,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时删除了相关规定,导致居住权未能获得法律化的制度表达,这种缺失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对居住权的保护出现了种种矛盾和不足。
(二)在他人之物上设定居住权的,权利人只能对所居住房屋享有居住的债权,而非物权
物权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当事人不能依其意思自由创设法律未规定的新的物权种类,也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5]。由于我国《物权法》在通过时最终没有采用居住权,由于当事人当然无法通过遗嘱、遗赠和合同设定物权性居住权,而只能通过设定债权性权利来满足其居住他人房屋和使用附属设施的现实需要。作为债权的居住权,由于权利无须公示,房屋上可能存在数个具有同等效力的居住权,这就使得居住权人难以对自己的权益获得稳定的预期。
案例1中,邱先生就采取遗嘱方式为自己的妻子在自己女儿的房屋上设立了一种债权性居住权。关于此案,依我国《继承法》第21条:“遗嘱继承或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规定,居住权及其义务仅仅存在于邱先生的妻子与其女儿之间,邱先生的女儿作为义务人,自应承担房屋上其继母的居住权负担,直至其去世。当然,由于此文的居住权并非物权,其设立无须公示,当房屋上同时存在数个债权性居住权时,极有可能引发“债权相容性和平等性与实际履行之间的冲突”[6],从而导致邱先生妻子的居住权可能无法实现。
(三)从民法理论上分析,单纯依靠债权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居住权,并不能对居住权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救济
依照物权债权区分论,物权和债权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两种不同的利益实现方式:物权主体通过对特定物或权利的直接支配来实现,债权主体则通过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来实现[7]。由此可见,物权是一种支配权,具有排他性、对世性,债权则是一种请求权、对人权。由于房屋居住权人享有的仅仅是债权,不能获得对世效力,因而无法对抗第三人,从而无法为居住权人权益保障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案例1中,邱先生的妻子可基于遗嘱对房屋占有、使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这种占有和使用并不具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如果邱先生的女儿将房屋转让与第三人,居住权人基于其作为债权的居住权将无法对抗第三人的所有权。在此情况下,邱先生的妻子唯一所能做的,只能是基于债的相对性原理,要求邱先生的女儿对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四)司法实务中,面对居住权的债权性,法官们不得不突破法律规定,通过寻求一种新的“裁判思维”,赋予居住权以物权性和物权效力,以实现居住权对第三人房屋所有权的对抗效果
如前所述,作为债权的居住权不具有对抗取得房屋所有权的第三人的效力。但理论的逻辑不能代替社会生活的现实逻辑。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往往以生活的逻辑来替代理论的逻辑。对案例2的裁判,有法官认为,张某某与李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但由于诉争房屋所有权并非完整的所有权,该所有权存在的权利负担即张某的居住权并不因所有权变更而发生改变,故张某仍享有房屋居住权。在此情况下,李某既可基于违约向张某某主张违约责任,也可待张某去世或放弃对诉争房屋居住权后完全取得房屋所有权,并可一并对张某某主张此期间遭受的损失。此一意见,是以生活逻辑对理论逻辑的一种扭曲,其错谬之处在于:
一是将张某的债权性居住权错误地认定为一种物权性权利,赋予了其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虽然在对张某是否因房屋转让而丧失居住权问题的认定上,裁判意见采用的论证逻辑是“根据利益平衡原则,作为具有人身属性的居住权应予优先保护”。但即使张某的居住权具有人身属性,从权利性质上而言,依然是一种债权,该意见明目张胆地用张某的债权性居住权来对抗李某的房屋所有权,何止谬以千里。
二是,该判决突破了法律的具体规定,用所谓具体案件判决的社会妥当性实现了对法的安定性的突破,以寻求法外正义。也许担心其意见无法在现行法律体系内找到依据,意见的主张者强调“对于兼具人身属性与物权属性的居住权”,虽然立法上并未对其做出“特别规定”,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居住权与所有权冲突的案例”,为解决问题,法官们应“大胆突破传统观念和成文法的局限”,“通过利益平衡原则”[2]67做出判决。对此,我们殊难赞同。虽然在价值取向上,现代民法出现了由取向法的“安定性转变为取向具体案件判决的社会妥当性”的转向[8]。但对社会妥当性的追求却并非毫无底线。在法治原则下遵循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原则,是每个裁判者均应优先遵循的思维方式。突破这一原则,须同时满足:第一,不优先考虑特殊性,会使具体案件的处理同法律的基本理想发生令人难以容忍的冲突;第二,特殊性同时被提升为普遍性,使今后的类似问题得到类似的处理[9]。但本案显然并不同时满足这两项条件。
为何会出现此裁判意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若依物权法定原则,法官们必将无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给张某的居住权提供有效的物权法救济。
三、完善居住权立法,将居住权纳入物权法,实现居住权的物权化
(一)将居住权纳入物权法,确立起物权性居住权,是解决当前社会居住需求这一普遍性社会问题和物权立法完善的必然要求
1.从时代需求看,确立物权性居住权,是解决当前社会对居住权需求这一普遍性社会问题的必然要求
实现“人人有房住”虽非关国家社稷、民族存亡,但对“过小日子”的平民百姓,却是“天大的事”。在当前,受制于主客观条件,尤其是土地资源稀缺,个人无力承受畸高的房价情形下,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居住问题难以通过房屋买卖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而是不得不通过取得居住权来解决。
首先,居住权有着庞大的需求主体,并非仅限于父母、离婚后暂未找到居所的一方和保姆。有学者将居住权设立的目的仅限于解决父母、离婚后暂未找到居所的一方(通常是女方)和保姆这三类人的住房问题,并认为这三类人的居住权需求,完全可通过替代方案得到解决[10]。既然问题都解决了,居住权在我国断无设置的现实需要。
上述学者的观点值得商榷,先不论替代方案是否可行,居住权的适用主体是否仅限于上述三类人就很可疑。事实上,居住权的主体并非仅限于上述三类人。如天津刘某,身有残疾,孤身一人,长期与大哥一家共同生活。大哥去世后,大嫂及侄子要求其搬出。法院认为,刘某长期与被告一家共同生活,已成为家庭成员,其居住权不因其大哥死亡而被剥夺[11]。此案中,刘某就并非属于前三类人。此外,有学者认为,居住权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并不仅限于父母、离婚妇女、保姆,还包括未成年人、远亲、收留的流浪儿童、孤寡老人以及特定时代上山下乡返城居住在舅舅、姨妈、叔叔、姑姑家的知青等人群。此外,现实生活中还会存在很多非立法者所能预料的对居住权的需求[12]。
其次,物权性居住权制度的设立,有助于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从1997年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养老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2013年,我国开始探索以房养老的试点,但困难重重。如果在物权法上确立起居住权制度,允许老年人在自己所有的房屋上设定物权性居住权,同时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将房子出卖给自己的子女或他人,事先实现房屋的变现,既可解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让老年人老有所居,还可减轻子女的养老压力,不啻是一种实现老年人自我养老的有效措施。
再次,居住权制度有着广阔的社会需求空间,其设立并非单纯为解决家庭成员或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而设定。从居住权的源流看,源自古罗马的传统居住权是一种人役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权的功能和适用范围已突破了传统人役权的限制:在适用范围上,由仅局限于离婚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逐步演进到广泛适用于一般财产权利人;在社会功能上,则从保护弱者的社会性功能逐步演进到作为实现所有人对财产利用多样化手段之一的投资性功能[13]。除传统居住权即社会性居住权外,投资性居住权,正随着现代社会人们对居住和投资的双重需求得到确认。德国1951年颁布的《住宅所有权及长期居住权法》所规定的长期居住权就是其典型代表。我国物权法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合资建房或购房时的居住权、分时度假酒店式产权中的居住权等投资性居住权作出规定。
2.从物权立法看,确立起物权性居住权,是应对居住权保护要求的物权法回应
依创设方式不同,居住权可分为物权性居住权和债权性居住权。两种居住权性质不同,权利内容、效力和保护方式也迥然有别。债权性居住权受制于自身特性,难以为居住权人提供充分的保障,也无法有效地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宜确立物权性居住权。
首先,确立物权性居住权,居住权人可依其物权,有效对抗房屋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排除其不当干预。案例1中,若邱先生的妻子享有物权性居住权,只要其在法定范围内合理使用住房及其附属设施,作为房主的邱先生的女儿即无权干涉。即使邱先生的女儿主张邱先生的妻子搬出或强行将其清出,邱先生的妻子完全可以其物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返还房屋。即使房屋灭失;若邱先生的妻子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还可以要求给予适当安置。
其次,确立物权性居住权,居住权人可采用物权法救济方法有效对抗第三人,排除第三人的侵害。物权性居住权具有对世性,如2005年《物权法(草案)》第185条“居住权设立后,住房所有权人变更的,不影响居住权”的规定。案例3中,张伯和赵姨基于赠予合同有权向阿宏主张居住权。若阿宏不履行赠予合同所负义务,依《合同法》192条,合同当可撤销无疑。但当阿宏及其妻子一旦将房屋售出,由于张伯和赵姨此时拥有的居住权仅具有债权效力,将无法产生对抗买受人的效力。故在此情形下,法院所做出的“撤销赠与,将房屋过户回赵姨名下”的判决不可谓为正确的判决。在此,法院事实上错误地赋予了张伯和赵姨债权性居住权以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社会有着对居住权的强烈需求。而“国家对一种权利体系所承担的基本义务”之一,在于“通过法律形式对这种权利体系予以确认”[14]。我国宜在未来整合我国民法典物权编时将居住权确定为一种物权。
(二)设立符合现实社会生活需要的物权性居住权,建立完善的居住权体系
在居住权的物权法立法上,建立什么样的居住权体系,以应对当前社会生活对居住权的现实需要,是一个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首先,未来的立法除规定意定性居住权,还应对法定居住权从立法上做出明确规定。2005年《物权法》草案第181条:仅就意定居住权做出了规定。所谓意定居住权,是指由房屋所有权人通过遗嘱、遗赠和合同等方式在自己所有的房屋上为他人设立的居住权。法定居住权,是指通过法律规定而设定的居住权。例如,法律可对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房屋享有的居住权,或未成年子女对其父母的房屋享有的居住权做出明确规定[15]。《物权法(草案)》第191条中所列因“婚姻家庭”产生的居住权,就属法定居住权范畴。对这部分具有人身属性的居住权,法律应无例外地赋予其物权性,确认其“为特定的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当然享有”,所有人“不得通过遗嘱、遗赠、合同等予以剥夺”[16]。
其次,未来的物权立法除不宜仅规定社会性居住权,对投资性居住权做出设定。所谓社会性居住权,是指“基于社会上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易遭受侵害而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而设立的居住权。社会性居住权为“生活中的弱者”而设立,一般不需要“居住权人支付对价”,可“满足弱势群体对房屋的需求”,有利于解决“家庭成员中对房屋的需要”[17]。社会性居住权为典型的人役权,一般不得转让和继承。所谓投资性居住权,是指为了消弭物权法定原则的消极作用,满足人们利用财产形式的多样化需求而提出和设立的居住权[18]。投资性居住权是适应社会发展对房屋的投资性需求而出现的。从社会性居住权向投资性居住权的转向,拓展了居住权的适用领域、范围,扩展了居住权的功能,即从居住权的社会性功能——保护弱者拓展到投资性功能——满足人们利用财产形式多样化要求的功能。因此,关于居住权的物权法设计,应适应物权理论从所有向利用的转变[19]趋势,对投资性居住权作出规定。
再次,在居住权体系和框架的建构上,我国未来的民法典物权编不应将居住权囿于家庭领域,而应突破其人身专属性,摆脱人役权性质的限制,全面考虑家庭生活保障和一般财产利用和投资领域的不同需要,对居住权做出全面的规定。具体而言,有两条不同的路径:其一,是在未来的物权法中将居住权设立为独立的、适用于一般财产权利人的投资性居住权,对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居住权问题,则在婚姻家庭法中另行做出具体规定;其二,首先对调整各种物权性居住关系的居住权作出统一规定,然后对那些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居住权以但书形式作出例外性规定[20]。
四、结 论
物权制度的演变史,实质上是一部他物权制度的发展史。物权法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多极的物之利用关系提供制度安排,以建立多极物之利用秩序[21]。作为用益物权的居住权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受制于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不可能像创设债权一样,在物权体系之外任意创设居住权这一新的物权类型。在此情形下,未来民法典宜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物权编中将居住权纳入其中,赋予其通过登记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以发挥房屋效用,真正实现“屋”尽其用。
[1] 杜鸿亮.遗嘱中设定房屋的居住权是否有效[EB/OL].http://data.jfdaily.com/a/6066216.htm.
[2] 孙翠,赵明静,孙卓.居住权与所有权权利冲突的裁判思维分析[J].人民司法,2013(23).
[3] 刘晓星.儿子将父母所赠房子出售 仅保留老人两年居住权[EB/OL].http://news.eastday.com/s/20140709/u1a8206642.html.
[4]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68.
[5] 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总第1册[J].台北:三民书局,2003:7.
[6] 孙毅.我国多重买卖规则的检讨与重构[J].法学家,2014(6):114.
[7] 王轶,关淑芳.物权债权区分论的五个理论维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7.
[8] 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J].中外法学,1997(2):25.
[9] 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8.
[10] 梁慧星.民法典起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6:244-245.
[11] 物权法草案对居住权的规定引争议[EB/OL].http://www.51test.net/show/1089147.html
[12] 申卫星.视野拓展与功能转换:我国设立居住权必要性的多重视角[J].中国法学,2005(5):82-83.
[13] 申卫星.视野拓展与功能转换:未来物权法设立居住权必要性的多重视角与制度构建[Z].海峡两岸民法典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中卷:物权法),第348页.
[14] 程燎原,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82.
[15] 钱明星.关于在我国物权法中设置居住权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2001(5):13-22.
[16] 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35.
[17] 陈华彬.设立居住权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利益[N].检察日报,2004-02-09(3).
[18] 申卫星.物权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09.
[19] 林刚.物权理论:从所有向利用的转变[J].现代法学,1994(1):23.
[20] 王富博.居住权制度适用范围初探——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J].法学论坛,2006(1/2):72.
[21] 高富平.物权法原论:第2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