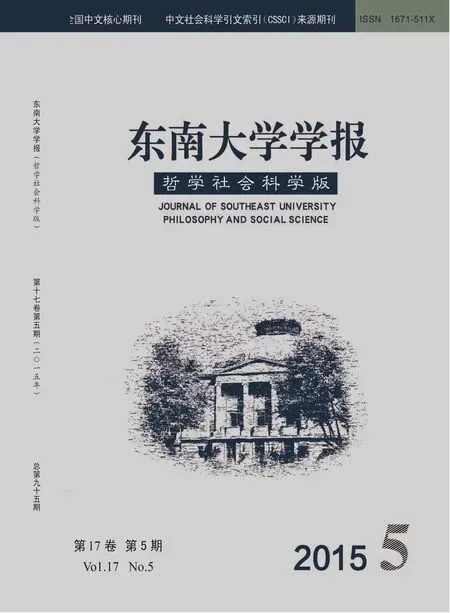民国时期医讼案鉴定制度研究
王启辉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9)
医疗鉴定是审判医讼案的关键环节,中国现代医讼案鉴定制度始于民国,其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外行鉴定内行”的知识性难题,这种难题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既是知识性的,也是制度性的。时至今日,医讼案鉴定的制度设计,仍无法回避“谁来鉴定鉴定者”的知识拷问。研究民国时期医讼案鉴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为当下医讼案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民国医讼案鉴定的肇始
1.传统检验制度的演变
传统中国没有独立的法医鉴定制度,但有历史悠久的仵作制度。仵作专门从事传统刑事狱案的检验活动。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
大州县额设三名,中州县二名,小州县一名,仍各再募一、二名,令其跟随学习,预备顶补;各给《洗冤录》一本,选委明白刑书一名,为之逐细讲解,务使晓畅熟习,当场无误;将各州县皂隶裁去数名,以其工食分别拨给,资其养赡。[1]5055
仵作制度发展到了清朝末年,已经流弊丛生,远远不能适应官府办案的需要,传统仵作开始向检验吏过渡。清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云贵总督沈秉堃等具奏将仵作改为检验吏,他们认为:
各厅州县仵作,虽有例设名额,大率椎鲁无学,平日于洗冤录一书,不特未经讨论间有不识字,义欲谙习文理通晓检验者实已戛乎其难,每于相验事件,尚多未能了澈,驯至误执伤痕颠倒错乱不一而足,若遇开检重案无不瞠目束手。[2]
徐世昌等人分析认为仵作制度失效的原因是:一方面,检验是专门的学问,需要生理、解剖诸术,而且必须确有经验,才能充当此任;另一方面,在社会看来,仵作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供奉衣食物极薄,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仵作职业不具有吸引力,不屑于充任仵作,而对于椎鲁无学之辈来讲,仵作又成了他们的谋生之所,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承担检验职责,结果导致有能力的人不当仵作,无能力人的滥竽充数。
基于传统仵作制度的以上弊端,徐世昌等人在《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改仵作为检验吏给予出身片》的奏章建议:
通饬各厅州县每庭选送身家清白、文理明通、年在二十岁以上聪颖子弟各二名,来省城入堂肄业。凡生理、死理检验法检验术修身体操,入门以洗冤录为主课,添用实验成案、中西医书、人体解剖学及在官法戒録等书择要教以补充洗冤录之所不足。定期一年,毕业后给予文凭,发回各庭充役,改名曰仵书,优给工食,比照刑书一体给予出身。
但这种新的替代传统仵作的检验吏制度,并没有真正发挥检验的实际功能,清王朝旋即覆灭。同时,检验吏制度在学科方面仍然能以《洗冤录》为主,无法真正为司法服务。
2.西式法医的引入
1915年,奉天高等检察厅呈司法部遵将高等法医学校原定章程经费表分别更正删除请鉴核施行文称:
为呈请事案,查本厅所辖高等检验学堂拟改为高等法医学校,前经本厅呈请核示在案,二月十五日奉指令开据呈及章程并表均悉检验事关重要,非有专门学术毫厘千里遗误滋多,该厅为慎重民命起见,拟将检验学堂改为高等法医学校,预培此项人材,用意甚善,本部自应准予立案,惟章程所载学科,内有洗冤录一课,究系旧时检验制度,不甚适用,应即从删,至解剖尸体以供学术上之研究,各国本甚注重,因中国风俗习惯不同,应取渐进主义,所称将来死囚或罪犯有愿将尸体解剖留有确切证书者,发交该校藉供实习一节,应准酌量办理。[3]
该史料显示,当时国民政府认为《洗冤录》是“旧时检验制度,不甚适用”。这就使延续了几百年的以《洗冤录》为主的传统检验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西医解剖为主的现代法医制度开始引入。
奉天检验学堂改为奉天高等法医学校后,制定了专门的学校章程即《奉天高等法医学校章程》,其中第2条规定“本校以养成高等法医人材担任审判上之鉴定为宗旨”。现代法医司法鉴定制度初现端倪。
从当时的高等法医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课程内容完全是西医化的。20多门课程中,解剖学、病理学、卫生学、细菌学、精神病学、药品鉴定学、裁判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这些专门学科和知识不仅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体系来讲是新的,对中国传统医学来讲也是新的,而对传统检验人员如仵作、检验吏的培训内容来讲,也是开创性的。[4]
历史上看,无论是雍正三年的仵作制度所规定的仵作培训内容,还是宣统元年所规定的检验吏的培训内容,其知识体系都是以《洗冤录》为主。高等法医学校的成立,完全排除了《洗冤录》为主导的培训内容,事实上宣告了传统检验制度的终结、现代法医制度的确立,这是历史性的重大变革。随后,法医院校和法医培养制度的影响慢慢向全国扩展。
3.法医鉴定医讼案的制度草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医培养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伴随着法医教育的发展,法医鉴定制度和法医鉴定组织也逐渐出现。
1932年8月1日,司法行政部成立法医研究所,任命林几为所长。[5]按照《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暂行章程》第1条规定:“本所属于司法行政部,掌理关于法医学之研究、编审民刑事案件之鉴定检验及法医人才之培育事宜。”该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医鉴定机构。
1932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颁行《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办事细则》第4条规定,该所第二科分为四股,具体职责如下:第一股掌关于化验毒质及与民刑案件有关之一切化学成分事项;第二股掌关于验断尸体或动物死体事项;第三股掌关于诊察事项;第四股掌关于检查物证病原及一切其他法医学检查事项。[6]1936年5月2日,司法行政部颁行《司法行政部法医学审议会组织大纲》,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为“计划改进法医及协助解决医学上之疑难问题起见,特设立法医学审议会,其会址附设于法医研究所。”[7]1936年7月11日,法医学审议会成立。按照《司法行政部法医学审议会办事细则》第2条规定,审议会设四组,内科组、外科组、理化组、病理组。至此,民国法医鉴定制度得以完善。
虽然法医教育制度和法医鉴定制度日趋完善,但这些全新的以西医为基础的法医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当中,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分量和比重偏小,不仅西医不能满足民众医疗的需要,法医制度的发展及法医人才的培养,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现代法医鉴定需要来讲,法医人才远远不足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因此,时人姚致强认为,至1933年全国法院“除江浙二省外,其他各省,皆无法医之设置”,遇有疑难案件“致检验吏无法收拾者”,各法院唯有“委托本地有名医师或医师公会代行鉴定”。[8]
作为草创的法医鉴定医讼案制度,与传统的仵作检验制度、检验吏检验制度相比,拓宽了鉴定的范围,提高了鉴定的专业性,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从法医职业属性来看,其最专业、最擅长的业务应是死亡原因鉴定。如果法医包揽医讼案的鉴定,就会产生两个比较明显的弊端:一,法医鉴定西医讼案超越了法医的业务能力;二,法医鉴定中医讼案超越了法医的知识体系。这种“跨界发言”的制度安排,既是不科学的,也是非正义的。
二、民国西医讼案的鉴定
1.法医鉴定西医讼案
民国初期,初步建立了西医讼案的鉴定制度,具体表现为:一是,鉴定主体制度。民国初期的西医讼案的鉴定主要由西式法医进行。二是,鉴定范围制度。首先包括医疗诊察事项,也就是说就因疾病的诊断行为发生纠纷的,属于法医鉴定范围,比如《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办事细则》第4条即规定“关于诊察事项”属于法医鉴定的范围。其次,法医鉴定范围还包括医疗行为、护理行为、司药行为,具体来说因医师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看护在护理过程中以及药剂师在用药过程中的行为出现纠纷的,都属于鉴定事项。中国现代法医学之父林几在《二十年来法医学之进步》一文中也提到司法之民刑案件中“医疗看护司药等责任过失问题”属于法医鉴定的范围。[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以尸体解剖为中心的检验鉴定制度仍然得以延续,也就是说法医鉴定的范围在以尸体解剖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民国时期,法律规定医讼案由法医行使鉴定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医讼案的医学鉴定,与法律规定并不一致。实践中主要做法是法院向没有法律授权的医学机关征询意见。为此,时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长的牛惠生于1935年2月呈请司法部明令各地法院关于医病讼案应请正式法医剖验尸体,以明真相事。牛氏认为:
年来,医病讼案纷至沓来,法院于接受此种案件时,多函询国内之医学机关,以求正确之鉴定;盖此项鉴定之文件,皆根据学理与事实而来,初无偏颇之意见也。惟一般病家于败诉之后,多疑及医学机关之鉴定文字有袒护同道之嫌,以致不服而上诉者,比比皆是[10]。
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当时医病纠纷已呈逐渐增多之势,为满足司法审判的需要,法院对于医疗专门问题往往求助于医学机关。从专业角度来看,对于医讼案的鉴定应当由医学专门人员来进行,这既符合事实,也符合学理,而且容易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但是,由于医学机关是医师行业组织,由其鉴定医师的医疗行为,往往会给病家造成同道袒护的嫌疑,以至于病家,乃至社会对鉴定结论缺乏信任,基于此种鉴定结论作出的裁判,往往导致更多的上诉案件。
牛氏进一步从病人死亡的原因及法院裁判角度分析认为:
医家治病,不幸而病人出于死亡,其原因究在于医家之误治,抑为疾病之不治,除主治医师之外,绝非他人所能揣测其原因,而加以切实之判断也。故医学机关之鉴定文件,也只根据法院之来文,作学理之推测,因此,法院于判决时无论胜诉之于谁方,皆难使败诉者心悦而诚服[10]。
在病人死亡的医讼案中,从专业角度来看,死亡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死亡既可能是医疗过错行为导致的,也可能是病人的自身疾病所致,这种死亡原因的判定,除主治医师更有深切的认识之外,其他的局外人或非当事人很难做出客观、真实的判定,如果仅凭“文件”来做间接、学理的推测更难得出客观的结论,也难使败诉者心悦而诚服。牛氏因此呼吁:
医之对象为病人,病人既死,则其对象为病人尸体,不幸而涉讼,亦当以尸体为唯一铁证,医者之是否误治,一经剖验尸体,不难彻底明了,否则舍病人之尸体而尚诉状或口头辩论之空谈,穷未见其能得是非真相也。惟是,尸体剖验,若委之于毫无医学常识之仵作之手,则不但不能使真相大明,抑且有构成冤狱之势。故此项剖验工作,除正式法医外,殆非他人所能胜任。[10]
牛氏认为,在出现病人死亡的医讼案中,尤其应当以尸体为中心展开专门的法医鉴定。从专业角度讲,不难对死亡原因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但如果不以病人尸体为中心而是根据诉状、辩论来分析死亡原因,既不能得出客观结论,实际上也无异于空谈。所以牛氏认为,对死亡医讼案的鉴定工作既非传统仵作所能胜任,也非医学机关文件推测所能解决,而应以尸体为中心由法医专门从事此项工作。
法医都是西医知识出身,其鉴定结论大致与西医临床医学相同,因此,法医研究所的鉴定,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医师的权益。例如,1936年8月25日《申报》登载一起案件:
上海虹口公平路普安医院院长兼仁济医院外科主任医师陈澄,被妇人马董氏在第一特区法院拎诉,因业务过失致使其子马老大于死一案,法院将陈之诊断书等送交法医研究所鉴定,推事冯世德开庭续讯并将法医研究所之报告发表,谓鉴定结果:陈之诊断并无错误,且必须用此种治法,其马老大之死实因身体亏弱、肚中有毒入于心脏所致,于陈之开刀并无不合,后即庭宣告判决陈澄无罪。[11]
实际上,民国时期,医病纠纷的鉴定实行的是多轨制,即既有法医鉴定,也有医学团体的鉴定,甚有不经鉴定,直接由司法官断处的。
2.从法医鉴定到西医师鉴定
法医鉴定医讼案为西医界所推崇,但是,随着对医讼案的深入认识,医界发现单由法医鉴定医讼案有其局限性,由医学团体鉴定医讼案更能体现鉴定的科学性。
1934年11月13日,为保障医家病家纠纷之诉讼案件,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呈请司法行政部文要求医讼案经过正式医学机关团体鉴定后判决。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注意到:
窃查国内年来医家病家纠纷,有纷至沓来之势。每一案件发生后,动辄由法院或被控之医家,起诉之病家将全部事实及经过情形,请求各地之正式医学机关公正鉴定,以备判定时之参考,用意至为周密,惟近据被控医师之报告,仍有少数法院之法官,对于此项鉴定文件抹杀不问者;亦有未经正式医学团体鉴定,而妄加判决者。[12]
当时的中华医学会已经认识到医讼案的专业鉴定对于维护病家和医家的合法权益有重要、积极的意义,但在当时也存在少数的法院和法官在审理医讼案时,不进行专业的医学团体鉴定而妄加裁判的,也有对于医学团体之鉴定报告抹杀不问的。中华医学会认为,由医学团体鉴定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用意至为周密”,意在推动此项鉴定制度的普遍运行。
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要求医讼案由医学机关团体鉴定的理由是:
医之为学,甚为专门。病情之变化更无常规。医师治病,初无不竭尽其智力者。不幸而病人死亡,究其原因,或为疾本不可为,或已失其时机,或因病人之特质,或系医师之误治,纷纭复杂,非深于医学者,不能分析也。故当此种案件发生,法官之处理自必棘手。盖法官虽明于法律,而非洞悉医理。如仅衡以人情,绳以法条,而不顾及其医学上之特殊情形,则真情难得,或有累于明德,是以凡正式医学机关根据学理与事实之鉴定文件,正为法官判断上之唯一良助,不言可知。[12]
上述理由重申了医师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非一般非专业人员所能判定,法官作为研究、适用法律的专门人员,自然没有判定医师医疗行为是非的专业能力,医学团体的鉴定应为医讼案的必然选择程序。但是,时人已经注意到法医鉴定医讼案的局限性问题。1947年《医潮》就南京市立医院阑尾炎麻醉休克死亡案发《向司法界进一言》称:
南京市立医院阑尾炎患者刁某因腰椎麻醉发生休克身死,地方法院竟判主治医师钱明熙以一年又六月之有期徒刑。早期治疗在任何病症里是很值得重视的,但是除了少数的例外,在多数的病症里,数十分钟的延搁不至于影响治疗的效果。实际病人未到医院之前,不到严重万分,是不肯就医的,而且是先求仙方,再试秘药,请最出名的中医凭过脉,吃了几剂草药不成功,请西医扎针也无效,最后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这总想到医院。这时挂急症号,急如星火地催请医师,其实前期也不知延误了许久!有效的治疗期间,已经失去,假如延误的过失,这过失是病家的,站在人道的立场,检察官应对病家提起公诉的。我国法官每以医学外行身份,专凭一己之见判断有关医药问题的是非,殊不自量,实则就是法医学者遇有特殊问题,也征询专家的意见,以为评判的根据。法贵平正,不平则鸣。这一点也极望司法界予以注意。[13]
以上史料显示,医界认为有关“医药问题”法官是外行人,没有能力判断医药问题的是非,即使是具有西医背景的法医,遇到医药问题上的特殊问题,应当征询医师的意见,而不是仅凭法医自身力量对医药问题作出评价。
1948年,广州牙科医学研究会副会长池方就法医鉴定医讼案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医师因业务上关系而致人死亡或伤害者,在刑法上属于业务过失,其罪较普通过失为重。但所谓过失之解释,在刑法第十四条为“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惟究竟何者为“应”为“能”为“不”为,自当以各种业务之学术进度及当时之实际情形以为断。查医学在各种技术中较为繁难复杂,且吾人知识范围有限,近代医学进步,日新月异,倘一旦发生医案诉讼,则恐非司法官或法医师少数人所能正确鉴定者。为慎重罪刑及保障医事人员业务起见,本人以为苟有此类事件发生,应由公私立医学机构团体,或该业务法团,共同加以缜密之研究,然后根据其事实处断,方足以成信。[14]
池方的以上论述实际提出了医讼案鉴定时适用的医学标准和相应的鉴定人选择问题,即医讼案“自当以各种业务之学术进度及当时之实际情形以为断”,非司法官或法医所能鉴定者,应由公私立医学机构团体或该业务法团处断。而公私立医学机构团体为医师组织,池方认为,医讼案的鉴定应当由医师组织鉴定医师的行为,而非由法医鉴定医师的行为。对此,宋国宾在其《医讼之面面观》一文中提出了相同的见解:
夫医学为至专门之科学,病人之不治,死于医或死于病,非专家不能判也。法官虽熟于法律之条文,而不娴于医理,故受理之际,必须函请正式医团作公正之鉴定,以为判决之时根据,而同时施于尸体剖验,以求事实之大明,法官不得存一毫武断之态度于其间也。鉴定矣!剖验矣![15]
即依宋国宾之见,医讼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病人没有死亡的,由医团作公正之鉴定;另一种类型是病人死亡的,应该以尸体为中心,以法医为主体进行死亡原因的鉴定,同时,由医团对医师的医疗行为进行鉴定。对此,《医潮》刊发的以南京市立医院的刁某身死案为例,向司法界强调病理解剖的重要性。
即以南京市立医院的刁案为例,患者有无心脏病,是地院裁判的关键之一,但是既无身后检验的根据,则殊难令人心服,至于患心脏病者可否施以麻醉剂,虽为另一问题,自亦不得一概而论。心病种类、病势轻重,皆为施以麻醉剂前必须考虑的问题,若患者故后,曾经病理解剖,详为检验,则一切疑问,可望迎刃而解。非但医者可以增加见识,法律上亦少困难。[13]
民国时期,医界对医讼案鉴定主体的认识,基本与现代医疗鉴定制度设计理念相吻合。
三、民国中医讼案的鉴定
1.对西医师鉴定中医讼案的质疑
“内行鉴定内行”能够保障对专门问题判断的科学性。临床医学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其专业问题的鉴定也应当遵循“专业问题同行鉴定”的科学规律。
民国时期,中、西医并存,在医讼案中,按照医学专业规律,应当是中医师鉴定中医讼案、西医师鉴定西医讼案。如此,才能保证医学鉴定的科学性和知识合法性。但是,民国时期,在有关医讼案鉴定的问题上,存在剥夺中医鉴定权的现象。
例如:
1929年,浙江鄞县有一姓张的人家,儿子张志元未满两岁因发热并全身出现红斑,急忙请医治疗,郑蓉孙医师诊断为麻疹,开的处方中有生石膏、生大黄等药,张志元服药后症状并未减退,后经两次复诊仍无效,于是转请董庭瑶医生诊治,用药也以生石膏、生大黄为主,仍未见效。随后不久患儿口鼻流血死亡。张家告到法院后,法院委托应锡藩医师进行鉴定,应锡藩为当地西医,他的鉴定意见是,医生过早应用了寒凉药物,可见郑蓉孙、董庭瑶先后对于张志元诊症究竟有无已达透发之程度并不精密审察,遽处以寒冷药剂以致疹点未能透发,因而致死,自属玩忽已极。[16]
从此典型案例来看,当时对于中医引起的讼案,在鉴定过程汇中,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讼案发生的原因是由中医师的医疗行为引起,从专业角度来讲,应当属于中医讼案,需要具体的中医专业知识来对医疗行为进行专业判定。二是,从主体来看,受诉法院委托了西医师一名,让不具有中医知识背景的应锡藩医师行使对中医讼案的鉴定权,这从专业性角度来看,确实有不合理之处,毕竟中医和西医分属于不同的专业知识体系,而且其内容十分庞杂,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医师来讲,很难做到既精通中医又熟悉西医,基本不可能做到中西贯通。因此应锡藩医师鉴定两名中医师的医疗行为,确实缺乏正当性。三是,从鉴定结论来看,应锡藩医师认为病人死亡完全是由于医师的医疗过错所致,这很难排除应锡藩医师到底是同情病家或是利用自己的鉴定权打压、排斥中医。
这起中医讼案既引发了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满,更引起了人们对此鉴定制度的反思。本案中,中医讼案由一名西医师鉴定,对此鉴定结果,郑、董二中医师当然不服,遂求助于宁波中医协会。宁波中医协会为“西医鉴定中医方药”上书卫生部请求卫生部转司法部请予纠正。宁波中医协会认为:
中西医术向属异途,中医无西医之学识经验,西医亦无中医之学识经验,是各自为学,不能相通……是此次冯检察官将郑蓉孙等中医所开之药方不发交中医专家研究,而竟发交西医应锡藩鉴定,似属有怠摧残中医;应锡藩西医对于郑蓉孙等中医所开之药方,不肯辞以不敏,而竟妄行鉴定,似属乘机推翻中医。苟此案成立,则将来国粹之中医无振兴之希望,大多数业中医者之生命尽在西医掌握之中,生杀予夺,惟其所欲矣。[17]
此案发生在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中医案”之际,在这种中医普遍得不到中央政府尊重的大背景之下,反映在中医讼案鉴定权的争夺上,西医明显具有垄断医讼案鉴定权的倾向,即使司法人员面对中医讼案的鉴定时,往往首先选择西医师,而不是中医师,但就从专业的角度而言,由西医师鉴定中医师的医疗行为,确实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之处,毕竟“中医无西医之学识经验,西医亦无中医之学识经验,是各自为学,不能相通”。对于接受鉴定委托的西医师应锡藩而言,其谨慎、合理的做法应是婉拒检察官的鉴定委托,而不应越俎代庖、妄行鉴定。这种非专业的鉴定既不能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也容易引起中医群体怀疑、抗争。
实质上,宁波中医协会鲜明地指出了“外行鉴定内行”的问题,但这本质上是当时立法及司法官的严重的西医倾向,故宁波中医协会认为是摧残中医、推翻中医。然而,卫生部对宁波中医协会的批复是:
该案既在地方法院涉讼,应候该院依法讯判,所请转详司法部一节,着毋庸议。仰即知照。[18]当时的卫生部对宁波中医协会的专业呈请采取了非专业化、司法化的消极处理方式,认为这是一个具体的司法个案问题,不是医学专业问题。在这里,卫生部转移话题、偷换概念,有意避开了当时争议较大的鉴定权的配置这一敏感话题。也就是说,如果中医讼案的鉴定权交由西医,就有可能威胁到中医行业、中医群体的生存空间,中医讼案的鉴定权问题,虽然在个案上属于司法问题,但在制度安排上,因关系到整个中医行业的发展,本质上也属于卫生部职责范围。
由于其主张未能得到维护,宁波中医协会再次上书卫生部。然而,宁波中医协会于1929年2月28日得到的批复是:
查医药无中西之分,应以科学为原则,此案以西医鉴定中药系法院指令办理,本部依法不能过问,所请应毋庸议,仰即知照。[19]
国民政府卫生部的批复貌似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中立地评判医药无中西之分,但科学本身又是西学的知识话语,因此,卫生部事实还是站在了中医对立面。不仅如此,卫生部更是以司法问题为由回避争议背后存在的鉴定制度的设置问题。
就“西医鉴定中医”问题提出异议的并非只有宁波中医协会,浙江省中医协会也呈文卫生部,但其收到的复函仍是:
鄞县地方法院令西医鉴定中医药方请予纠正一节属司法范围,本部未便过问。[20]
2.中医师鉴定中医讼案的确立
在民国时期,对于中医讼案的鉴定组织及鉴定程序有明文规定的,当属中央国医馆和中西医药研究社。
1935年11月8日,中央国医馆呈文司法行政部称:
查各省市国医因执行业务发生处方诉讼案件,该管法院动辄以刑诉第一百十八条委任国医分支馆或医药团体充任鉴定人,而当事人以不服鉴定之故或同法一百十九条声明拒却,致诉讼无法解决。倘不令筹补救方法实不足以断疑案而昭折服。本馆有鉴于此,爰订处方鉴定委员会章程延聘富有学识经验之国医九人为委员,嗣后各级法院遇有处方诉讼案件,如当事人不服当地国医分支馆或医药团体之鉴定声明拒却时,本馆交由该委员会重新鉴定,以昭慎重。[21]
司法行政部于1935年11月21日通令各级法院一体遵照。
从此史料来看,到了1935年,对于中医讼案的鉴定有了明显的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凡中医师执业过程中所发生的处方诉讼案,不再交由西医师或西医师组织来鉴定,而是委任国医分支馆或医药团体充任鉴定人,实际上就是由中医师鉴定中医讼案。二是,如果鉴定结论不能被当事人所接受,对于中医处方讼案可以交由更高层级的处方鉴定委员会鉴定,而委员会成员完全是由“富有学识经验之国医”充任,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赋予了中医师对中医讼案的鉴定权。
同时,中央国医馆也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处方鉴定委员会章程》[21],一并呈请司法行政部。按照其规定:(1)处方鉴定委员会之鉴定以当事人不服当地国医分支馆或医药团体之鉴定,经法院函请该馆重新鉴定者为限。因此,其鉴定为重新鉴定,为首次鉴定结论之后提供救济机会。(2)委员会设有委员七人至九人,由馆长聘任之并指定一人为主席,须由委员过半数之出席方得开会,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方得议决。因此该鉴定施行多数人合议制。(3)由主席指定委员一人做初步审查,初步审查意见分送各委员签注后,应由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初步审查意见提出会议如不得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同意时,应由主席另行指定委员一人复审查;复审查意见分送各委员签注后,应由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初步审查意见与复审查意见提出会议如均不得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时,应由主席呈请馆长裁决。(4)鉴定书由指定之委员作成,但均由全体委员签名盖章交主席送呈馆长核定,以示负责。
积极推进中医讼案内行鉴定的还有中西医药研究社。1936年,中西医药研究社成立了“中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并向司法部呈文呈请训令全国各法院指定该社为中医药讼案鉴定机关之一,鉴定委员会由“中西医药研究社理事会选聘中西医药专家九人组成”,并明确提出“遇中医药讼案之须鉴定者均委中医团体行之。”[22]中西医药研究社认为:
以中医药团体而行中医药讼案之鉴定,于理固无不合,惟我国今日之中医药团体尚少真正之学术机关,此可不必讳言,则其鉴定时贿赂之施,感情之用,又何能免。[22]
中西医药研究社首先肯定了中医药团体鉴定中医药讼案的合理性,但在现实中,这种合理的鉴定制度未必能够得到落实,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学术机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当时的制度容易受到贿赂或人情因素的干扰。
而针对法医鉴定中医的现象,中西医药研究社认为:
我国今日之医制,中医与西医并行,使今日之法医,以行西医药讼案之鉴定则可,若行中医药讼案之鉴定,则殊非宜也。因中医药讼案完全根据经验而来,与科学医药不同,故其治病亦崇尚经验而疏于理论。若法医之曾未一涉中医之藩篱,宜其无能为得失之观测也。故法医之在我国,不克尽负医药讼案之鉴定责职,已甚明矣。[22]
中医药研究社再次重申了“同行鉴定”的基本原则,对当时的医学鉴定而言,中医药研究社认为法医属于西医,由法医鉴定西医讼案“则可”,但是如果由法医鉴定中医讼案,则超越了法医的鉴定能力,不能得出中医师“得失之观测”结论。
为争取司法部认可,中西医药研究社承诺接受鉴定“不受酬报”,同时,在《中西医药研究社中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章程》第5条规定:
本会本中西医药研究社服务社会之旨,为社会服务,接受中医药讼案之鉴定,及审定他人中医药讼案之鉴定,不受报酬。[22]
需要注意的是,《中西医药研究社中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章程》就鉴定的范围和鉴定适用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在鉴定范围方面,第14条规定:如讼案有须理化检验者,本会得转请法医研究所或上海市卫生试验所代行之。第15条规定:如讼案有须检验或解剖尸体或毁坏物体者,则由法院法医与法医研究所行之,本会概不执行。而在鉴定适用标准方面,《中西医药研究社中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章程》第7条规定:本会凡一讼件之鉴定或审定必求其公正允当,并根据中西医药学理与经验,附以说明以为各该讼案判决时之参考。《中西医药研究社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委员服务须知》第3条规定:各委员接得鉴审案件及关系文件后,务须根据学理与经验做详细之鉴定。
对中西医药研究社的呈请,司法行政部于1936年11月27日发布第6343号训令称:
对于法院鉴定事务,尚不无足资辅助之处,嗣后各该院受理关于中医药讼案遇有不易解决之件,得酌量送由该社办理。[23]
中西医药研究社的积极行动争得了对中医药讼案的鉴定权,有利保护了中医师的权利。
中医药讼案鉴定也有委托中医专门学校进行的。1933年间发生一起案件,楼介旅居绍兴,生子甫六月,患瘄延汪竹安诊治,服药一剂而殇,楼以业务上过失杀人诉汪于法,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接受高等法院检察处之委托,经教务处许究仁先生根据药方为之鉴定,并出具鉴定书。[24]
总体而言,在民国时期,围绕中医讼案的鉴定权问题,逐步发展出较为完善的中医讼案鉴定制度,中医讼案由早期的西医垄断鉴定权,经过中医团体的积极努力和争取,逐渐取得了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同情,特别是中央国医馆处方鉴定委员会和中西医药研究社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的成立,基本上确立了中医讼案的鉴定权由中医师和中医团体行使。中医专门鉴定机构也对自己的鉴定行为作出了比较细致、科学的规范,以保障鉴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甚至为取信于社会和政府主管部门而主动要求免费鉴定。同时,在病人死亡的案件中,司法机关还采取尸体检验和药方评判一并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医讼案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判定问题和病人死亡原因的鉴定问题,而此二问题是中医医讼案医师责任成立的关键问题,例如:
1930年,闸北太阳庙路潘陈里八号门牌崇明妇人毛蔡氏投四区警署控称,伊夫毛渭岩,今年四十一岁,日前因寒热小恙,于二月五日延医生蔡有康诊治,讵遭庸医误投药石,盖因热而用热药医治,是促病人之死,要求究办。该署当将蔡有康传唤到署讯据供称,毛蔡氏并非仅我一人医治并无错误云云,该署遂以事关人命即令二十七保十一图地保沈小和投地方法院报验,由朱检察官等莅场检验后谕令收殓,候将药方评判有无错误以凭核夺。[25]
四、结 语
民国时期,随着西医尸体解剖的引入,法医鉴定制度逐渐确立,以医学判断为主要内容的医讼案鉴定也逐渐制度化、规范化。
民国初期,医讼案鉴定主要采取法医鉴定的模式,随着医界对医讼案鉴定问题的认识深入,医讼案鉴定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法医主要鉴定死亡原因,而关于对医疗行为的是非判断则由医师进行,这符合“专业问题同行鉴定”的基本原则,也符合法律关于鉴定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中医讼案的鉴定问题上,民国时期,也经历了法医鉴定向医师鉴定的转变。但是,由西医师鉴定中医讼案,同样是外行鉴定内行,不符合“专业问题同行鉴定”的要求,通过医界的努力,中医讼案由中医师鉴定的科学制度也得以建立。
自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行以来,中国医讼案的鉴定一直处于双轨制的状态,既有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有法医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法医鉴定,医界对此怨声载道。2010年《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尚未废止的情况下,各地就医疗损害案件的鉴定各行其是。一方面是国家没有统一的医疗损害案件鉴定制度,另一方面又是各地方自行制定“地方制度”,造成医疗损害案件鉴定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考察、回顾民国医讼案鉴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为当下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
[1](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2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改仵作为检验吏给予出身片[N].政治官报,1909(780):12-13.
[3]司法部指令奉天高等监察厅呈请改设高等法医学校预备检查人才准予立案文[C].政府公报类汇编,1915(15):110.
[4]奉天高等法医学校章程[C].政府公报类汇编,1915(15):140-144.
[5]知令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所长就职日期[C].广东省政府公报,1932(200):134.
[6]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办事细则[C].司法行政公报,1936(16):11-12.
[7]司法行政部法医学审议会组织大纲[C].司法公报,1936(113):62-63.
[8]姚致强.近年来我国法医之鸟瞰[C].社会医报,1933(190):3964.
[9]林几.二十年来法医学之进步[J].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47(6):14.
[10]呈为呈请明令各地法院关于医病诉讼案应请正式法医剖验尸体以明真相事[J].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5,21(3):321-322.
[11]陈澄医师无罪,法医鉴定诊断无误[N].申报(上海)1936-8-25(14).
[12]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为写在医病纠纷案件呈请令饬采取专家鉴定由[J].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4,20(12):1561-1562.
[13]向司法界进一言[J].医潮,1947,1(7):1-3,9.
[14]池方.医权保障运动[J].牙科学报,1948,2(8):13.
[15]宋国宾.医讼之面面观[J].医药评论,1935,7(9)1.
[16]附法院检察官起诉书[J].中医新刊,1929(12):2-3.
[17]为西医鉴定中医方药上卫生部转司法部请予纠正呈文[J].中医新刊,1929(12)2-3.
[18]批宁波中医协会据呈西医妄行鉴定中医方药请转详司法部迅即纠正着毋庸议文(二月十二日)[J].卫生公报,1929,1(3):27.
[19]批宁波中医协会呈为西医妄行鉴定中西药方请更行审议转详司法部讯予纠正一案本部依法不能过问问(二月十八日)[J].卫生公报,1929,1(3):9.
[20]代电浙江省中医协会鄞县地方法院令西医鉴定中医药方请予纠正一节属司法范围,本部未便过问(三月七日)[J].卫生公报,1929,1(4):72.
[21]为准中央国医馆函称关于处方诉讼案件,如当事人不服当地国医分支馆或医药团体之鉴定,拟径函本馆会重新鉴定由(附中央国医馆处方鉴定委员会章程)[J].司法公报,1935(80):22-23.
[22]中西医药研究社中医药讼案鉴定委员会章程[J].法令周刊,1936(338):8,9.
[23]中医药讼案得由法院酌量送由上海中西医研究社鉴定令[J].法令周刊,1936(338):7.
[24]汪竹安业务上过失杀人案之鉴定[J].浙江中医学校校友会汇刊,1933(6):43.
[25]呈控庸医杀人案[N].申报(上海),1930-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