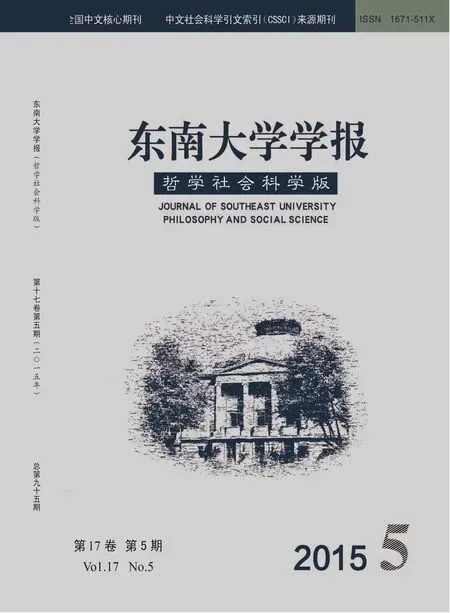自我、身体及其技术异化与认同∗
刘俊荣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1436)
一、“自我”从形而上到形而下
现代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研究可追溯到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在笛卡尔那里,自我源于对一切知识和真理的彻底怀疑,正是通过这种彻底的怀疑及其对怀疑本身的反思,笛卡尔试图找到某种最终不可怀疑的存在,那就是处于怀疑之中的“我”与“思”。由此,他提出了作为其第一哲学原理的“我思故我在”。就笛卡尔而言,作为“思”的主体之“我”,是独立于肉体而存在的思维灵魂之“我”,思维、灵魂与“自我”是完全同一的,自我即灵魂、灵魂即自我。而“我思”只能确证其自身的存在,对除自我之外的他物需要借助于超越怀疑之外的上帝来加以明证。由此,上帝存在便成为终极真实的原因,万物与自我的存在都依存于上帝,自我成为上帝的附庸和明证上帝存在的手段。
洛克试图通过对人格与自我同一性的解读来消解笛卡尔的困难。对笛卡尔而言,“心灵永远在思想”,思维是“我”的本质规定,正是“我思”才印证了“我”的存在。我只是一个思维的存在物,“我思维多久,就存在多久。一旦停止了思维,我也就同时停止了存在”[1]26。但在洛克看来,心灵并非总在思想,只有在自我意识到自己在思想时,心灵才思想着,人之所以能够思想,能够成为有别于他人的“自我”,源自于人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力,“只有意识能使人成为他所谓‘自我’,能使此一个人同别的一切能思想的人有所区别,因此,人格同一性(或有理性的存在物的同一性)就只在于意识。而且这个意识在回忆过去的行动或思想时,它追忆到多远程度,人格同一性亦就达到多远程度。现在的自我就是以前的自我,而且以前反思自我的那个自我,亦就是现在反思自我的这个自我。”[2]130在此,人格与自我取得了意义上的同一,自我通过同一的意识确立人格的自身认同,并通过思维把握人格同一的自己。洛克近乎通过自我意识的延续性解决了自我的同一性问题,但事实上,当他将自我意识直接置换为自我意识的主要形式即“记忆”时,依赖记忆而存在的自我同一性,因记忆可能的间断或忘却而失去其同一的基础。作为一个经验实体之人,因在不同时间可能拥有不同的记忆,就应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甚至一个个碎片化的记忆将产生不同的人格,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消解了“人格”或自我同一性问题。尤其面对失忆人问题,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更显得无能为力。纵然,洛克将人格从整体性的人之实体中抽象出来,试图摆脱经验个体的限制而克服记忆的间断或忘却,但呈现在这个记忆里的所谓同一的人格之我实际上成了独立于身体的抽象物。而这一抽象物只能存在于虚幻之中,记忆不可能与时间剥离,离开了时间的记忆只能是虚无。因此,与笛卡尔一样,洛克的自我概念的确定性基础也被时间所动摇。
在康德看来,无论求助于经验还是上帝都无法为“自我”提供可靠的存在论基础,能够为“自我”提供可靠基础的只有“先验的自我意识”。通过感官所获得的关于自我的杂多材料必须被主体所接纳以形成感性表象,并在先验自我意识所生成的先验对象意识中才能产生统一的自我。他说:“对象就是所予的直观之杂多在对象的概念里得到统一的那种东西”[3]159。在此,“对象”即“自我”不再是外在于主体并时刻动摇着主体确定性的纯粹客体,而是由主体的先验意识所自我设定、自我建构的东西。由此,康德的“自我”摆脱了纯粹异己的“对象”以及所有局部经验的桎梏,其全部的经验内容已被抽干和剔除,是纯粹的先验之我。事实上,康德对自我的存在论阐释并不成功,尽管他把自我规定为以自身为目的的生存之物,但是他并没有对作为“我思”的先验自我的存在方式做出规定,没有从纯粹理性上对自我进行存在论的说明,更没有解答主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沿着康德的思路也根本不可能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因为康德把事物和人格都看作现成者,这样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仅仅是主体与客体这两个实体之间的认识关系。他认为,自我不仅仅是“我思”,更是“我思某某”,而康德忽视了“我思”的“某某”对自我的建构作用,这样世界现象被康德所冷落,作为“我思”的“自我”是没有世界的。海德格尔通过对康德存在论的批判,认为先验自我就在于预先构建了一个既定的视域并在该视域之内构造出对象,此后才能够进行表象和整合。由此,海德格尔把康德的“我思”和时间联系起来,从生存论的视角洞察了“我思”与时间的联系。自我在时间中得以显现,是我思某物的活动,并通过所思之物显现自我的存在。这样,海德格尔的自我就成为拥有了时间性的活生生的生存个体,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主体和没有生机的概念。
以上对“自我”的哲学探究,无疑属于形而上层面的,自我与身体的实体性关系被纯粹的“我思”、意识、纯粹统觉等所取代,身体对自我来说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即使在海德格尔那里身体也只不过是自我构建的工具。由此,自我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之我,源自于身体的欲望、冲动、本能、情感等完全被理性自我所遮蔽,理性判断成为支配自我行为的全部动因,漠视了身体直觉、道德良知在自我行动中的价值。
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以及哲学主体间性的建构,自我从世界之上返回到世界之中,作为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自我,不再仅仅是哲学研究的焦点,也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自我区分为两个方面,即作为认知主体的主我(I)和作为认知客体的宾我(me)。“主我指的是我们对我们正在思考或我们正在知觉的意识”,“宾我……指的是人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的想法。”[4]2在他看来,宾我即经验自我包括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和社会自我,其中“物质自我”指个人的身体及其属性,“精神自我”指我们感知到的自身内部的心理品质即对自己的感受,“社会自我”指我们如何被他人看待和承认即他人所看到的我。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则认为:“自我知觉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这面镜子而获得的。通过这面镜子,一个人扮演着他人的角色,并回头看自己”[5]9。在这里,他主要是从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解读自我的,强调的“是我们想像中的判断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真实想法”[4]48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对库利的思想进行延伸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交互作用在自我产生中的作用,指出:“自我,正如它能成为它自己的客体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果,它因社会经验而产生。当自我出现后,它为它自已提供它的社会经验,因而我们得以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4]74杰里.M.罗森堡(Jerry M.Rosenberg)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自我概念是个体关于其自身作为一个生理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存在着的人进行反省的产物,它由各种态度、信念、体验以及各种评价、情感等因素所组成,是个体确认自己的依据。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则从知觉和自尊的评价方面阐述了自我概念,认为自我概念是自我知觉与自我评价的统一体,是个体对自己心理现象的全部经验。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是现实化了的本能,它不是盲目地追求满足,而是在现实原则的指导下力争避免痛苦又获得满足,是本我与超我的协调者,对内调节心理平衡,对外适应现实环境。
无论詹姆斯、库利、米德还是罗森堡、罗杰斯等人,在对自我的分析中,尽管已将自我从世界之上拉回到了世界之中,由形而上回到了形而下,但都还没有完全摆脱笛卡尔以来主体意识哲学的影响,仅仅把自我看作是一个与内省、反思、评价等智力活动相关的概念,而没有给予具身的感性之我以更多的关注,只是把身体当作了承载智力、意识等精神的容器,忘却了精神、意识、反思等产生的现实基础。事实上,精神、意识、反思等活动及自我概念的形成不仅离不开社会情境、交往体验、社会镜像等,而且必须有身体的在场。因为正是身体的在场我们才被带入到特定的场景之中,并通过身体展示自我、体验自我、生成自我。
戈夫曼(Goffman)认为,身体在人们的交往中发挥自我“代言人”的作用。“在交往秩序中,参与者的专注和介入——哪怕仅仅是注意——永远是至为关键的……”[6]411-412他强调:文化脚本仅仅是人们的表演框架,表演时的姿态、道具等对控制观众对自我的评价、印象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自我的观念不仅仅与自我感觉有关,舞台、观众、文化脚本等自我之外的因素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当下的节食、锻炼、服装、化妆、美体、整容等塑身活动就是一个较好的注脚,这些活动不仅成为不少人追求身体之美的价值取向,而且成为自我认同和彰显自我的标杆。
但是,戈夫曼仍然是从二元论出发的,将自我与身体当作了两个不同的存在,而且更多地强调了自我对身体的控制,身体仍处于“被动”的状态,没有成为行动的主体。而且按照吉登斯的观点,随着社会规范、文化制度对自我和身体的入侵,自我与身体的矛盾更为凸显。一方面,身体作为与生俱来的资本,成为部分人进行钱色交易、器官交易,甚至明码标价的工具;另一方面,受社会期待、消费观念、文化追求等因素的影响,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同,身体变成了被给予的、异己的东西,成为自我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从而,使以往仅在个人私密处所进行的身体装束行为转变为当下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消费行为,把对身体实施的改造和修饰视为消费时尚,并试图通过对身体的投资换取更多的经济、精神回报,身体完全被异化为自我和他者的工具。
为此,梅洛.庞蒂强调,身体是人之存在和自我建构的始基,心灵与身体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身体的自我,自我是具身的,身体本身就是身与心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心”的容器。身体离开了心灵将失去意义,心灵离开了身体将无所寄托,只有在身心的统一体之中,身、心才能成其为身、心。
二、自我与身体自我
自我,首先属于人类的一个个体,是基于个体自身整体的存在,这一整体既包括精神之我,也包括肉体之我,是精神自我与肉体自我的统一。心灵、意识、反思、欲望、情感、冲动等是融合互渗的,纯粹的心灵之我、精神之我或无心的肉身之我、器具之我,只存在于哲学分析的文本之中,在现实中没有其置身之地。个体通过他人或镜像而形成的关于自身的评价,严格地说只能称之为自我意识而不能称之为“自我”。“自我”的一切定义或界定,表征的仅仅是自我概念而不能代替现实的自我,自我就是身心统一的存在。当代生命技术所面临的诸多伦理难题,与对自我的肢解密不可分,如知情同意问题。在生命技术的临床应用中,履行知情同意体现了对患者自主权的尊重,但当我们强调自主时完全排斥了身体直觉、情感感受等所谓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一味地要求患者必须基于理性的判断,将哲学之思的纯粹理性之我机械地套用到患者个体。这实际上是忽视了身体的在场,将患者当作了精神自我与身体自我的二元存在,没有给身体自我留下任何余地。从詹姆斯的观点来看,就是仅仅强调了精神自我,而忽视了物质自我和社会自我。事实上,患者作为身心统一的现实社会存在,其理性判断不可能完全与其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相分离。躯体的疼痛、心理的绝望、他人的期待等都可能左右患者的自我判断,作为健康的他者无法将自我的体验和判断完全类推到患者身上,用他者的自我代替患者的自我。当然,作为罹患身心痛苦的个体也不可能完全从健康他者的镜像中发现真实自我的影子,库利的镜像自我理论在此将失去其效力。
在现实生活中,受社会文化、他人评价、自我意识、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自我与身体及其身体自我往往出现心理认同分离之情形。尤其,在现代生命科技背景下,对身体的重塑和改造如变性、变脸、整形、美体、基因修饰等,身体自我的认同问题日益受人们所关注。所谓身体自我,是个体对自己的相貌、体格、体态、体能等方面的看法与评价。技术在改变肉身的同时,也改变着个体的心理。肉身的改变并不总是与心理的调适同步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如果本我基于快感、欲望、冲动等渴望对肉身进行改变,重塑肉身,而自我不能适度地把握本我并对超我的理想诉求判断有误时,实施的变性、变脸、整形等技术就可能造成自我心理上的落差,对不理想的手术结果产生抱怨,因手术后的不适产生焦虑、失望、恐惧等负性心理。甚至,怀疑手术后的我还是不是原初的自我,手术后的身体还是不是受我支配的身体,原初的自我身体与当下的身体自我能否调适。如:不少变性者在手术变性之后往往不能完全抹掉原来的影子,处于原初本我与真实自我及理想自我的角色矛盾之中;部分整形者按照社会文化期待的标准和评价实施手术之后,因术后的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偏差而不敢面对现实;也有部分器官移植患者在手术后,因体力的衰弱、生存质量的降低、对他人的依赖等而失去了原有的自信及对自我的认同。
心理学家Sonstroem等对身体自我的研究表明,身体状况与自我价值感呈正相关性,健康的身体及良好的身体活动能力可以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精力的维持、力量知觉等对个体心理有较大的影响。他认为,“身体自我是自我结构的重要基础,身体自我以个体的物质性整合进整体的自我观念之中。”[7]同样,在社会学家布迪厄等人看来,社会现实是既在场域之中也在惯习之中的双重存在,来自于社会制度并融入在身体之中的惯习,集结着个体的社会地位、个人品味、性情系统等因素,这些因素表征着某一个体所隶属的社会阶层,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走路、交谈、衣着、活动方式等方面,对其所属的社会阶层加以区别,身体濡染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固有特征,这在个人的言谈举止、气质性情、思想品味等方面都会有所体现。就此而言,身体重塑的过程也是建构自我、展示自我的过程,是身体社会化的呈现过程。正是身体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与建构,自我在身体的异变中才可能远离原有的判断,造成身体自我在心理认同上的困惑与迷惘。但是,如吉登斯所言:“朝向身体的回归,产生了一种对认同的新追求。身体作为一个神秘领域而出现,在这个领域中,只有个体掌管着钥匙,而且在那里他或她能够返回来寻求一种不受社会规则和期望束缚的再界定。”[8]257虽然身体受到了公共性的入侵,并潜在着被工具化、商品化、趋同化之忧,但是这毕竟彰显了身体的存在,而且打开身体的钥匙最终掌控在个人手中,个人有权利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我们强调自我的具身性和身心的统一性,目的也正在于此。处于袪身状态的自我,是抽象的我、观念的我,其价值和尊严完全与身体无关,判断的依据和标准只能是他者的评判,从他者的镜像中体认自我的价值和尊严,而身体的价值和尊严被彻底遗忘。当下,对个体自我的惩诫也往往由身体来承担,体罚、劳役、酷刑等无不针对身体而实施,试图通过对身体的规训达到驯服自我之目的。因此,唤醒身体的尊严和价值,将身体归还自我,在自我的人格、尊严和价值中给身体留下应有的位置,这对于思考和释解当下的生命科技伦理难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异化身体的自我认同
身体是人之自我的具体表征,正如吉登斯所说:“自我,当然是由其肉体体现的。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8]61-62身体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而且如梅洛.庞蒂所主张的,身体是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个体的差异首先在于身体的差异,心理、气质等人格因素的不同总是通过身体及身体行为表现出来的。但是,身体仅仅是判断人之为人的基础,而不是区分不同人类个体的标度,人与人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人格是自我判断的根本标志。但是,人格与身体密不可分。就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而言,人格往往意味着一个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它可以脱离人的肉体及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存在,这实际上是笛卡尔式的二元思维的结果,将人格视作为独立的精神存在。人首先具有人之为人的身体从而与动物相区别,然后才具有个人之为个人的人格而使人与人相区别。因此,自我认同问题与身体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自我认同和定位必须有身体的在场,身体在场是维持连贯自我认同感的基本路径。在技术社会中被异化了的身体,能否得到自我认同,实现身体与自我的统一,直接关涉着个体的生活信念、尊严与社会融入等问题。
就器官移植来说,倘使大脑移植成功,如果将A的大脑成功地移植到了B的躯体上,那么移植后的个体究竟是A还是B?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按照斯温伯恩关于人格同一性标准的表述:t2时间的P2与早先t1时间的P1作为同一个人的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9]223如果以身体为标准,人格同一性的表述应为:t2时间的P2与t1时间的P1是同一个人(person),当且仅当P2有着与P1同样的身体。就身体结构的基本相似性而言,大脑移植后的身体与移植前的身体并无显明的差异,不会影响P作为人的存在,但从身体的具体组成来说,P2已不是P1。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身体的变化直接决定着人的自我认定?如果这样,一个80岁的老年人P与其在10岁时的身体也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就其内部器官而言,无论功能、大小、结构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难道我们能够说P不再是P吗?答案显然是否定性的。为此,有学者建议身体标准需做以下调整:t2时间的P2与t1时间的P1是否同一,并不是说P2与P1在物质上的同一,而仅仅是构成P2的物质与构成P1的物质有着序列的连续性。[10]3从这一修正的身体标准来看,P在年老与年少时尽管在身体的物质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变化前后的物质形态具有序列连续性,年老身体是年少身体自然发生的结果,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依此,大脑移植之后之人既非A亦非B,它与A和B都不具有物质形态上的连续性,应当是新的个体C。但是,按照这种修正了的标准,一个受精卵与其所发育成的个体也具有序列的连续性,难道我们可以说二者具有自我同一性吗?
按照笛卡尔的观点,自我是一个纯粹的思维实体,是与大脑、身体和经验等相区别的独立存在,其自身是永恒不变的,讨论自我认同问题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而吉登斯认为,所谓自我“是个体在意识中经过反思性投射形成的对自身较为稳定的认识与感受”[8]58,是个人依据其自身经历所形成的反思性理解,它根源于个体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吉登斯在强调自我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自我认同中的调适问题。事实上,身体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身体的异化常常伴随着信念的危机,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生活态度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身体异化的理解和调适方式。器官移植受者的自我认同,不但受其移植后的生存质量、健康水平、个人体验等自我因素所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家人、社会等他人因素的制约。尤其对于那些公众比较敏感的生命技术如变性、变脸等,家人、他人及社会的评价可能直接影响着患者个体的感受与认同。而且,仅就其个人而言,由于手术后患者在性别、面貌等方面与此前存在着较大的反差,这势必造成其原有经验和记忆的断裂,挥之不掉曾有的过去。从而,可能产生焦虑、多疑与不安,无法在当前的状态中找到自身的存在坐标,只能在窘迫中将当前转交给反思的意识。这样,他势必要问“我该怎么做”。为了寻求答案,他不仅需要自我调节,转换社会角色以及修复自我概念,如:将供体器官接纳为自己的一部分,将变性后的性别视为自然,努力去熟悉变脸后的容貌,等等。而且,需要他人的理解、安慰与同情,需要得到他人合理的、能够接纳他的一个解释系统。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伯里认为,合理的解释系统有助于个体面对人生进程的破坏时维持个人的自我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减轻慢性病压力的缓冲器。只有在个体与社会的适应与建构中,异化的身体才可能走出自我认同的樊篱,实现自我与身体的统一。然而,这一历程常常是艰辛曲折的,个体总有不适的可能。因此,异化身体的自我认同并不单纯是个体对自我的反思性理解,而是个体与社会互动建构的过程,社会应尊重个体,个体也应包容社会。否则,势必产生自我认同的障碍。
四、身体异化的道德维度
生命技术与身体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一方面生命技术通过对身体的改造、修饰或包装,在不断地改变着原初的肉身;另一方面身体的需要又规划了生命技术的发展方向,为生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理论上说,生命技术对身体的建构能力是无限的,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替换患者病变的心脏、肾脏、肝脏,甚至子宫、大脑等脏器,可以通过手术改变个体的容貌、性别等特征,而且可以通过基因工程、胚胎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等合成生命、设计婴儿、克隆后代,“未来的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将会利用不断发展的基因重组技术,改变人的体能、智能和行为品质,改变人的自然进化方向,重新设计新人类。”[11]394而且,部分科学家对此抱以乐观或支持的的态度,如生物学家沃森说:“没有人有胆说出来……在我看,如果我们知道怎样添加基因,制造出较好的人类,何乐而不为?”[11]395遗传学家J.亨贝尔说:“每一代为人父母者,都会想要给儿女最新、最好的改良特质,而不会听天由命,遗传到什么染色体就接受什么染色体。”[11]395在1986年和1992年美国民意调查中,40%—50%的人赞成用基因工程改良身体与智力[12]129。但是,理论上能够做的现实中未必应当做或可以做,认为科技研究无禁区,社会不应对科技研究施加任何操纵和控制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各行其是的自由,会给所有的人带来毁灭。”[13]117尤其对于身体的技术干预,较一般的技术应用更为敏感,因为身体是人的实体存在,关涉着人的自我人格和尊严。对此,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一书中写道:“我们是否将触发一场人类毫无准备的灾难?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的观点是: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拢。”[14]220
在宗教神学观念中,人是上帝的摹本,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上帝,对生命的任何人为干预都是企图扮演上帝,都是对上帝的亵渎,甚至是不道德的。依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作为对自然生育方式的干预,突破了自然的界限,使用了不自然、至少不是纯自然的方式,以人为干预的手段来达到生育的目的,这是否违背上帝的意旨或扮演上帝?扮演上帝指称什么?我们如何区分某一行为究竟是在扮演上帝还是在执行上帝意旨?因此,英国学者霍普(Tony Hope)指出:“在我们能够决定哪些可能被认定为扮演上帝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是错的。因此扮演上帝的观念对于决定该做哪些事没有帮助。”[15]67-68也有些学者从自然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技术干预违背了自然的本性和人的本来面目,“这不是自然的,因此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15]67然而,“不自然的”意味着什么?是否只要有人类的技术干预就是“不自然的”?在人类身体中包含有多少的“人工”的成份才是“不自然的”?此外,“不自然的”为什么就是不道德的?其伦理证据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不自然的”与“不道德的”划等号。事实上,并非所有“不自然的”都是不道德的。如:生老病死本来是自然规律,但人类却总是试图通过医疗技术手段人为地与疾病相抗争,这难道是不道德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而言,技术干预都是道德的,主要的问题是:技术干预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被接受或干预的道德底线是什么?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依此,确保身体的完整性是最大的孝和最大的善,任何破坏身体完整性的技术行为都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而器官移植无论对器官供体还是器官受体来说,都是对身体完全性的破坏,均使原有的身体不再完整。但是,在现代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心脏、肾脏、肝脏、胰腺等移植已完全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同样,避孕技术、辅助生殖技术、变性手术等,曾几何时也被人们所禁止,现在也被公众所包容。甚至有学者认为,当前被各国所禁止的对人的生殖性克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也将被人们所接受,如张华夏先生所说:“现在我们不能接受克隆人,但将来总有一天会接受它”[11]396。这是否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固定的、统一的道德标准或道德维度?
笔者认为,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状态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普适价值的存在,这是人类本性及协作共存使然。无论孔子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基督教所强调的“己所欲,施于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美国心理学家谢洛姆.施瓦茨(Shalom H.Schwartz)等学者通过在44个国家对25000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者进行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人们在自主、尊重、公正、慈善、快乐、自律、安全、权力、成就、刺激等方面,具有普遍的价值追求。因此,普适性的道德准则不仅是人类和谐共存之所需,而且有其现实基础和可能性。技术对身体的干预和异化也势必遵循这些共识的道德准则,确保人的个性和自主,尊重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正如康德所强调的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作可操控的对象或工具。人及其生命是生命技术作用的直接客体和最终目的,生命技术的道德调控也必须以人及其生命为准绳,对身体的技术干预只有控制在基本的道德维度内,才能捍卫身体的尊严,也才能确保生命技术的健康发展。
德国学者罗默尔(H.Rommel)指出:“个体价值应优先于其他价值,也就是说在冲突的情境下,人的个体存在以及保障这种个体存在的东西要作为价值序列的第一级而得到维护”[16]98。这里所强调的个体价值首先是“人的个体存在以及保障这种个体存在的东西”,而“人的个体存在”即人的包括生命在内的身体的存在,而“保障这种个体存在的东西”即人的人格和尊严。人的身体的存在以及人格和尊严,高于人的其他任何方面的需要、价值和利益,这体现了对人的身体的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人的身体和人格尊严在其他价值、利益面前具有优先性、不可交易性和不可妥协性,康德说:“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替代,才是尊严。”[17]53只有在身体和人格尊严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自主、隐私、公正等其他价值或利益。生命技术对人的干预必须以维护人的身体的存在和人格尊严为前提,在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基础上护卫人的其他方面的利益和需求。就器官移植而言,其目的在于救治患者的生命,但由于生命寓于身体之中,是具身性的存在,这就需要通过对身体器官的更换或组装来实现。在这里,身体与生命是直接同一的,其本身就是目的,技术以及供体器官作为移植的手段已经融入到身体之中,成为人的生命和身体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器官移植虽然改变了原有身体的状态,但只要其维持了自我身体和身体自我的内在规定性,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就能够得到伦理上的辩护和说明。心脏、肾脏、肝脏、胰腺等器官移植,之所以能够得到专家、学者和公众的广泛支持,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并没有逾越道德调控的底线。某些器官移植之所以饱受争议,主要是因为它们影响到了个体或社会其他方面的价值和利益,现代国际社会之所以普遍禁止“人曽混合体”的生殖性研究,正是基于对人及其身体的认定和人格尊严的维护。此外,生殖系基因治疗、生殖性克隆等技术,其伦理争议均与后代自我生命及身体的自决权,以及人格尊严等问题密切相关。
人的生命和尊严具有齐同性、不可量化性。只要是人类个体,无论其生命质量如何、身体状况如何,都具有同等生存的权利和尊严,捍卫生命的神圣和尊严,是生命技术伦理中义务论得以确立的基础,也是义务论进行道德判断的原点。临床上在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之所以时常将患者病情的危重程度作为优先考虑救治的因素,而不是首先考虑患者社会价值的大小,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样的不可逆性和人格尊严的神圣性。“每条人命作为人命都是有同等价值的。人的尊严的不可侵害性的效力独立于其身心状态,也独立于‘个体的人的生命的可预见的长短’”[16]99。因此,只有在个体生存能够得到确保的前提下,其他利益和价值的权衡才得以可能,也只有此时功利主义的利弊计算方式才能派得上用场。正如罗默尔所言:“只有在基本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优先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功利主义的原则才能发挥效力”[16]99。这也印证了我国传统的古训:“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据此,当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利与生命健康权利发生冲突时,生命健康权利优先于知情同意权利;当个人利益与社群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要个人的生命健康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损害,则应当优先考虑社群利益;当社群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高位价值优先于低位价值,等等。
总之,个体生命和人格尊严的维护需要身体的在场,身体自我是生命技术调控的道德底线,一切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必须以身体为准绳。
[1][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M].关文运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 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美]乔纳森堡.布朗.自我[M].陈浩莺,等 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5]柳夕浪.为了共生的理想[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6]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闫旭蕾,葛明荣.论身体、自我与身体自我[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6.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 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9]Richard Swinburne,“Persons and Personal Identity”[M]//H.D.Lewis(ed.),Contemporary Britirh Philosophy.London:Allen&Unwin,1976.
[10]Harold W.Noonan.Personal Identity[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9.
[11]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美]约翰.奈斯比特.高科技高思维[M].尹萍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13][美]哈代.科学.技术和环境[M].唐建文 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14][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震荡[M].任小明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5][英]霍普.医学伦理[M].吴俊华,李方,裘劼人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6]甘绍平.道德冲突与伦理应用[J].哲学研究,2012(6):98.
[1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