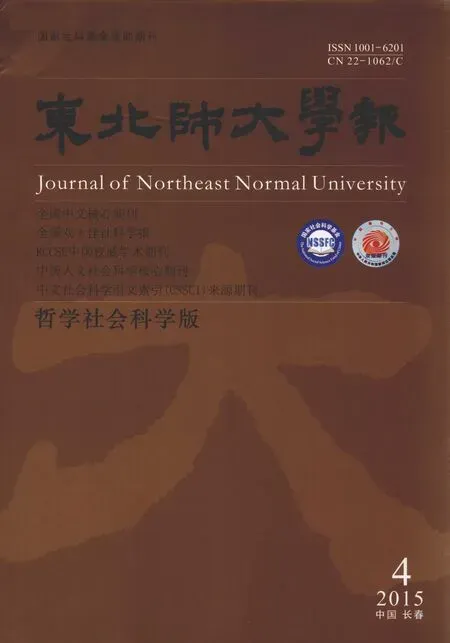认知指示语维度下诗歌语篇的多层结构分析
刘风光,杨诗妍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认知指示语维度下诗歌语篇的多层结构分析
刘风光,杨诗妍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艾略特提出的“诗歌的三种声音”理论与斯托克韦尔构建的认知指示语视角下小说语篇多层结构分析互益互补,二者结合为诗歌语篇的认知文体研究提供启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作为研究语料可三分为第一人称视角隐性叙述诗、第一人称视角显性叙述诗、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诗。三类诗歌的认知指示转移多层结构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别认知指示语的推进与抽离以及三种声音的转换,旨在探讨诗歌语篇多层结构的诗学效果。
认知指示语;多层结构;诗歌语篇;罗伯特·弗罗斯特
一
指示语“deixis”一词源于希腊语,其研究一直是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热点问题。罗素从意义指称论的角度开启了指称语的哲学研究,并将其归纳到自我中心性(egocentricity)维度,并用“我、这、这是”等简化模式表达这种中心性。基于罗素的研究,莱文森总结并强调了指称中语境的重要性,并将指示语划分为五大类[1]。
随着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进一步融合,指示理论也被应用于各类文学体裁的分析中。早在1973年,德国叙事理论家汉布格尔在其专著《文学的逻辑》,文学家、语言学家班菲尔德在1982年专著《不可言说的句子:小说语言中的叙事与表现》中就提出了指称域可以从现实世界交际中的“我、这里、现在”转移到叙事世界中人物的“我、这里、现在”。这种研究文学语篇指示语的视角后来不断被学界接受。随后,西格尔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叙述理解与指示转移理论的角色”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指示转移理论(Deictic Shift Theory),将指示语分析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认知指示语的概念应运而生[2]。斯托克韦尔提出了认知指示语的概念,并将其分类[3],同时斯托克韦尔提出指示语与文学语篇中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角色、读者、隐含读者等概念紧密相关,并从指示语的维度构建了一个多层结构模式。该模式应用前人提出的指示转移理论对文学语篇指示语在指示场中的推进(push)和抽离(pop out)进行了详细阐释,为叙述类语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尽管斯托克韦尔的叙事语篇多层结构模式对从认知指示语角度研究文学语篇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国内对文学语篇中的认知指示语研究还着墨甚少。在目前的几项研究中,刘风光、杨维秀以诗歌语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认知指示语在解读语篇中的重要性[4]。王琳、王安乐对指示转移理论和认知指示语的分类进行了概述,并以雪莱的14行诗《奥兹曼迪亚斯》以及小说《呼啸山庄》为例进行简要解析[5]。吴莉、徐文培也运用指示转移理论对小说《呼啸山庄》中的文学语篇进行认知语用文体分析[6]。但以上研究仅对斯托克韦尔提出的理论进行回顾并佐以少数例证,并没有结合文学语篇语料对认知指示语的应用加以详细阐析,未探讨其文学效果。刘风光、贾艳萍虽然对文学语篇中的指示语进行了认知语用文体研究,以小说《达罗威夫人》为例对认知指示语在文学语篇中的应用进行了阐述[7],但其研究语料却仅限于意识流这一类叙述手法特殊的小说语篇。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斯托克韦尔提出的多层结构模式似乎更适用于叙述视角独特的小说语篇分析。但与小说语篇相比,诗歌语篇的语言更加抽象简练。诗人为精炼语言多省略视角转移的标志,因此斯托克韦尔提出的多层结构模式并不完全适合解读诗歌语篇。但是,艾略特提出的“诗歌的三种声音”,即诗人对自己说话的声音,诗人与听众对话的声音以及与诗歌中人物对话的声音与该多层结构模式有诸多契合之处。因此,作者尝试运用认知指示语和指示转移理论,结合认知指示语叙事语篇多层结构和诗歌的三种声音,重新构造了诗歌语篇的多层结构模式,并以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语篇为语料,对此多层结构模式进行论证。
本研究以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语篇为语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相比美国20世纪同时期其他杰出诗人,如艾略特,弗罗斯特的诗歌语言淳朴自然,多为对新英格兰乡村生活的叙述,其风格接近自然语言。其二,对弗罗斯特诗歌的研究涉及文学性和文学主题。目前国内弗罗斯特诗歌语言学研究多集中在隐喻、提喻等修辞方法上,而在国外语言学研究中仅有少数论文对弗罗斯特诗歌叙述特点加以阐析。国内外均没有从认知指示语的角度研究弗罗斯特的诗歌。因此,以弗罗斯特诗歌语篇为语料,可以丰富对该诗人作品研究的视角,有助于深入探讨其作品的内涵。
二
斯托克韦尔在《认知诗学》中,以小说《弗兰克斯坦》为例,构建了指示语的多层结构模式,并进行了详细阐释。鉴于诗歌语言的独特性,作者以斯托克韦尔理论为基础,探索了适用于诗歌语篇的多层结构。
该多层模式可由诗歌语篇分为内外两部分。诗歌语篇外部由文外声音及理想读者两个对立概念组成。文外声音是诗人生平、创作背景、文学批评、前人研究等所有信息的集合。文外声音构建出诗人最客观、全面的形象,是一种理想化的概念。真实读者仅为文外声音中的一部分。而与之相对应的理想读者假设读者具备文外声音中的所有信息。真实读者仅代表理想读者中的一部分。
诗歌语篇内有两对对应概念,即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倾听者。隐含作者是特定创作背景下的作者概念。其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时代变迁、阅历积累、挫折打击等。不断变化的隐含作者又通过诗歌语篇塑造一位叙述者,借叙述者之口表达观点和情感。而隐含读者是隐含作者倾诉的目标对象,通常是一类或几类特定的人群,并且根据隐含作者的变化而变化。
以弗罗斯特诗歌为例,文外声音是弗罗斯特本人和诗歌所有信息的集合;理想读者是全能读者,拥有弗罗斯特本人及诗歌语篇的所有知识;真实作者是弗罗斯特本人;真实读者是现实生活中的读者个体,具有个体差异。弗罗斯特诗歌中的隐含作者不断变化。在经历肺结核病痛折磨,从哈佛大学退学,长子夭折等一系列变故后,《家葬》的隐含作者就是一位痛失爱子的父亲,一位苦心安抚爱妻的丈夫,一个苦闷疲惫的男人[8]。因此隐含读者可能是有相同丧子经历的中年人。
诗歌语篇内叙述者与倾听者可由“诗歌的三种声音”理论进行细化。“诗歌的三种声音”理论最早在艾略特发表的同名文章中提出。“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是不对任何人说话时的声音。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无论是多是少—讲话时的声音。第三种是当诗人试图创造一个用韵文说话的戏剧人物时诗人自己的声音;这时他说的不是他本人会说的,而是他在两个虚构人物可能的对话限度内说的话。”[9]由此可以推断出:第一种声音的倾听者是叙述者(分裂的)自己;第二种声音的倾听者是诗歌听众,与隐含读者十分相似;而第三种声音的倾听者是诗歌语篇中的其他虚构人物。叙述者(分裂)自我、诗歌听众和诗歌中虚构人物皆为倾听者。
大部分抒情诗歌运用的都是第一种声音。即叙述者将自己一分为二,一半发表观点,直抒胸臆,另一半冷静倾听,做出回应。这类诗以戏剧独白为代表。但第二种声音和第一种声音界限并不明晰。有些作品中叙述者提到了“你”(you)并不一定针对诗歌听众,有可能是诗人的自言自语,对分裂自我的对话。例如,在《牧场》一诗中,“不会去太久—你也来吧”[10]37的“你”就有不同理解方式。一种观点是弗罗斯特在诗中用“枯枝残叶”象征着诗人要放弃19世纪陈旧的诗歌创作手法,并向“你”征求意见,你是否也愿意与诗人共同前进,故此处是第二种声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诗人对摒弃陈旧的诗歌写作方式有所迟疑,并通过自问,以期获得更加坚定的立场。因此后者属于第一种声音。第三种声音在以对话为主的叙事诗中更为常见,且容易识别。如在叙事抒情诗《补墙》中,两个邻居春日里一起修补充当田地分界线的石墙。作者摒弃全知视角,采用其中一位邻居“我”(I)的视角,“我”说的话即为第三种声音。诗歌语篇中第二、三种声音分界线有时也不清晰,容易引起争议。上文解释的《牧场》中,有学者将这首诗解读为诗人写给自己妻子的道歉诗。“你”是诗人对妻子的呼唤,请求妻子的和解,希望她赶快把那些如同枯枝败叶的琐事清理掉,享受更为美好的时光[11]。因此这里的“你”与诗歌语篇中塑造的妻子形象对话,是第三种声音。
建构上文所述多层结构的目的是清晰展示诗歌语篇中认知指示语的转移和映射的方向。当指示中心在建构模式中从隐含读者到叙述者方向移动时,即指示语向更深层推进(push)时,语篇真实作者不断深入读者思想,并且通过指示语的映射抒发情感,达到移情的目的。当视角从倾听者到隐含读者方向移动时,读者的关注中心不断抽离(pop out)特定情景。从人物对话、戏剧独白、人物心理活动中逐渐抽离到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但在诗歌语篇中,类似雪莱的《奥兹曼迪亚斯》,能在短短14行诗句,进行两次转述的诗作并不常见。此外多数诗歌开篇即进入主题,直接将指示中心投射到叙述者身上。因此诗歌语篇中从隐含作者到叙述者之间的推进和倾听者到隐含读者之间的抽离被弱化。但是,指示转移仍然存在,且通常发生在一种或两种声音相互转换的过程中。借助此模型,我们可以了解三种声音中认知指示语的指示转移方向及对象,从而厘清诗人的写作思路,解析诗人表达的真实情感。
三
鉴于不同类型诗歌中认知指示语的指示转移体现出不同的特点,笔者试将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别,对其认知指示语的指示转移加以分析。
弗罗斯特诗歌分类方法各异。其中,美国诗人、批评家乔欧亚在《罗伯特·弗罗斯特与现代叙事》一文中将弗罗斯特的叙事诗分为4类:民谣(ballad)、无韵体第三人称线性叙事(linear narrative)、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戏剧叙述(dramatic narrative)[12]。
尽管乔欧亚在他的文章中对弗罗斯特的叙述诗加以分类,但其准确性却有待考证。第二类线性叙事和第四类戏剧叙事界线不分明,而且学界对戏剧叙事的阐述少之又少。因此,作者尝试将弗罗斯特诗歌分为第一人称视角隐性叙述诗、第一人称视角显性叙述诗、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诗3类,并在不同分类中应用认知指示转移多层结构进行分析。
(一)第一人称视角隐性叙述诗
诗人以第一人称视角,向读者转述他看到的场景。笔者将此类诗定义为“隐性”叙述诗的原因是尽管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描写,但在诗歌语篇中第一人称却从未出现。在这一类诗中,作者的形象被弱化,对事物的观点看法也并不直接抒发,而是通过对景物、事物的描写启发读者思考意象的含义,品味作者要抒发的情感。弗罗斯特这类诗歌以景物、景色描写为主。例如,在《沙丘》中,弗罗斯特描述了大海与陆地连接处褐黄、干燥的沙丘。这首诗的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基本一致。因此由隐含作者到叙述者之间的指示转移被省略。诗中的第一句话,“海浪是绿色的,潮湿的”中的绿浪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意象。而这句话中的“绿浪”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将指示中心由读者直接推进到叙述者描述场景的指示域中。叙述者主要采取了诗歌的第二种声音,叙述者向隐含读者描述他看到的景色。在诗歌末尾时,叙述者也没有将读者抽离出该指示域中。
由此可见,此类诗歌中认知指示语的指示转移比较简单。对读者来说,只要能够理解作者描述的意象,理解隐含作者的意图就可以理解诗的大意。
(二)第一人称视角显性叙述诗
显性叙述诗的叙述者,即第一人称,在诗歌语篇中反复出现,故此类诗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通常带有戏剧独白的色彩。弗罗斯特这一类诗歌比较常见,著名的有《未选择的路》《雪夜林边小驻》《牧场》等。但是,与第一类叙述诗稍有不同,此类诗歌的隐含作者可能与叙述者重合,也可能不重合。当二者不重合时则诗歌开篇出现由隐含作者到叙述者的指示转移;二者重合时则省略该步骤。
隐含作者与叙述者重合最典型的例子仍是《牧场》一诗。第一句开篇“我要出去打扫牧场的水泉”,“我”直接将读者推进到诗歌的指示域中,使叙述者和读者处在同一指示中心中,从而与读者进行对话。在该过程中,叙述者运用了第二种声音,与读者进行交流。而第二种声音的采用促使发生了指示转移,其目的是将读者推进到叙述者的指示域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从而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诗歌的内涵以及情感。而“不会去太久—你也来吧”中的“你”(you)也可能是诗歌的第一种声音,即叙述者对一个分裂的自我的对话,一种自言自语。此时没有发生指示转移,但是却强调了叙述者自身所在的指示域范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立场的重申或思考。
而在《仆人们的仆人》一诗中,叙述者是一位神经质的家庭主妇。女叙述者的丈夫为了获得物质利益给她分配了无休无止的家务,沉重的家务负担和丈夫无止境的物质追求让她感到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13]。显然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不能重合,二者之间存在指示转移。但这种转移不是一次形成,而是通过叙述者的连续讲述而逐渐凸显的,而且此过程需要隐含读者进行指示转移识别才能确定。本诗中,诗歌采取了“戏剧独白”的叙述手法,既向诗歌听众“你”提出了很多问题,试与隐含读者进行交流,获得情感共鸣,同时也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叙述者不断进行第一种和第二种声音之间的转换。如诗歌前半部分“这种感觉你也有过,但愿没有”[10]144,一方面叙述中的“你”,使用了诗歌的第二种声音,询问诗歌听众是否有过相似的体验;另一方面叙述者利用诗歌的第一种声音自问自答。女叙述者因为孤单、神经错乱,只能把分裂的自我当作倾诉对象。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隐含作者不仅向隐含读者们表达了他对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还帮助读者了解了农妇的真实故事和情感。
(三)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诗
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诗中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身份可能会有较大差别,因此通常出现指示转移。正如前文所述,《家葬》的隐含作者是一位痛失爱子的父亲,而诗歌的叙述者却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客观全面地讲述事件的始末。因此在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中间必然出现了指示转移,将读者推进到该情境中。第一句“在被她看到之前/他在楼梯下看到了她”中的“她”与“他”将读者推进到第三人称旁观者的指示域中,而“看到”(saw)则将读者推进到过去的一个时刻。这种向过去时刻的推进也意味着事件已是既成事实,故比较客观。而在诗歌语篇中,痛失爱子的丈夫与妻子的交流不是通过转述,而是以直接对话的形式出现。这一部分叙述者使用了诗歌的第三种声音,即诗歌语篇中虚构人物对话的声音。在这类诗中第一种及第二种声音通常不出现,其第三人称视角叙述客观性,限制了作者抒发强烈主观情感。
以上为弗罗斯特三类叙述诗以及多层结构模式下诗歌声音转化的阐述。上文所述例子均比较典型,但在一般诗歌分析中多层结构之间声音转化界限更模糊、复杂。例如《山妻》(组诗)从五个部分,即《孤独》、《害怕空屋》、《笑容》、《一再重复的梦》、《冲动》刻画了女性从压抑到觉醒的过程[14]。
《山妻》组诗前三部分属于第一人称视角显性叙述诗。该部分以女性叙述者为视角,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不重合。诗歌伊始,隐含作者将指示中心转移到叙述者“山妻”上,随后这位女叙述者讲述了她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在第一首诗《孤独》中:“一个人不该非要这般挂念/像你和我这般挂念/当那对鸟儿飞来绕屋盘旋/仿佛是要说声再见”[15]160,虽然学界对于“你”指的到底是谁有不同的解释,但却一致认为“你”绝不是女主人公的丈夫。一种解释将“你”当作诗歌听众,女叙述者正在用第二种声音与诗歌听众进行交流;也可以将“你”解释为叙述者分裂的自我,因为孤独,没有其他倾诉对象,所以只能自言自语。独白式的叙述恰恰揭示了女主人公对其婚姻状态的不满以及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诗歌的后两部分是典型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诗。隐含作者开篇即用“她”将指示中心投射到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上,并运用诗歌的第二种声音,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向诗歌听众描述妻子无法摆脱的梦境。最后妻子因为恐惧,在跟随丈夫到林间锯木的间隙,藏进了蕨丛,再无踪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山妻”。后两部分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证实了妻子悲惨的生活,阐释了孤独与死亡的严肃主题,反映了女性饱受压迫折磨的现实。
由此可见,从隐含作者到叙述者之间的指示转移研究可以帮助读者厘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倾听者、隐含读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从而确定诗人对所描写事物或事件的真实情感;而对三种声音转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看似缺少逻辑条理的诗歌语篇中,准确找到叙述者的叙述对象,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歌语篇。
四
综上,笔者以三类诗歌开篇部分为例,对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指示转移进行了简要的阐析,而对其结尾部分指示转移却着墨甚少。这与诗歌语篇的特殊性是密不可分的。不同于其他文学语篇或其他类语篇,在较短小的诗歌语篇中,结尾往往缺少指示转移的抽离过程。大部分的叙述者故意没有将读者抽离出诗歌语篇中,这也营造了阅读诗歌意犹未尽的效果。读者在阅读结束后,仍然置身于诗歌中的指示域中,久久不能平复抽离。这种抽离的缺失往往会更加引人深思,回味无穷。
本文通过指示语、指示转移理论综述回顾,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源于小说叙事语篇的多层结构模式与诗歌的三种声音相结合,构建出适用于诗歌语篇分析的多层结构模式。同时本文也将此结构运用到诗歌语篇的分析中,以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为语料,将其诗歌分为三类。通过对诗歌语篇中指示转移的分析挖掘诗歌的内涵,验证了利用多层结构模式在指示语维度下对诗歌语篇进行分析的可行性,丰富了认知指示语的语用文体学理论体系。
弗罗斯特的诗歌语言清新自然,诗歌中的指称清晰易辨。但在转述频繁的诗歌中,从隐含作者到叙述者的推进可能会反复进行多次。诗人也可能在此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声音,而每一次推进,每一次声音的转化都会投射出新的指示域,体现了不同的诗学效果。但篇幅所限,本文仅举几例验证了该多层结构模式的可行性,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关注。
[1] Levinson,S.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68.
[2] Segal,M.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and the role of deictic shift theory [A]. Duchan F,Bruder A & Hewitt E (eds.).DeixisinNarrative:ACognitiveSciencePerspective[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3-17.
[3] Stockwell,P.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43-46.
[4] 刘风光,杨维秀. 语用学视野下的诗歌语篇研究 [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38-40.
[5] 王琳,王安乐. 认知指示语与叙事语篇理解 [J].英语研究,2009(3): 18-22.
[6] 吴莉,徐文培. 文学语篇中指示转移理论的认知分析 [J].学术交流,2009(1): 151-153.
[7] 刘风光,贾艳萍. 文学语篇中指示语的认知语用文体学研究 [J].语言教育,2013(8): 37-44.
[8] 郭心民.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自传主题诗评析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38-140.
[9] 艾略特. 艾略特诗学文集 [M]. 王恩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249.
[10] 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诗选 [M]. 江枫,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11] 陕来. 诗始于喜悦,终于智慧—由《牧场》看弗罗斯特诗的渊源 [J]. 语文建设,2010(7-8): 80-83.
[12] Gioia D. Robert Frost and the narrative [J].VirginiaQuarterlyReview,2013,89(2): 185-193.
[13] 李应雪. 欲望的诗歌,平衡的诗学:弗罗斯特一组叙事诗的主题探索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5):51-55.
[14] 李应雪. 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叙事诗的多重主题探索 [J].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9):115-119.
[15] 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诗选 [M]. 曹明伦,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60.
An Analysis of Multi-layered Model of Poetic Discourse in the Dimension of Cognitive Deixis
LIU Feng-guang,YANG Shi-yan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116044,China)
Eliot’s “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multi-layered model of fiction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deixis proposed by Stockwell (2002). The fusion of these two theories sheds light on the cognitive 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poetic discourse. Taking Robert Frost’s poems as data,the paper divides his poems into three categ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ir narrative features,namely,first person implicit narrative poems,first person explicit narrative poems and third person narrative poems. The studies on the “push” and the “pop out” of cognitive deixis,as well as on the shifts of the three poetic voices aim to explore the poetic effects in the poetic discourse.
Cognitive Deixis;Multi-layered Model;Poetic Discourse;Robert Frost
2015-03-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ZH101);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3189)。
刘风光(1973-),女,吉林辽源人,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杨诗妍(1990-),女,辽宁沈阳人,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H0
A
1001-6201(2015)04-0122-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4.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