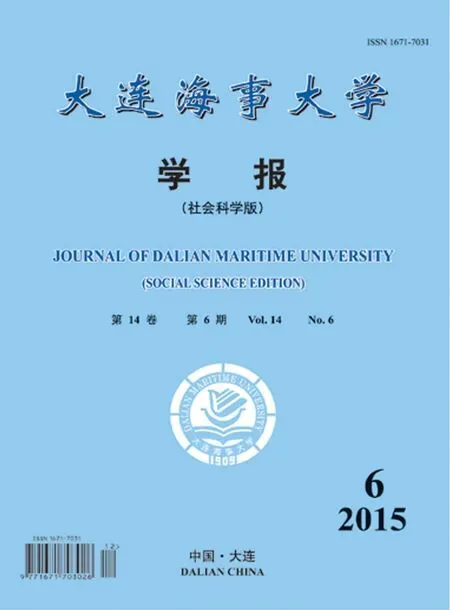中国《海商法》迟延交付责任制度之检讨
傅婧英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法律与风险管理部,北京 100080)
中国《海商法》迟延交付责任制度之检讨
傅婧英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法律与风险管理部,北京 100080)
从中国《海商法》中关于迟延交付的概念入手,分析学界和实务界对迟延交付责任制度的不同认识,就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论证,并对完善制度建构提出建议,如在《海商法》中完整地引入“合理期间”的概念、将承运人违反适航和直航义务的责任由货损扩大至经济利益损失等。
迟延交付;责任制度;合理期间;海商法
在航运技术不发达、海上贸易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船货双方对海上货物运输的时间要求并不十分严格。基于这一原因,在传统的海运立法中,承运人对海运货物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货物的灭失或损坏(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换言之,承运人只对货物的有形损失承担责任,至于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纯经济损失则不在考虑之列,故在立法中迟延交付制度便没有被提到议程上来。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贸易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对国际航运的效率性需求日趋提升,加之有了长足进步的航运技术也可以适度满足此种要求,于是,在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中首次确立了迟延交付制度,其中规定,承运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或未能在合理期间内送达货物的,均属于迟延交付。之后,我国《海商法》部分地采纳了《汉堡规则》的规定,即只规定承运人未在约定期限内交付货物为迟延交付,而没有采纳公约中使用的“合理期间”的概念。由此,学界和实务界对迟延交付制度中是否应涵盖“合理期间”的概念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时至今日,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运量的增加,我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国家,在海上运输中面临的纷争势必也会增加,在海上运输中因迟延交付而产生的相关问题变得不容忽视,并且亟待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本文试图从迟延交付的问题产生、观点争议和概念解读等角度展开分析,明晰我国《海商法》迟延交付制度的瑕疵之所在,并提出修改建议。
一、问题的产生
在业已生效的国际海运公约中,《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都没有对迟延交付作出规定,只有在1978年通过并于1992年生效的《汉堡规则》中,才第一次规定了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的责任。公约中将迟延交付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承运人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交付货物,即为迟延交付;其二,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对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要求的时间内,承运人未能交付货物的,也视为迟延交付。①《汉堡规则》第5条第2款:“如果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或者虽此种约定,但未能在按照具体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要求的时间内,在海上运输合同所约定的卸货港交货,即为迟延交付。”简而言之,不论合同中是否约定了货物的交付时间,只要在事实上导致了迟延交付的后果,承运人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国虽非《汉堡规则》的缔约国,但在我国的《海商法》中也有限制地采纳了公约中的迟延交付制度。所谓有限制地采纳,是指只承认在超出合同约定时间的情况下,承运人须承担迟延交付的责任,但对于合同中没有约定交付时间而承运人未能在合理期间内交付货物的情况,《海商法》中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海商法》第50条第1款:“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于是便自然地使人们产生了疑问:如果承运人未能在合理期间内交付货物,承运人有无责任可言?
二、观点之争
有观点认为,《海商法》第50条第1款之所以要专门为迟延交付确立定义,就是有意排除承运人对所谓的不能在合理期间交付货物的法律责任,换言之,如果在运输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交付货物的期限,承运人对迟延交付货物的责任便不能成立。[1]这一观点似乎符合立法的本意。交通部政策法规司在《海商法》颁布之后,组织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条文释义》,其中对《海商法》第50条作出了特别的说明,即“本条关于迟延交付责任的规定,是从《汉堡规则》引进的。但是与《汉堡规则》第5条第2款规定相比较,本条第1款第一句后面删除了如下字样:‘或虽无此项约定,但未能在考虑到实际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要求的时间内’,将《汉堡规则》的承运人迟延交付责任改为本条的‘约定迟延交付责任’。这是考虑到我国海运实际情况,被删去一段条款的操作性等因素决定的,希望读者予以注意”[2]。
但是,尽管有上述解释,也有观点主张:《海商法》第50条第1款并非是对承运人在“合理期间”内交付货物所负责任的法定排除,而只是对迟延交付的概念作出了不周延的表述。[3]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交付自然是迟延交付,但在逻辑上并不等于迟延交付只有未按约定时间交付这一种情形,而不能含有其他情况。所谓“其他情况”,可以根据《海商法》的其他条款或者《合同法》等其他法律来确定。根据《合同法》第290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那么,即使国际海上运输合同中对交货期限没有明确约定,承运人也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在“合理期间”内将货物运至约定地点,否则,同样构成迟延交付。[4]
三、对相关概念的解读
就其本质而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根据《合同法》第123条第3款*《合同法》第123条:“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海商法》作为《合同法》的特别法,《海商法》另有规定的,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由此引发两个问题:何谓“另有规定”,何谓“没有规定”?
1.何谓其他法律“另有规定”
“另有规定”是指其他法律规范对同一调整对象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在合同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货物运至约定地点,*参见《合同法》第290条。否则,无论承运人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且损害赔偿的范围既包括货物损失,也包括经济利益损失,其中经济利益损失以承运人的合理预期为限。*参见《合同法》第113条。
但是,反观《海商法》的规定,只有在合同约定了确切的交付时间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迟延交付,而且,即使构成迟延交付,承运人也仅在具有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参见《海商法》第50条第2、3款。同时《海商法》还规定了迟延交付达60日以上的,可以推定货物灭失,并按灭失来赔偿。*参见《海商法》第50条第4款。
相比较而言,《海商法》在迟延交付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和法律责任及赔偿限额等各个方面,均作出了不同于《合同法》的规定,不可不谓其“另有规定”,而且,《海商法》是针对整个迟延交付的规则作出了系统化的特别规定,而非仅对迟延交付的适用范围作出特别规定。
2.何谓《海商法》中“没有规定”
如前所述,《海商法》已就迟延交付作出了系统化的特别规定,《海商法》第50条第1款之所以强调“合同约定的时间”,其根本目的就是排除对“合理期间”概念的适用,进而有限制地适用迟延交付制度,因此,不应视为“没有规定”,更不应该对《海商法》第50条第1款和《合同法》第290条加以机械地对比和教条的解释。
从法律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应将《海商法》中关于迟延交付这一体系化制度肢解开来,然后再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相互嫁接。诚然,《海商法》中对迟延交付的定义较之《合同法》而言少了“合理期间”的概念,但《海商法》中对迟延交付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及赔偿责任的规定,都是与迟延交付的定义相契合的。换言之,只有符合《海商法》第50条第1款所定义的迟延交付,才能适用《海商法》规定的迟延交付的其他规则,即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和责任限额等。而《合同法》不但对迟延交付的定义与《海商法》不同,而且对于相应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也与《海商法》迥异。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海商法》对于超过“合理期间”的交付“没有规定”,据此主张适用《合同法》,将超过合理期间的交付也纳入迟延交付的范围,那么此种迟延交付就不应再回归适用《海商法》中关于迟延交付的其他规定,如此一来,《海商法》中关于迟延交付的责任这一制度体系便形同虚设。
在此,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论上的假设。设想,如果将超过约定交付时间的迟延交付按照《海商法》的规定处理,而超过合理期间的迟延交付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将导致整个迟延交付制度在适用中的扭曲与失衡。通常而言,在合同中就货物的运抵时间明确作出承诺的承运人,相较于没有作出此种承诺的承运人来讲,应该承担更为严苛的责任。但是,按照前述的解释方法,在承运人超过约定时间的情况下交付货物,虽然要承担责任,但此种责任仍然是在海上运输合同法的框架之内确定的,故承运人仍然有权援引海商法中为承运人规定的各项抗辩和责任限制的权利。但是,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交货时间的情况下承运人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交付货物,如果按照所谓的《海商法》无规定时就应适用《合同法》的理论,则对此种迟延交付责任的确定便进入了合同法的框架,如此势必导致一种结局:无论承运人是否有过错,均须承担赔偿责任,其不得援引《海商法》规定的免责事由,亦不能享受《海商法》中关于承运人责任限制的规定,此种结果无疑有悖于“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则。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一种貌似合乎逻辑的解释,却推演出了违背逻辑的结论,有鉴于此,不应对《海商法》中迟延交付的规定做狭隘解释,所谓《海商法》中对超出“合理期间”交付货物的责任“没有规定”就应适用《合同法》的结论值得商榷。
四、《海商法》的制度瑕疵
根据上述分析,虽然不应仅凭《合同法》中对承运人在“合理期间”内的迟延交付责任有所规定,就硬性地将海运承运人的责任置于《合同法》的框架之内,但是,毋庸讳言,《海商法》在这一问题上的制度建构确实存在缺陷,由此导致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由货方自行承担货运迟延的损失。
《海商法》中迟延交付制度的意义在于重新平衡船货双方的利益,对货方进行适度保护,迟延交付责任不但包括因迟延导致的货物毁损,还包括因迟延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从表面来看,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规定,但是,由于海商法中关于迟延交付的概念不周延,致使此种规定不能适用于在合同中未约定交付时间的情况下发生的迟延交付。此外,如果避开迟延交付责任制度的规定,从承运人违反适航或直航等项基本义务的角度请求其赔偿迟延交付的责任,也同样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因为在承运人违反基本义务的情况下,《海商法》只要求其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责任,而不承担经济利益损失。因此,平衡船货利益的目的在迟延交付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传统观念认为,国际航运中充满风险,故不宜对承运人苛求货物运抵时间,而且国际贸易中已经形成以提单的买卖代替实物交易的交易习惯,托运人和提单持有人可以通过出让提单的方式将货物的在途风险(包括运抵时间风险)转移出去,而不必因货物不能在合理期间内运抵卸货港而遭受经济利益损失。但是,在当今条件下,航海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国际贸易也不囿于提单买卖,而且即使如击鼓传花一般进行提单买卖,也终有鼓停花落之时,终究有人要面临货物最终交付的问题。整个航运过程中,货物一直处于承运人的掌控之下,承运人更有能力避免货物迟延送达卸货港的风险,却要求货方自行承担相关风险产生的经济利益损失,显然不符合责任分担原则,也不利于损失的避免。
综上,《海商法》的制度缺陷在于迟延交付的责任虽然包括赔偿经济利益损失,但是,适用范围却不包括在“合理期间”内发生的迟延交付;现行《海商法》中规定的船舶适航和直航义务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货物在“合理期间”内运抵卸货港,而一旦承运人违反义务(例如因不合理绕航)而导致迟延交付,在赔偿范围中却不包括经济利益损失。
五、完善迟延交付制度的建议
笔者认为,可通过如下两种途径弥补《海商法》中迟延交付责任制度的缺陷:
1.在《海商法》中完整地引入“合理期间”的概念
综观各国海商法,虽然立法所依据的国际公约各有不同,但部分国家的海事立法在迟延交付问题上已经开始借鉴《汉堡规则》的制度建构,将“合理期间”明确规定为迟延交付的判断标准。例如,1998年《澳大利亚海上货物运输法》第4A条第2款规定:“本条中,如果没有在合同约定或合理的时间内在合同约定的卸货港交付,则视为货物的迟延交付。”1999年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第166条第2款也规定:“如果承运人未能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规定的卸货港,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如无此种约定则在根据实际情况对于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来说合理的时间内交付货物,应视为迟延交货。”[5]由此可见,在《海商法》第50条第1款中引入“合理期间”的概念,是修补迟延交付制度瑕疵的最佳方式,也符合公平分担海运风险的历史潮流。
2.将承运人违反适航和直航义务的责任由货损扩大至经济利益损失
由于承运人原因导致的货物延误,主要包括承运人提供的船舶不适航和未尽直航义务(即承运人进行了不合理绕航)。船舶适航自《海牙规则》生效以来一直被奉为承运人的首要义务,违反了该项义务,承运人将不再受免责和赔偿限额的保护。违反直航义务通常被视为根本违约(fundamental breach of contract),在美国则称之为对合同的背离(departure from the contract),两国法律中的表述虽然略有差异,但精神实质相同,只要违反该项义务,托运人即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承运人便不得依据被解除了的合同享受免责。合理速遣与前两者并称为英国法中承运人的三大默示义务[6],其重要性都远远高于迟延交付。既然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包括了货物的有形损失和经济利益损失,那么违反适航、直航和合理速遣义务的赔偿责任至少不应低于迟延交付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海商法》中规定,承运人违反上述义务既应赔偿货物损失,也须赔偿经济利益损失,那么,即使在迟延交付的规定中不包括“合理期间”这一概念,货方也可以请求承运人赔偿因违反合同下的基本义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从而使合同中未约定交付时间时发生的迟延交付在另一个层面上得到救济,进而使迟延交付制度的瑕疵得到克服。
事实上,在英国早有判令违反适航义务的承运人赔偿经济利益损失的先例。在Anglo-Saxon Petroleum Co. Ltd V. Adama Stos Shipping Co. Ltd案中,《海牙规则》被并入了租约当中,由于船舶在租期内出现故障,最终造成了经济利益损失。Devlin J.勋爵认为,《海牙规则》中的loss or damage并没有任何条款对其加以限定,它的作用是用来调整海上运输合同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会只限于货物的损失,因此承运人对因迟延交付或错误交付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应该赔偿的。[7]
将承运人适航、直航和合理速遣义务的赔偿责任范围扩大至经济利益损失,不但可以弥补我国《海商法》中关于迟延交付责任制度的瑕疵,还可以克服在赔偿责任范围上的不协调现象,可谓一举两得。
六、结 语
我国《海商法》中的迟延交付责任制度不包括“合理期间”的概念,此种概念的缺失属立法者有意为之。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无法通过法解释的方法引申适用《合同法》中的“合理期间”的概念,由此导致一种结局:只有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交货时间的情况下,才有迟延交付责任制度得以适用的余地。因此产生的制度瑕疵,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解决:其一,在《海商法》第50条第1款中全面引入《汉堡规则》中关于迟延交付的责任制度,即补充引入“合理期间”的概念;其二,将承运人违反适航和直航义务的赔偿责任范围由单一的货物灭失或损坏扩大至经济利益损失,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解决合同中未约定交货时间时产生的迟延交付问题。
[1]司玉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问答[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55.
[2]交通部政策法规司,交通法律事务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41.
[3]尹东年,郭瑜.海上货物运输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24.
[4]徐欣.论迟延交付的概念[J].世界海运,2002(5):32-33.
[5]司玉琢,胡正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条文、参考立法例、说明[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203.
[6]WILSON J 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M]. 6th ed. London: Pearson Longman, 2008:9-24.
[7]田正大.论迟延交付[J].中国海商法年刊,1993:130-132.
2015-09-16
傅婧英(1983-),女,经济师;E-mail:fujy@sinosteel.com
1671-7031(2015)06-0077-05
DF961.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