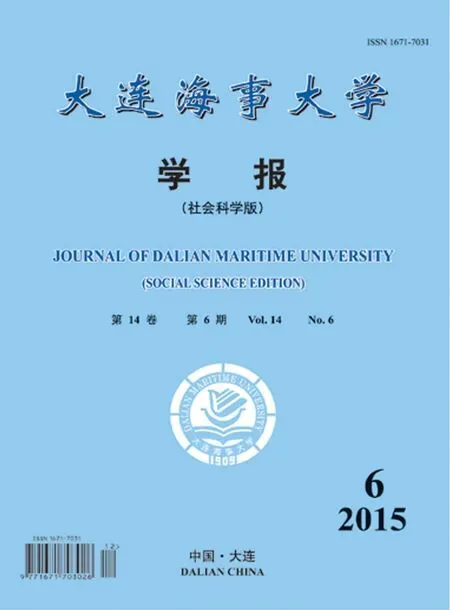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公私观考察
王 猛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2488; 2.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公私观考察
王 猛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2488; 2.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公私观念是日本人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内容和特点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考察。政治层面,天皇是公的顶点,是公的来源。天皇之公的下层是武士阶级的公私体系。该体系具有多重性、相对性、私在公的支持与控制下发展、“御恩-奉公”的伦理观等诸多特点。社会层面,村落共同体和庄主为公,家(家庭)为私,家的成员是私的践行者。公私关系是结合了上下、主从两种关系在内的特殊形式。家的层面,家之公是家的成员之私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恩情与奉公是其基本伦理道德。因为本家与分家的观念,家之公也有大公与小公之分。分家之小公在本家之大公面前,只能是奉公的私的存在。
日本;江户时代;公/私;公私观
公私观研究是日本问题研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题,其关系到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而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公私观被认为是日本人传统公私观的原型,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来被日本学者所重视。但是,因为日本人公私观复杂多样,而且难以单独用中国公私观的研究方法——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进行探讨,所以中国学界至今未有学者对其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文化形态论的方法对该领域进行探讨。文化形态指的是文化系统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和顺序,是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结构。具体到本文而言,就是对江户时代日本人公私观进行层次性、类型化的研究,然后找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之间的联系,进而归纳出公私观的特点。
一、天皇之公与武士之公的对立统一
江户时代的公私观是在继承了室町时代的公私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虽然同为武士阶级掌握政权,但是因为政权的组织形式不同,加上两个时代之间战国时代的影响,江户时代在封建统治的集权形式上更加严密。统治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江户时代的公私观和前代既有相似之处,又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早在律令制时期,在中国公私观的深刻影响下,天皇作为最大的公就确立了在日本公的最大领域。而中国自然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比皇帝更大范围的公——“天下为公”却未被日本人所继承。天皇依靠与神的渊源,确立了日本公的宗教权威。武士掌握政权后,虽然天皇丧失了世俗权利,但是天皇作为日本最大的公的地位并未动摇。天皇一直是公权利的合理来源。源赖朝、足利义满、丰臣秀吉都是通过从天皇那里获得将军等职位来确立在日本的统治地位的。德川将军也是通过天皇任命的方式进入公的行列的。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迫使后阳成天皇任命其为征夷大将军,从而把地位从正二位提升到从一位太政大臣,确立了其公权利的地位。1611年,《诸条例》第1条规定:“诸如右大将军家以后各代公方之法式均可遵奉之。”该条例的目的是要论述武家政权的独立性,同时宣布武家政权具有公的性质,其法令需要遵守。虽然武士阶级获得了公的资格,进入了公的领域,但是他们掌握政权后,仍然把公家和武家作为不同的阶层截然分开。公家指朝廷以及贵族,而武家指幕府以及掌握政权的武士阶级。公家演变为与武家相对应的一种含义。也就是说,武士阶级在把武家和公家在公的领域中统一的同时又把二者截然分开。形式上,天皇的公对于将军的公来说,具有优越性和上位性。而实际中,武家对公家却进行了各种严格限制。
幕府首先限制了朝廷在官职授予方面的权利。“武家诸者官位之事,若无推举则不宜被授之。”[1]意思是说,没有武家推免的官员,朝廷不得承认。这就防止了地方大名和朝廷结合形成反对幕府的势力。德川家康还谋求和朝廷不同的官位体系。1615年,《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武家之官位诸事,应在公家官员之外。”这样,武家就可以建立与公家不同的官位制度。如此,朝廷官职和武家官职就分离了。对于不同官位体系下的公家和武家,《武家诸法度》称:“公家众之公家学问应昼夜不断而为之。”公家作为“家职”,主要承担“朝役”;武家喜好文武弓道,承担“军役”。如此,公家和武家在官制上完全被分开,朝廷变成文官的世界。公家只能专注于文,不能靠近武。而且,“无论老小,违背行仪法度者以罪罚之”[2]113。日野资胜在日记中针对公家学习骑马、兵马、铁炮时说:“此不合古法,应止也。”日野资胜的父亲日野辉资作为织田信长的“公家阵参众”曾一度备受重视,被“武家化”了,但资胜就任“武家传奏”后,虽然仍然与武家有密切联系,却不能习武射箭了。
德川家康主要通过摄家向朝廷传达幕府的意见,从而达到管理天皇的目的。摄家是朝廷的核心,由关白担任,三公(内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之职也被其所占据。江户时代的摄家成为将军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与古代的含义完全不同。从《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2条可知:朝廷内部,三公位于亲王之上。历史上的“朝廷传奏”变为“武家传奏”。“紫辰殿御条目”露骨地表现出关白对天皇的态度:“如禁里(天皇)、仙洞(上皇)御政不正,也要敢于直言。”而灵元天皇把阻碍自己行为的关白称作“私曲奸佞之恶臣”,可见其关系之紧张。德川幕府通过摄家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公家没有实质的东西。
从以上诸多内容可以看出,武家对于公家在权利掌握方面具有优越性,朝廷在世俗权利方面完全服从于幕府。朝廷最终成为一个拥有领地不如一个普通大名、且花销需要幕府支付的形式上的公。称学问为其“擅长之事”的天皇作为日本最大的公也只能停留于精神层面了。
总之,幕府将军依靠天皇授予官位的方式获得了公的资格,从而使武士阶级进入公的行列。朝廷和幕府之间是形式上的上下关系。将军面对天皇时并不把自己称作私,说明天皇与将军的关系停留在了公的层面,武家社会中奉行的公私观也就不会用于将军对待天皇上。事实上,幕府不但没有对朝廷奉公,反而在诸多领域限制朝廷。公家和武家在公的层面上统一的同时又被截然分开。
二、武士政权中公私的重层结构
第一,武士阶级在天皇那里得到公的资格,进入公的领域以后,确立了独特的公私体系。公的领域是以公A(将军)为顶点,层层下移的重层结构,如公A1、公A2、公A3……。上层的公要求下层具有公的性质,行使公的权利。如,幕府视大名为公,在事关国家制度的根本事项上,要求藩具有公的性质。大名要求家臣也成为公,行使公的权利。幕藩体制下的公指的就是这种从上到下的权利统治秩序。与此同时,每层的公面对上层的公时,又成为私。“幕府∕将军”对于“藩∕大名”来说是公,“藩∕大名”是私。而“藩∕大名”对于“领地∕家臣”来说是公,“领地∕家臣”为私。渡边浩指出:“公和私是一对相对概念,从小箱子看大箱子时为公,而谦虚表达自我时则为私。”[3]所以,私是相对于公而言的。公和私是相对的概念,相对性是武士政权中公私观的重要特点。公是私,私也是公。公和私不仅不是二元对立的,而且是相对的,且可以相互转换的。
第二,公可以发展私的领域,但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幕藩体制允许私以公为据点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大名可以私自建立自己的宅院,即私宅。而且,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下层的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私的决定。但是,德川幕府继承了丰臣秀吉太阁检地的成果,在地领主在自己私领中建立的区域性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中世的公被否定。幕藩体制下的私领域必须是在公的允许下存在,且不可以在私的领域内重新确立公的领域。如《武家诸法度》第6条规定:“诸国主并领主等不可致私诤论,平日须加谨慎也。”该规定明确表明幕府禁止各藩挑起争端。第8条又规定:“国主城主一万石以上者并近习之物头(者),私不可拾婚姻事。”可见大名的婚姻也并非私事,不能自行决定。第16条则规定:“私之关所、新法之津留,制禁事。”法律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该制定中不允许藩对法律之事情自行处理,即知行国内不可以设立私法。而各藩对于家臣的约定条款中也有“家臣可拥有私宅,但不可设立私法”等内容。纪州家家法中规定:“嫁娶不可私自为之。”[2]116家臣在私领域方面被大名限制了。
第三,上位的公与下位的私是主与从、御恩与奉公的关系,但奉公的直接对象是上一层的公。奉公被武世阶级誉为高尚的道德伦理。大名从幕府那里获得封地,大名就要奉公于将军。同样,家臣从大名那里获得俸禄、知行,家臣就要奉公于大名。奉公是需要尽忠且不惜生命的。这种奉公精神是战争年代缔结的同生共死的约定。江户时代虽为和平年代,为主君战死沙场的情况已经少之又少,但奉公、效忠作为武士阶级的基本伦理备受幕府的重视。1611年,德川家康命令各个大名在“誓文三条”上签字,宣誓效忠和服从德川家。1635年,《宽永诸士法令》要求武士“砥砺忠孝,严守礼法”[4]。
然而,重层结构下的公私观致使武士们经常困扰于公和私的矛盾冲突中。公、私的层次性决定了私直接效忠于上一层的公。上位的公(小公)和上上位的公(大公)发生矛盾时,奉公的对象往往优先于小公。能充分反映这种公私激烈矛盾冲突的莫过于“赤穗复仇事件”。该事件表现了武士在面对大公和小公时的不同立场。大公是以将军为权利顶点的幕府,小公则是以大名为主人的藩的层面。因为浅野违背了将军的意图,所以被处以死刑,且罢黜武士身份、剥夺封地。46名家臣为了奉公,不惜牺牲自家的利益,甚至生命。荻生徂徠指出:“46士为主人复仇之事乃知耻表现,为忠义之举。然此仅为浅野家臣所言,实为私。因浅野伤殿中被令切腹则视吉良为仇敌,明知幕府否却引发骚动,乃法律所不允。”[5]也就是说,浅野无视幕府而伤害吉良义央的行为是不顾公家的私之行为;浪人替主君报仇,实现自己忠义之心的行为也被认为是私。作为幕府官员,徂徠切断了公与私的领域,确立了国家之公对藩之公的优势地位。但是正如源了圆所述,徂徠建议对浪人的处分不是枭首、斩罪等刑罚,而是剖腹。通过剖腹,一方面能够理解浪士们的心情,为他们保全作为一个武士的尊严;另一方面,对于违法行为,应该站在公的法律上给予处罚。由此可见,徂徠是在把公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同时,又把他们统和在了一起。而对于武士来说,面对幕府的处理方式,他们也必须接受两点:“一是46家臣为主君报仇是义士;二是46名家臣因为杀害了吉良义忠,应被处以死刑。”[6]这两点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武士心目中也就糅合在一起。
幕藩体制下的公私关系就是这么一种自上而下的主从关系,即“将军→大名→家臣→……”。这种关系下的伦理价值观念被赋予了忠诚、简朴、自律、献身等内容。“顾其身,得主人,尽奉公之忠,交友厚信,慎独身,专于义。”[7]但是,这些伦理观念的对象只停留在距离私最近的公的层面上,是大名对将军、藩士对藩主、家来对旗本的效忠。
总之,武士政权的公私关系以及由其产生的公私观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公是一个多重构造,有大公和小公之分;其次,公和私是相对的,公=私;再次,公允许私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但被限制在一定范围;最后,公相对于私来说,处于上位,要求私尽忠、奉公。
三、村落共同体中的公私观
在社会层面,村落共同体及其首领(庄官)是公,每个家(或家庭)则为私。
据统计,江户时代农村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80%以上。而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农民又处于较高的阶层。这样,村落成为江户时代主要的社会存在形态,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共同体。村落为共同体,而庄官为共同体的首领,村落和庄官具有公的性质。日本古代的“おおやけ”本来就是指代村落共同体及其首领。虽然律令制传入后,受中国公私观的影响,日本的公指代了朝廷以及天皇,进而指代了国家和统治者,但是村落共同体及其首领作为公的观念一直保留下来。丰臣秀吉太阁检地以后,中世的庄园制被摧毁,大量的自耕农出现。自耕农这种分散的农业经营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人们依靠农村共同体及其首领来保护家庭存续的心理。德川幕府继承了太阁检地的成果,在经过几次检地以后,幕府得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这样,农民变为本百姓,世袭幕府分给自己的份地。作为回报,农民需要缴纳地租,服劳役于幕府。
幕府的公权利和作为私的农民之间的连接者正是庄官。江户时代的庄官一般由村落共同体的首领担任,是村里的财富拥有者和权威代表者。幕府正是利用了村落首领的这一点,使庄官具有双重身份。一边他们作为农民,耕种土地,住在农村,是农村共同体的首领和代表;另一边作为政府管理农村的官员,又具有武士阶层的性质。幕府征收农村税金时并非直接对每个家庭征收,而是采取村庄承包的方式。江户时代武士住在城下町,每到征收税金的季节,才来到农村,把缴纳税金的文书交给庄官。庄官除了按照文书的要求确定每个家庭应该承担的份额外,还要把政府的文书传递给其他村庄,即从一个共同体传递到另一个共同体。传递的顺序是政府规定的,这样,税金的缴纳完全变为以村庄为单位,政府只要把开头的工作做好即可。庄官通过农民和武士的特殊身份把农民纳入幕府公权利的控制之下,成为公的代表,每个家庭成为服从于庄官的私。
这样,庄官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纯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并非单纯的武士阶层的主从关系,而是融合了二者在内的特殊的公私关系模式。这种特殊的公私关系使得公既有温情的一面,又有奉行上级政权指示对其进行压榨的冷酷一面。温情表现为庄官积极为村落共同体的繁荣而努力。如通过“寄合”方式商讨村里大事、兴修水利、制定村规、为减轻农民租税劳役而努力等。冷酷则表现为不顾及农民的承受能力不断加重课税及劳役等。当温情大于冷酷时,农民便服从听命于公,并积极奉公。奉公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积极参与村子里的共同活动,诸如兴修水利、共同祭祀、为保证村子边界与邻村争斗等。因为租税是保证农民土地所有的必要条件,所以缴纳租税也是奉公的表现。私只有服从、奉公于作为公权利的庄官,效力于作为公领域的村落,才会得到温情的庇护。否则,就要受到公的处置,如村落中的“村八分”、公权利中的法律制裁等。
当冷酷大于温情时,农民就不会服从、奉公于庄官,而是向更高的公权利申诉。如农民被课以重税无法承受时,他们会认为责任在庄官,向庄官以上的公权利争取权益或替换庄官。当上层的公权利也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时,他们会诉诸更高一层的公权利。这种斗争甚至演变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百姓一揆。用公私关系解释的话,就是作为私的庄民向上位的公申诉下位的公的过错。如果农民以藩为攻击对象,他们就把希望寄托于将军或天皇。如弘化三年南部藩一揆请愿道:“百姓乃天下百姓,期待公仪垂怜。”[8]571《那谷寺通夜物语》中则含有对天皇的期待:“对公领已不抱希望,冒死请求收留我们为京城王之百姓。”[8]14正是因为民众希望好官能带来仁政,所以才把公作为权威的象征,并指向更上层的公。也就是说,在农民的思想里,上位的公更具有权威,更值得信赖。
农民追讨庄官的行为,实际为一种所在层面上私对公的暂时叛离。这从私对公绝对效忠的武士伦理观来看是大逆不道的。而且,向上位的公申诉下位的公之罪过的行为也是和武士的公私观背道而驰的。因为武士奉公的对象为所在层面的公,一般不会寄希望于更上位的公。
总之,虽然农民也有公主私从、公优越于私的公私观念,但是阶级矛盾会导致所在层面公私的暂时分离,致使农民诉诸更上位的公。
四、家层面的大公与小公
除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村落共同体)的公以外,江户时代的日本人还面对着一个与之联系更加密切的公——家。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人而言,“‘家’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的存在,也是他们终生为之奋斗并终生受其辖制的精神的存在”[9]。家是依靠血缘以及模拟血缘方式而组成的共同体。它是成员、家产、家名等的总称,以“父家长制”“长子继承”等为主要特点。其中,父家长制就是指父亲作为家长掌握对家的统治权,掌管诸如子女婚姻、财产分配、惩罚权等权利。于是,家确立了公的领域,家长确立了公的地位,而家的成员成为私的存在。
江户时代的家是以恩情与奉公为基本原理的。家是成员得以生存的最后堡垒,家给成员以温情的保护。有血缘关系的家长自不待言,从小就奉公于主家的奉公人也是在主家、家长的庇护下生存的。家长对奉公人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且这种关心是不论辈分高低的。住友家就指出不能忽视丁雅的作用,说:“丁雅极为重要,要认真对待之。”[10]并在家训中专门提到对丁雅的照顾,“生病时需悉心照料”,充分体现了住友家对奉公人的关心。可见,从生活起居到成家立业,家长完全把奉公人作为家中的一员。与家的恩情相对应,家的成员要奉公于家。要做到这一点,每个人就得各得其所、各安其业。武士要修炼本领,时刻效力于主人;农民要安心经营农业,纳税、服役,争取土地永久的耕作权;工匠要努力磨炼技术,使家的技艺代代传承;商人要专心经营生意,维护家的声誉等等。
但是,江户时代的家是有本家和分家之分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本家,但是“本家-分家”是江户时代非常普遍的存在方式。作为私的家的成员既要面对分家之公,也要面对本家之公。而本家和分家之间也确立了公私关系。这样,家的成员、分家、本家三者之间就有了复杂的公私关系。
对于作为私的家的成员来说,分家为小公,本家为大公。人们既要奉公于“小公=分家”,又要奉公于“大公=本家”。确切地说,为了“小公=分家”的延续和繁荣,必须首先效忠于“大公=本家”。戴季陶早在《日本人论》中就这样叙述武士阶层的家观念:“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11]武士阶层奉行的效忠、奉公观念在奉公于分家和本家时得到了统一。武士的“小公=分家”包含家业、家格、家名三个要素。家业是指武士从主人那里得到的俸禄。家格是指家的资格,这种资格是依据家系以及先祖的功绩而定的。家名是凝结了一家的名誉、地位、财产的名义。这些东西的得来正是主君所赐。为了保证“小公=分家”的荣耀以及繁衍,武士的首要任务就是效忠、奉公于“大公=本家”。“忠”成为武士阶层奉行的伦理价值观的核心。
不仅武士阶层,庶民阶层中也有很多人面对家的小公和大公。如商家的学徒在拥有了自家店铺以后,就有了分家和本家之说。分家要严格按照主家的家训经营;每逢过节或祭祀的日子,也要先到本家祭祀祖先。本家也比较重视奉公人的忠诚程度。无论是小时候开始奉公的“子饲奉公人”,还是“中年奉公人”,他们都大量接受了奉公伦理的教育。诸如“当代家业之繁荣非自身之功劳,而是祖先世世代代之功德、父母教养,不可忘也”[12],“每年正月、七月,聚集一起,于先祖灵前诵读,此乃严守之家法”[12],“继承家业直至末代,至关重要”[13]等。通过这些家训的训导,使奉公人认识到祖先之功劳、家业的重要性,明白效忠于主人的必要性。
这样,分家在本家面前成为私的存在。主家的兴衰与分家密切相关,所以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要舍分家之私而成全本家之公。赤穗事件中“46义士”正是不顾及分家之私而奉公于本家的表现。《南总理八犬传》《菅原伝授手習鑑》《一谷嫩军记》《朝夷巡道记》《赖豪阿阇梨怪鼠传》等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描述了分家和本家发生矛盾时优先于本家的伦理价值观。庶民阶层中舍分家优先本家的表现虽然没有武士阶层那么惨烈,但是分家的一切行为都要以本家的规定和要求为行为准则。
总之,家的层面确立了与个人联系最密切的公,是层层下移的公私体系的最下层。正因为家之公与私的关系的紧密性,所以出现了把主人模拟为家长、把主人家模拟为本家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层面的公私观具有普遍性。
五、结 语
本文以公与私为主线,分析了江户时代政治层面(政权内部)、社会层面(村落共同体)、家的层面的公私观。其中,社会层面、家的层面的公私观念是受到政治层面公私观影响下出现的,是对政治层面公私观的模拟。
综观江户时代各个层面公与私,可以发现不能简单地给公和私以明确的定义,即不能说公是什么、私是什么。公和私是一种领域概念和关系概念。从国家之公到家之公,从武士的私领到分家之私,公和私都是有领域范畴的。但是,这种公私又不是绝对的,而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的,公私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概念。家(家长)面对村落(庄官)时为私,而面对家的成员时则为公。这就出现了公是私,私又是公,即“公=私”的重叠式结构。可见,公是具有共同体性和首领性的。该特征没有离开日本古代“おおやけ”的性格。这决定了公具有领域上的封闭性和关系上的上位性。领域上,国家作为公达到了最大范围;关系上,天皇作为公到达了最高位。这样,国家和天皇没有了任何的私性。与公相对应,私具有个体性和从属性。这就决定了私具有领域上的私密性和关系上的下位性。领域上,私缩小至个人的私欲、私念;关系上,私降至权利体的最下层——被统治阶级的个人。被统治阶层的个人没有了任何的公性。
上述公私关系下的公与私奉行公主私从、恩情与奉公的伦理。主与从、恩情与奉公是相辅相成的。公一方面强调奉公的必要性。林罗山、荻生徂徕等思想家都强调了政治层面奉公的合理性;家的层面,家长无不把奉公写进家训里。另一方面,公不忘施恩情于下位的私,从而使私奉公时忘记私欲、私情。主人对家臣的关怀、庄官对农民的照顾、家长对奉公人的体贴都是公的恩情的体现。公是以恩情换取私的奉公,而私则是以奉公换取公的恩情。私如果想要继续得到公的恩情就要效忠于公,一心为公。江户时代的私一般不强调恩情的合理性,而只把奉公内化于内心。这是源自于私对公之恩情的感动,同时又符合了公对私奉公的要求,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恩情与奉公在每个层面上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政治层面的恩情表现为公给予私的权利和私领等,村落层面表现为庄官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以及为村庄谋福利等,家的层面则表现为家长给予成员生活方方面面的照顾。奉公也是如此。政治层面的奉公表现为为政权统治服务,村落方面的奉公表现为缴纳租税、参加村落共同体的相关事宜,家的层面的奉公表现为为家的繁荣和延续而努力。需要注意的是,庄官特殊的身份,造就了村落方面恩情与奉公的特殊性。
总之,江户时代的公与私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命题,是分析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重要线索。以上公私观的特点不仅对江户时代,而且对之后的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1]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3.
[2]小路田泰直,等.日本史における公と私[M].东京:青木书店,1996.
[3]渡边浩,等.比較思想史的脈絡 から見た公私問題[M].京都:将来时世代国际财团·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1998:121.
[4]朝尾直弘,等.日本歴史:第4巻[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245.
[5]中西仁.日本的公私観念の批判的理解を目指す社会科授業設計[J].社会系教科教育学研究,2006(18):67.
[6]田原嗣郎.赤穂四十六士論―幕藩制の精神構造―[M].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70-71.
[7]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97.
[8]谷川健一,等.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第6卷[M].东京:三一书房,1981.
[9]李卓.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J].世界历史,1993(4):72.
[10]吉田丰.住友総手代勤方心得[M]//商売繁栄大鑑·日本の企業経営理念:第4巻.京都:同朋社,1984.
[11]戴季陶.日本人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67.
[12]宮本右次.鴻池善衛門家訓について[J].国民経済雑誌, 1964,110(3):38.
[13]吉田實男.商家の家訓――経営者の熱きこころざし[M].大阪:清文社,2010:214.
2015-06-21
王 猛(1981-),男,博士研究生,讲师;E-mail:1839993443@qq.com
1671-7031(2015)06-0103-06
K313.3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