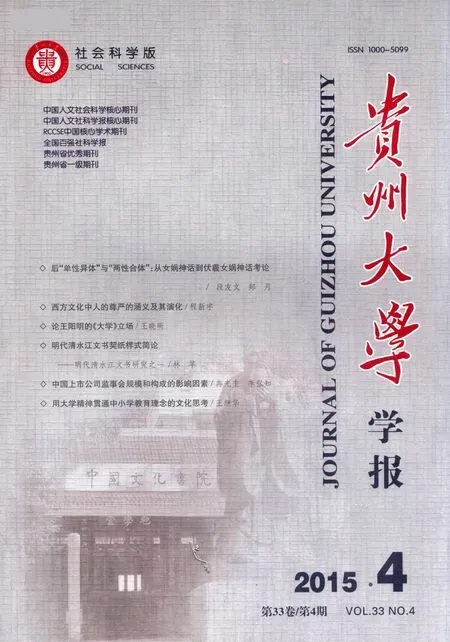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李 旭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浙江杭州 310025)
一、引论:儒学尊德性、道问学的张力与阳明良知学中的情理构造
在儒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张力,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对峙就体现了这一张力。这一张力其实在孔子那里就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以仁救礼、释礼归仁,抉发出“仁”为君子之道的第一义,奠定了儒学尊德性的传统。以仁为核心美德的儒学尊德性传统或多或少带有重情的特征。尽管“仁”之义涵广大精微,孔子对“仁”的解释也圆转多方,但仁者“爱人”可以说是最素朴简易的解释。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更突出了仁德的情感性。宋儒中程伯子明道一脉以感通性的与物同体解释仁,继承了孟子的理路。程叔子伊川则不赞成“专以爱为仁”,根据其性、情、理、气相分的形而上构架,他认为爱是情、仁是性,仁者固然博爱但爱并不就是仁[1]。朱子继承伊川的理路而释“仁”为“爱之理,心之德”,强调了仁爱的理性特征,但毕竟“爱”是基本的,没有爱,也就谈不上爱之理。不过,“仁”虽然在孔孟儒学中是最基本的德性,却不是唯一的德性,《论语》和《中庸》都以智、仁、勇为天下之达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普世价值”。在孔子那里仁、智并提,君子成德需要仁、智兼修。《论语》以“学而”为首篇,即体现了孔子之道好学尚智的取向①参见《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概括君子之道,与孔子的仁、智并举一脉相承。但“尊德性”和“道问学”两者在孟子和荀子那里开始各有所偏重,儒学的大成中道品格有所缺失。
孟子虽然也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但突出的是仁和义,他以“是非之心”作为“智”之端,“智”成了道德判断的先天能力,与孔子所讲的知人、好学之智其实有很大差别。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之学主要张大的是儒学中尊德性的一面。与之不同,荀子的儒学则发扬了孔子之道中重学识、博文约礼的传统,张大的是道问学的一面。从荀子儒学与孟子儒学的差别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中偏重尊德性的孟子一脉具有重情的特征,而偏重道问学的荀子一脉则对人的性情持相当负面的看法,更有崇理(礼)、尚智的取向。
程朱理学的道统说尊孟子而贬荀子,也肯定了仁是“爱之理”,但其格物穷理的致知路向还是淡化了儒学的情感底蕴,使得“天理”的核心范畴具有了客观的义理性质,天理人欲的截然对立就与此相关。程朱理学对孟子学的修正最鲜明地体现在朱子明确认为不仅《中庸》讲的“喜怒哀乐”之情有中节不中节的问题,而且孟子讲的四端也可能不中节,“若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便是不中节”[2]。基于这一认识,朱子接受孟子那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四端②《孟子·公孙丑上》。的观点,但对孟子在与告子论辩时提出的“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③《孟子·告子上》。这一论断,朱子其实是有保留的。既然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也可能不中节,因此它们就只是仁、义、礼、智之端,而不能等同为仁、义、礼、智,君子修德要达到德盛仁熟的境地仅靠善端的良知良能是不够的,还需要穷理致知的道问学工夫。因此,程朱理学虽然也以“仁”为根本德目,但其穷理致知的进学路向实际上相比孟子而言更具有崇礼、重智的理性特征,“道问学”有盖过“尊德性”的趋向,这在遍注群经的朱子那里更为明显。朱子极强的道问学路向在当世就遭致了陆九渊的异议,在明代中叶又遇到了王阳明心学的强大挑战。
阳明心学在义理上始于对朱子学中心与理为二、知与行分离的不满,实际上也包含对朱子学过强的道问学取向的不满。阳明重新光大陆九渊心学的路向,主张“心即理”,并且倡言“知行合一”,走向了一条与程朱理学格物穷理、知先行后不同的成圣路径。也可以说,阳明不满于程朱理学对孟子学的修正,实际上是重新彻底地回到了孟子学尊德性的道路上,他在江西平定宁王之乱以后专以“致良知”为立说宗旨,更彻底鲜明地回到了孟子尊德性的学脉。那么,阳明的良知学是否可以说也是以“情”①指四端的道德情感。
为本的呢?如果可以认为阳明讲的良知就是孟子说的四端,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良知”就是先天的道德情感。阳明那里的“良知”是否也有朱子所指出的不中节的问题,是否也只是德性之端?道德情感能充当道德认知和践履的充分条件吗?如果在伦理生活中我们一任性情,那是否会导致私欲和意气混入道德感情中来,发生“认欲做理”的危险?事实上,在阳明后学中确实有过假良知之名而肆情任意的流弊。明末儒者刘宗周就曾指出过这类良知学中的流弊: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受其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发挥其师刘宗周的见解一再地指出“以情识为良知”失却了阳明良知学的本旨②《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以情识为良知”果真违背了阳明良知学的本旨?孟子的四端难道不是情识,不是从道德情感中生发出的道德意识?阳明的良知学思想从孟子发展而来,自无疑义。更有甚者,阳明在晚期对情感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认为“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③《传习录》卷下,第290条。《传习录》的分条根据陈荣捷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以下不再单独注明。,这样不仅四端,而且七情也属于良知了。由此看来,“情识”“一是皆良”的观点并非王门后学的妄作,在阳明本人哪里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然而,主张“以情识为良知”并非良知学本旨的观点在阳明本人那里同样可以找到论据。在我看来,这倒不是象黄宗羲认为的那样,因为阳明以“良知”为喜怒哀乐“发之中”④《明儒学案》,第639页。在阳明那里“良知”是贯通未发已发的,即便他有时讲到良知是“未发之中”,也只是因方设教的权说。如果固守良知为“未发之中”,错失阳明“事上磨练”的宗旨,将会有“荡之以玄虚”的弊病。,即便在发用处求良知,也未必如黄宗羲所言“便入情识窠臼去”⑤《明儒学案》,第212页。。因为在阳明良知学的成熟期他不再笼统地以孟子的四端来讲“良知”,而是突出了四端中的“是非之心”,以涵摄四端的“是非之心”为良知。“是非之心”在孟子那里是“智”之端,可以理解为是实践中的理智辨识能力。“以情识为良知”是否非阳明的本旨,还得看他对“是非之心”怎么解释。
因此,在阳明的良知学中情感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断定的问题。他的良知学并非简单承袭孟子,通过对《大学》《中庸》等经典的重新解释并参之以他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和百死一生的人生历练,他的“良知”概念具有丰富的含义,必须通过分析他的“良知”概念与孟子四端说的继承发展关系,分析他如何以良知学来重新解释《大学》格致诚正诸条目以及《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我们才可以比较完整地理解他的良知学,仔细分疏“良知”的各个层次中情感的地位。照瑞士哲学家耿宁先生在其近著《人生第一等事》中的分析,阳明良知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其“良知”概念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作为自然禀赋的向善的情感,这个良知概念是对孟子四端说的继承;第二重含义是“对本己意向中的伦理价值的直接意识”,这层含义是对孟子“是非之心”的一个发展,其中包含了自知、独知的自我意识;第三重含义是“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是本体论层面的概念,用阳明自己的话来说是“乾坤万有基”[3]如果耿宁先生这一分析不错,那么阳明的第二和第三个良知概念就不只是孟子四端意义上的道德情感,而是包含了更深广的内涵。在阳明相对孟子而言发展了的良知概念中情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以情识为良知”是否只是阳明前期良知思想中包含的问题,在第二和第三个良知概念中是否得到了克服?相比第一个良知概念,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和“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是否结合了更多“道问学”的因素而具有更强理性特征?如果“良知”是情感性的道德主体,那么在良知中是什么样的基本情感在起作用?这些就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二、从物上穷理回到有感之知
阳明突破朱子学的权威而立己说,并不象今人那样是为了理论创新,而是出于身心学问的内在困惑。阳明早年曾笃信朱子格物穷理之说,这从他亭前格竹而致病的著名故事也可以看出。几年后阳明虽然对朱子读书格物之法有了更贴切的认取,开始悔悟先前泛求天下事物之理而不懂循序渐进,这其实是对朱子格物说的片面理解,但“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①年谱“弘治十一年”。,在朱子那里还是没有找到成圣贤的真切门径[4]。因此,阳明自家学问的发端处就是要解决这个“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问题。从阳明年谱来看,这个问题获得真正解决的起点是“龙场悟道”。
年谱记载,正德三年戊辰,阳明谪至贵阳龙场,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这当然不是说阳明开始领悟了朱子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而是说他突破朱子的格物穷理说而形成了自己对格物致知的独到理解。“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②年谱“正德三年”。这就是阳明在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所悟的关键。圣人之道就在自家心性中,不必求之于事物,因此格物致知也就不必到物上穷理,而是要明心见性。阳明此时已经体认了心学的要义“心即理”。他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所悟,尤其是将自己的所悟运用到对朱子以来最基本的儒家经典《大学》的解释,发展出了一个迥异于朱子学的学问路向。
阳明突破朱子学自立己说的起点是“知行合一”说,并由此出发,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对《大学》的解释,标举出其中的“诚意”条目,并否定了朱子的《大学》改本而重新回到古本。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以他对“格物致知”的自家证悟为基础,而这一证悟的实质乃是以“心即理”的心学觉解置换朱子“格物穷理”的问学工夫。陈来教授指出,“在阳明哲学中知行观的解决与心理观有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所以阳明也说,以心理为二故知行为二,以心理为一故知行合一”[5]。因此,我们只有理解了他的“心即理”说,才能真正明白“知行合一”的本体基础;反过来,了解“知行合一”说,也有助于我们从践履工夫出发理解“心即理”这一思辨命题。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非常著名,但它并非如常识所想的那样是一个提倡道德方面知行一致的应然命令,而是在本然中追溯应然的道德本体之发现。它说的是“知行是一个”,而非“知行要一致”。这不仅与朱子的知行观相异,也与一般常识对知、行的理解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就连徐爱这样阳明的早期亲炙弟子一开始也不能明晓这一学说。
《传习录》记载: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③《传习录》卷上,第5条。
从这段话来看,徐爱在伦理领域中理解“知行合一”说,知是知孝、知悌之类伦理的知,行是行孝、行悌之类伦理的行,徐爱据常识认为知、行事实上经常是分离的。阳明的应对则是认为知而不行的“知”不是真知,真知一定是知行一体的,他用《大学》“诚意”条目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阐明“真知行”的特征。好好色、恶恶臭这类感性活动具有鲜明的知行一体的特征,阳明顺着《大学》的理路认为伦理认知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我们也可以说,在阳明看来“知孝”“知弟”这类“德性之知”与“好好色”“恶恶臭”一样具有情感动力,同属于“有感之知”④关于“有感之知”的概念,参陈嘉映教授《说理》,第175页。以下其字面意思即“带有感觉地知道”,区别于名相之知、推论之知,大体相当于墨子的“亲知”概念。。未曾被私意隔断的有感之知,就是阳明所言“知行的本体”。这个“感”不只是声色臭味的感官之感,而是“紧切着实”的情感之感。感受活动一般地具有牵动我们的本己生命的切己特征,这正是阳明以好好色、恶恶臭以及饥寒痛痒这类感性感受来类比地阐明德性之知的“知行合一”性质的现象根据。但是,在这段关键论述中阳明并没有明确阐发出这层现象根据,并没有讲明知孝知悌如何能够具有好好色恶恶臭一般知行合一的特征,因此也遭致了一些学者对其“知行合一”说的质疑。
韩国16世纪理学家李退溪在阳明学方传入韩国之际就批评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其以见好色、闻恶臭属知,好好色、恶恶臭属行,谓“见闻时已自好恶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以此为“知行合一”之证似矣。然而阳明信以为人之见善而好之,果能如见好色自能好之之诚乎?人之见不善而恶之,果能如闻恶臭自能恶之之实乎?
孔子曰:“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又曰:“我未见恶不仁者。”盖人之心发于形气者,则不学而自知,不勉而自能,好恶所在,表里如一,故才见好色,即知其好,而心诚好之,才闻恶臭,即知其恶,而心实恶之。虽曰行寓于知,犹之可也。至于义理则不然也。不学则不知,不勉则不能,其行于外者,未必诚于内,故见善而不知善者有之,知善而心不好者有之,谓之“见善时已自好”,可乎?见不善而不知恶者有之,知恶而心不恶者有之,谓之“知恶时已自恶”,可乎?故《大学》借彼表里如一之好恶,以劝学者之勿自欺则可。阳明乃欲引彼形气之所为,以明此义理知行之说,则大不可。①《退溪先生文集》卷四一,第26页。转引自《四端与七情》,第252页。
对退溪的这个批评,李明辉教授为阳明提出了两点辩护:其一,“《大学》传文以‘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来说明‘诚意’之义,这只是运用‘类比’(analogy)的手法,并非真的以‘恶恶臭,好好色’为‘诚意’。这犹如孔子以‘好色’喻好德’,并非他真的认为‘好色’与‘好德’是一回事”;其次,“退溪强调:‘人之心发于形气者,则不学而自知,不勉而自能,好恶所在,表里如一。’这固然是一个可以体验到的事实,但这也正是阳明的类比所诉求之点。因为根据孟子,在义理的层面上,良知、良能也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2]185。这个辩护中的第二点是关键性的。退溪认为对“义理之善”的知与行在本质上有别于好好色恶恶臭,“不学则不知,不勉则不能”,这个看法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相悖。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道德情感来论证性善,恰是为了阐明道德义理也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天端倪。这种原发性的道德情感即是知行合一的。就此而言,四端的德性之知与“好好色恶恶臭”的感性本能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是“有感之知”,它们是“同类”关系,而不只是“类比”关系。从孟子和阳明的理路看,孔子说“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这并非因为“好德”不具有如“好色”一般原发的知行合一本质,而是因为德性之知天然的知行本体被私意、习气深深地遮蔽了,因此需要一番致知的工夫来回复这本体。阳明后来“致良知”的学说发掘的就是这一“心的逻辑”。
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说来解释《大学》格致诚正的工夫,是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深层理据。由此可知阳明在龙场悟道后的早期学说中虽还没有明确提出“致良知”的口诀,但孟子的良知思想已经是其“知行合一”说以及对《大学》相关解释的根据。我们可以看《传习录》第8条: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阳明在这里以孟子讲的“良知”来解释《大学》“致知格物”之“知”,理路非常显豁。由此可见,“知行合一”的本体正是孟子讲的“良知”,而此“良知”乃是“有感之知”,这在孟子“恻隐之心”的义例中非常明显。孟子的四端说正是陆王心学“心即理”说之所本。这个“理”不是事物自在的定理,而是在道德情感中生成的义理。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作为道德感受并不只是意向地指向仁义礼智的道德义理,而是意向地构造出此义理。牟宗三先生说:“‘心即理’不是心合理,乃是心就是理;‘心理为一’不是心与理合而为一,乃是此心自身之自一。此心就是孟子所谓‘本心’。”[7]简言之,在孟子和陆王心学的系统中,“心即理”的“理”乃是人心的情理,仁义礼智“理”即是本心的朗现,此本心即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道德情感。因为道德义理就是从本心中发出来的,就是良知的自觉,不是求之于外物,因此自然有实行出来的内在趋向,这就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根据。
阳明以《大学》“诚意”条目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阐明“知行合一”,昭示了“德性之知”作为“良知”具有和感性活动一样的切己自发性质,同属“有感之知”。阳明这一阶段立说的重点在澄清“求理于事物”的迷误,救治由此而带来的心与理为二、知与行分离的弊病,因此将恻隐羞恶一类的道德感知与好好色恶恶臭之类的感官感知混同视之,标举出《大学》“诚意”以作为“知行合一”的经典理据。如果对阳明的这一立言宗旨弃置不顾,只是抓住“良知”自发的感性特征,那么好色、好货之类感官情欲就可能混入“良知”中来,产生“以情识为良知”的弊病。要避免这一流弊,就必须进一步将恻隐、羞恶之心一类的道德情感与好色好货之类的感官感受分别开来。
从前面退溪的质疑来看,义理层面的知行与感官形气层面的知行显然有差异,退溪讲的“知善而心不好者有之”,“知恶而心不恶者有之”,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表明了这一点。阳明可以说这种意义的知已经不是真知,不是“知行的本体”了,但既然恻隐羞恶之心与好好色恶恶臭同属于“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为什么只是前者需要致知诚意的工夫?阳明基于“知行合一”说发掘了道德感知与感官本能同属“有感之知”的类本质,但还必须进一步明辨它们的差异。显然,恻隐羞恶的道德感知更容易被私意障碍,要恢复这种天然的道德感知,需要去除私意障碍,而这首先需要在私意和道德情感之间做出辨析和抉择。这样孟子讲的四端中的是非之心作为道德判断的功能就必须凸显出来,成为阳明良知概念中核心的要素。
三、是非之心的天理与人情
按照耿宁先生的分析,王阳明的第二个良知概念是“对本己意向中的伦理价值的直接意识”[2]195,亦即阳明晚期四句教中的“知善知恶”之心,或者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孟子的“是非之心”。耿宁认为,这个层次上的良知概念,在王阳明那里是1519—1520年间开始成熟的,在此之前他用了好几个不同的表达来称谓这种对善的和恶的意向做出区分的道德意识,如“见心体”“天聪明”“本心”、“独知”[2]213。如“天聪明”的概念,即是“知善知恶”的良知概念: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①《传习录》卷上,第71条。。此处的“志”、“天聪明”,即良知,明确区分于自发的善意念,已经不是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意义上的良知良能,而是善恶意念之上更高层次的道德意识。良知与意念的层次划分在阳明的书信“答魏师说”中更为明确:
所云:“任情任意,认作良知,及作意为之,不依本来良知,而自谓良知者,既已察识其病矣。”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矣。[3]242“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照这个界定恻隐、羞恶、恭敬之心这类道德情感都只是“意”,良知是“知得意之是与非”的道德判断能力,相对自发的道德情感处于更高意识水平。阳明因此对孟子四端中的“是非之心”作了提升,使之相对恻隐、羞恶、恭敬之心获得了一个更高阶的地位。照此,这第二个良知概念具有对各种情意进行辨别的理性色彩,阳明并据此明确反对那种“任情任意,认作良知”的误解。可以想见,这种误解与阳明第一个作为“有感之知”的良知概念密切相关,而且这种误解想必在阳明后学中颇有影响,以致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发挥其师刘宗周的见解一再地明确反对阳明后学中“以情识为良知”的观点。
阳明第二个良知概念所具有的存理去欲的色彩非常强烈,如下面一段陆澄所记载的话: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②同①,第39条。
这种将好色好货好名的欲望当做心中贼、当做盗取粮食的鼠类而加以扫除廓清的道德主张与早期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阐明知行合一之论看起来简直是自相矛盾。由此亦可见,良知判断意念是非善恶的准则仍是“天理”,即孝、弟、忠、信这些伦理义务①在阳明那里“天理”还具有中和“至善”的意义,不只是一般伦理的善。例如他在南京任鸿胪寺卿的时候,弟子陆澄因儿子病危的消息而忧闷不能堪,他以“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劝解陆澄忧戚不能过度《传习录》卷上,第44条,体现了阳明心学的中道理性特征。。
阳明这一严于天理人欲之别的良知概念是否类似于康德有禁欲色彩的“实践理性”概念?是否剔除了情感因素,因而会面临实践动力缺乏的问题?如果阳明的第二个良知概念只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判断能力,那么它将面临阳明曾经对治过的知行两分的危险,需要在良知之外另寻实践良知的动力,这样它反而不如第一个作为道德情感的良知概念那样能知行合一了。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是否包含有情感性的践履动力?在阳明这里,答案当然是“有”。因为在阳明这里良知分辨的是非善恶并非外在的事物之理,而是心志本身的分别条理,在阳明“心即理”的理路中是非善恶的根据被回溯到了主体的好恶认同中:“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②《传习录》卷下,第288条。“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这听起来是一种极端恶劣的主观主义,与那种将道德判断看做偏好之表达的情感主义看来如出一辙③陈来教授就认为,阳明“只好恶便尽了是非”的思想尤其与康德排斥好恶的实践理性相悖(《有无之境》,第215页)。。情感主义是19、20世纪之交欧美流行的一种道德哲学思潮,它消解掉了所有善恶是非判断的公共性、客观性,使得普遍有效的道德认同和批判变得不可能,因为道德评价在情感主义那里变成了没有约束力的偏好之表达,“这是善的”被等同为“我赞成这,你也赞成吧[8]。伦理学中的这种情感主义对道德而言是解构性的,将使得公共的是非变得不可能,在是非善恶的判断方面人们将变得莫衷一是。心学在人心中寻找善恶是非的根据,尤其需要将自己与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情感主义道德观区分开来。孟子特别强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些都是普遍的而非特定地域和时代的人才具有的道德情感。他甚至从感官好恶的普遍性来论证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④《孟子·告子上》。
因此,从孟子的思路来看,以道德情感为善恶是非的根据,并不导致取消道德准则的公共性、普遍性的相对主义。但阳明此处并未将作为是非之来源的“好恶”界定为人心所同的好恶,为相对主义的解释留下了空间——你有你的好恶,我有我的好恶,因此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这种相对性的好恶是非固然可以在个体生存中有其意义,但无法运用到公共的伦理政治领域。
阳明将是非归结到好恶,是一种张扬主观性的情感主义吗?牟宗三先生对这段话有一个解释,他认为,阳明“是把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智也,羞恶之心义也’两者合一而收于良知上讲,一起皆是良知之表现。良知底是非之智就是其羞恶之义。阳明说‘好恶’就是孟子所说的‘羞恶’。”[6]138如果接受这个解释,那么良知作为“是非之心”仍是情感性的,而且和恻隐、羞恶之心落在了同一个层次,不能够充当恻隐、羞恶、恭敬之心是否中节的判准。但恻隐、羞恶之心也有不中节的可能,阳明是明确承认的。例如,阳明如此答复门生黄勉之关于宋儒批评韩愈“博爱之谓仁”的质疑:爱之本体固可谓之仁,但亦有爱得是与不是者,须爱得是方是爱之本体,方可谓之仁。若只知博爱而不论是与不是,亦便有差处[3]217。此处“爱得是与不是”的判断,显然就是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由此可见是非之心是比爱的情感更高一层的理智判断。再如,阳明超出俗见不以落第为耻而以落第动心为耻⑤年谱弘治六年。,表明羞恶之心也有发得当与不当的问题。
窃以为,阳明“是非只是个好恶”的讲法不能无病,容易导致以情识为良知而纵情任性的流弊。舍勒在讨论“良知主体性”问题时就提出过质疑:“这个向我们窃窃私语、告诉我们(只是以错误的方式)一些被我们看作是良知陈述的东西,它究竟是良知,还是另一种感觉或冲动?”[7]391阳明将良知归结到好恶上,难以避免这样的质疑。正如陈来教授所指出的,心学虽然克服了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缺乏实践动力的弊端,但又陷入了另一个弊端:在心学,没有意志与意念的分离、理性与感情的两分,本心与心交叉使用,良知即体即用,良知包含感情好恶,可以成为践履原则,但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它借用了感性的力量,便无法排除感性的渗入,以致“任心率性而行”都可在良知的名义下求得合法性,使纯粹的良知无法保持忠贞,这是王学“左派”的发生在理论上的必然结果。这也许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道德主体如果是“纯粹实践理性”,则失去了活动的力量,而道德主体涵容了感情因素后,又导致了感性参与决定意志动机的弊病[4]217。从阳明的第二个良知概念来看,他明确讲“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此处批评“在心学,没有意志与意念的分离”有失公允。但是阳明本人的一些论述不精准,也要为这类误解负责。良知作为“是非之心”与“羞恶之心”究竟是什么关系,与一般的好恶是什么关系,是一个还有待探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阳明那里作为是非之心的第二个良知概念在原发的道德情感基础上具有了更强的理性特征,可以作为喜怒哀乐以至恻隐、羞恶之类情感是否中节的内在判准。但是,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在阳明这里也还是完全先天的道德判断能力,是先天的德性之知,无关乎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作为是非之心,良知包含理智,但这种理智却并非来自多闻多见的好学,而是心灵先天的明觉察识能力。或许正是因为在阳明这里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不重道问学的资借,因此是非之心的理智又往往被好恶的情感所左右,良知与意念发生混同而带来以情识为良知的弊病。
四、良知本体的精诚、戒惧与洒落
在耿宁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中,第三个作为“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的良知概念与第二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更为微妙。耿宁将这三个概念分别简称为心理—素质概念、道德—批判概念,以及宗教—神性概念①《人生第一等事》,第273页。关于这三个概念在名称、所属范畴、实现方式之间的简要差别,参见陈立胜“在现象学意义上如何理解‘良知’?——对耿宁之王阳明良知三义说的方法论反思”一文中的图示。。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为什么是宗教-神性概念,与作为道德-批判概念的良知差别在什么地方?“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作为阳明第三个良知概念在何种意义上扩展了前两个良知概念?耿宁先生指出,这个良知本体是“作为‘心(精神)’的作用对象之总和的世界的起源”[2]271。因此,这个良知本体作为本原不仅是知善知恶的道德主体,而且也是更宽泛的作为世间万象之始基的一般主体。对这个作为一般主体的良知,阳明有诗咏之: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3]870
这个作为乾坤万有基的良知颇近于古希腊哲人阿拉克萨哥拉所讲的宇宙心智(nous)和黑格尔那里的世界精神,具有普泛本体论意义,不再是一个狭义的道德哲学概念。但良知本体的彰明与道德修养的工夫密不可分,因此也并非一个超离了道德实践的理论概念。
阳明的良知本体概念也可以在孟子的思想中找到渊源。孟子思想本就有道德形而上学的维度,如他对自我的本体性彰显: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②《孟子·尽心上》。。这是将四端都归摄到“我”,这个“我”是众德兼备的笃诚之体,由此诚体的体证而有莫大之乐。以“诚”为本,是《孟子》《大学》和《中庸》的通义,这是对春秋时代“忠信”德目以及孔子之“仁”的本体化解释。阳明立说之始就标举“诚意”为《大学》头脑,其心学统绪又上承孟子,以“诚”为良知本体顺理成章。孟子以孩提之童的知孝知弟为良知良能,还只是从自发伦理意识的现象上说,没有将“良知”本体化。阳明“致良知”教讲“事上磨练”,也注重从事父事兄的切近伦理生活中启发良知,但又不限于此,而是要求将此事父事兄的良知扩充开去达之事事物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孟子所讲的“万物皆备于我”。如果因为于事亲从兄处致良知的真切简易而局限于此,那样又会有遮蔽良知本体之病。阳明在答聂豹的信中说: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③《传习录》卷中,“答聂文蔚第二书”。
以宋明理学中的“体用”范畴来说,真诚恻怛是良知之“体”,事亲之孝、从兄之悌、事君之忠是良知本体之“用”,用虽万殊而体实归一。阳明这一思想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具体化了,对阳明而言这个“我”乃是真诚恻怛的良知本体。阳明以“诚”为良知本体,上接《大学》《中庸》《孟子》,下承周敦颐《通书》,这并不难理解。稍有蹊跷的是他说一个“真诚恻怛”,将孟子四端中的“恻隐之心”特别凸显出来,提升到了本体的地位。按照程朱理学性、情、体、用的分疏,仁是性、是体,恻隐之心是情、是用,以“真诚恻怛”来说良知本体似有不妥。阳明以这一从概念逻辑来看似乎不当的表述所要显示的大概是“体用不二”的意旨。那么,为什么是“真诚恻怛”,而不是“真诚羞恶”“真诚恭敬”①在程朱理学中“诚敬”是一个重要的表述,阳明不言“诚敬”,而言“真诚恻怛”,表明孟子四端中的“恻隐之心”在他那里更为根本,“恭敬之心”地位要低。“真诚是非”?首先,这当然是因为“仁”在儒家诸德目中具有根本的地位。其次,阳明晚年大张明道的“万物一体”论,而物我一体相通的现象根据正是恻隐之心的“感触神应”。不过,良知本体的“真诚恻怛”也不能完全着实了在“恻隐之心”上理解。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把“恻怛”理解为伤痛、哀痛,那么“真诚恻怛”着重点其实是在“真诚”,否则说事亲从兄都是以哀痛之情为本体,那根本不通。“恻怛”所表示的不是伤痛,而是触物而发的感应之几。阳明讲万物一体,正是从人心的感应之几上讲的,否则“万物一体”就只会是一个夸诞不实的观念。阳明弟子里就有对“万物一体”论表示疑惑不解的,阳明对答如下: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②《传习录》卷下,第336条。这是对“人心与物同体”说的一个具体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未发之蕴意也尽显其中了。这个“与物同体”乃是以“我的灵明”为主脑的同体,而“我的灵明”又无非是个“感应之几”。因此,良知的“真诚恻怛”之本体乃是感应之体。这个真诚恻怛的良知本体作为感应之体与阳明第一个良知概念有什么差别?阳明讲良知本体的真诚恻怛,岂不是回到了第一个良知概念?
当然,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后面的良知概念包含、深化了之前的见地,而不是对之前见识的放弃。良知本体的概念相对第一个良知概念的差别在于,虽然本体的真诚恻怛是情感性的,但这种情感充周于心灵的动静之际,从《中庸》的“未发已发”和《易传》的“寂-感”之分别来看,在寂然不动的未发之时良知本体已是一片真诚恻怛,已具“感应之几”,如此才能“感而遂通”,才能“物来顺应”。这个真诚恻怛的良知当其未发之时并非一种特定的情感——如恻隐、羞恶、恭敬之类;也没有呈现为有分别相的伦理德行——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但既然是万物一体的真诚恻怛,也就不是无情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情怀”。未发之“情怀”与已发之“情感”③这里必须有感受意向,而不只是感受功能,如果只是功能,那就是“性”,而不是“心”了。阳明明确以“未发之中”为“心体”,而不是“性体”。
的关系可以比拟于舍勒那里感受意向③与感受状态的关系[7]310,“情感”是带有被动性的心灵感受,而“情怀”则是主体自发的精神感受。四端、七情因为触境而发,现分别相,是“情感”,良知本体“未发之中”的真诚恻怛是浑沦未分的,是“情怀”。这个浑沦未分的真诚恻怛之情怀是“心之太极”,有善有恶的情意发动则是“意之阴阳”。严格说来,良知本体真诚恻怛的感应之几既不只是主动(阳性)的精神感受,也不只是被动(阴性)的心灵感受,而是静中有动的灵机。而且,在阳明这里虽然他有时突出良知在“未发之中”方能见出全体,但根据他讲“事上磨练”的精神,“发而皆中节”的情感之中和并不低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良知即体即用,即精诚即神应,舍勒那里精神情感与心灵感受之间此高彼低的价值级序在阳明这里并不成立。良知作为万物一体的感应之几既是真诚恻怛的满腔子实心,又包涵虚灵明觉的应物之妙用,既是仁体,也是知体。良知作为虚灵明觉的知体知个什么?在孟子那里,“智”是“是非之心”的发用。
我们前面分析了,“是非之心”是阳明第二个良知概念的本质内涵。那么良知本体如何涵摄“是非之心”?良知作为“是非之心”首先是自我省察的道德意识,即“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善念恶念就是善恶之几,这个“几”属于“已发”。“是非之心”作为知善恶之几的良知要在已发的念头上做涵养省察的工夫。在我们尚未接触事物、善念恶念都还没萌动的未发之时,是不是就谈不上是非善恶?因此也用不上省察之功?此处关键在于,意念未发之时,心是不是纯善无恶。阳明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明确地指出了“未发”的静的状态并不就是《中庸》的“未发之中”。如弟子陆澄所记载的问答: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①《传习录》卷上,第28条。第76条陆澄与阳明师生间关于此问题还有进一步的问答,阳明认为美色名利之念未起的时候还不能说是“未发之中”,他仍然用了疾病的比喻,“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
由此可见,阳明认为“去人欲、存天理”的省察涵养功夫不仅意念发动时需要,在意念未发的静时也需要。因为在未发时好色、好利、好名之类私欲只是潜伏着,并没有绝去,遇到机缘仍旧会滋长,只有将这些私欲扫除荡涤,“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才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才是天下之大本。因此,在未发的宁静存心时也需要省察克治的功夫。意念未发的静时省察克治功夫,就是《论语》讲的“修慝”②孔子在回答樊迟关于“崇德、修慝、辨惑”的问题时将“修慝”解释为“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是指一种道德内省的工夫。“修慝”的话题在《论语》中出现得不如“改过”多,在宋明理学中才成为关键的修养工夫,与“改过”的纠之於已发之后不一样,修慝是治之於未发之前,阳明的“破心中贼”就是“修慝”。,就是《中庸》讲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慎恐惧是君子对道的谨守,对偏离道的警觉,由此警觉,才能涵养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对“感”的警觉防闲,是对孔子讲的“非礼勿视听言动”的深化,也是对驱动非礼之感的私欲“病根”的防闲克治,只有时时刻刻保持戒慎恐惧的防闲功夫,才能荡涤人欲保全天理,真诚恻怛的良知本体才能复得完完全全。这就是“闲邪存其诚”③《周易·乾·文言》。因此,戒慎恐惧在阳明那里是致良知的基本功夫,良知的虚灵明觉中有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警觉。由戒慎恐惧而“闲邪存其诚”,才能涵养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立天下之大本。
阳明还指出了戒慎恐惧的工夫与良知的和乐并不矛盾,反倒是保障良知之乐的凭靠。在“答舒国用”一信中阳明解答了敬畏与洒落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区分了《中庸》保守君子之道的“戒慎恐惧”与《大学》“正心”条目讲的“恐惧”④如果借鉴舍勒的情感现象学分析,可以说《中庸》讲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尚未有形象客体的“感受意向”,而《大学》讲的“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的“恐惧”则是由对未来之危险的表象而引发的“感受状态”。:
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歧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动多拂戾而流于欲速助长。是国用之所谓“敬畏”者,乃《大学》之“恐惧忧患”,非《中庸》“戒慎恐惧”之谓矣。程子常言:“人言无心,只可言无私心,不可言无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心不可无也。有所恐惧,有所忧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3]211
此处《中庸》“戒慎恐惧”与《大学》“有所恐惧”的差别颇近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畏”与“怕”的差①《存在与时间》,第30~40节。。用海德格尔的形式化分析来看,《中庸》所言君子的戒慎恐惧“所惧”的是把良知引向昏昧放逸的不睹不闻之物,所“为之而惧”的则是良知本体;《大学》所言恐惧“所惧”的则是对自己私欲的各种威胁,所“为之而惧”的则是私己的利害,这恰恰会遮蔽良知本体之正。《大学》所言“恐惧忧患”之类情感遮蔽的,正是《中庸》的戒慎恐惧所要开展和保全的——良知本体,即天理[8]。我们可以说,前者是私欲的迷情,而后者则是良知的觉情,是守道入理之情。也可以说戒慎恐惧——如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本身就是道心、道情。这一戒慎恐惧的觉情所展开的,就是从“人心惟危”中抉发出来的“道心惟微”,就是随处随时可能被人欲遮蔽的天理。天理常存而良知“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就是真洒落。这种洒落不同于纵情肆意的感性快乐,而是“无入而不自得”的安稳的快乐。就其生发于良知本体的中和而言,这种安稳的快乐是不息的常乐,既存在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中,也存在于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中[9]。哀中惧中仍有乐,这似乎有违人们的常识。关于这一点,阳明和学生之间有如下对话: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②《传习录》卷下,第292条。
“须是大哭一番方乐”,可见阳明并不主张压抑或消除正常的感情,不同于主张不动情的道家或斯多葛派哲人。
但是,“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又在一个更深的本体层次上肯定了不动心的安稳之乐。真诚恻怛、戒慎恐惧与洒落之乐是良知本体的三个基本情态。严格来说,戒慎恐惧是存养良知本体的工夫,安稳洒落是致得良知本体的境界,真诚恻怛才是良知本体。良知触物而发表现为四端七情发而皆中节的情感,或收敛凝一而为未发之中万物一体的情怀,而保障心之本体未发之时天理纯全,触物而发喜怒哀乐无不中节的机括,乃是良知本身的是非之心。良知动静一如的洒落,出入于是非之心的机括。良知觉情是受天理调御的情感,因此并非情识而肆,良知学万物一体各正性命的情怀必定要落实在日用伦常的事为中,落实为四端七情发而中节的中和,因此并非玄虚而荡。
阳明讲“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其尊崇天理处似与朱子不异。从他标举出四端中的“是非之心”来看,从他讲戒慎恐惧以存天理来看,阳明的致良知教并非纵情肆意的情感主义。良知既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根本,又具备分别本末、厚薄、先后的理智以求得人的身心和谐[10]。所以能调御四端七情,使之发而皆中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阳明这里“天理”作为是非之心的极则并非事物之定理,也不是由经典和圣人之言的权威所最终裁定的,而是良知本身展开的自然条理。所以良知的虚灵明觉之理智在根底上又无需道问学的格物穷理之迂回与辛劳,而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这才是阳明与朱子的最大差异处。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良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天灵智是否真能不假道问学之功而做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这是良知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本文能解答的问题了。
[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182.
[2]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5.
[3](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2009.
[7]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8](美)麦金泰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4.
[9](德)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10]黄万机.王阳明学说的现实意义和价值[J].教育文化论坛,201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