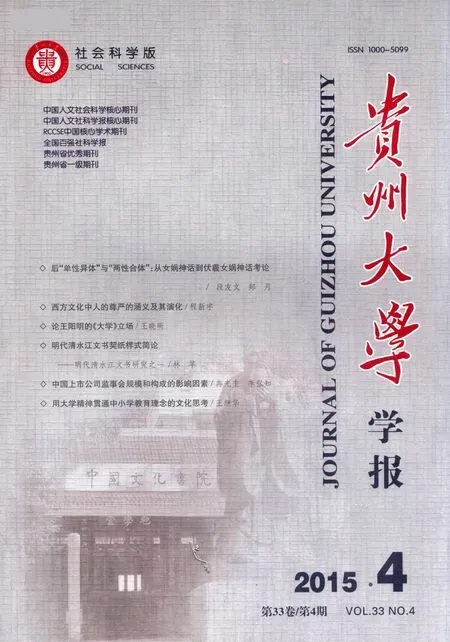从王阳明与贝克莱的对比看晚明心学的宗教转向
彭玉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柏拉图主义者大体上都是瞧不起中国哲学的,例如黑格尔把孔子视为一个智者,认为仅仅是西塞罗的一本书就“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1]120。而除了一些学术大家,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哲学后往往容易跟随黑格尔亦步亦趋的来审视中国哲学。他们往往信服其概念的严谨性和理论的完整性,并以此标准来解读中国哲学。从哲学作为概念辩证法的层面来看,中国哲学确实不能算是一种论证严密的学说。但是从学说内容和价值导向来说,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主题上又存在着共通性。例如王阳明作为儒家“心学”的代表人物,其学说与西方哲学中的观念论无论如何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笔者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将阳明心学与西方哲学相对比,脑子里不时的会闪出柏拉图、贝克莱、康德或克尔凯柯尔等人的身影和学说。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王阳明和贝克莱都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这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从认识论角度看,阳明的理论和贝克莱的论述尽管是有着不同的论证指向,但其论述和结论上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价值取向。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考察王阳明与贝克莱学说的相近之处,并以此出发来分析阳明后学的宗教转向。
一、心外无物与致良知——王阳明与贝克莱哲学对比分析
大体上来说,阳明和贝克莱的理论出发点都是心外无物,尽管他们论证的结论分别是良知和上帝,但都有着以完善的人性为取向的论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克莱的学说的宗旨与致良知也有相似之处。
阳明的理论核心可以概括为“心即理”,他试图以此推论出心为本体,并最终论证出良知乃是宇宙本体。这一推论的起点是心外无物,在《传习录》中,阳明通过“南镇观花”的类比来论证心外无物或心与物同在的道理。友人质疑说“花树深山自开自落与我心何相干”,这一条可以视为从常识的角度对阳明心学的质疑。在常识看来,外物之理或外部世界的存在都是客观自在,与人无关的。但阳明要挑战的就是这一常识,阳明的解释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这一解释被当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罪证而在中学教科书中成为被嘲笑的对象。阳明的解释并不是要消解万物的存在,而是说其与心同在。同样被嘲笑的还有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理论。贝克莱同样向世俗之见——物质实体的存在发起了挑战。他预设了常识所提出的疑问,“公园里的数、壁橱里有书,不必有人来感知她们”,并回答道,你只有走近壁橱才能确定书的存在,而不在壁橱旁你能做的仅是想象,“这种说法只足以表明能在自己心中构成各种观念…我们纵然尽力设想外界事物的存在,而我们所能为力的,也只是思维自己的观念”[3]33。
阳明和贝克莱说心外无物容易被曲解为无物存在,事实上他们只是想论证观念的实在性。在阳明处,“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4],“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有是意,即有是物”[5]。阳明“心即理”的理论是要打破程颐的“以物为理”,扭转对物作自在的自然实存的解释,推动由求物到求心。阳明“物是意之所在”的说法与贝克莱很接近,后者认为“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笔者认为,如果将这句话译为文言文,可以直接译为物乃意之所在,这一译法比“存在即是被感知”更能反映出贝克莱的原意。在贝克莱处,也同样面临着“使物落空”的质疑。贝克莱解释说,他要解构的只是哲学家所说的物质这个概念,而并不是要怀疑凭感官所能感知到的任何事物的存在性。如果“承认我们所食、所饮、所穿的,都是感官的直接对象,而且它们不能在心外存在…要称它们为事物而非观念”[3]40,这也是可以的。如果换成阳明的说法,他可能会说,要是理解了意和物的关系,意和物是可以换用的。
心外无物说突出了心的地位,但心如何存在便成为了问题,如果这一探究走向极致便有可能通向一种怀疑主义。休谟正是从这里出发解构了自我,认为自我只是一个心灵剧场,不存在自我,而只有相继而起的一个个观念。但阳明和贝克莱的哲学都是有价值取向的。他们即使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也会回避,如果没有心或灵魂的存在,阳明的良知和贝克莱的上帝便没有着落。即使是怀疑论者休谟,也只是谨慎的在认识论上质疑了上帝存在的论证,而在实践中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阳明突出心的中心地位所要论证的只是良知的高贵,即“良知自知”或“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对良知的推崇也是一种对良知的信仰,他仍是在寻找一种值得人敬畏之物,并由此达到至善。阳明所寻求的慎独或者说“破心中贼”,与基督教新教的基督徒与上帝的私人对话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贝克莱提心外无物理论的目的是要论证上帝的存在,他所从事的研究目的在于促使人们考察上帝以及人们的职责,明白了这些真理,“则我们会产生戒慎之心,恐惧之念,这正是促使人向善的最大动机,防人为恶的最好武器…认识并实行这些真理,人性才能达到最完满的境地”[3]104。可以说,尽管阳明和贝克莱所推崇的最高物并不相同,但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却异曲同工,都在于实现导人向善,完善人性,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用致良知来概括。在晚明,阳明信徒发起了对阳明的造神运动,一定意义上,阳明成为给他们带来真理或天言的的普罗米修斯乃至耶稣,只不过他没有殉道而已,同时,伴随着阳明心学的平民化趋向,阳明心学越来越需要借助于因果轮回,报应不爽等宗教因素来广为传播,阳明学派也越来越带有了宗教的特征。
二、阳明心学的宗教化转向
王阳明早年曾溺于神仙之学和佛氏之学。以龙场悟道为转折,阳明抛弃了这些“异端”走向“正统”,开始了阳明心学的构建过程。不过,阳明后学的发展轨迹却呈现了与此相反的方向,到了晚明,阳明后学,特别是其中的平民儒者或者说有平民化倾向的儒者在阳明心学中重新加入了很多的宗教因素,使得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宗教转向。这也使得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更为亲近。
关于阳明心学的宗教化趋向的研究主要开始于90年代中期,学界在对颜钧、王畿和林兆恩等人的个案研究中来分析阳明心学的宗教化趋向,以此研究为基础,晚明儒者的宗教化开始得到关注。关于这一趋向,可以描述为以下形式,“儒门功过格运动”,“修身运动”,“善书运动”或“道德劝善运动”。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良知信仰化的趋向,一是以三一教为代表的导人向善运动。应该说,这两种形式的发展与晚明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它早已经潜在于阳明心学之中。
一方面,良知在阳明的学说中的地位类似于贝克莱哲学中上帝的角色。良知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阳明学说中的物都是为良知而存在的,阳明学说中的宇宙是种目的论的存在,都是为了良知而存在。天地万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要通过人的存在而体现出来。阳明并不关心也没有回答作为人的意向之在的物的来源问题,而是将其转化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良知便成为了宇宙万物的本体和归宿。阳明将良知视为天理和最高的原则,但是对于良知却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由于存在着良知个人化的问题以及由此招致的批评。阳明后学中便会产生出将良知信仰化的趋向,这使得良知成为了一种客观化的能为大家所共同理解和尊奉的原则或理念。在良知信仰化之下,产生的诸如修身运动或儒门功过格运动便不难解释。对于他们来说,格物不是要去认识世间万物,而是从赋予万物存在以意义的心处来探究,格物旨在排除蒙蔽良知的人欲;因而阳明心学的禁欲主义化便不难理解。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晚明的“斯多葛主义”运动。
另一方面,阳明所倡导的儒学社会化或平民化运动中便蕴含着其走向宗教化的因素。儒学要扛起劝民向善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借助于释、道资源,明末出现三一教便不足为奇。儒生们在对普遍是文盲的、理解力有限的平民百姓传道时,必须将儒学将的通俗易懂,甚至修改其中的某些内容,加入一些诸如鬼神惩戒、因果报应等因素。而为了迎合人们避祸求福的心理,甚至不惜公开利用一些宗教手段来宣扬并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
如果说阳明心学本身为宗教化的趋向准备了某些理论基础,那么晚明社会环境的变迁则推动了这一趋向的发展。一方面,随着晚明政治转向黑暗,以嘉靖朝和万历朝为代表的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的尖锐,促使一部分士大夫厌倦黑暗的政治而投向良知信仰的怀抱,而更注重个人的修行。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受到冲击,原来稳固的家族伦理体系出现了一些裂缝,在此情况下,人们更需要借助于宗教或信仰的力量来安慰漂泊无着的心灵,知识分子面对日益崇尚奢侈的世风而走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平民百姓则需要借助于三一教等有组织的力量来求得心安。这两种形式的代表分别有王畿和林兆恩。
王畿是阳明心学宗教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将良知作为一种终极实在和信仰的对象。它既是道德实践的先天依据,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良知就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善”,柏拉图用太阳比喻来描述善,就像太阳是万物能被看见以及使万物生成的原因一样;“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他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是在”[6]267。柏拉图的这一理论后来经新柏拉图主义的中介而被基督教用于论证上帝。从这个意义上,王畿的良知离基督教的上帝距离也不远,只要将良知人格化便有通向一种一神教的可能。
而使阳明心学社会化的典型人物是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林本人并不相信鬼神和轮回,并试图从理论上解释某些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是他却认为现实中需要鬼神这一假设,特别是在传道中他仍借助于这些因素,他认为:“若齐民之愚也,余恐其信因果之未甚耳,齐民之信因果也甚,则必不敢肆然而为恶矣。”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给阳明心学加入宗教元素是其平民化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的策略。这类似于伏尔泰的认识,他虽是个无神论者,但却认为社会需要上帝,“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出来”。
三、结论
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哲学在认识论和价值导向层面有很多的相似性。他们论述心外无物的目的都是要推导出心的高贵从而推导出良知或上帝。阳明认为心赋予万物以存在价值和意义,而这一意义就在于致良知,即“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但阳明搁置了万物的本源这一宇宙论的问题。贝克莱却需要回答这一问题,从而只能得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心灵—上帝的结论。一定意义上,如果阳明也需要解释万物起源问题的话,可能也需要走类似于基督教的论证思路。
阳明推导出良知的崇高地位本身就蕴含着通向宗教化的因素。以上层知识分子走向信仰和平民儒者借用释、道思想为形式,阳明心学越来越带上了宗教的某些特征。阳明所推崇的良知以及林兆恩为揉合三教所说的“道”在一定程度上都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来源存在,都有发展为一种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神的可能。但可能由于传统儒学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阳明心学并没能发展为一种宗教。不过,阳明的良知说与基督教的上帝说之间也许并不存在鸿沟。我们看到,20世纪最著名的阳明信徒之一的蒋介石也同样是一名基督徒,阳明的致良知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在他那里得到了和谐共处。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明)王阳明.传习录(下)[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275.
[3](英)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明)王阳明.传习录(上)[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6.
[5](明)王阳明.传习录(中)[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137.
[6](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