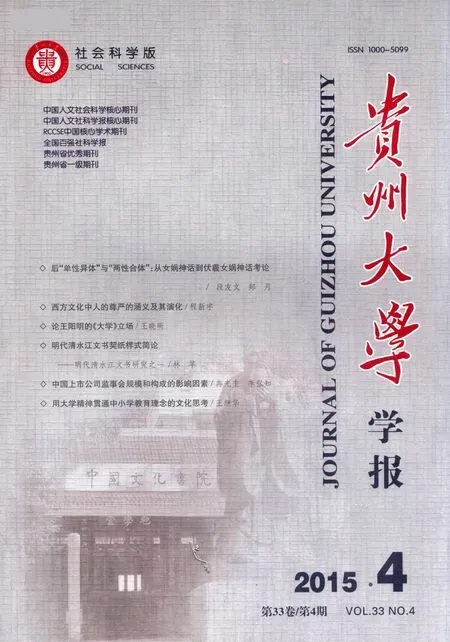“单性异体”与“两性合体”:从女娲神话到伏羲女娲神话考论
段友文,郑 月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国传统神话是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征,闪现着民族灵魂的搏动,这些仍然活跃在民间的历史回音以巨大的向心力将各民族成员凝聚在一起[1]。在中国神话史上,女娲与伏羲经常以对偶神的形式同时出现,并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灵。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涉及,但论述者或是论证自己学术见解时有所旁涉,谈及之处较为简略,或是虽花费笔墨较多,却对其转变痕迹缺乏系统辨析,原因探究方面有单一之嫌,不够全面。女娲神话和伏羲神话在我国神话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关于二者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以及其中蕴藏的内涵仍有挖掘探讨的空间,因此,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资料的整合与爬梳,意在更好地还原女娲神话、伏羲神话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过程,探究两位“始祖”神话传承中的特点与规律,试图综合各家之说,渗入典籍、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相关资料,对女娲伏羲神话的文化蕴涵作更加深入的论述:一方面,是对古史的回想与敬重;另一方面,也期待在此项探索中找到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既可怀古,亦能鉴今。
一
关于女娲神话和伏羲神话的出现,从已有论述和各方面资料可知,女娲神话比伏羲神话产生的时间更早,且两者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历史特点,即最初为女娲独尊神话,之后经过伏羲女娲平等抗衡的阶段,最终进入伏羲为主、女娲从属的神话发展时期。女娲早期以始祖的形象独立出现,早于伏羲并成为我国神话史上第一批女性神祗,有着多方面的材料证据。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人类社会经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社会。在母权制社会里,妇女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和中心,也是氏族部落繁衍的决定者,女性拥有绝对的社会权力。早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远高于男性,与此相应,女性崇拜与女神崇拜也极为盛行,因此,最先出现在人类话语系统中的神祗为女性。并且,从典籍文献的记载可知,女娲较早出现于《山海经》《楚辞》等古籍之中,《楚辞·天问》有:“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2]445从典籍文献产生的时间看,这两部先秦文献应是表现女娲神话原初意义的重要古史,文献中都没有提及伏羲而只说女娲,也可知女娲产生时间之早。
通过女娲神话产生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及文献记录可知,该神话的最初流传形态很大程度上源于原始先民早期的生殖崇拜观念,与女性的“生”之能力有关。上古时期的原始初民由于对生育奥秘的未知,将“生”视为一种伟大而又神奇的力量,出于对女性繁衍能力的膜拜,创造出以“生”为主要功能的始祖神,女娲即为代表。关于女娲的“生”之内涵,典籍文献和相关学者都有提及。《说文解字》以“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3]的记载,将女娲视为创生万物的神女。部分学者对女娲的生殖功能曾有论述,如王增勇曾将“女娲之肠”的“肠”作为“花肠”之说[4],因古人曾以为胎儿乃女性肠子产出,因此,这里的“肠”实则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又如,赵国华曾利用“娲”与“蛙”发音相同、意蕴相似,认为“蛙”为女性生殖器的代表,随后发展为生殖女神[5]。不仅如此,考古学对女娲的生殖意蕴也有实证发现,在山西乡宁吉县人祖山的柿子滩,有一处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内的一方岩画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女娲早期的“生育”意象,经相关学者考证与鉴定,岩画所绘实为女娲,该人物特征明显,两腿分开并且乳房硕大,双腿周围散布着许多小点,为女娲育人之情境,具有浓厚的生育意蕴[6]。该岩画与汉代画像砖相比,既有时间早晚之分,也有内涵意蕴之别,不同于汉画像砖中“人首蛇身”的女娲形貌,它所体现出的女娲崇拜更加原始[7],是父系社会之前远古先民最纯粹的崇仰图景。种种资料都表明,女娲神话的产生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并且与当时的生殖崇拜观念密切相关。
女娲神话的“生”之内涵,实则具有“育生”“化生”“促生”三个层面的意蕴。“育生”主要指女娲的创造能力,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8]601女娲先以黄土捏人,后引绳于泥,人类诞生于女娲亲力亲为的造人活动中,显现了女娲自身强大的创育能力。“化生”则指女娲由己身化彼神、由己身化彼物的功能,“女娲之肠化为神”“化万物者”“一日七十化”等都是对其化育能力的描述,她不仅化生出众多神灵,而且还以身体发肤化作世间万物,成为真正的创世始祖。“促生”之说,主要源于女娲高禖说:为使人类能够长久不息地生存繁衍,女娲创制了婚姻制度——不仅典籍有“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行媒始行明矣。”[8]599“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9]的记载,同时,在晋东南、晋南等地也有女娲与高禖相合附会的真实资料所印证。据考证,晋南河津高禖庙供奉的禖神即女娲的化身,此地高禖庙的祭祀时间为农历三月十八,与女娲诞辰一致。晋东南各地高禖庙数量众多,也与女娲曾在此区域内活动频繁有关。孟繁仁先生考证,分布在黄土高原山西的众多女娲遗迹,基本都是在《尚书·禹贡》所记载的“霍山以南”的“冀州之域”,即今日的山西晋东南、晋南一带[7],该区域的女娲与高禖有形象置换及粘合附会之情形。从典籍文献及地域社会的资料可知,女娲以禖神的职责开创了男婚女嫁的新时代,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繁衍壮大。她不仅以自我之伟力创人,以自身之精华化人,而且还怀抱着人类长久传承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帮助人类延续种族生命,这也更加显示出女娲古老、伟大且崇高的始祖地位。
二
生殖崇拜观念是女娲神话产生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当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后,人们的生殖崇拜也从单纯的女性崇拜转移到男性上,这也成为伏羲神话出现的一大因素。伏羲神话的产生时间晚于女娲神话,且其最初演发之际也为个体独立成形,与女娲并无关联。伏羲之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封禅》篇。该篇列举了早期的古帝王系统:无怀氏、虙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虙羲”作为其中之一出现。在同时期的《商君书》《战国策》等典籍中也有对于伏羲的记载,其中均未提及女娲,可知伏羲神话的产生最初也是自为一体的。战国中期时,《庄子》有载:“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10]这里,庄子将伏羲列在禹、舜之后,可见此时伏羲的地位不及禹、舜二神,伴随着父系社会的发展,其地位方才不断得到擢升。台湾青年学者刘惠萍认为,伏羲最初或为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社会时某个氏族部落中能力出众的首领、英雄,后来在“神话历史化”①神话历史化,主要是将神话看做历史传说,将天神下降为人的始祖,将神话故事当作史诗看待,构成一些虚幻的始祖及其发展谱系。及战国末年“五德终始”②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历史观。“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学说的影响下,伏羲逐渐被神化,地位也有了新的提高[11]19。“从战国至秦汉,时代越往后,关于伏羲的记载越详细,伏羲功业越卓著,在古帝王世系中的地位越高。这说明,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对伏羲的记载经历了一个从神到帝,从凌乱到系统的衍化过程。”[12]
伏羲女娲的结合,乃后人有意粘合,由此出现了伏羲、女娲“双性合体”的现象,这一原始神话思维,主要源于人类渴望从两性互补中达到强健的心理愿望的表现。关于伏羲、女娲二人共同出现的时间,张光直认为,伏羲、女娲交尾图早在商代即已出现:“安阳西北冈殷王大墓出土木雕中有一个交蛇的图案,似乎是东周楚墓交蛇雕像与汉武梁祠伏羲、女娲交尾像的前身。”[13]此种观点虽为猜测,但从商朝简狄吞卵生契的神话传说及相关的历史可知,商代是母系氏族社会走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伏羲、女娲并列的雏形在个别地域有所反映是可能的。至汉时,伏羲、女娲二者的结合已有了确凿的证据,究其此时出现的原因:一方面,该现象源于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一种“阳精”观念的表现——此观念是人类繁衍生存的灵化意识,将男性看作太阳,女性看作月亮,认为日月相合即为男女婚配,人们将伏羲以“日神”相待,曦本为“父曦”,日月则为“曦月”,伏羲女娲交尾图即是通过阳光受孕的“阳精”观念的体现[14]。另一方面,从现实背景来看,一则汉代处于父权社会,伏羲神话作为巩固政权及提高男性主体地位的需要不断得以增衍,在其扩充发展过程中,伏羲女娲神话作为其中重要一支得到完善并成型;二则,汉代正是阴阳五行观念勃发兴盛之际,女性主阴、男性主阳、阴阳结合的思想在汉时得以升华,关于伏羲的许多神话传说都与此观念有关,如伏羲观象制易,始作八卦、伏羲“制俪皮嫁娶之礼”等,并且,人类此时已摆脱早期原始思维的束缚,对于生育的认知更加成熟,许多神话由无性繁衍发展演变为两性繁衍,配偶神相继出现,而伏羲女娲说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整个汉代的社会背景及思想观念为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提供了根基,经过汉代文人政客的加工,伏羲与女娲一同成为华夏民族的远古始祖。
伏羲女娲相互结合,二者结合后的形象几乎都以“人首蛇身”出现。关于伏羲、女娲的形貌特征,《楚辞·天问》王逸注:“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文选·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生,女娲蛇躯。”这些典籍记录为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外观提供了证据。除典籍记载外,伏羲女娲神话也形诸于画像。战国时期楚先王庙堂的壁画已有伏、女人首蛇身的形象,到汉代时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地都出现了“人首蛇身”的墓室画像。如山东境内保存的汉画像石中就有大量的伏羲、女娲像,无论表现何种主题,画像中伏羲、女娲都为人首蛇身状,且多数画像为伏、女交尾图。其中一幅为高禖、伏羲、女娲画像。此画中伏羲、女娲虽无交尾,但二者由高禖左右怀抱各一,将两人连接,因伏羲、女娲都有创制嫁娶的功能,此画像将高禖、伏羲、女娲融为一体,既直观地表现出伏羲、女娲的微妙功绩,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生殖崇拜意蕴。伏羲、女娲同体时以蛇身为缠绕结合点,与我国古老的蛇图腾崇拜密不可分。图腾是早期社会氏族或部落的标志性或象征性符号,由于原始社会中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人们将动植物作为自己的亲属及保护神,将其视作崇拜物,以此寻求一种超自然力来保护自己。而图腾生育信仰是图腾观念的重要内容,伏羲女娲蛇身图,即是人们将蛇视为强大生殖力的外在表现。因此,蛇意象在神话的具体表述中,便代表了生命的起源与死亡,蛇在以无性繁衍的女始祖神话中,充当了男性的生殖力量,成为致使女性受孕的一种神奇的存在。同时,在蛇图腾崇拜中,蛇也被看作阴阳交合的象征和化生万物的伟大神力代表。蛇崇拜的核心是关于阴阳构精的信仰,以生殖和繁衍为主题,伏羲女娲交尾图便是阴阳构精的象征符号[15]。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的大量出现,除了有先民强烈的图腾崇拜和殷切生殖繁育心理外,也有人们对阴阳两极巫术力量的信奉与运用。
三
女娲由人类始祖女神变为伏羲的配偶神,由独体的造人创世神到与伏羲共同成为人类始祖的转变,其深层内涵中隐喻着女性地位的下降,这也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此种现象在中国神话发展史上不乏其例,如楚人先妣由女禄高阳衍发出一对配偶神高阳与高唐,又如夏、商的始祖神姜嫄、简狄均配为帝喾之妻,成为依靠男性神存在的女神,失去了其作为始祖的特质,居于从属地位[11]159。“从女神崇拜转换到男神崇拜的过程并非截然分立的,其间仍应有一段错综纷乱的时期。在这个过渡阶段,为成功地使女性的生殖能力转换到男性神灵身上,在许多民族中会出现‘双性同体’神的现象。如汉唐墓葬艺术中的许多两尾相交或连体形式的伏羲女娲画像等,也都明显地标志着这一过渡期的痕迹。”[11]159“双性合体”的现象实则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过程中一种典型的文化操控现象。伏羲地位的上升并非一蹴而就,必然伴随着社会过渡变迁的大背景,经由不同朝代民众的感知、认同、接受的社会心理活动逐渐得到认可,伏羲神话成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以及进入父系社会初始阶段之中,两种社会制度相互抗衡较量的一种文化表现。随着父权制全面取得胜利,后人还将许多其他神祗英雄的成果归于伏羲,其地位最终得以稳固,成为人们公认的三皇之首。然而,在女神降位、男神上升的历史阶段,统治者出于政治需求,出现了过度抬高宣扬的非理性现象,为了贬低女性地位,提升男性权力,以“产翁”为内容的神话成为统治者的舆论工具,如《山海经》所载:“鲧窃息壤以湮洪水,不迨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2]536鲧本为男,这里却将禹的出生归于鲧腹所生,此神话便是“产翁”制的代表。伏羲的地位正是在父权社会迫切的政治需求中不断上升,位列三皇之一。关于“三皇”的说法虽各异,但除先秦时期将其归为“天皇、地皇、人皇”这种笼统的说法外,更常见的表述有“伏羲、女娲、神农”“伏羲、神农、祝融”“伏羲、神农、共工”“伏羲、神农、黄帝”以及“燧人、伏羲、神农”,伏羲均位列其中,而且几乎都居首位,伏羲三皇之首的地位在西汉末年已成定论。从今天地域社会中的伏羲信仰也可观照到这一现象:甘肃天水保留着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气势最恢宏、保存最完整的明代伏羲庙宇建筑群。与物质遗迹相合。该地关于伏羲的非物质文化也十分盛行,1988年天水恢复伏羲公祭,目前已发展为伏羲文化旅游节,文化的勃发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振兴。除天水之外,山东泗水的羲皇故里、邹城、曲阜等地的伏羲庙,河南淮阳的太昊陵以及全国许多地方留存的伏羲遗迹,都是伏羲神话曾盛行一时的实物见证。
从对女娲、伏羲神话的发展轨迹及其内涵分析可知,女娲、伏羲神话的演变与历史、社会发展规律成正向比例,女娲神话的出现伴随着早期社会女性权力的主导地位,以及原始先民生殖崇拜特有的思维方式,其后成为伏羲的配偶神,女娲神话与伏羲神话的发展由单性异体经由后人粘合附会到双性合体,于是合体形象出现。并且,二神虽都以“始祖”著称,但其内涵应是各有侧重,从对女娲、伏羲二者的功绩看:女娲的伟大功绩主要集中在“创造人类”“炼石补天”“创制婚姻”“制止淫水”“制造笙簧”等方面。从其功绩可看出,人类初生、修天补地、男女结合这些女娲所进行的活动,几乎都与创世时期的灾难与未知紧密相连;而伏羲的功绩主要集中在“始作八卦”“发明渔猎工具”“造书契”“创历法”“人工取火”“制瑟作乐”等方面。卦画乃中国文字的雏形,书契、历法等都是文明时期的象征物,不难看出,伏羲所作的贡献几乎都为文明时代之后的进步之举。因此,女娲是人类初生时期我国最原始的女性神,以“创世始祖”为指向,而伏羲则是将早期初民带入文明时代的男性神,以“人文始祖”为特征,二者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神话面貌,都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四、结语
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探索女娲、伏羲神话的演变轨迹,更要从二神神话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入手,以古之始祖神话鉴今之社会发展。“神话传说不仅是人类幼年时期的产物,而且还记载着幼稚天真的过去,并伴随着人类社会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前进,最终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存在。”伏羲女娲神话作为我国古老的神话脉系之一,早已深入我国传统文化的根部,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女娲创造生命、关注人类生存,其中体现了强烈的母仪万世的生息精神;女娲修天补地、消灾除患体现了其无所畏惧的担当精神;女娲在混沌时期所具有的创生气魄、为天下生计着想的民族观念,正是当下我们在构建现代社会时所需要的重要品质。而伏羲的八卦符号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精神和哲学智慧最主要的源头,这一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解释世界、认识自然以及规范社会人伦的一把钥匙,其中包含的阴阳变异、和合大同的辩证思维,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16]。同时,伏羲在带领人们走向文明社会进程中,创制生产工具、创造文字书契的开拓精神,那种自强不息、刚健向上和永求进步的进取精神也同样为当今社会所汲取。追寻伏羲女娲神话生成、演变的历程,探索其中的必然规律与文化特质,将根祖文化的怀念与沉思重归于心,在重塑中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气质、加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焕发中华儿女奋发图强之风貌等方面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段友文,陶博.重述神话: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再造——〈碧奴〉〈后羿〉〈人间〉解读[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34-138.
[2]袁珂.山海经校注[M].增补修订本.成都:巴蜀书社,1993:445.
[3](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96:32.
[4]王增勇.何为“女娲之肠”[J].民间文化,2001(1):101-102.[5]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71.
[6]靳之林.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与繁衍之神——抓髻娃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7.
[7]孟繁仁.黄土高原的“女娲崇拜”[J].中国文化研究,1999(2):105-109.
[8](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马骕.绎史[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5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81.
[1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7.[11]刘惠萍.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
[12]孙玉红,杨恒海.中华文明起源的初探:伏羲文化[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36.
[1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266-267.
[14]张振犁,陈江风,等.“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M].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15]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37-838.
[16]杜松奇.伏羲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当代人文精神[J].甘肃社会
科学,2013(4):134-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