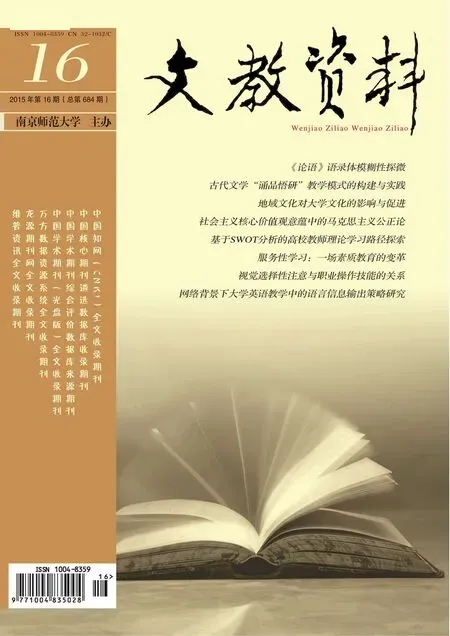中西文化比较再思考——《中西体用之间》读后
万玲玉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2)
晚清的中国社会是一部冲突与整合的巨著,在这本巨著中,文化的推陈出新成为重头戏。学者王法周认为,以往研究中西文化问题,大部分人是从文化结构入手,也就是以物质、制度和精神这样三个层次来划分,难免有些缺陷。而学者丁伟志、陈崧所著的《中西体用之间》以体用范畴切入中西文化问题,突破以往的研究定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也对我所承担的课程《中西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体用的内涵界定
“体用”之成为偶词,始于儒家经传的注疏。《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以礼之体主于敬者,源出于《孝经》:“礼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礼之本也。”范氏之说礼,直言之,即以敬为体,以和为用。是以体用之连璧,起源甚早,且为申明经义而设。同时体用二字各表一完整的实义,对立互证,而成为偶词[1]。由此看出古人对于体用的最初界定是比较抽象和模糊的。
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方克立认为基本涵义有二:一是指本体(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北久矢认为清末的中体西用论是以“体”为存在的精神指导原则,以“用”为外在的应事方术和具体措施。张岱年认为,“清末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谓体用都属于‘学’的范围”,“所谓体指文化的最高指导原则,所谓用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
耿云志认为,“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是非常清晰、非常确定的。一则体用这一对范畴是中国思想史上特有的,本来就有相当的模糊性。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用关系如何,历来就争论不休。再则,表达中体西用的观念,在当时曾有不同的表述方法”,“所以,给中体西用做出精准的界说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办不到的。正因如此,这个口号,这个观念框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不同人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2]。因此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体用的内涵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固定的模式,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在。
二、关于中西体用的产生、演变与评价
1.中体西用的产生
关于谁最先提出这种思想,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陈旭麓先生认为是冯桂芬首先提出的,沈寿康最早一字不差地表述出来,孙家鼐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了诠释。郝锦花基本持上述观点,并认为张之洞使这一理论最终完型。但戚其章认为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是薛福成。《中西体用之间》认为师夷长技说是近代认识西方与学习西方文化思潮兴起的最初萌动、有力催发。
对于这种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释。姜慧颖认为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郭长清认为是由洋务派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及自身具有的矛盾性决定的。殷俊玲、吴忠民等认为深厚的文化背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对中西文化认识上的差异,趋利避害的防卫心理,夷夏观念的日趋淡薄等。《中西体用之间》作者基本属于此列,他认为中体西用说是在提倡西学和反对西学的论战中形成的,是争论的产物,冯桂芬和李鸿章等人在洋务早期发表的议论,已经勾画出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格局。
2.演变问题
其一是过程论,王春楣和黄士芳提出他经过从“中体西用”到“中西和用”的过程,陈江琴认为中体西用思想大体经历从西艺到西政到西教三个演变阶段。其二是会补论,戚其章认为在戊戌维新时期,曾经提出两种中体西用论,一种是维新派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西体用的会通论,一种是洋务派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西体用的补救论。其三是两积论。杨金銮提出戊戌变法时期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支。一支是康梁为代表重新诠释中体西用并开始接受民权说,另一支是张之洞为代表,捍卫纲常,大力强化中体,蓄意限制西用。其四是变种论,曾维纶指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王新命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贺麟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新儒家及50年代以后的港台新儒家,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模式,是“中体西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3.评价问题
其一,基本否定“中体西用”说。如黄逸峰等认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亦即利用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也。这里的‘中学’和‘西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封建主义体系,一个是资本主义体系,硬把两者糅合在一起,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3]。
其二,把“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时代思潮进行动态地分析,认为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社会作用基本是从积极转为消极。如皮明庥认为,起初颇具变革精神,后来成为对付维新派和革命派而变成保守甚至反动的东西。陈旭麓认为,中体西用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而且那个时代除此之外也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到甲午战争才“是对‘中体西用’宗旨最残酷的批评”[4]。黎仁凯、侯玉臣等人认为,“中体西用”论“本质上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的混合物,是自相矛盾、具有两重性的思想理论。《中西体用之间》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而到了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的模式已经无法框住新的文化主张、思想内容,中体西用论的基调变了——从提倡采用西学的革新论调变成反对以西方为模式变法改制的保守基调。
其三,基本从正面角度肯定“中体西用”论。何晓明认为,“我们今天可以批评‘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是却无法否认它适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代表民族文化自觉变革图强的求索精神,积极谋求古今中西文化的建设性交融,在实际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突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作用”[5]。王先明提出“中体西用结构,突破了传统文化观体用同源或体用不二模式,在兼取中西的双向选择中形成了体用二元模式”,构成了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6]。
三、关于中西文化比较方法的思考
耿云志说:“中西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差异比较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重要的是从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中认识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而发生深刻的文化自觉。”[7]学者李毅指出,以纲常名教为内容构成的道统和法统,是中体西用论不敢触动、无法逾越的禁区,这构成了以体用模式界定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在矛盾[8]。
《中西体用之间》运用大反差的比较研究方法,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步履维艰和中国文化创新的出路展示出来。作者一方面通过展现近代知识分子在传统和价值之间的一种紧张的心理冲突,学人在提倡西学时难以摆脱矛盾心境的困扰说明中国文化革新和进步的艰巨。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创新的发展趋势充满信心,作者主张超然摆脱一切成见的束缚,兼收并取,以革新精神创立符合时代水平又包容固有文化精华的新中国的新文化。正如雷颐所说:“无论对传统采取什么态度,都只有实践操作意义上的行与否、利与弊,而无道德价值意义上的对与错、是与非。”[9]因此不再纠结于体用二元模式的思考,不再胶着于名词概念的争辩,不再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不再争论是非对错、孰优孰劣,而是放弃泛道德主义的评判标准,虚心平等宽容地对待中外文化。这才是中西文化比较方法的正确方向。
[1]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3]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2).
[4]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5).
[5]何晓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纲领.光明日报,2002-12-17.
[6]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
[7]耿云志.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广东社会科学,2008(3).
[8]李毅.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再认识.道德与文明,2002(1).
[9]雷颐.超越“中西体用”—〈中西体用之间〉读后.开放时代,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