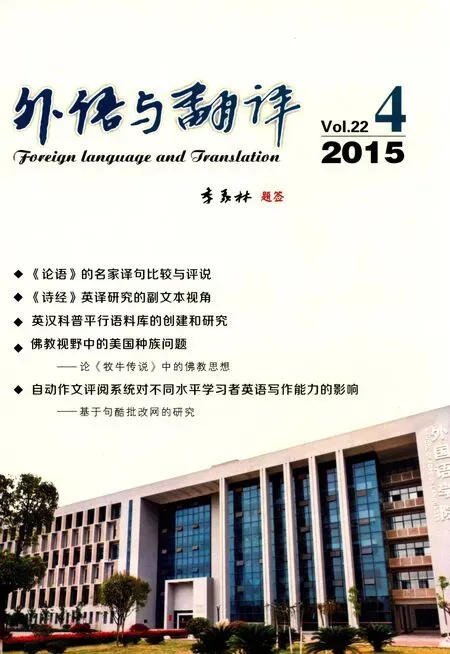《语言与军事:联盟、占领与和平建设》评介*
陈 昕
《语言与军事:联盟、占领与和平建设》评介*
陈 昕
“在全球许多军事行动中,对语言及文化符号系统的关注已到达一个中心位置”(Tymoczko 2007:26)。语言是一种社会活动,不仅是人们日常活动中传情达意、沟通思想的符号手段,而且在人类活动的最极端形式中,尤其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冲突、战争中,发挥中心作用。Chilton(1998:3)指出,宣战是一种“言语行为”,而一旦开战,也只能通过言语行为开战并维持相关的军事行动。可以说,从战前的军事准备、战时的军事部署,到战后的谈判签约等,从情报搜集、宣传攻势,到难民安置、维和重建等,语言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语言与军事的关系长期以来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语言与军事》论文集是“战争中的语言”项目2011国际研讨会的成果,从军事联盟、空间占领和和平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语言在军事行动中的中心作用。
1.“战争中的语言”项目简介
“战争中的语言:冲突中语言接触的政策与实践”项目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资助,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和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合作执行。项目负责人是雷丁大学的Hilary Footitt教授和南安普顿大学的Michael Kelly教授。该项目旨在开辟一直受到忽视的、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的新学术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于三方面问题:一是各国政府、军队和国际组织在冲突、战争中的官方外语政策;二是个人在冲突、战争中与外语相关的经历;三是个人经历与官方政策之间的关系。
项目于2008年5月1日启动,2011年10月31日结束。其间,项目组成员共参加了42次学术会议、发表相关主题演讲,并于2009年5月和2010年5月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举办了两期工作坊,主题分别为“口译员、笔译员和语言家在冲突中的角色”和“在战争中遇见‘他者’:两个案例研究”。2011年4月7日至9日,“战争中的语言:冲突中的语言接触政策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召开,来自英国、意大利、塞浦路斯、德国、加拿大、西班牙、法国、日本、爱尔兰、芬兰、比利时、斯洛文尼亚、美国等13个国家的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2012年4月至2013年1月,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相继出版了《战争中的语言:冲突中语言接触的政策与实践》(Footitt & Kelly 2012a)、《语言与军事:联盟、占领与和平建设》(Footitt & Kelly 2012b)、《翻译和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的维和行动、冲突与语言》(Kelly & Baker 2012)和《战争之语:外语与英国在欧洲的战时努力,1940-1947》(Footitt & Tobia 2013)等4本论文集或专著,组成帕尔格雷夫“战争中的语言”研究丛书。
2.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是该丛书的第二本,收录了提交给2011年国际研讨会的15篇论文,Footitt和Kelly担任主编并分别撰写了前言与结语。“战争中的语言”项目最初选取二战中西欧的解放∕占领(1944-47)以及波黑的维和行动(1995-1998)作为分析案例,分别由雷丁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负责,但随着项目的推进,研究范围逐步扩大,辐射面越来越广,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上述两个案例。本书收录的论文探讨了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内发生的区域性或全球性冲突与战争:从18世纪到当今世界,从一战、二战,到朝鲜战争、塞浦路斯冲突、北爱尔兰冲突、波黑战争,到近期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地域波及爱尔兰、英国、法国、芬兰、斯洛文尼亚、朝鲜半岛、波黑和塞浦路斯。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处处留下了武装冲突的印记,而参与这些战争的军队很少只说一种语言,跨地区、跨国界的军事行动总是令他们必须直面说另一种语言的军队和平民。本书讨论的这些冲突和战争中,语言在军事行动的准备阶段、“热战”的对抗阶段和“热战”后的占领或维和阶段,对军事行动效果、联盟间∕军民交流与沟通、斡旋与谈判、和平建设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收录的论文主要围绕三个主题:语言在军事联盟中的作用,语言在空间占领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如何参与冲突后的一系列事务。每个主题都包含至少一位来自从业者组织(如英国国防部、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英国文化协会等)的作者,提供专业机构对该问题的关切和看法。
Footitt(2012b:5)指出,战争研究似乎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误区,即想当然地认为军事行动几乎总是以占支配地位一方的语言进行,或至少以观察评论方的语言进行。本书的第一部分即以四个典型案例挑战以上错误假设,不但揭示出军队中的多语现象,而且对军队中的文化杂合问题提出思考。在实践中,语言军事联盟以多种形式形态存在。Tozzi的论文《一支军队,多种语言:18世纪法军的外籍士兵和语言多样性》探讨了18世纪法国旧制度时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法国军队兵员构成和语言多样性。Kleinman的《“在喧哗与迷惑中”:法国-爱尔兰联合对抗英国战争中的平民与军事语言家(1792-1804)》讨论了这一时期外国人受雇于法国军队的真实经历,尤其是法国-爱尔兰联合对抗英国期间为法军服务的爱尔兰人。Heimburger的论文《共同战斗:一战协约国联合作战的军事协同语言问题》阐述了英国和法国一战时联合作战的语言沟通问题,尤其是军事译员与联络官的战时角色和经历。Lewis的论文《战争中的语言:英国国防部视角》认为应长期坚持军队中的文化、语言教育,而不是应一时之需。军事语言家可以与军方直接雇佣或通过第三方雇佣的平民译员相辅相成,以满足军事行动中的语言需求。
本书的第二部分关注语言如何在空间占领的权力关系中发挥作用。Svoljsak的论文《意大利军队在斯洛文尼亚被占领土的语言政策,1915-1917》探讨了语言如何成为占领方的政治工具。如果说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界限在斯洛文尼亚案例中是清晰明确的,那么Kujamaki的论文《为第三帝国调解:北芬兰二战时的军事翻译文化》则论述了另一种边界已模糊渗透的关系,该论文是芬兰科学院资助项目“军事翻译文化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大批会讲德语的芬兰人为德军作译员,使得“他者”与“我者”的区分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Catherine Baker的论文《当波斯尼亚仍是联邦国家时:英国军队及其塞族共和国译员,1995-2007》继续探讨了外军存在导致的忠诚与身份模糊问题。Fernández Sánchez的论文《一位双语军官对朝鲜的回忆:近看朝鲜战争中未经训练的译员》则将军事占领的内涵拓展到谈判桌上。停战谈判是战争的继续,而充满敌意的双方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时,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一场隐形的语言战争。Tobia在《战争受害者:二战难民与英国的首次接触》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安全部门对赴英难民的身份确认(以剔除蓄意渗透的间谍)和情报搜集工作。Chriost在《爱尔兰语区:爱尔兰语与北爱冲突》论述了被英国当局关押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如何在监狱中学习爱尔兰语并将其作为张扬民族身份、追求民族独立的抵抗手段。Fitchett的论文《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项目:帮助冲突地区的口译者》探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为军方服务的当地译员困境,指出他们的杂合身份以及不受本族语者和军方信任造成了这些译员的“隐形”和易受伤害性。
本书的第三部分关注战后或冲突后的相关语言问题。Charalambous的论文《在冲突频发的塞浦路斯学习“他者”的语言:障碍与可能性探索》探讨了在塞浦路斯的希腊族社区教授土耳其语的可能性和实际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Hare与Fletcher的论文《用英语解决冲突:英国文化协会的维和英语项目》介绍了英国文化协会的维和英语项目,该项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推行。Askew的《塞-克语与南斯拉夫一起消失了吗?波黑的语言与身份问题新探》与Taylor的《在国家博物馆中展示“异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与“战争中的语言”项目》两篇论文从语言记忆角度探讨了战争与和平的延续问题。
3.本书特点
作为一本探析语言在战争、冲突中角色的论文集,本书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研究具有跨学科性。本书论文作者来自13个国家,既有在真实战争中调兵遣将的军事指挥官,又有旨在保护冲突地区译员的职业译员,既有将语言作为维和手段的组织机构,又有向普通大众讲述战争故事的博物馆管理者。论文作者职业、身份的多元化和研究背景的多样性为“战争中的语言”这一核心主题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新思路与新视角。本书的15篇论文涵盖了战争研究、国际关系、历史学、文化研究、人类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学科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还原、重建语言在战争与冲突中举足轻重、却常常被忽视的角色。
其次是资料详实权威。本书作者特别注重从现有的国家、外交、军事档案等各种史料中寻找有关语言的蛛丝马迹,对大量史料进行了深度挖掘,以全新、多元的视角搜集整理出与语言相关的内容。此外,本书作者还从个人回忆录、日记、信件、报纸、存档证词等资料中寻找语言与战争的相关内容。这些资料并没有详细、清晰地记录语言接触和语言政策,因为这并不是这些资料撰写和保存的初衷,但是鉴于语言在冲突、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问题就像捉迷藏一样处处散落、隐匿于字里行间、只言片语之中,需要研究者凭借敏锐直觉、丰富经验和专业精神拨开历史的重重面纱,将一块块碎片拼成一副完整的图画,将冲突与战争中的语言实践全貌展现在读者面前。研究当代的冲突和战争时,鉴于一些档案和相关文件还处于保密状态,本书作者采访了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军事人员、语言中介或其他抵抗军事当局的人士。
4.评价与反思
本书的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是揭示了翻译在冲突、战争中的作用。冯佳、王克非、刘霞(2014)对近二十年国际翻译学研究动态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发现,“翻译与冲突”已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本书15篇论文中有9篇论文专门论述或涉及到翻译问题。Footitt(2012b:3)认为本书的部分论文明显得益于翻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例如,Heimburger总结了军事冲突需要语言介入的四种情况:一是军队本身的语言多样性;二是情报搜集和对敌宣传的需要;三是在“他处”作战需与当地居民交流;四是与他国军队联盟作战。Catherine Baker和Fernández Sánchez探讨了翻译在冲突后的维和行动与谈判活动中的作用。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加剧,翻译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911事件后,西方情报机构对译者的需求量猛增。但是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显示,联邦调查局仍然缺乏快速、精确的翻译能力,有超过12万小时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含有潜在情报价值的录音没有被翻译(Bielsa 2009:17)。自2006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推出专著《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以来,“翻译与冲突”这一研究主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国际译学界陆续出版了相关期刊、论文集与专著(参见王祥兵、穆雷2013b)。
其次是突出了译者在武装冲突中的身份困境。一方面,武装冲突中的本族语译者因通晓他者的语言、具备与“敌人”沟通的能力,而被本族人视为“通敌者”、“间谍”,遭到排斥,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Kujamaki发现,二战时期,德国战俘营利用有双语能力的苏联战俘协助日常管理。但是,充当译员的战俘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被其他苏军战俘视为“叛徒”,甚至在战后被杀。Catherine Baker也注意到为英军提供语言服务的塞族译员同样面对忠诚与认同的困境。不少塞族人对他们持敌对态度,甚至公开侮辱、威胁他们,因此这些译员不得不时刻“保持低调”,过一种“双重生活”。这种情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表现的更加明显。Fitchett指出,许多当地译员的死亡或受伤是由于本族人对他们发起的暴力袭击,他们被视为“通敌”的异类、叛徒。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译员的雇主并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保护。语言服务使用方一般通过第三方机构雇佣本地译员,这种间接雇佣模式造成雇佣方与使用方责任模糊不清,译员的权益得不到合法、有力保障。作为职业译员的专门组织,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冲突地区的口译员”项目应运而生,以敦促译员雇佣方和使用方承担相关责任、履行相关义务,帮助口译员获得应有的权利和保护。
第三是强调了语言在民族身份建构和认同中的重要作用。Cronin(2006:1)指出,“如果以前意识形态是影响政治交流的主要方式,那么身份问题现已取而代之。”而民族身份的建构和认同与语言密不可分。Humboldt(洪堡特 1999:52)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可以说,语言是各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在本书中,Tozzi指出法国大革命使语言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对于法国军队里的外籍士兵而言,不会说法语被视为不忠行为。Charalambous分析了塞浦路斯被两种语言、两个民族分隔的局面,希腊语和土耳其语构成了两个民族“我者”和“他者”的明确界限,要想通过语言和谐达到民族和谐绝非易事。而在波黑,Askew指出,随着塞-克语在官方语境的消失,波斯尼亚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试图人为地刻意强化本族语言与其他两个民族语言的不同,将语言差异作为民族特色,使语言成为民族身份标志和个体自我认定民族的方式。
本书的确如“战争中的语言”项目的研究目的所言,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对语言在冲突、战争中的角色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注意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在本书中的缺失。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与外族语言接触的冲突、战争,如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但是,国内学界尚未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对这些战争、冲突给予应有关注,王祥兵、穆雷(2013a)梳理中国翻译史研究文献后,发现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研究严重不足。国际译学界更是缺少中国学者用英语写作发表的有关中国战争翻译史的论文,目前,仅有王宏志(Wong 2007)的一篇学术论文探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译者与郭婷(Guo 2009)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论述国民党、共产党和侵华日军三个政治、军事场域中译者培训、雇佣与翻译实践活动的博士论文。
作为“战争中的语言”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语言与军事》一书对语言在军事联盟、空间占领和冲突后事务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重新审视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与冲突、战争的互动关系,为战争研究、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学者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尤其是给中国研究者提供了启示与借鉴,语言政策、翻译研究、外语教育已经上升至国家利益、国防安全、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学界研究成果可以为领导层的决策过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Bielsa,E.2009.Introduction[A].Bielsa,E.& C.W.Hughes.Ed.Globalization,PoliticalViolenceandTranslation[C].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1-21.
Chilton,P.1998.The role of language in human conflict: Prolegomena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as a factor in conflict causation and resolution[A].E.S.Wright.LanguageandConflict:ANeglectedRelationship[C].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2-17.
Cronin,M.2006.TranslationandIdentity[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ootitt,H.& M.Kelly,Eds.2012a.LanguagesatWar:PoliciesandPracticesofLanguageContactsinConflict[C].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ootitt,H.& M.Kelly,Eds.2012b.LanguagesandtheMilitary:Alliances,OccupationandPeaceBuilding[C].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ootitt,H.& S.Tobia.2013.WarTalk:ForeignLanguagesandtheBritishWarEffortinEurope,1940-47[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Guo,T.2009.Surviving in the violent conflict: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 [D].Birmingham: Aston University.
Kelly,M.& C.Baker.2012.InterpretingthePeace:PeaceOperations,ConflictandLanguageinBosnia-Herzegovina[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Tymoczko,M.2007.EnlargingTranslation,EmpoweringTranslators[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
Wong,L.W.2007.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during the Opium War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839-1842)[A].M.Salama-Carr,Ed.TranslatingandInterpretingConflict[C].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41-57.
冯佳、王克非、刘霞,2014,近二十年国际翻译学研究动态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1):11-20。
洪堡特,1999,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祥兵、穆雷,2013a,中国军事翻译史论纲[J],《外语研究》(1):84-90。
王祥兵、穆雷,2013b,学术著作翻译的理想模式——以赵文静中译本《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为例[J],《中国翻译》(4):79-82。
(陈 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471003 河南洛阳036信箱30号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翻译活动与译者研究”、军队院校外语教学协作联席会第二批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军事职业教育背景下的我军官兵外语能力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科研基金暨军队“2110工程”学术研究项目“军事翻译能力建设若干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4CYY003、WY201406A、2014XYY012。
2015-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