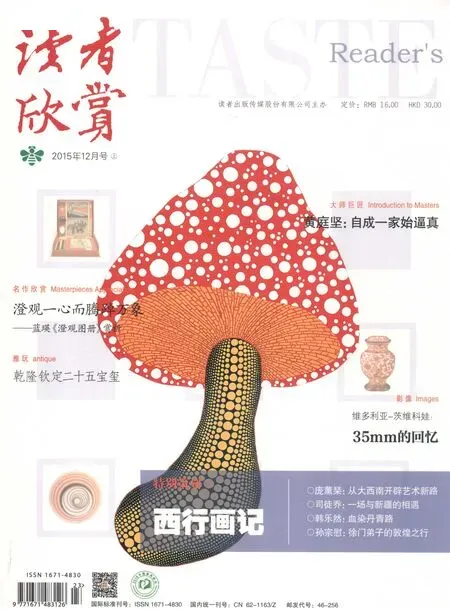父亲章乃器的收藏往事
文/章立凡
父亲章乃器的收藏往事
文/章立凡
乱世收文物
在老一辈的知名人士中,父亲以爱好文物考古著称。1948年底,父亲应中共中央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有系统地收藏文物并形成系列,就是1949年初北上以后开始的。当时,国共内战仍在进行,国民党达官显要纷纷南逃,加上土地改革的原因,一些地主乡绅被打倒,很多文物流落到社会上,价格之低,达到了现今无法想象的程度。
1949年春,民主人士们从东北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饭店。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和沈志远、千家驹三人给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写了封信,希望做一些经济方面的工作。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商量,南喜出望外,立即聘请他们出任顾问,并在东单大羊宜宾胡同找了一所房子,安排三位在北京安了家。后来,他们又都被陈云聘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参与接收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以及统一全国财经的工作。
父亲在东北时就开始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后,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当时北京的文物“泛滥街头”,其中真伪混杂,良莠不齐。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鉴赏家,既搜集到很多好东西,也上过不少当,交过不少学费。
有了收藏的历史机遇,还要有收藏的缘分,父亲的优势是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有良缘。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前清内务府郎中庆宽的后裔)先生等,也与父亲时有切磋。
由于经常打交道,一些古玩商也跟父亲交了朋友,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着他,会直接联系送上门。当时北京经常搜集文物的,除了父亲还有康生、陈伯达、邓拓等,就这么有数的几个人,他们的收藏旨趣也各有不同。
父亲收藏文物的资金来源,一是手头的薪水,二是从上川公司抽回的资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创立了上川公司,成长比较迅速。光复后他到台湾,买下了台湾糖业公司。后来内战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准备将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转让了,转赴香港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在地产上经营得比较成功。
父亲这个人公私分得很清楚,1949年出任新政府公职以后,他认为自己不宜再经营企业,便向董事会提出辞职,该公司因无人主持,随即歇业。他将自己在公司的投资逐步抽回,用以收集文物。
三屋子文物敞开捐献
父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出于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为他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他有比较充裕的收藏时间和空间。后来新政协召开、共和国成立,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出任粮食部长后,他就越来越忙碌了。到1954年向国家捐献文物前,他已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
手头有一通父亲1953年12月致郑振铎先生的信函底稿,全文如下:
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持续发酵时,正值博鳌亚洲论坛举办期间。在博鳌亚洲论坛“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分论坛上,吴浈不得不面对疫苗监管问题。
送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郑振铎局长
西谛我兄: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否则,一起搬过去,将来又搬到你们那里去,十分费力;放在原处过久又不放心,占了别人房子问题也多。
如何先请考虑,不久将面谒作决。
章乃器1953.12.9
从信的内容看,此前他已表达过捐献的意愿,这时因要从大羊宜宾胡同搬家到灯草胡同,便促请郑振铎尽快安排接收这批文物。
1954年初春,郑先生从故宫派来了6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1100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文物部门曾提出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但他没有同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捐献时连数目都未清点。
收藏要交学费
对于搜集来的文物,父亲通常会请一些朋友共同鉴赏;但在整理分类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他曾定制大批锦盒,将那些来时无包装的文物妥善保护。文物入藏时,他经常会在锦盒上写一些文字或心得,记述藏品的来源、品类、特点,有时还会记下孙老(孙瀛洲)或他本人对这些器物的评语。
我幼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橱柜逐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有次父亲特地给我看一把做工精细的青铜短剑,此剑一点都没有生锈,闪动着柔和的光泽,通体被一种规整的网格纹所装饰。他指出这把剑的特殊之处,是网格纹饰可能采用了化学工艺。1954年,他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时,曾建议他们收下这把剑,但故宫的专家看不明白,此物竟未入选。20世纪60年代报载有越王宝剑出土,形制与此剑相同。我在回忆录《都门谪居录》中曾提到这柄剑,最近翻阅父亲留下的文字,发现自己将这把剑与另一柄“吴王自用剑”记混了。
父亲收藏过一件在文字考古上有重大意义的著名青铜器“二祀邲其卣”(现藏故宫博物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我所见,其他各种商鼎周彝,大大小小有几十口,还有七八面铜鼓,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器。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谈到,父亲的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几乎涉及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按门类成系列搜集,确实是父亲收藏的一大特点,特别是在铜、瓷、玉器门类的收藏上,历代有代表性的器物都尽量搜集。
例如,他曾精心搜集了几十件宣德和仿宣德铜炉、铜器(王凤臣、张鸣岐、胡文明三大制炉名家的作品都在其中),他说:
这批铜炉、铜器,是按照前人著作,依不同的款式、铭文、铜色,有计划地收集的。其中比较珍贵的,有鼎式金片炉、吴邦佐铭文炉、琴书侣铭文炉、王旭铭文炉等;雍正、乾隆、咸丰、行有恒堂仿宣炉也是比较少见的。宣德的双耳瓶、觯、铜盘等,也远比铜炉难得。
瓷器是父亲收藏中的大项,除广泛搜集宋代五大名窑外,元明青花及清三代官窑也是他的搜集重点。而对于晋唐辽金以上的古代瓷器,他的收藏也很可观。我所见年代最远的瓷器,是一只汉代的黄釉埙。其他如晋青瓷鸡首壶、唐秘色釉圆盖、宋“宣和元年”枕、明龙纹宣德大盘、清粉彩开光三秋瓶等,品相都相当完整。还有一只巨大的乾隆粉彩灯笼尊,“文革”结束后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时,发现他们的“中国通史陈列”中有一只同样的,正好配成了一对。以上仅系记忆中的个别精品,无法一一枚举了。
父亲的玉器收藏也很丰富,我印象较深的有良渚文化“鸟纹大玉琮”(“文革”抄家后流入首都博物馆),还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蛾(“文革”后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大量的商周秦汉古玉和明清白玉珍玩。
父亲在书画方面收藏较少,比较知名的是《梅花三咏》手卷。他说:“字画作假太多,收藏字画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他自认没有张伯驹、张傚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
在杂项收藏中,他曾搜集到稀有的全黾甲甲骨刻辞、漆器名家姜千里制螺钿漆圆盒、卢肤之制螺钿插屏等;竹雕名家张希璜、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濮仲谦、周芷岩、潘西风等的作品,他也多有搜集。
我曾经问父亲:“你收藏了那么多文物,上过当吗?”父亲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赝品中若有很美的东西,尽管年份不够,我也是要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
本来就随时准备捐献给国家
1957年,他以往搜集、保护和捐献文物的行为,反倒成了罪状,在报纸上屡屡出现颠倒黑白批判他的文章和漫画,并引发了一桩持续8年的诉讼。
1957年以后,父亲赋闲在家,除了大量读书,收藏又重新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内容。他的个人生活很简单,除抽烟外没什么嗜好,虽然工资降了,但每月仍有结余,他把这些钱也用在搜集文物上了。
父亲搜集和捐献文物的资金,来自他从上川公司撤出的个人投资。因该公司已经歇业,1956年初,征得上川公司股东们的同意,他把该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港九地产公司的房产出售,清算后分给股东,结束了全部企业,当时股东们都很满意。不料“反右”运动中却有人利用此事作为政治打击的手段,导演了一场上川公司股东控告章乃器“欺骗股东”、“私自结束上川公司”、“偷税漏税”、“逃避公私合营”的闹剧。
这场官司导致约3000件文物被法院冻结,但因起诉理由和证据都不充分,一直未能判决。1963年,父亲因批评“大跃进”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后,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64年判决章乃器败诉,为此,父亲甚至遭到羁押。
当时,法院所主持的文物清点估价相当混乱,很多成组的文物被拆散了,在谈到自己搜集的柴窑藏品(10件左右)被拆散查封时,他抗争道:“这是参考各家有关柴窑的记载,经过多年的搜集,还征询了文物业中的人才能办到的。但完全被忽视、被破坏了!”此外,一组包括鼎、豆、盉、觚、尊的越窑祭器,也遭到同样命运,他认为“是对辛勤努力集中起来的成组珍贵文物的鲁莽灭裂的打击”。
父亲所要坚持的,其实不是文物的最终归属,而是保护收藏系列的完整性。他事后对我这样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我一辈子没在乎过。30年代我为救国破家,40年代为建设新中国舍弃香港的产业,你是知道的。这点收藏,本来就随时准备捐献给国家。但他们采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对待我,我是要据理力争的。我维护的是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根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入库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剩下1134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将大部分发还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私人未必能做得到科学保管。父亲生前很重视文物的系列保护,在博物馆里,文物的文化价值得以传播,捐献者的文化精神得以昭示,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