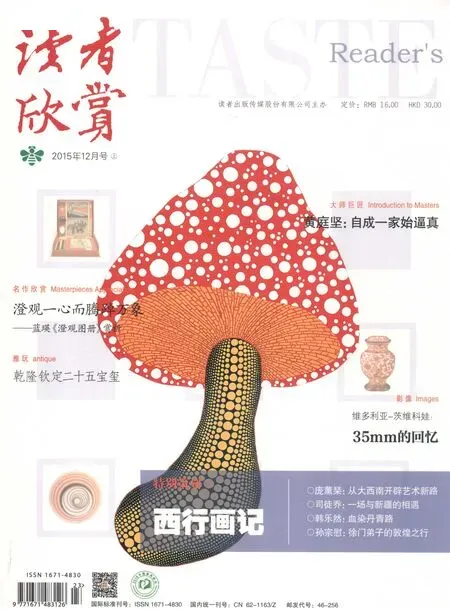庞薰琹:从大西南开辟艺术新路
文岩泽
庞薰琹:从大西南开辟艺术新路
文岩泽
著名作家傅雷在《薰的梦》中写道:“薰的梦是艺术的梦,精神的梦。一般的梦是受环境支配的,故梦梦然不知其所以梦。艺术的梦是支配环境的,故是创造的,有意识的,是清醒的梦。”
庞薰琹是个不安的灵魂,他为艺术的梦想探索一生、追随一生。1932年,他最早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且旗帜鲜明,身体力行。虽然决澜社只存在了短短三年,却为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播下了种子。对于决澜社的解散,自是时代选择的结果,而对于庞薰琹而言,却促成了他艺术之路的重要转折。
到贵州去
1936年至1946年间,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为了采集边疆民族资料用于研究和陈列,组织了三项关于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有一项是考察贵州的民间艺术,该考察组的负责人就是庞薰琹。这个考察组从1939年11月开始到1940年2月结束,调查了贵阳、龙里、安顺、贵定等地苗族村寨80多处,采集400余件标本,并绘制了民族服饰纹样和民族风情图。在国家艰难之际,庞薰琹和他的组员们为保存珍贵的民俗史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庞薰琹能够进组担任负责人,和他的一段经历密不可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一大批在北平的学校、研究机构南迁,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建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人才汇聚西南边陲,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庞薰琹也来到了昆明。英雄汇聚,各展所长,庞薰琹在陈梦家、沈从文等人的鼓励之下,开始了古代装饰纹样的研究,并绘制了四册《中国图案集》,在西南联大教授中传阅。由此图集作媒介,庞薰琹不久便结识了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梁氏兄弟的推荐之下,庞薰琹进入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1939年9月正式受聘,担任专员职务,专门负责研究中国历代器物上的图案,对彩陶、汉砖、铜器纹样进行收集和研究。
就在庞薰琹沉浸于古老器物上“死”的纹样研究之时,一项研究“活”纹样的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针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计划。正好此时中央博物馆迁到昆明,学者们距离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如此之近,有了地理上的便利;其次就是西南苗民的衣纹样式向来被世人称道,而中央博物院准备陈列的一个大类便是西陲边疆民族资料,现在去采集正当其时。于是1939年11月,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了贵州民间艺术采集团,由庞薰琹负责,同时借调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芮逸夫做助理。芮逸夫曾在1933年前往湘西考察,收集了大量当地苗族的语言、歌谣和故事,在调查研究方面经验丰富,而且还有一定的摄影技术,可谓是庞薰琹的理想工作伙伴。
方案敲定之后,1939年11月20日,中央博物院向教育部呈报了考察计划,随后又致函贵州省政府请求协助。12月9日,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复同意,庞薰琹和他率领的民间艺术采集团即日出发,由此开始了一段“艺术之旅”。
艺术之旅不艺术
中国的西南边疆当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近乎未解之谜,所以对边疆地区进行考察就被看做一件极为冒险的事—一是本身路途险要,二是当时流传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民间传说,如“见血封喉”、“放蛊”等。另外,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常常会到当地抓壮丁,当地人一听是官府来人都会大门紧闭。这些困难都为考察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1940年到1946年间,庞薰琹创作的主要作品有:白描《母与子》《归来》《吹笙》《跳花》《卖炭》《收地瓜》《卖柴》《收桔》《汲水》《持镰》《缝补》《脱脚休息》等;水彩《捕鱼》《赶集》《垂钓》《跳花》《畅饮》《割稻》《洗衣》《笙舞》《捉鱼》《车水》《小憩》《丧事》《射牌》《情话》《收割》《黄果树瀑布》《双人笙舞》《桔红时节》等。仅从这些作品的标题,便不难看出他对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的关注。对民间装饰艺术的浓厚兴趣,使得庞薰琹获得了一把开启民族艺术的金钥匙。
1939年12月9日,庞薰琹从昆明出发,不料第二天车就坏在了贵州的普安。大概由于战时车况差,司机师傅都修不好,大家只能等着从安南来的车接。但是考察的任务重,庞薰琹和芮逸夫就地先考察起来,但司机师傅说车随时会来,两人又不敢跑太远,就这样左等右等,整整耗了三天车才来。后又经过两天,直到12月15日他们一行才抵达贵阳。不巧的是,15日正好是星期五,彼时政府双休,所以直到18日庞薰琹才和政府官员们对接上。
然而,当庞薰琹带着中央博物院的公函兴冲冲地到民政厅接洽时却碰了个钉子—厅长孙希文不仅劝他们返回昆明,而且说收集资料这件事根本办不到—他们公职人员受宋美龄委托搞一套苗族服装都没办到,何况是一群书生。厅长劝他们不要空想,也拒绝给他们开介绍信,而且放话说,考察团一定要去的话,省里不会派人保护。面对“钉子”,庞薰琹和芮逸夫没有气馁,经过多方周旋,他们得到了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杨秀涛、大夏大学教授吴泽霖等热心人士的帮助,获得了非正式的介绍信,终于踏上了考察之路。
当时,从昆明到贵阳要坐三天两夜的公共汽车,到了贵阳又要走一二十里山路才能到达村寨。寨子的情况如预想一致,庞薰琹与芮逸夫一到寨口,寨里的人就躲到山中去了,连续几天的情况都是如此。但还是有三两个孩子大概是好奇,在寨口东张西望。庞薰琹想了一个办法,准备从小孩子那里寻找进入村寨的突破口。他们去糖果铺买了一些糖,在村寨口吃起了糖果,这个办法吸引来了一些小朋友。经过了几次试探和询问之后,村寨人知道了他们此行没有恶意,只是来收买衣服花边,也就消除了对二人的戒备之心。于是,二人开始对村寨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芮逸夫主要负责拍摄照片作为记录,他的这批摄影照片也成为中国民族志摄影的先例。庞薰琹主要负责采集标本,这使他开始着迷于少数民族服饰上那些美丽的纹样,这些纹样对于他来说是在摩登的上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异宝藏。
庞薰琹一边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生产生活习俗,一边收集物质文化遗产—收购民间艺术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跋山涉水,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苗区开展工作,先后调查了80多个苗、布依等族村寨,并运用民间文物搜集法、实地摄影法、以图画和文字记录民间工艺等方法,甚至亲身参与体验,较系统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宗教、巫术、神话、传说、图腾、歌谣、音乐、舞蹈、语言等,获得了宝贵的调查资料。
1940年3月,在考察完四县的60多个村寨,搜集标本400余件后,庞薰琹和芮逸夫回到昆明。回到昆明伊始,庞薰琹便开始陆续绘制贵州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装饰纹样,直至同年来到四川。通过这次考察,庞薰琹尤其强调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找“民族形式”,他说:“敲铜面盆的四川艺人、拉陶坯的云南农民、街头捏粉人的老艺人、贵州的苗族姊妹们,他们从没有停过锤子,停过转盘,停过手,停过针,他们从没有为创造民族形式的问题而苦恼过。可是在他们手里创造出来的东西,却充分地表现了民族形式的特征,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熟悉传统,熟悉生活。自己的生活就是群众的生活,自己的喜爱就是群众的喜爱,所以得来全不费工夫。而那些关起门来,远离大众生活的人,他们不仅为创作‘民族形式’而苦恼,而且也为他们创作出来的‘民族形式’不能被大众所理解、所接受而苦恼。”
“一幅装饰画有没有表现出装饰性,构图起主要作用。在装饰画构图中,装饰结构起决定作用。装饰构图中的结构,等于人体的骨架。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陶器上的装饰,就表现出非常注意装饰结构。”
开辟艺术新路
1940年,当庞薰琹拖着病体来到成都时,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受到此时期提出的“科学救国”主张的影响,再加上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委托在法留学时的旧识、曾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的李有行创建了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开设艺术、建筑、音乐三科,培养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实用艺术人才。受李有行之邀,庞薰琹辞去了中央博物院的工作,赴该校任实用美术系主任。为躲日军轰炸,庞薰琹带领学生和一家四口到北川郫县,在吉祥寺尼姑庵中上课。他常对学生说,中国有很多很多宝贝,要吸收自己文化的营养。但光是这么讲,学生觉得隔得很远。于是当年暑假,他在吉祥寺的大殿里开始构思日常用品的设计,绘制《工艺美术集》。
与此同时,庞薰琹展开了绘制系列作品《贵州山民图》的工作,这一系列创作经历了几年时间才最终完成。《贵州山民图》是由20幅工笔重彩画构成的组画,这组画具体描绘了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生活和劳动场景。在这组画中,庞薰琹非常精妙地在工笔重彩画中穿插了西方绘画的形式,画面的表现手法一改往日“决澜社”外在的笔触激扬,而是在运用装饰画处理方法的同时融入了更多的个人感情,使得画面的激情由内而外迸发。
庞薰琹1941年创作的《笙舞》,描绘的是苗家人在节日中载歌载舞场景的一幅作品。这幅画的构图被处理得平面化了,绚丽的颜色、略微夸张的人物表情使得画面具有装饰画般的精致效果。画面中人物盛装打扮,吹笙跳舞,亲密却又不显得局促,正面、侧面、背面的人物都刻画得很到位。庞薰琹对人物的脸部进行了大胆的夸张表现,人物和整个构图协调一致,具有装饰韵味,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工笔画。而画面人物衣服上的纹样刻画得非常精致,就连十字绣的纹样都能分辨得出—这些纹样平添了画面的细节,又不同于西方具有装饰韵味的油画。画面中远山及树木都呈现出一种淡雅、柔和的色彩,与近处鲜艳的民族服饰形成鲜明对比。
庞薰琹的这组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绘画作品,生动自然,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使观者仿佛身临其间。这是庞薰琹与当地苗民长期共处后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艺术来源于生活,庞薰琹拂去了巴黎的奢华,拂去了上海的浮躁,静静地品味这诗一样的民族艺术,创作出诗一样的作品。
1942年,第三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重庆举行。庞薰琹的朋友事先未经他本人的同意,从他所画的《贵州山民图》组图中选出两幅送去展览。然而,这两幅画送到中国画组去审查,被评委说这不是国画;送到西画组去审查,被说这不是西画;最后送到图案组去审查,又被说这不是图案。最后勉强地与油画挂在了一起。庞薰琹气愤地说:“一个中国人,用的中国的毛笔,画在中国的绢上,画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凭什么不承认它是中国画?我自己画的油画,我自己始终不承认它是‘西画’。”一些慧眼识珠之人,譬如驻英大使顾维钧就非常赏识庞薰琹的作品,特地购入10幅《贵州山民图》作为礼品赠予英国皇家学会。
正如后人评价的那样:“抗战时期,他的艺术有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工艺美术上,成为一个设计家;二是画风融会中西,回归东方传统,用中国的材料创造了一种完全东方式的绘画形式……(他)在井然有序的设计意识中注入了抒情诗意,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独一无二”的源头,除了可以回溯到1940年深入贵州的艺术之旅外,还可以回溯到1925年正在法国留学的庞薰琹参观的巴黎博览会。这届博览会的主题是“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新装饰艺术运动在这届博览会上大放异彩,艺术装饰风格也由此被推上国际潮流舞台。这次参观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这让庞薰琹对1941年创作的对工艺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个兴趣陪伴且改变了他的一生,也让他以另一种形式的探索重塑了自己的艺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