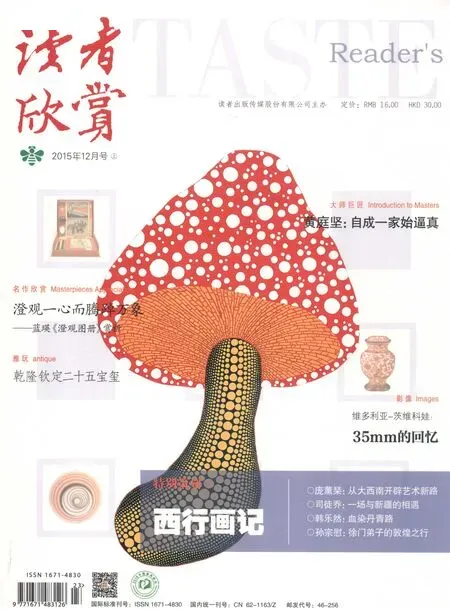孙宗慰:徐门弟子的敦煌之行
文静一
孙宗慰:徐门弟子的敦煌之行
文静一
1942年阴历元宵节前,我赶到青海塔尔寺,主要为看塔尔寺庙会,因塔尔寺庙会以元宵节最盛,蒙藏各族信徒来此朝拜,近10万人。不信佛教的及汉族、回族也有很多人来此,主要为做买卖或观光。我则对各民族的生活服饰等感兴趣,故画了些速写。后来我就学习用中国画法来画蒙藏人生活。速写稿比较详细,也有凭记忆画成油画“藏族舞蹈”之类的。
—孙宗慰
机缘巧合赴敦煌
孙宗慰1912年生于江苏常熟,本来的小康家境因一些原因而中落,他在亲友资助下勉强才读到高中毕业,随后在南京市的一所小学谋了一份教职。从小喜欢绘画的孙宗慰一直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1934年,孙宗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并成为徐悲鸿的学生。此时的徐悲鸿刚从法国回来,正着手在国内美术教育界建构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写实语言体系。这也就是人们一直认为的,孙宗慰在艺术上一直追随徐悲鸿体系,被视为徐门弟子的代表者的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中央大学于1938年迁到重庆。孙宗慰也随校入川,在战事流离中完成学业,并留校担任了助教。3年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把他和绘画大家张大千轰动文化界且毁誉参半的敦煌之行联系在了一起。
1941年春,张大千碰到了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吕斯百,张大千告诉吕斯百自己计划去敦煌探访千佛洞,并想找一个有绘画写生能力的助手同行。吕斯百想到了系里的年轻助教孙宗慰,便向张大千推荐。张大千曾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短期授课,对学生时期的孙宗慰印象颇好,听吕斯百提起,也觉得他是极好的人选。在吕斯百的动议和安排下,孙宗慰停薪留职一年,追随张大千开始对敦煌壁画进行临摹与研究工作。孙宗慰的西行,“虽晚于赵望云,但早于大家熟悉的吴作人、董希文”。他也因此机缘,成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开拓者之一。
因为孙宗慰带着大量的画具,所以他没有同张大千一起乘飞机到兰州,而是先取道成渝公路,而后从成都换乘火车到西安。而从西安往兰州的一段路只能靠步行、搭车和骑驴并举,这样在战火中走走停停,他用了两个月时间才到达兰州。西行途中虽然经历曲折,孙宗慰却也收之桑榆,一路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了更日常的接触和观察。一向对普通人生活状态感兴趣的孙宗慰,被蒙古族、藏族的边地风情深深吸引,画出多幅国画和油画,日后都成为他的代表作。
西北之行的临摹与研究
到敦煌后,孙宗慰的工作比较繁重,包括摹绘壁画、写生彩塑,对洞窟外的景致也做了大量写生,以便对照着为洞窟编号。学西画的孙宗慰第一次系统地接触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对敦煌壁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留下一批精彩的写生临摹稿。这段经历,在他此后大半生的绘画中都留下了痕迹,一些重要作品尤其国画,多是根据这批临摹稿来进行重新创作。他在敦煌期间的工作细节,除了当年的日记有录,还可从他多年后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我与张大千的关系》里看到许多。如在1968年11 月22日的一份材料中,他这样记述从敦煌返回青海塔尔寺的:
1942年阴历元宵节前赶到青海塔尔寺,主要为看塔尔寺庙会,因塔尔寺庙会以元宵节最盛,蒙藏各族信徒来此朝拜,近10万人……我则对各民族生活服饰等感兴趣,故画了些速写。后来我就学习用中国画法来画蒙藏人生活。速写稿比较详细,也有凭着记忆画成油画“藏族舞蹈”之类的。在塔尔寺住了约三个月,要为张大千整理画稿,收集寺内建筑上的装饰纹样。工作之余则向喇嘛画工学习从制作画布、颜料到画后装帧等方法及壁画方法(以期与敦煌佛画传统相近)。
1942年5月底,孙宗慰和张大千在兰州作别,张大千独自返回敦煌继续临摹和研究,孙宗慰则按照原先和学校的约定回去复职。因碰上山洪暴发,车票难求,孙宗慰在兰州被困三月余才回到重庆。不过,就是在这段被迫滞留兰州期间,他潜心整理了自己的敦煌临摹勾线稿及青海塔尔寺写生稿,并完成了油画“藏族舞蹈”等作品的初稿。
孙宗慰的西部之行为他带来了艺术创作方面的山洪似的爆发,而这些作品从艺术价值上来看也是相当值得称赞的。孙宗慰的这些西行题材作品,也使徐悲鸿大为惊叹。
1942年秋,孙宗慰从兰州回到重庆后不久,徐悲鸿受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在重庆磐溪筹建中国美术学院,即决意聘孙宗慰为副研究员,当时同被聘为副研究员的还有画家吴作人、张安治、李瑞年、陈晓南和冯法祀等。1945年,孙宗慰在重庆举办“西北写生画展和个人作品展”,徐悲鸿亲自题写前言,文中赞弟子:“以其宁郁严谨之笔,写彼伏游自得、载歌载舞之风俗,与其冠履襟佩、奇装服饰,带来画面上异方情调,其油画如藏女合舞,塔尔寺之集会,皆称佳构。”
西北之行成就人生精彩
1945年,孙宗慰在重庆举办西行个展,时任《大公报》主编的王凡生为其作品《驼牧》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所为者何?求其自我”,这大概算得上是对孙宗慰西行绘画的点睛了。
经西行历练,在同时代人里,孙宗慰已经显现出他的独特画风,而西部之行可以说是孙宗慰绘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顶峰,诞生了一套完整的蒙藏风情图卷。油画《冬不拉》和《驼队》,分别完成于西行途中的1941年、回到重庆后的1943年,其绘画方法的不拘,表现出他在现实主义写实语言架构中的突破。“这其中有一批专画背部形体的作品,每幅仅一人,背对画面,而形体的微妙和服饰造型的丰富,都使作品摆脱了简单的写生状态而引发了想象空间。如在“蒙藏生活图”系列中的《集市》《背影》《对舞》等作品里,或‘西域少数民族服装系列’,都采用了这种类似于中国画中‘留白’的处理方式。”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评价。
西北之行是孙宗慰人生的精彩一页,不仅在他的画里留下了奔放的线条与炽烈的色彩,也让他回到美院许多年以后,还保留着使用藏族碗筷、冬天戴狐皮藏帽的习惯。
“西画的办法是告诉一个艺术家如何画所见,古法则是告诉艺术家如何画所知。在创作中可以发现,孙宗慰的视角极其复杂,他不是定点视角,他的视角似乎很漂移,这种漂移来自于中国古法里的‘游观’,他不是画他所见,而是画他所理解的世界。”
包括徐悲鸿在内的许多老一辈油画家,都有一段“从洋到土”的艺术历程。曹星原说:“徐悲鸿后期的土油画确实很不好,可他实际上是在找一些东西。”或者说那是一种本地化尝试,“他们都在追求一种信念,油画要画出‘我’的精神。我究竟怎么去表现我?今天再回头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哪个油画系的老师敢站出来说,我敢跟孙先生比书法、比线条、比造型能力?”
1946年,徐悲鸿接任北平艺专校长,孙宗慰又获聘为副教授,也进入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打粥》等国画代表作即出在这一时期。1955年,以原北平艺专为基础成立的中央美院再次进行院系调整,孙宗慰被调到中央戏剧学院,参与建立舞台美术基础教学体系。这以后,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加上个人的身体病痛,孙宗慰渐渐疏离于美术界的主流语境而被淡忘,除了教学中示范的戏装人物写生,甚至少有人知道他的西行经历以及他曾画过那么多独具个性的油画、国画作品。对于孙宗慰而言,西行亦成为他此生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
——徐悲鸿经典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