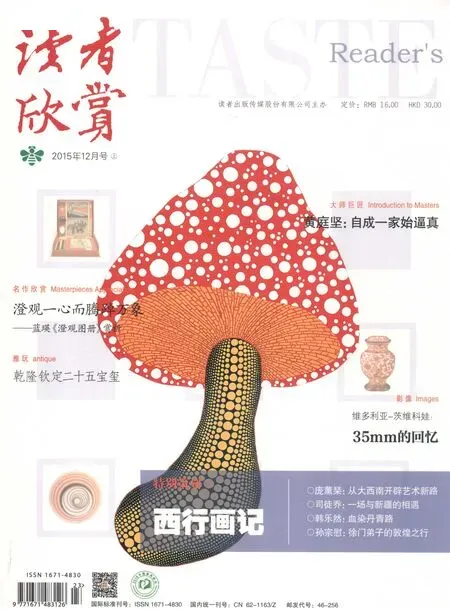韩乐然:血染丹青路
文静一
韩乐然:血染丹青路
文静一
韩乐然是中国美术界第一位朝鲜族共产党员,虽然在世仅仅49年,但他留下了丰厚的艺术遗产和考古成果,特别是对西北地区的艺术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韩乐然在西部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在兰州、乌鲁木齐等地举办了十多次画展。这些作品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使石窟艺术这一民族文化瑰宝被社会所认识,另一方面,他艺术地展现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初入西北
1937年,韩乐然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到祖国,此后的几年,他在烽火岁月里东奔西走,从武汉到延安,又从重庆到西安。此间,他被委派至刘澜波负责的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为“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撰稿、绘制封面,曾画巨幅油画《全民抗战》悬挂于武汉黄鹤楼。他与甘肃山丹培黎学校校长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交流新闻写作,到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又被委任为李济源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在晋东南国共两军驻地从事抗日统一战线联络工作,以记者的身份在黄河以北调查民情、战况,并在八路军前线总部向彭德怀报告了国民党的反共信息。他代国民党93军参谋长转告投奔八路军意愿,准备由宝鸡回重庆时被国民党宪兵队逮捕,被押解西安后在狱中坚持斗争,苦度三年铁窗生涯,直至1943年初被假释营救出狱。
韩乐然出狱后,并没有恢复行动上的自由,且在艺术上也被干预不准画劳苦大众,所以他只好带着学生黄胄由华山写生画起,恢复艺术生活。1944年,韩乐然携全家由重庆迁居兰州,1945年与潘洁兹一起赴青海西宁写生,临摹塔尔寺壁画并观摩唐卡。后北上沿河西走廊到敦煌,南下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寺等地,用油画、水彩描绘边疆少数民族生活,此间创作了油画《拉卜楞寺前歌舞》《青海塔尔寺庙会》《赛马》等。他还临摹了很多敦煌石窟壁画,并且在兰州举办了个人画展。
1946年1月,《艺术生活》旬刊社在兰州省立图书馆举办了韩乐然、鲁少飞、潘洁兹、常书鸿、赵望云画展。同年3月他从兰州出发,历经西宁、永登、武威、永昌等地旅行写生。这是韩乐然的第一次新疆之行,他在乌鲁木齐作画、办展,并只身从乌鲁木齐出发做了5个月的南疆之行,先后考察了吐鲁番、库车地区的十多处历史遗迹,画了近百幅水彩、油画,并临摹了一批石窟壁画。
1947年,韩乐然乘坐路易·艾黎支援的卡车,带着两名培黎学校的学生和另外两名助手再赴新疆。
他的助手赵宝琦回忆:“我们乘坐一辆维吾尔族老乡的两轮马车,黄昏时从库车出发,走了一整夜,太阳初升的时候到达了克孜尔镇。我们休息了片刻,雇了四头毛驴驼行李和工具箱,步行翻山,中午到达了目的地—克孜尔千佛洞。”韩乐然一行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临摹工作,临摹油画共计30余幅,整理编号壁画窟75个,并做了详细的摄影记录和图案记录。
叶浅予称韩乐然为“第一个研究克孜尔石窟艺术的中国画家”。
二进新疆
韩乐然二进新疆,北至乌鲁木齐,东至哈密,南至喀什,几乎走遍了新疆。新疆丰富的历史文物及十几个民族特异的风情陶醉了他,新疆成就了他西域考古的业绩,也充实了他的画囊。
韩乐然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他以水彩和油画为媒介,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民族风情图画。诸如织毯、纺线、剪毛、晒谷、磨面、打馕、浇地、打水、养马、钉马掌、磨刀、售布、卖酸奶等劳动情景,是他关注底层劳动群众的真诚表现;还有奏乐、歌舞、午餐场景,画面自然是维吾尔族人民欢迎他的仪式,也是他与兄弟民族的人民同欢共乐的写照;他也画出了马车夫休息的情况,尤其是赶牛车者在傍晚时刻做礼拜的纪实,更见他对宗教习俗的尊重。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记录了考古发掘的亲身经历,记录了守护克孜尔石窟寺的房东子女宰牲款待的盛情,为房东夫妇做合影的写生。韩乐然曾将此事专门讲给家人听,家人在此画上写道:“这个老人曾经做过法国人勒库克的助手,当他明白帝国主义的罪行后,非常热情地帮助画家工作。”
《铁匠》《汲水》《水磨》《钉马掌》细致地描绘了当地民族看似普通的劳动场景,流露出韩乐然对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真实情感。那些盘腿坐在地上撕羊毛的老人、弹唱的乐师、正在烤馕的妇女、打铁的两位铁匠、熏皮子的维吾尔族男子,以及在硕大的院子里一群妇女一边晒着粮食一边聊天的其乐融融的场面,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浓郁的人间烟火味,更多的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的生活态度。作品《维吾尔族用餐》描述的是在一间很简陋的平房里一家人坐在地毯上享受着午餐的场景,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他们用手进餐的习惯,而家中的主妇正要走进来为他们添加食物,用具摆设简单又富有民族特色,显得干净利落。韩乐然没有刻意刻画人物形象,而是用几笔简单的线条准确地勾出了人物动态及结构。韩乐然的很多风俗类作品中都巧妙地描绘了一些古老的用具,如纺车、织毯架、水磨等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生产工具。
韩乐然的作品呈现出的景象就像是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绿洲城镇,好像是你的熟人、与你擦肩的小贩,或是正在忙碌的铁匠,抑或是在街市上看到的出售奶酪鲜果的妇女,这是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现实,表现了画家的所见、所想与所为。这种态度与他的身份和立场不无关系,他的革命情怀是与其艺术创作融为一体的。
不止于新疆
除了关于新疆的作品,韩乐然的其他作品大部分产生于甘肃甘南和青海,是藏族和哈萨克族人民生活的写照。这些作品大约有20幅,多半为水彩画,其余为油画。其中多描写那美丽的高原上哈萨克族和藏族妇女捣米、晚炊、捻毛、浣衣、背草等劳动的情景,又有赛马、舞蹈等文娱活动场面。还有几幅水彩画画的是甘南拉卜楞街市人员来往的情景,可以看出他对建筑的兴趣和描绘建筑形体的熟练技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油画《渡河》,母亲怀抱幼子骑马渡河,父亲坐骑之侧又有小马随行,充满人情味和人性关怀;水彩画《女木工》,通过3位藏族妇女躬身劳作的近影与远处闲散的几位僧人的对照,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深深的同情之心;《负水》令人很自然地想起吴作人1946年制作的《藏女负水》,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这类似抒情小诗的画面上用色彩演奏了一曲劳动妇女的颂歌;最震撼人心的是油画《塔尔寺前朝拜》,巍峨的青海塔尔寺落雪后更加壮观,寺前的信徒正在雪地上匍匐爬行跪拜,雪地上横向的粗笔既是他们前行的履痕,也在视觉上强化着这种前行的动感。
韩乐然是画家,也是考古学家,尤其作为中国研究克孜尔石窟寺艺术第一人,不仅在洞窟上留下了宝贵的题记,留下了韩式的编号,还留下了数十件摹件,这些壁画临摹包括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以克孜尔居多,油画、水彩兼有。因此,又可以说他是用油画、水彩西画艺术形式临摹中国壁画之首创者。一个艺术家如此看重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如此精心临摹古代壁画,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和传承,而将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进行了猛烈的碰撞。韩乐然不仅仅看到了克孜尔壁画“其色彩之新,构图之精,画风之异,都接近于印度犍陀罗风”,又可以看出“近代西洋画中的新派作风,可能由19世纪起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得古代作品,影印刊布于欧洲社会以后的影响和变化是可能的”。
自1944年至1947年,韩乐然用近3年的时间走遍了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创作了几百幅民族气息浓厚、反映西北各族人民生活和祖国大好河山的油画、水彩画。对于韩乐然的画作,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常书鸿评价说:“看着他的画,每一幅都充满了光和色的明快,毫无板滞生涩之感,他那纯熟洗练的水彩画技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可惜的是,1947年,韩乐然从乌鲁木齐返回兰州,所乘飞机于中途失事罹难,走完了短暂却丰富的一生。韩乐然曾有过新疆考古5年的计划,还曾设想建立西北博物馆以珍藏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作品。虽然他的计划没有来得及付诸实现,他更没有看到其为之奋斗、梦想中的新中国的诞生。不过,他的近200幅作品如今已被珍藏在中国美术馆,而他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献身的精神将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