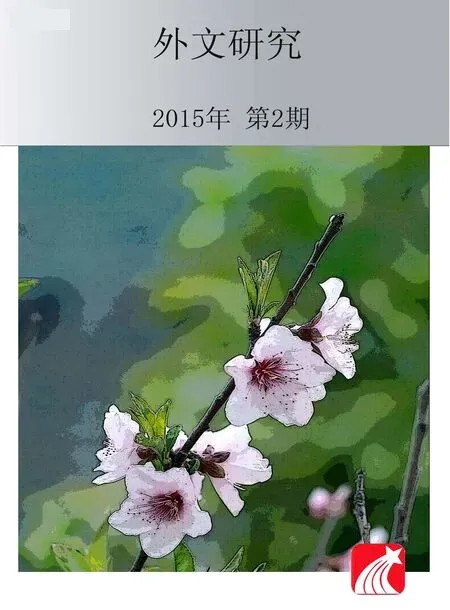试析动后NP为数量宾语的把字句
北京大学 王婷婷
试析动后NP为数量宾语的把字句
北京大学 王婷婷
本文从数量宾语把字句入手,观察把后NP与动后NP之间的关系,指出至少存在两种语义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和等同识别关系,语法意义为“影响源+把+受影响者+动作+支配对象”。另外还存在一组把字句与这两类具有不同的句法结构,前两种关系中“把NP”与谓语部分关系比较紧密,这种“把NP VP”与其后数量短语的关系比较疏离,这类把字句中“把NP VP”为话题,其后的数量短语为说明。
把字句;数量宾语;整体-部分关系;等同识别关系
0. 引言
本文讨论保留宾语把字句中的一种“数量宾语把字句”。关于保留宾语把字句,学者们已有过一定程度的讨论。本文通过对一些现有相关研究的重新审视,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同时从把后NP与动后NP的语义关系入手,分别对两种类型的数量宾语把字句进行讨论,另外从句法差异中理出另一类比较特殊的把字句,此类把字句从形式上看与数量宾语把字句相同,但是二者的深层构造具有很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数量宾语把字句的语法意义进行描写,以期能够对其他类型把字句的研究有提示作用。
1. 把后NP与动后NP(数量宾语/数量名宾语)的关系
关于把后NP与动后NP之间关系的描写,前贤们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吕叔湘 1948b, 1980; 丁声树等 1961; 朱德熙 1985; 薛凤生 1987; 李裕德 1991; Sybesma 1992, 1999; 叶向阳 2004),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把后名词和动后名词之间有关系,考虑到把后名词有时也是受动词支配,因此认为动后名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支持这一论述的学者占多数;另一种则认为把后动词短语是整体,无论动词后接什么成分,都是一种状态变化的结果等,因此动后名词无论是保留宾语还是其他类型的宾语,其特殊地位都没有存在的意义。(薛凤生 1987)但大多学者在把后NP与动后NP具有隶属领有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一点上已达成共识,也有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现象。如叶向阳(2004)指出,把后NP与动后NP还存在“加附关系(把大门贴了封条)”与“‘花费光’的关系(把钱买了车)”,李裕德(1991)也讨论了具有“成为义”的把字句。
前人关注的大多是动后NP为普通名词短语的情况,鲜有对动后NP为数量结构的情况进行单独研究。吕叔湘(1980)曾指出把字句中存在偏称宾语的情况,如“把衣服脱了一件”中“一件”就是偏称宾语,指“全体里边的一部分”(吕叔湘 1948a, 1948b);李裕德(1991)从数量角度考察了把后NP与动后NP的关系,指出“他把橘子吃了三个”表示从整体中减少或增加的含义,“数学家把突变现象分为七种”表示划分或分解的因果关系,“徐鹏飞随手把新送来的公文拿起一件”是前两类的叠加,即既表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又表示因果关系。
前人对数量宾语把字句的观察很有启发但是并不全面。首先把字句中动后的数量宾语有的可以补出名词,有的却不可以,比如“把衣服脱了一件(*马褂)”与“把橘子剥了一半(皮)”。另外把后NP与动后数量宾语之间并非全部都是整体-部分关系,这一点前人也有所讨论,如表示“成为义”的把字句,或表示“花费光”的把字句等,但都过于零散,我们发现这些类别背后是具有共性的。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数量宾语把字句并非表达整体-部分关系,也不是前人所讨论到的“成为义”/“花费光”的关系,并且与其他数量宾语把字句具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因此本文尝试对把后NP与动后NP(数量宾语)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以期能够对把后NP以及动后NP的性质得到更深入的理解*本文讨论的例子一部分来自CCL语料库,一部分来自前人文献中讨论到的例子。其中语料搜索我们以“把”和数词“二”、“三”、“几”、“多”为关键词,间隔长度为10,共得到23 073条语料,其中数量宾语把字句共3642条。。
本文主要关注下列四组例子中把后NP与动后数量宾语之间的关系:
(1)A. 走了两步,感觉沉重,就把它捡起来两块拿着。
B. 令大家惊讶的是,他一回来,就把所有的产业分成了三份。
C. 他们又会说,应该把这个香蕉一掰两半,这时候,你就会进退两难。
D. 巴索沙埃,加速赶上中国选手,而且越跑越快,一下子把中国的姑娘甩了十多米。
2. 整体-部分关系
把后NP与动后NP能够表达整体-部分关系的句式有下面三种:
(2)A. 把NP1V NP2“把橘子剥了皮” B. 把 NP1V Num-Cl “把猪杀了三头” C. 把NP1V Num-Cl NP2“把橘子剥了一半皮”
其中前两种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究其原因应该是C式是A式的延伸,二者的中心词都是名词短语,因此A和C的句法表现应当是一样的,从语义上看A(C)和B都表达整体-部分关系。但是如果以数量宾语为出发点来看,则C的地位较A来说更为基础,语义上C(A)和B都表达整体-部分关系。这两种思路的不同在于,前者看到的是“整体-部分”关系这一共性,而后者则看到的是“整体-部分”关系这一共性背后的差异,即同为数量结构(即偏称宾语)表达整体-部分关系,为何有的能够补出名词,而有的则不可以。下面我们将顺着第二种思路展开讨论。
首先,表达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数量宾语把字句共同遵循一条语义原则,即“语义所指范围大的成分在前,而语义所指范围小的成分在后”(沈阳 2001),这也就决定了表示整体的名词性成分只出现在把后的位置,而表示部分的名词性成分只出现在动后的位置。但是很明显只此一条原则并不能解释数量宾语把字句所表现出来的句法差异。
(3)A. a. 把橘子剥了一半 b. 把橘子剥了一半皮 B. a.*把狗砍了一条 b. 把狗砍了一条腿 C. a.*把森林砍了两棵 b.*把森林砍了两棵树 D. a. 把衣服脱了一件 b.*把衣服脱了一件马褂
上例中把后NP与数量宾语全部满足“语义所指范围大的在前,语义所指范围小的在后”,但是不同的数量宾语却呈现出不一样的句法分布,因此我们根据数量宾语的不同将其分为A类与B类数量宾语把字句,并分开讨论。
(4)A类:由单独的数量结构(无名)构成的数量宾语
B类:由数量名短语构成的数量宾语
2.1 把后NP与数量短语构成的整体-部分关系(A类)
(5)A. 走了两步,感觉沉重,就把它捡起来两块拿着。
B. 去把那边的葫芦摘两个下来,要连着长藤,咱们来练流星锤。
C. 我饿慌了,这会儿已经头昏眼花,便把自己那份粥吞下了一两调羹。
D. 伊牧师脸上瘦了一点,因为昼夜的念中国书,把字典已读了两本,还是念不明白。
这一类把字句从形式上看动后NP无法补出其他名词,从语义上看动后数量结构中的量词与把后NP具有选择关系。我们认为这是数量宾语把字句遵循的最基本的语义原则,即“动后数量宾语中的量词默认与把后NP形成语义上的选择关系”,这种语义上的选择关系也就是搭配关系,而把后NP既可以是普通名词短语,也可以是代词。如:
(6)A. 把它捡两块拿过来。 B. 把挂在竹钉上的衣服扯了两件扔给他了。
当把后NP与动后数量宾语中的量词没有这层语义关系时,就会产生非法的例子。如:
(7)A. 把橘子剥了一半 B. 把衣服脱了一件 C. ?把狗砍了一条 D. *把森林砍了两棵 E. *把钱买了好几枝
上例中“橘子……一半”、“狗……一条*如果“狗”能够用“条”当量词的话,则合法。”、“衣服……一件”都合法,但是“森林……两棵”、“钱……好几枝”是非法的。这条原则背后的动因在于汉语量词的基本功能。
汉语中量词的本职之一就是为物体划分单位,每个量词本身就预设着量词后的名词短语与整个数量名词所表示的名词短语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类似于英语中表达整体-部分关系的词汇,如end(结尾)、half(一半)、corner(角)。Gerstl & Pribbenow(1995)曾指出,像end、half、corner这类词预设着介词后的名词短语和整个名词短语词组具有整体-部分关系。如:
(8)A.theendofthestoryispartofthestory
B.halfoftheapplesinthebasketispartoftheapplesinthebasket
C.acornerofthetableispartofthetable
他们认为end、half和corner这类词的出现本来就意味着the story(故事)和the end of the story(故事的结尾)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the apples in the basket(篮子里的苹果)和half of the apples in the basket(一半篮子里的苹果)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汉语中的量词的出现,比如“一本书”中的“本”就是这种整体-部分关系(“书”与“一本书”)的外显形式,这一特点反映在把字句中就是,当量词后面没有出现其所能够搭配的名词时,量词优先与把后NP形成搭配关系。
2.2 把后NP与数量名短语构成的整体-部分关系(B类)
这一类别中数量宾语的量词已经与其后的名词搭配,因此与把后NP不再具有上述的量词制约的情况,但是其与把后NP却受到另一条语义原则的制约,从而导致下面的句法差异:
(9)A. 把橘子剥了一半皮 B. 把狗砍了一条腿 C.*把森林砍了两棵树 D.*把衣服脱了一件马褂
对于上例中把后NP与动后NP的关系描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第一种是“可让渡/不可让渡”*这里将领属关系的可让渡和不可让渡借用过来。,第二种是“整体/部分”。如果从让渡关系来解释的话,“皮”和“橘子”、“腿”和“狗”之间是不可让渡的关系,所以“把橘子剥了一半皮”和“把狗砍一条腿”能说,而“把森林砍了两棵树”和“把衣服脱了一件马褂”不能说,是因为“树”和“森林”、“马褂”和“衣服”之间是可让渡的,这么一来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这种“不可让渡”的关系,显然“皮”和“橘子”的关系与“我”和“爸爸”的关系比起来,后者的不可让渡性要比前者自然得多。
袁毓林(1994)在考察一价名词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一区别,指出“爸爸”应属于亲属称谓的亲属名词类,“皮”则表示隶属整体的一个部件,属于部件名词,二者同为一价名词。而在“把橘子剥了皮”中,“皮”作为谓语动词的受事分裂为受事“皮”与支配的领事“橘子”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橘子”是“皮”的配价成分,动词与宾语“皮”之间具有句法、语义的选择关系,与“橘子”无选择关系。这一见解非常巧妙地解决了此类把字句中动词与宾语之间的支配问题,但是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同样是一价名词,表示整体-部分关系的“把橘子剥了皮”能说,而表示亲属关系的“把王冕死了父亲”就不好;另外同样是表示整体-部分关系,“把人砍了一条胳膊”能说,而“把人剪了一片指甲”就不好。
这说明单纯以“让渡”或“隶属”无法解决所有的数量宾语把字句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观察。如果我们将B类把字句同A类做一下对比可以发现,二者所表达的整体-部分关系其实并不一样,A类的整体-部分关系是独立的个体与集合的关系,而B类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功能域”(Functional Domain)的制约。所谓“功能域”,Cruse(1979)是这样描述的:
...apartnotonlyhasadeterminatefunction,butthisfunctionhasadeterminate“domain”,thatis,itisexercisedwithrespecttosomeparticularwhole(whichmayitselfbeapartofamoreinclusivewhole)...
比如说,门是房子的一部分,把手是门的一部分,而把手的功能域只能是门,而不能是房子,因此我们有“门把手”,而不具有“房把手”这种表述方式。(董秀芳 2009)可见,对于某类名词,天生就需要某一整体为其提供功能域,只有功能匹配的才能造出合法的句子,就像量词一样,这类名词预设存在一个功能域内的整体*判断功能域的形式标准或许可以从其构成整体-部分复合词的情况看出来,如“橘子皮”、“狗腿”,但是不能说“森林树”和“衣服马褂”。,我们同样可以说这类名词与量词类似,生来就预设着一种整体-部分的关系。而与量词不同的是,该类名词与其他名词发生语义联系受到功能域的限制。
例(9)中“皮”的功能域是“橘子”,“腿”的功能域是“狗”,他们之间是“功能整体-功能部分”的关系。而C与D虽然也是表达整体-部分关系,但是“树”离开“森林”还是“树”,并不预设一个功能整体,“马褂”离开“衣服”还是“马褂”,并不预设一个功能整体,相反,它们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的。
另外把后NP作为动后NP的功能域,必须是与其功能直接联系的,不能够跨域,因此“把人剪了一片指甲”与“把手剪了一片指甲”相比,后者要自然得多,因为与“指甲”直接相关的功能域为“手”,“人”则是相对于“手”来说更大的功能域。
由此我们推断B类数量宾语把字句中的把后NP与数量宾语虽然也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与A类所受的限制不同:A类受到来自量词选择方面的制约,B类受到来自动后名词功能域的制约。
3. 等同识别关系
语料中,除了上述表达整体-部分关系的数量宾语把字句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类把字句,在前人的研究中多以“成为义”把字句来概括。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两个小类:
(10)A. a. 令大家惊讶的是,他一回来,就把所有的产业分成了三份。
b. 陈清扬说,人家总要揪着她头发让她往四下看,为此她把头发梳成两缕,分别用皮筋系住。
c. 大多数以农为本的农民,恨不得把现有的承包地一亩变两亩。
d. 人们如果可能把一天当两天用,会使这世界的精神与物质的涵量更大的!
B. a. 他们又会说,应该把这个香蕉一掰两半,这时候,你就会进退两难。
b. 我没有说话,伸手从桌上拿起了那封信,把它一撕两片,抛掷在地。
c. 为控制烟量,他吸烟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
d. 鸿渐恨不能告诉她,话用嘴说就够了,小心别把身体一扭两段。
上述A类中的把后谓语动词可以是单音节的成为义动词,如“变”、“当”等,也可以是动补式动词,其补语经常由“成、为、作”等词充当。上述B类虽并非成为义动词,也不含补语,但是从形式上可以变换为表示等值的成为义动补形式,如“把香蕉一掰[掰成]两半”。
这类把字句中动后NP使得把后NP的外延逐步明确下来,使二者建立一种等同关系。如果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动后NP使得听话人能够更具体地重新识别出把后NP所表达的内容。我们称这种关系为等同识别关系(Identificational Relation)*这里借鉴的是对Copular Be的分类方案中的Identificational BE的情况。BE前NP一般是一个对听话人来说不明确的变量,而BE后NP的作用是给这个变量赋值,比如:Clinton is the president of USA.Clinton的所指并不明确,是一个变量,而the president of USA则明确了其所指,确定了其外延。(具体请参Sakahara 1987)。
前人文献中也有从外延的角度来分析类似把字句的,如李裕德(1991)从逻辑出发,指出此类把字句中把后NP是属概念,而动后NP是种概念,后者明确概念的外延,所以“把后NP=动后NP”,同时指出这种“种-属”关系多出现于“分解、划分种类”的把字句中。比如:
(11)A. 数学家把突变现象分为七种。 B. 人们把化学元素分为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两大类。
C. 他们家老爷子把家产分作三份。
D. 天文学家们把天空划分成几十块。
李文指出,上例中的“突变现象”、“化学元素”、“家产”、“天空”表达的都是内涵,而动后的数量短语“七种”、“两大类”、“三份”、“几十块”使得这些概念得以具体化,明确了其外延。
我们发现单纯以“种-属”关系来定义把后NP与动后NP过于局限,并且这类把字句中除了具有“分解、分类”这一层含义之外,更重要的含义是“成为义”。如:
(12)A. 为此她把头发梳成两缕,分别用皮筋系住。
B. 他把拐棍摔成两截,后来家人又为他换了一根新的。
C. 这里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大体上分两种:一种叫日常性质问题;一种叫重大的问题。
通过观察语料我们发现此类把字句中谓语动词多含有“成、为、作”等表示“成为义”的补语,即使不出现,也可以通过某种句法手段补出,据此我们认为此类把字句需要凸显的语义关系并非“分”,而是“成为”。另外动后NP的作用也并非“明确概念的外延”。如:
(13)A. 把一缕头发梳成两缕。 B. 把昨天买的一斤肉切了一碗。 C. 把112种化学元素分为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两大类。
这组例子中把后NP都受到数量短语的修饰,“一缕”就是指真实或可能世界中的“头发”的具体所指范围,指明了其外延,那么动后数量短语是否还能说是“明确把后NP外延”呢?根据陆丙甫(1988)、刘丹青(2008),名词短语前的定语可以分为内涵定语和外延定语,其中外延定语是指“用来给名词赋以指称、量化属性,表明它在真实世界或可能世界中的具体所指范围,即在不改变内涵的情况下指明其外延,由指示词、冠词、数量词语、量化词语充当”。(刘丹青 2008)由此可见,能够修饰名词短语的数量短语的本职之一就是指明其外延,因此如果说上例中的“一缕头发”、“昨天买的一斤肉”、“112种化学元素”都是“概念”,而需要动后的数量短语来明确其外延的话,显然解释力不足。
在此我们认为动后NP的作用是重新确定把后NP的外延,建立一种等同关系,使得说话人能够重新识解把后NP的外延。既然是“重新”,就意味着在“把头发梳成两缕”中的“头发”一定具有外延,具有指称性,也就是说,在词汇层面把后NP仅仅是一个NP,此时它只能表特性而不表个体,没有指称特征(胡建华、石定栩 2005),进入句法层面之后才能够得到解读(参见Chomsky 1995;胡建华、石定栩 2005),句法环境明确了其所指,这时的把后NP才具有指称性。并且这一外延是受到“把”约束的,一定是指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受到影响的那些“头发”,而不会是所有世界上的“头发”。因此上面例子中,动后的“两缕”、“一碗”、“两大类”这些数量短语是用来帮助重新识别把后NP“一缕头发”、“一斤肉”、“112种化学元素”的具体外延,建立起一种等同识别关系。
此类把字句中,由于动后数量宾语与把后NP是等同识别的关系,因此无论动后数量宾语是否有名词中心语,都存在这种关系,这种等同关系是内在的,其外在可以有多种包装形式,如数量、内部构造、价值等。
(14)A. 把大气划为几个层次。(数量) B. 把衣服包了一个包袱。(构造) C. 把钱买了好几包烟。(价值)
通过把后NP与数量宾语之间的等同识别关系,至少可以对部分数量宾语把字句的不合法的情况做出解释:
(15)A1. 把雪堆了一个雪人。 B1.?把雪堆了一辆汽车。 A2. 把钱买了一辆汽车 B2.?把钱买了一个克林顿。
上面A组的例子中,通过“一个雪人”和“一辆汽车”使得“雪”和“钱”的集合变得更明确,而听话人在处理B组例子的时候,会显得比较费力,因为“雪”和“一辆汽车”之间似乎建立不起比较自然的等同关系,“钱”和“一个克林顿”之间似乎也建立不起比较自然的等同关系,也就是说,即使通过“一辆汽车”和“一个克林顿”,听话人也无法识别把后NP的外延,除非听话人在合作原则的驱使下在其中寻找相关性,比如把雪堆成了汽车形状的,或人贩子用钱买了一个同等价值的佣人叫克林顿等。Sybesma(1999)曾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歧义现象:
(16)把昨天买的肉切了一碗。
Sybesma指出上例既可以是结果宾语把字句(“一碗”表示“切”的结果),也可以是整体-部分关系把字句(“一碗”表示“肉”的一部分),造成这种歧义的原因就在于数量宾语把字句中所存在的两种语义关系:整体-部分关系与等同识别关系。当“一碗”表示“切”的结果时,把后NP“肉”与“一碗”之间建立了一种等同识别关系,“一碗”重新确定了把后NP的外延,使得听话人能够重新识别把后NP。当“一碗”表示“肉”的一部分时,把后NP“肉”与“一碗”之间则是前文所讨论的整体-部分关系(A类)。
4. 特殊谓语关系
上述两类把字句在数量宾语把字句中占大多数,另外还有一部分数量宾语把字句既不表达整体-部分关系,也并非等同识别关系。如:
(17)A. 巴索沙埃,加速赶上中国选手,而且越跑越快,一下子把中国的姑娘甩了十多米。
B. 几十名官兵组成的打井队,一天就把老井向下挖了三米多。
C. 可是他照常活蹦乱跳地把我拖了二百多米,生龙活虎地一掌把我推下水稻田。
D. 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
它们除了从语义上不具备前两类的特征之外,还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如:
(18)A. 把它捡了两块 B. 把所有的产业分成了三份 C. 把这个香蕉一掰两半 D. 把中国的姑娘甩了十多米
首先,D中的数量结构能够受状语的修饰,我们以“快、都、才、仅仅、已经”等测试。
(19)a. 把它捡起来*才/*快/*都/*仅仅/ *已经两块(了)
b. 把所有的产业分成*才/*快/*都/?仅仅/ *已经三份(了)
c. 把这个香蕉一掰*才/*快/*都/*仅仅/ *已经两半(了)
d. 把中国的姑娘甩了才/快/都/仅仅/ 已经十米(了)
其次,D中的数量结构能够出现在情态动词后面,我们以“可能、应该”来测试。
(20)a. 把它捡起来*可能/*应该两块(了) b. 把所有的产业分成*可能/*应该三份(了)
c. 把这个香蕉一掰*可能/*应该两半(了)
d. 把中国的姑娘甩了可能/应该十米(了)
再次,D中的数量结构前能够加否定词,我们以“没”测试。
(21)a. 把它捡起来*没两块 b. 把所有的产业分成*没三份 c. 把这个香蕉一掰*没两半 d. 把中国的姑娘甩了没十米
除此之外,D中的“把NP”与数量结构之间允许语音上的停顿,此时数量结构一般都有自己的修饰成分。如:
(22)a. *把它捡起来啊,足足/差不多两块 b. *把所有的产业分成啊,足足/差不多三份
c. *把这个香蕉一掰啊,足足/差不多两半
d. 把中国的姑娘甩了啊,足足/差不多十米
石定栩(2006)指出,动后的数量成分如果具备这些受状语修饰、前加情态动词、被否定词否定等特点,那么它们“显然已经不再是体词性指称成分的一般特点,而是谓词性陈述成分的特点,应该另寻解释的办法”。
在我们看来,这类把字句与前面三类具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其根本在于两者具有不同的句法结构。前三类把字句中的“把NP”与谓语部分的关系比较紧凑,这也是传统语法一直将二者分析为一个句法单位的原因(如“把”为介词,则为状中结构;“把”为动词,则为连谓式)。而此类把字句中的谓语部分的动词与其后数量短语的关系比较疏离,与“把NP”的关系比较紧凑。我们认为,“把NP VP”与其后数量短语之间是话题-说明关系,以“把中国的姑娘甩了十米”为例,“把中国的姑娘甩了”整体作为话题,而“十米”则是对该话题的说明。刘探宙(2014)曾对汉语中的话题-说明关系做过深入的探讨,指出无论是主谓关系还是话题-说明关系,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相对关系,“离开主谓关系单独说谁是主语、离开话题-说明关系单独说谁是话题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要是被说明所确定的对象就可认为是话题,不管是什么形式。这一论述对我们启发很大,无论从“把NP”与数量短语之间的句法疏离关系或是语音停顿特点都可以看出此类把字句中“把NP”与数量短语之间具有汉语话题-说明关系的特点,其中“把NP”可以被看作是独立的句法成分,数量短语则是对这一话题的说明。
5. 数量宾语把字句语法意义的初步探讨
前人对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1. 处置说;2. 致使说;3. 影响说;4. 多义说。邵敬敏、赵春利(2005)曾指出“致使和处置都是深层的语义关系,并非把字句独有的语法意义”,我们支持这一观点,而单就数量宾语把字句来说,无论把前NP对把后NP进行了何种处置或致使把后NP产生了何种结果都略显局促,因为把前NP所处置或致使产生结果的对象应当为动后的数量宾语,而非把后NP。从这一点上,影响说的适用性更高,因此我们倾向于将数量宾语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理解为“影响”,这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 动词所支配成分是哪个NP;2. 把后NP是如何“受影响”的,或者说受到了何种“影响”。
5.1 动词支配的问题
李临定(1984)指出,能用“把”提前的成分,可以是单个动词的宾语,可以是整个动词短语的宾语;郭锐(2003, 2007)进一步指出,把后NP可以看作只是VP的宾语(如例〈23A〉)、只是V1的宾语(如例〈23B〉)、即是V1又是VP的宾语(如例〈23C〉):
(23)A. 他把民国恨得咬牙切齿。(只是V1的宾语)
B. 把嗓子说哑了。(只是VP的宾语)
C. 把饭吃完了。(即可是V1的宾语,也可是VP的宾语)
单就数量宾语把字句来说,因为动词后面已经有了自己的宾语,则把后NP很难被认为是另外一个句法上的宾语提前。因为据我们观察,即使把字句中谓语部分是双及物动词,如“送、给”等,把后NP仍然无法被视作其另一个宾语。如:
(24)小李昨天把这箱水果给了他三个,这儿还有七个。
退一步来看,假设把后NP是谓语动词的支配对象,如李裕德(1991)就认为整体-部分关系类的数量宾语把字句中把后NP是动词的支配成分,如下面三个例子:
(25)A. 把鸽子吓飞了三只。 B. 把蚂蚁踩死了三只。 C. 把小鸡踩死了三只。
李文指出,不能因为A中“吓”的对象可以是所有鸽子,B中“踩”的对象可以是所有蚂蚁,而C中“踩”的对象不能是所有小鸡,就将其支配对象区别对待;而要从把后NP的性质入手提出“集合概念”的解决方案。在A中,“吓”的对象“鸽子”是一个集合概念,动作的“整体对象是‘鸽子’而不管吓着了多少只”。同理,在B和C中,“踩”的也是“作为整体的”蚂蚁和小鸡,不管个体如何。因此,这里把后NP都是V1的支配对象,因为它们是一个集合概念,因此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动作是否达及把后NP。
这一观察将数量把字句中的V1和把后NP的关系准确描述出来了,问题在于“集合概念”与“整体对象”之间的差别。如果把后NP带上限定性的定语,那么是否还是集合概念?显然在这一类数量宾语把字句中,动词的直接支配对象应当是其后的数量宾语,以“小孩把这兜葡萄戳破了三粒”为例,“戳破”的葡萄只能够是三粒,而并非整兜的葡萄。
另外,袁毓林(2010)在讨论配价的时候指出,“把黄瓜切片儿”这一句式中把后NP与动后NP的语义角色分别为“受事”与“方式”,这正是我们所讨论的等同识别类数量宾语把字句,其中“片儿”可以补出数量成分,而谓语部分可以补出成为义的补语,如“把黄瓜切成十片儿”。很显然,这里的处理方式是将把后NP当作动词的支配成分。在我们看来,把后NP并非动词的支配成分,前文曾说到等同识别类把字句的语义重心在于“成为”,谓语动词“切成”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其后的宾语实施广义上的支配,而把后NP“黄瓜”语义上只能是“切”的支配对象。
因此,数量宾语把字句中谓语动词的支配对象只是其后的宾语。如果这样,那么如何解释前人观察到的谓语动词对把后NP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对“受影响”这一题元角色的认识。
5.2 “受影响”的题元角色
李裕德(1991)讨论动词的支配范围时指出,前文(例〈25〉)中,B与C不能因为“踩”支配的对象可以是所有的“蚂蚁”而不能是所有的“小鸡”就将其看作两个不同的句式,前者动词支配“蚂蚁”,后者动词支配“三只”,从而指出“蚂蚁”和“小鸡”以及“鸽子”是一个集合概念,而“‘吓’的整体对象是‘鸽子’而不管吓着了多少只”,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集合概念”和“整体对象”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前者指内涵,后者指外延。而名词“鸽子”只有进入了句子层面才会具有外延,具有指称性,并非只是指集合概念,但是这个外延是受到约束的,一定是在语境中动作能够影响到的那些东西的集合,而这个集合通过“把”引入*比如“夏红一不小心抬肘把一个杯子撞倒了”这句中,隐含着一层意思:在当前说话语境下存在一个以上的物体(包括杯子)在某个可能世界里会被夏红撞到。。再如下例:
(26)没有,没有任何响动。日本夫人不会放声地哭。一阵风把槐叶吹落几片,一个干枝子轻响了一声。
这里的“槐叶”无论是指整体还是部分,一定是在这个语境下“风”所能影响到的叶子的集合。张伯江(2001)指出,从句法临摹性的观点来看,把字句中之所以不允许光杆动词的出现,其实质就是“影响性”这种语义要求的句法结果,动词后面带上表示结果意义的词语来表达事件所带来的状态变化。我们认同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这些表示状态变化的结果意义的词语可以进一步地明确把后NP受到的影响,“把槐叶吹落了几片”中,“把”引入一个语境中可能受到影响的“槐叶”集合,而在这个集合中,一定有成员和动词前后某个成分有语义的关系,在这里就是“几片”被“吹落”了,也就是说,在把后NP这个集合里一定有成员受到了把后谓语部分的影响,在这里是“几片”,这就是把后NP受到的影响。
这样我们也能够解释Huangetal.(2009)“受影响”的题元角色所面临的“模糊”问题,转述如下:
(27)A. 我把心爱的杜诗抄了二百多首在笔记本上。
B. 东阳把臭黄牙露出来好几个。
C. 他闭上眼,把心中的小格拉开几个。
D. 你等着看吧!迷,去把学者们叫几个来,说我给他们迷叶吃。
Huangetal.(2009)指出,把字句中把后整个谓语部分给把后NP指派了“受影响”的题元角色,其所面临的问题是把后NP如何受影响,比如上例中把后NP“心爱的杜诗”、“臭黄牙”、“心中的小格”、“学者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根据本文的观点,A中“心爱的杜诗”这个集合中一定有“二百多首”成员被“抄”了;B中“臭黄牙”这个集合中一定有“好几个”被“露出来”了;C中“心中的小格”这个集合中一定有“几个”被“拉开(非现实性)”了;D中“学者们”这个集合中一定有“几个”被“叫来了”(当然这里的“一定”都是可能世界中的事情,具体是否已经发生还要看其他因素)。①Huang et al.(2009)提出的没有影响的反例,我们也可以做出如下尝试:
5.3 语法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两类数量宾语把字句中把后NP都可以说是一个受到影响的集合,其中整体-部分类把字句的把后NP是谓语动词可能影响到的语境中的物体的集合,而等同识别类把字句的把后NP本身则是受到影响的集合,其外延在听话人的认知里(或现实世界里)被改变。无论哪一种,把后NP都是受到了某种影响,而把前成分和把后成分的关系是影响源(起因)和受影响者的关系,因此数量宾语把字句的语义结构可以尝试做如下描写:
(28)影响源+把+受影响者+动作+支配对象②动后数量宾语作为支配对象这一点可以通过成分删除来测试。数量宾语把字句中动后成分如果删除,语义一定发生变化(要么把后NP受到全部影响“把肉切了”,要么就会生成不合法的句子“*把头发绑成”);另外把字句中的动作并非总是支配把后NP。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至少动后NP是支配对象这一点是肯定的。(参见沈阳 1995)
根据这一语义描写,我们可以对数量宾语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有更清晰的认识。首先存在影响源(把前NP)、影响对象(把后NP)、影响源使得影响对象受到影响的具体行为方式(VP)、行为方式的支配对象(数量宾语)这四个要素。从行为方式和其支配对象的关系可以看出,动词只单纯地支配其后的数量宾语,而并不支配把后NP,把后NP与动词的联系是通过其与动后数量宾语之间语义上的关联产生的(如本文讨论的整体-部分关系、等同识别关系),并非句法上的支配关系。
6. 结论
通过对数量宾语把字句的观察,我们发现数量宾语把字句的把后NP与动后NP存在两种语义关系,即整体-部分关系与等同识别关系。其中整体-部分关系中,当动后NP为数量(无名)短语时,其制约因素来自于量词与把后NP的匹配度;当动后NP为数量名短语时,其制约因素来自于把后NP与动后NP的功能域的辖域。而等同识别关系中,我们指出前人所说的“成为义”更多地来自于听话人的识别,动后NP在听话人的认知里改变了把后NP的外延,建立起一种等同关系。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类与前两类数量宾语把字句形式一样,但句法表现完全不一样的特殊谓语把字句,我们指出其中的“把NP VP”共同做句子的话题,而其后的数量短语为说明成分。综观数量宾语把字句,其语法意义应为“影响源+把+受影响者+动作+支配对象”。
a. 他把一个大好机会错过了。
b. 我会把他恨一辈子。
c. 小孩把他想得要死。 a中“把”引入一个语境中能够受到影响的集合,这个集合里有所有可能世界中可能被错过的“一个大好机会”,“错过”明确了这个集合中在现实世界受到影响的成员。b、c中“把”引入一个语境中能够受到影响的集合,这个集合里有所有可能世界中可能被“想得要死”的“他”,“想得要死”则明确了这个集合中在现实世界受到影响的那个“他”。
Chomsky, N. 1995.TheMinimalistProgram[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ruse, D. A. 1979. On the transitivity of the part-whole relation[J].JournalofLinguistics(15): 29-38.
Cruse, D. A. 1986.LexicalSeman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stl, P. & S. Pribbenow. 1995. Midwinters, end games, and body parts: A classification of part-whole relations[J].JournalofHuman-ComputerStudies(43): 865-889.
Huang, C. T. J., Y. H. A. Li & Y. Li. 2009.TheSyntaxofChines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kahara, S. 1987. Roles and identificational copular sentences[A]. G. Fouconnier & E. Sweetser.Space,Worlds,andGrammar[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2-288.
Sybesma, R. 1992.CausativesandAccomplishments:TheCaseofChineseBa[M]. Holland: Holland Institute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Sybesma, R. 1999.TheMandarinVP[M].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董秀芳. 2009. 整体与部分关系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的表现及在汉语句法中的突显性[J]. 世界汉语教学 (4): 435-442.
郭 锐. 2003. 把字句的语义构造和论元结构[J]. 语言学论丛 (28): 152-181.
郭 锐. 2007.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胡建华,石定栩. 2005. 完句条件与指称特征的允准[J]. 语言科学 (5): 42-49.
李临定. 1984. 动词的宾语和结构的宾语[J].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103-114.
李裕德. 1991. 整体—数量宾语把字句[J]. 汉语学习 (2): 19-22.
刘丹青. 2008.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J]. 中国语文 (1): 3-20.
刘探宙. 2014. 汉语口语中的话题句末重置句[R]. 首届主观化理论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未刊.
陆丙甫. 1988. 定语的外延性、内涵性和称谓性及其顺序[J]. 语法研究和探索 (4): 102-115.
吕叔湘. 1948a. 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全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48b. 把字用法研究[A]. 季羡林,黄国营.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吕叔湘选集[C].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545-573.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邵敬敏,赵春利. 2005. “致使把字句”和“省隐被字句”及其语用解释[J]. 汉语学习 (4): 11-18.
沈 阳. 1995. 数量词在名词短语移位结构中的作用与特点[J]. 世界汉语教学 (1): 14-20.
沈 阳. 2001. 名词短语分裂移位与非直接论元句首成分[J]. 语言研究 (3): 12-28.
石定栩. 2006. 动词后数量短语的句法地位[J]. 汉语学报 (1): 51-58.
薛凤生. 1987. 试论“把”字句的语义特性[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4-22.
叶向阳. 2004. “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J]. 世界汉语教学 (2): 25-39.
袁毓林. 1994. 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J]. 中国语文 (4): 241-253.
袁毓林. 2010. 汉语配价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J]. 中国语文 (6): 519-524.
朱德熙. 1985.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 马应聪)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市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文是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汉语主宾不对称性对比研究”(2013BYY006)的部分成果。
H043
A
2095-5723(2015)02-0049-10
2015-01-27
致 谢: 北京大学沈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探宙先生、河南大学姜玲先生及匿审专家曾为文章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谢过,文中误谬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