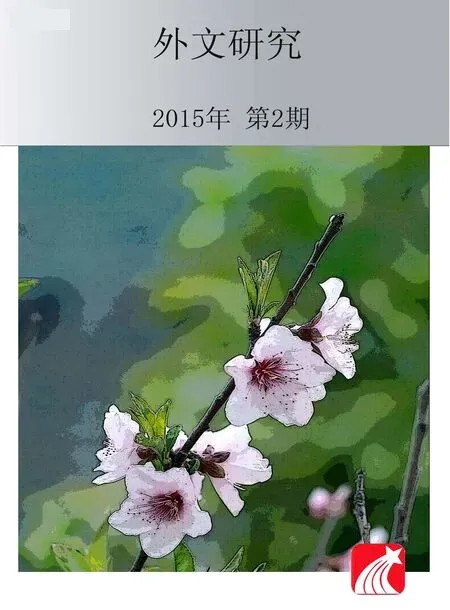《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逻辑游戏”
江南大学 张俊萍 石亚楠
《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逻辑游戏”
江南大学 张俊萍 石亚楠
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路易斯·卡罗尔所著的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镜中奇遇》中,很多情境、情节及人物语言、动作呈现出一种有趣的“逻辑游戏”。这种逻辑游戏主要有逻辑对称(包括空间、时间、状态的对称)和逻辑悖论(包括逻辑荒谬、逻辑混乱、逻辑叠加、自相矛盾等)两种表现形态。不论是逻辑对称还是逻辑悖论,实质上都可以追溯到深刻的语言学问题。可以说,该书在童稚情趣外表下深藏着哲理。
逻辑;悖论;对称;卡罗尔
一、《爱丽丝镜中奇遇》及其研究述评
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1832—1898)虽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但令其闻名于世的却是两部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两部《爱丽丝》的中国译者赵元任曾这样说起这两部作品:“我相信这书的文学价值,比起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亦比得上……罗素就多次引用过此书来阐述深奥的哲学问题,因此就是成年人,如未读过也很有一读的必要。”(转引自苌苌 2010: 112)此言一点也不为过,这两部儿童文学作品中确实蕴含着众多适合成年人玩味和思索的哲学问题,特别是逻辑问题。
与《爱丽丝梦游仙境》相比,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设计了类似前作的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情节,女主角爱丽丝梦中进入镜子世界,遭遇到与现实世界截然相反的事情。与《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爱丽丝镜中奇遇》也包含了大量令人拍案的双关语、谐音等语言游戏,以及多首滑稽模仿当代著名童谣或诗歌的胡闹诗(nonsense verse),展现了路易斯独特奇幻的文风。但显而易见,后者更富有逻辑学色彩和哲理内涵。近年来,中外学界对于《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并纷纷从纯文学角度延伸到其他领域。理查德·雷德勒(Richard Lederer)评论了卡罗尔小说的“语言魔力”,说他为读者展示了一场词汇的魔法盛宴,他可以从帽子中拽出单词,可以将一个词劈成两半使用,也可以让单词在空中跳舞,当然,也可以让单词以任何一种奇怪的方式消失在任何一个奇怪的地方(Lederer 2010: 179)。戴维·瓦格纳(David Wagner)则在《无意义的使用》中指出,卡罗尔的创作灵感可能来源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学思想(Wagner 2012: 205),他探讨了卡罗尔的哲学研究及逻辑发展的过程,并且分析了卡罗尔作品中的语法游戏和语言游戏。他指出:作品中语法和语言游戏的巧妙使用正是卡罗尔作品大受儿童喜爱的重要原因。儿童会发现,在某一特定语境中学到的词汇放到另一个语境中则会不适用;而卡罗尔作品的引人之处就在于他对于词汇的使用在句子中绝对没有一点语法错误,但是往往却以一种无意义的方式出现在看似合理的情境中(Wagner 2012: 209)。苌苌探讨了爱丽丝作品中的“现实世界”、“镜中世界”和“梦中世界”的真伪问题,并指出作品中涉及的梦不再是我们被告知的“梦是我们想象力的衍生物”,而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反映”(苌苌 2010: 112)。池佳在《儿童文学家Lewis Carroll的数学世界》中论述了《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双重梦问题:“双重梦似乎将人们引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从而分辨不清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梦。”(池佳 2008: 20)池佳也探究了卡罗尔在这两部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数学意识和数理逻辑方面的成就。封宗信则运用认知诗学理论分析了《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逻辑荒谬,并阐释了该作品融逻辑艺术与文学艺术为一体的语言策略。他认为,《爱丽丝镜中奇遇》在语言的创造性和逻辑悖论层面,分量超过了《爱丽丝梦游仙境》(封宗信 2011: 31)。他评论道,《镜》是童话艺术,也是叙事艺术、语言艺术和逻辑艺术。卡罗尔让我们通过现实世界与奇幻可能世界之间的联系,思考意义与无意义、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悖论(封宗信 2011: 36)。纵观近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有学者注意到《爱丽丝镜中奇遇》中与逻辑学相关的语言问题和哲学问题,也略略涉及到小说中的逻辑悖论问题,但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事实上,《爱丽丝镜中奇遇》中设置的很多情境、情节及人物话语、动作都表现为有趣的“逻辑游戏”。这种逻辑游戏主要有逻辑对称(包括空间、时间、状态的对称)和逻辑悖论(包括逻辑荒谬、逻辑混乱、逻辑叠加、自相矛盾等)两种表现形态。不论是逻辑对称还是逻辑悖论,实质上都可以追溯到深刻的语言学问题。正因为此,该书在童稚情趣外表下深藏着哲理。
二、《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逻辑对称
《爱丽丝镜中奇遇》涉及到的最典型的逻辑游戏便是逻辑对称问题。“对称”(symmetry),指图形或物体相对的两边的各部分,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特别是指物体或图形在某种变换条件(例如对于平面的反应等等)下,其相同部分间有规律重复的现象。其中较常见的对称为“镜面对称”。“镜子”在《爱丽丝镜中奇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贯穿全文、深化主题,作品中的逻辑问题也多数与镜子相关或由镜子引出。爱丽丝在梦中进入到镜子世界,然后展开了一系列与现实相反的活动。镜中世界一切事物都与现实相反:空间是逆向的;时间、记忆都是双向的;状态、行为准则是随意的。这些都体现出了逻辑对称的原则。
空间对称是《爱丽丝镜中奇遇》中最为典型的逻辑对称现象。镜中世界的空间概念与现实世界的完全相反。方向问题是空间对称的一个显著例子。爱丽丝在镜中世界里发现,越朝着某一目的地走,离目的地反倒越远,逆着方向走却能到达目的地,因为镜中的运动方向与现实中的正好相反。最奇特的一个空间对称的例子便是爱丽丝和白皇后到底有没有移动的问题。白皇后带着爱丽丝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又累又渴的爱丽丝停下来之后却发现她们还是呆在原地没动,白皇后解释道:“你知道,在这里要想停留在原地,就得和你一样竭尽全力跑!”(卡罗尔 2012: 52)在现实世界中,人以地球为参照物可以从一个地点转移到下一个地点。而在镜中世界,情况相反,惟有移动才能呆在原地不动。爱丽丝在镜中发现了一本书,但是无论怎么看上面的单词她都不认识,琢磨了半天之后才想到自己是在镜中,理所当然,书上的字都是倒着的。所以爱丽丝便在镜中世界里找了一面镜子,果然,透过镜子的对称,字又变正常了。引人深思的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镜子里的镜中世界,即第二个镜中世界。依据对称原理来说,这个镜中世界里的万物形态等都应该和现实世界里的完全一致。问题在于,这第二个镜中世界是否就是现实世界?还是和数学中的平行原理一样,只是和现实世界平行对称的另一个虚幻世界呢?第四章中,爱丽丝见到红国王在睡觉,特威度迪(Tweedledee)对爱丽丝说,“他正在做梦……他梦到你了……要是他梦里没有你,你认为你会在什么地方?”(卡罗尔 2012: 98)而在第一章中读者得知,爱丽丝正是自己做梦才进入镜中世界的,也就是说,镜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爱丽丝的梦中,包括红国王做梦。但根据特威度迪所说,爱丽丝出现在红国王的梦里,似乎爱丽丝整个经历包括做梦的过程也属于红国王的梦,到底爱丽丝在红国王的梦里,还是红国王在爱丽丝的梦里?这里如“庄周梦蝶”一样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即空间意义上由于镜像形成的无限循环对称。
在《爱丽丝镜中奇遇》中,作家把镜子造成的对称性从空间扩展到时间,所有时间也以空间的形式对称起来。由于镜子是对称物,所以在卡罗尔描述的镜子世界里,大家是倒着过日子的,即按明天——今天——昨天的顺序过日子,既然倒着过日子,那么记忆也可以是逆向的,将来的事情也就可以记住,进而卡罗尔提出双向记忆,不仅能够记住过去发生了什么,将来发生的事也能保存在记忆中,形成了过去与未来的对称。当爱丽丝问白王后:“你记得最清楚的是些什么事情?”白皇后是这样解释时间对称问题的:“ 哦,下下个星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现在有一个国王的使者正坐牢服刑,可是审讯要等到下星期三才开始。当然,最后才是他犯罪。”(卡罗尔 2012: 117)这样的时间顺序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反,但恰好体现了时间对称原则。
在《爱丽丝镜中奇遇》中,还出现了状态对称的现象。比如,通常认为的挂在墙上的画、钟表的图案、花儿等等都是静止的,但在镜中世界这画是可以动的,钟表里的老头竟然可以露出笑脸,花儿也可以说话。在现实世界中,与人说话时,谁先开口说话就表示礼貌;而在镜子世界中,则变成了谁先开口说话就表示不礼貌。在现实世界中,做一个动作会花费时间,这是常识,而在镜子里,却正好与现实相反,做动作是为了节省时间。《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红皇后对爱丽丝说:“行个屈膝礼,这样节省时间。”(卡罗尔 2012: 44)卡罗尔巧妙地利用对称原理将现实与镜子世界里的状态完全颠倒过来,使读者在感到滑稽可笑的同时又发觉意味深长。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逻辑对称,《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对称现象也包括标准规范的对称。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若要同意某件事情就会说:举双手赞成;而在镜子世界中,经过镜子的对称,若一个人举双手,则表示反对。且看下面这句话,“你没办法否定,你举双手也否定不了”(卡罗尔 2012: 224)。 这明显违背了现实中的行为准则和标准,但正是如此,才使现实中本来无意义的准则在镜子中变得有意义。在第九章中,当爱丽丝来到宫殿门外,按门铃要求进入时,发现不管她如何拼命地敲门,始终没有侍卫来开门。此时,一只年老的青蛙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不该那么做,不该那么做……你知道,要这样对付它……你别理它,它也就不理你了,懂吗?”(卡罗尔 2012: 242)果真如此,爱丽丝停止敲门后,门就开了。第五章中,爱丽丝在商店买鸡蛋,店主(羊)说,买两个比买一个便宜,而且店主并不把鸡蛋递到她手里,而是放在店里另一头的架子上,爱丽丝想去拿,却发现鸡蛋离她更远。因为在镜中世界,“买下”鸡蛋便是归还之于货架。这些违背了现实中正常逻辑的行为准则在镜子世界中全都变得有意义了。这便是对称和“反向”的作用及妙趣所在。
三、《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逻辑悖论
《爱丽丝镜中奇遇》中另一明显的逻辑游戏是逻辑悖论。悖论,是指一种导致矛盾的命题,在逻辑学上指可以同时推导或证明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的理论体系或命题。《爱丽丝镜中奇遇》中出现的逻辑悖论包括逻辑荒谬、逻辑混乱、逻辑叠加、前后矛盾四个方面。
第一种是体现逻辑荒谬的有趣情境或对话。比如,爱丽丝在镜中发现椅子竟然是一棵在生长的树,屋子里还有一条小溪在流淌。第六章中,矮胖人(Humpty Dumpty)询问爱丽丝的年龄,爱丽丝说七岁六个月。矮胖人说:“你要是早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只长到七岁’……不过,来不及了。”(卡罗尔 2012: 142)从矮胖人的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认为人的年龄是可以控制的,想活到几岁就活到几岁,而这种逻辑思维在现实世界中显然是荒谬的。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镜中世界的矮胖人竟然对爱丽丝说:“字词有脾气,特别是动词。动词最傲慢了。形容词可以任你摆布,动词可不行。不过,我能把他们全都治得服服帖帖的。顽固不化!这就是我要说的。”(卡罗尔 2012: 148)话语中的字词被赋予人的性格特点,这无疑匪夷所思。在镜中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正常的逻辑、规律、法则似乎都变得不适用。本来在现实世界正常的现象和物品在镜子世界中的人物看来,似乎都显得荒谬,同样,在现实世界中荒谬、不可能的现象在镜中也可以变得合情合理。
第二种则是逻辑混乱现象。这也是在《爱丽丝镜中奇遇》中出现最多的有趣现象。在第一章中,爱丽丝故意抓住白国王的铅笔不让他写字,白国王此时竟说,“下次我要换个细一点儿的铅笔,这个铅笔写得不舒服”(卡罗尔 2012: 22)。这显然是逻辑混乱,笔写得不舒服,与当时情境有关,与笔的粗细无关。镜中的花儿评价现实中的花儿之所以不会说话是因为他们都睡着了,而睡着的原因是因为土地太松软了。这也是逻辑混乱的表现,土地松软与花儿是否睡觉的逻辑关系是强加上去的。第二章中,当爱丽丝和白皇后跑完之后,爱丽丝说自己很渴,皇后便拿出了饼干让爱丽丝“解渴”,这里显然将“饿”和“渴”混为一谈。第八章中,骑士说自己贴在头盔里很结实,像闪电一样结实。这里将物体的牢固度和速度的逻辑关系搞乱了。“闪电”是用来形容速度的,不是形容“结实”的。第九章中,红王后问爱丽丝一个问题:“从狗嘴里拿走骨头,留下什么?”(“Take a bone from a dog: what remains?”)爱丽丝以正常的逻辑谨慎思忖这个问题:“如果我拿走骨头,骨头当然不会留下,狗也不会留下,狗会来咬我的,我肯定也不会留下!”但红王后的正确答案却是匪夷所思,似乎完全不合逻辑,她说:“是狗的脾气留下了。”(卡罗尔 2012: 229)
第三种逻辑悖论现象是逻辑叠加问题。第六章中,当爱丽丝感叹“一个人没有办法不长的”(“One can’t help growing older”)(卡罗尔 2012: 142)时,矮胖人却说,“也许一个人没办法,但是两个人有办法”。(“One can’t, perhaps, but two can.”) (卡罗尔2012: 144)这里便出现了数学逻辑中的简单叠加问题。略懂英语的读者知道第一个“一个人”(one)泛指“人”,重点不是可列数叠加的“一个人”,但卡罗尔把它偷换成数字“一”(one),因而利用数字叠加造成了有趣的问答。另一个叠加问题是时间叠加问题,红皇后这样对爱丽丝解释如何度过冬夜的问题:“我们总是两三个白天,两三个夜晚放在一起过的。在冬天,我们有时候最多把五个晚上放在一起过。那样暖和些,懂吗?”(卡罗尔 2012: 232)现实世界里,时间只能一天一天过,但是在镜子里,日子可以像“盖被子”一样叠加起来,冬天太冷了,多盖几床被子就会暖和,同理,冬夜叠加起来过似乎也会暖和一点。这里是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日子在卡罗尔笔下不再是抽象无形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物体,所以可叠加。
最后一个逻辑悖论的问题是前后矛盾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白国王有无胡子的问题。第一章中,爱丽丝将白国王拎起来放到桌子上,白国王惊魂未定地说道:“我可以肯定,亲爱的,我当时每一根胡须都变得冰凉冰凉的!”(“I turned cold to the very ends of my whiskers!”)(卡罗尔 2012: 22)而白皇后则说道: “你没有长胡子啊。”(卡罗尔 2012: 22)国王说自己的胡须都吓得冰凉了,说明国王有胡须,但是白皇后却说国王没有胡须,这便是悖论里的逻辑前后矛盾。还有便是关于新旧拨浪鼓的问题。在第四章中,爱丽丝发现了一只拨浪鼓,根据爱丽丝的描述,这“只是一个旧拨浪鼓……又旧又破”(卡罗尔 2012: 102),特威度顿(Tweedledum)回答道,“我当然知道它是又破又旧的了!”也就是说,这是一只旧的拨浪鼓,但是之后特威度顿又说道,这“不是旧的……是新的……我昨天刚刚买的——我的好看的新拨浪鼓啊!”(卡罗尔 2012: 102)到底这个拨浪鼓是旧的还是新的?作品里没有明说,只提供了这样前后矛盾的说法。
四、充满童趣的逻辑游戏和富含哲理的语言问题
不难发现,不论是《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逻辑对称现象,还是逻辑悖论问题,都是符合儿童认知心理和儿童逻辑思考的,可以说是充满童趣的逻辑游戏,但在有趣的逻辑游戏背后则是深刻的语言学问题。逻辑悖论和逻辑对称多数是语言使用引起的。逻辑一词(logic)与“逻各斯”(Logos,希腊文)相关,而“逻各斯”(Logos)则是动词“lego(说)”的名词形式,原意为“言说”、“话语”,据此派生出“道理”、“理性”、 “思想”、“本原”等涵义(朱清华2009: 98)。可以说,“逻辑存在于人类语言之中”(王寅 2014: 31)。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也曾阐发语言的逻辑本能,“认为语言具有逻各斯本质,逻辑学与语言本身具有一种直接同一关系”(转引自王寅2014: 67)。可见,逻辑与语言同构,逻辑问题与语言有密切联系。逻辑对称和逻辑悖论多数与语言使用有重要关系。
《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逻辑对称本质上是“镜子”隐喻的拓展使用,卡罗尔把以空间对称、映象反向为主要特征的“镜面对称”延伸到时间、状态、规范等领域的对称或同义“反向”上,使镜子隐喻贯穿全书,从而引起读者的认知陌生感和新奇感。而《爱丽丝镜中奇遇》所设的众多逻辑悖论也大多与语言的多义和语言字面义、隐喻义、引申义等的交叉混合使用有关。例如,当爱丽丝感叹 “一个人没有办法不长的”(“One can’t help growing older”)时候,作者让矮胖人把这个泛指的“one”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数字“one”,所以“一个”(one)人不行,那“两个”(two)人总行了吧。又比如,白国王所说的“我当时每一根胡须都变得冰凉冰凉的”(“I turned cold to the very ends of my whiskers”)其实是一种隐喻表达,表示吓得冰凉的程度,通常不必实指有无胡子。而在这里,作者让白王后撇开隐喻义直接从字面义去理解,因而质问白国王:“你根本没有胡子!”再如,“从狗嘴里拿走骨头,狗会留下脾气”这一荒谬答案,与英语中“发脾气”(lose temper)一词的字面义、引申义的双重语义有关,“lose temper”意为“发脾气”,而“lose”本意为“丢弃、留下”,正可应答于 “从狗嘴里拿走骨头,留下什么?”(“what remains?”)那一问题。“发脾气”与“留下脾气”(“lose temper”)的两项词义可以同时回答那个问题。可见,卡罗尔童话的荒诞逻辑、趣味逻辑多数建立在语言的有趣使用上。
在第八章中,语言使用所带来的逻辑混乱达到极致。爱丽丝向骑士问起一首歌的名字时,骑士做了振振有词的回答,但在爱丽丝看来似乎出现了四个答案,正确答案是什么?爱丽丝如堕云雾。骑士的回答是:1. 这首歌的名字叫作《鳄鱼的眼睛》。(“The name of the song is called ‘Haddocks Eyes’.”)2. 人家是这么叫它的名字的,其名实应叫作《古稀之人》。(“That’s what the name is called. The name really is ‘The Aged Aged Man’.”) 3. 歌曲叫作《办法和手段》,但是,仅仅是起个名而已!(“The song is called ‘Ways and Means’. But that’s only what it’s called, you know!”) 4. 歌曲实际上是《坐在大门上》(“The song really is ‘A Sitting On a Gate’...”)(卡罗尔 2012: 209-P211)。这里,歌曲的真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由于谓词“is”的灵活使用,爱丽丝(也是读者的化身)所感受到的逻辑混乱其实在骑士的语言系统中一点也不混乱。在骑士的话语中,“歌曲是什么”(歌曲的指称对象。“is”表示所指的对象,即“reference”)、“歌曲被叫作什么”(歌曲之名或人类对其的命名。“is”表示被指称之名,即“name”)、“歌曲的名字是什么”(歌曲的名字所指称的对象。“is”表示所指的对象,即“reference”)、“歌曲的名字被叫作什么”(人类对“歌曲之名”的命名。“is”表示被指称之名,即“name”)是四个意义上完全有区别的句子;而且“歌曲”与“歌曲名”指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因此,在镜中骑士那里,“歌曲叫作什么”与“歌曲名叫作什么”具有不同的答案。而在我们的日常逻辑中,“歌曲名是什么”与“歌曲叫作什么”是同义问题。
卡罗尔巧妙地将语言问题和逻辑问题结合在一起,在提出语言问题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强大的逻辑能力和丰富的逻辑趣味。读者就如《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爱丽丝一样,在逻辑和语言的奇境中越来越好奇(“curiouser and curiouser”①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觉得自己越来越好奇,卡罗尔用的就是符合儿童逻辑思维特征的 “curiouser and curiouser”,“curious”(好奇)一词是多音节形容词,其比较级应该是“more and more curious”。一般说来,在英语中,单音节形容词的比较级的写法,是在形容词后面加 “er”。)。
Lederer, R. 2010. The word magic of Lewis Carroll [J].WordWays(3): 178-181.
Wagner, D. 2012. The uses of nonsense—Ludwig Wittgenstein reads Lewis Carroll [J].WittgensteinStudien.NeueFolge(1): 205-216.
池 佳. 2008. 儿童文学家Lewis Carroll的数学世界[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封宗信. 2011. 《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的认知诗学分析[J]. 外国语文 (2): 31-36.
苌 苌. 2010. 真假都未必[J]. IT经济世界 (9): 112.
刘易斯·卡罗尔. 2012. 艾丽丝镜中奇遇记[M]. 许季鸿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王 寅. 2014. 语言哲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清华. 2009. 海德格尔早期对Logos的存在论诠释[J]. 江淮论坛 (6): 98-103.
(责任编辑 屈璟峰)
通讯地址: 214000 江苏省无锡市 江南大学外语学院
I561
A
2095-5723(2015)02-0073-05
2015-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