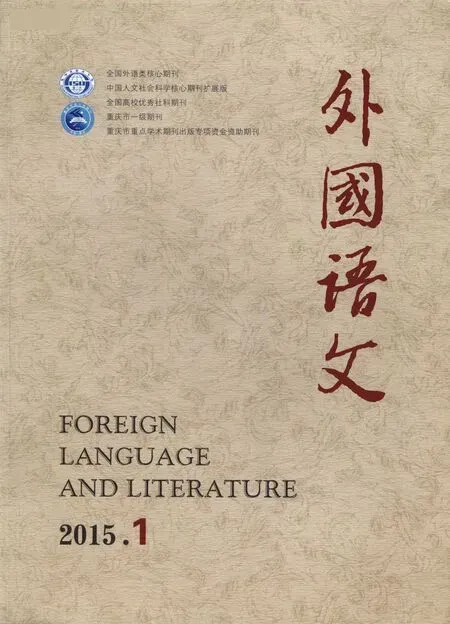我秀故我在:从经典走向现代的莎士比亚爱情喜剧——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第十二夜》
李伟民
(四川外国语大学 莎士比亚研究所,重庆 400031)
1.引言
当代如何演绎莎士比亚戏剧,如何在文本改编和舞台演出上呈现莎士比亚的喜剧精神?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对外国戏剧,特别是莎剧解禁的惊喜之后,在改编上有所突破、创新?通过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精神,如何使今天的观众获得心灵的震颤和会心一笑?即在话语语言之外,利用动作、姿势、符号的语言达到“被震撼的敏感性”(安托南·阿尔托,2006:111)。这是每一个试图在当代把莎剧搬上舞台的改编者首先面临的问题。应该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第十二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改编的范例。该剧在国内演出三十多场,1994年赴日本参加了“’94亚洲、太平洋地区青少年戏剧节”,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在莎剧改编和演出中,如果仅仅亦步亦趋地照原样扮演,已经很难获得观众的认同,更别说引起观众的共鸣了。而改编演出的失败,责任并不在莎士比亚,而在于改编者是否具有“我秀故我在”的创新、独特的眼光和崭新的舞台呈现,以及借助于莎剧使观众体味到当下的某些社会图景和人情世故,以获得心灵的放松。
2.我“秀”故我在:喜剧之魂的拼贴与戏仿
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莎剧演出形式的演变时,就会懂得“寻找更多样的手法”(吴光耀,2003:83)是莎剧被搬上当今舞台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改编莎剧的难点,更是每一个改编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代戏剧从精英文化、审美文化、现代主义转变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的今天,对莎剧的改编,我们对“时尚流行性、平民世俗性”(丁罗男,2009:284-296)也应该抱有宽容的态度。我们认为“秀”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审美经验接地气的形式创新”(Li Weimin,2013:30-37)。携世界莎剧演出潮流,我们看到,当今的莎剧演出可以说是利用各种艺术形式的五花八门的改编,原封不动地搬演已经少之又少了,也难以普遍获得观众的认同。“秀”(Show)体现了莎剧改编的现代性,其精神内核是与当下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戏剧观念上,打破了单纯模仿西方莎剧的格局,既通过莎剧反映社会人生,表现人的价值尊严,也更为关注以审美娱乐大众,升华人格,陶冶情操。“秀”主要在于通过阐释莎剧丰富的内涵,揭示莎士比亚与现代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新的时代莎士比亚给人类社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秀”表现,莎士比亚对人类情感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描写的独特方式,以及对人类情感的探密。“秀”又联系当下社会,通过互文、拼贴、变形、挪移、重构、解构、映射出万花筒般的现实人生。“秀”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创作方法在当代大行其道,给观众带来的是多方位的视听娱乐享受。莎士比亚的普世性,已经成为各种戏剧风格、流派吸收他者导表演理论、经验的一张畅通无阻的介绍信,并且演绎出无数的莎士比亚的副产品。“秀”体现了文本和舞台改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主要表现为,从形式与语境出发,拉开当代观众与莎士比亚的距离;或者宣称遵循原著精神甚至细节的演出,希冀当下的观众能够重新回到莎士比亚戏剧产生的时代。“秀”也是融入了后现代元素的莎剧演出,呈现的是互文、戏仿与解构的莎剧演出。在莎学现代性的框架之内,后现代性永远是一种当下状态。后现代强烈地质疑各种知识定论赖以形成的基础,情节不断被复制或增殖,在新文本的自我形成过程中,寻求对原作的吻合、解构或颠覆,并在暗喻或换喻中形成新的意义。“秀”也是不同民族审美艺术与莎剧全方位的深度融合。因为时代要求我们演出莎剧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编。正如安托南·阿尔托所说:“当戏剧使演出和导演,即它所特有的戏剧性部分服从于剧本时,这个戏剧就是傻瓜”(安托南·阿尔托,2006:34)。
当中国的莎剧演出已经从幕表戏、初期的话剧、戏曲演出、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思想指导下的演出,进入了采用多种艺术手段,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于一炉的探索、发展、繁荣的新阶段的时间段,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倾情打造,何炳珠、刘立滨导演,舞台设计章抗美,何瑜、范志博、于洋、黄蕾、闫汉彪、唐黎明、李晔、赵倩等表演的话剧《第十二夜》就是充分利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形式,以“富于诗情的青春气息”(方平,1983:29)和超脱的游戏精神,融西方戏剧与中国戏曲表现手法于一炉,既深刻体现莎氏喜剧的人文主义气息,又能够吸引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一部中国莎剧。本文将从文本与他文本、文本与舞台之间的对话,即拼贴、戏仿和互文性的角度,从《第十二夜》的人物、主题、情节及内容出发,分析其改编策略。
通俗而非庸俗、低俗与粗俗,时尚也非时髦、随意与粗糙,莎剧生命力的奥秘存在于不断的舞台演出之中。青艺版《第十二夜》在艺术上追求大雅与大俗兼具,采用拼贴、戏仿的舞台呈现方式,在喜剧精神的体现上可以说是颇得原作之神韵,而在具体艺术手法上却使之尽量“中国化”,这一改编策略则与当今观众的审美口味与成分有关。该剧的内容与主题都没有离开原作,这一点表明“人们对仿体的接受也是建立在对本体和仿体之间所存在的内部联系之上的”(徐国珍,2003:25)。《第十二夜》尽管与原作有诸多的内部联系,但经过拼贴、戏仿和间离,以至于这种转换已经演变为一个“中国式的莎剧故事”了,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是在文化提供的各种伴随文本之上的‘重写’”(赵毅衡,2011:50),而形成这种改编的超文本格局,在中国化、流行化和时尚化中与其他对《第十二夜》的改编共同被接收与延续,并“将严肃与游戏(客观性与游戏性)搀在一起”,(弗兰克·埃尔拉夫,2003:57)喜剧体(讽刺、幽默、滑稽模仿)与严肃体熔为一炉,舞台上剧中人的纯真爱情成为“想象视点”中的纯情的中国少男少女。青艺版《第十二夜》经过对原作的拼贴与戏仿,已经在形式上建构了当代莎剧的呈现方式,它既是莎氏的原作,更是中国的莎剧《第十二夜》,而其中采用的拼贴与戏仿,以及由此而显示出来的互文性,反映的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渴望纯真爱情的某种期盼和憧憬,以及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所持有的大胆而浓烈、开放而清新、挚诚而轻松的态度,改编通过拼贴、戏仿、互文性在中国舞台上重新建构了莎剧的喜剧精神。该剧“秀”的超文本性已经在舞台呈现中非常生动地体现出来了,其中对美好爱情的憧憬,纯洁的相恋和善意的恶作剧体现了伊利里亚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的美丽梦幻,薇奥拉被定位于“聪明而纯情”的年轻貌美,心地善良,忠于爱情的少女。纯洁爱情的理想模式隐含了改编者与观众之间潜在的“理想模式”与少男少女关于爱情的大众想象,而这种模式谁又能说不是对于过度商业化、消费化社会的一种精神反拨呢?
3.怎样拼贴:内容与形式
3.1 舞台与服装的拼贴
从中国莎剧改编的历史来看,青艺版《第十二夜》与其他成功的莎剧改编一样,在导演和表演思想、技巧已经相当成熟,体现出导演和演员对主题意蕴把握的自信,通过拼贴和戏仿,以通俗化、现代特征、中国特征表现当今青年对爱情的理解已经成为导表演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为了体现舞台的“假定性”,“在假定性的环境和事件中求得真实性的效果”(谭霈生,2005:373),演员化妆和舞台布景采用象征爱情的隐喻,如人物造型的小丑化脸谱,主要演员面部“蝴蝶”、“玫瑰”的“文身贴”等美饰图案,现代而又明丽的服装,小丑那具有中国戏曲特点的服饰,向观众传达出浓郁的青春气息、爱情意蕴和文化特色。在通俗与高雅两者之间,为了更能接近青年观众,该剧的舞台布置简洁而具有象征性,舞台上的三组钢管象征着城堡、客厅、窗户、森林以及葫芦型的酒器,显示出既象征了原作提供的氛围,又具有现代特色和中国意味。舞台布景采用简洁的金属支架,在舞台灯光的反射下,象征各种不同的场合和地点,金属支架既可以成为人物表达感情,显示心理,表达爱情的依托物,也可以在舞台上形成不同层次的表演区间,隐喻为不同的地点,显在与此在共同呈现在观众面前,熠熠闪光的金属支架布景,甚至可以成为拴马桩和磨刀石。借助于金属支架多重隐喻的指涉,在稳定与自由流动的时空中体现出舞台的“假定性”(何炳珠、刘立滨,1994:67-71)。这里既有剧情的叙述,也有间离效果的运用,既可以在此进行爱情的独白,又可以让观众体会到游戏的愉悦;既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再现,也可以是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氛围的营建。正如黑格尔所说:喜剧“本身坚定的主体性凭它的自由就可以超出这类有限事物(乖戾和卑鄙)的覆灭之上”(黑格尔,1981:293-294)。在该剧中,舞台布景与人物服装成为阐释原作精神,拉近与当代中国观众距离的重要手段。该剧中的人物并不是原作中穿着古典、人物动作老派、对白慢条斯理、拿腔拿调,异域特征明显的莎剧中的复古形象,而是一群身着亮丽、时尚,清纯、大方、朝气蓬勃,具有青春气息的少男少女。在演出服饰的选择中,既有白色西服、牛仔裤、系在前腰的衬衣、半透明的纱裙,也有中式对襟上衣、小管裤、皮鞋、迷彩服、贝雷帽、时尚T恤,更有鲜明中国戏曲特点的丑角服饰等。透过这些人物的服装所显示出来的符号指向,不仅在拼贴中建构、延展了原作的喜剧精神,拉进了与当代观众的距离,也在对原作的特定解读中,显示出莎士比亚的经典性、多义性。而这样的戏仿,使我们所看到的是,既“没有冲淡或丢掉莎士比亚,更增加了现实的亲切感”(刘厚生,1994:12-13)。在改编中,无论是导演还是充满朝气的青年演员,在把握莎氏喜剧精神的总基调中,以青春、亮丽的“游戏般地阐释”(冯大庆,2000:24-25),在莎剧与当代中国观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喜剧精神沟通的桥梁。
该剧几乎处处都贯穿了时尚、通俗的爱情隐喻。由此可见导演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大众化的爱情游戏氛围,从而使该剧在与莎剧的互动中显出了以拼贴为手段达到的对“爱”的互文性思考。按照巴赫金的理论,这种互文性表现为一种对话和交流,因为“任何一个表述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话(交际和斗争)中的一个对话。言语本质上具有对话性”(巴赫金,1998:194)。青艺的《第十二夜》正是通过拼贴、戏仿的互文性书写,以原作的内容、精神和喜剧精神为宗旨,以充分中国化、通俗化和游戏化达到了狂欢的大众娱乐效果。喜剧是以“幽默、讽刺、嘲弄,戏谑人们的错误、愚蠢、滑稽,以此达到欢乐的目的”(黄美序,2007:518),使观众在“充满生活情趣的意境中获得艺术欣赏的喜悦”(谭霈生,1984:189)。尽管青艺《第十二夜》的互文性被用来显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Kristeva,1986:36)以及“任何文本都是引语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Kristeva,1986:36)。但是,经过改编的叙事呈现出的仍然是处在与原作文本的交汇之中叙述路线,是在对原作创造性演绎的基础上,通过对原作流行化、时尚化、通俗化的拼贴来进行复述、追忆和重写,并将其呈现于舞台之上的。从该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本与舞台的转化中,经典与通俗、流行与过时、时尚与落伍、熟悉与陌生成为与莎士比亚相遇的关键词,由于该剧的拼贴、戏仿已使其自身成为一种既与原作喜剧精神相契合,也相当“中国化”的莎剧。
3.2 音乐拼贴:高雅与通俗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第十二夜》与莎剧原作中的情节大体一致。该剧中人物的爱情纠葛、三角恋爱与乐观、青春向上的戏剧精神较好地体现出莎氏原作中的喜剧性,而该剧正是通过音乐拼贴营造出原作的喜剧氛围的。正如布莱希特所说:“由于引进了音乐,戏剧的常规被打破了:剧本不再那么沉闷,也就是更高雅了,演出也具有了艺术性。”(贝·布莱希特,1990:309)作为一出爱情喜剧,《第十二夜》的音乐性不容忽视,原作中的悲剧性、喜剧性插曲和音乐评论,既参与了剧情,又成为推动剧情发展,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手段。(罗义蕴,1999:48-51)而且由于莎士比亚在该剧中赋予音乐以神奇的力量,那么在舞台的呈现中巧妙地植入音乐元素,进行拼贴和组合,包括大胆植入中国音乐、歌曲,甚至是通俗歌曲就成为该剧导演的首选。该剧以“现代流行的通俗歌曲作为全剧的音乐成分,借以表达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传达和表现出莎士比亚赋予此剧中音乐形象——民间的歌和诗的歌”(何炳珠、刘立滨,1994:67-71)。戏一开场,在强烈的迪斯科音乐声中,伊利里亚的少男少女在“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着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送你一枝玫瑰花,哪怕你长得不那么美丽”以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的演唱、京白中拉开了大幕。这一开场,既营造出原作的欢快的气氛,又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众爱情的宣泄模式。我们看到,在该剧的第一幕第一场中公爵说:“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尽量地奏下去。”(莎士比亚,中华民国三十八年:3)(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此时,中国人熟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如泣如诉的“化蝶”的旋律,从幕后传出,当公爵的侍臣说“她要像一个尼姑一样,蒙着面目而行,每天用辛酸的眼泪浇沥她的卧室……”公爵一厢情愿地说:“只有他充满在她的一切可爱的品性之中,那时她将要怎样恋爱着啊!给我引道到芬芳的花丛;相思在花阴下格外情浓”(莎士比亚,“中华民国”三十八年:3),这时《梁祝》的音乐再次奏响。在爱情这一主题中,拼贴通俗与高雅音乐尤其是通俗歌曲,成为该剧采用的主要手法。“音乐拼贴”旨在于调动中国观众的亲切感、熟悉感、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青年观众的共鸣,由于“选曲的对位、对味。苏芮的《牵手》、李宗盛的《凡人歌》、陈明真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张洪量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呢》、侯牧人的《小鸟》、潘越云和齐秦的《梦田》,戏谑式的,能够唤起童年、幼稚记忆,以及反讽的《丢手绢》《打倒列强》、《我是一头小毛驴》和《小小牧童》共同成为该剧的爱情宣言。这些具有一定政治色彩和“精选的流行歌曲穿越几个世纪的时空,准确地传达出爱情的苦恼和甜蜜”。(冯大庆,2000:24-25)同时,也在通俗化中诠释了莎剧的喜剧精神和爱情主题。
在原作的第二幕第二场的歌曲中有骑士、小丑和侍女的三人轮唱,“闭住你的嘴,你这坏蛋”,“明显是一种通俗歌曲”(罗义蕴,1999:48-51),要体现原作的通俗性,并对观众做中国通俗化的处理,在拼贴中选用中国通俗歌曲显然也能够鲜明地体现出该剧的喜剧精神与时尚性、通俗性。在这里,几个主要角色被演绎为当代中国式的带有积极意义的体现青春、朝气、现代、时尚的“爱情欲望的化身”式的追求纯粹、理想爱情的“时尚青年”,特别是对薇奥拉、奥丽维亚、费斯特小丑唱词的拼贴,显示了这一特色。例如薇奥拉、奥丽维亚深情地唱到: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我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
奥丽维亚所唱:
你的甜蜜,打动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样的闪烁、闪烁,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美可靠,外在美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
突然想爱你,在这温柔的夜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触动了我的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
以及薇奥拉和奥丽维亚的合唱:
爱到几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在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几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
而对小丑唱词的拼贴更让观众获得了一份亲切感。在原剧中斐斯脱小丑唱道:
你到那儿去,啊我的姑娘?听呀那边来了你的情郎,嘴里吟着抑扬的曲调。不要再走了,美貌的亲亲;……什么是爱情?它不在明天,欢笑嬉游莫放过了眼前,将来的事情有谁能猜料?不要蹉跎了大好的年华;来吻着我吧,你变十娇娃,转眼青春早化成衰老。(莎士比亚,“中华民国”三十八年:29-30)
而在青艺的《第十二夜》中则改编为费斯特小丑手持话筒的演唱: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
原作中小丑所唱:
当初我是个小儿郎,嗨呵,一阵雨儿一阵风;做了傻事不思量,朝朝雨雨呀又风风,年纪大了不学好,闭门羹到处吃个饱。娶了老婆要照顾,法螺医不了肚子饿。一壶老酒望头里灌,掀开了被窝三不管,朝朝雨雨呀又风风。(莎士比亚,“中华民国”三十八年:95-96)
在此处拼贴成为: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边,把利字摆中间。我是个小儿郎,做事不思量,任人来笑骂,把眼泪往肚里咽。……有了梦寐以求的金钱,是否就算是拥有一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
正如该剧导演所说,小丑的“白”和“唱”都是“利用傻气作掩护道出饱含深奥哲理与人生真谛的名言警句,这是他智慧的体现”(何炳珠、刘立滨,1994:67-71)。这里的歌唱既是叙事更是抒情,是深得中国戏曲唱之神韵的有意为之,通过通俗歌曲的演唱,将热恋中少男少女的心态以抒情的方式“戏剧化”(谭霈生,1984:248)了。在“爱情的幻想曲”中,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对人生的新评价是“爱情高于一切”(方平,1983:58)。在西方戏剧中“演员的表演艺术也以戏剧的绝对性为准绳。演员和角色的关系绝不允许显现出来,演员和戏剧形象必须融合成为戏剧人物。”(彼得·斯丛狄,2006:9)这就是代言体——演员化身为角色,但是由于青艺的《第十二夜》中的拼贴,很多角色的歌唱,已经不仅仅属于“戏剧人物”了,成了演员直接向观众说话的——叙事体,并与“当代的东西拼在一起”(孙惠柱,2006:223)。显然青艺的《第十二夜》在充分吸取了中国戏曲的表演特点,在突破了西方戏剧的这一限制上用足了工夫。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时而一体,时而分离。小丑以夸张的外部动作和类似于中国戏曲脸谱的舞蹈、化装,使“观客感觉到极明了之,观念极愉快之地步”(齐如山,2012:2-7),从而成为该剧的一个亮点,通过丑角的唱、做、舞使观众对这个“丑角”的聪明、机智、滑稽和幽默留下了深刻印象。诚如布莱希特所说:“如果歌词表现了多情善感的内容,那么音乐就应该要使观众能发现演员一本正经表演的事件原来是可笑和庸俗的。”(贝·布莱希特,1990:323)从拼贴所带来的舞台审美效果来看,此时青艺的《第十二夜》和莎氏原剧中的内容、情节和人物不只是作为作者的创造物出现的,他(她)都成功地成为表现自己思想、行动和情感的主体,由此,一个经过拼贴的全新的叙述者视角经过中国化、时尚化的改造,成功地营造出原作狂欢、幽默的喜剧氛围,因为“莎士比亚也有不少狂欢节本性的外在表现:物质和肉体基层的形象、正反同体的粗野言辞和民间饮宴的形象,……完全摆脱现有生活秩序的信念……它决定了莎士比亚的无所畏惧和极端清醒……这种积极更替和更新的狂欢节激情是莎士比亚世界观的基础”(巴赫金,1996:249)。青艺版《第十二夜》的互文与戏仿实现了“本文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合统一”(朱立元,1996:117),即相对于莎剧来说,该剧在内容与情节上既紧扣其喜剧精神,而形式又是全新中国式、时尚化的演绎。此时舞台叙述者的视角,着眼于调动中国观众的游戏记忆,嵌入当下时尚、通俗的卡拉OK歌曲,一曲曲深沉而又颇带生活哲理的通俗歌曲,成为表现消费社会人们向往纯真爱情的理想追求,其中也暗含了摈弃了道德伦理说教对爱情的偏颇理解,通过“莎士比亚‘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哈罗德·布鲁姆,2011:224)。我想,这也正是青艺版《第十二夜》的积极意义之所在。可以说,经过如此拼贴,该剧已经在中国化、时尚化的呈现中实现了与莎剧的复合统一,融合多种表演形式,实现了莎剧的当代转型。尽管经过拼贴的舞台呈现方式融入了中国元素和时尚元素,但毫无疑问,内容与情节的互文性也是该剧能够赢得广大观众喜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说互文性是“从本文之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本文而指向其他先前文本,这些文本把现在话语置入与它自身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文本中”(王瑾,2005:40)。那么青艺的《第十二夜》在拼贴中所显示出来的互文性,在将原作内容植入其舞台表演的过程中,不但与中国传统婚恋观有着某种契合,而且,既联系着中国当代社会的价值观、爱情观,又在文化、时空、高雅与通俗、经典与时髦上置换了先前的文本,但是这种“置换”却是以游戏式表演的中国化、时尚化、时髦感、时代感和流行性(相对于那一时代的观众而言),与当下青年的审美趣味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不乏无伤大雅的噱头,以幽默张扬向善、向美,批判、嘲讽的“拼贴”、“戏仿”作为旨归和特征的。该剧以再现“莎士比亚原作精神的新的演出方法”(吴光耀,2003:73-75)传达原作的内涵、诗意、青年的天性,以时空自由、节奏流畅的舞台调度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手法与通俗时尚的夸张表情、动作建构了莎剧原有的喜剧精神。同时,该剧的拼贴在互文性中显现出健康、积极向上的“伦理视点”。因为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延续性和时下社会人们所秉持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导演在处理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其道德价值判断取向时显得更为通达,故《第十二夜》通过对现实中扭曲的人性给予了善意的嘲讽和戏谑,使善良的世俗愿望、欲望和想象得以在艺术幻觉中得到替代和满足,进一步增强了该剧的喜剧效果。对于马伏里奥妄想获得绅士地位的幻想,包含了莎氏对自己及其父母“谋求贵族地位计划的嘲笑”(斯蒂芬·格林布拉特,2007:50-51)。这种“伦理视点”是通过一系列的游戏显示出来的,无论是“丢手绢”、击剑、骑马和黑屋子的游戏均显示了改编者对莎剧喜剧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改编中的放松心态,促使“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被移至另一系统中”(蒂费纳·萨莫瓦约,2003:5)。在该剧中,由于大量采用了拼贴所造成的戏仿与互文性,无论是喜剧氛围,人物情感,还是文化语境,都与莎作原剧形成了故事、情节相似度很高的一致性,即故事线索、情节发展、人物设置、矛盾的冲突与解决等基本要素,仍然保留在其中,但其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即舞台呈现方式在互文性中显示出解构中的综合建构。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历史,民风还是习俗,民族还是文化,时间还是空间,情感还是道德,并不是外在于文本的孤立的背景或不相联系的各种因素的简单叠加,而是“文本间性”在两种戏剧观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磨合。对原作《第十二夜》的舞台演绎,早已有大量的莎剧改编实践。而青艺版《第十二夜》的创编,又处在改革开放,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时期;其中既有对莎剧经典性的应有的尊重,又有强烈的创新渴望;既有话剧的叙事特点,又有戏曲的抒情因素;既有对原作喜剧精神的深刻理解,又有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自信;既反映了莎剧人文主义的总体精神,又有通俗化、娱乐化、时尚化的拼贴与戏仿艺术形式的建构,而上述诸种因素的集合,终于使该剧成为一部颇受老中青观众喜爱的一部莎剧。
3.3 语言拼贴:戏谑的当代性
对于戏剧来说“语言才是唯一的适宜于展示精神的媒介”(黑格尔,1981:270)。显然,青艺版《第十二夜》的导演深谙这个道理。由此,语言拼贴成为该剧的另一主要特征。“诙谐有两种:幽默和打趣”(西塞罗,2007:798),通过优雅迷人的幽默和嘲笑中的打趣,在语言方面,该剧进行了大量拼贴,并且由于这样幽默与打趣的拼贴造成了非常强烈的戏仿效果,例如:玛利亚恶作剧拉掉托比的裤腰带的戏谑“红花配绿叶”、“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除害)!”马伏里奥的“还是那只‘猴票’”,“麦当劳”、“汉堡包”、“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比窦娥还冤啊”;安德鲁·艾克契克爵士的:“我要是学过文学,那该多好啊”,“旱地拔葱”;费斯特小丑“戴着和尚帽不一定就是和尚”、“八月十五庙门开呀……”、“炸酱面”、“手机”;薇奥拉的一声“哇塞”,“我妈不让我随便拿人家的东西”、“我妈不让我跟别人打架”;马伏里奥的“咱们院里今年不贮存大白菜了,改存土豆了”、托比·培尔契爵士读“挑战书”时“还他妈是韩国话”、“降龙十八掌”;奥丽维亚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西巴斯辛的“七星大法”、“天马流星拳”,以及兄妹二人的“打花巴掌得,老太太爱看莲花灯”,等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戏谑式的幽默、打趣语言的拼贴成为拉近莎剧与当代观众的重要手段。语言特有的时代、政治、文化、大众和中国特色获得极强的喜剧和反讽效果,而“京白”的运用也增强了该剧的喜剧效果。该剧对原作语言的戏仿与拼贴,营造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生活和中国特色的美学色彩,使得原作与改编之间发生了多方位、多角度、多意蕴的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在发生互动关系的文本与现代舞台建构交错重叠的情况下,“用语言美产生独立的想象”(贝·布莱希特,1990:9),通过显示其文本性质的符号,内在的情节安排、话语也往往产生出与原作不同性质的喜剧效果和向当代观众更符合国情、民情、欣赏习惯,也更接地气的辐射能力,即经过拼贴与戏仿,其变异体不一定是以原作的语言、主题、艺术形式,甚至是调侃的“笑料”为载体的文本,它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写意的,它是造型艺术、音乐、舞蹈、当代语汇在舞台上的杂合。例如剧中采用戏谑式的“韩语”等“多国语言”朗诵“挑战书”的游戏场景,用大哥大通话的戏拟,赏赐“桑塔纳”、“换炸酱面”戏谑式的语言拼贴等等,都充分显示出莎剧改编所拥有的巨大空间,以及改编的当下意义。
《第十二夜》对原作的“吸收”和“改编”既是在文本之间,即文本必然的改编;也是在文本与舞台之间,即舞台的综合性呈现。通过拼贴、戏仿等互文性,确立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由莎氏原作改编为中国舞台上的《第十二夜》,它们之间经过拼贴与戏仿表现出来的互文性表明其喜剧精神可以在不同文化、民族、观众、语境或风格特征中有机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交融的审美共同体。对于表演(语言、服装、歌曲、音乐、舞蹈)舞台、语境来说,正如钱锺书先生引用《第十二夜》“If this were play’d upon a stage,I could condemn it as an impossible fiction”所指出的,“使此等事而在戏中演出,吾必斥为虚造不合情理耳”,“戏中人以此口吻论场上搬演之事,一若场外旁观之话短长,则看戏者即欲讥谈‘断无兹事’,‘万不可能’,亦已落后徒为应声,而大可怵先不必置喙矣”(钱锺书,1986:827-828),即通过对原作的戏仿,该剧在新的语境中形成了自己的意义潜势。在这个虚构的舞台上,蕴含着正解的表意、表情模式,观众反而会融入该剧所提供的情景之中,在“假”戏真看中获得审美艺术享受。在这种主观化、时尚化、通俗化的调侃与戏谑中建构了属于“他者”的喜剧性,从而在改变了原有文本意义潜势里,生发出新的潜势,并由此构成了其独有的互文性潜势。所以这种改编,通过其当代演绎,可以比较从容地以自己民族文化、戏剧的审美特点,甚至是导表演者的艺术才华,以及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与原作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使我们建构起当代中国观众观赏的审美视点。
4.如何戏仿:在文本与舞台之间寻找平衡
莎士比亚的五幕抒情喜剧《第十二夜》是其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在中外舞台上均有不少成功的改编和演出。正如世界著名导演彼得·布鲁克所说:“为了让莎士比亚戏剧在今天获得一种鲜活的生命,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人必须不拘泥于莎士比亚,将作品和他们身处的时代联系起来,然后再回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去。”(玛格丽特·克劳登,2010:144)因此,挑选这样一部经典名作进行改编,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当前改编莎剧,也是每一个莎剧改编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几经斟酌之后,改编者最后仍然选定了该剧,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有利于完整人物形象创造”(何炳珠、刘立滨,1994:67)。在充分想象和喜剧化的基础上,用我们熟悉的现代人的方式,挖掘作品中的喜剧元素,塑造人物形象,体现其性格特征,“从生活入手去理解角色、靠近人物,寻找准确的人物自我感觉,”(何炳珠、刘立滨,1994:67-71)用观众熟悉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张扬其中的喜剧精神,以求达到“情节借用是制造陌生化效果的重要手段”(陈世雄,1996:138)的艺术效果。这就涉及如何戏仿的问题。青艺的《第十二夜》的导演要求“在不损害作品的主体和精神中展开想象的翅膀”(何炳珠、刘立滨,1994:67),在表演中,演员需要“寻找十六七岁花季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自我感觉和特有的心态……初恋的感觉;寻找那‘追星族’们对自己崇拜的偶像的执着、真诚、奔放”(何炳珠、刘立滨,1994:70),“爱你没商量的纯情”(何炳珠、刘立滨,1994:67-71),可以说,导演的这一指导思想,是为该剧带来青春气息的根本原因。
戏一开场,强烈的迪斯科音乐和舞蹈就营造出狂欢的气氛,在伊利里亚那个不吃饭,光谈恋爱的地方,少男少女,贵族贫民在轻松热闹,欢天喜地中演绎了《各遂所愿》中的爱情。紧接着悠扬的小提琴协奏曲流淌出《梁祝》的爱情主题。随着剧情的展开,19世纪的口琴也不断奏出《梁祝》,奥西诺公爵在花园里的练的是太极拳,托比·培尔契爵士、费斯特小丑、安德鲁·艾古契克爵士和玛利亚以中国儿童相当熟悉的《丢手绢》做着欢快的游戏,公爵在花园里用大哥大传呼仆人,奥丽维亚吟诵着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当安德鲁·艾古契克爵士要占玛利亚便宜的时候,却被玛利亚用中国儿童熟悉的恶作剧,用膝盖狠狠地顶了裤裆一下。安德鲁没有沾到任何便宜:“哎哟,当着这些人我可不能跟她打交道。“寒暄”就是这个意思吗?”(莎士比亚,“中华民国”三十八年:8-9)这一让人熟悉的恶作剧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将浪荡子的无聊,被人愚弄,侍女的聪明、顽皮通过鲜明而富有喜剧性的动作把人物的精神面貌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喜剧效果非常强烈。玛利亚在观众的笑声中达到了对安德鲁这类先生们的教训与讥讽。显然,导演意在通过这样的戏仿,恢复“戏剧的原始目的”,(安托南·阿尔托,2006:61)在“娱人”——这个戏剧原始目的的作用下,其戏仿效果和互文性已经成为该剧的主要特征,而通过“将戏剧与通过形式的表达潜力,与通过动作、声音、颜色、造型等等的表达潜力联系起来”(安托南·阿尔托,2006:61),营造出特有的幽默、轻松、戏谑的喜剧效果。
如果我们单从故事和情节看,青艺版《第十二夜》与原作几乎毫无二致,以当下意义上的时尚化、通俗化使“演出具有为观众所熟悉的传统要素”(彼德·斯丛狄,2006:108)但从演出的效果来看,通过演员以当今少男少女戏仿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乐观精神获得观众的认可,则成为该剧改编成功的标志。我们认为,对有价值的西方文化的“热烈追求”(张隆溪,2004:13)已经成为中国导表演改编莎剧的持久动力。这种原著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互涉、交流,实质是通过整体与局部的间离所造成的戏仿效果在文本与舞台之间“秀”出狂欢化特征的互文性。该剧既在整体上是间离的,包括舞台设计、服装、人物表演、音乐、歌舞等;又在局部一再间离,从而不断强化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这种整体与局部的“陌生化效果是和表演的轻松自然相联系的”(贝·布莱希特,1990:197)。因为“莎剧总会有不同的连接点能让戏剧进入个体的生活。因此这些连接点必定是人性化的,也必定满含着现世的热情”(玛格丽特·克劳登,2010:18)。但却是以戏仿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以间离效果所显示的戏仿,例如薇奥拉说:“莎士比亚非要我去公爵的府中”以及唱完歌以后声情并茂的一声“谢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0),小丑手持话筒表面滑稽而内含深刻哲理与人生酸甜苦辣的演唱,马伏里奥把贮存大白菜改为贮存土豆的插科打诨等等。这种“音乐间离”、“语言间离”、“道具间离”、“观众与剧情的间离”、“演员与角色的间离”(陈世雄,2003:322)中的戏仿对营造舞台上的轻松、愉快也起到了不容忽视和令观众会心一笑的作用。再如奥利维亚在描述自己姣好的面庞时,以:“一款浓淡适中的朱唇两片;一款,灰色的倩眼一双,附眼睑;一款,玉颈一围,柔头一个,等等”。(莎士比亚,“中华民国”三十八年:20-21)在这一爱情宣言中,即使是间离效果的运用也恰到好处地使观众体会到莎士比亚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爱情,当奥丽维亚与薇奥拉翩翩起舞之时,后者顺理成章地以莎士比亚的名义朗诵出莎士比亚在该剧中爱情诗歌片断。这一间离手段的运用不但没有令观众感到意外,观众反而在一种游戏、愉悦的心态下对人物的矛盾心情,该剧的爱情主题有了更为深入也更加放松的理解。该剧“间离”方法的运用,使演员能够在戏仿中跳出角色和剧情,“以朗诵者的身份面对观众朗诵,然后再回到角色的自我感觉里”(何炳珠、刘立滨,1994:67-71),这种“Verfremdung表演上的‘间离’与episch结构上的‘叙述性’”(余匡复,2002:80)在熟悉中收到陌生化的效果,而“陌生化本是一种喜剧方法”(王晓华,1996:49)。借助“间离”,在互文性关系形成的双向交流作用下,原作中的喜剧精神得以通过现代的方式得到中国化的延伸和放大,即可能将观众带回到莎剧文本的“元语言”(弗兰克·埃尔拉夫,2003:56)中去,从而形成了原作文本与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舞台演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证明了“把高雅和通俗文化割裂开来的价值判断是似是而非的”(维克多·泰勒,2007:480),既在中国特色浓郁的舞台表演中,张扬了莎氏的喜剧精神,强调了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联,又在其游戏的氛围、戏谑的动作与语言中蕴含了积极向上,健康、愉悦的大众爱情主题,更在其故事、情节、结构中利用中国经典爱情音乐、通俗歌曲、俗语、俚语、笑话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合情合理、合剧情合原作精神,指涉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使莎氏的喜剧精神得以通过戏仿这种形式实现文本与改编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人文主义者所热烈歌颂的爱情更富于时代精神”(方平,1983:61)。该剧通过戏仿所建构的舞台呈现方式,既是莎士比亚喜剧精神的一次展示,又在这种展示之外明显呈现出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另一文本。二者之间的交叉与互构有利于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消除了因为时代、文化、形式所带来的陌生感,对莎氏剧作从人性普遍性角度的演绎,也会使观众产生更为放松也更为深刻地理解。通过戏仿,青艺《第十二夜》的舞台演出已经彻底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了。中国话剧舞台上《第十二夜》的中国元素,已经成功地在轻松、调侃、幽默、放松状态下以游戏心态,对爱情所坚守的理想主义,寻找真爱和两情相悦给予了喜剧性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青艺的《第十二夜》是对原作在民族化立场上的戏仿与互文、吸收和改编、解构与建构。它们之间的互文性主要表现在主题的沿用、故事内容、情节发展走向等的主要线索,以及其喜剧性上,而且无论是文本还是舞台,原作还是改编,都是以“寻找爱”、表现“爱”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而通过戏仿,青艺版的《第十二夜》则在“爱”的,既传统又现代的情感故事中衍变出更为民族化、时尚化、通俗化的形式。可以说,青艺版的《第十二夜》以强烈地青春气息和现代气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青年人对纯真美好爱情的追求。
5.大众化梦想:经典的当代演绎
对于莎士比亚之后的“显性伴随文本”(赵毅衡,2011:42),我们的改编不可能脱离副文本因素的经典意义。而由于“伴随文本的普遍性”(赵毅衡,2011:42),莎剧也被不断改编、上演。戏仿表现为一种“有意地漠然模仿”(胡全生,2002:128-129),而青艺版的《第十二夜》恰恰是以莎氏原作为骨架,以拼贴和戏仿为手段,以时尚、通俗、青春、欢乐、愉悦建构其艺术呈现方式,注入当代中国的元素,将其挪移到新的语境中。该剧的通俗性是对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共赏的艺术高品位追求,这需要“超常的想象力自由驰骋,才可能给观众营造一个奇妙的世界”(谭霈生,2005:306)。人物之间的调侃、幽默与“商业化的职业戏子”(洪衿,2005:139)对社会的讽刺形成了“互文的一面”(胡全生,2002:129)。该剧中的幽默、戏谑、调侃是形成戏仿的主要指涉方式,而正是中国化、时尚化的建构是形成这一差异性的主要原因。该剧中的反悖与戏仿,以“其他人物的言行”(W.C.布斯,1987:337)说明中国化、时尚化、通俗化这种演绎形式、喜剧效果触发点、情感宣泄,以及改编者的改编指导思想决定的舞台呈现方式,是已经顾及中国文化环境、当代社会语境、民族欣赏习惯,观众期待视野所特意为之的。
作为充满青春气息的《第十二夜》利用“情绪化表述”,人物的动作也在激起心灵反应中产生了“戏剧性”(陈世雄,1996:91)。一系列的动作拼贴与戏仿,在构建的幽默气氛中,既以熟悉打破陌生作为舞台建构的主要艺术手段,又以高雅、通俗的音乐和歌声,以及戏谑的朗诵、击剑、舞蹈等表现青年男女爱情中的误会、初恋,表演以“真实感和观众的艺术感受同步”(张殷,2008:416)为原则,以充分调动观众的想象空间,为青年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营造狂欢的氛围为创作原则。故此戏仿构成了“一个文本的内部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文本的关系的总和(引文、戏拟、转述、否定等)”(秦海鹰,2004:19-30),而这一点恰恰成为互文性的明显标志和《第十二夜》戏仿的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正好说明“互文性与源原文本互为悖反”(李玉平,2014:167),才使喜剧效应在跨越时空中不断得到放大。由于该剧对原作进行了“长衫子改夹袄——取长补短”,甚至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观众通过充满幽默、戏谑、调侃的台词和一系列令人发笑,有强烈喜剧隐喻效果的动作,领略到其间所蕴涵着的能指内质的“质料性”化为所指“‘事物’的心理表象”(罗兰·巴尔特,2008:23-25),促使所隐喻的健康欢快、明朗热情、高雅世俗、真挚和谐的爱情观得到了展现。从而也使我们通过舞台的反悖与戏仿能够追踪和摄取我们对生活的反映和对社会的看法。戏拟是对一篇文本改变主题但保留风格的转换,原作中的“风格”通过拼贴所达到的戏仿与互文,已经转化为中国式的幽默、戏谑、讽刺、纯真的爱情、善意的挖苦、捉弄与打趣了。通过对所有互文性现象的观察,我们发现“所有互文性现象在文中达到的效果——势必包含了主观性”(蒂费纳·萨莫瓦约,2003:83)。而由这种“主观性”所形成的审美效果,既在整体上解构了我们原有对莎剧的认知,又在拼贴、戏仿中再一次建构了莎士比亚的喜剧精神和对真善美的讴歌。
6.结语
我们认为青艺版《第十二夜》对原作的拼贴、戏仿与互文性显示了游戏式的狂欢,并通过这种狂欢化的游戏建构起当代中国舞台上的青春版《第十二夜》。该剧舞台建构的主体特征表现为,其主体和主旨在自然性的“乐感之乐”(刘小枫,2007:169)中,突出青春的调侃、幽默、戏谑和带有当代娱乐特点的“能指游戏”,并且以“秀”激发、暴露观众的欲望、向往、困惑,以及通过显在欢快感的获得,审美的挪移性满足和想象性建构走向经典(四川外语学院莎士比亚研究所,2011:71-79)。青艺版《第十二夜》之“秀”乃是莎剧现代性的鲜活证明,“莎剧的现代性就是包括后现代表现形式的改编”(李伟民,2013:4-9)。在拼贴、戏仿中呈现的互文性,改编者令该剧成功地给出了既有莎剧元素也是“时尚喜剧”、“都市戏剧”(傅谨,2002:191)的表达特征,而二者合一所体现出来的经典精神与商业价值、清纯与时尚并重的莎剧改编形式,使观众在充满诗意的欢快与幽默、调侃与戏谑中将莎剧与大众梦想的娱乐化链接在一起,从而成为当今中国话剧舞台上一部充满时尚动感,具有强烈观赏性和时代特色的莎士比亚爱情喜剧。
[1]Li Weimin.Shakespeare on the Peking Opera Stage[J].Multicultural Shakespeare:Translation,Appropriation and Performance,2013,10(25):30 -37.
[2]Kristeva Julia.Word,Dialogue and Novel[M].The Kristeua Peader,Toril moie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6.
[3]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M].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4]巴赫金.对话、文本与人文[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94.
[5]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49.
[6]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丁扬忠、张黎、景岱灵、李剑鸣,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7]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M].王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陈世雄.戏剧思维[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9]陈世雄.三角对话:斯坦尼、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322.
[10]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
[11]丁罗男.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284-296.
[12]方平.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3]弗兰克·埃尔拉夫.杂闻与文学[M].谈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7.
[14]冯大庆.丢呀丢呀丢手绢——看游戏的《第十二夜》[J].中国戏剧,2000(3).
[15]傅谨.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91.
[16]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M].黄灿然,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224.
[17]何炳珠,刘立滨.寻找体现莎翁剧作的最佳形式[J].戏剧艺术,1994(4).
[18]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洪衿.洪深文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9.
[20]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研究:叙述结构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1]黄美序.戏剧的味道[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518.
[22]李伟民.戏与非戏之间: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与川剧《马克白夫人》[J].四川戏剧,2013(2):4-9.
[23]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67.
[24]刘厚生.同莎士比亚开了一次亲善的“玩笑”——看锦上添花的新《第十二夜》[J].中国戏剧,1994(5):12-13.
[2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9.
[26]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25.
[27]罗义蕴.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评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又名《各遂所愿》及其歌[J].戏剧,1999(2).
[28]玛格丽特·克劳登.彼得·布鲁克访谈录(1970—2000)[Z].河西,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9]齐如山.戏中之建筑物[J].戏曲艺术,2012(1):2-7.
[30]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四五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827 -828.
[31]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一集·第五种)[Z].朱生豪,译.上海: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32]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19-30.
[33]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M].辜正坤、邵雪萍、刘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0-51.
[34]孙惠柱.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23.
[35]谭霈生.谭霈生文集(论文选集1)[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373.
[36]四川外语学院莎士比亚研究所.莎士比亚研究动态(2)[J].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学会/四川外语学院莎士比亚研究所、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1(1):71-79.
[37]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38]谭霈生.谭霈生文集(论文选集II)[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306.
[39]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0]王晓华.对布莱希特喜剧理论的重新评价[J].戏剧艺术,1996(4):49.
[41]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337.
[42]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M].章燕、李自修,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480.
[43]吴光耀.多样化:戏剧革新的必由之路[M].上海:上海戏剧学院霞光工程,2003.
[44]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98.
[45]徐国珍.仿拟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5.
[46]余匡复.布莱希特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80.
[47]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3.
[48]张殷.中国话剧艺术舞台演出史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416.
[49]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0]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第十二夜[VCD].北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2000.(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第十二夜》在中央戏剧学院1994届表演系毕业演出的《第十二夜》基础上进行了再加工。文中的所有对白、唱词均根据该光碟,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99年版演出记录。)
[51]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