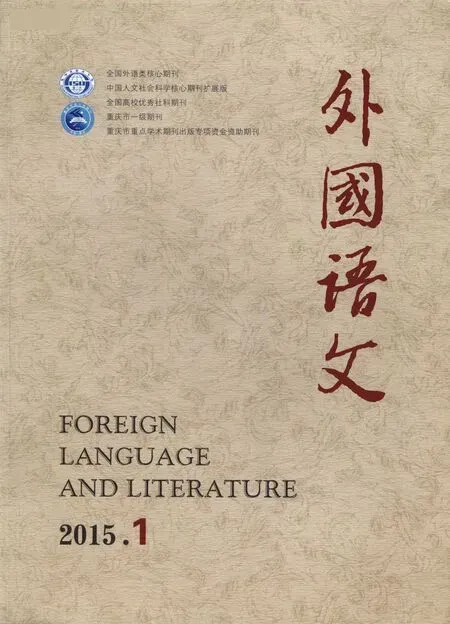赖特晚年对俳句的选择及其抗争意识的弱化——以《我本无名小卒》解读为基点
钟 蕾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重庆 400031)
1.引言
理查德·赖特(1908-1960)是非裔美国作家,其小说、诗歌创作均富有特色,影响颇大。他身后出版的诗集《俳句:别样的世界》(Haiku:This Other World,1998)收录了他生前创作的817首俳句,可谓盖棺之作,其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独特性都有别于小说,呈现出别样风景。从目前来看,人们对其小说研究较多,诗歌却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故而,他这一创作形式的成就有待学界去发掘,也应当受到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重视(Wright,1998:1)。郑建青教授编著的《理查德·赖特的别样世界——赖特俳句研究的多维视角》(2011)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研究赖特俳句的专集,“通过这个集子,读者能够体验和感知赖特俳句的诗性及其诗歌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研究者对赖特俳句的关注”(钟蕾,2012:172)。本文意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赖特的俳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以期从其他角度来探究和进一步认识这位美国黑人作家的美学观。
作为非裔美国作家,赖特同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接受和吸收了美国文化却又保留了非洲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这种双重文化身份是逐渐形成赖特文学创作中黑人美学观的重要源泉。曾艳钰(2004:68)将美国黑人美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原黑人美学和新黑人美学两个阶段,认为前者为后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赖特的黑人美学处于原黑人美学阶段,即作品主要的语言是情感性的,从早期完全被奴役、被虐待的状态开始觉醒,提出对白人压迫的抗争。他的黑人美学思想在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中已经奠定,主张对压迫的暴力抵抗。“在写于1927年的《黑人创作的蓝图》一文中,理查德·赖特指出:黑人文学创作应该从表现中产阶级黑人的理想和挫折转移到下层市民的愤怒和不满。一时间,赖特式的抗议文学大量出现,‘抗议’成为黑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黄晖,2002:23)因此,赖特的早期小说创作,充满了抗争的火药味,将他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年时,赖特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经济上也由于出版受阻而陷入困窘,赖特心中非常苦闷,想要寻求种族抗争的新出口。与此同时,布莱斯翻译的日本俳句在美国出版,标志着俳句作为一种诗歌形式被正式介绍给西方读者,赖特从朋友那里获得布莱斯翻译的日本俳句并仔细研读。他迷恋上了日本俳句并深受俳句中禅宗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不再像早期的小说那样充满火药味。(钟蕾,2014:128)
当然,“他并未在俳句中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个人主张,显然俳句这一新形式表现了他非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Hakutani,2014:101)。
本文从俳句的创作背景、文体形式及意境内涵三个视角来解析赖特一首著名的俳句《我本无名小卒》,意在阐释由于晚年四处漂泊、经济受困、疾病缠身,赖特为了排解心中反对种族主义的忧愁,故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形式——俳句。这种抗争形式与早年的小说不同,弱化了赖特早年强烈的黑人身份意识,空寂的禅意境暂时麻痹了赖特内心的苦痛。可见,这是赖特对种族主义的无奈抗争,“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2.俳句:晚年无奈抗争的选择
赖特一生都与种族主义作不懈的抗争,以期求得身份的认同。他早期的诗歌延续了小说中的暴力主题,比如诗歌“Rise and Live”,“Between the World and Me”等等,有时其中的暴力近乎自虐。可是期望破除种族主义、获得身份认同的梦想一直难以实现,无奈和困惑之下,他意欲寻求种族主义抗争的新出口,以期得到内心的平静。
受法国政府邀请,赖特和家人于1946年5月2日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他离乡背井,在法国度过了14年余生,于1960年去世。他觉得巴黎宁静美丽、有趣迷人,而纽约的生活不再令他满意。“我喜欢法国的生活方式。2000多年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确保了其美学价值的首要地位,并且赋予人们舒缓、宁静的生活节奏。”(Fabre,1985:127)赖特最初视法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度,尤其喜欢法国没有种族歧视的氛围,可他后来发现法国的自由并非如他想象,如果不贴上政治标签,他就不能在法国的报刊上发表文章。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使赖特内心感到强烈的不安和无奈:他既不是法国人,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的生活;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其身上刻着种族歧视的印迹,外来者的情绪油然而生。14年的异国漂泊使赖特自比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克洛斯·达蔓,无国籍、无身份也无根。这种尴尬让他尝尽身份认同的焦灼感,从而产生一种“无名小卒”(nobody)的悲伤。现代文学大师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似乎也被这种跨国从属关系和跨国身份所困扰,她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将巴黎视作自己的家乡。“斯泰因跨地域的身份宣称——这使她自己游离于一个摆脱不了的国家背景和另一个生活居住的大都市之间。”(Jahan,2009:23)当代诗人艾略特诗中如幽灵般的人物的谈吐举止,并非只是对以往英国和美国、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家诗歌元素的偶然组合,更是他跨国身份的写照。
晚年的赖特精神上受到跨国身份的困扰,身体上也饱受疾病的折磨。他身患阿米巴痢疾(amoebic dysentery),长期不规则发热、夜间盗汗、腹痛腹胀、脱水等各种身体的不适折磨着他。他所服药物的重金属成分对心脏危害很大,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由于身体虚弱,“特别是生病卧床,无力坐在电脑前写作的身体状况限制了他写作的长度,他只好把单词分解为音节以适应自己短促的呼吸”(Wright,2012:viii),从而俳句这一短小的文学形式成为当时赖特创作的最佳选择。同时,因出版受阻,他在经济上也遭遇危机。多种因素使他迷恋上了日本俳句,“他喜欢俳句的脆弱感——犹如蛛丝。同时,这种令人冥想的形式,让赖特在生命最绝望、最糟糕、最自我怀疑的那段时间获得些许内心的平静”(Rowley,2001:505)。
病魔折磨之下的赖特创作了4000余首俳句,其中817首在他去世后经整理出版。“在生命的尽头,赖特长期住院,无疑已经疲于反对种族主义,而是尽力逃脱种族主义的束缚,从纳奇兹到孟菲斯,从芝加哥到纽约,最后于1947年离开美国住在法国。或许在俳句的世界中赖特才寻找到精神世界的宁静。”(Kodama,2011:128)正是在这种流落异乡、病魔缠身、经济受困的尴尬处境中,赖特已不再像早年那样用雄浑有力、精气充沛的长篇话语来从事文学创作。他早前盈腔的愤懑,对种族主义积极的抗争,只能无奈地由适合其当时抗争形式的短小凝练的俳句所取代。
3.俳句:作为黑人心声的另类表达
日本俳句被誉为世界上最短的格调诗,源于奈良时代的和歌(Waka)。俳句分为长歌和短歌,最早是31个音节,五行,5-7-5-7-7的节奏,后来,长歌逐渐消失,在明治时代短歌演变为现在的俳句。传统的日本俳句在形式上通常有如下特征:首先,整首诗只有十七个音节,5-7-5三个诗行。从形式上看,5-7-5十七个音节的诗歌并不都是俳句,“俳句内部结构的核心部分要有停顿/切语,它将俳句中的意象形成内部的对比”(Gurga,2011:170)。切语前的一部分作为基体,后一部分作为叠加。其次,俳句中有表时间的季语,季语是俳句中的重要组成因素,它如同诗歌中的诗眼,是理解俳句的关键所在。第三,俳句以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描绘一个独立的事件。最后,俳句通常使用直白而非比喻的意象。
赖特研究日本俳句,并尽量在俳句创作中保留日本传统俳句的形式,同时又融入西方诗歌元素,以短小、精炼的形式表达他无奈抗争种族主义的黑人美学。下面分析赖特的一首著名俳句《我本无名小卒》的形式特点:
I am nobody:我本无名小卒:
A red sinking autumn sun那轮沉落在秋天的红日
Took my name away.(Ⅰ)掠走了我的名字。
首先,这是一首形式上典型的俳句,它采用5-7-5三段韵17音节。这种短小的形式,无规律的押韵由于受字数和音节的限制,在描写实物时简单、凝炼;表现感情时含蓄、温婉,这也符合禅宗的特点:凝炼、含蓄。
首句“I’m nobody”在许多经典诗歌中出现过,由于形式的不同,表现力也不尽相同。《奥德修斯》和《伊里亚特》被合称为《荷马史诗》,故事中讲述到当独眼巨人残杀奥德修斯的队友波吕斐摩斯时,奥德修斯把没有勾兑的烈性葡萄酒给他喝,并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没有人”(ουτι),“My name is nobody”,成功欺骗了独眼巨人,帮助队友逃脱了独眼巨人的魔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在她的抒情诗“I’m nobody,who are you?”中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表现自己隐世脱俗,与世无争,冷眼看世事的内心状态。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则在“Tulips”中用自白的方式表达自己心灵的呼喊,一句“I am nobody;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xplosions”将诗人的情感穿梭于“自白、自我、自杀”之间,并将罗伯特·洛威尔所开创的自白派诗风推到顶点。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飞翔号”大帆船》这首诗中也用到“I’m nobody”,该诗清晰地表达了水手Shabine的身份困惑和强烈的民族感:
I’m just a red nigger who love the sea,
我只不过是个热爱大海的红脸膛黑人,
I had a sound colonial education,
我曾受过良好的殖民地教育,
I have Dutch,nigger,and English in me,and either I’m nobody,or I’m a nation.
我身上流着荷兰、黑人和英国人的血,于是,要么我谁都不是,要么就是一个国家。(杰汉·拉马扎尼,2013)
“他把在加勒比海盆的冒险远航,用标准的英语并以换行押韵的抑扬格五音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杰汉·拉马扎尼,2013:76)诗歌在nobody和nation上重读,用 either...or...连接、对比,突出了水手Shabine的内心挣扎,表现其强烈的民族感。
无论是奥德修斯的长篇史诗,艾米莉·狄金森的抒情诗,还是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白诗以及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抑扬格五音步诗都用到过这句“I’m nobody”,可见该句的含意是多重而深刻的。然而,赖特这首诗受日本文化影响,采用传统俳句5-7-5的形式,它既没有长诗的强烈抒情和自白,也没有明显的韵脚和对比来表现类似于德里克·沃尔科特诗中水手那般鲜明的民族感和强烈的对抗感,当然更不及赖特早年的小说那样犀利,运用复杂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相应的思想、感情,积极表现黑人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它只是在短小、凝练的俳句形式中微弱地表现诗人无奈的种族主义抗争。
其次,“俳句中常使用切字,有缩短和统一的功能。赖特用英语标点符号(感叹号、冒号和逗号等)替代切字,比如常用冒号替代切字,用于表达一种情感或悔恨”(Hakutani,“Introduction”,10-11)。这首诗里的冒号表切字功能,把不同质的两种物体分开。诗歌的第一句作为基体:失去自我的静态的人,第二句是并置的意象:动态的秋日,两者一静一动,形成巨大的张力。“在这个三段式诗形中,上句中的/I(我)和下句中/my name(我的名字)被描写自然界的夕阳的中七从句式上切割,从而消解了语义的连贯性,带来的停顿感就如同山水画中的留白,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并在秋天残阳投射出的幽玄禅境中感受自然的神秘和人类的渺小!”(李怡,2010:136)意象的并置创造出断裂,从“我”(I)这个意象到“沉落的红日”(red sinking sun),这两个意象转换突然而意外,然而第三段中的动词“夺走”(took)迅速将断裂缝接起来,语意得以补充。这种意象并置带来的语意断裂和它对不可知事物的突然揭示能够在读者身上产生深刻的反思,让读者不禁感叹赖特寻求身份认同的无奈和无助。
此外,诗歌中有表时间的季语:“秋天”,诗中秋日象征西方世界,作者赋予秋日动作,即“沉寂”(sinking)和“剥夺”(took),拟人化的手法暗示象征白人社会的秋天剥夺了代表黑人身份的我,在白人社会中无法得到身份认同。“赖特也许将秋天的红日象征西方世界——美国——它剥夺了诗人的姓名和身份,或许就是非洲黑人的姓名和身份。”(Kiuchi,2011:34)在这首俳句中,即将沉寂的秋日与最为无名小卒的我形成强烈的对比:我是被动、静态的无名小卒;一轮沉寂的秋天的红日发出动作,剥夺了我的身份,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凸显了这一对矛盾,即我代表没有自我身份的黑人,即将沉寂的秋日象征诗人心中即将陨落的白人文化。黑人的身份被白人剥夺,不为白人承认。“动词took字面上指落日对叙述者发出的暴力行为,其实隐含着南方对黑人的暴力行径。”(Morgan,2011:112)在诗人眼里,这个季节的红日是“沉寂”的,不是上升的,表达了诗人对象征美国种族主义的红日将要陨落的信心。诗人借物吟志,表达他改善和解决美国黑人种族问题的渴望,希望黑人能和谐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过上与白人一样的生活。
诗中的冒号和季语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它们提示读者,秋天作为季语,本应该是个收获的季节,然而“我”(I)却被这个季节的红日剥夺了身份。第一节以“我”的口吻叙述,是主体性的表现,而在表切字功能的冒号之后,迅速转向自然界客观事物的描写。沉寂的红日剥夺了我的主体特征,“赖特在诗中既是客体又是叙述者,诗歌描述了诗人名字被剥夺和主体性被极度压抑的状况”(Hakutani,2014:138)。
总之,俳句的短小形式,意象的叠加并置、使用切语及运用季语的写作手法不仅帮助赖特书写其种族主义抗争的无奈,也引导读者感受诗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渴望,在意象并置的断裂中体会诗人压抑的情感。赖特的一生都从事激烈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晚年感到身心疲惫,接触到俳句这种短小而细腻的创作形式,才找到了抗争的一种新的出口。赖特期望利用这种短小、凝练、温婉的俳句形式来构建一个种族平等的想象中的精神世界。
4.俳句:种族主义的镇痛剂?
赖特晚年迷上俳句不只是因为俳句的形式符合他气若游丝的身体状况,更是因为俳句中的意境、禅宗的教义让他心里能够获得些许的宁静。禅宗是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四大宗派之一,在中国形成后传入日本。日本俳句的内容和意境中贯穿禅宗的思想,要理解俳句,就应体验禅宗的“顿悟”(mu/nothing)。“这种顿悟就是空无的状态,空无的实现以去除主体性为前提。”(Hakutani,2014:9)禅宗倡导sabi和wabi,sabi指平静的美、孤独美,wabi则指从贫寒中产生的美学欣赏,是贫寂之美。禅宗以朴素的、空寂的自然状态追求淡泊、贫寂的生活情趣,推崇人的顿悟,尤其是六祖倡导的“顿悟”法门。这种顿悟不是冥思苦想,而是整个身心挣脱尘网束缚、万念俱空的瞬间彻悟。
赖特晚年寄居法国,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这是一种逃避的表现?还是一种心灵平静的满足感?晚年的赖特是孤独的。在他的抗争中,平生夙愿无法得以实现;赖特是贫寒的,生活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因为晚年的创作不如早年有丰厚的经济回报;赖特也是空无的,自我身份既无,则完全倾向于人与自然融合的顿悟。赖特躺在病床上,用清净的禅心来细致地体察和感悟自然万物中蕴含的闲寂幽远的禅意,并把这些空灵的美感和悟化的意象视为心灵痛苦的解脱。下面继续来看那首俳句:
I am nobody:
我本无名小卒:
A red sinking autumn sun
那轮沉落在秋天的红日
Took my name away.(I)
掠走了我的名字。
传统的俳句避免以人为中心来表达情感,而是竭力以自然为中心。长诗易于说理,而俳句则尽量避免说教的语言(Wright,2012:252)。在这首俳句中,赖特虽以第一人称“我(I)”开启诗行,似乎突出了“我”的主体性,但当读完此诗,却发现“我”被剥夺了主体性,是被去除了主体性的“无名小卒”。那么“我”是如何成为“无名小卒”,失去主体性的呢?
诗人使用感官形容词“红”(red),感官动词“沉落”(sinking),赋予太阳生命力。继而,“我”(I)的身份被红日剥夺,成为无名小卒。这种没有身份认同,失去身份的“我”最终也变成了没有思想、没有血肉的“物”。在“我”(I)失去名字的瞬间,实现了空无(nothing/mu),最终实现了我与自然的统一。这象征着赖特俳句时刻的到来。“俳句时刻可被定义为人与物体结合的瞬间,最终人变成了物,实现了人世间永恒的普遍真理。”(Morgan,2011:92)实际上,这种俳句的精髓就在于人类去除主体性,通过沉思,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这个角度上看,诗人表现了他极其无奈的内心世界。因为这种主体性一直是诗人追求的身份认同,然而在接受了禅宗思想,经过沉思、得以顿悟之后,却又接受这种无我(non-ego)的心境。这种“无我”不是诗人的主动选择,而是被象征白人统治的秋天的红日夺去,种族主义中的被迫认同。
诗歌中的“我”(I)处于静态,一个“无名小卒”(nobody)。本应是静态的秋日却发出了两个动作:“沉落”(sinking)和“夺走”(took)。动静之间的张力随着太阳的落下而融入黑暗中,预示着人世的喧嚣、命运的沉浮与落日余晖一同消失,消逝在黑暗中。于此同时,赖特心中的种族主义抗争意识受到禅宗教义影响,他体会到在禅宗的教义中才能获得心灵的些许宁静,人与自然才能真正和谐统一。Kodama(2011:128)认为:“理查德·赖特并非皈依佛教,而是从布莱斯的俳句选集中深刻地理解了禅宗思想,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晚年卧病在床,他显然无力也疲于与种族主义做斗争。也许他所能找到的最后一片心灵的净土就是俳句的世界……但是他仍然无法摆脱他的过去。”从Kodama的评述中我们也能读出赖特无奈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沃尔科特诗中的水手Shabine也在寻求身份认同,与赖特有着共同之处:都是黑人,均打上了民族的印记,同时都想获得白人社会的肯定。诗的最后一句“要么我谁都不是,要么就是一个国家”所提出的两个选择,强烈表现了诗人的身份焦虑和民族抗争意识。不同的是,在赖特的这首俳句中已无强烈的民族抗争情怀。诗人首先用“我本无名小卒”定下了基调,即一种无根性。表切分功能的冒号突出了后面两行诗句,解释了“我”被剥夺身份,无根性的原因。其中并没有直接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也没有豪言壮语的抉择,而是用秋日这一意象象征白人社会,掠夺我黑人的身份,“我”却束手无策。秋日的主动和“我”的被动之间的强烈对比再次表达了诗人的被动和无奈。
同时,“nobody”这一称呼不仅是困扰赖特的符号,也是“沃尔科特所纠缠的那个绰号,老谋深算的奥德修斯(Odysseus)用到过;同样地,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也都用到过;诗中的‘我’是颇具密码暗示意味的,这个假定的‘谁都不是’实际上却包含了多种‘是’(译注:即身体的混合性)——由荷兰、非洲和英国的祖先们所给予的遗传学角度上的想象中的身体,由这个诗中人物所包含的不同民族和种族文学的身体”(杰汉·拉马扎尼,2013:76)。以上这些诗中的“nobody”,或是打着幌子欺骗独眼巨兽、逃脱险境的称呼,或是孤独隐于世的自我表征,抑或是内心挣脱的自白,都突出了“我”①本文中所出现俳句除标注外均为作者中译。的主体性。而赖特由于受禅宗的影响,深知只有当自我的主体性去除时,才能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俳句《我本无名小卒》中,赖特的存在与他的名字一同消失,这是一种无言的状态。诗歌中的语句不是为了表达意义,而是为了清除我们与实物之间的障碍,在寂静的禅意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然而,同时升起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即如赖特真的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果真淡泊于种族主义的抗争了吗?对于他一生的夙愿和作为一个具有良知的黑人作家而言,他真能通过俳句的禅宗教义来达到心灵的平静吗?真的能治愈他无身份和终身为之焦虑的痛苦?或许,我们只能说,这只是赖特黑人美学观的一种转向。这种转向当中除了包含无奈成分,可能更多的是抗争的弱化,而绝不是现实和文学中存在的种族主义的镇痛剂。
5.结语
俳句写作是为内心需求找到一种新的、有效的表达方式。赖特晚年选择俳句,虽有渴求万物和谐、人与自然统一的心愿,然而却也属无奈之举。赖特学习俳句,并将之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俳句既继承了日本俳句的禅宗意理和简洁含蓄的形式,又对其进行跨国文体的创新,最终将东方禅宗思想与西方现代生活融合起来。他的俳句代表作《我本无名小卒》抒发了诗人抗争命运的挣扎,同时也有怀旧的叹息,其虽为禅意之下人生的顿悟,但更是一种真正的绝望。诗人意识到当星光和意义同他的名字一起消失时,个人将不能诠释自己(Fabre,1985:52)。留给他的,只有在贫寒、孤寂的禅境中体察自己的无根性。青壮年时期赖特运用小说把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的赖特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受禅宗的影响,他的创作不再像早期小说那样充满火药味,而是采用俳句短小、凝练的形式,宁静、温婉的禅意来表达其无奈的反种族主义思想。诗人并非放弃了种族主义的抗争,而是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另一种抗争的方式——俳句。这确实体现了赖特黑人美学观的某种程度上的弱化,但终究不是消失。
[1]Fabre,Michel.Wright’s Image of France[M]//The World ofRichardWright.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5:127.
[2]Fabre,Michel.From Revolutionary Poetry to Haiku[M]//The World of Richard Wright.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5:52.
[3]Gurga,Lee.Richard Wright’s Place in American Haiku[M]//Jianqing Zheng.The Other World of Richard Wright:Perspectives on His Haiku.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1:169-180.
[4]Hakutani,Yoshinobu.Wright’s Haiku as English Poem[M]//Richard Wright and Haiku.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14:89-107.
[5]Hakutani,Yoshinobu.Introduction[M]//Richard Wright and Haiku. Columbia:University ofMissouriPress,2014:1-16.
[6]Hakutani,Yoshinobu.Wright’s Haiku and Africa[M]//Richard Wright and Haiku.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14:131-141.
[7]Jianqing,Zheng.The Other World of Richard Wright:Perspectives on His Haiku[M].Jackson,MS.:UP of Mississippi,2011:xi.
[8]Jahan Ramazani.A Transnational Poetic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23.
[9]Kiuchi,Toru.Zen Buddhism in Richard Wright’s Haiku[M]//Jianqing Zheng.The Other World of Richard Wright:Perspectives on His Haiku.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1:25-42.
[10]Kodama,Sanehide.Japanese Influence on Richard Wright in His Last Years:English Haiku as a New Genre[M]//Jianqing Zheng.The Other World of Richard Wright:Perspectives on His Haiku.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1:122-133.
[11]Morgan,Thomas L.Inverting the Haiku Moment Alienation,Objectification,and Mobility[M]//Jianqing Zheng.The Other World of Richard Wright:Perspectives on His Haiku.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1:92-121.
[12]Rowley,Hazel.Richard Wright:The Life and Times[M].New York:Henry Holt,2001:505.
[13]Wright,Richard.Haiku:This Other World.[M].Yoshinobu Hakutani & L.Robert.Tener.New York:Arcade,1998:1.
[14]Wright,Richard.Haiku The Last Poems of an American I-con[M]//Yoshinobu Hakutani& L.Robert Tener.Arcade,Publishing:New York,2012:viii;252.
[15]黄晖.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理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2(3):23.
[16]杰汉·拉马扎尼.周航译.诗歌、现代性和全球化(上)[J].世界文学评论,2013(16):76.
[17]李怡.论理查德·赖特的俳句——一种对日本俳句继承与改良的文学新实践[J].当代外国文学,2011(3):133-142.
[18]钟蕾.一蛙激起千层浪 评理查德·赖特的别样世界——赖特俳句研究的多维视角[J].外国文学研究,2012(4):170-172.
[19]钟蕾.火车意象的二重奏:理查德·赖特俳句中的黑人美学与和谐生态[J].外国文学研究,2014(4):127-133.
[20]曾艳钰.论美国黑人美学思想的发展[J].当代外国文学,2004(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