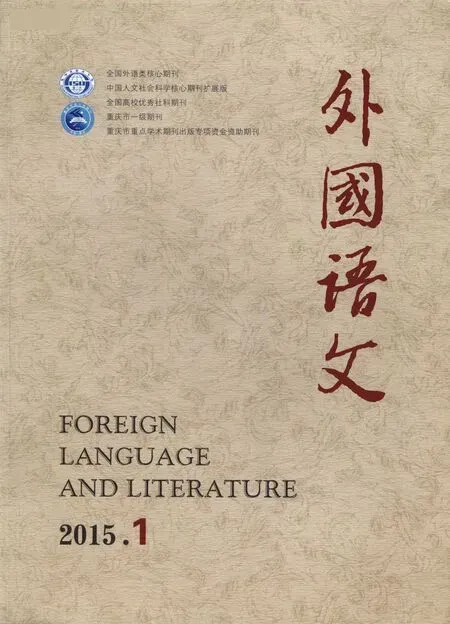奥德修斯之旅:《六月庆典》的文化隐喻
田 静
(重庆理工大学 语言学院,重庆 400054)
1.引言
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以一部《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自《看不见的人》出版后40余载,除了发表一部论文集与短篇小说集以外,埃利森并无长篇小说问世,他的文学创作能力曾因此备受质疑。1999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艾里森的《六月庆典》(Juneteenth),这部作品几乎凝结了埃里森40年的辛勤创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Saul Bellow)评论说,“拉尔夫所涉笔的内容,无人可以匹敌。他的作品没有人可以写出来——作为一个作家,这是一项值得称颂的荣事。”(拉尔夫·埃利森,2003:2)美国文学评论界认为:“如果将《看不见的人》看作一部美国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么,《六月庆典》就是一部美国的《尤利西斯》。”(拉尔夫·埃利森,2003:10)《六月庆典》的出版及其所获的褒奖不但有力地回应了外界对埃利森的质疑,而且超越了《看不见的人》所关注的主题。《六月庆典》通过讲述一个黑人牧师与白人养子的恩怨情仇,来隐喻黑人种族与美国民主的关系。如果说《看不见的人》是一部黑人寻求身份认同的史诗,那么,《六月庆典》则是关于一个民族过去与未来命运的历史寓言。主人公布里斯(Bliss)是一个白人妇女与一个黑人所生的孩子,他的母亲诬陷孩子的父亲是黑人希克曼(Hickman)唯一的兄弟巴布,巴布被判处了绞刑,希克曼的母亲也因此在悲伤中死去。希克曼克制着悲痛将这个孩子养大,希望爱能化解种族间的仇恨,但是布里斯却逃离了希克曼,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桑瑞德(Sunraider)。《六月庆典》以新的视角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关系、美国民主、种族融合、宗教与政治等主题做了深刻的探讨。在《六月庆典》中,埃利森广泛汲取非裔美国民间文化遗产和美国主流文学传统,神话、民俗、象征、仪式等文学原型与意象成为重要的表意手段。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指出:“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形象。是可供人们交流的象征。”(诺思罗普·弗莱,2006:142)原型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神话,神话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学经验的一些最基本的因素,神话是人类共享的心理结构、精神源泉和集体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流模式,甚至是一种认知图式。埃利森通过对神话的使用,揭示不同种族在文化上共有的深层结构,探寻解决种族问题的途径,从而反思美国种族关系与民主的未来。
2.奥德修斯的漂泊
埃利森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认为:“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发现《荒原》和《尤利西斯》中,古代神话和仪式被用来为素材提供形式和意义;我发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神话和仪式,同样可以被运用,……仪式成了社会形式,艺术家的作用就是识别它们并把它们提高到艺术的水准。”(Ellison,1964:174-175)事实上,在1937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埃利森大量研习了艾略特、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庞德、海明威、福克纳、赖特等作家的文学写作技巧。神话、传说、仪式等成为埃利森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幼年时期,布里斯(欢快,幸福之意)与希克曼快乐地生活在南方;在他成年的时候,因听信一个白人妇女说他是她的孩子,布里斯逃离了希克曼,迷失了自我。希克曼与布里斯的故事模仿了《圣经》原型:伊甸园—诱惑—堕落。同时,布里斯的自我寻求之旅,希克曼对布里斯的拯救也源于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故事。诚如哈佛大学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家小盖茨所指出:“像艾里森和里德这样的小说家创造的文本都是双声的,他们的文学传统既包括白人的也包括黑人的,而且是从黑人方言传统提升出来的比喻模式。”(Gates Jr.,1988)从早期黑人踏上北美大陆这块土地开始,黑人一方面与自己的母文化疏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挣扎中求生存,接受新的语言与文化,面对这种“双重传统”,形成了黑人独特的“双重意识”。
希克曼与布里斯的故事隐喻了黑人与白人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在埃利森看来,“美国南方不是由奴隶制的历史,而是由后重建时代以及这个国家对种族隔离法案(Jim Crow)的态度所定义的。”(Warren,2005:190)《解放宣言》所宣称的平等被种族隔离法所出卖,《解放宣言》并没有为黑人带来真正的自由,不过是有形的铁链换成了无形的枷锁。在六月庆典上,希克曼讲述了黑人在美洲大陆的遭遇。“历史告诉我们,所用的铁锁链和船只都不配用来运猪,……因为猪的成本太贵,不像黑人那样还允许一定数量的浪费和死亡。”(拉尔夫·埃利森,2003:120)黑人在北美大陆的经历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历史,遭受了约拿人被吞入大鱼腹中的痛楚,品尝了加沙的参孙被毒瞎双眼的无奈,经历了被捆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挣扎。“这是噩梦、劫难、奴役、痛苦、迷惘的世界;人类的想象尚未对之产生影响,像城市、花园这样的人类愿望的形象还未牢固地确立以前的世界;这个世界堕落、徒劳,处处是废墟和墓穴、折磨人的刑具及替愚蠢树碑立传。”(诺思罗普·弗莱,2006:208)黑人族群的经历如同穿越漫长的地狱,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才换来了些许自由,却不得不以“双重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创造的世界。黑人在美洲大陆的历程如同奥德修斯在大海上的遭遇。奥德修斯先后遇到凶猛残暴的波吕斐摩斯巨人、精通魔法的喀儿刻和美艳的塞壬女妖,其征程布满荆棘。黑人从非洲部落横穿大西洋到北美大陆,从奴隶制到南方种植园,从解放到重建,从向北方移民到城市化的推进,黑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出埃及记”。在埃利森看来,种族主义如同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卡德摩斯(Cadmus)播撒的龙齿(意为不和的种子),是美国民主最大的威胁。希克曼提醒黑人记住自己族群的苦难经历,并不是要播种仇恨的种子,而是表明这种苦难是这个民族不可抹杀的历史记忆,黑人在这片土地上倔强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也应该受到上帝同等的眷顾,“他们可以讥笑我们,但不能否认我们。他们可以诅咒我们,杀害我们,但不能毁灭我们。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来自这片土地,我们的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泪浇灌了这片土地。”(拉尔夫·埃利森,2003:131)如同犹太人的逾越节,六月庆典是南方黑人庆祝解放的盛大节日,这个节日对黑人而言,其意义如同《独立宣言》于美利坚民族一样。但是在埃利森看来,六月庆典不过是名不副实的仪式,虽然名义上废除了奴隶制,但是隐形的种族主义却无所不在,六月庆典不但应该成为反思历史的契机,而且也应该成为黑人再次觉醒的契机,同时也是美利坚民族自我救赎的契机。
布里斯既是一个白人,也是一个黑人。埃利森以此警示如果黑人的命运始终在漂泊,白人同样会迷失自己;如果不能正确对待黑人的遗产,美国的未来就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布里斯逃往美国北方去寻找冒险、爱情以及梦中的家园。反讽的是,种族主义在北方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北方如同奥德修斯所面对的大海,虽波澜壮阔,却也暗流涌动。布里斯根本不知道要寻找的母亲是谁?要追寻的白人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他试图忘记自己从哪儿来,却不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向何处?布里斯迷失在大都市的喧嚣之中,他先是以电影制片人和骗子的身份出现,其后又成了支持种族迫害的参议员。布里斯希望抹去过去的经历。吊诡的是,黑人文化中的民间传说、黑人教堂中的应答唱和、爵士乐的即兴复段、低音贝斯等技巧早已经渗透到布里斯的血液里,被布里斯运用得炉火纯青,成为他在北方生存的重要工具。“朋友们,公民们,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在我们这块高尚的土地上,记忆就是一切:是试金石,是威胁,是指路星。我们去往何处取决于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来自何方取决于去往何处——可还是有所区别的。”(拉尔夫·埃利森,2003:13)
布里斯自小在黑人的文化环境中长大,谙熟黑人的布道和即兴演说。“要记住就是要遗忘;要遗忘就是要有选择、有创造地记住,这由我们梦想和誓约的本质所决定的。是的,让我们记住,在这片国土上,创造就是毁灭。”(拉尔夫·埃利森,2003:16)布里斯布道式的即兴演讲、对美国价值观似是而非的阐发、对梦想自相矛盾的确认与否定、明快的节奏、同语反复与层层递进的表述分明就是黑人的喻指方式。言此及彼是黑人基本的语言技巧和生存策略,是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矛盾心理的集中体现;对白人文化的拒绝与改写,对黑人传统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愫,社会压迫造成的情感冲突与自我实现的迷茫,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了布里斯的身上。在埃利森看来,布里斯的遭遇,也是黑人族群的遭遇。
在《六月庆典》中,埃利森把西方文学经典的奥德修斯与黑人的民俗文化融于一个黑白混血的主人公身上,揭示了黑人族群艰辛的生命历程。自从黑人踏上北美大陆这块土地上开始,黑人文化就成了这个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利坚民族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多样性与混杂性的,所以一个白人或多或少也是黑色的。埃利森以此表明黑色与白色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肤色之名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六月庆典本是庆祝黑人解放的重大日子,但是黑人能够庆祝什么呢?埃利森以此隐喻黑人族群漫长的解放之旅,同时触及了美国社会一个敏感而又深刻的问题:为什么黑人忍辱负重为白人养育了孩子却换不回感激和同情?难道只是因为肤色的差异?还是文化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仇恨?还是经济与政治利益所驱使?希克曼与布里斯的故事实际上再现了黑人在美国的历史遭遇:为什么黑人为这个国家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总是被视而不见?为什么黑人所为之奋斗、付出生命代价换取的梦想却最终将他们抛弃?尽管如此,埃利森并没有把《六月庆典》写成像《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以及《土生子》(Native Son)那样的抗议小说,埃利森拒绝对种族关系作任何本质主义表现。埃利森既反对黑人妥协主义,也反对黑人激进主义,同时也强烈批判种族主义。在埃利森看来,任何抹杀黑人历史的行为都是对美国自由民主价值的否定;如果不能正确对待黑人的遗产,美利坚民族将永远漂泊在无边的海上。
3.奥德修斯的归航
与其说布里斯在北方想要寻找自己的母亲,毋宁说他想要寻找自己的历史文化之根。布里斯的漂泊不但没有为自己找到理想的精神家园,而且还招来了杀身之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刺杀他的正是他与一个黑—白—红混色姑娘热恋所生的孩子。以煽动种族主义起家成为参议员的布里斯终食自己种下的苦果。“布里斯决定成为桑瑞德参议员是对个人历史的强烈否认。更严重的是,这一行为否认美国经验中的黑人性与美国文化的关系,它拒绝接受美国过去历史的复杂性。”(O’Meally,1980)当布里斯斩断他与黑人父亲联系的时候,当他背叛养育他的黑人文化的时候,他也就没有了历史,成了无根的浮萍。纯洁的种族梦想不过是一个西西弗斯神话(Sisyphus),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纯正的白人文化,也没有一部纯正的白人历史。埃利森以此警示: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忘记过去,就不可能走向未来。
奥德修斯只有回到故乡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意义;美国社会只有直面曾经对黑人所犯下的“原罪”才能达成种族间的和解。“西方古典神话与非裔美国民间传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暗示了布里斯需要整合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混血儿)以实现一个完整的自我。”(Rankine,2006)希克曼认为:“一个真正的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教育家,他知道,我们只有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上帝的恩赐,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还有多长。”(拉尔夫·埃利森,2003:119)希克曼被称为“上帝的号角”,幻化成了基督的象征;希克曼这一圣父形象兼具摩西的伟大使命与基督的救世情怀于一身。希克曼对布里斯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自己的兄长因他被判处了绞刑,母亲也因他而死,但是希克曼战胜了复仇的心理,以爱养育他。布里斯出走以后,希克曼仍然以各种方式关注着他的成长。“我们像一群年老体弱的侦探,出于爱一直在追踪着他。我们甚至都不必考虑,也不必讨论,就是想他,总说到他,到处寻找他。主啊,我们多么怀念小布里斯呵。我想,我们怀念他的诺言。”(拉尔夫·埃利森,2003:301)当希克曼获悉布里斯有危险的时候,他和黑人同胞即刻赶到华盛顿去救他。希克曼的华盛顿之行既是寻找迷失方向的游子,也是挽救紧张的种族关系的努力。埃利森在笔记中写道,“对希克曼来说,布里斯既象征着一种美国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象征着一个有宗教发展潜力的人。希克曼把黑人命运看作美国民主前途的具体表现;看作注定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看作是终将受到世人尊敬的备受蹂躏的人。”(拉尔夫·埃利森,2003:339)
当布里斯被枪击后,他不停地呼唤着希克曼的名字,“他在神志紊乱中就开始呼唤希克曼。当他被推进手术室时,他在呼唤他;当他从麻醉药中醒来后依然在呼唤着他,尽管他十分虚弱,但仍坚持让人把这位老人带到他的病房。”(拉尔夫·埃利森,2003:37)希克曼再次以爱和包容接纳了布里斯,和他一起回忆起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忆起在教堂里的圣歌、所唱的赞美诗、所做的演说与吟唱布道,回忆起黑人文化中兔子与熊的故事,布里斯渐渐地明白了自己是谁。黑人民俗文化滋养了布里斯的心灵,就像埃利森所指出,“民俗提供了一个群体特征的最初素描。……它用表达群体生存意志的象征说明这种智慧;它通过群体的生和死来体现这些价值观。这些素描可能是粗陋的,但它们在表现教化世界的群体努力方面却是深刻的。”(Ellison,1964:172)黑人民俗文化蕴涵了丰富的智慧,它是黑人在压抑中求生存所创造的亚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悟,是构成美国文化丰富而独特的景象。“希克曼从两种文化源流中汲取营养:非裔美国人的宗教传统,把自己与上帝和社区联系在一起;以林肯为代表的美国政治传统——个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他把作为个体的自我与整个民族联系在了一起。”(Butler,2000:225)
对布里斯来说,希克曼是既是一个父亲,也是一种精神安慰。希克曼对布里斯的包容象征了黑人文化对美国文化的拯救。希克曼倾注一生的心血希望布里斯能够成为像林肯那样的政治家,因为林肯为美国的民族和解走出了一大步,但是布里斯辜负了希克曼的期望,预示了美国民主进程的复杂与坎坷。在华盛顿希克曼参观了林肯纪念碑,重温国父对自由价值的诤言。“他(林肯)是我们中的一员。不仅仅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他尽力所能争取到的自由,还因为他摆脱了那种承袭的可怕傲慢,他们是不对我们承认这种傲慢的。就凭这些,他成为一个男子汉,为我们所有将获得自由的人指明了道路,没错!”(拉尔夫·埃利森,2003:270)在希克曼看来,林肯是美国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林肯的政治信仰超越了种族利益,是指导美国走向未来的基石。希克曼对美国民主的信仰基于“承认每个个体的价值并接受民主所必要的约束”(Schor,1993:123)。桑瑞德的被杀,美国冷战的困境,南方在法律上所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北方在事实上对种族法案的默许。所有这些不仅导致了美国的混乱,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民主的根基。埃利森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卡拉汉(John Callahan)教授指出:“如果说《看不见的人》的背景是种族隔离,那么《六月庆典》则是设置在种族融合即将来临的变革氛围之中。”(Rice,2003:117)埃利森自己说《六月庆典》的大约时间是1955年,其时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红色恐怖言论的笼罩下,冷战的“铁幕”已经落下,又是民权运动爆发的前夜。五十年代的美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要么坚持美国民主价值的基本原则,回到开国元勋们所设立的理想,重新开始。
以希克曼为代表的黑人之所以能够忍辱负重、以德报怨,在于黑人文化遗产所赋予他们对生活的尊重,对生命权力与追求幸福权力的坚守,在于他们对美国民主承诺的信心,在于他们对杰斐逊和林肯所开创的事业的虔诚。“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信任是宗教性的。这种信任如果说不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至少具有绝对和普遍的权威。……孩提时,我们就听到长者在谈话中断言或者暗含这种信任。在我们教育过程的每个新阶段,这一观念都不断被强化。……我们可以不信任或者不喜欢我们的同胞以国家的名义所做的许多事,但是我们的国家本身、其民主的制度和光辉的前途是不容置疑的。”(理查·德罗蒂,2006:6)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埃利森把希克曼融入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希克曼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希克曼以实际行动为一个自由而充满人性的未来敞开了大门。在希克曼眼里,过去如果被误解或被抛弃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以希克曼为代表的非裔美国人超越了奴隶制,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世界,促进了一个新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的基础就在于《独立宣言》所承诺的自由民主价值。
希克曼的政治信仰与救世情怀使他超越了一个普通黑人的身份,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普遍号召力的公众人物,他是传递美国自由火炬的继承人,是美国核心价值的捍卫者。在希克曼看来,“美国人是因为差异而疏远也因共同的民族命运而牵涉到一起”(Bredley,2010:44)。希克曼与布里斯的故事因此构成了美国民族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在美国民主进程中,黑人为美国民族形成和国家现代性所做的贡献,为美国文化多样性的贡献不但应该被铭刻,而且应该成为美国反思过去并走向未来的源泉。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殊命运以六月庆典为标志,美国的民主被奴隶制背叛。如果美国作为伊甸园的梦想,允许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升自己,实现多样性的统一,那么美国的自由价值就不应该拒绝黑人。埃利森以奥德修斯的归航和回归非裔美国民俗文化隐喻了美国必须回到《独立宣言》和《解放宣言》中的信仰,并实践这些理念,才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必由之路。
4.结语
《六月庆典》一开篇就引用艾略特(Eliot)《小吉丁》的诗句——“历史也许是奴役,历史也许是自由。瞧,那一张张脸一处处地方,随着那尽其是能爱过它们的自我一起,现在它们都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模式下更新,变化”(拉尔夫·埃利森,2003:1)。小说开篇处的这一引用表明埃利森将把历史作为关注的中心,尤其是黑人的历史,正如书的扉页所写,这本书是献给他出身于彼的已消失的部落:美国黑人。埃利森以六月庆典这一黑人的重大节日为题拷问:黑人通往自由之路为何如此漫长?埃利森以西方古典神话为原型,以非裔美国民俗文化为源泉,把个人救赎与文化救赎缝合在一起,以此隐喻黑人族群与美国民主的关系。因此,《六月庆典》既是一部黑人族群的“出埃及记”,又是一个美利坚的奥德修斯之旅,是关于美国民主命运的历史隐喻。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为美国民主歌颂,他写道:“我们是最伟大的诗歌,因为我们置身于上帝的土地:我们的本质是我们的存在,而我们的生存在于我们的未来。其他民族认为他们自己是对上帝荣耀的赞歌,而我们把上帝重新定义为我们自己的未来。”(理查·德罗蒂,2006:12)正是基于对美国民主价值的这种信念与信心,埃利森在《六月庆典》中塑造了希克曼这样一个集奥德修斯、摩西、基督与林肯于一体的黑人形象,丰富了黑人性的内涵,洞悉了黑人历史对美国民主的影响;阐明了美国价值对黑人信念与种族和解的意义。联系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与混乱,《六月庆典》无疑提供了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选择。
[1]Bradley,Adam.Ralph Ellison in Progress:From Invisible Man to Three Days Before the Shooting[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2]Butler,Robert J.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Ralph Ellison[M].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0.
[3]Ellison,Ralph.Shadow and Act[M].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64.
[4]Gates,Jr.Henry Louis,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xxiii.
[5]O’Meally,Robert G.The Craft of Ralph Ellison[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120 -121.
[6]Rankine,Patrice D.Ulysses in Black:Ralph Ellison,Classicism,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M].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6.
[7]Rice,H.William.Ralph Elliso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ovel[M].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03.
[8]Schor,Edith.Visible Ellison:A Study of Ralph Ellison’s Fiction[M].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3.
[9]Warren,Kenneth W.Chaos Not Quite Controlled:Ellison’s Uncompleted Transit toJunetteenth[M]//Ross Posnock.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lph Ellis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90.
[10]拉尔夫·埃利森.六月庆典[M].谭慧娟、余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1]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M].黄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6.
[12]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