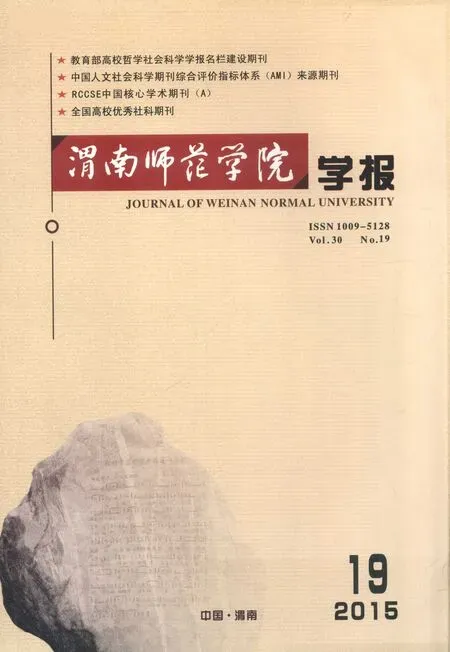各家论司马迁撰《史记》宗旨评议
叶 庆 兵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00)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各家论司马迁撰《史记》宗旨评议
叶 庆 兵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 250100)
历史上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有诸多说法,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完成父志说、实录说、谤书说、发愤著书说、成一家之言说等。这些说法有一些依据,但往往失之偏颇,不能概括《史记》全部内容。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应该有整体思维,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同时不能持一成不变的观点,要实事求是,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去探讨其撰史宗旨的变化。
司马迁;《史记》;宗旨
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完成父志说、实录说、谤书说、发愤著书说、成一家之言说等。这些说法有一些依据,但往往失之偏颇,不能概括《史记》全部内容。学界主要有5种观点,笔者予以分别论述。
一、完成父志说
刘知几在《史通·正史篇》中说:“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 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凡百三十篇, 都谓之《史记》。”[1]337《隋书·经籍志》亦云:“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世,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2]956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和司马迁对父亲的承诺。今摘录如下: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3]3295
从这段司马谈的痛切陈词,确实可以看出,司马谈有让司马迁完成自己未竟事业的期望。尤其是“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以及“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都明确地对司马迁提出了续作《史记》的要求。但是完成父志是否就可以视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呢?所谓宗旨,也就是撰写《史记》的终极目的,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吗?这似乎并不能成立,如果真的仅仅如此,那么恐怕《史记》难以取得现在的成就。而且以完成父志为司马迁撰史宗旨有一些不合理处。
第一,司马迁自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3]3293司马迁二十游历不应该视为简单的游学过程,实际上是司马谈对司马迁的一种培养,目的是让司马迁开阔眼界,同时采集、积累材料,将其培养成为史学人才。这种目的从司马迁游历的地点就可以看出来,江淮的会稽、禹穴是古史中的重要地点,沅湘是楚国的中心地带,汶、泗齐鲁是思想文化的中心,鄱、薛、彭城是历史名城,彭城还是楚汉之争的著名战场,这些地方都是历史容易积淀下来的地方,因此让司马迁去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游历,而不是自然风景区观赏,很明显是要让他亲身去感受活生生的历史,培养史学素养,积累历史材料。而且这些经历在司马迁著史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作用。如《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3]46又如《孔子世家》曰:“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3]1947可见,司马迁的游历经验对他著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可以反证司马迁之少年游历确实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甚至是有任务在身的。也就是说,司马迁为撰《史记》而作准备是很早就开始了,绝不待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换言之,即使司马迁没有来得及接受司马谈的临终嘱咐,他还是会撰写《史记》。
第二,完成父志说本身就还有待追寻,如果说司马迁撰史是为了完成父志,那么司马谈撰史又是为了什么呢?也就是说“父志”所指,还应该继续追寻下去,才能了解司马迁作史的终极目的。司马谈作史的目的,从其遗言中可以窥见一二,其临终遗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从这番话中很明显可见出司马谈有深深的家族荣誉感和使命感,将死之时,他首先交代的其实是“续吾祖”,也就是继承祖宗的事业。其次他才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很显然,司马谈所谓“吾所欲论著”,其实也是“续吾祖”,是对史官世家记载历史责任的继承。司马迁对父亲的遗训心领神会,“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里的先人不是司马谈,因为是时司马谈虽将死而未死,是不能称为先人的,实际上先人就是司马谈所说的“吾祖”。反观《太史公自序》言: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3]3285-3286
正是对其司马氏家族“世序天地”“世典周史”的历史概述,这是不应忽视的,因为这显然是司马迁在表明身份,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以世掌史官的家族后人自居,又明确表示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很明显,司马迁撰《史记》的一个目的,便是继承史官家族的事业,承担史官的职责,这其中当然包含司马谈未竟的事业,但仅以“完成父志”为其宗旨,显然内涵太小,无法囊括。
二、实录说与谤书说
《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2738所谓实录,是说司马迁记述历史事实真实可信,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感情,如实地履行史官的责任和义务。
与实录说相对的是“谤书说”。“谤书说”出现在东汉,班固的《典引序》记载,东汉明帝曾当众指责“太史公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 非谊士也”[5]2156。《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 流于后世。”[6]2006第一次明确称《史记》为谤书。 唐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注中释“谤”曰:“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美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6]2007
持“谤书说”的人把司马迁所记“汉家不美之事”都视为是诽谤,这很明显是出于维护统治者的尊严,维护君主权威而作出的判断,他们并不真正着意于司马迁所记史实的真假,而是司马迁对最高统治者有所指摘的态度。因此,谤书说其实根本不符合《史记》的实际,也不可能成为司马迁撰史的宗旨。具体说来有以下依据:
首先,《史记》体大思精,鸿篇巨制,开创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庞大体系,而在各体之中,都有许多是与汉家史事无关的,如本纪当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十表当中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都与汉家史事无甚关系;八书中的每一书都详尽地考证源流,不仅仅是记汉代之事;世家中的每一篇也是远追始祖;至于列传,从《伯夷列传》到《蒙恬列传》28篇所叙也都是汉以前人的故事。如果说司马迁撰史就是为了写一部谤汉之书,有什么必要绕这么大的圈子?可见以谤书来概括《史记》博大精细的体例和构思,根本就无能为力。
其次,如果司马迁撰史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谤汉,那么他笔下所记的汉代必定是丑陋不堪。司马迁确实指出了西汉政府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准书》这样评述汉武帝: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3]1420-1421
又如《封禅书》对汉武帝迷信方士神仙之术,屡屡被骗的事情作了详细的记录。但是,对于西汉的繁盛司马迁也从不讳言,如同样是《平准书》,司马迁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3]1420很显然,对于汉家经济繁盛的局面,司马迁并没有回避,而是同样作了如实的记载。同样,司马迁对汉武帝也并不是一味的贬损,《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3]3303这明显是对汉武帝的肯定。又如《淮南衡山列传》:
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3]3088
这里司马迁如实记载淮南王与伍被的谈话,实际上,他是同意伍被的观点,认为汉武之世是治世的。如果司马迁果作谤书,那么还会认为汉武之世是治世吗?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司马迁对于汉家天下,其实并非存心诽谤,相反,司马迁对汉家统治的成功之处和缺失都作了如实的记载,“不虚美,不隐恶”,所以才可以称之为实录。
但是实录只能说是司马迁撰史的态度和精神,却并不能看作是司马迁撰史的宗旨。如果说司马迁撰写《史记》就仅仅是为了如实地记载下一部从古至今的通史,那么这部通史一定不能达到现在的高度。《史记》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说正是由于它不仅仅是实录的历史,而是一部有个性、有态度的历史。司马迁的个性和态度首先体现在《史记》的取材上。从炎黄时期到司马迁当时,几千年间的事情数不胜数,要想在一百三十卷内把这几千年的历史记述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必然会进行取舍,而在取舍之间,就必然会有编选者司马迁的主观态度渗入进去,因此就决定了《史记》不可能是完全实录,司马迁也不可能以实录为撰史的宗旨。例如,由于司马迁人生经历的特殊,在人物的选取上,司马迁就多记述悲剧历史人物的事情,韩兆琦先生在《史记评议赏析》中就曾称《史记》是“悲剧人物的画廊”[7]108,这显然是司马迁有感于自己的身世,作了选择的缘故。
其次,在编排上,也可以看出《史记》并不是完全的实录。如世家所记都是诸侯,但是陈涉出身贫民,司马迁因为“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3]3311,而将陈涉列入世家;孔子本是布衣,但其“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3]3310,所以司马迁也将他列入世家;高祖之后,汉孝惠帝即位,但吕后掌握实权,所以司马迁不作《孝惠本纪》而作《吕太后本纪》。在这些地方,司马迁都超越了历史的表面,看到它深刻的本质,因而对《史记》的编排作了调整,这显然不是实录,但却能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
第三,之所以说《史记》并不是简单的实录,还因为这是一部带有鲜明感情色彩的历史。实录的历史无需也不能带有感情因素,更不能掺杂主观议论,但是在《史记》中,情感的抒发和对史事的议论却总是难以掩抑。如《伯夷列传》写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2124-2125
这完全是议论了。又如《礼书》曰:“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3]1159这又是直接的抒情了。记史而掺杂着抒情和议论,就很难说是实录。
第四,除了这些之外,最重要的是,《史记》中有些记载是不符合史实的。如《司马穰苴列传》记载:“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扞燕晋之师。”[3]2157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在此条下注云:“按春秋行师,犹以古法约束;用杀以立威,战国始有此风,春秋无有也。《战国策》明言司马穰苴湣王时人,史公属之景公;即‘将军’‘司马’之称。亦当在战国六国相王后,恐史公误也。”[8]240《魏公子列传》记述:“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3]3377《史记札记》(作《信陵君列传》)于此条下云“按《魏世家》,安釐王元年,秦拔魏两城;二年,又拔二城;三年,拔四城;四年,秦破魏,予秦南阳以和;九年,秦拔魏怀……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矫夺晋鄙军救赵。盖自魏安釐王立,无岁不有秦兵。……所谓‘诸侯不敢加冰谋魏十余年’,是史公极意描写之笔,无事实也。”[8]275
三、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指的是《史记》是为抒情而作,是指司马迁在某种压力下(李陵之祸)产生了创作的动机。李陵之祸确实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遭受宫刑的耻辱,在司马迁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痛切陈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自己本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却没有想到“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其中的冤屈痛苦不言自明。而下狱之后,“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4]2730,又可谓尝尽了世态炎凉。这段苦难的经历,对司马迁撰史必然会产生影响,例如我们前面说的《史记》中的人物多悲剧色彩,例如韩信、李广、白起、周亚夫、伍子胥、晁错、屈原、孔子、苏秦,甚至是称王称霸的陈涉、项羽、秦始皇,在司马迁的笔下,他们都充满了悲剧色彩。诚然司马迁所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这种悲剧意味的突出,必然与司马迁所掺入的个人情感有关。读《史记》很容易感受到世态炎凉,人心不古。据统计,《史记》中描写世态炎凉的篇目有12篇[9],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道:“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3]2448通过“客曰”直接把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的关系揭露了出来。又如《司马相如列传》写道:“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3]3000可当司马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奉使通西南夷路过蜀地时,“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3]3047。在《货殖列传》中更是直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3]3256这都很明显和他的不幸遭遇是有关系的,正因为他特殊的不幸遭遇,亲身经历、感受过,才让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理解得特别深刻,因而影响到了《史记》的取材和创作。
但是发愤著书说能不能成为司马迁撰《史记》的宗旨呢?我们认为还不能,因为这种浓烈的情感倾向并不是贯穿《史记》全部的,《史记》的鸿篇巨制、精密安排,一定是更加深入、客观、详细的计划和安排,其目的也并不都在于抒发一己的感情。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抒情,有直接的,也有借叙事来体现的,但都应该视作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而并不能认为这就是撰史的主要目的,因为如果以抒情为目的,《史记》的史料价值一定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歪曲史实,这是一个合格的史学家一定会避免的。
四、成一家之言说
应该说成一家之言说是最像司马迁撰史宗旨的,但是关于“成一家之言”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还有待明确。对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认识,历史上存在多种说法,如:
(一)私家说
这是指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区别于官家的私家之言。明谢肇淛《五杂俎》指出:“《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10]267吴忠匡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中也认为:“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作史的主要宗旨。”他还指出,司马迁父子最早撰写《史记》是希望其成为一部官书的,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有“臣迁谨记” 的题署,这显然是作者初稿时的手笔为后来定稿时所删汰未尽的,完全可以证实在作者未被刑之前想望成为官书。但是在遭遇李陵之祸,承受腐刑之后,“司马迁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著述要成为官书,已经完全无望,他的以古史家的秉实纪史的原则,也决不可能见容于汉王朝钦定的国教和传统的观念,于是他退而负责地、严正地用‘一家之言’这一词义来表明他所持的‘颇识去就之分’只‘欲以文采表于后世’的创作态度”[11]。
(二)一子说
也就是说司马迁撰史的目的和先秦诸子的儒家、道家等相同。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就曾指出:“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12]4628但问题是,司马迁该归入哪一家?在研究史上讨论得最激烈的是把司马迁归入儒家和道家的分歧与纷争,双方势力相当,到了也争不出个结果,以致出现了调和派,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儒道并重。实际上,在《史记》中崇儒倾向有依据,例如对孔子的尊崇,对儒家学脉传承的记录和探讨等都可见一斑,但是对道家也不乏认同,《太史公自序》全录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就是尊道的文章,司马迁肯定会受到他父亲的影响,而且司马迁自己对汉武帝的大兴土木等行为持否定态度,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就可以看到他的态度。其实,儒道本来就不是决然对立的,司马迁融合儒道是很自然的事情,应该予以承认,而不是一定要肯定一方压倒另一方。此外,司马迁的思想中,还有许多远远超出了儒道思想的东西,例如《货殖列传》中对人的享受、欲望的肯定,对人们逐利在推进历史前进过程中的作用的肯定,都是与儒、道背道而驰,因此,实际上很难将司马迁归入任何一家。那么司马迁有没有可能成为独立于先秦诸子之外的另一子呢?我们认为不太容易,因为纵观先秦诸子的思想,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子,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大多集中于一个方面,并且常常能够提炼出一些核心的思想和概念,他们与哲学和宗教是十分接近的。但是司马迁不行,我们做不到从《史记》中提出他的核心思想,去概括他的全面的思想。因为《史记》中涉及的面太广泛了,有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地理、音乐等等,这样庞大的思想体系,是不可能归纳成几个要点的。
(三)成为“史家中的一家”说
该说见罗文博《论史记的成一家之言》(《阜阳师院学报》1983 年第4 期)。实际上,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要成为史家之一家的说法与“私家说”是相类似的,只不过是“私家说”更强调的是“私”家而已。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成为史家中的一家,也有一些问题难以解决。第一,在先秦诸家学派中,有儒家、道家、法家、杂家等,但根本不存在“史家”,也就更别提成为史家中的一家了;第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历叙自己的家世,“司马氏世典周史”,如果说成为史家中的一家,指的是成为撰史者中的一个流派,那么司马氏家族早已经实现了,无需等到司马迁来实现。第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一则说:“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二则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三则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可见其撰《史记》,主要是继承,“非所谓作也”,可见并不是要在史家中另辟蹊径,成为“史家中的一家”。
(四)认为成一家之言的一家就是史家
白寿彝先生在《说成一家之言》一文中认为:“司马谈和司马迁都重视他们家曾经世袭史官的历史,他们也立志要把写史作为家学。……他们父子有一种共同的思想感情,就是要把家族的‘家’ 跟作为学派的‘家’统一起来。……在史学领域里提出‘家’的概念,并在实践上实现了‘成一家之言’,这在司马迁个人, 是超越前人的成就,在史学的发展上, 标志着我国史学已经规模具备地成长起来了。”[13]张大可先生也认为:“从学术上说,司马迁自成一家就是一个历史家。”[14]18高振铎先生也指出:“我认为司马迁不属于上述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这是产生六家的先秦所根本没有的一家……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史家之言,而不是其他六家中任何一家之言。”[15]汪高鑫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一文中对此说又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确立史家之言有以下根据:一是司马迁是以论载历史为己任的;二是司马迁著史是为了言志,他认为司马迁著史的目的从学术来说是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也就是要统一《六经》思想, 统一天下学术;三是司马迁有志于构建史学理论。[16]
五、探求治国之道说
朱枝富在《论司马迁撰史宗旨》中认为“究天人之际”是从哲学角度探求治国之道,对风行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说提出质疑,提出治国关键在天而不在人;通古今之变是从历史角度探求治国之道,也就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成一家之言是从思想方面探求治国之道,也就是提出自己在治国之道上的一家之言。[17]探求治国之道固然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之一,但是在《史记》中还有许多与治国之道无关的内容,如《刺客列传》,其宗旨显然是在记述这些刺客令人称道的行为与品行,而不是探讨治国之道,仅以探求治国之道来概括《史记》的宗旨,尚嫌过窄,无法概括《史记》的全部内容。
六、结语
我们认为要探讨《史记》撰写的宗旨必须把握几个原则:
首先,要从《史记》整体内容出发,力求所得出的观点能够概括《史记》的全部内容,因为如果司马迁撰史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那么至少《史记》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按照这个宗旨来撰写和编排的,《史记》在编排、取材、评价、撰写等方面,都应该与之相适应。
其次,对于司马迁的一些概括撰史宗旨的总结话语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不能拘泥于此,而应该以《史记》的内容作为检验和考量的标准,并作出合理阐释。
第三,不能以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看待《史记》的撰写宗旨,因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几乎贯穿其一生,人一生的思想总会有所变化,而且司马迁的一生中还发生了许多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事情,最明显的当然是李陵之祸,这些事情应当会导致司马迁撰史宗旨的变化。
基于以上几个原则,我们认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应该作分段考察。
司马迁早年即有撰史准备,这或许是司马谈的安排,或许是司马迁自觉的意识,这个阶段一直到司马谈的故去。此一阶段,司马迁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应该还是学习和积累,以及帮助司马谈搜集整理撰史的资料,这一时期,他的撰史的意识和宗旨可以说还不成熟,主要还是司马谈的传授和灌输,而司马谈所传授和灌输的是作为史官世家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此,继承史官世家的事业,这应该是司马迁最初撰史的宗旨,父亲的临终遗命更是对他的激励,也是其动力。这从《太史公自序》的开头即可看出。
司马谈故去之后,司马迁独立撰史,肯定会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这一阶段他的撰史思想日渐成熟,撰史宗旨也渐渐明确。在正式接手撰史工作,也是正式“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之后,司马迁曾发感慨:“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时他对于继承史官世家的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继承一家之事业的小的宗旨,而发展成为继承《春秋》——继承大的记载历史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就是白寿彝等先生所认为的要确立“史家”的一家之言,这显然是一种升华。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答壶遂问。在答壶遂问中,司马迁充分肯定了《春秋》以及《诗》《书》《礼》《乐》《易》等六经,同时也把撰写《史记》的目标拔高到了和六经同样的高度,不仅仅是要记述历史,还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术潮流进行梳理和总结。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一生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司马迁撰史还单纯是出于史家的责任感,此后则更渗入了他对历史、人生的个性化的理解和领悟。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撰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取材上,偏重于选取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入传;在史事的记载上,常常着重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揭露;在行文中,甚至常常直抒胸臆,抒发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
因此,《史记》确实是一部有感情的史著,也就是前人所总结的“发愤著书”的史著。但是必须明白,这种发愤著书的行为是在李陵之祸以后才发生,在这之前司马迁已经着手著史了,《太史公自序》明言:“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縲绁。”[3]3300可见司马迁撰写《史记》必不待李陵之祸以后,而且,“发愤著书”也不能囊括《史记》全部。因此“发愤著书”并不能成为其撰史的宗旨,但我们不否认这也是司马迁撰《史记》的目的之一。
最后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关于“成一家之言”的“一家”为历史家当最符合实际,从《史记》的规模、气势、体制来看,司马迁显然是将其作为当时当世的集大成的史著来撰写的,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构建历史学的期待和设想,而且从实际的情况来说,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确实也曾为中国历史学成熟的标志,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成为后世史学家撰史的楷模,其体例、撰史的理论和原则,多为后世史学家所继承。但是要达到这种有意识地创建完善历史学科的高度,那应当是司马迁撰史非常成熟之后的事情,甚至司马迁是否真的形成了这种意识,还是值得怀疑和探讨的。
总括来说,司马迁撰史的宗旨,首先是出于史官世家的责任感,要继承史官职责如实地记载下历史事件,总结出历史规律;其次,在撰史过程中,司马迁也在渗透和穿插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于政治、经济、学术等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悟;最后,他可能还有意识地在创建历史科学的理论和体系。
[1] [唐]刘知几.史通通释[M]. [清]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唐]魏征.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梁]萧统.文选·典引序[M]. [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8] [清]郭嵩焘.史记札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9] 江文贵. 论《史记》中人情世态描绘的特点及其成因[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22-25.
[10] [明]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1] 吴忠匡.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J]. 人文杂志,1984,(4):76-80.
[12]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十六卷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 白寿彝. 说“成一家之言”[J]. 历史研究,1984,(1):55-60.
[14] 张大可,俞樟华.司马迁一家言[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社,1995.
[15] 高振铎.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J]. 贵州社会科学,1985,(5):48-49.
[16] 汪高鑫.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J]. 安徽大学学报,2000,(3):112-117.
[17] 朱枝富. 论司马迁撰史宗旨[J]. 史学史研究,1985,(4):24-29.
【责任编辑 梁红仙】
Discussion on the Aim of Historical Records by Sima Qian
YE Qing-bing
(School of Literature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On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about why Sima Qian wrote this book. Some people think Sima Qian wrote this book to fulfill his father’s last wish, while others think he just recorded history honestly. In addition, some researcher say Sima Qian wrote Historical Records to release emotions or “create a philosophy of one’s own”. Some people even think he just wrote this book to defame the Han dynas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se options are correct but they can’t reflect all contents of it correctly. On this subject, we should consider Historical Records as a whole and be honest to combine with Sima Qian’s whole life.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aim
K204
A
1009-5128(2015)19-0040-08
2015-09-05
叶庆兵(1992—),男,安徽太湖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