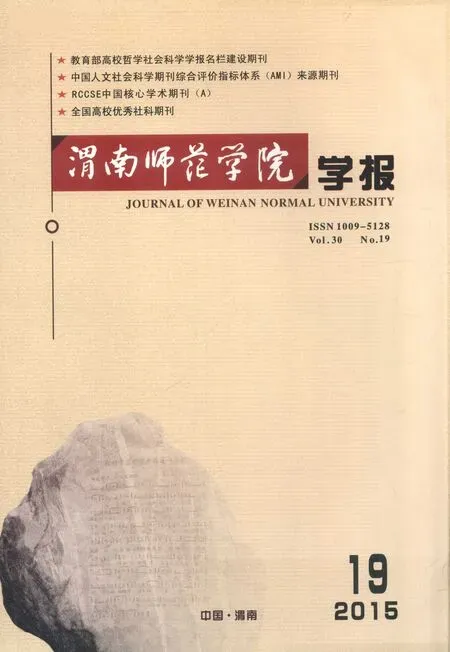论《史记》的相人情节及司马迁的相术思想
赵 佳 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论《史记》的相人情节及司马迁的相术思想
赵 佳 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因司马迁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原则,其叙事不乏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相人”算得上是其中一个离奇的叙述情节,司马迁在解释人物命运的时候,经常穿插一些相术家的预言,这些预言在经历了扑朔迷离的事件后,竟然神奇应验。这种安排不仅是汉初相人风气盛行的大背景使之然,更多地暗含了司马迁独到的相术思想。
《史记》;相人;相人风气;相术思想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59,无论在史学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称得上是一座丰碑。太史公司马迁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697的创作原则,成就了这一伟大著作。《史记》的叙事不乏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司马迁在叙事的中间往往穿插一些离奇的逸闻逸事,为史家叙事增添了几分神秘性和趣味性。“相人”算得上是《史记》叙事中一个离奇的叙述情节,太史公在叙述人物生平经历的时候,经常穿插一些相术家的预言,并且,这些预言在经历了扑朔迷离的事件后,竟然神奇应验。这一叙事情节在整部《史记》叙述中并不仅仅是个例,而是一种俯拾即是的现象,这种叙事情节安排不仅是汉代相术盛行的大背景使之然,更多地暗含了司马迁独到的相术思想。
一、相人(术)概述
(一)释名
“相人”由来已久,但是我们对“相人”的认识还有失偏颇,所以,首先要明确何为“相人”?《说文解字》曰:“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诗》曰:‘相鼠有皮。’”[3]72可见,“相”不同于一般的看,而是一种极其认真仔细的观察;在原始社会,古人放眼望去,无非是野草乔木,这大概是“相”字从目从木的原因。
但是随着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人们省视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牛马牲畜也变成了“相”的对象,史书中就记载有相牛马的风气。《史记·日者列传》记载:“黄直,大夫也……以相马立名天下。”[4]陈兴仁先生认为相人应该出现在相牲畜之后[5]2-4,他认为按照因畜致人的因果类推的逻辑思维定势,人们很自然就会从相牛马,转向审视人类自身。[5]2-4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陈先生也进行了文献的考证。可见,“相人”不是早期相术存在的唯一形式。
“相术”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记载: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遍相众宾。[6]808-809
此处所说的“相术”,显然是指“相人”,可见相人亦即相术一种。以三国时魏时为界,曹魏之前多将给人看相这一行为称为“相人”,之后则名之“相人术”(相人的方法)或“相术”。
随着时代的变迁,“相人(术)”与“相术”的界定逐渐模糊化,当今学界的相关研究或以“相术”概括相人的内容,或不再区分“相术”与“相人术”,所以《中国方术大词典》“相术”条标明:“审察人的形貌以判断其性格及福寿休咎的方法。包括相面、相手、相骨、相声、相气色等。”[7]377
(二)相人(术)的发展
《史记》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即使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但主要还是以纪实为目的,谈到《史记》中的相人情节,当然与汉初以前的“相人风气”有直接的联系。那么,相人到底是发生于哪个时代呢?荀子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8]72可见,“相人”离荀子的时代不远,据学者考证,相人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左传·文公元年》记载: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叔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厚于鲁国。”[9]510
竹添光鸿在《左传会笺》中注曰:“相人之见于经典是为始。”[10]2另外,在《左传·文公元年》还有一个例子: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子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柴声,恶人也,不可立也。”弗听。[9]513
从这些仅存的记载可以看出,相人的风气至少在春秋战国时的贵族阶层中已经形成。
这种相人风气的产生源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三代之际,王朝的更替,带来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殷王朝被推翻,带来了神学政治的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君权神授的哲学思想;西周末年,国人暴动,打破了天子国君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进入春秋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的变化,使人们开始思考命运——从以前的以血缘远近为依据来决定命运的天帝决定论,转变为不论人的血缘关系,而以人的体型为依据的自然决定论。[7]正是这种先天的因素,为“相人(术)”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气候和土壤。
汉朝是出身农户的刘邦带领一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平民阶层的人,经过腥风血雨打出来的。这些出身卑微的下层民众一跃跻身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最上层,无疑是对战国以来已经失势了的以血缘亲疏定贵贱的天帝命论的更为巨大的一次打击;除此之外,从汉朝建立到汉景帝时期,上层统治阶级一直信仰黄老思想,秉承中国传统阴阳五行观念;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说上天的意志是通过人体现出来的,所以理所当然从人的身上也可以探寻出天的旨意……这种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为相人(术)的发展和看相习俗的风行创造了适宜的条件,所以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相人热潮。
相人作为汉初一种社会风气,自然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反映,史学家作为历史的实录者,理所应当记载了这一社会现象,所以《史记》出现大量的相人情节,也在情理之中。
二、《史记》的相人情节
《史记》中记载的相人情节,大多通过人物相貌、体貌特征来预测人物命运,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没有明确叙述运用何种方法,只是强调了结果,以指明人物命运吉凶的。从预言内容来看,这些预言都准确地预测了人物一生的重要经历和归宿,具体而言,这些情节大多通过相人,可以得知人的贫富贵贱和生死寿夭,下面作具体分析。
(一)预测贫富贵贱
《史记》中的相人情节多为被相者原本并非大富大贵之人,但相人者预言此人终将富贵显达,历经扑朔迷离的事件后,这一预言得以应验。
《高祖本纪》是帝王之相的一个典型例子。太史公开篇就埋下了伏笔:“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因为高祖具有非比寻常的相貌,“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能够令位及权贵的吕公大惊,高祖的大富大贵显而易见。《高祖本纪》中还记载了一位不知名老父为吕雉母子及刘邦相面的情节。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事实证明,吕公和不知名老父的预言都极为准确,刘邦终成一代帝王。
《赵世家》记载了赵简子通过相面选太子的情节,因相者姑布子卿言“天所授,虽贱必贵”,赵简子后又经过考察,废太子伯鲁,最终立出身卑微的毋恤为太子。在那个重“礼”的时代,赵简子能够越出长幼尊卑的界限,可以看出相人的巨大作用。
《张丞相列传》记载:“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张苍因体貌脱俗而免于一死,后相继为赵王相和代王相。该篇还记载:“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开始周昌不以为然,后来经赵尧举荐,御史大夫周昌就被调任赵国相国,而赵尧受高祖器重,由刀笔小吏擢升为御史大夫,果然代替了周昌的位置;还记载了长安善相工田文“与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贱时会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后来这三人果真都为丞相。
《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将军卫青少时贫贱,因为是私生子,所以“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卫青曾经随主人去甘泉居室,碰到一个善相术的钳徒,告诉他说:“贵人也,官至封侯。”卫青当然不敢相信,自我解嘲说:“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但是后来因他的姐姐卫子夫受到武帝的宠幸,被立为皇后,卫青也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因为在反击匈奴战争中屡立战功被封为长平侯。
可见,上到帝王,下到将相,相术对他们一生的运势都进行了准确的预测。此外,相术在准确预测人物命运的贫富贵贱之后,对婚姻的缔结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高祖本纪》中,吕公以刘邦奇,以之为上客,并且不顾吕媪反对,以女妻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外戚世家》的相关记载更为曲折:魏王豹很痴迷相术,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个玩笑。著名相者许负相薄姬,言其将会产下天子,魏王豹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生天子,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决策,背汉而命丧黄泉。谁曾想到“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后来,薄姬为刘邦产下孝文帝。
《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早年因家贫,富人没有愿意与之结亲的,可后来:
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
张负通过相面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认为“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于是将女儿嫁给了陈平,而陈平终究位及丞相。
《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牙昏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营太史邀家庸。太史邀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当形势发生变化,法章成为齐襄王时,太史氏女也就成了“君王后”。
可见,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市井小民,甚至是一个弱女子,都能够通过面相,而判断一个人的命运的否吉,从而决定是否与之缔结婚姻。
(二)预测生死寿夭
《史记》中并不全都记载的是关于预测人物富贵显达的例子,还记载了一类预测人物生死寿夭的相人情节。
《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条侯周亚夫还不是河内守时,许负为他看相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当时周亚夫难以相信,说:“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说:“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后三年,因其兄周胜获罪,周亚夫果然续为绛侯。但是最终却因“谋反”的罪名,五日不食,饿死在牢狱之中。
同样一则故事记载在《佞幸列传》中:汉文帝十分宠幸邓通,于是让善相者给他看相,结论是邓通“当贫饿死”。文帝认为:“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 为了避免邓通贫困饿死的命运,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谁料后来得罪景帝,被罢斥,获罪,最终也摆脱不了“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的命运。
《范雎蔡泽列传》记载: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原闻之。”唐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于涂。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
由这个故事可以得知,通过相人,不仅可以预测出人物的贫贱富贵、祸福,还可以预测出人物的寿命。
(三)其他
《史记》中大量的与相人有关的情节,并非都是为了预测人物的贫富贵贱、生死寿夭,有些并不以记载相术预测的准确性为目的,而仅仅是因为所叙述的历史人物以相术为一种游说工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蒯通以相术说韩信背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淮阴侯列传》记载楚汉战争后期,刘邦项羽已斗得精疲力尽,而这时的齐王韩信却坐山观虎斗,拥兵自重,成为双方都极力争取的主力军。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所谓的奇策就是用相术来说服韩信。当韩信请教相术的秘诀时,蒯通煞有介事地说:“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 韩信被说得心动,于是进一步询问结果,蒯通在示意韩信屏退左右之人后,故弄玄虚地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 实际上,蒯通是劝韩信不要满足于封侯拜将,要自立为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最后韩信经过几天的犹豫还是没有下决心背叛刘邦,后来韩信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担心其功高盖主,通过吕后之手将韩信处死。在这里说客蒯通只是利用了当时人们对相术信仰的心理,企图说服韩信自立为王。
三、司马迁相术思想的双重性
纵观《史记》,司马迁对待相术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他一方面肯定相术的不可抗拒性,但是另一方面又对相术持一种否定怀疑的态度,这种思想的双重性看似矛盾,但其实质却是一致的。
(一)承认相术预言的准确性及其不可抗拒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司马迁笔下记载的大量相术情节,最终都是神奇应验的,并且这种预言的准确性是不可抗拒的。《佞幸列传》最能说明这一点:汉文帝为了保证邓通有足够的财富,避免其“当贫饿死”的命运,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后来却因得罪景帝,被罢斥,获罪,“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汉文帝作为一代帝王,为了改变邓通的命运,可以说使尽了浑身解数,结果还是人算不如天算,邓通最终没有摆脱被饿死的命运。可想,作为普通大众又如何抗拒预测的结果。
此外,这种不可抗拒性还表现在违背预测,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吴王濞列传》中记载:“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授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 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邦既然发现刘濞有反相,考虑到毕竟都是刘家人,血浓于水,竟然没有收回成命,而是抱着侥幸心态让刘濞作吴王。后来吴王刘濞果然发动了七国之乱,几乎使大汉基业倾覆,不能不说这是刘邦自己酿下的苦酒。
从《史记》中大量的关于相术的记载可以看出,秦汉之际,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贵为帝王,都对相术有着相当的信仰。帝王的面相可以预示着未来,大臣的命运在司马迁看来也是无法改变的,司马迁记载了这方面的现象,并不是抱着批评的态度,而是持肯定和欣赏的态度。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是先秦以来神秘思潮流风余韵;其次,也是司马迁推崇道家思想,试图破解天人关系的尝试。司马迁毕竟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在用历史眼光审视一个个历史人物,他们的命运令人捉摸不定,他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时,只好把有些人物的命运归结为天生注定,甚至是神秘的力量。此外,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作为社会历史“实录”的《史记》,只不过是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而已。
(二)同时持否定、怀疑的态度
虽然《史记》记载的不少有关相术的事例,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准确性,但综观全书,司马迁个人对相术是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的。这点从他自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世家》)
太史公曰:吴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 ”于戏,惜哉!
(《游侠列传》)
从以上太史公自己的两条评论,可以看出,司马迁本人对相术既不是绝对的支持,也不能说是彻底的反对,至少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他折中于夫子,认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又引用民谚“人貌荣名,岂有既乎”,认为“人貌荣名”只是历史的偶然性,所以,盲目的“以貌取人”只会造成人才的流失。
此外,在揭示人物命运的时候,司马迁并不是一味遵从天命,而是尽量从人事上进行说明。比如对周亚夫的悲剧人生,司马迁虽然认同相者之言,特意交代一句“条侯果饿死”,但是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时,他并不满足命里注定的宿命,而是从条侯自身缺陷来找原因,归结为是“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导致“终以穷困”,直至悲惨死去的厄运。
这一观点在《项羽本纪》中表现得更明确:比如在评价项羽乌江自刎时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完全从客观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人物的成败得失,认为人物的得失不在于天命,而在于人事,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司马迁虽然在承认相术准确性的同时,又对相术持一种否定怀疑的态度,但实质上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这样记载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充满着矛盾,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以貌取人”都可以应验,作为实事求是的史学大家,当历史人物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现象时,将其如实地记载下来是完全正常和正确的;其次,“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否认有意志的‘天’的存在,但是他主要的思想倾向不是深信,而是怀疑,不是顺从,而是违抗”[11]284,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司马迁试图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究天人之际”,而不是盲目地顺从迷信鬼神,这一点与其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一致的;此外,不可忽视“李陵之祸”对他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影响,经历过人生重大变动的司马迁能够以更为冷静、敏锐的目光去剖析社会,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盛世,他转向为一种批判怀疑的态度审视历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相人情节是《史记》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司马迁对待相术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但这一点并不违背史家的“实录”精神。相反,司马迁却以“实录”为纽带,巧妙地将二者调和起来:记载相人预测的准确性,是为了真实记载人物身上发生的相人预言应验的真实事件;对相人怀有怀疑否定态度,也来源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真实个例。它们不仅无损于《史记》,反而使《史记》的叙述更为深刻、客观,为其增色不少。
[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汉]班固.汉书[M]. [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汉]许慎.说文解字[M].[宋]徐玄,校订. 北京:中华书局,1963.
[4] [汉]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陈兴仁.神秘的相术——中国古代体相法研究与批判[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6] [晋]陈寿.三国志[M]. 陈乃乾,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7] 陈永正.中国方术大辞典[K].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
[8] [战国]荀况. 荀子集解[M].[清]王先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卷八[M].昆明:凤凰书局,1978.
[11]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朱正平】
Plots of Fortune Telling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ima Qian’s Thoughts on Fortune Telling
ZHAO Jia-l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Beibei 400715, China)
Historical Records is China’s first biographical general history. Because Sima Qian held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from ancient time to the present and the expression of one’s own ideas” as his creative principle, he wrote some mysterious narrative plots, and the plot of fortune telling is a bizarre narrative plot. Sima Qian, when explaining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often interspersed with a number of prophecies of fortune telling, which experienced a bewildering event, and even magical fulfillment. This arrangement is not only caused by the custom of fortune telling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but much implicates Sima Qian’s unique thoughts about fortune telling.
Historical Records; fortune telling; custom of fortune telling; thoughts on fortune telling
K204
A
1009-5128(2015)19-0030-05
2015-06-08
赵佳兰(1992—),女,甘肃天水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