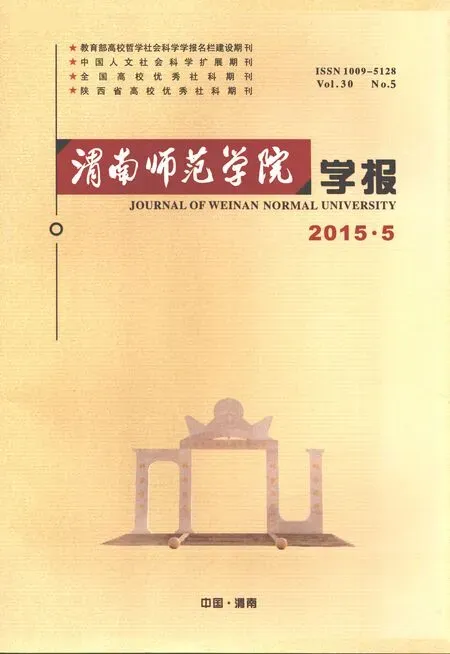对朱子“兴”论的探析与反思
韩 国 良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对朱子“兴”论的探析与反思
韩 国 良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由一系列分析不难看出朱熹所说的“比”实际就是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兴”,而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比”,朱熹则将其完全归入了“赋辞”中。至于朱熹所说的“全不取义”的“兴”则更纯粹是他个人的发明,它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所作的论述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孤立地来看,朱熹的“兴”论思想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但是如果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的论述加以比较,其局限性无疑也是非常大的。
朱熹;兴辞;托事于物;全不取义
在中国文论史上,朱熹对于“赋比兴”之“兴”的诠解可谓是独具一格的。它独就独在一别前人传统的解释,而认为“兴”是完全无义的。这样的理解不仅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代学者所作的论述相抵牾,而且与中国传统文论中其他方面的“兴”论思想也是扞格不容的。不过,由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兴”论思想在中国文论史上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并且这一影响直到今天也仍在继续。这对我们正确理解“赋比兴”的涵义,以及与“赋比兴”相关的“兴寄”、“兴象”的含义显然都是很不利的。也正鉴此,所以对这一问题再加探索无疑仍是很必要的。
一、朱熹“兴”论的基本蕴含
关于“兴”的涵义及其与“比”的差异,在朱熹之前已有十分准确的解释。如东汉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1]796唐人孔颖达说:“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已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2]271唐人皎然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3]30北宋程颐说:“兴便有一兴喻之意;比则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4]40程颐又说:“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类是也;曰兴者,因物而兴起,‘关关雎鸠’、‘瞻彼淇澳’之类是也”。[4]311综合以上各家论述,不难看出所谓“比辞”实际上也就是像“温如其玉”“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之类的话,前者语见《诗经·秦风·小戎》,后者语见《卫风·硕人》。它们不仅都是“直比”式的“比方于物”,而且还基本上都是带有比喻词的。再进一步说,也就是它们都只涉及事物的形象而并不涉及文本的义理。而所谓“兴辞”则应当是指这类句子,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卫风·淇澳》“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莹”等等。它们都是对外物的依托,都是取物为譬、引物为类,都是借助外物来托起或撑起一定的义理,或者说使主体的心怀、自我的情意得到发明、有所托依。再明确说,也即是虽然大而言之,“比”与“兴”二者都属譬喻,但是无论是它们的侧重点还是审美效果都是有很大不同的。“比”的侧重点在象在似,通过“比辞”旨在使本体表现得更鲜明、更生动、更直观、更形象;“兴”的侧重点在义在托,通过“兴辞”旨在使本体表现得更深微、更蕴藉、更婉曲、更有余意。刘勰、孔颖达之所以都认为“比”和“兴”的艺术差别乃在“比显而兴隐”[5]601,其中的缘由正在这里。南宋林景熙说:“比,形而切;兴,托而悠。”[6]750元人方回说:“比徒以拟其形状,不若兴而有关于道理。”[7]268与上文郑众、孔颖达等的说法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它们实乃一脉相承的。
弄清了郑众、孔颖达等有关“兴”的认识,接下来再看朱熹的解释。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无论是对“比”还是对“兴”,他的理解与前人都是很不相应的。关于朱熹对“比兴”的解释,最有名的就是他在他的名作《诗集传》中所说的以下两句话:“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8]1-4。可是如果将这两句论说与他在其另外两部著作《楚辞集注》《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论说加以对比,将不难发现他们讲的都是很不明确的。
综观我们所能见到的朱熹有关“赋比兴”之意的论说,他对“兴辞”的理解,一言以蔽之,就是“兴”是完全无义的。再具体说,也即是“兴”的功能就只是引发,除此之外,它就再无其他任何功用了。如朱熹《楚辞集注》说:“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9]6《朱子语类》说:“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诗》之兴,是劈头说那没来由底两句,下面方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10]2067-2072“兴只是兴起,谓下句直说不起,故将上句带起来说,如何去上讨义理。”[10]2085。
不过,对于“兴辞”的“全不取义”,朱熹只是就总体上、本质上说的,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朱熹又将其分为四类:第一,以物之有无起兴。如《朱子语类》说:“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10]2071又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芑,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不必更注解。”又说:“‘山有枢,隰有榆’,别无意义,只是兴起下面‘子有车马’,‘子有衣裳’耳。”[10]2084显而易见,在朱熹看来以物之有无兴人之有无,就纯是起一个引发作用,它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意或者义理并无什么瓜葛。《楚辞集注》说:“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也。”[9]6所谓“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也即《九歌·湘夫人》中所说的“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显然在朱熹看来,由于它也是拿沅、澧之“有”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未”,因此自然也是“初不取义”,也即“本不取义”“原不取义”的。
第二,兴而兼比。本来在朱熹那里,“比”与“兴”是有很大差别的。如其《朱子语类》说:“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10]2069又说:“问:‘“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注作比义。看来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亦无异,彼何以为兴?’曰:‘他下面便说淑女,见得是因彼兴此。此诗才说柏舟,下面更无贴意,见得其义是比。’”[10]2102看来,在朱熹眼里,比的本质就是譬喻,兴的本质就是引起。二者所言之事之所以一个必须出现,一个则可不出现,这本来就是由它们的内在本质决定的。
不过在另一方面朱熹又认为:也正是因为“兴”的本质只是引起,并不取义,所以它有时也可与“比”合而为一。如《朱子语类》说:“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腚)也好,角也好。”[10]2069仔细体味朱熹这段论述,应当说他把“兴而兼比”的道理讲得是很清楚的。有关这一点,在他的《诗集传》中也同样有体现。如《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朱熹注曰:“比而兴也。……王室陵夷,而小国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见伤为比,遂兴其忾然以念周京也。”[8]88尽管这里说的是“比而兴”,而《朱子语类》说的是“兴而兼比”,但是其具体指向显然是完全一致的。日人青木正儿说:“先举比喻然后叙说真意之法,叫作兴”,“只叙述比喻,而真意隐藏着的,便是比”[11]59-60。彼此对照,不难看出青木正儿所说的“兴”与朱熹所说的“比而兴”或“兴而兼比”实际上也是完全同旨的。
当然也需注意,在《诗集传》中朱熹所说的“比而兴”(有时也说“兴而比”)并不都是指“比”“兴”合一。在很多时候它实际上乃是指比、兴的连用。如《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熹注曰:“兴而比也。……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于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因以乔木起兴,江汉为比,而反复咏叹之也。”[8]6也就是说在以上这八句诗文里,“南有乔木,不可休息”只是用以兴起下文“汉有游女,不可求思”,除此以外别无他意。而后面四句则是以江汉之“广”之“永”与“不可泳”“不可方(桴)”,比喻汉女“端庄静一”,难以苟得。十分明显,在这里的“兴”与“比”只是前后相连,它与前面的《关雎》《麟趾》的“比”“兴”同体实是不同类的。又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对此,朱熹注曰:“比而兴也。……言桑之润泽,以比己之容色光丽。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从欲忘反,故遂戒鸠无食桑椹,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8]37这无疑也是一个“比”“兴”相连的例子。
第三,兴而兼赋。也即是说描写的虽是实物实景,但对人的情思却同样具有引发作用。这一用法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触景生情。对景、物进行直接描写,这自然是“赋”,但是由于它们同时对人的思绪又有某种启发,因而这自然又属“兴”。如《朱子语类》说:“问:‘《兔罝》诗作赋看,得否?’曰:‘亦可作赋看。但其辞上下相应,恐当为兴。然亦是兴之赋。’”[10]2098《兔罝》,诗见《诗经·周南》:“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对此朱熹注释说:“肃肃,整饬貌。罝,罟也。丁丁,椓杙声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卫内者。化行俗美,贤才众多,虽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犹如此。故诗人因其所事以起兴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见矣。”[8]5意思是说由于文王“化行俗美”,“虽罝兔之野人”干起活来也“整饬”端方,有规有矩。由此诗人遂触景生情,推想到即使这样的乡间野人也可充作“赳赳武夫”,捍卫公侯。朱熹把这样的描写称为“兴之赋”,也即可以起兴的“赋”或者说用以起兴的“赋”,别的且不说,就是这一称谓本身也把他的本旨展现得很清楚了。
不过对于这种“兴之赋”,朱熹在《诗集传》中更为常见的称谓则是“赋而兴”。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朱熹注曰:“赋而兴也。……周既东迁,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8]42与上文所说的“兴之赋”的例子加以对照,不难看出二者实是如出一辙的。但是正如上文“兴而比”“比而兴”的情况一样,在《诗集传》中在有的时候朱熹所说的“赋而兴”也同样是指“赋”“兴”连用的。如《卫风·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朱熹注曰:“赋而兴也。……言我与女本期偕老,不知而见弃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则有岸矣,隰则有泮(畔)矣,而我总角之时,与尔宴乐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复以至于此也。此则兴也。”[8]38也就是说“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是“赋”,“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以下则是“兴”,二者也是前后相连使用的。
另外,在《诗集传》中,朱熹还曾指出过一个“赋而兴又比也”的例子。这个例子见于《小雅·頍弁》:“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肴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对此朱熹阐释说:“赋而兴又比也。……此亦燕兄弟亲戚之诗。故言有頍者弁,实维伊何乎?尔酒既旨,尔肴既嘉,则岂伊异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茑萝施于木上,以比兄弟亲戚缠绵依附之意。是以未见而忧、既见而喜也。”[8]161揣其文意,显然是说在这段诗文中开头六句主要在着力铺陈兄弟宴饮的场面之盛,所以是“赋”。而“茑萝”二句一方面借茑萝缠木以比兄弟亲戚的缠绵依附,而另一方面又为下文的“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的情感抒发提供了引子,所以它们不仅属“比”,同样也属“兴”。十分明显,在这里朱熹之所谓“赋而兴又比”,实际上也就是在一段“赋辞”之后又加上了一段“兴而兼比”的兴辞。如果为了便于理解起见,朱熹完全可以在前六句之后标曰“赋也”,然后再在后六句之下标曰“兴而比也”或“比而兴也”。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让表述显得更为集中更为概括,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有故弄玄虚之嫌。
第四,全不取义。虽然按照朱熹的解说,“兴辞”都是“全不取义”的,但是由于“兴”可兼“赋”、“兴”可兼“比”,所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说它全部不涉义理,也是不够恰当的。即使像上文所列第一种情况,以物之有无兴人之有无,严格来讲,依一般的逻辑,它也同样是可作“兴而兼比”看的。因此,这里之所谓“全不取义”,实指那些既不兼“赋”也不兼”比”的“兴辞”,它们才是真正与思想义理全无关联的。对此朱熹虽然讲得并不多,但是所述也是颇为明确的。如《朱子语类》说:“兴,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鸠是挚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洁净和柔之物,引此起兴,犹不甚远。其他亦有全不相类,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虽皆是兴,与《关雎》又略不同也。”[10]2096-2097又说:“(《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先生以为无甚义理之兴。”[10]2128如果说“其他亦有全不相类”这一表述,其中也还可能包括有“以物之有无兴人之有无”的情况的话,那么,“倬彼云汉”云云,“先生以为无甚义理之兴”,所指恐怕就只能是一种完全不涉义理的“兴辞”了。
二、对朱熹“兴”论的评判剖析
总观朱熹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朱熹所说“兴而兼比”以及“以物之有无兴人之有无”实际上就是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兴”;朱熹所说的“兴而兼赋”,从郑众、孔颖达等的表述看,实际上也只能视为“赋”。至于“全不取义”的纯粹的“兴辞”,在郑众、孔颖达等的观念里,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位置的。彼此对照,不难得知朱熹对于“赋比兴”的理解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所作的解释,其差别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对朱熹的“兴”论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下面再对他的“比”论作两点补充。其一,如上所示,郑众、孔颖达等都认为“比辞”只关物象而不关义理,并且它们绝大部分还都是带有比喻词的。如上所列,《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就是典型的例子。可是对这类比喻,朱熹却标之曰“赋也”[8]36,据此则朱熹显然把郑、孔等人所说的“比辞”也看作了“赋辞”。
其二,依据上文所作的引述,朱熹显然把“比辞”分为两类:一是“比”“兴”合体,所比之事也同时出现在下句。换句话说,也就是既有喻体,也有本体。二是单独使用的“比辞”,只有喻体而没有本体。用朱熹的话说也就是“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楚辞之中那些“香草恶物之类”的描写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然而在事实上依照郑众、孔颖达等人的解释,这些“香草恶物之类”的描写实际上也同样是“托事于物”,取物为譬,引物为类的,只不过其所托之事、所托之义没有在下文直接写出罢了。举例来说,如屈原《离骚》云:“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在这里尽管诗人只写出了兴体,而要兴起、托起的对象并未出现,但是其基本理路无疑仍是晓然可见的。具体来说,其基本理路即:倩女蛾眉,丑女谮之。贤士美德,谗佞害之。就像倩女每每遭妒于丑女一样,贤德之士也往往是很难取容于谗佞小人的。很显然,在屈原的这两句诗文里是明显潜藏着这层意思的。
大概也正因为“香草美人”一类的修辞和“关关雎鸠”之类的描写具有同样的托助功能,所以王逸、刘勰等皆认为这类“兴辞”和《诗经》之“兴”是一理相贯的。如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2]2-3刘勰也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通背,原作信,据范注改)旧章矣。”[5]602如前所述,大而言之,“兴辞”也同属一种譬喻,也正因如此,所以王逸才以“引类譬喻”来说明《离骚》“依《诗》取兴”的含义。刘勰说“讽兼比兴”,虽然没有王逸说得明确,但他既然批评两汉时期“赋颂先鸣”“比体云构”“辞人夸毗”“兴义销亡”,则显而易见他也同是把“香草美人”之类的描写当作“兴辞”看的。因为两汉赋颂所缺少的就是“香草美人”之类的兴托,而如枚乘《七发》“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之类的只关物象、不关义理的比喻,则是触目皆是的。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无论在《诗经》还是楚辞中都有这样的篇目,前者如《硕鼠》《鸱鸮》,后者如《橘颂》。这些篇目与“香草美人”之类的描写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它们通篇都是写“物”的,而并不只是一些零星的或者松散的片断,仅占整个文篇的一部分。这类篇子依照朱熹“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的理论,显然也同样应当视为“比辞”,可是如果遵从郑众、孔颖达等的表述,它们无疑也同样展现的是“托事于物”,取物为譬,引物为类的路子。具体来说,《硕鼠》《鸱鸮》所潜含的理路显然是:硕鼠、鸱鸮不劳而获,缺乏善心,令人厌恶。在上者贪得无厌,不恤众庶,也让人痛恨。《橘颂》所潜含的理路显然是:橘树受命不迁,遗世独立,生于南国。人生在世,也应该以橘为师,洁身自爱,秉志不移。很显然,在这些全篇皆“物”的作品里,也都同样存在着一个由物及人的托证逻辑。我们历来所说的“托物言志”,其实都是指这类作品言的。用一两句话来描写一个外物,而不指出它所托助的本体,与用一个整篇来描写一个外物,而不指出它所托助的本体,这在具体理路上应当说是并无差异的。
如果以上所说不错,则显而易见对于朱熹的“兴”论思想,我们还可进一步再作如下总结,即朱熹所说的“比”实际就是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兴”,而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比”,朱熹则将其完全归入了“赋辞”中。至于朱熹所说的“全不取义”的“兴”则更纯粹是他个人的发明,它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所作的论述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孤立地来看,朱熹的“兴”论思想也有独到之处,但是如果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的论述加以比较,其局限性无疑也是非常之大的。
首先,他把“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些只关物象、不关义理的“比辞”作“赋”看待,太过偏狭,与“比”的称呼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比”字古形本来就是两人相并,“比方”“比照”“对比”乃是它的本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等等描写既然与“比”的词义契若合符,仅仅因为它们喻体、本体同时出现,不符合“所指之事常在言外”的私家规定,就把它们排除在“比辞”之外,这样的做法显然太武断。尤可需要注意者,这些带“如”的修辞方式,自古以来人们都将其作“比”看待,几乎可以说是人无异词,不顾这样的客观实际,而一遵自我的主观之需,对这类约定俗成的世俗观念任加改变,这样的学术理路显然也是很不明智的。
其次,认为“兴辞”只是引发,“全不取义”,这样的理解不仅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的论述两相抵牾,而且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其他“兴”论思想也是扞格不容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论所说的“兴”除了“赋比兴”之“兴”外,还有“兴寄”之“兴”和“兴象”之“兴”。所谓“兴寄”也就是有所寄托、有所托寓的意思,“兴”“寄”二者乃属同意并列关系。所谓“兴象”也即有所托载之象,“兴”字在此也是作“托”讲的。再明确说,也即无论是“兴寄”之“兴”还是“兴象”之“兴”,它们都旨在强调文学创作、文学意象应当展现一定的情感、一定的义理,实事求是地说,它们与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赋比兴”之“兴”实可谓是一脉相应的。可是如果像朱熹那样认为“赋比兴”之“兴”只是引发,“全不取义”,这样的论断不仅会破坏中国古代“兴”论思想的整体统一,而且也必然使“兴寄”“兴象”这两个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的理论源头受到遮蔽。
此外,还有一点也需注意,那就是朱熹的“比兴”学说虽不乏独到之处,但是在它里面也存在着不少矛盾。譬如“兴辞”既是“全不取义”的,那它靠什么引起下文呢?这显然就是很令人费解的。再譬如朱熹说“比辞”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而“兴辞”则不仅“全不取义”,并且其所指之事也“常在下句”。既是如此,则“比辞”显然应较“兴辞”更含蓄。可是对于二者的审美效果,朱熹却谓“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10]2069-2070,这样的表述也同样让人不知所以。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兴”论学说在中国文论史上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明代徐渭说:“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然决不可以意义说者。”[13]458清姚际恒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14]1今人刘大白也云:“(兴)就是把看到听到嗅到尝到碰到想到的事物借来起一个头。这个起头,也许合(和)下文似乎有关系,也许完全没有关系。”[15]686十分明显,以上所有观点应当说都是受到了朱熹的启发的。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不少学者甚至进一步认为“兴辞”不仅“全不取义”,而且与“赋”“比”也是不相兼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作用,那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押韵。这一看法与朱熹的认识虽然颇有不同,但显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诚然,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我们也可见到这样的注解:“因所见以起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8]12此注见于《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下。但是不难看出依朱熹的理解,这里之所谓“在东”“在公”,也应属于以物之有无以兴我之有无的灵活用法,其根本之点乃是以物之“在”以兴人之“在”。有的论者说朱熹这里仅是取“东”“公”押韵,“以声解兴”[16]17,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所以如果据实而论,最早提出“押韵”说的还应当是朱熹的好友项安世:“作诗者多用旧题而自述己意,如乐府家‘饮马长城窟’、‘日出东南隅’之类,非真有取于马与日也,特取其章句音节而为诗耳。……《王》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戍甲之劳;《郑》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兄弟之鲜。作者本用此二句以为逐章之引,而说诗者乃欲即二句之文,以释戍役之情,见兄弟之义,不亦陋乎!大抵说文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者之意也。”[17]47虽然项安世这里并非专论“比兴”,但是他认为“兴辞”之用纯在“音节”之助,对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今人何定生、顾颉刚云:“‘兴’的定义,就是:‘歌谣上与本意没有干系的趁声。’”[18]702以《关雎》为例,“作这诗的人原只要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单调了,太率直了,所以先说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只在‘洲’与‘逑’的协韵。至于雎鸠的情挚而有别,淑女与君子的和乐而恭敬,原是作诗的人所绝没有想到的”[19]676。彼此对照,不难发现他们所作的这些阐说实可视为对项氏之说的进一步发挥。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甚至还以数字起兴的儿歌乃至示威口号为例,来说明“兴辞”纯为押韵的特点。前者如“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后者如“一二三四,战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20]112-113等等。争论了一两千年的“比”“兴”概念,最后竟沦落到要靠儿歌或示威口号来加以说明,这样的情状实是令人没有想到的。
为了更进一步展现朱子“兴”论的不足为据,下面我们再作一点补充,那就是《诗经》的时代毕竟离我们比较远,在那个时代由于宗教观念的影响,当时人对于自然的崇拜与我们今天必是有异的,他们取法自然的习尚较之今人无疑也要更虔诚。只是由于诗歌创作毕竟重在情感抒发,它所追求的乃是情感的逻辑,并不像议论文那样逻辑严密,所以才导致了不少“兴”句初看上去与其下文并无联系。但是尽管如此,如果认真加以体味或者借助古人的训释,其借自然为助、崇尚天人合一的用心还是足可察见的。
举例来说,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上下文之间就很难一下子看出有什么联系。可是毛传、郑笺却说:“兴也。摽,落也。盛极则隋(堕)落者,梅也。”“梅实(果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谓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则衰。”“求女之当嫁者之众士,宜及其善时。”[2]291也就是说梅树的果实熟透之后就会坠落,追求我的庶士,也应在我风华正茂时娶我。十分明显,借助汉人对此的训释,其假托之旨就明晰多了。再如《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仪乃是人的门面装饰,人有礼仪就如鼠之有皮。直至今天,那些不顾礼仪廉耻的人仍被斥为“没脸没皮”,由此足见在传统文化中“皮”与“礼”的关系。所以《相鼠》一诗由鼠之有皮而证人当有仪,可谓正反映了上古先民托物助证的心理。有的学者因为下文的“相鼠有齿”“相鼠有体(指肢体)”与其后面的“人而无止(容止)”“人而无礼”只有押韵关系,没有语意联系,便谓“兴辞”可不取义,甚至全不取义,殊不知这完全只是一种修辞技巧,整首诗歌主要乃建基于“皮”与“礼”的象似上。“齿”与“体”之所以但取押韵,只不过是因为文势所在,也即诗歌重章叠句的需要,而灵活采用的一种修辞技巧罢了。如果没有“皮”与“礼”的象似为前提,那“齿”“体”二章诗文的写作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再如《周南·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表面看来“趾”“定(腚)”“角”与下文也只有押韵关系,但实际上这首诗歌乃是以兽中麒麟出类拔萃为助,说明公之子、公之姓、公之族也同样都属人伦之英,不同凡俗。用以起兴的乃是麒麟,而并不是麒麟的趾、定(腚)、角,只是为了诗歌押韵的需要以及形式的活泼,诗人才采用了这种比较灵动的形式罢了。如果仅仅以此为据,就贸然断定《诗经》之“兴”可不取义,甚乃全不取义,这也同样太机械了。
当然,一些诗歌纯粹流于由物及人的形式,上下句之间并无语意联系,这一现象在后世也确实是不乏其例的,但是这只能视为对“兴”的表现形式的灵活借用,我们已经不能再把它们当典型的“兴辞”看待了。如果因为这些“兴辞”变体用法的产生,就从而企图推翻前人有关“赋比兴”的论说,对它们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这样的学术习尚显然也是很不严肃的。
三、结语
由以上所述足以看出,虽然在哲学领域里朱熹的贡献非常之大,但是在对“赋比兴”的阐释上,他的这种不顾前人的传统认识,不顾“赋比兴”之“兴”与中国古代文论中其他“兴”论思想的因承关联与整体统一,一心只求理论创新,刻意彰显个人新见的做法,我们实是不敢恭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诗经》《楚辞》还是汉魏古诗看,郑众、孔颖达等汉唐学者的旧说都可以说是通行无阻、惬当周延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它们全盘推翻而另立新释。尤其需要注意者,虽然“赋比兴”的概念首见于《周礼》,而《周礼》乃是先秦旧籍,但是由于先秦旧籍每有后人附益,所以“赋比兴”的说法,也很有可能起于汉初的经师。即使退一步讲,“赋比兴”的提出确实在先秦,那汉人在时间上距离先秦也毕竟比较近,他们的诠解显然是不能轻易否定的。本来,在朱熹之前人们对于“赋比兴”的看法虽有分歧,但并不复杂,可是自从有了朱熹的新说,人们对于“赋比兴”的理解从此就变得更加淆乱了。
[1] [唐]贾公彦.周礼注疏[M]//孔颖达,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孔颖达,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唐]皎然.诗式[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 [宋]林景熙.霁山文集[M]//四库全书:第11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元]方回.桐江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8] [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 [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M].隋树森,译.上海:开明书店,1947.
[12] [汉]王逸.楚辞章句[M]//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明]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清]姚际恒.姚际恒著作集:第1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
[15] 刘大白.六义[M]//顾颉刚,等.古史辨: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 陈丽虹.赋比兴的现代诠释[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17] [宋]项安世.项氏家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何定生.关于诗的起兴[M]//顾颉刚,等.古史辨: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9] 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0]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责任编辑 朱正平】
An Explanation and Reflection on Zhu Xi’s Idea about Xingci
HAN Guo-l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 China)
By a series of analyses we can arrive at the following reviews that Zhu Xi’s idea about Bici was the same as Zheng Zhong and Kong Yingda’s idea about Xingci, and that Zheng Zhong and Kong Yingda’s idea about Bici was included in Zhu Xi’s idea about Fuci, and that as for Zhu Xi’s idea about Xingci which mean noting. It was more simply Zhu Xi’s private fabrication which was more irrelevant to Zheng Zhong and Kong Yingda’s idea about Xingci. Looked at in isolation, Zhu Xi’s idea about Xingci are also special and valuable, but its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 are too immense.
Zhu Xi; Xingci; relying on external things; meaning noting
I206
A
1009-5128(2015)05-0058-07
2015-01-05
韩国良(1964—),男,河南新野人,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论与佛道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