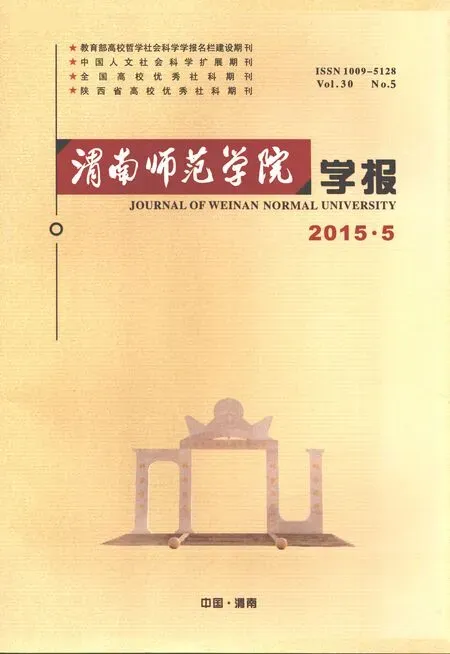论高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成因——以《农民父亲》和《血色高原》为中心
王俊虎,付玉琪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陕西籍作家高鸿从事文学创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已经声名大噪的柳青、路遥、陈忠实等知名作家之后发声,并没有遮蔽他的创作个性与创作追求,加上作品借助新兴的网络平台传播,更是获得了读者的极大关注,得到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肯定。李建军认为:“高鸿有着像大地一样朴实、深厚的底层情怀,作者有着良好的伦理感和健全的人性观,艺术感相当好。”[1]鹤坪指出:“高鸿显然不是快餐文学的制造者,他寄予小说写作显见的个人风格、表达形态、丰富性和多义性。”[2]基于对陕北农村生活的熟悉,高鸿小说中,无论是短篇小说《矿难》中愚昧顽固的广生,还是《沉重的房子》中坚韧顽强的茂生,或是《农民父亲》中不惧苦难的父亲,他们大多带有黄土高原宽广的气魄和胸襟,为了保证家族血脉的延续,不惜一切代价克服生存条件的限制,成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与精神动力。相比之下,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虽大多善良多情,却也不可避免地依附男性、充当配角,被动地接受着自己的命运。直到《血色高原》,作者才着力塑造出一系列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细究高鸿作品关于女性的描写可以发现,他对于女性地位的认识是渐进式变化的——由初时的边缘描写、侧面衬托的配角逐步成为作品着力歌颂与赞扬的主人公。
一、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一)早期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边缘书写
长篇小说《农民父亲》通过刻画伴随父亲整个生命过程的四个伟大的女性,着力歌颂了在饥荒年代谱写顽强不屈的生存奋斗史中“农民开拓者”父亲形象。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女性的形象无疑都是附属于男性的主体地位而存在。细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塑造人物时不可避免地从男性视角来审视女性——一切以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为主——她们的宽厚理解是维持家庭的基础,她们的勤劳善良则是作为婚姻一方应尽的义务。在当时的农村社会条件下,“农村人是不把女孩子当人看的”[2]111。因此对于塑造一个伟岸的男性形象来说,她们的人格特征在作品中往往起到辅助和衬托男性的作用,而相应地失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
1.大翠
在《农民父亲》中,大翠是第一个走近父亲身边的女人。出身贫寒的大翠不怕吃苦,虽然初见时带着“山东妞撒嗲气”的忸怩作态而不招人待见,粉碎了父亲对于媳妇的所有幻想 但她还是用自己金子般的心慰藉了父亲的心——同样年幼的大翠陪伴着父亲一同成长,与之共同承担着带领家族传承下去的重任。虽不受父亲的喜欢,然而勤快的大翠干活从不含糊,手脚麻利,劳动起来“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任劳任怨”[2]31,加之人缘又好,在村里有很好的口碑;在父亲为了维持全家生存而遭受批斗时,大翠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罪责,只因不忍看着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遭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侮辱,但却因此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秉着到了济南就能过上“共产主义社会”的好日子的目标,父亲一家决定逃荒,大翠始终是父亲的尾随者和支持者,最终也成为了拯救父亲一家的牺牲者——逃难途中细心的她发现高粱已经吃完了,大家却还没有到目的地,所以就不吃东西,索性将最后的干粮留给了丈夫而自己被活活饿死。当父亲发现那个鼓鼓囊囊的、大翠用生命节省下来的粮食袋子,那个最初“彪乎乎”的少女已经带着她的眷恋和不舍离开了她最亲的人。大翠这一形象虽肯定了女性的无私奉献与自我牺牲精神,然而作者在刻画时却毫不犹豫地站在男性视角,将缘由归结于妻子的义务,反映了作者此时并没能摆脱传统的家庭观念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女性仍是作为附属的一方存在的。
2.宋桂花
在高鸿笔下,寡妇宋桂花的形象应是最有思想解放意味的角色。她风流漂亮,直率坦诚,“分明是从天而降,不食人间烟火”[2]37,她是父亲一家在逃难路上遇到的“恩人”,虽初次相遇,却愿意倾其所有救助父亲一家,宁愿抛弃相对宽裕的家境转而跟随父亲去过乞讨生活。虽然在村子里有过与刘支书等男子的不良风评,然而却没有影响她如菩萨般善良的形象。不同于大翠,桂花“白白净净,面若桃花;明眸皓齿,风情万种,身段妖娆,风摆杨柳;秀发如云,漆黑明亮。衣服也穿得很体面,干干净净,没有补丁”[2]51,完全是城里女人的形象,在与父亲的相处中,桂花几乎符合父亲心中对于“爱情”的所有定义。他们二人那种突破精神防线的“狂欢”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被奶奶的对于“克夫命”的偏见而扼杀,“奶奶虽然对这个女人感恩戴德,但是并没想让她做父亲的媳妇”[2]63,这个“妖精一样的女人”[2]63比父亲大十岁,而且门风不好,所以梁家不能要这样的女人。命运多舛的她在与父亲一起躲避野猪群时走散 历经坎坷三年后才又重聚 却仍旧不能在一起——那时父亲已经在奶奶的要求下组建了新的家庭,不同于逃难路上单纯的生存危机,平淡的生活里受到来自世俗道德的刁难和冷眼,加上本身疾病的折磨,桂花最终悲凉地、有些疯癫地离开了人世。面对各方面的刁难她不曾退缩,却没能阻止厄运连连;面对调皮不懂事的“我”,她眼中的期待与温暖,却只得到“我”的刻意忽略,挣扎着不与她接近。所以宋桂花的形象又是悲剧性的。尽管她已经不甘被命运左右而独立地作出了选择,然而付出与回报的均衡还是难以达到。这个唯一点燃父亲心中爱情之火的坚强的女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仍然无力扭转悲剧性的结局——“一撮黄土收艳骨,数寸薄板掩风流”[2]191。
3.母亲(玉梅)
母亲是在逃荒乞讨到梁家河的时候遇上父亲的,并在奶奶的授意下被父亲接纳。这就导致了她在理智和情感上的双重怯懦,进而在个人定位上出现严重偏差:她并非妻子,只是帮佣。母亲的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放在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上,这必然首先出于感恩父亲的收留,再者是传统“夫为妻纲”的观念所致。曾经的“情敌”出现后,丈夫对她的态度越来越暴躁,经常吵架,有几次甚至动手打了她,村里的流言更让她难以招架。“帮佣”身份让她在面对丈夫的背叛时除了郁郁寡欢,始终不敢流露出责怪丈夫的意思。她深谙反抗也只是徒劳,毕竟他们之间并无感情,只有相伴,她既无力改变被丈夫冷落的现状,也无法让自己不在意外人的眼光和嫉妒的内心。压抑的心理负担以及长期劳作的生理负担给她以致命的打击,痨病折磨推波助澜,导致母亲最终带着不甘与遗憾悲怆离世。
4.继母
桂花和玉梅的相继离世,也让父亲的心蒙上了阴霾。随后在奶奶的干预下,父亲又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农村女人做了“我”的继母,同时又收留了她的三个孩子,这样一来更加重了家里的负担。不过继母的善良能干还是帮助父亲带领这个大家庭和睦地生活下去,她坎坷的命运在与父亲相依为命之后也逐渐变得幸福起来——父亲不只关照她,也以对亲生子女的胸怀尽心尽力地抚养她的孩子,最终因上山采药不慎跌落山崖而去世。作者的这一设定,父亲“在看继母的时候若有所思”[2]211,“继母跟父亲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父亲 继母这样卑微地存在在父亲身边 始终没有作为独立的个体的生存意识,只是丈夫、男人的帮衬与绿叶,继母形象是对女性悲苦命运的挽歌。
5.奶奶
作为封建家庭的家长,奶奶代表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她的性格具有两重性,既坚强果断又胆小软弱;既固执己见又心慈知足。她以“身体健康”为统一标准为父亲寻找伴侣,一心做着自己认为的最有利于梁家香火发展的行动与决定。实际代表着传统女性对于三从四德封建伦理道德的认可与遵从。社会的风云变化给奶奶的生活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逃荒,避难,再逃荒,最终安定在“梁家河”,她的一生,既享受了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也亲历了亲人的不断离去,既开明大义地接纳了同样出身贫寒的逃荒者,又因伦理道德的固有标准而打散了儿子一生唯一的爱情。
总的来说,《农民父亲》中的女性形象或吃苦耐劳、善良纯朴,或坚毅倔强、不拘礼数,或卑微怯懦、任劳任怨,共同点都是勤劳持家,都是家庭难得的贤内助、丈夫事业的好帮手。由此可见,这些贯穿故事之中的女性始终作为男主人公的附属存在,而失掉了独立的人格——她们无疑为了满足男性的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需求而存在,并非是“自己的”,从侧面反映出女性为了家族利益,为了全局而挣扎在命运途中的坚忍、牺牲与奉献精神。
(二)后期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重点书写
在随后的一部长篇小说《血色高原》中,作者则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女性的形象——仁慈大爱并充满抗争意识的外婆,承袭了外婆的坚忍但又保持自己个性独立的母亲,她们就像作者在后记中写到:“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也有很多人所没有的包容大度。她们嫉恶如仇,却又大慈大爱。”[3]335还有好强顽固且不苟言笑的奶奶、忍辱负重又善良开明的大妈、痴情不悔的姑姑秀秀、为爱痴狂突破伦常的大嫂柳叶,形形色色的各类女性跃然纸上,以下主要通过分析外婆与母亲的形象,从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透视作者对于女性命运书写的微妙变化与深切感情。
1.外婆
外婆的一生扮演着三个重要的角色:年轻时作为女法师,说着“贪为败处故,害人亦害己”[3]7的禅语,周游全国各地,为穷人驱魔祈福,治病救人;在躲避日本人侵略时与游击队员老吴相识,并在就医过程中暗许芳心 首次动了抛开法师身份的念头而作为女人与老吴在一起;作为法师的游历途中救下母亲并收养为女儿,自然地成为“我”的外婆,后来又相继收留了房东老爷的儿子祝俊,生下老吴的儿子抗战,在路上救助弃儿铁蛋,担任了故事中母性最强的角色。
历经沧桑的外婆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亲历了生生不息的命运之轮。苦难给了她坚强的意志,无论是在艰难生存的饥饿困境,还是在战争袭来的关头,或是洪水冲垮了家里三代人生活的厄运里,甚至在受尽批斗欺侮与劳动改造的岁月中,她的坚强、隐忍、宽恕和包容保护了这个脆弱的家庭,使之在乱世动荡中得以存活。如此忍辱负重的外婆却也只是个普通人,是个不那么“神性”的人:受到祝老爷的荫庇,她会为了遵守简单的口头承诺而强迫母亲嫁给恩人的儿子;碍于既定的封建传统,她让母亲裹小脚,也剥夺了母亲决定自己姓氏的权利;只因自己内心纠结,青梅竹马的平子终其一生都没有被她接受;面对村里人对于抗战的父亲身份的猜疑,她从不作为到不在乎的过程也是纠结的;身陷批斗风波,养子铁蛋为了一己私利的冷漠和背叛也让她不知所措……
作者对外婆的形象倾注了大量的感情,从不同的角度给了外婆不同的定位。她是封建家长的代表,自私地认定有主宰孩子们命运的权利;然而她又是充满人情味的母亲,会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尽量迁就晚辈们对于生活的希望和要求。外婆带着她作为女法师的禅性佛理,戴着普度众生的母性光环,在命途多舛的年代顽强地展开羽翼护佑着她的孩子。外婆对于外界事情与人物的判定不再依靠男人们的视角和想法,而是凭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处理事务,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行动。
2.母亲(贾张英)
“一直以来,我很敬佩母亲的性格,刚毅不屈,乐观向上。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天还没有塌下来呢。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这句话都可以很好地诠释。三十年代的战火,四十年代的饥荒,五十年代的劳改,六十年代的洗礼,母亲一步步都挺了过来,像村头的那棵老槐树,饱经沧桑,用她那巨大的树冠为我们遮阳挡雨,防霜避雪。”[3]318相比外婆的感性关怀,母亲更多了些理性的成分。母亲在跟随外婆长大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了她的坚强和善良,也教会了孩子们“爱、宽容、仁慈”。在大爱之下,母亲严于律己 坚守着道德的底线 却也保留着一些执拗与抗争的小性子。作为女性,在时代的背景下总有着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无奈,她不是个无神论者,却坚信人的命运并非天注定而不可逆转;她勤俭持家,敢于抛头露面到街市上买水饺来偿还债务;她嫉恶如仇,坚定果决,拒绝浪子回头的祝俊而坚守家庭安宁;她仁慈心软,接纳并关照曾经给予她们伤害的亲人铁蛋。
《血色高原》是作者开始转向“母亲题材”的开始,女性所起到的中心作用对家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贯穿文章中各个结点的男性形象则从侧面衬托了外婆和母亲的坚忍和大爱的美德。
二、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初探
(一)陕北农村传统观念的局限性
陕北地区历来就是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土地肥沃,但是由于多年的开垦,水土流失很严重,因此很多地方都成了光秃秃的山茆,沟壑纵横,梁茆密布,山大坡陡,河谷深切,地广人稀”[3]58。这里的山坳间飘扬着高亢的信天游,正是这样的环境才孕育出了陕北农村独特的、沿袭已久的观念:以家庭为中心,以长辈为中心,讲究家族观念,同心同德。《农民父亲》先是为了家族的生存,为了期待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目标而举家逃荒至陕北,同样也为了延续血脉,作为家庭唯一支柱的父亲在奶奶的授意下,被迫罔顾自己意愿而组建新的家庭。奶奶以家长的无可撼动的地位,左右着全家人的命运。《血色高原》里,作者对于黄土高原广袤地理的描绘,对婚丧嫁娶民俗的介绍,还有地地道道的信天游和大秧歌,都使得以外婆为主的人物展开的更加细致入微,反映了陕北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作者的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无论是因“克夫命”而终究不得与父亲厮守的寡妇宋桂花,或是为了信守承诺而被迫与祝俊结婚的贾张英,她们的幸福几乎被那无形的、森严的封建家长制度扼杀了——这无疑是由黄土高原多年的农耕文明决定的旧生产关系和旧体制造成的巨大悲剧。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乡土中国”的文化精神氛围让经济贫困、生活资料匮乏所带来的乡村人际矛盾上升到了更深的层次,从而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悲剧。作为曾经的不甘命运的抗争者,家长们的专制独断看似带着亲情和关怀,实际上则埋葬了连带自己在内的对于个性自由和独立的梦想
(二)生活时代的局限性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在观照作品尤其是人物时,始终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始终影响着人物的命运。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中国大地经历了“大跃进”、大饥荒以及多年战争,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对于农民阶级,尤其是生活在陕北地区相对闭塞的农民来说,要达到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和行为上的彻底改变,也是很有难度的。虽然作品中并没有刻意渲染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策内容,然而作为女性来讲,在那个落后的年代,相夫教子本就是天职,秉承着传统观念的人们似乎一直用着苛刻的“三从四德”来监管着女性的行为,稍有差池便如同《血色高原》中未婚生子的外婆曾经经历过的那样:“那些熟悉而亲切的面孔一夜之间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像一层寒冰冷冷地将外婆包裹了起来,孤立了起来。整个村庄一夜之间似乎也将他们遗弃,变得面目狰狞,阴森可怕。”[3]28纵观这两部作品,作者将关注目光由最初的坚定勇敢的男性角色转向了一直被忽视被弱化的女性,正是出于对女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她们善良而且软弱,在很多的时候需要依附男性存活。《血色高原》体现了作者对于母亲题材的探索,也是他对于女性地位与命运的重新审视,充满了人性的暖意。
(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时候始终从农民的心理与感受出发,似乎要赋予他们高洁的人生品质:坚忍顽强,独立自由,把他们放在道德的高处,然而作为农民的自卑与精神封闭,又使得他们故步自封,留在自己的狭小园地里。尤其对女性来讲,在本该得到满足自己的合理要求时,既要考虑为人子女的局限,又要担忧身为人妻的约束。这无疑是高鸿从男性角度对女性的解读,虽有局限,却真实生动、鲜活可感。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农民,有的人物愚昧麻木、自私自利,带有小农阶级的局限性;也有的人物具有个性解放先兆与萌芽,不盲目相信命运、仁爱宽宏、对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想法。总之,高鸿的小说作品立体而多样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农村女性地位的演变过程,体现出作者对于农村、农民,尤其是农民女性的人文关怀。
[1]李建军.另一性质的底层写作[J].当代小说,2009,(4):28-29.
[2]鹤坪.乡土写作的一次突围[J].小说评论,2010,(4):210-211.
[3]高鸿.农民父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4]高鸿.血色高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