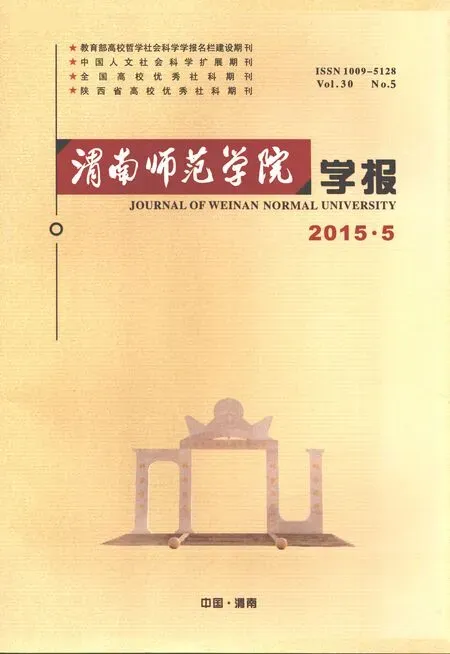魏晋时期西域宗教文化与乐舞绘画艺术
韩文慧,高益荣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历史文化研究】
魏晋时期西域宗教文化与乐舞绘画艺术
韩文慧,高益荣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魏晋南北朝是泛神论的时期,短短400年间西域大地上即出现了祆教、道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宗教文化往往是社会背景的真实反映,同时又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西域文化艺术的集大成代表是西域的乐舞绘画艺术,西域乐舞中的文学、绘画、造像艺术等因素都受到当时宗教文化的影响。文章从西域地区流行的祆教、佛教、道教三种宗教文化出发,试图寻找其对西域乐舞、绘画艺术的影响与贡献。
魏晋;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西域;乐舞绘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众多民族逐渐兴起,纷争不断。此时,文化反而在政治的夹缝中异军突起。这一时期的西域乐舞、绘画艺术发展较快,其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很大,祆教、佛教、道教先后经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宗教音乐、宗教演出开始盛行,并出现了许多宗教石窟及绘画,这都成为西域地区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是现实世界在人类想象中的一种投影,每一种社会、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宗教反映出来。恩格斯说:“宗教是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1]250如果我们要寻找西域文化对西域戏剧的影响,那么,宗教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一、祆教文化与歌舞、幻术
在中国史料记载中,有关祆教的记载始于公元5世纪中期,据推测可能是从当时奉北魏使命出使西方的董琬等的见闻材料中所得。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创立。在我国俗称“拜火教”,又因其崇拜日月星辰等天象,也称为“祆教”,“祆”字从“礻”从“夭”,为祭祀天神之义。一种说法认为祆教于公元4世纪传入新疆。还有人指出:“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西域应当就有祆教影响。”[2]总之,祆教传入后,为西域多数人所接受,至今为止,祆教的拜火习俗仍然留存在新疆当地维吾尔民族居民的生活当中。维吾尔婚俗中,新娘上车前,要将其用褥子或毛毯抬着在门外的火堆上转一圈;探望生病的孩子时,要用燃着的松柏树枝的烟将客人熏一熏才能进门;婴儿夜晚爱哭闹时,也习惯用松柏树枝的烟熏一熏,这都是祆教文化在西域新疆民族中的遗迹。
祆教传入西域后至南北朝时期已较盛行。《魏书》卷102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3]2265“(高昌国)俗事祆神,兼信佛法。”[3]2243这里所记以祆教为主,佛教处于次辅地位;《朝野佥载》卷30中记载有关祆教的音乐:“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至祆前舞一曲。”[4]57从记载中看,祆教祭祀活动中,琵琶、胡笛是其主要演奏乐器,鼓则用来乐中击节,使祆乐节奏分明,铿锵有力。在《旧唐书·睿宗记》中记载了有关祆教舞蹈的概况:“初,有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5]161这里所谓僧婆陀,应是西域伊州一火祆教教徒。伊州有祆庙,祆主名翟槃陀,与此婆陀都应是祆教徒。“表演‘灯舞’形式,燃灯上千炬”,“基本舞蹈词汇则是‘联袂踏歌’即手拉手”踏节而歌。唐初诗人张说所作《踏歌词》对此舞有生动的描述:“龙街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锦阙万重开。”这种“龙街火树千灯艳”和“灯轮千影合”即是西域祆教徒具有代表性的祭祀舞蹈形式。《新唐书》中所说的“连袂而歌,唱《葱岭西曲》”[7]307,正是指从西域来的祆教乐舞。可知能歌善舞的西域各族人民在信奉祆教后,又发展了原有的乐舞,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推进了西域的乐舞,可以说对西域乐舞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斯坦因在敦煌所获文书中有唐光启元年书写的沙州、伊州地方的地志残卷。其中关于伊吾即今哈密的火祆记有:“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这里“素书”为“素画”的误写。
我国西域乐舞中的幻术,也来自于祆教。《两京杂记》卷5称:“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正因为祆教教徒信天神,所以他们富于天文知识。《魏书·西域》“悦般”条称:“其国有大术者,蠕蠕来抄掠,术人能作云雨狂风大雪及行潦,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3]2269这实际上是祆教教徒善识天文,能呼风唤雨的写照。而祆教教徒祭祀时,都有乐舞伴奏,《朝野佥载》卷30称:“有僧祆神庙,没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4]49祆教对龟兹佛教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现在遗存于库车、拜城的龟兹佛教石窟中,有最具代表的中心柱支提窟,其造型为窟门敞开,中间为中心柱,把窟分成前后室,并在中心柱两旁辟为甬道,这是明显依照早期宗教仪式形式修筑的。这种左右开通道的建筑结构即源于祆教文化。
二、佛教中的歌舞壁画
佛教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传入西域新疆,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发展至它的顶峰时期,当时的西域诸国都信奉佛教,佛事频繁,诵佛扬义的佛乐也因佛事的繁盛而兴盛。《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寺庙千所。”于阗有“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3]2262。这一时期西域僧人趁势逐次进入中原宣扬佛法,翻译佛经,散播佛乐。从西域到中原,寺院林立,高僧辈出,大大促进了丝路各地石窟、寺庙建筑和雕塑、绘画、佛乐以及佛剧艺术的大步长进。
佛教经典文学对我国乐舞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的诗化与乐舞故事的情节化上,佛僧太虚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其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文学文体的变化上:“佛教之经典翻译我国或是五七言之新诗体,或是长诗。长行之中,亦有说理、述事、问答,乃至譬喻等,与中国文学方面,亦有极大之裨益。至于唐朝以后之文体,多能近于些事顺畅以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教之熏陶也。……梁启超谓:我国之《孔雀东南飞》之长诗,即受此影响,或可尽信。”[7]35另外,他还论述到佛教对中国戏剧文化的影响:戏剧,中国之戏剧,多是演前人之故事,或惩恶,或劝善。而佛教之戏剧亦然,如《目连救母》《归元镜》等,移风易俗,使人回恶向善,皆大有功于教化也。
20世纪初期,探险家在龟兹(今新疆库车)昭怙厘佛寺中发现了一个不平常的舍利盒,经过剥离,舍利盒盖身周围绘着一副形象极为生动的乐舞图,它的编制似有歌舞戏的规模。日本《美术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熊谷宣夫的文章,对舍利盒及其绘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8]这只舍利盒上的乐舞图,是西域著名的歌舞戏“苏摩遮”(乞寒胡戏)的真实再现,表现了古代西域人民的生活习尚与宗教信仰。那些现世苦修,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佛教精英们,总是把伎乐歌舞当作天国享受幸福的一种美好象征。同时也说明,优美动人的龟兹乐舞已经很自然地被佛教利用,成为传播佛教教义和渲染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的十分形象有力的工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西域歌舞戏剧才能留存得更久远。
佛教善于借用音乐舞蹈这种美的形式宣传教义,吸引僧众信徒。《大智度论》中说:“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易 ,是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9]268乐舞被佛教的利用是多功能的,既要使众生“心柔软”“受化易”,又要用乐舞作为向佛的供物。《天宫伎乐图》除有众多演奏乐器的伎乐外,还有托花盘、舞璎珞、献宝镜的天人,这些都表示了对佛的供养。
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第188窟窟顶绘有一副“无恼指鬘缘”的因缘故事画。在《贤愚因缘经》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舍卫国一辅相,巨富,生子曰无恼,勇武有力,后入一婆罗门受教,聪明过人,婆罗门师妇看中欲诱。一次,波罗蜜师与众弟子外出,留无恼在家,师妇多次引诱,被拒绝,恼羞成怒。师来,毁面破衣,诬无恼奸她。师怒,阴为谋害,假说欲成正果,必须于七日内杀千人,斩千指为鬘。无恼按师言,外出杀人,杀到999人,城内无人敢出,无人可杀。其母看见无恼饥饿,担饭来,他要杀母成千人。母斥责之,他告其故。母说,斩指可以。此时,佛现。无恼欲杀佛,追之不及。佛为说法,大彻悟,放下屠刀,成比丘。”这个因缘故事在壁画中具体表现为:佛脸向左侧坐于方座上,头上戴有塔式宝盖,正欲向佛的头部劈去。这是在无恼欲杀其母时,佛突然出现,无恼转而欲杀佛时的情景。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38窟凿于西晋时期,根据石窟不同的窟形有不同的壁画题材风格。此窟窟顶有一副“乾闼婆作乐赞佛缘”的故事画,主题思想是乐舞供养。“供养”是佛教教徒进行宗教活动极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在佛典中不遗余力地宣传“供养”。如果没有众人的供养,就无法养活一大群僧尼,从而佛教就无法存留。此乐舞供养故事出于《撰集百缘经》:在印度舍卫国南城有一乾闼婆王名善爱,长于弹琴,并善歌舞,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所以骄傲自大,“佛知其意,寻自变身,化作乾闼婆王,将天乐神般遮尸弃,其数七千,各个执琉璃之琴,侍卫左右,善爱便自取一弦之琴而弹鼓之,能出于七种音,令众人欢娱舞戏,昏迷放逸,不能自持。尔时如来复取般般遮尸弃琉璃之琴,弹鼓一弦,能出于数千万中,其声婉妙,清澈可爱,闻者舞笑,欢娱爱乐,喜不自胜。时善爱闻是声已,叹未曾有,自鄙惭愧,即设诸杀肴膳,供养佛僧”。
佛要把深刻的道理讲给沉迷的人们,唤醒他们并带给他们天国的幸福,因而在说法至微妙处,常伴有音乐、歌舞,天人伎乐,从各个方面涌向画面,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乐队,富有浓厚的情趣。
佛教经典成功地与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艺术,其中也包括音乐、舞蹈、杂技、戏剧形式相融合,使之艰涩难懂的佛经说教世俗化与形象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为西域乐舞戏剧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
三、道教中的符咒塑像
道教是中国汉民族的传统宗教,源于古代的“长生不死、肉体飞升”等巫术及秦汉时的神仙方术思想。它产生于东汉顺帝以后,当时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的普遍瓦解为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道教的诞生正好可以回应汉末社会天崩地裂式的大变乱,从而证明社会史的理论,即宗教的形成与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7]33
《隋书·地理志》称,汉末“是时受道者,类皆兵民,胁从无名之士,至晋则有士大夫矣”。佛教的传入,大大刺激了汉族原有的有神论思想,特别是黄老、神仙家思想,从而加快了道教的建立。因此道教的发展,是由本土文化与外来的各种文化相撞击、交流、吸收而形成的。关于道教形成的社会背景,有学者指出:第一,有神论大泛滥;第二,统治者对神仙方术的关心;第三,经济衰落,社会危机加深;第四,社会动荡;第五,佛教传入。[10]17
西域先民信仰道教的历史大约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东晋末年,高昌已有道教流传,南北朝经隋唐迄宋元时期,道教在西域地区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唐代在西域的天山南北修建了许多道观,如伊州所属伊吾县有祥麰尼观、大罗观,柔远县有天上观,高昌有□汤观、周楼观等。隋唐时代,回鹘人已是高昌的主体民族,回鹘人信仰道教是十分自然的事,从吐鲁番发现的关于道教的大量文物也充分说明当时西域人中信仰道教的人确实不少。有关道教符咒的经籍在《道藏》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这些著述内容复杂,携带了许多易学的信息。所谓“法术”首先是指以符和箓为本的道术秘法。由于符箓在体式上已有象征的特点,这就会很自然引入易学的思想理念。故而,符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蕴含着易学的旨趣。
“居不可无桃”是中国也是西域独具特色的文化,其表达了人们要求吉祥、平安的愿望。西域人对它情有独钟,桃符—桃木浮雕上有钟馗,人们相信桃木能治鬼避邪。有关桃的神话传说在中国古代西域有很多,相传他可以治恶鬼。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用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称为“桃符”,春联就起源于“桃符”。
东晋以后,道教为阐发教义、抵抗佛教,争取信徒大量构造了他们自己的经典。从此开始注重形象的宣传,于是造像绘画之风大大兴起,北魏时的道教里出现了“佛道二尊像”。郑午昌在他的《中国画学全史》中指出:“大佛固盛极于时,同时北魏道士若寇谦之等,亦尽力宣扬道教,后至渐效佛徒所为,以绘画点苏造天尊之图像。于是前此为少数信者零碎之道教画,至是乃大盛,几与佛画并行于中国。然其所谓道教画者,终不能拖佛之窠臼,是视道家善佛画者兼及道画,故如出一手,亦我国自魏晋以来,故以浮屠老子并称,而道释画为一流之故欤!是可谓道教画者,及佛画之化身。”[11]39
这一时期,道教所行乐舞对西域乐舞戏剧多有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成熟期,道教经典、斋仪逐渐形成了完备的体系,道教音乐也随着道教的成熟而初具规模。道教大约于公元4—5世纪即东晋十六国时期传入丝绸之路中西段。在丝绸之路中道的今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出土的随葬物品中,有大量反映道教的内容。吐鲁番是西域丝绸之路中道通往中原的要隘,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昌地区各邦国与中原各代政权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北魏以来,高昌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麴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道教文化也随着高昌汉王国与中原各地的广泛联系交流而传播至盛。从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中足以明鉴:“北凉十四年(公元418年)的《韩渠妻随葬衣物》文书末尾写有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在一件高昌和平元年(公元551年)的衣物疏中,绘有道教的符箓。符纸朱书。上方正中绘画天神形象,左手持刀,右手持叉,神像写有符咒”,间或能辨出“黄天帝神”“鬼不敢来近”“急急如律令也”字样。“在同一时期另一件出土文书中,还见到有道教符”。诸多出土文物足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一带道教文化传播的盛况。北魏时期,西域乐舞已大量外传,尤其是龟兹乐舞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新颖,深受中原仕女的赞赏和喜爱。《通典》卷143称:“自宣武(北魏世宗500—515年)以后,始受胡声,泊于迁都,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鼓、铜钹、打沙锣、胡舞铿锵镗镗,洪心骇耳。”龟兹乐如此赏心悦目,必然为道教人士所羡慕,并撷取其精华为道教服务。
祆教文化对西域歌舞戏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祆教祭祀歌舞、幻术中,同时也表现在一些祆教石窟建筑中;佛教文化对西域戏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石窟的绘画艺术及一些有情节的佛本生故事上,又融合了戏剧的音乐、舞蹈、杂技,为西域乐舞提供了新的形式;而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家宗教,主要表现在神仙方术、道教鬼神的壁画以及符咒中。从而,我们可以清楚地勾勒出这样的脉络:一是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文化的繁荣及其发展轨迹;二是别具艺术魅力的西域宗教文化与乐舞绘画艺术相融合,形成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歌舞戏剧。西域宗教文化对西域乐舞绘画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促进西域文化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周菁保.西域祆教文明[J].西北民族研究,1991,(1):27-33.
[3] [北朝]魏收.魏书:卷一百零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唐]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张曼涛.佛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书店,1987.
[8] [日]熊谷宣夫.从库车带来的彩绘舍利盒容器[J].美术研究,1957,(2):14-27.
[9] 谭树桐.龟兹佛教文化论集[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
[10]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1]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朱正平】
The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 and Dance,
Drama and Painting Ar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Period
HAN Wen-hui, GAO Yi-r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rts, Sha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Wei and Jin dynasties is a period of pantheism, only 400 years witnessed the Zoroastr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other religions uprising. Religious culture is the real reflection of social background, and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Wei and Jin period,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art is represented of the western dance, drama and painting art. The factors of the western dance and drama such as literatur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art we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culture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 such as Zoroastrianism, Buddhism, Taoism, tries to find its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dance, drama and painting art.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Silk Road; religious culture; western religion; dance, drama and painting
K235
A
1009-5128(2015)05-0083-04
2014-11-24
甘肃省教委科研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YCX14134)
韩文慧(1985—),女,新疆昌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高益荣(1958—),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戏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