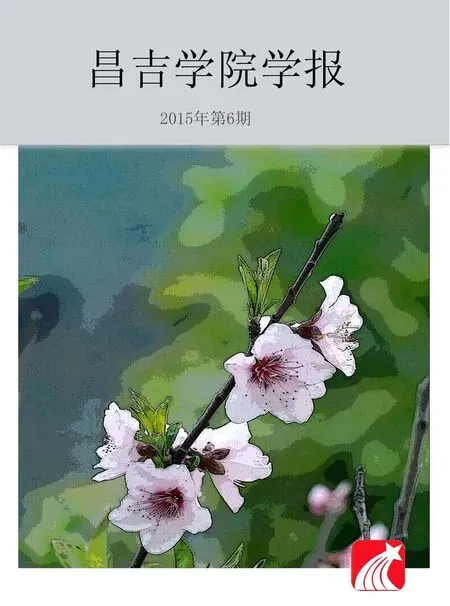乡土·性别·死亡
——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小说叙事主题研究
杨慧娟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乡土·性别·死亡
——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小说叙事主题研究
杨慧娟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马金莲是出生于80后的宁夏回族女作家,近年来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影响力。她的创作以精细的笔墨如实呈现了西海固这片土地上回族人凡俗的日常生活,并着力挖掘着“苦土”之上人们生存的美好与温情。在细致朴实的叙事中,作家始终关注着西部乡村回族女性的生活命运,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回族女性形象。她的笔下,浮沉在岁月长河中的乡人们的生命尊贵而丰饶,即使死亡,亦有一种肃穆宁静的风度。马金莲的创作扎实、厚重,是优秀的文学永远来自于大地与泥土的最佳证明。
诗意家园;悲情乡村;回族女性;死亡
如果要在“作家马金莲”之前加上几个标识性很强的定语的话,宁夏西海固、回族、80后、女作家都是令其辨识度极高的语汇。90年代宁夏文学林郁郁葱葱成长之时,因了文学发展的良好氛围,宁夏回族女作家的创作也默默积蓄着灵感与力量,不断成长着。近年来,宁夏回族女作家以其独特的少数民族女作家身份在文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回族女性独特的视角书写着西部这方天地的人生故事,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出生于1982年的马金莲就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位。她始终执著书写着西海固这片土地上回族人凡俗的日常生活,并着力挖掘着底层生活中人们生存的美好与温情。在对宁夏西海固回族生活、心理、风俗的表达和书写上,马金莲的创作努力提炼出别具意味的叙事主题。
一、诗意亦悲情的乡土叙事
同大多数西海固走出来的作家一样,马金莲也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正因为个人生活经历与成长的心路历程都与这片“苦土”有着千丝万缕、深入肌理的联系,在其创作中,倾情书写这片自己深爱的“苦土”成了马金莲创作的主要题材。在她笔下,乡土呈现着不同的面影:一方面,面对故土经济的欠发达与物质的匮乏,作家心怀深刻的依恋,倾情书写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生存的自足与温情,乡土在其笔下呈现出了“诗意家园”的面影。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了作家“在场者”的身份,也无可避免地描摹这方“苦土”之上的“丑”与“悲”,直视生存苦难,乡土由此亦凸显出“悲情乡村”的面影。
《父亲的雪》一篇中,马金莲细细描摹着一个倔强小女孩失去父母后寄居在叔婶家的成长心路历程。父亲意外离世、母亲无奈改嫁他乡,善良叔婶的收留和养育以及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后爸的默默关爱与陪伴,展示出的是艰难时世中民间珍贵的道义与人世的温情;《远处的马戏》中,阿西燕和阿依舍两个小姐妹赶集归来碰上了马戏团,孩子的新奇终于在昂贵的门票前打上了休止符,贫苦人家孩子的懂事让人心疼;《旱年的收藏》中,9岁的芒女到地窖偷萝卜,她眼中地窖里萝卜铺天盖地的盛景让读者想到了农家人匮乏紧巴的日子,但9岁芒女充满童趣的经历及思索却也令人不觉莞尔;《六月开花》书写了农家峰儿分窝时人们忙碌的场景,在小主人公赛麦眼中,大人们的忙碌、大姐的害羞与甜蜜、二姐的调侃与打趣,都是那么难于理解,唯有梅花表里金色的颤巍巍绽放着的金梅花让赛麦好奇万分……这些小说中都写到了生存的匮乏和艰辛,但是经由小主人公童真的目光牵引,生活的苦难成为了定格的背景,而物质极度匮乏之中孩子们充满童真童趣的念想与愿望则显得格外珍贵和令人心疼。马金莲在着力展现乡土社会生存状态的同时,将困顿的现实与艰难时世中的诗意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诗意的畅想中寄托着作家超越性的人生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几篇小说均运用了童年视角进行乡土叙事。马金莲以儿童感性、纯然、未经世俗濡染的视界呈现广阔的成人社会、现实生存秩序。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诗性记忆。在马金莲儿童视角的小说中,童年的回忆充满了使我们有切肤之感的细节。她所书写的童年记忆、乡土经验、个人成长等等主题均带有作家自身的生命经历与情感记忆,凝聚着作家个体的情感积淀与生命体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叙事作品不仅蕴含着文化密码,而且蕴含着作家个人心灵的密码。”因而,“依据文本及其叙事视角,进行逆向思维,揣摩作者心灵深处的光斑、情结和疤痕,乃是进入作品生命本体的重要途径。”[1]在以童年视角展开的乡土叙事中,泄露的是作家如同孩子怀恋母亲一般的对家乡的温情眷恋,使其笔下的乡土流溢出诗意家园的光辉。
马金莲出生成长于“苦甲天下”的西海固,正是因了“在场者”的身份,作家也无法避免地描摹着这方“苦土”上的“丑”与“悲”,直视着生存的苦难,令其乡土叙事带上了悲情色彩。《掌灯猴》中,生存的艰辛让人窒息,穷汉程丰年的女人为了一家大小的生计,做了“掌灯猴”。但为了男人的尊严和女人的自尊,女人做了五年“掌灯猴”却一直隐瞒丈夫。作家对“配角的配角”(李进祥语)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描写,饱含着人世艰辛的苍凉与无奈。《糜子》中,农人们用无比辛勤的劳作和满心的愿望努力地获得丰收,而这种劳动与期待却被糜子即将成熟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破了,爷爷深夜离家讨生活,奶奶一夜间老去了好几岁,农人们视为生存根本的粮食给了他们期待,却最终打破了人们关于生的美好愿望。在这里,乡土与苦难、匮乏、悲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马金莲笔下,还有这样一类作品,作者通过对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的农民形象的贬抑化塑造,表达出的是鲜明的恋乡恋土情和对城市文明的排斥与背离。小说《庄风》、《富汉》中,外出务工赢得财富的乡人们最终均以惨烈的死亡和悲戚地归乡作为终结。《少年》中,两个背井离乡远赴广州打工的孩子,在外经历了挣扎苦痛最终归乡,乡土终究成为他们无法拒绝的生活方式和永远亲切的气息。
二、世俗又超俗的女性叙事
作为一名回族女作家,马金莲创作的另一独到之处在于她在笔下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回族女性形象。清贫、洁净、忍顺、坚韧、向善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品格。对于西海固回族人而言,伊斯兰教不仅仅是“谨守拜功,完纳天课”的坚定信仰,更是他们浸润其中,深入生命肌理的精神资源。也正是源于此,在马金莲的作品中,鲜见宗教许多的清规戒律,更多的却是一种与世俗生活水乳交融,带着道德教化色彩的宗教情怀,这些使她的作品带有了独特的内在精神力量。马金莲小说叙事中的回族女性形象,有的命运多舛,历经了人生的大悲大恸,有的艰辛度日,在生存的困顿中默默抗争……作家对西海固回族女性生存的苦难和坚韧的痛楚感和真切关注,在这些回族女性形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在关注本民族女性的情感、命运,尤其是心灵的疼痛感这一点上,作为回族女作家的马金莲已然抵达了许多男性作家无法到达的深度。
《五月散记》中八十三岁的四奶,九岁成了童养媳,一生生养了六个儿子却个个在壮年离世,四奶含辛茹苦拉扯孙儿长大,虽然历经人生苦难,但四奶没有“祥林嫂式”的倾诉,只是如“一潭秋水似的平静”。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四奶睡在母亲为她缝的糜子袋上——“总是手脚很收敛地侧身睡上去。腿蜷着,双脚并得齐齐的,两只手散放在枕边……四奶睡觉总是收敛着手脚,她的睡相拘谨、沉稳、平静”。[2]在这里,作家写出了一名回族老人对自身的要求,对命运的忍顺。正是在对回族人世俗生活的点滴书写中,马金莲引领着我们去感受和理解回族人深入肌理的精神内核。除了老人,回族少女和“碎媳妇”也是马金莲倾力书写的对象。《永远的农事》通过孩童的眼睛捕捉了一个农家姑娘“烂眼子”在日复一日的农事中的成长轨迹,让读者领略了“永远的农事”之艰辛与劳作之美。作家在《丑丑》中塑造了一个别样的回族少女形象。她倔强、美丽、大义、敢于自主选择自己的幸福,甘为族人承担劫难。她对于命运的抉择、爱情的坚贞、家族的大义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一回族少女身上也许寄托着作家一种超脱世俗的美好理想:回族女性面对自己的命运,不再是一味地忍顺,而是勇敢争取自己的幸福,体现了女作家对回族女性命运的探索和关注。《碎媳妇》中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一个初为人妇的回族女子的谦恭、隐忍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中国当代文学长廊贡献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无疑,作品的叙述是细密而意味悠长的,婆媳、妯娌之间的微妙情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严丝合缝且无孔不入。在这篇作品中,马金莲精密如实呈现的不仅是西北乡村的农家日常生活,更是“乡土中国”女性生存伦理价值的缩影。《搬迁点的女人》《窑年纪事》中回族女人凭借自己过好日子的信念和一双巧手把一片荒地、一间破窑经营成了有声有色、热热火火的日子,马金莲以从容不迫的笔触道出了在岁月磨砺中,一个勤劳本份的回族女人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不可或缺,向读者许许展开了一幅动人的西部乡村回族女性生活命运的画卷,在其细致朴实的描述中,亦全面展示了时代变动当中西部乡民们的日常生活面貌与内心的期待与向往。
三、宁静而尊贵的死亡叙事
马金莲也是一位勤勉、虔诚的作家。作为一名女性,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是人生中必须的角色。尤其身在农村,这些角色背后所包纳的义务和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远胜过城市女性,因此,在这样的情状中能够坚守内心对文字的挚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金莲做到了。也许正是源于对文学的这份勤勉与虔诚,马金莲在自己的这方“文学园地”里默默耕耘,收获颇丰。发表于2013年《民族文学》第9期后被《小说选刊》(2013/9)、《小说月报》(贺岁版)相继转载的中篇小说《长河》就是这片园地里最美好的收获,可以视作马金莲近年来创作的一次超越。《长河》是一篇叩问生死的小说,荣获《民族文学》2013年度奖后,评委在颁奖词中写道:“就女性叙事价值而言,《长河》可以说是一部当代《呼兰河传》,和萧红一样写出了家乡父老乡亲的苦难中的人性美,写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作品在平淡叙述中蕴藏着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信仰,来自优美而质朴的语言,也来自对人性、对自然、对灵魂的无限关怀”[3],给予了作品高度的评价。
《长河》中书写了村庄里的四次死亡:正值壮年的伊哈因意外猝然死去、年仅12岁的少女素福叶因心脏病突发失去了生命,久病卧床的母亲被疾病耗尽心力凄然离世,德高望重的穆萨爷爷在静默无言的大雪中悄然无常。这四次死亡的书写对象中有童年、青壮年,也有中年、老年,有男人也有女人,对他们而言,死亡有时在最没有预想的时刻猝然来袭,有时又像悬在人们心头的一把利剑,让久病缠身的人们在现世的煎熬中苦苦等待着它的来期……马金莲通过不同群体、不同形态的死亡的书写,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死与生均是人生常态,如影随形,每个人终会面对。正如她在《〈长河〉创作谈中》所言:“从孩童到中年到老年,从男人到女人,我发现死亡是每一个生命都要面对的课题,区别只在于时间的迟早。于是我集中书写了死亡。就像生一样,死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4]值得注意的是,《长河》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书写了死亡,更重要的是运用童年视角,从少年“我”的眼中,牵引出了村庄中成人、孩童以及“我”对死亡的认识与思索,最终表达了更深层次的生死观:生弥足尊贵、死亦宁静大美。正值壮年的伊哈在秋季意外丧生,“我”看见成人世界对生命猝失的惊愕与痛心,没有“海底耶”的伊哈葬礼带给了孩子们失望,却也展示着民间世界的艰辛与温情;少女素福叶死于万物竞生的春季,朝夕相处的伙伴的离世,让成人世界惋惜,更使“我”对死亡开始有所思索;经历了久病卧床的母亲在四季的更替中逐渐病重走向死亡,也目睹了她与父亲的恩爱、斗气、怨嗔……亲人的死亡带给“我”的是切肤之痛和成长的洗礼;德高望重的穆萨老人在无言的大雪中悄然无常,在对老人一生的回顾中,一个怀抱信仰、笃重情义、勇敢担当的回族老者形象跃然纸上。老人的葬礼庄重肃穆却也洋溢着喜气,“男人们头上的白帽子像一盏盏明灯,擦过漫长的生死路途,照亮了我们的眼睛”[5],这一次,“我”感受到了死亡的高贵、宁静和美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可以说,在马金莲笔下,四季农事如一首无韵的歌谣,周而复始却动人依旧。而浮沉在岁月长河中的乡人们的生命尊贵而丰饶,即使死亡,亦有一种肃穆宁静的风度——这正是《长河》带给读者最独特的审美体验。
作为一名80后的宁夏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创作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始终执著书写着西海固这片土地上回族人凡俗的日常生活,并着力挖掘凡俗生活表象之后人们生存的美好与温情,尤其是对于回族女性日常生活以及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描写,使得她的小说深深地烙上了特定地域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宁夏文坛的后起之秀,马金莲深受石舒清等作家的影响,她的语言细腻绵密,文风平实质朴,其小说无论从主题以及艺术上都趋向于向宁夏文学整体价值与意义的靠拢,努力追求着对“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6]等的书写和表达。在默默地坚守与耕耘中,我们期待随着题材的拓宽与思考的深入,宁夏80后回族女作家马金莲能在“自己的园地”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4.
[2]马金莲.五月散记[J].六盘山,2005,(2):23.
[3]新华网.马金莲《长河》等获2013《民族文学》年度奖.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3-12/29/c_ 118752960.htm
[4]新浪网.“马金莲的博客”.《长河》创作谈.2013年10月2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64acd80101ge9p.html
[5]马金莲.长河[J].民族文学,2013,(9):53.
[6]贺绍俊.宁夏文学的意义[J].黄河文学,2006,(5):121.
I206.7
A
1671-6469(2015)06-0001-04
2015-09-20
宁夏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宁夏回族女作家创作研究》(SK1308)成果。
杨慧娟(1983—),女,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回族文学、女性文学。
——评钟正平《知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