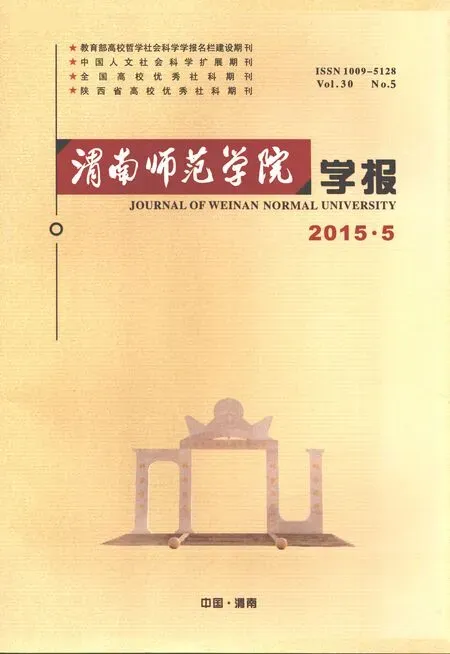晚明狂者精神复归与儒学平民化趋势加剧
单 磊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政治与哲学文化研究】
晚明狂者精神复归与儒学平民化趋势加剧
单 磊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晚明时代,程朱道统愈显腐朽,与理学抑制人性的律己主义方向截然不同,心学对人内心的自律性深信不疑,“致良知”逐渐被社会接受,体现“人”的主体性的狂者精神得以实现高级复归。这有力地促成了陈旧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消解和新型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由此,程朱理学塑造的等级秩序趋于瓦解,平民意识逐渐觉醒。在以心学为思想基础的狂者精神激荡下,泰州学派掀起的儒学平民化运动导致中国文化的平民化进程加速,平民知识群体形成。
晚明;狂者精神;泰州学派;平民化
学术素养是一种话语权。是否拥有和多大程度上拥有这一话语权,决定了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自然也决定了该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治人”的“劳心者”与“治于人”的“劳力者”(《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之间的差别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点。
隋唐之前尤其是魏晋时期,贵族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伦理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学术素养,尤其被以注重道德规范的经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所支配。诚如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所言:“不过分地说,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由于作为社会主宰者的资格是来自他们的人格,所以实际上人格的培养又在于学问。……而这一主宰,又因此是知的道德的主宰,所以在这里学问就成为支配民众所不可缺少的机能了。”[1]99在一个等级森严而层级间流动僵滞的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学术素养如何,往往并非取决于依赖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的后致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先赋性因素或转化为社会性因素的世袭秩序,简单地说,就是出身。这里的出身不仅指隐含着社会阶层底蕴的家族背景,还包括政治集团、活动地域、师承源流等,而这些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或群体的文化视野、思想观念、学术见解等。因而,学术思想的变迁与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瓦解或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既可以是后者的体现,又是促进后者实现的内在动力。
田余庆先生将“由儒入玄”视为魏晋时期士族得以形成的必备要素[2]35,就颇具洞见,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变迁对社会阶层或群体形成的重要影响。处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士族垄断文化资源,比寒门子弟更便于获取知识、提升素养,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政治强化贵族门阀统治,反过来用这一社会性规则来强化有利于巩固这一规则的学术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儒入玄”使得衰周至秦汉之际的平民化趋势发生逆转。自“唐宋变革”以来,平民化才得以继续向社会深层扩展。
如果说“由儒入玄”是魏晋士人对抗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进路,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由理入心”是晚明平民知识群体对抗以程朱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进路呢?循此思路,本文以学术思想变迁为切入点,探讨肇端于先秦时期的狂者精神在晚明时代的复归对儒学平民化趋势加剧、平民知识群体形成造成的深刻影响。
一、心学勃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狂者精神复归
狂者精神不是晚明时才诞生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狂”的基因。《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国文化的狂者之旅大概自此开始。之后,狂者精神饱经历史沉浮,不断调适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却始终保持狂者精神的思想内核。
在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中,“狂”曾是知识群体普遍的精神状态。“处士横议”的传统、“游侠”的传统、自由文人的传统、浪漫的诗骚传统、绘画的大写意传统、书法的狂草传统等人文艺术的固有性无不与狂者精神有不解之缘;儒家的圣人理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情怀、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皆为狂者精神的构建提供了理念和学说的基础;先秦士狂、魏晋诞狂、唐代诗狂及明代圣狂是狂者精神在不同历史段落的特异呈现。[3]其中,“圣狂”是对明中后期心学领袖王阳明的赞许性称谓。
中国古代是一个个体人格不受重视、平民意识十分淡化的时代,本应居于历史创造和历史认识主体地位的“人”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心学激荡下的狂者精神试图改变这种窘迫局面。程朱道统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无法满足新兴阶层试图掌控话语权的欲望,体现“人”的主体性的狂者就诞生了,晚明越来越多的狂者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走向其反面。与程朱理学抑制人性的律己主义方向截然不同的是,心学对人内心的自律性深信不疑,“致良知”越来越被知识阶层所接受。
心学是儒学在特定历史段落的升华,其内在动力之一便是狂者对腐朽的理学思想的清算。程朱理学是官方借以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认为是代表明廷意志的国家思想。程朱理学所塑造的道德规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扮演着积极进步的角色,延至明中期,衰败迹象已然暴露无疑。装腔作势的伪道学流毒人间,将人毒害成扼七情、灭六欲的儒学祭品。理学家们最不能容忍“狂”的气息,对“狂”的解释几乎都是负面的。明廷试图通过官方意志控制御用刀笔吏宣扬客观上已经过时的旧观念,而对民间社会的离心倾向十分恐惧,动辄斥为“悖谬”“异端”。文化专制使人几近窒息,言论悖于纲常礼法者,多被以“狂”为名定罪。种种强化腐朽道德规范的举措,在自由放荡风气日益深入人心的晚明已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腐朽不堪的理学体系内充斥着改弦更张的声音。
心学之所以能动摇理学的话语霸权,并成为一股日益强势的在野力量,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学术根源。继蒙元而起的朱明皇朝世俗化趋势加剧,现代性因素增长,平民阶层力量壮大,尤其是“人”的主体性得到肯定和张扬。儒家伦理秩序和道学体系已然无法满足新兴阶层试图掌控话语权的欲望,也无法解释纷至沓来的新现象。强势的旧秩序挤压着新事物的发展空间,一般性的进步因素不足以挣脱旧秩序的桎梏。敢于打破旧秩序、呼唤新思潮的狂者便应运而生了。
中晚明占据狂者精神的制高点,是中华文化狂狷传统的集大成时期。这一时期,各阶层、各领域几乎都被“狂”风浸染,“狂”成了全社会普遍的文化情致和生活韵致。[4]81-82
二、狂者精神对学术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解构
如果用一个传神之词概括整个晚明的学术思想状况,那无疑就是“破坏”。偏执的政治导向、失序的学术规范、沉沦的学术道德导致了无根的学术思想。各种学术思潮、学术现象和学术问题纷至沓来,深刻地影响了晚明以降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解构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学术思想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狂者精神复归。
狂者精神的真谛在于向善的内心、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品格,即“寄情于寥廓之上,放意于万物之外,挥斥八极,傲睨侯王”的“心狂”和“内存宏伟,外示清冲,气和貌庄,非礼不动”的“形不狂”,而非行为举止荒诞不经,“毁灭礼法,脱去绳检,呼卢轰饮以为达,散发箕踞以为高”,“迹类玄超,中婴尘务,遇利欲则气昏,遭祸变则神怖”的“形狂而心不狂”[5]。以心学为思想武器的狂者显然具有这种品质,他们不迷信威权、成说,敢于打破陈旧格套,“剖性命之微言,发儒先之秘密,如泉之涌地,如风之袭物,开遮纵夺,无施不可”[6]863,狂者“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非名教之所能羁络”[7]703,这种自由解放的精神显然“比朱学更带些近代的色彩”[8]7。
值得注意的是,心学对理学的疯狂解构并非只有“破旧”,还有“立新”,因而是一种革命性解构。嵇文甫先生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在其代表著作《晚明思想史论》中频繁出现“时代精神”“革新”“破除”等词语。他认为心学家信由己心、行有己意的反叛意识在解构中隐含着重构:“一方面大刀阔斧,摧毁传统思想的权威,替新时代做一种扫除工作;同时他又提出许多天才的启示,替新时代做一种指导工作。”[8]13颇具世界视野的嵇文甫还认为:“理气二元论和反理气二元论的对立,正类乎欧洲中古末期经院哲学中实在论和唯名论的对立。”[8]109他认为,王阳明充满自由主义气息,当与马丁·路德并称。心学“狂禅运动”被嵇文甫定性为“道学革新运动”和“反朱学运动”,而“狂禅运动”的起因是程朱道学的种种弊端:以道学正统自任,左拒陆学,右排浙学;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八股程式,陈陈相因。繁琐支离、因袭墨守使得横行于宋元明学术思想界的程朱道学盛极而衰,陈白沙、王阳明相继举起“道学革命”的旗帜,“一扫二百余年蹈常袭故的积习,而另换一种清新自然的空气,打倒文化八股化的道学,而另倡一种鞭辟近里的新道学”[8]1-3。王学重视个体人格,尊重人的自然性,促进社会合理化、世俗化是其风行一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东林士子的温良革新,还是王学左派的狂禅之风,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思想体系,体现出合理化、世俗化、平民化、个体化特色。
狂者不是圣人,不能超凡脱俗,若不律己以修,则容易步入极端,走向对生活和社会的否定,结果不仅无法完成一个至高的境界,甚至沦为出世主义或感性放任。[9]291显然,这不是现代性的学术思想。沟口雄三指出:“体制儒学一直是完全自上而下的专制的、父家长制的意识形态;而各时代的儒理学则是密切联系那一时代的现实,或和现实的矛盾作斗争,并使它反映在理观中,从而进行自身的变革。这样,随着时代的前进,体制儒学的僵化和脱离现实,造成了它和儒理学的隔阂,结果,由于后者的‘近代的成熟’,这个隔阂更加扩大,终于使前者成为后者的变革对象。”[10]48那么,晚明学术思想“近代的成熟”体现在哪里呢?
晚明的狂者用实践做出了回答。为抵制理学对学术思想的束缚,心学激进派与温和派(“狂禅派”与“修正派”)都赋予“狂”以积极意义,试图以此冲击旧有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思想体系,其中,激进派掀起的“狂禅运动”更是把狂者精神演绎到极致。这一运动的实质就是以一种极其激烈的方式瓦解理学树立起来的僵化秩序,摧毁卫道者重重拱卫的祭坛,祛除潜伏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巫魅,重塑以合理化、世俗化、平民化、个体化为价值内核,以“人”的觉醒为根本标志的新型秩序。
晚明思想体系在看似一片混乱中实现了断裂、重组与再造。由历史的实践效果来看,“立新”工作尚存不足,但“破旧”工作值得称道。狂者精神使得人们头脑中的自我意识觉醒,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增强,越来越多的知识者试图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史载:“悖叛朱夫子,明示攻击,敢为异说而不顾……为人弟侄者,有长兄叔伯在前而对客妄谈,略无顾忌。”[11]462-465“有明一代学问,凡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说,却要另出意解。”[12]404
狂者精神在晚明的高级复归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还突出地表现在历史观的变化上。民间知识者倡导心性“无善无恶”,直接导致历史评判不以传统的和官方设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而主张“本自心师”“心外无物”,以内心深处的“良知”作为准绳作出独立的历史评判。这固然有失偏颇,但他们强调人的尊严,肯定人的欲望,弘扬主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主张人的自由,并使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浪潮,涤荡着僵化观念,冲击着等级秩序,可谓功勋卓著。
三、泰州学派的狂者精神与儒学平民化运动
程朱理学为祸之烈令人发指,等级秩序强化、平民意识疏淡是其直接恶果。心学对它的矫正很大程度上是从学术思想的平民化着手,突出地表现为三点:作为布道主体的狂者的平民化、作为布道内容的思想的平民化和作为布道对象的受众的平民化。这些颇能体现沟口雄三所谓“近代的成熟”。
(一)作为布道主体的狂者的平民化
崛起于民间的心学支派之一泰州学派是晚明儒学平民化的真正推动者。其领军人物王艮、何心隐等人的平民身份促使他们较多地关注平民生活,洞悉平民思想,表达平民诉求。
这一阵营狂者辈出。王艮的儒学平民化实践深入人心,为他赢得了煊赫的声誉,史载:“王氏(王阳明——引者按)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13]7276
为了启蒙市井的崇高理想,他们设坛讲道、奔走呼号,拒受“官德禄”的诱惑,或拒绝仕聘(王艮、王襞父子),或弃考不仕(颜钧、何心隐),或弃官致仕(李贽、罗汝芬),甚至不惜付出惨痛的代价,如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何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14]80。布衣狂者会通古今的器局、卷舒自如的胆略、狂放不羁的霸气无不令人感佩。正是在狂者精神的激荡下,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运动才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
(二)作为布道内容的思想的平民化
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比较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将“致良知”转向实践层面的“百姓日用”之学。
作为主将的王艮是具有狂者精神的平民思想家。他主张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7]714-715,将圣人与百姓拉到同一个层面;他树立的平民知识者当有“为王者师,为天下万世师”的理想,涤荡着潜伏在知识精英内心深处的文化优越感;他倡导的“爱身如宝”“明哲保身”的开明理念,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他坚守的“致良知”推崇个体人格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凸显人的自然主体地位,并以此来抗拒“存理灭欲”的程朱道统。
泰州学派在儒学平民化实践中发展出具有自由、独立、平等内涵的模糊的现代意识。“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皆为真圣人”的理念超越了庸俗的等级秩序,为草根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也使得伦理教化大权散落社会深层。
(三)作为布道对象的受众的平民化
泰州学派将学术思想的传播明确地指向普通民众,是致力于将儒学话语权由士大夫阶层转向愚夫愚妇的学术思想的伟大实践。
为实现平民社会的美好理想,泰州学派一扫精英阶层垄断教化的理念,广纳底层人民为徒,授以知识,晓以大义,开启民智,壮大平民声威。他们将文化知识传入社会深层,真正意义上推动了“述通效劳于草莽,牗开盲聋于四海”[15]31的教育平民化巨轮。乡野鄙夫的平民意识和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愈益疯狂地批判陈腐的等级秩序,平民话语权日益增强。
泰州学派是个讲理想、重德化、爱实践的学术团体,“它不是以‘位’即以职权为自己的关怀,也不是以‘齿’——自然秩序的权威,而是以德为标准”,平民讲会运动使得一大批“有德之人进入基层社会的精英层,改变了它的原有结构”[16]219-220。具有知识民主性质的平民教育理念和平民讲会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宋学以士大夫个人的完美道德为统治乡村的枢纽、以士大夫的德风为自上而下地感化民众的乐观主义(新民)、以士大夫的严于律己的道学修养(学至圣人)为必需的方法论(格物穷理);而把自己置于与民众同等的地位(亲民、万物一体之仁),寄希望于发挥民众现有的良知(满街都是圣人),把道德的承担者从士大夫、官僚、地主扩大到商人、农民、劳动者,亦即所谓自父老、布衣至田父、野老以及市井庶民”[10]39。
四、结语
席卷知识界的儒学平民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把儒教道德广泛扩散到民间、使民众主体性地承担乡村秩序的精神革新运动”[17]。植根于民间沃土的泰州学派的“‘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容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18]289,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教化导致的文化畸形状态,多少有些像17世纪不列颠人把繁文缛节的基督教改造成简洁、易操作的新教的“清教徒运动”。
由是,以在野(民间)知识群体为主要构成的基层(民间)社会精英群体初现雏形。这个群体为维护乡村稳定、传承民间文化、改善民生乃至构建乡村民众对平民知识者的认同感贡献殊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为晚明社会开启了“自由个体化社会之路”[16]220。晚明以降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绅士”阶层与之不无关联。
[1] [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上)[J].读书,2010,(3):65-72.
[4] 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 [明]屠隆.鸿苞集:卷四十四[M].明万历三十八年茅元仪刻本.
[6]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9]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0]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索介然,龚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 [明]李乐.见闻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明]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 [明]颜钧.颜钧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 宣朝庆.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7] [日]沟口雄三.俯瞰近代中国[J].读书,2001,(9):91-98.
[18]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刘 蓉】
Reversion of Untamed Spirits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Intensification of Confucianism’s Populist
SHAN Lei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Revert of untamed spirits was triggered by WANG Yang ming idealistic in Late Ming Dynasty. Revert of untamed spirits had promoted deconstruction of old academic thought system and reconstitution of new academic thought effectively. The hierarchical order established by NEO-Confucianism was shaken, and civilian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gradually. As well as the tendency, populist movement was developed by Taizhou school.
Late Ming Dynasty; untamed spirits; Taizhou School; populist
B249
A
1009-5128(2015)05-0038-04
2014-11-17
单磊(1985—),男,河南新蔡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