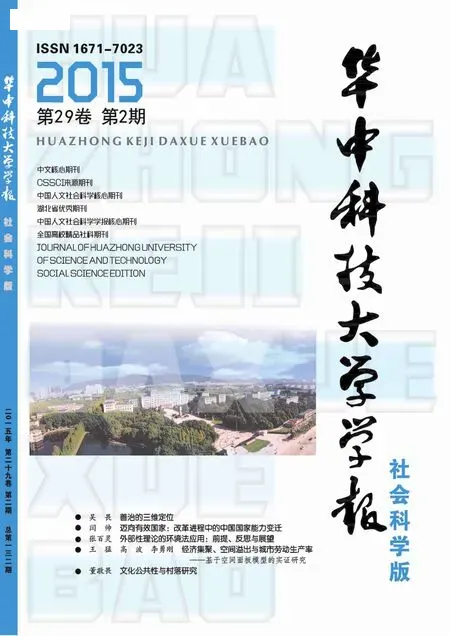同意的难题
——论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同意
王宇环,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同意的难题
——论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同意
王宇环,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自西方启蒙时期开始,政治理论家们便将同意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古典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前国家的自然状态中,人们是通过同意授权统治者,赋予其进行统治的权利,使其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具有了合法性。但是同意理论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譬如洛克《政府论》中的默认同意难题;再如在当代社会,面对大而复杂的共同体,古典社会契约论中的同意虽然在证成国家建立的合法性中具有吸引力,但是难以满足对于后续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实际论证,于是发展出崭新的同意概念,即将民主程序中的投票或参与等同于同意。本文要论证的就是这些新的尝试都是不成功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最终从同意转向了公共理由。
同意;政治合法性;默认同意;民主;公共理由;审议
同意在政治学中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能够提供充分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同意理论主要来源于启蒙时期的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在此理论中,同意作为公共权力的来源具有同数学公理一样的确定性。古典社会契约理论描述了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人自愿同意订立一个契约使自己进入公民社会,处于一个政府的控制之下。同意的目的在于改变当事各方的权利结构,通过同意使统治者拥有了统治权利,同时也建立了个体公民遵守法律这一政治义务的主要基础。同意的德行在于:(1)在实现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的和解上,排除了强制。因为一方面人们同意一种公共权力,且这种公共权力能够维护一种保护个人权利的政体,是维护自由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可以理解为人们通过授权国家对其施以法律约束的方式自主地限制了自己的自由。(2)调和了平等与公共权力的紧张,同意理论从平等的视角对公共权力进行审视,需要回答既然人们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只有某些人能够掌握公共权力?同意理论的答案是,通过我的同意,我授权你拥有公共权力,授权调节了平等的价值与公共权力的垄断之间的矛盾。同意理念的规范价值主要体现于为某种类型国家的建立提供合法性,那么其能否为后续国家、某种政治制度、某位领导人抑或某个政治决策提供合法性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两方面的论证:(1)洛克《政府论》中的默认同意能否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2)民主过程中的投票或参与能否等同于同意?在考察的过程中会以美国学者约翰·西蒙斯对同意的两个条件的界定为基础:首先,同意必须是故意地(intentionally)、有意识地(knowingly)或慎思地(deliberately);其次,同意必须是自愿做出的[1]35。
一、默认同意能否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当同意是通过保持沉默或不行为的方式被给予时,就叫做默认的同意。同意理论中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将居留在某国领土范围内看做对其政府表达了默认的同意,这一理论在洛克的《政府论》中得到了阐述。默认同意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同意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难题,即“谁的同意”。人们的祖先在自然状态中给出的同意,不能够作为当今一国国民的同意,于是理论家们便以默认同意的形式作为当今一国国民的同意表示。在考察洛克的默认同意理论时,可以发现洛克把“占有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领地的任何部分”作为默认同意的标志,默认的同意即是以某种沉默的方式为标志来表示对某项或某些条件的赞同。“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认的同意,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用的期间,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这不管他所占有的是属于他和他的子子孙孙的土地,或只是一星期的住处,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事实上,只要身在那个政府的领土范围以内,就构成某种程度的默认。”[2]74-75
对洛克默认的同意存在很多批评意见,譬如人们想要收回同意而进行革命的时候,即使他们仍然身处一国之内,但是他们将会否认仍然对政府持有默认的同意。又如一些从未听说过同意学说的个人,他们从未想过同意与否这件事,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默认地同意了政府。再者洛克论证默认同意时存在自相矛盾,他曾否定人们有自然的义务来遵从他们生而处于其中的政府,却又主张一国之内的居民有义务服从其法律,因为他们居住于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所以他们表达了对一国法律默认的同意。再如默认的同意并没有区分正当的权威与专制的政权,因为即便在君主专制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仍然居住着大量的访客,按照洛克对默认同意的解释,这些访客便给予了君主专制国家以默认的同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定要为默认的同意提供某种道德基础,那便是一种礼节[3]45-50,是对政府这一施恩者的感激,因为身处一国之内的人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安全的保证、得到了社会的福利,等等。这种观点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建立在非成员的礼节基础之上,实际上亦是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在这种论证中,默认的同意已经显得多余了,它成了利益表述的一种工具。
洛克对默认同意的论述还招致了其他的一些批评,如果将居留在政府领土范围内作为一种同意的表示,那么移民相应地成为不同意的表达,正如休谟敏锐地指出的:首先,我们无法认同一个不懂外国语言,也不了解外国的生活方式,且日复一日地靠微薄的收入生活的贫苦农民或手工业者有自由选择脱离自己的国家。因为移民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人们还可能因为失去家庭、社会和文化上的依附而付出巨大的成本。其次,人们是无法选择出生地的,当一个人到了可以做出移民决定的年龄时,他已经在很多方面都强烈地依赖于他的祖国,这使离开变得十分困难,也就是说,居住固有的非自愿性使其无法与同意等同起来。学者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也针对将居住等同于默认同意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见,第一,他指出一个拥有土地和不动产的人,在离开其国家时,必定要失去其财产,或至少将其财产以低价变卖。换言之,只要国家以影响其管辖内人们财产的价值和有用性的方式管制财产,那么上述问题就是无法避免的。第二,只有其他的国家愿意接受移民,且没有限制性的移民条件时,移民才是可行的。即便如此,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对移民者来说仍然存在困难。譬如说在何种程度上移民者可以被看做接受了新国家的权威,如果一些乐于接受移民的国家,需要以移民完全接受其国家的权威为代价,那么仍然无法确认移民者的选择是否是出于自愿的[4]767。再者,默认的同意使正当的政府和纯粹靠强力支撑的非正当政府之间的差异不存在了,处于世界上最坏的暴政的领土范围内,好像也构成了对该政府的默认同意,因为在默认的同意理论中是不存在默认不同意这一概念的。
上文所述通过某种程序或行为来表达同意都是尝试在群体的行为中发现同意,而尝试从个体的行为中寻找同意是否成功呢?通过“同意”的定义,我们发现自愿性是同意的主要特征,因为每一个个体生来就是处于某个政府的控制之下的,那么这些个体同一个特定政府的联合是否是出于自愿的呢?是否对控制他们的政府表达了同意呢?一种观点尝试论证,如果个人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迁移出去,并且自由地选择一个其权威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新的国家,那么他的选择就是自愿的,无论是选择继续处于原政府的控制之下,还是选择一个新的国家。当然,如果不考虑退出的成本的话,理论上这种选择是可能的,但是这种选择是否可以称为自愿呢?卡西内利认为并非如此,“一种联合是可以接受的仅当一个人能够使自己在任何时候摆脱控制。在一个人打破规则之后,他能够从俱乐部、集会、政党、劳工联盟以及专业组织中退出,而不必招致惩罚。”[5]398但是如果从一个国家退出伴随着对政府规则的破坏,则居民是一定要遭受制裁的,而居民并没有对政府规则事先表达同意,因为居民并没有有意识地通过自愿地移居而接受这个规则。整理一下这里的论证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一国之内的公民如果自具有公民身份的时刻开始选择一直居住在该国的话,那么他就对该国政府表达了默认的同意,直到他们选择通过退出而表达不同意时。如果退出是因为对现存权力或秩序不满的话,那么退出很有可能伴随着对某种政府规则的打破,也就是说此时他们不同意一开始被认定为默认同意的规则。要想让论证逻辑继续下去,那么这些想要退出的人应该被给予某种权利,即通过无条件退出来表达不同意,但是由于他们打破了现存规则,他们是要受到制裁的。既然同意并不存在了,制裁的合法性又来自何处呢?社会契约论是尝试在源头上解决移入问题的,但是社会契约论的困难却出现在立约者的后代身上,不可能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回到自然状态中去通过订立契约来表达对国家及其强制性的赞同。由此可见,试图从个体的行为中发现同意也是不成功的。
二、投票或政治参与能否等于同意
在当代的政治理论中,对于同意的讨论是伴随着对民主程序的讨论的,许多理论家将同意等同于民主程序中的投票选举或者政治参与,“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拥有被治者的同意”[5]391。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这两种民主模式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但却在用民主程序表达同意这一点上走到一起。他们主张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及参与的权利,在当代西方普选的背景下同意主要被理解为有投票权的公民投票或参与选举代表的过程。但这种同意理论的缺陷在于:首先,同意总是由人口中占很小比例的一部分给出,尤其在现代大型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不参与选举,并且有相当比例的投票者表达的是反对意见。那么根据同意的定义,表达同意的人们是对获胜的候选人进行投票的那些人,那么落选候选人的支持者也就是不同意者了。既然同意的比例如此之小,我们无法复制古典社会契约中的一些主张:或者将不同意者视为与同意者处于战争状态中而将其消灭(如霍布斯),或者无视他们的存在,让他们继续忍受自然状态中的不便(如洛克),或者创造一个不存在不同意者的神话(如卢梭)。另外,正如哈里·贝兰(Harry Beran)指出的,一些打算支持获胜候选人的选民由于个人的原因而未参与到投票中,如患病等,那么选举的结果对他们来说不是就不具有合法性了吗?同时,在两次选举之间达到了法定投票年龄的人们,在达到法定年龄时,由于未到下一次投票时间,那么能够说由于未给其机会对上一次投票表达同意或反对,就说上一次投票结果对其来说没有合法性吗?因为假设在他们达到法定投票年龄之后,立刻给其机会表达同意或反对,也许他们会对上一次投票结果表示同意,也就是说上一次投票结果对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的他们来说是具有合法性的。所以,绝不能由于偶尔未参与投票,或没有机会参与投票,就断言投票结果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合法的[6]72。将投票等同于同意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就是无法保障社会契约理论所设想的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建立国家时的参与规模。其次,既然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来界定同意,那么必须要做的是赋予选举制度以合法性。然而一旦进入一个共同体之后,服从制度的权威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强制,缺乏对选举制度的同意破坏了同意的自愿性。而且选举程序本身致使选举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正如社会选择理论对投票的批评那样。既然对谁将成为同意者的划分存在着任意性,那么这本身就极大地削弱了同意的内涵。因为同意自古典社会契约理论中发展而来,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之下,个人知道他们一旦同意便会成为被治者、是表达同意的人,而不会因为选举程序使自己的身份存在任意性。最后,将同意等同于投票选举获胜候选人,使同意多余了,因为它没有赋予同意比选举程序更多的内容,将同意与投票等同起来是将同意本身工具化了。
另外一种理论认为投票或参与就意味着同意了投票或参与的结果,而无论投票或参与的结果与个人投票的内容是否一致。但是投票行为与参与过程能够等于同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如果说投票或参与就意味着同意了投票或参与的结果,那么投票的结果是什么呢[7]126?参与投票的个人怎么能在未经民主程序产生投票结果之前就已经同意了其结果呢?除非先证成民主决策程序的合法性,如果是这样,那么证成政治合法性的就变成了民主程序而不是同意本身。其次,正如斯坦伯格所说的,“这至少不是自明的”(it is at least not self-evidently clear)[8]117。他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投票行为并没有提供个人涉足与互动的背景(does not provide a context of pers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而这对于同意关系来讲是必需的。在当代大型、复杂的工业社会中,自由选举涉及大规模的选民,并且大多数选民与其代表之间从未有任何私下的接触。现代民主国家的选举不能与一个小型会议相提并论,在小型会议中人们之间存在面对面的互动,因此说参与到选举中来就意味着同意其选出的代表似乎是令人奇怪的。在这一意义上,索明更加详细地提出了两点理由:其一,在任何一个大型的政治组织中,只要这种政治组织是大于面对面的共同体的,那么任何个体的投票对政府政策的实际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于是,这种同意模式对证成个人自由来讲是毫无贡献的,实际上,个人并没有真正的权利来决定其应该生活于怎样的政体之下。其二,当人们的每次投票对投票结果的影响都很小的时候,投票者就会出现"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当人们的投票根本无法改变结果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动机去寻求足够的政治信息来帮助自身恰当地(correctly)投票。结果是投票行为都可能是无知的(uninformed),而这种理性的无知是与“同意”所蕴含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驰的①参见Ilya Somin.“Revitalizing Consent”,Harvard Journal of Law&Public Policy,Vol.23,No.3(2000):753-806中对同意的“单一话语”(Voice-Only)模式缺点的论述。。另外,自由民主的投票方式没有更好地克服人的有限理性问题,正如周光辉教授所指出的,“理性认知的方法、手段和工具是不完备的,理性认识的前提和结果是非完善的,理性的认识能力和理性认识所能把握的对象也总是有限的。”[9]135第二,斯坦伯格认为选举/同意模式的合理性很难被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投票构成一种同意方式在经验上并不正确。因为从民主传统来看,民主投票过程是试图提供给公民表达反对与异议的一种方式,那么公民参与到投票中为什么不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其未选择的代表的反对意见呢?把投票等同于同意似乎武断地封闭了一种可能性,即选举是提供公民以表达反对的途径,也就是说投票者没有被视为平等的主体,因为在投票过程中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得到尊重,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多数人的决定之中[8]117-122。
支持将投票和参与等同于同意的普拉门纳茨认为参与选举或决定的过程便意味着直接或间接的同意,直接同意是对通过投票表示赞成的某人或某项决议的同意,间接同意是当结果与投票人意志相反时对其自愿参与到其中的制度或投票结果的同意。皮特·辛格质疑普拉门纳茨的主张,认为其很难满足同意的条件,即一个人在投票的时候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普拉门纳茨的拥护者约翰·詹金斯②关于以下詹金斯的主张,参见John J.Jenkins.“Political Consent”,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20,No.78(Jan.,1970):60-66.认为需要区分写下选票这一行为与参与到选举过程的行为,普拉门纳茨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谈论个人对投票的理解的。那么,一个人参与选举并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同意获胜的候选人,但也蕴含着他同意获胜的候选人,无论获胜的是谁。但是詹金斯提出,在现实中,很多参与投票的人仍然不清楚选举程序的本质,所以这些投票者无法意识到他们对获胜的候选人或者政府有任何义务,他们也无法意识到获得最高选票的候选人成为了法定代理人或者权威,因为他们并没有将选票投给他们。但他又主张虽然存在着无知,但是这种无知并不是普遍的。针对皮特·辛格的主张,即很多人是认同选举制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的同意,因为在一种语言形式(如承诺)或者系统化的行动与伴随它们而产生的感受或信念之间是有分歧的。同意的必要条件应该是一种心理的态度,那么对于给出同意的行动来说,投票的动机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詹金斯的回应是同意行为并不需要心理学上先在的同意,人们完全可以在反对的情况下给出同意,譬如父母们完全可能在强烈反对其子女婚姻的情况下给出同意。这种情况与投票之间的不同在于,在投票中我们给出直接或间接同意的方式是标准化或规范化的。他认为同意的意愿是有强弱的,但是同意也不完全否定心理状态,对于直接同意来说,一个人在选举中投票给他选择的候选人,他是有适当的感情的,但是这种感情的存在是不能够作为同意的标准的,因为它是无法公开获取的;否定心理化的感情针对的是间接同意。如果独立于心理上的衍生物,同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詹金斯认为得到一个人的同意至少是获取了一种避免干扰、无法容忍、反叛的保证。需要区分同意与支持,投票的公众同意政府意味着他们允许政府的治理,其中一定比例的选民是支持其统治的,这是一种心理上赞同的态度。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表达了同意,可能在心理上他并不希望同意的事情发生,或者对其是否发生持有一种冷漠的立场。例如,我同意了借出我的教室作为会议室,但是我宁愿教室不被借出仍归我自己使用。又如我同意了在我的房间摆设一个盆景,但实际上我对是否摆设盆景这件事情并不关心,所以在这里虽然表达了同意,但是却没有心理上支持的意思。
其实,普拉门纳茨和詹金斯给出了将投票等同于同意另外的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投票是一种授权的行为,投票使选举的获胜者有资格获得做决定的权利,否则他是没有这种权利的。投票意味着同意选举中获胜者的权威,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区分授权与同意。选举的获胜者的确是拥有了做决定的权威,但赢得选举的胜利只是获得权威的必要条件,权威实际上是法律所授予的,是多数决定的程序所授予的,而不是同意,因为许多人将选票投给了选举中的失败方,我们不能说他们也对获胜者表示了同意①Tom Christiano指出同意理论的困境在于,首先为什么假设一个人的投票被理解为同意投票的结果?为什么不能假设投票纯粹是对结果施加影响呢?为什么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成员资格使他同意决策必须以多数原则做出呢?第二,把人们的投票看做构成同意的惟一路线是人们应该同意结果,因为他们已经参与了,这便产生了义务。但这种观点离同意理论太远了,同意理论是人们同意或不同意应该取决于他们,而不应该被正确的道德观点所决定。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民主”词条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mocracy/.。卡西内利(Cassinelli)将普拉门纳茨的这种观点总结为同意的自愿性不在于个人有自由来选择候选人,而在于他们拥有自由来投票。投票人同意的不是政府的任何特殊行为,而是政府实行这种特殊行为的权利,也就是说同意的是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则[5]394-395。卡西内利提出了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投票的动机在心理学上并不是与代议制政府的意识相关,因为人们投票可能是由于责任意识,或者希望遵从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群体的行为,或者对特殊议题或者对候选人感兴趣。投掷一枚选票的行为不可能涉及人们对于代议制度本身的反思[5]395。
三、从同意到公共理由
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同意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是尝试将同意等同于居住而呈现的默认的同意,或等同于投票或参与。但是这些对于同意的释义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将其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都是不成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将其来源从同意转向公共理由,换言之,从“自愿性”转向“可接受性”,从民主投票的单一环节转向民主审议加投票的双重程序。审议程序输入的是公共理由,强调理由的可接受性,而不是同意的核心内涵,即自愿性。理由的可接受性在以下两方面得以证成:(1)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公共理由诉诸的是公共利益。(2)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审议参与者们公开陈述理由。
首先,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公共理由诉诸的是公共利益。在投票前进行公开的审议,每个人的主张都应该诉诸他人可以接受的理由,在讲理的过程中,完全个人利益导向的偏好便会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因为这些理由并不具有可接受性。加之在审议过程中,信息更加充分,观点更加开放,人们的偏好可以重新得以形塑。审议能够激发参与者将利益寓于政治共同体的福祉之中。其实,公共利益是被构建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是由审议的参与者们构建出来的,从规范的意义上讲,它并不具备惟一性和先验性[10]308。反对意见指出,在审议中存在将阶层利益或个人利益伪装成共同利益的情况。回应这一反对意见,一方面参加审议的人都要秉持着通过审议来化解分歧这一原则,所以审议者都应该真诚地提出互相可以接受的理由;另一方面在审议过程中如果人们提出的理由不能够说服他人,那么审议便要求个人重新塑造自身的偏好,这是因为个人的目标与审议的目标相矛盾了。所以,在形成合法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是要排除任何自利动机的,这要求审议者都要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立场提出理由。审议者参与公共辩论可视为一种自我审查,因为公共辩论的目标是产生一种理性的决策,所以任何自私的理由都要排除掉。当然,所谓的公共利益也不是虚无的和先在的,而是经受住了审议考验的目标、利益和理想。审议者也必须要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所提出的理由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领域,每个审议者都要基于相互性的视角,充分考虑其他审议者对其提出的理由可能给予的反应。于是一项政策或法律如果是通过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理由而得以证成,那么该政策或法律便是合法的。
其次,理由的可接受性要求审议参与者们公开陈述理由。在一个审议的程序中,审议者支持或反对某项决议的理由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由上的分歧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审议程序的起点。在审议程序中,最为核心的便是理由的交换,人们的偏好以及对于偏好的证成均处于审议者的监督之下。审议程序“对审议者应提供和接受何种理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参与者据以审议的理由应是理性的,并能为所有人所接受。”[11]53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公共理由必须能够为致力于公平合作、自由平等的个体所普遍接受,所以必须出于一种公共的视角。如科恩所说的,“通过公开地陈述理由来解决集体选择问题,只要基本的制度框架是通过自由的公共审议建立起来的,它就是合法的”[12]176。并且,审议中所提供理由的内容必须是公共的,或者用詹姆斯·博曼的话说,理由的公开运用是对话性的、反思性的和可重复性的[13]37-39。譬如我们不能通过诉诸神启或自私的个人利益来证成决策的合法性。当然这并不否认在涉及专业问题时可以依赖专家,只是审议的公共性要求专家陈述理由的方式是公民们可以理解的,或者参加审议的专家是值得信赖的。审议民主论者认为所有理性的参与者赞同的理由才是理性的理由,理性参与者的赞同是评价好理由的标准,所有理性参与者赞同的政策或法律才是合法的。因为参与审议的人均关心自身的利益,且每个人又都试图使决策的结果能为他人接受,这就需要审议者修正对自身偏好和信念的理解,且持一种包容的态度。审议程序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程序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表达、审查和权衡的方法”[14]195。
结语国家或一项民主决策的合法性必须能够面向所有公民而得到道德上的辩护,也就是说,面对合理多元主义的社会状况,政治合法性解释了什么样的政治安排和公共政策是公民原则上能够接受的。民主审议与公共理由的结合呈现了公共理由以民主和平等为基本前提的特点,要求基本的政治安排能够为每一个人提供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理由的可接受性弥补了同意的自愿性在证成政治合法性中存在的难题。
[1]约翰·西蒙斯:《隐然同意与政治义务》,载毛兴贵编:《政治义务:证成与反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Theodore Waldman.“A Note on John Locke’s Concept of Consent”,Ethics,Vol.68,No.1(Oct.,1957).
[4]4 Ilya Somin.“Revitalizing Consent”,Harvard Journal of Law&Public Policy,Vol.23,No.3(2000).
[5]C.W.Cassinelli.“The‘Consent’of the Governed”,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12,No.2(Jun.,1959).
[6]Harry Beran.The Consent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New York:Croom Helm,1987.
[7]Peter Singer.Democracy and disobedience,New York 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8]Jules Steinberg.Locke,Rousseau,and the idea of consent:An inquiry into the liberal-democratic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London:Greenwood Press,1978.
[9]周光辉:《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10]杰克·奈特、詹姆斯·约翰逊:《聚合与审议:论民主合法性的可能性》,载谈火生编:《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诺埃里·麦加菲:《民主审议的三种模式》,载谈火生编:《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乔舒亚·科恩:《审议与民主的合法性》,载谈火生编:《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James Bohman.Public Deliberation:Pluralism,Complexity,and Democracy,London:The MIT Press,1996.
[14]塞拉·本哈比:《走向审议式的民主合法性模式》,载谈火生编:《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 胡章成
The Dilemmas of Consent:On Consent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WANG Yu-hua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266100,China)
Since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political theorists have taken consent as the ba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In the classical social contract theory of Hobbes,Locke and Rousseau,it is clear tha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peoplem the exertion of political power by the governor was legitimated by authorizing a governor,endowing him the right to rule.However,consent theory itself faces a series of dilemmas,such as the dilemma of tacit consent i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by John Locke and the dilemma that in the contemporary large and complex society and community,consent which is still attractive to justify the built of a legitimate state meets more difficulties in the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a future state,in the meantime,theorists develop a new concept of consent taking vote or participation as consent.In this paper I will discuss all these attempts are unsuccessful.The resour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ransforms from consent to public reason eventually.
consent;political legitimacy;tacit Consent;democracy;public reason;deliberation
王宇环,政治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讲师,研究方向为证成与正当性理论、审议民主理论。
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路径研究”(QDSKL1404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从同意到公共理由:论政治正当性来源的发展”(201413036)
2014-11-25
D0
A
1671-7023(2015)02-00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