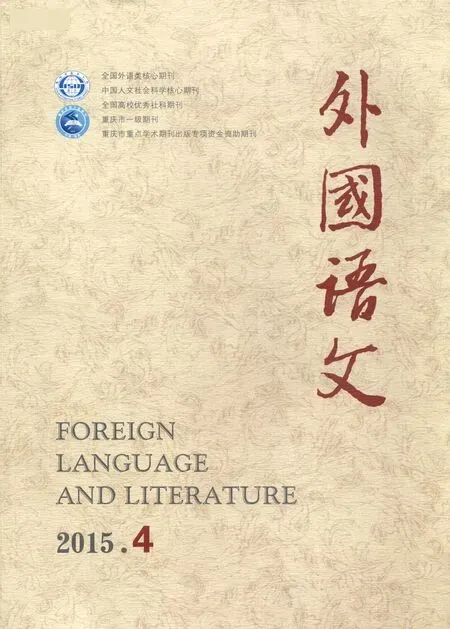“God”汉语译名之嬗变——兼论晚清《圣经》汉译活动中的“译名之争”
刘念业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1.引言
《圣经》汉译的历史若从唐代景教徒的翻译活动算起,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了,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今天的中国人谈起《圣经》中的造物主时,有人说“神”,有人说“上帝”,还有人说“天主”。实际上,在漫长的《圣经》汉译历史中,“God”的各种译名层出不穷,有据可考的译名迄今为止不下十余个,各个时期的译经人士就此问题进行了反复的争论。争论内容涉及到传教策略和中西方宗教哲学等诸多方面,争论的过程和结果往往也是不愉快的,经常发展到针锋相对甚至相互敌视的境地,显示出译名问题的棘手。争论最为激烈的两个时期是天主教传入的明末清初和新教东来的晚清时期,而争论的结果也奠定了今日“God”译名的最终结局。另外,参与译经和争论的人士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他们所主张的译名及其背后的逻辑往往透视出其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
2.天主教的译名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Lefevere,1992:14)《圣经》汉译始终和基督教①某些学者用基督教专指新教,本文中的基督教,若无特别说明,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最早的译经活动可以追溯到唐代景教的传入。当时的聂斯托利派传教士把希伯来语“Elohim”或叙利亚语“Eloh”音译为“阿罗诃”,意思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此外,他们有时还借用道教和佛教的用语,如“真主”、“天尊”、“佛”等来表现基督教至高无上造物主(杨森富,1996:53)。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初期对“God”等神学术语的翻译也一时难以决定,便将拉丁语“Deus”音译为“陡斯”。后来,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又意译为“天主”,即天地的主宰。利玛窦在早期沿用了“天主”二字,后来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看见中国古代圣贤用“天”和“上帝”来指天地的主宰,于是改变初衷,把“Deus”翻译成“天”和“上帝”;后来,利玛窦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说“天”不过是一种义理,他便放弃了“天”,以“天主”和“上帝”并用(王治心,2004:15)。不过利玛窦似乎更偏向于“上帝”一名,认为儒家典籍中的“上帝”才真正表达了基督教所认定的最高存在“God”的概念,在其《天主实义》第二篇中他曾这样写道:“吾天主,及古经书所称上帝也。”(朱维铮,2001:21)利玛窦也承认中国人对于最高存在的理解与基督教具有很大的差异,但他把这归因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对孔子学说的歪曲,认为“它(程朱理学)背离了儒学最初的内容,从原来的有神论走向了泛神论和无神论”(孟德卫,2010:47。)
利玛窦去世后,译名“天”和“上帝”受到同为耶稣会士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的反对,他认为这两个译名不足以表现“God”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之所以用这两个译名是出于传教策略上的考虑,“徐保罗(光启)坦率地向我承认,他坚信‘上帝’不可能是我们的‘天主’,古今文人均对‘天主’一无所知。但我们的神父们出于好意和特别是为了不使儒生们感到反感,认为应把‘天主’称为‘上帝’”(谢和耐,2003:21)。后来,龙华民走得更远,“干脆抵制使用‘上帝’和‘天主’这两个中文词汇,而主张将拉丁文中‘Deus’音译成中文来代替。”(邓恩,2003:270)之后随着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传信部传教团等传教差会陆续入驻中国,中国的传教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各差会的传教思想不同,彼此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于是有关译名问题和利玛窦传教策略的争论逐渐从耶稣会士内部探讨扩展为各差会间不同传教方针的冲突。译名“上帝”和“天”遭到了耶稣会外其他差会传教士更为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具有任何关于最高存在的认知,任何将“上帝”和“天”与基督教的“God”相提并论的企图,都是对异教观念的妥协和对“God”的亵渎。维护利玛窦传教思想的耶稣会士则针锋相对与之进行了长久而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也逐渐从术语翻译问题转为祭祖祀孔的礼仪问题,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历经数次讨论,教皇克莱芒十一世(ClementⅪ)于1704年做出决定: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禁止礼拜堂里悬挂有青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祭祖,禁止牌位上有灵魂等字样(王治心,2004:119)。自此,“天主”这一译名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译名。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天主教当时为了垄断教义和民众信仰生活,禁止随意把《圣经》翻译成各国文字,《圣经》汉译对于明末清初传教士而言并非主要任务,基本停留在《圣经》片段的翻译。第一部天主教的汉语《圣经》全译本(思高本)直到20世纪中叶方得以完成。比较而言,新教主张“《圣经》至上”,信徒可以通过阅读《圣经》跳过教会直接和“God”沟通交流,故始终把《圣经》翻译作为首要任务。1807年,新教传入中国,大规模的《圣经》汉译活动随即出现,各种汉语译本不断涌现,直到集大成者的“官话和合本”于1919年出版,新教传教士的译经事业方告一段落。但在这一百余年的译经活动中,译经人士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仍是“God”的译名问题。由于新教没有像罗马教廷那样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此进行最终裁决,传教士译者逐渐“分裂成针锋相对的两个派别,一度断送了新教传教士译者努力结成的《圣经》汉译联盟”(Lazich,2000:263)。
3.新教早期的译名
新教虽然较天主教更早推出完整的《圣经》汉译本,但其所采用的译名则受到后者的影响。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之前随身携带有一部《圣经》汉译稿《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经后世学者研究,一般认为这部译稿的作者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让·巴塞(Jean Basset,又译为白日升)。此译稿虽非全译本,也没有公开发行,但却成为马礼逊学习汉语和译经工作的重要参考。在此译稿中,“God”被译为“神”,马礼逊译经之初也采用了这一译名,并未沿用天主教的官方译名“天主”。马礼逊给出的解释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实践表明,使用‘天主’这一译法并没有使中国人归依基督教,而是使中国人将之与‘菩萨’混为一谈。”(Morrison,1843:201)不过,马礼逊抵制译名“天主”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不便言明的原因,即新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方面的竞争。
之后,随着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不断学习,马礼逊对译名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发现“神”字不足以向中国人表达基督教的至高主宰,于是在其翻译的《圣经》全译本《神天圣书》也使用过“真神”、“神天”和“神主”等译名。该译本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圣经》全译本,于1823年出版①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Marshman)在印度于1822年出版了其《圣经》全译本,成为历史上第一部汉语《圣经》,但由于该译本产生于印度,翻译质量不高,并未大量印行,对近代《圣经》汉译活动影响不大。,对之后的译经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提倡“上帝”译名的新教传教士译者是米怜(William Milne)。他是新教来华的第二位传教士,也是马礼逊传教和译经的助手。在他看来:“‘神’的意义过于宽泛,有时会被误认为是中国人的众多神明之一,从而误导迷信思想严重的中国人……汉语中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词汇来翻译‘God’,但最接近的译名应该是‘上帝’。”(Milne,1838:318-319)但是,米怜的看法并未改变马礼逊,也没能影响到《神天圣书》中所采用的译名。真正把译名“上帝”发扬光大的是他的“学生”麦都思。
1817年,英国人麦都思(W.H.Medhurst)来到马六甲一带华人社区协助米怜进行传教工作,米怜实际上成为其汉语学习和神学思想上的导师。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麦都思成为《圣经》汉译最为重要的译者,也是译名“上帝”忠实的拥趸。1827年,另外一名《圣经》汉译的重要人物郭实腊(Gutzlaff,另译为郭士立)也来到马六甲,并结识了麦都思,一度过往甚密。在其主编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郭实腊使用了“神天皇帝”、“神天上帝”、“皇上帝”和“上帝”等,但越到后来就越常用“上帝”和“神天”两个词(爱汉者,1997:13)。米怜和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和郭实腊逐渐成为《圣经》汉译的核心人物。俩人于19世纪30年代来到广州,担任了第二个《圣经》全译本《新/旧遗诏圣书》的主要翻译工作。该译本于1838年出版,采用的译名是“上帝”。为了赢得英国传教界人士对该译本的支持,麦都思在1836年致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就汉语《圣经》新译本给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报告》中,公开批评了“神”这一译名,认为:“早期译本采用的‘神’字意思实际是‘灵’(Spirit),传教士、信徒和异教徒都认为这个译名是完全不恰当的。”(Medhurst,1836:10)值得指出的是,洪秀全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得到此译本,遂创立“拜上帝教”,并发起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于是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境内出现了两部《圣经》全译本,分别采用了“神”和“上帝”两个不同的译名来翻译“God”,加上天主教传教差会所使用的“天主”,基督教的至高主宰在同一语言中竟然拥有了三个不同的名号,令很多中国信徒和传教士都迷惑不已。译经人士逐渐产生了联合起来推出统一译名的愿望,但在鸦片战争前,清廷推行禁教政策,传教士的活动均处于地下状态,联合译经难以实现。不过随着清廷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圣经》汉译活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4.“译名之争”的爆发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弛教,大批传教士随之涌入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圣经》汉译问题很快再次浮出水面,因为“几乎所有在华传教士都逐渐萌发出一种追求更好译本的强烈愿望”(Medhurst,1849:388)。于是,从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在各传教差会、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以及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支持下,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举行了以“讨论汉语《圣经》译本现状”为主旨的传教士大会,试图联合起来翻译一部完美的汉语《圣经》。
会议期间,传教士译者们就修订和翻译计划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在把“God”和“Spirit”两个重要术语译成汉语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一派传教士赞成使用汉语典籍中的“上帝”或“帝”来翻译“God”,用“神”来翻译“Spirit”;另一派则主张用“神”来翻译“God”,用“灵”来翻译“Spirit”,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究竟用哪一个词来作为“God”的译名?以麦都思为代表的大部分英国传教士主张采用“上帝”或“帝”,而美国传教士则主张用“神”。由于两派传教士均坚持己见,会议最终未能就“God”的汉语译名问题形成一致决议。会议结束后,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的传教士译者开始执行所分配的译经任务,并纷纷撰写和发表有关译名问题的各种论辩文章、小册子和书籍,以期能够说服对方接受自己主张的译名,“译名之争”就此形成。
参与此次“译名之争”的核心人物有英国的麦都思和理雅各(James Legge),美国的裨治文(E.C.Bridgman)、娄礼华(W.M.Lowrie)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即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基督教自身的神学理念,具体来说,即中国人是否具有对“God”的认知和“God”本身的内在涵义。
5.“神”派传教士的翻译观
两派译者首先围绕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便是中国人究竟曾否有过“true God”的概念和知识,即中国人是“一神论者”还是“多神论者”。答案如果是前者,采用中国人所崇拜的神明的名号来翻译“God”便显得顺理成章;答案如果是后者,采用中国人某一神明的名号则显然是不能被接收的。
美国传教士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就得出了答案,即“中国人自始自终都是多神论者,没有至高存在的概念……中国人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宗教信仰极为相似,都是多神崇拜,翻看中国古代和现在的所有书籍,没有一处可以明确看到中国人对至高主宰的认识”(Bridgman,1847:125)。
既然中国人是彻头彻尾的“多神论者”,那么就只能选择一个中国人众多神明的通用名称,即一个能够表达所有神明的“类名”。美国传教士认为这种翻译策略实际上也是《圣经》被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时所普遍采用的,因为“希伯来语《圣经》中的‘Elohim’一词就是一个‘类名’,并非至高存在的‘专名’,可以同时表达异教的神明和基督教的耶和华……当‘七十士译本’的译者把‘Elohim’翻译成希腊文时,他们所选用的也是‘类名’‘Theos’,而非希腊人主神宙斯(Zeus)的名号。在把新约《圣经》翻译成拉丁语时,使徒先辈们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没有采用罗马人主神朱庇特(Jupiter)这一‘专名’,而是采用了‘类名’‘Deus’”(Boone,1848:18-19)。美国传教士认为:“异教民族的所有神明都属虚构而非真正存在。耶和华拥有取代所有异教神明的绝对权力,他不是要在多神主义的体系中被拥立为主神,而是要彻底取代他们。耶和华不会同意自己被当作异教徒的朱庇特、海神、天或佛。就此而论,必须采用‘类名’来翻译‘God’。”(Boone,1848:20)
那么,汉语中的哪个字眼才符合这样的标准呢?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典籍和注疏书籍进行了考察。譬如:《孟子》中的“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易经》中的“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阴阳不测之谓神”等等。一番研究之后,他们认为,这个合适的“类名”就是“神”。他们解释道:“‘神’这一字在大部分情况下被用作名词;就名词而言,‘神’的所指又分为抽象和具体两种,在后一种情况下,‘神’正是中国人所崇拜的各种无形存在的普遍名号,这种意义在汉语中最为常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可以用作‘God’的译名。”(Boone,1848:25)
当然,美国传教士并不认为“神”这一译名是完美的,“当中国人用‘神’来表达‘God’,他们的思想可能和《圣经》中的‘God’意义迥然不同,但这并不是反对‘神’这一译名的理由。汉语所能提供的字眼中,它无疑是最合适的,我们只需更正中国人对这一字眼的错误理解即可。”(Lowrie,1846:585)也就是说,“神”一旦被确立为正式的汉语译名之后,这个字在汉语中的原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既指耶和华也指中国宗教中的一切神明,不过这些神明将全被打成伪神。
6.“上帝”派的观点
面对“神”派译者的主张,“上帝”派起初的回应显得有些软弱无力。在中国人是“多神论者”还是“一神论者”的问题上,该派核心人物麦都思没有直接回应,仅表示“中国人在远古时期的确奉行多神崇拜,但这种多神崇拜和一神崇拜一直是并存的。”(Meduhrst,1848:490)至于采用“类名”来翻译“God”,麦氏也基本认同,但强调“‘类名’必须含有和至高存在相关的性质,而‘神’这一译名无法表达至高存在”(Medhurst,1848:492)。一番交锋之后,“上帝”派传教士开始考虑妥协,准备放弃“上帝”,转而主张采用“阿罗诃”这一音译名号。但“神”派传教士并不善罢甘休,态度十分强硬,坚决要求采用“神”这一译名。
眼看“上帝”派传教士即将“投降”之时,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却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积极捍卫“上帝”这一译名。早在1843年香港传教士翻译大会上,他曾是唯一反对“上帝”译名的英国传教士。翻译大会后,理雅各因身体健康原因回英国休养。1848年重返中国之后,他开始转而支持“上帝”这一译名,并满腔热情地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理雅各针锋相对地就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类名”这两个关键问题对美国传教士进行了猛烈批判,戏剧性地改变了“译名之争”的走向。
6.1 中国人的“上帝”即“God”
为了阐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理雅各撰写了一部名为《中国人对“God”与“Spirits”的认知》(The Notions of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的长篇巨著。理氏在书中开篇便写道:“中国人是否具有关于‘God’的认知呢?在他们所崇拜的众多存在中,是否有一个最突出、最崇高、最特殊的存在,以至于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认识到他的威严与崇高呢?他是不是立于天地万物之中永得荣耀的唯一主宰呢?万事万物是否因他而成,归他所有,为他存在呢?”(Legge,1852:7)理氏告诉读者,他本人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是:“坚信不疑和绝对肯定的……中国人拥有对‘God’的认知,他们所崇拜的最高存在正是我们所崇拜的最高存在。”(Legge,1852:23)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理氏同样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一番研究,并发现了一部其他传教士尚未关注到的典籍《大明会典》。该典籍详细记录了明代的礼乐、祭祀和皇帝祭天大典。理氏如获至宝,在其书中援引了大量例子,例如:
仰惟玄造兮于皇昊穹,时当肇阳兮大礼钦崇。臣惟蒲柳兮蝼蚁之衷,伏承春命兮职统群工。深怀愚昧兮恐负洪德,爰遵彝典兮勉竭微衷。遥瞻天阙兮宝辇临坛,臣当稽首兮祗迓恩隆。百辟陪列兮舞拜于前,万神翊卫兮以西以东。臣俯伏迎兮敬瞻帝御,愿垂歆鉴兮拜德曷穷。(Legge,1852:25;原文出自《大明会典》卷82)
在这段祷文的英文翻译中,“玄造”被理氏译成“mysteriously-working Maker”,即“神秘的造物主”,而中国的皇帝则带领他的臣民在祭坛向造物主“帝”拜倒,并承认自己的权力来自“帝”。“万神翊卫兮以西以东”被译成“all the spirits accompany Thee as guards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在理氏看来,这里的“神”实际上就是《圣经》中的“Spirit”。通过对《大明会典》所载祭祀情况的研究,理氏宣称:“从上述祷文和典乐中不难发现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他就是万事万物之主宰、至善至爱、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且永恒的存在。‘神明’和人类都赞美他,歌颂他,并因他而存在,因他而喜悦。他就是中国人在其最高规格祭祀中所崇拜的‘上帝’,也是我们的‘God’。”(Legge,1852:31)
当然理雅各也承认不能把中国的宗教同新教相提并论,他认为中国人也存在一些迷信思想,主要表现在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两方面。但理氏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祖先称为某种神明。至于偶像崇拜,理氏把其归因于中国人对“God”的认知仅仅是通过“自然神学”的方式获得的。理氏还就此问题比较了古代犹太人、罗马人和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认为古代犹太人和罗马人也存在严重的偶像崇拜,中国人犯的那些“错误”并不足以为奇。而且,在理氏心目中,中国人的宗教道德水准还在古罗马人之上,中华文明也远胜过其他许多文明,他写道:
中国人的庙宇不像罗马人神庙那样充满可憎的欲望。中国人也不会对诸如角斗士那样的游戏和演出趋之若鹜。虽然我并不是要赞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或是把这个民族打造成道德楷模,但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所有异教国家中的确占有独特的地位。这个国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注重礼仪,在文明上优越于其他东方民族。(Legge,1852:59)
也许这种文明高低程度的比较多少显得“政治不正确”,但理氏对中国文化无疑是充满好感的,考虑到19世纪的中西方力量对比,这种精神尤为难得。当然理氏对中国这一“他者”文化的偏爱并非空穴来风,他在书中该部分最后总结道:
一想到如果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走向坟墓,却没有一个人的头脑中有“God”,或念叨过“God”的名字,这种想法就让人不寒而栗。实际上,一个民族如果丝毫不知“God”的存在,就不能延续到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无疑是一神教,而这和他们延绵不绝的悠久历史绝非毫无关系。而且我坚信,和其他因素比起来,这种一神教对中国文明的繁衍生息作用最大。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的确可以避免其他强大国家的入侵,其对孝的推崇和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也能够维持其政府的良好运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无政府主义,但真正能够保持中华帝国发展,避免走向腐朽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民族从古至今都保持着对“God”的崇拜。(Legge,1852:59)
6.2 God,Elohim,Theos并非类名
通过对《大明会典》的考察,理雅各明确表示中国人存在对“God”的认知,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就是“God”。之后,他接着批判“神”派传教士的第二个主要论点,即“God”、“Elohim”和“Theos”均是“类名”,他们的汉语译名因此也须是一个“类名”。理氏从词汇学角度分析了何为“类名”。在他看来,“类名”作为某一类事物的统称,其所指包括众多个体,但不论这些个体相同与否,他们在这一‘类名’下地位平等(Legge,1852)。理氏以“狗”和“树”这两个字为例具体说明何谓“类名”。理氏认为这两个词汇均为“类名”,就词汇学角度而言,不论是何种狗,所有的狗都是平等的,也不论是何种树,所有的树都是平等的。在理氏看来,一个“类名”表达了很多个体的存在,并且就所蕴含的共同性质而言,一个“类名”下的所有个体都是平等无差别的。厘清“类名”在词汇学上的性质之后,理氏反问道:“难道‘God’是一个‘类名’吗?难道有很多其他存在具有和‘God’相同的属性,并且就这一属性而言,那些存在和‘God’是平等的?”(Legge,1852:75)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God”是独一无二的。既然“God”不是一个“类名”,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词汇呢?理氏告诉读者:“God”从来就不是一个“类名”,实际上只是一个“关系词”,表达一种相对的概念。在理氏看来,“‘God’一词并不表达存在本质(essence)或是任何有关耶和华存在的概念,它的真正意义来自‘God’与其所主宰的世间万物所构成的关系。”(Legge,1852:73)理氏这一论述已经涉及基督教自身的神学理念,而他的观点可谓惊世骇俗、相当激进,因为这种看法在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本身就极富争议,在普通西方人头脑中,“God”从来都是表达的一种绝对存在。
“神”派传教士对理雅各的上述两个观点自然是愤怒不已,纷纷指责理雅各亵渎和背叛了基督教教义。然而,理雅各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妥协。1877年,当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中国传教士大会时,理雅各专门撰写了《儒教与基督教之关系》(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一书,再次宣称:“中国经典中的‘帝’和‘上帝’就是‘God’,就是我们的‘God’,真正的‘God’。”(Legge,1887:3)应该说,理氏的论述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是一种历史存在的真实再现,而是传教士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是以西方为中心投射出来的产物,但是,较之其他传教士,理雅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观念无疑是最为欣赏和同情的。在参与“译名之争”不久,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经典,并相继完成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的翻译工作,成为西方世界著名的汉学家。
7.结语
理雅各的加入给“上帝”派打了一剂强心针,两派人马均无法说服对方,于是分道扬镳,推出了各自的译本。两部译本虽均取名《新/旧约全书》(相继于1854年和1863年出版),但分别采用了“上帝”和“神”的译名。“上帝”版译本由于得到近代著名文人王韬的襄助,译文更为流畅地道,使用也更为广泛,《圣经》汉译史上著名的“委办本”《圣经》即此译本。然而,“译名之争”并未就此结束,沉寂一段时间后,英美传教士继续就此问题发表文章,相互指责,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参与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1890年,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召开了第二次中国传教大会,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希望传教士译者重新联合起来推出统一的“和合本”翻译计划。不过在译名问题上,传教士仍未能达成妥协,大会最终决定,联合翻译完毕后的“和合本”在日后出版时分为“上帝”版和“神”版分别印刷,各传教差会自行选择使用(Lewis,1890:Xli)。自此,近代《圣经》汉译史上有名的“译名之争”终告结束。
“译名之争”反映出两派译经人士对待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神”派译者试图在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全面改造中国人的信仰,“上帝”派译者则试图从中国宗教文化中寻找到与基督教的契合之处,“完善”中国人的信仰。争论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上帝”和“神”两个译名并存于世,再加上天主教的官方译名“天主”,“God”在汉语《圣经》中竟出现了三个主流译名,就《圣经》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和传播而言,这种现象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曾说:“传教士们走遍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异教国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和翻译《圣经》,但在为‘God’寻找一个恰当的译名问题上从没有遇到在中国这样严重的困难。”(Mateer,1901:61)狄考文的话其实无意中道破了“译名之争”的玄机所在。当传教士怀揣把福音传播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宏大计划时,他们在很多地区都取得了成功。但当他们来到中国之后,立即发现其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极度悠久、文明高度发达的异教民族,中国人的头脑中已经充满了各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概念,没有留下太多空白等待他们来书写。显然,传教士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把福音告知中国人,而是如何成功地在汉语言文化框架内植入基督教信仰,但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信仰与文化的紧张,《圣经》汉译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是涉及深层次的基督教神学和中国宗教哲学问题,就此而论,“译名之争”实际上反映出翻译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概念移植的困境。
[1]Boone,William Jones.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Elohim”and“Theos”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8(1):17-52.
[2] Lazich,Michael C.E.C.Bridgman,America’s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M].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
[3]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M].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2.
[4]Legge,James.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William J.Boone[M].Hongkong:Hongkong Register office,1852
[5] Legge,James.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M].Shanghai:Kelly& Walsh,1877.
[6] Lewis,W.J.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
[7]Lowrie,W.M.Remarks on the Words and Phrases Best Suited to Express the Names of God in Chinese[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6(12):577-600.
[8]Mateer,C.W.The Meaning of the Word 神 [J].The Chinese Recorder,1901(2):61 -72.
[9] Medhurst,W.H.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M].London: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36.
[10]Medhurst,W.H.Reply to Boone’s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Elohim”and“Theos”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8(10):489-520.
[11]Medhurst,W.H.Things in Shanghai[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9(7):384-390.
[12]Milne,William.Some Remarks on the Chinese Terms to Express the Deity [J].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8(9):318-320.
[13]Morrison,Eliza.A.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Vol.1)[M].London:Longman,1839.
[14]爱汉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5]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M].余三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孟德卫.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的调适策略与汉学的起源[M].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17]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8]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首次撞击)[M].耿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9]杨森富.唐元两代基督教兴衰原因之研究[M]//刘小枫,编.道与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0]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