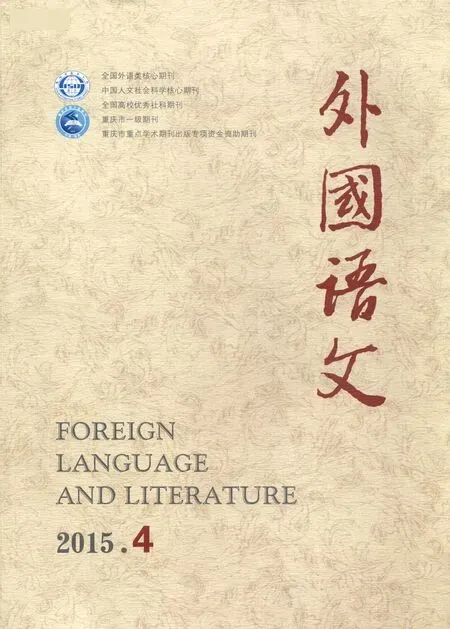文学作品中方言翻译再思考
王恩科
(贵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方言富含地域文化色彩,形象生动,是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喜爱的创作元素。从中国的《红楼梦》到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下简称《历险记》),读者总能领略到方言的魅力。作家精心选择的方言让读者会心一笑的时候,却给小说的译者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将原文的方言译成标准语还是方言?成了摆在译者面前的两难选择。译成标准语,不仅原文的方言特色丧失殆尽,而且原文方言所产生的文学艺术效果也很难在译文中得到充分体现。以方言译方言,虽然译文有助于再现原文方言的艺术魅力,但所呈现的地域特色却与原文方言的地域特色相去较远。因此,文学作品中方言的翻译是译者颇感棘手的难题,翻译理论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难以达成共识。难怪有学者几年前就指出,“至于在理论上方言能否用于翻译,仍然是一个价值判断上的两难问题……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翻译理论界尚未真正有效地解决的问题。”(王宏印,2003:210)虽然方言翻译只是文学翻译中一个不为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但处理是否得当却会在塑造人物、烘托环境等方面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面对我国翻译界目前“对方言翻译的研究很少见”的情况(陈吉荣,2010:67),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是有必要继续和深化对方言翻译的探讨,既为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充实尽微薄之力,也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借鉴。
1.方言及其功用
方言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的使用是比较常见的,中英小说概莫能外。以虚构的威塞克斯为背景的系列小说中,哈代使用了许多英格兰南部方言,马克·吐温的《历险记》使用了大量黑人英语,诺贝尔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也不例外。在我国,方言在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红楼梦》中既有东北方言、山东方言、江淮方言、云南方言,也有其他方言,不仅方言的种类多,而且数量也不少,其中仅江淮方言有据可查的就有37个、云南方言也有58个;(林纲、刘晨,2011:168-170);清代末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列传》)其人物对话几乎全部使用吴语;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许多小说中,陕西方言更是随处可见。难怪有学者认为:“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某一地方言或几地方言的运用。”(柯玲,2005:44)中外作家之所以对方言喜爱有加,就在于方言的恰当使用能使小说增添标准语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仅就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修辞功能而言,田中阳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种:“首先是在人物语言的描写中,它能摹声拟态,随声传形,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其次是比喻、双关、反语、通感、夸张等修辞格,在方言语境中显得更鲜活且富于个性化;再次,还表现在对当代小说家语言风格形成的影响上。”(田中阳,1995:86)美国学者理查德·刘易斯认为黑人英语主要有16种文学功能,王艳红将其总结为如下四种:“人物刻画、文化继承、情感激发与政治观点。”(王艳红,2010:44)本文无意归纳总结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种种功能,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的确有着标准语不易替代的艺术功能。
尽管方言能发挥标准语不易替代的艺术功能,使文学作品增色不少,但由于中英方言在书面形式、同一语言内部不同方言之间的联系上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中英小说在方言使用及其读者接受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不同。英语文学中,小说大部分使用方言而依然成为名作的不乏例证,《历险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部,但汉语中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比较明显的例子当属《列传》了。这部小说的人物对话几乎全部使用吴语,“这种吴侬软语在江浙沪一带,人们读来自然懂,甚而还能领略到说话人的神情姿态。然而这段说白倘让幽燕之地的大汉来看,不啻像在读天书”(吴元栋,1995:42)。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与韩邦庆好友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相比,《列传》的命运就耐人寻味了。韩邦庆在创作《列传》时,孙家振曾劝其改用白话,韩邦庆不以为然,最终导致两人几乎同时出版的小说遭遇不同的命运。小说写成20多年后的1925年,孙家振在《退醒庐笔记》中有一段十分发人深省的回忆:
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至两书(按:指《海上花列传》及己著之《海上繁华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日《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竞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敢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黄岩柏,1991:53)
尽管《列传》被胡适在1926年《〈海上花列传〉序》中誉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黄岩柏,1991:53),但也摆脱不了“不获风行于时”的悲惨命运,或许只能靠张爱玲的白话文译本“延续”其生命了。孙家振针对《列传》命运的这段回忆,就汉语小说中方言使用而言,至少给我们如下启示。首先,慎用“限于一隅”的方言;其次,区分“限于一隅”的方言与“到处流行”的“京语”类方言;第三,小说中方言使用失当,“遂令绝好笔墨竞不获风行于时”。
原创文学作品中方言的情况如此,翻译文学中的方言又如何呢?翻译文学作品从接受的角度看,与原作一样也是独立的艺术个体,因此在方言的评价上有着与原作大致相同的标准,但翻译文学毕竟与原作有着割舍不断的种种联系,因此对翻译文学中方言进行评价要比原创文学更难更复杂。
2.理论争鸣
方言频繁见于原创文学作品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只要使用恰当,其艺术效果和魅力也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翻译文学中使用方言,人们的观点就没有那么一致了,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支持者中间,有大家熟悉的林以亮、刘重德、郭著章、奈达、卡特福德等(韩子满,2002:86-87)。从王宏印“采用方言的某些表达法,但不直接采用现成的词句”看(张谷若,2003:211),他并不反对使用方言。就国内翻译界而言,“对于英语方言汉译的讨论,多数集中于对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中威塞克斯方言的翻译……作为方言对译法的支持者,大多数研究只是对译本作了对比,给出了想当然的主观评价,并没有给出理论依据,缺乏说服力。”(王艳红,2010:3)纵观我国翻译界支持者的论述,王艳红的以上评述不无道理。与支持者相比,反对者也阵容强大,并不示弱。卞之琳、傅雷、王佐良、孙致礼、韩子满等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几位。
卞之琳在《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中指出,虽然他很清楚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独白和对白类似“我国京剧的‘京白’和昆剧的‘苏白’”(陈国华,1997:50),但他在翻译时并不用北京土话予以区分,因为“我操纵不了北京土话,而且,更主要的,原则上不想这样做”(同上)。并认为“我国过去有人翻译哈代小说,就煞费苦心,把原用英国多塞郡方言写的对话译成山东话,效果是中国化到地方化了,过了头,只有引起不恰当的联想。山东风味,恰好有失原来风貌”(同上)。
傅雷曾经指出:“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杀,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傅雷,1984:547)傅雷这句话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方言有其自身的“生命与灵魂”,即充分肯定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价值;其次,是译者使用方言会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即不赞成方言互译。傅雷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恰恰是许多反对方言互译的人喜欢引用的名言。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傅雷的这句话。这句话的前后两部分相互矛盾。既然原作中的方言有其“生命与灵魂”,译文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方言呢?难道译文中的方言就没有“生命与灵魂”吗?除了这句话的前后部分矛盾外,第二部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它不符合逻辑。某种汉语方言是汉族某个聚居区通行的语言,毫无疑问,使用这种方言的人只是泱泱中华大地上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如果说译文中使用这种方言就能“变外国人为中国人”,那么我们试问:如果译文使用通行全国的普通话,外国人难道就成了超中国人或全球华人吗?其次傅雷的论断在方言和标准语的使用效果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如果不顾话语的内容,仅仅就言说方式而论,翻译毫无疑问都是“变外国人为中国人”。例如,巴尔扎克不懂汉语,深受我国读者喜爱的《高老头》中文本不可能出自巴尔扎克之手如果不是傅雷将巴尔扎克变成“会说汉语”的“中国人”,我国广大读者对这位法国文学大师也许只能“望洋兴叹”。对于这样的“变”,作为译者的傅雷没有反对,广大文学批评者非但没有责怪,反而赞叹不已。译文中使用方言毫无疑问也引发了类似的“变”,无非是把使用方言的外国人转变成了满口方言的中国人罢了。总不能因为我们中间有人说方言就把他排除在“中国人”之外吧?既然译文使用标准语和方言都“变外国人为中国人”,那么仅仅反对方言的使用不就有失偏颇吗?因此,如果不考虑译文中方言使用的具体艺术效果,仅就理论分析而言,认为译文使用了汉语方言就会“变外国人为中国人”,并以此反对方言互译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王佐良在翻译彭斯诗歌时就不主张使用方言。我们知道,彭斯的诗“用的主要是他的家乡方言低地苏格兰话(Low land Scots)”(陈国华,1998:89),他本人也“意识到用方言写诗给大多数读者带来的语言障碍”(同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在他的诗集末尾附上一个词表,解释诗中所用方言词的意思”(同上)。在翻译这些苏格兰地域色彩十分鲜明的诗篇时,王佐良认为,“以方言译方言,即使能办到,也不可取,因为那不仅会带来一种与原作不一致的地方情调,而且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种外加成分”(同上)。王佐良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还是看看他本人翻译的《佃户的周六夜晚》吧。陈国华在“王佐良先生的彭斯翻译”一文中指出,《佃户的周六夜晚》描写的是苏格兰一个普通佃户周六夜晚的生活片段,其中辛勤劳作了一天的父亲回家、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和拉家常等是用苏格兰方言写成的;18世纪的苏格兰,英语一般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而苏格兰方言则在非正式、随便的场合使用,所以彭斯使用苏格兰方言描述佃户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显然经过慎重的考虑和选择”,毕竟“描绘这样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苏格兰风俗图,自然非用苏格兰方言不可”(陈国华,1998:90)。原诗从第14节起讲述的是父亲宣讲《圣经》和全家祈祷的情景,最后3节则是诗人抒发对苏格兰和苏格兰人民的歌颂和祝福,但这一部分中诗人没有使用一句苏格兰方言。可以说,原诗在语言风格上的这种显著差异显然是诗人有意为之,因此“这种鲜明对照如果在译文中得不到任何体现,不能不是一种遗憾”(陈国华,1998:90)。《佃户的周六夜晚》中,从方言到标准语的变化,不仅是原诗语言风格变化的显著标志,而且还是轻松幸福的家庭生活话题向庄重严肃的宗教话题转变的语言形式标记。王佐良的译文全部采用普通话翻译,显然无法如实再现原诗的上述变化,其艺术效果不可能不打折扣。
国内有关方言翻译的论述中,引用较多的是孙致礼对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译文中山东方言的使用所做的评论。孙致礼认为:“从语用的角度看,‘抱上锅,撮上炕’似乎跟原文比较对应,都表示热情接待客人,但从文化习俗来看,差距是显而易见的”(2003:49),亦即,造成了“文化风习上的扭曲”(同上)。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上述译文要么对大部分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要么使能理解的读者产生错误的联想,因此这种“以土话译土话”,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做法“代价委实太大”(同上)。最后,就方言如何翻译他得出如下结论:“依笔者之见,对于英语里的地方方言,不折不扣的对等传译是做不到的,但却有一个‘打折扣’的体现办法,就是把话译得‘俗气’一些。”(同上)这就是说,尽管以方言译方言存在诸多问题,“不折不扣的对等传译是做不到的”,因此“把话译得‘俗气’一些”,无论如何是“一个‘打折扣’的体现办法”。这种“俗气”一点的译法虽然消除了读者理解上的困难,但原文的文体信息、方言所蕴含的其它信息不也丢失了吗?而且对文学作品而言,比文化信息更为重要的艺术效果也“打折扣”了。因此,这样的变通是否就比方言译方言更好,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不能一概而论。
韩子满在方言翻译问题上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除了颇具深度的论文《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以下简称《局限性》)外(韩子满,2002:86-90),《英语方言汉译初探》(2004)可能是目前国内该领域唯一的专著。在《局限性》一文中,韩子满从方言在英汉两种语言文学作品中的形式、文学作品中使用情况、读者的接受、语用功能、艺术效果等几个方面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虽然译文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传达出了一些乡土气息,但就方言成分在原文中的主要功能来看,他的译法并不成功。”(韩子满,2002:88)究其原因,“首先,译文未能体现出方言成分在原文中增加真实感的功能”。“其次,原文中方言成分暗示人物身份的作用在译文中也未得到传达”;“再次,严格说来,译文也未能忠实于原文”(韩子满,2002:88-89)。究竟如何翻译方言,他最后指出:“在方言翻译中,通常意义上的‘忠实’或‘对等’是基本上做不到的,语义或语体上的损失要比标准语翻译大”;但在“明确方言的功能”下,有两种解决办法,即:“如果原文中方言主要是用来确立地理背景的,这时我们只能束手无策,放弃在译文中传达这个功能的努力;如果原文中方言是用来表明人物不同的身份和教育的,那我们则可以采用其他补偿的手段来传达这个功能”(韩子满,2002:89)。上述解决方案中,第一种其实是知难而退,选择放弃,第二种所谓的“其他补偿”办法,韩子满并没有明确说明。倒是在另一篇文章《过犹不及——浅论译文的归化问题》中(韩子满,2000:73-77),他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相比之下,孙译本对原文中这些方言成分的处理就要好得多。尽管用通俗的汉语口语也译不出原文的地域特点,但是这样至少表现出了人物的身份,而且也能为广大读者理解。”(韩子满,2000:75)也就是说,“用通俗的汉语口语”翻译英语方言,虽非完全令人满意,但与张谷若的译法相比,却是“对原文中这些方言成分的处理就要好得多”。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十分令人信服。首先是“通俗的汉语口语”同样“也译不出原文的地域特点”;其次是“通俗的汉语口语”不一定能够“表现出了人物的身份”,因为“通俗的汉语”只是一种语体,是言说者根据场景做出的一种选择,与言说者的“人物身份”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第三,译例不能有效支撑论点。他在上述结论后给出孙致礼译本中的两个例子,其中一例如下:
How nonatural the brightness of her eyes did seem,and how they stood like waxen images and talked as if they were in a dream!Didn’t it strike ’ee that’twas so?Tess had always sommat strange in her,and she’s not now quite like the proud young bride of a well-be-doing man.(第37章)
苔丝的眼睛那么亮,好不自然哪,两人就像蜡人一样站在那里,说起话来恍恍惚惚的!你不觉得是这样吗?苔丝向来就有点古怪,眼下哪里像是个有钱人的新娘子,一点也看不出得意的样子。(韩子满,2000:74)
克莱和苔丝婚后不久就决定分手,分别前重回两人曾经热恋过的塔布篱牛奶场,向老板和工友告别,上述例句是他们离开牛奶场时老板娘对老板说的话。原文中方言的使用主要显示老板娘文化水平不高,但译文的通俗却并不能“至少表现出了人物的身份”。倒是张谷若的译文由于使用了通俗易懂的方言,反而多少“表现出了人物的身份”来,如:“俺看苔丝的眼神那么亮,那么不自然,他们说起话来那么忽忽悠悠地,一举一动也那么木雕泥塑一般!这些情形你没看出来吗?苔丝那孩子本来就有些跟别人两样,这阵儿一点也不像是个嫁给有钱的人那种得意的新娘子。”(张谷若,2003:298)尤其是孙译本的“有点古怪”和“眼下”与张译本的“跟别人两样”和“这阵儿”相比较,后者更像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村妇的语言。总之,该例句并不能有效地支撑作者得出的结论,即:“通俗的汉语口语”“至少表现出了人物的身份”。此外,哈代小说中方言的使用还与语境有关。上述对话就是牛奶场老板夫妇与当地员工在一起这种方言语境中发生的,就像苔丝在家里跟父母使用土话一样都是语境使然。
《英语方言汉译初探》(英文)是韩子满为文学作品中英语方言汉译贡献的一部力作。该书详细阐释了英汉方言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如书面体系、读者接受、社会功能等,分析了英语方言汉译的一些实例,提出了英语方言汉译的五条原则,基本内容如下:(1)完全对等是做不到的,一定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2)具体分析每个方言词的语境,决定是否有必要移植其方言特色;(3)给原文增加真实感和地方色彩的方言因其无法跨文化移植只好放弃,但其他功能的方言词则应予以妥善处理;(4)使用汉语的飞白、方言来翻译英语方言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而且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阅读困难;(5)刻画人物和增加幽默感的方言不应被忽视,由于译入语无任何方言可传递其语义和风格意义,所以一定的补偿手段是必要的。这五条原则更多的是不能怎样译,至于如何译,却并没有给出多少可资借鉴的“原则”,倒是其后建议的两种办法明白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使用汉语俗语(Colloquialisms)和注释(Notation)(韩子满,2004:105-111)。据此可以看出,在英语方言的汉译上,该书作者认为使用方言不在推荐之列。
《试论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浮躁〉中的“瓷”为例》是近期的研究成果。该文认为,“从原文可以看出,陕西方言中的‘瓷’可以表达复杂的意义和人物感情,也是原句中的精彩之处,原译中几乎所有的误译和漏译都忽略了这一点,而只将人物的动作简单表现出来。”(李颖玉、郭继荣、袁笠菱,2008:66)“作为反映地方特色的小说作品而言,方言文化负载词的深层含义未能得到充分展示,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同上)该文最后提出如下建议:“事实上采取积极措施、优化译文表达、增强关联效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同上)上述建议看似有理,实则非常模糊,因为“优化译文表达、增强关联效果”毕竟见仁见智,译者难免无所适从。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该文针对译者的许多误译给出的改译,其自身所用词汇全为标准语而非方言词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申出该文在方言词翻译上的基本策略:即准确透彻理解原文方言词,用标准语表达之。既然认为贾平凹小说中“陕西方言中的‘瓷’可以表达复杂的意义和人物感情,也是原句中的精彩之处”,那么使用标准语“只将人物的动作简单表现出来”,恐怕很难说译者就很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也很难说译文就恰如其分地“表达复杂的意义和人物感情”,再现了“原句中的精彩之处”。虽然该文前后观点不免有些矛盾,但从这些矛盾之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文学作品中方言词巨大的艺术魅力和跨文化翻译的重重困难。胡宗锋“以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先生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的英译文中的错译、误译和漏译为例,阐述了在文学翻译中,正确理解作家作品中所用方言的重要性”(1999:163)。对于贾平凹小说中方言的翻译,究竟用译入语的方言还是标准语,胡宗锋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但从文章提供的方言误译的改译看,他所使用的标准语而非方言说明,该文虽然早于《试论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浮躁〉中的“瓷”为例》近十年,但基本观点是大体一致的,即以标准语译方言。
除了国内上述反对方言互译的声音外,引用较多的还有哈蒂姆(Hatim)和梅森(Mason)在《语篇与译者》中的例子。哈蒂姆和梅森提到多年前苏格兰的一场争论,那是一部外国电视剧中用苏格兰方言再现俄国农民引发的。他们认为:“这种再现方式使人们很可能将苏格兰方言与低下的社会地位相联系,这毫无疑问并非当事人所想要的。”(Hatim&Mason,2001:40)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使用苏格兰方言,但其基本态度则是不言而喻的。一些研究者在引用上述例子反对文学作品中方言互译时,似乎忽视了其中地域方言与社会阶层方言的错位,毕竟苏格兰方言属于哈蒂姆和梅森划分的五种方言中的地域方言,而原作中俄国农民的语言则属于社会阶层方言(同上)。如果那部电视剧的译者不是使用苏格兰方言,而是使用英国农民的语言,不知道是否会引发人们的争论呢?
纵观上述反对方言互译的观点,其理由大致如下:(1)地方情调错位;(2)引起原文所没有的联想;(3)文化扭曲;(4)理解障碍。对于如何翻译,反对者建议的主要方法如下:(1)普通话;(2)普通话中俗气一点的表达方式或通俗的汉语口语;(3)注释。上述理由中,(1)的确是方言互译的短处,(2)和(3)却是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本质属性引起的,因为译文是在新的互文性系统和新的文化场域中解读的,所以这两种不足不为方言互译所独有,何况译文的内容能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关于“理解障碍”,许多汉语名著尤其是《红楼梦》使用大量方言的情况,可以对其起到釜底抽薪的质疑作用。反对者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化解上述部分矛盾,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因此而冰释,更不用说原作在使用方言时所预设的艺术效果能否得以再现了。
那么,就翻译策略而言,方言互译有其理论依据吗?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翻译策略上的“归化”和“异化”之争便成为翻译理论界的热点话题。尽管目前学界就异化和归化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但归化和异化在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中都具有各自不易替代的作用却是争论双方都不否认的事实。目前,翻译界中“异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孙致礼,2002:40)。不管这样的呼吁或预测是否代表21世纪我国文学翻译的发展趋势,毋庸置疑的是,异化为主流话语引入“异质”成分、促进文化的丰富性方面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普通话是汉语的主流话语,除了欧化的词汇和句式是“异质”成分外,各地方言同样也是“异质”成分。那么,张谷若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使用山东方言的情况又如何呢?吴文安和朱刚的分析可谓透过现象、直抵本质。
当前,中国不少学者提倡外译中时要采取异化式翻译,他们也往往引韦努蒂为证……然而他们在反对归化、提倡异化翻译时所举归化的例子,有些并不是归化式的,反而恰好属于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例如,孙致礼先生提到张谷若把《苔丝》中的英语方言译为山东方言的例子“抱上锅,撮上炕”,认为“恐怕至少90%以上的中国读者看不懂这句山东土话的意思”,属于乱用替代的归化式译法,应该摒弃……那么山东方言是中国的主流透明话语么?很显然不是。恰恰相反,90%的中国人不懂的方言是不同于中国主流话语普通话的异质性成分,是主流话语之外的“其余成分”。既然如此,译为山东方言的译文就会扰乱中国当前的普通话主流,属于异化式译文,绝不是归化式译文。(吴文安、朱刚,2006:97-98)
既然山东方言是“中国当前的普通话主流”之外的“异质性成分”,是主流话语得以丰富的源泉之一;既然异化是与归化并存的翻译策略,更是目前国内许多研究者提倡的翻译策略,那么如果不考虑个别译例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应该否认张谷若在译文中使用山东方言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方言是作者精心设计使用的艺术元素,在作品中发挥着标准语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具有标准语所不具备的艺术价值;方言互译属于目前翻译界所竭力倡导的异化翻译,是再现原作方言特殊作用和艺术价值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否认方言互译的合理性。
为了走出目前方言翻译研究的困境,深化方言翻译的研究,我们有必要把方言的翻译问题分成两个层次:一是策略层面的问题,即方言该不该译成方言;二是技巧层面的问题,即如何翻译方言。很显然,这两个问题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将它们放在同一平台上归并研究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以往反对方言互译的研究者往往将这两个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一方面承认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却因其翻译难度大、部分互译实例效果不一定理想而否认方言互译的合理性,进而在不知不觉中间接否认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论述过程中前后矛盾的尴尬局面。与此相似,方言互译的支持者往往“只是对译本作了对比,给出了想当然的主观评价,并没有给出理论依据,缺乏说服力”(王艳红,2010:3),因此使得他们对方言互译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将方言翻译的问题区分为两个层次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反对者摆脱论述中前后矛盾的尴尬局面,也有助于支持者摆脱具体译例的束缚,从理论的高度探索和进一步认识方言互译的合理性,为方言互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承认方言互译的合理性,并不等于说方言互译是方言翻译的唯一途径。由于方言及其翻译的极端复杂性,方言的翻译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途径。在方言翻译的问题上,我们既要承认互译的合理性,又要允许多种翻译途径的尝试和互补,只有这样,方言翻译的实践才会百花齐放,方言翻译的理论探讨才会逐步深入。
3.读者接受
对英语方言的汉译,理论探讨不仅必须而且也是十分有益的,但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争论,显然与翻译界近年来主流的研究方法——描写法是不协调的。为了对方言翻译有一个更为直观和全面的认识,我们有必要看看我国翻译界争论最多的张谷若译本《德伯家的苔丝》吧。“德伯太太是说惯了土话的;她女儿在‘国家学校’里,受一个伦敦毕业的女教师教导,已经第六级及格,所以说两种话;在家里或多或少地说土话,在外面或者和有身份的人谈话,说普通话。”(张谷若,1984:28)这是小说开始部分的一段话,它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说至少使用了标准语和土话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实际情况,尤其是人物对话部分,的确如此。难怪张谷若在1936年版“译者自序”中指出:“原书叙述,描写的地方,译文用普通的白话文,这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至于原书的对话,本是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英国话,一种是英国道塞郡(Dorset)一带的方言。所谓普通的英国话,就是Daniel Jones,Harold E.Palmer,Walter Ripman诸人所说的英伦南部受过教育的人所讲的话。”(张谷若,1936:1-2)“我最初本来一概用北平的方言来译原文的对话。但是后来觉得,原文分明是两种话,译文里变成了一种话,那怎么成呢?”(张谷若,1936:2)客观地讲,张谷若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途径,译文中抹去人物对话的方言特征,不可能不辜负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对话来塑造人物性格的良苦用心,不可能不影响原文中的人物因使用方言而产生的艺术效果。译者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哈代使用方言的良苦用心,那么译者以方言译方言的良苦用心读者领情吗?请听听当时读者的心声,看看专家的评论吧。
译者用北平语来翻译书中的标准的英文,至于原文的道塞郡的方言,他用了山东东部的方言来译。这样读上去便更觉传神了。不太懂山东方言的读者,或者觉得山东话读来没有北平话流利,然而那亦何殊于不大懂道塞郡方言的英国读者去读哈代的原文呢?(林辟,1940:118)
张君除了采取“道地”译笔以外,并且还勇敢地用中国北方的方言(山东东部)译原文Dorset的方言,因此,“倷”,“啥”,“俺”一类土头土脑的字眼在本书中到处可见。笔者在这里还想指出本书另一个特殊的美德,那是注解的详尽。(萧乾,1937:43-44)
在萧乾的眼里,“勇敢地用中国北方的方言(山东东部)译原文Dorset的方言”与“注解的详尽”同样都是译本的美德。几十年前如此,那现在情况如何呢?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于2000年公布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书目100本”,在入选的仅仅22本外国文学译本中,张谷若1957年的译本《德伯家的苔丝》就赫然在列。从重庆几所大学①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统计时间为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底。哈代这部著名小说四种主要译本②张谷若1984年译本、孙法理译本、孙致礼译本、吴迪译本。的借阅来看,张谷若的译本占了总人次的48.6%,远远超过其他译本,读者的钟爱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就方言的翻译而言,张谷若的三个译本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1936年版在译本末的925条注释中,有72个用于解释方言,除两个北平方言外,其余为山东方言。1957年和1984年的两个版本改第一版的尾注为脚注,其中前者有306条脚注,后者432条脚注。两个新版都只有一条脚注与方言有关,其余均与方言无关,但这并不表示两个版本仅用一个方言词。这两个版本相对于第一版而言,方言词的使用呈现递减的态势。如方言互译反对者们经常引用的译例“抱上锅,撮上炕”,在1984年版本中已经改为更易理解的方言表达方式“又搂又抱,又亲又啃”。通读张谷若横跨近50年的三个译本,我们发现,其中使用的方言词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减少,但最显著的变化是小区域方言为大区域方言或普通话所替代,不过原来的大区域方言基本保留了下来。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孙家振在80多年前的感慨:“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敢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总之,以方言译方言的张谷若译本,不仅在其出版初期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大学生欣赏哈代这部名著的首选译本,难道这对文学作品中方言翻译的理论探讨不正具有某种启发吗?
4.结语
方言极具文化色彩,因此也就成了跨文化翻译中难度较大、失真较多的语言成分。这些失真既然是翻译本质属性使然,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方言的翻译上任何求全责备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理论界对方言翻译的探讨,理应放弃以往规约性的研究理路,更多地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仅凭名人的只言片语就否定了文学作品中方言互译的合理性不是科学的态度,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在经过多年的长足进步后仍需警惕和尽力避免的研究思路。对于文学作品中方言翻译这样的复杂现象,我们应该将其区分为该不该用方言翻译和如何用方言翻译这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以往许多研究中前后观点矛盾的尴尬,也有利于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层面抓住主要矛盾逐一突破,从而将方言研究推向深入。文学作品中方言的翻译,我们既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全面深入的探索,也需要关注方言翻译的实际情况,更需要将文学作品的最终消费者——读者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我们对方言翻译的研究就有可能尽量避免以偏概全,得出在理论上合理并符合译本接受实际情况的结论。对文学作品中方言翻译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化和推动文化负载成分的翻译研究,而且还可以对翻译实践,尤其是目前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翻译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由于方言自身及其使用的极端复杂性,对其翻译的研究自然也是困难重重,见仁见智,更何况笔者才疏学浅,目前还难于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方言翻译研究犹如一块蕴含丰富的宝地,等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探索开发。
[1]Hatim,Basil.& Mason,Ia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陈国华.论莎剧重译(下)[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3):48-54.
[3]陈国华.王佐良先生的彭斯翻译[J].外国文学,1998(2):84-90.
[4]陈吉荣.摄入性改写视域下的翻译理论研究——以方言翻译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2):67-70.
[5]傅雷.致林以亮论翻译书[M]//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韩子满.过犹不及——浅论译文的归化问题[J].外语教学,2000(2):73 -77.
[7]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86-90.
[8]韩子满.英语方言汉译初探(英文)[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9]胡宗锋.试论文学翻译中的方言理解与翻译——读贾平凹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英译文[J].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163-166.
[10]黄岩柏.论《海上花列传》等吴语小说的历史教训[J].辽宁大学学报,1991(1):53-55.
[11]柯玲.论方言的文学功能[J].修辞学习,2005(3):43-45.
[12]李颖玉,郭继荣,袁笠菱.试论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浮躁》中的“瓷”为例[J].中国翻译,2008(3):64-67.
[13]林纲,刘晨.《红楼梦》方言研究二十年评述[J].湖南社会科学,2011(4):168-170.
[14]林辟.两部汉译哈代小说[J].西书精华(廿九年夏季号),1940:115-118.
[15]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16]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2003(1):48-51.
[17]田中阳.论方言在当代小说中的修辞功能[J].中国文学研究,1995(3):86 -92.
[18]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9]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0]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1]王艳红.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伦理与换喻视角[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
[22]萧乾.评张译《还乡》[J].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四期),1937:43 -49.
[23]吴文安,朱刚.翻译策略的语境和方向[J].外国文学评论,2006(2):90-99.
[24]吴元栋.自设樊篱[J].新闻记者,1995(8):42.
[25]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上、下册)[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