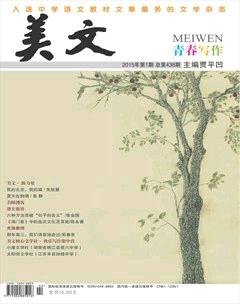他朝迢迢
段文昕
我活了十五年。
不顾一切想要看自己十七岁的样子。
说不上为什么是十七岁,或许是因为,十八岁太过于沉重,那时候的所有事物在别人开始已是定局,自己容易摇摇摆摆,收起棱角不动神色地做大人。十七岁太美,不用背负全世界的重量,可以恣意妄为,可以不顾一切。
记起爷爷。小时候性子大,爷爷从家乡搬来广州与我们同住一年,我便趾高气扬地“指挥”了他一年。那时他踩着自行车送我上学,我坐在后座动弹,脚伸进车轮子里面,爷爷踩得很慢,便只是鞋子卡住了,无奈脚也拔不出来。我煞有介事地叫起来,爷爷一回头便紧张得不得了,连忙停车,路旁有个修车的老伯伯,爷爷急忙叫住他,说:“我孙女的脚卡住了,帮帮忙。”
那是我记忆以来,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称我为,他的孙女,岁月不饶人,这也是最后一次。
那个伯伯从另一旁轻松地把我的鞋子扯出来,爷爷立刻笑了出来,那个伯伯没好气地用方言说着爷爷蠢,爷爷听不懂,只是哈哈地笑着,说终于没事了。
人的记忆总是很奇怪,我记不起第一次拿奖状的时候,记不起第一次摔跤的时候,记不起第一次哭的时候,却记得有一次从学校回家的时候,爷爷问我问题,我摆弄着他刚陪我买的玩具说了一句:“你好烦啊。”他说:“哈哈,我好烦。”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却每次回想时挥之不去他的脸。
我就这样不顾一切地生活着,十五年。
记起父亲,他和爷爷性子很像,温文尔雅,偶尔会暴躁抱怨,或许他年迈时会是比爷爷更要安静的人。我不愿去想父母年老的样子,因为现在的我叛逆冲撞,但最不愿伤害的,是朝夕相处的他们。
记起所爱,大多三分钟热度。就像茶凉人便走,没什么好争论也没有什么好说。就像布丁太炽热总会融化,就像流水太冷冽总会結冰。
三月轻雾,花开浅谷。春日蝶,年华无臃茧。
八月清河,草生堤堰。夏日蝉,岁月无薄纱。
九月高岸,叶落沙砾。秋日穗,流年无沉积。
冰月冽风,雪满枝丫。冬日梅,韶华无复返。
遇见很多人,知道他该是一阵风,她该是一场梦。或许等到哪天我终于成了听懂但不愿说话的哑巴,应该认认真真地种下桂花树,煮酒慰风尘,毕竟,少年如歌。
人间何处问多情,他朝两忘烟水里。
南方有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