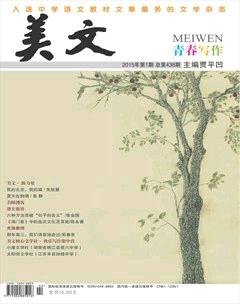夏天在倒塌
鲁静
鲁 静 1993年生,四川泸州人,中文系本科在读。曾获“作家杯”第十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人民文学》主办“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大赛小说组优秀奖等。
一、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夏天到来的时候,我总是日复一日地想起一个人。
那年我们高考,我发挥得不错,可以上一个普通的二本。但是为了他,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复读,只希望来年能考到他的那所大学。
他的名字叫若凡,像是诗人的名字。
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当回首往事时,就像剥开一只洋葱,一片一片,总有一片让你泪流不止。
我曾经在高四的夜晚无数次地想起若凡,于是我在一个个作业堆积如山的晚自习,抽空给他写明信片。我们学校以严格的管理著称,高三校区在一座小山上,与世隔绝。早晨的时候,山上烟雾缭绕,水气氤氲,如同仙境;而到了夜晚,却有些冷。山上的高三校区只有一家文具店,我在那里买了整整一盒明信片,五十张。那里的明信片说不上好看,只不过印着俗气的风景画,但这于我而言并不重要。我把明信片塞进课桌抽屉里,晚自习的时候心血来潮会抽一张出来,旁若无人地在上面写着分行的句子。我多么希望我写下的这些句子,可以变成一首首美丽的小诗;但很可惜,我并不会写诗。我只记得,若凡会写诗。
在那一个个忙碌而压抑的夜晚,我平均一周会给若凡写两三张明信片。等到周末,学校会在周日上午放半天假,大家都利用这短暂的时光逛街、吃大餐、睡觉、看电影,而我却哪儿也不去,径自下山,走一段路,到邮局去把堆积起来的明信片一股脑寄给若凡。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若凡的确切地址,我只知道他的学校和专业,我想这样他应该能收到我的明信片。
然而很可惜,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他的回复。
我想,或许我应该告诉他,我给你寄了明信片,你记得去学校收发室取哦;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只要能为他写下这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便已满足。
我给若凡写的最后一张明信片,是在高考的前夜。山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明明是夏天,我却加了件外套。我不知道要写什么,这时忽然想起了电影《一页台北》里的场景,似乎也是这样下着小雨的夜晚,冷清的街头。安静的书店里,男主角为了追随远在巴黎的女朋友,认真地自学法语,总是用法语重复地念着同一段话:
你好,菲菲
你好吗?
巴黎好吗?
我为你学法语
我很想和你一起在巴黎生活
但是我没有钱
巴黎是爱情的世界
没有你,台北很寂寞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工作
日复一日
我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我一直在想你
想我们两个走在巴黎的街头
你是我的幸福
永远……
我把这段话写在了明信片上,我能明显感觉到握着笔的手有些颤抖。写完后,我把明信片夹在了笔记本里。原本我打算高考一结束就去邮局把它寄出去,后来却有些不舍。时至今日,那张明信片依旧安静地躺在我的笔记本里,甜蜜地沉睡着。或许它将永远不会醒来,正如你将永远不会看到我寄给你的四十九张明信片。
二、我遇见你,我记得你
我和若凡相识,是在高一的时候。那时我们分别就读于不同的重点班,他不认识我,而我却知道他,只因为他的名字永远稳坐在光荣榜前三名的位置上。那时候,学校里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社,正在招兵买马。我第一次见到若凡,便是在文学社的干部竞选大会上。他个子高高的,瘦而挺拔,目光炯炯有神,穿着白色T恤和淡蓝色牛仔裤,来得颇晚。
“嗨,冯若凡,我们这里还有位子!”与我同行的女生冲着站在阶梯教室后排焦急地寻找座位的他挥了挥手,他旋即走上前来,坐在我们身旁。
“原来你就是冯若凡啊……”我低声道。
“怎么,你认识我?”若凡问。
我笑了起来:“久闻大名啊,你成绩很好的,我常听夏薇薇说起你,她和你同班。”
“哦,”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如同和煦的阳光,问,“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黎晓澈。”
“我知道你,我听夏薇薇说起过你,是个才女。今日有幸一见,实乃荣幸!”
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接话,只是羞涩地笑着,低下了头。我坐在第一排的角落里,埋着头帮老师做记录。到了若凡上场,他挺直了腰板,冲着所有人笑,那笑容如同早春的雨露,缓缓流过我的心上。不知怎的,写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的手居然微微地发抖,笔也险些从手里飞了出去。不过几个字而已,我却写了好久才终于一笔一画地写完。
若凡競选的职位是社长,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的能力原本就足以担此大任。好在我也成功竞选上了编辑部部长,这让我欣喜不已,大约是想到即将和若凡一起工作了。
夏薇薇是我初中时期的同学,关系还算密切,高中时和若凡分到了同一个班。后来我天天缠着她给我讲更多的关于若凡的事,她被我弄得不胜其烦,指着我额头骂道:“你个花痴啊!”那时每天下晚自习我都和她一起回家,我们俩慢悠悠地走在昏黄的路灯下,一边喝着奶茶,一边乐此不疲地讨论着关于若凡的种种。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故意放慢脚步,心里多么希望这短短的一段路可以变得绵延无尽。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若凡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那时我们年级一共有两个重点班,我们班在二楼,他们班在五楼。每次我要把稿子或是文件交到他手里都需要爬上那一级级的楼梯,虽然气喘吁吁,却从未觉得有半分累意。他的影子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不由得想见到他,想看到他对着我微笑。于是我想方设法为自己制造机会,譬如把稿子分成好几次交给他,或是想出各种关于工作的问题与他讨论。
可是,十六岁的我,还留着傻不啦嘰的齐刘海,并不懂得如何穿衣打扮,总是穿着宽松肥大的校服,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疲于奔命;胆小内向,甚少与人交流,不善言谈,一紧张就会舌头打结,脸蛋一下子就红了……
想到这些,我突然觉得很伤感很绝望。
然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决定义无反顾地为若凡写一首诗。
那是一堂百无聊赖的物理课,我依旧埋头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文学社新收的稿子整整齐齐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其中就有若凡的稿子,是几首小诗。我不懂诗,只是呆呆地看着纸上他那好看的字迹,突然觉得会写诗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于是我胡乱地写一些分行的句子,在我心里,它们就是诗,是最美丽的小诗。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若凡的时候,就注意到他脖子上有一个疤痕,像是月牙的形状。为此我还特意厚着脸皮向他的死党打听了一番,得知是在一次小手术中留下的疤痕。我觉得这个月牙形状的疤痕真是美极了,它就像一只飞倦了的蝴蝶,轻轻地停靠在了他的身上。
于是我在小诗里写道:那一弯小小的月牙,是一只孤单的蝶,承载着我所有的秘密心事,亲吻你。
写完之后,我把这张薄薄的粉红色信纸小心翼翼地折了起来,沿着那一级级的楼梯朝五楼走去,心脏扑通直跳。我托夏薇薇帮我把信转交给若凡,她疑惑地看了看我,欲言又止。
那一整天,我都觉得惴惴不安。若凡迟迟没有给我回复,我很失望,心里猜想,或许是他是没看懂那诗?
次日早上六点半,我准时到教室上早自习,盯着英语书看了好一会儿单词后,同桌拍了拍我,用书本挡住下半边脸,低声说:“今天早上读语文啊……”我这才回过神来,环顾四周,大家果然都在抱着语文书,耳畔也终于传来了之乎者也的声音。
我心里一阵慌乱,连忙把英语课本扔到一边,从课桌里扯出语文书,翻到第一页,大声朗读起来。
“喂,你刚才想什么去了,一直在读那一页单词。”同桌又推了推我。
我说没什么,又假装无比认真地朗读起了文言文。这时我才发现,我刚才读了半天的英语单词,竟一个也没记住。
这时我终于发现,我的脑海我的心,早已被一个人给牢牢占据了。
若凡终究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曾无数次想要开口问他,你是否看过了我为你写的诗?只是我终究没有勇气开口,只得任凭所有的心事,就这样如风般不了了之。
不知怎的,我总是想起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话:“我遇见你,我记得你。这座城市天生就适合恋爱,你天生适合我灵魂。”
三、香樟树的歌
我和若凡曾经的高中,有着大片的香樟树。一进校门,便有两排整齐茂密的香樟树,一共八十棵;教学楼旁也有着几棵高大的香樟树,夏天的时候有着浓密的绿荫,窗外的阳光晒不到教室里来。我曾经无数次在上课的时候盯着窗外的香樟树发呆,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满腹心事却又无从诉说。
高一结束分文理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追求我想象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文科班生活。我本以为若凡会选择理科,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也坚定地选择了文科。我曾经亲眼看见年级主任站在教学楼走廊上语重心长地劝他学理,并且反复问他:“你为什么就那么想学文科呢?!”若凡浅浅地笑了笑,说:“我要考新闻系。”
年级主任大约也是拿他没辙了,无奈地扬了扬手,说:“那你就按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吧。”
如我所料,我们班成了文科重点班,若凡的班成了理科重点班,而他也被分到了我们班。一想到我们就要每天都坐在同一间教室了,我心里百感交集,说不出是喜还是忧。
若凡辞去了文学社的工作,专心做学校广播站和电视台的工作,毕竟他从小就立志要从事新闻行业。我依旧留在文学社,从编辑部部长晋升为主编,每天都与文字打交道。我和若凡的距离终究是越来越远,像两条朝着未知的方向无限延长的平行线。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顶着“特级教师”的头衔,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每次月考过后,要根据班级名次重新调整座位,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依次挑选座位。若凡天资聪颖,即使被广播站和电视台的琐事缠身,成绩依旧拔尖;而我与他的成绩终究差距太大,只能坐在离他远远的地方,在他的身后,默默地看着他的身影发呆。
可是我是多么想坐在他旁边啊。
有一段时间,我迷恋上了仓央嘉措的诗《见与不见》,总是在上课的时候,随手在草稿纸上反复地写着这些凄婉的句子: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 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 不去
……
高二的中途,我毅然辞去了文学社的工作,开始一头扎进学习里,只为了能坐在离若凡更近的位子上。我不再伤春悲秋,不再埋头在草稿纸上写字,而是安安分分地背政史地,与一道道艰深的数学题作斗争。在一个个静谧无声的晚自习里,我埋头奋笔疾书,完成一张又一张的试卷,手心里满是温热的汗。我能听到窗外的香樟树在晚风的吹拂下发出的窸窣作响的声音,像是一首悠扬的歌谣。
我的成绩终于开始稳步上升,到了高三的时候,我终于考到了班上前五名,和若凡的名字紧紧地挨在一起。那一次选座位,我鼓足了勇气,选了他旁边的位子,顺理成章地与他成为了同桌。
“嗨——”坐到他身边去的时候,我这样局促地同他打招呼,心跳得厉害。
四、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夏薇薇对若凡的心意。
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班里举办毕业酒会。我破天荒地喝了一杯啤酒,有些微醺。回到教室,便是茶话会,大家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自己玩自己的。我看见若凡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耳朵里塞着耳机,听着歌,一言不发,神色凄怆。我想要走上前去安慰他,却终究没有勇气。高三一年,虽然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同桌,却终究是交集甚少。
我看见夏薇薇出现在了教室门口,朝若凡招了招手。若凡跟着她,下了楼,朝着教学楼旁的香樟树下走去。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他们在香樟树下说了很久的話。香樟树旁没有路灯,光线黯淡,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只看见若凡缓缓地伸出双臂,拥抱了夏薇薇。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我多么希望这只是我的幻觉。
再后来便是看成绩、填志愿,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若凡发挥得一般,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新闻系,每天都忙着拍片子、写采访稿;而我仍旧做着不切实际的幻梦,想要和他考到同一所大学,于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复读。此时的我们彻底成了陌路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年,我一路南下,考到一所位于南方沿海的城市念大学。我不知道我所在的城市距离若凡所在的城市有多远,我只知道从这里坐火车到那里,要坐整整三十六个小时。
有一天,夏薇薇在QQ上对我说:“你还记得你曾经写给若凡的信吗?”
“嗯?”
“对不起,其实当初,我根本没有把它交到若凡手里。”
“哦。”我强装镇定。
“因为,我与你一样喜欢他。”
“我知道。高中毕业的晚上,我看见他在香樟树下拥抱了你。”
“嗯。那是因为,他对我说,对不起,我已经心有所属了。我抱抱你吧。”
我对着电脑,沉默了许久。
时值盛夏,我所在的城市经历了一场台风。我在台风天里躲在宿舍,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不由地想起那四十九张他或许从未收到过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倘若他收到了我的明信片,故事的结局是否会有所改变;然而这样也很好,我们终将彼此怀念,即便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悲伤地坐在他的身旁。
我又为若凡写了一张明信片:
去不了的地方都是远方
回不去的世界都是家乡
而我却向往比远更远的地方
我在明信片的收件人地址一栏,写下了三个字: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