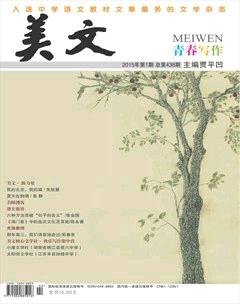那片海,被风吹干了悲伤
胡识

插图:彭建德
以前,每次听到阿妈、阿弟和村里人管我叫鸡架子时,我总会恨得咬牙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多吃饭,多运动,不做狗(不生病的意思),把自己养得胖乎乎。后来有一年,我还真做到了,他们再也没管我叫鸡架子,都认真地喊我的名字,还给我零食吃。就此,我可乐坏了。
可好景并不长,不幸运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我多想吃点饭却没得吃,我多想运动却没得时间,阿妈总把我叫到地里跟她一起劳动。小伙伴们都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愉快地玩耍,他们嘲笑我是个娘儿们,连女孩子做的事我都得做。
阿爸好几年没有回过家,每个晚上,我们仨就并排坐在泡桐树底下,一会儿看看西边,又一会儿瞅瞅南边,我们压根就不知道广东在哪儿。
隔壁的老爷子说,风吹来的方向就是深圳,他老长的鼻子常常能闻到鱼腥味,他还说他在收音机里听过一首歌,叫什么《春天的故事》来着,他只记得有这么半句歌词这样写着,“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老爷子的大娃就在那个南海边捕鱼,他捎信回来时提及过我的阿爸,他说有一次在海边看到过他,他俩还互相给了烟,抽完烟,我的阿爸就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好几万个人头里。可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我的阿爸,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也一定在那座城市。
听老爷子这么一说,我们仨从此以后就将眼睛挪向风吹来的方向。
我们仨以为人生的每一场风都是温暖的,然后我们连饭都顾不上吃,就是拼了命地站在泡桐树下昂起头。结果,一场风的邪却把我给刮倒了。那一年,我罹患上一场大病。阿妈便每天抹着眼泪坐在床头,她说,我今后连做鸡架子的资格恐怕都没有了。可我不信,我举起手招来阿弟,阿弟看看她又看看我。
她是阿弟玩的最要好的小姑娘,他俩常一起跳格子,扭皮筋,每次我想加入他们,她总是气急败坏地说:“鸡架子,你给我走开。”我只好悻悻地跑到屋里打开黑白电视机,虽然那电视机里从没有出现过人,但我还是很喜欢听那”沙沙”作响的声音。我记得小人书里说过,海边有很多沙,如果起风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沙就会落遍整个世界。我猜,电视机里的“沙沙”声应该也来自海边。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找到我们仨想要的那片海。
我的海后来成了阿妈的泪花,也成了阿弟的鼻涕。隔壁村的老中医说我熬不过那个秋天,他把我比成家门口的一棵长满蛀虫的小泡桐树。那年春天,那棵我曾和阿爸一起栽下的泡桐树确实没有开出紫蓝色的喇叭花。我们仨以为它可能要晚点才会开花,于是忘了给它施药。
阿妈跪在地上不停地摇晃老中医的手,老中医实在拗不过,他只好答应阿妈,把我死马当活马医。老中医给我开了一个方,阿妈便负责给我熬药,阿弟负责帮泡桐树捉虫,我则躺在阿妈和阿爸睡过的被子里想象那一片海。
在那片海,我看到有一个男人款款地迎面朝我们仨走来,他手里抱着很多很多颗荔枝,深红的个头,圆滚滚的。他要出去闯荡的那天就答应过我们,回来时会给我们带好多好吃的。只是,还没等我来得及伸出手,他和那些荔枝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只好沿着那片海,又撕心裂肺地喊他的名字,我希望他能够听见。
也就是我想象海的那天,阿妈把我和阿弟带到了村旁的河边,阿妈说,如果有天我也去了海里(死的意思),她就和阿弟一起跳进河里。
阿弟听后就扯着我的衣角说:“哥哥,你说我们在海里还会见面吗?”阿弟把眼前的那条看不到尽头的大河比作海。于是我又想起小人书说的那样,河水河水,你要流到哪里去?我要流到小江里。江水江水,你要流到哪里去?我要流到大海里。
我笑了笑,對阿弟说:“能,一定能!”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再后来,我们都没流进大海里。那个被桐花洗劫的春天,阿爸在河岸找到了我们。结果,我们四个人彼此深情地望了好久。
我和阿弟扯着阿爸的手问:“阿爸,你说,海长什么样呢?”
阿爸说:“等你们长大后就会知道。”
我又回过头问阿妈:“那什么才是长大呢?”
阿妈看了看阿爸又转向看着我,说:“长大,就像我和你的阿爸一样。”
如今,我成了一名中医生,每次再接触到一些带有海字的草药,我的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那片海。说真的,我现在长这么大,还没有看到过海。
阿弟从海边打电话对我说:“哥,我看到海了,可它怎么比我们家的河要小很多啊?”
我听后真感觉奇怪,海怎么会比河小呢?这时,小人书里的一句话又映入眼帘: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望无际的水,它比海要大得多,人们便乘坐着风在那方水里游来游去。
我的病也就是水给治好的,当然里面加了很多味草药,都与这世间的情感有关。所以,当我今天再听到有人管我叫鸡架子时,我也不觉得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