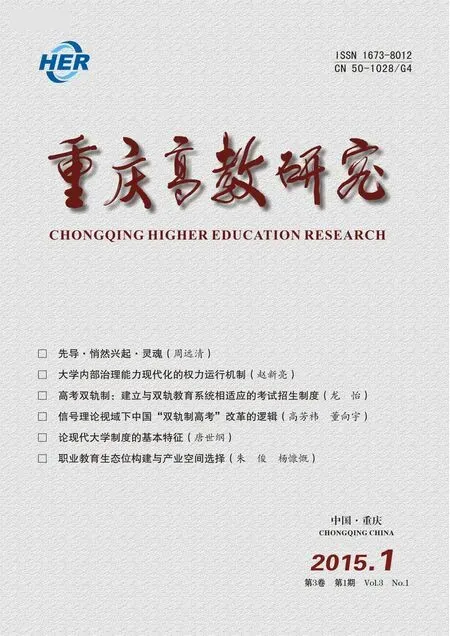信号理论视域下“双轨制高考”改革的逻辑
信号理论视域下“双轨制高考”改革的逻辑
高芳祎,董向宇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200062)
摘要:从信号理论视角论证“双轨制高考”改革的合理性,这种新的评价方式有助于不同类型的人才向适合他们的院校发信号,且类似的招考制度已经被国际经验所认可。改革要想成功,一方面需要建立具备信号甄别能力的科学评价方案,通过评价主体、内容与方式的多元化,将不同类型的人才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依赖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受程度,而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双轨制高考”改革依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面临一定的挑战。
关键词:双轨制高考;高考改革;信号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4-09-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唐世纲(1979-),男,湖南江华人,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和高校课程与教学研究。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5.01.008
一、引言
职业教育当之无愧是2014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聚焦点。自年初以来,政府高层官员在多个场合频频表态,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国务院、教育部等多部委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等相关政策文本。如此大幅度的动作凸显了这场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基础教育素质导向以及社会人才供给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事关全局,必须做好。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人,从人才成长规律的角度出发,影响高素质技能人才养成的因素包括前提性因素和过程性因素。前提指生源质量,过程指培养阶段施加的影响。前者对高素质技能人才养成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后者发挥作用的空间。可以说保证优质生源是提升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起点。它的实现需要依赖两条途径:一是提高下级学校的教育质量,二是改革招生机制以选拔合适的人员。由于选拔机制对于学校教育具有明显的指挥棒效应,那么二者之中又以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在对职业教育的其他环节进行改革的同时,上游的招生改革必须同步跟进。近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开始试水职业教育招生机制改革。2005年,上海市高职院校开始试点单独招生。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明确表示,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1]。新高考模式又被称为“双轨制高考”。有人对之寄予厚望,甚至期待它能“扭转职教困局”,有人则持谨慎保守态度,认为“亟需商榷的难题尚多”。本文尝试运用信号理论,对“双轨制高考”改革的合理性、策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
二、“双轨制高考”改革的合理性:基于理论与域外经验的分析
(一)“双轨制高考”改革合理性的理论分析
信号理论由信息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1974)首先提出。“信号是有关某种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特质的信息”[2]142,如兴趣爱好、工作能力等,它是表达主体某种特点的介质。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广泛存在的背景下,如果想让别人了解自己这方面的信息,就需要发出信号。这种拥有信息的一方为了获得信任而披露自己私人信息的行为叫做发信号(signaling)。相应地,无信息的一方采取行动引起有信息的一方披露私人信息的行为被称为筛选(screening)[3]。在含有选拔、评价性质的实践活动中,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困境,都存在着一个信号发出→信号筛选→形成判断的机制。例如,在就业市场上,雇主无法立刻了解应聘者的能力,文凭就成为一种有效的信号。雇主在筛选人才时会设置一定的门槛,可能是获得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证书,也可能是获得某类职业资格证书。
高考是一个不同于企业招聘,但却具有类似机制的过程。招生方需要了解对他们而言陌生的投考者的能力、兴趣等,以判断投考者是否达到进入大学学习所需的基本条件,从而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考查内容;而投考者为获取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必须向招生方就所需信息发出信号以表达自身具有合乎要求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统一入学考试制度就成为招生方试图引起投考者披露私人信息(发信号)的筛选行为。从信号理论的角度看,高考的实质是招生方依据入学基本条件实施筛选行为,考生根据招生方的筛选任务向其发信号,招生方再依据考生所发信号判断其是否满足自己的要求,最终决定该考生能否入学的过程。
如此一来,就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既然招生方实施筛选行为依据的是人才培养目标以及要达到此目标考生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倘若不同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习所需条件不同,要求考生所发出的信号就应不同,筛选行为也应当有所区别。唯此,高考这一甄选机制方能发挥作用。我国目前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目标显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依据通行的人才分类方式将人才分为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四类的话,则普通本科院校重点培养学术型和工程型人才,职业院校更侧重培育技术型与技能型人才。不同类型人才的基本智能条件有较大差异,且是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例如,学术型和工程型人才通常更擅长数理逻辑思维,技能型和技术型人才的视觉空间智能和身体运动智能表现得更突出。因此,应通过不同的筛选机制来引导投考者发信号,以进行甄别,方为合理。相比之下,现有高考制度使用统一的筛选行为——纸笔测验,按分数高低分等录取,反映的却是入学条件上量的差异而非质的差异,与上述逻辑相悖,自然起不到有效的甄选作用。所以,改变现有的高考制度,为不同类型的学校提供适切的招生通道就是合理且必要的。
(二)“双轨制高考”改革合理性的经验分析
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检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对我们判断“双轨制高考”改革的合理性也有一定价值。
美国的高等院校类型多样,招生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别。少部分知名大学实行竞争性招考政策,申请者需要提供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简称SAT)或具有同等效力的ACT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成绩、高中阶段的学业成绩、个人陈述文章、推荐信函等材料,国际考生还需提供托福成绩。大部分院校实行“最低限度筛选”政策,接纳符合最低入学标准的学生[4]。而社区学院作为承担美国职业教育的重要机构,实行注册招生制度,对所有已完成中等教育有继续学习意愿的人实施开放入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入学者可以单凭个人意愿修读任何课程,有些课程也对申请修习的学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已经完成某些基础课程,或者某门相关课程的成绩达标。但学校通常会提供支持服务,以帮助学生获得修读资格[5]。
在德国,学术轨与职业轨分离得较早,在中学阶段已经完成。文理中学的学生毕业后即获得综合性大学的入学资格,职业专门学校和高级专门中学的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入高等专科学校或者职业学院学习。作为德国高等职业教育主体的高等专科学校实施申请入学制度,学校审核报考者的申请材料后学生即可免试入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高职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个趋势,即越来越多的文理中学生有意愿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针对这部分申请者,高等专科学校要求他们在申请入学前补一个与申请专业相一致的预实习经历[6]。
我国台湾地区于上世纪末开始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多元入学方案改革,最终于2002年废除了已实施半个世纪的大学联考。目前采用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包括主要面向学术型人才的学科能力测试(简称“学测”)和指定科目考试(简称“指考”),凭以上两项成绩可申请进入普通大学。另外还有面向应用型人才的技术职业院校升学考试,名为四技二专统一入学测验(简称“统测”),据此成绩可以申请四年制技术职业院校、两年制专科学校或普通大学,有“技优入学、科技院校繁星计划、甄选入学及联合等级分发等多元入学管道”[7]。实际也是将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分开筛选。
综上所述,“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入学筛选方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并被证实有助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向录取院校发出有效信号。
三、“双轨制高考”改革的策略
论述了“双轨制高考”改革的合理性后,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怎样设计引起信息披露的有效筛选机制,以便将真实信号与无关噪音区分开来。斯宾塞认为,信号可以经过后天努力做出调整,信号调整付出的成本被称为信号成本(signaling cost)。有效的信号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信号的成本对不同类型的人一定不同。具体来说,信号的成本必须与个人能力成反比。高能力的人采纳这一信号的成本很低,因此可以获利,低能力的人采取这一信号的成本很高,得不偿失。第二,高能力的人愿意选择这个信号。如果高能力的人对待这个信号的态度模棱两可,这个信号就失去了有效性[2]143。
据此推理,“双轨制高考”要想有效,首要前提是能够将具备不同能力的人区别开来。学术型人才可以低成本通过针对他们的考核,其中高能力者甚至能够轻松自如地达到筛选条件,进入理想的院校学习;而针对职业类人才的考核则恰恰相反,技术技能型学生可以在考试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顺利地向录取院校发出信号,但其他类型的考生想要通过考核则需付出高昂的成本。现实情况表明,统一入学考试制度的效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大大降低,尤其是不利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筛选。非学术型考生想通过考试向心仪院校发信号需要付出非常高的成本,甚至不得不压抑自己在艺术、体育、动手操作等方面的天赋。在此现实背景下,打破统一考试、走向综合与多元就成为一种应然的趋势。
2008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建立和完善对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作为高考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高校招生考试的录取标准逐步向“多元化评价”过渡,意味着评价主体、评价内容与评价方式都应趋向多元。就评价主体而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从政策层面将高职入学考试的评价权力下放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试行的自主招生、单独招生改革在实践层面将评价主体进一步扩大到院校,应当说高考评价主体单一化的局面在纵向维度上已经被初步打破,有利于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院校实际有针对性地选拔人才。但在横向维度上,目前的评价方案依然由教育主管部门或教育机构主导,作为人才最终流向地的企业却缺少发言权,这容易导致企业与院校的人才甄选标准不一致,通过院校考核的入选者并非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从而降低了入学考试的信效度。因此,给企业适当的参与渠道,让他们能够在早期人才筛选环节发挥能动性,有助于完善评价方案,最大程度地甄别出高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同时激发企业持续关注职业人才培养的动力。
就评价内容而言,关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具体应当考察哪些方面的能力,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理想状态下应当在对本专业岗位群需要的职业素养进行全面的调研后再进行规划。但每个行业都设置一套筛选标准在现实操作中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在评价内容的安排上既要考察一般性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又要适度关照到不同行业的特殊需要。针对这三类内容的考核通常需要通过不同的评价方式。新颁布的《决定》和《规划》皆提出要“重点探索‘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综合评价招生、自主招生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等考试招生办法”。传统的纸笔测验是针对学术型人才的选拔设计出来的,能够反映投考者的基本智能条件,但对于职业能力的考察难免有“纸上谈兵”的局限。与纸笔测验呈互补关系的表现性评价则能通过客观测验之外的行动、作品、表演、展示、操作、写作等更真实的表现来展示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8]。因此,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筛选采用纸笔测验与表现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更加合理。用纸笔测验检测考生的基础知识,同时以表现性评价来反映投考者的动手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符合“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双轨制考试改革的思路。
其次,为了满足有效信号的第二个条件,需要让不同类型的投考者乐于接受专为他们设计的筛选通道。面对分流考试,学术型和工程型人才自然会选择参加普通大学招考,而技能型和技术型人才也愿意根据自身特长参加职业类院校招考。但现实情况是应用型人才的种子不愿选择职业教育,即便承担高昂的成本和失败的风险也一定要进入学术型人才的筛选通道。原因有二:一是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后对应的工作多处于社会结构的下端,无论是硬性的经济收益,还是软性的社会声望都逊于普通本科毕业生。此外,工作的稳定程度、职业发展前景等都不令人满意。以职业声望为例,有学者将国内81种职业分为7个声望等级,排在前几位的职业包括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教育/司法/传媒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等等。而职业院校毕业生则主要从事中低层专业技术工作(如各类技术员、护士等)、农村专业技术工作和产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工作的职业声望排名均在后4位[9]。因此,只有当高职院校毕业生同样能拥有一份收入可观且受人尊敬的工作,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与乐观的职业前景,应用型人才的种子才会主动选择参加“职业轨高考”,“双轨制高考”改革才能最终完成并达到目标。二是职业类工作的弱势地位传导至教育系统,导致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同样“不受待见”。多年来对职业教育拨款远低于对普通本科院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投入;学历歧视在就业市场上广泛存在,高职教育被默认为是统一高考失败者的无奈选择。与普通本科院校拼命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情况类似,迫于现实压力,大批高职院校谋求向本科院校升格,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同质化倾向日趋严重。因此我们不仅要实现教育筛选方式的多元化,还要建立多样性的教育系统,保证拥有大批类型不同但在质量和声誉方面不分轩轾的优质院校。这需要政府提高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让职业院校有能力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与高质量的实训基地。职业院校也需要优化培养方案,提升管理水平,稳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消除过去外界对其“差生集中营”的刻板印象。同时,在普通教育系统和职业教育系统之间建立“立交桥”,保证职业教育系统考生如有意愿可以再次进入普通教育系统,降低选择的机会成本。事实上,提高“双轨制高考”改革有效性的第二个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并非单纯的教育改革能够实现,从中也可窥见高考改革的难度有多大。
四、“双轨制高考”改革面临的挑战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改革过程中面对各种阻力可能出现停滞、反复,甚至有夭折的危险。有学者总结高考改革的经验后认为:“与考试技术相关的改革大多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更加曲折。”[10]“双轨制高考”改革既有技术更新,又有制度变革,更有制度之外社会观念的改变,其复杂程度可以想见。下面就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双轨制高考改革面临的挑战。
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学子,这种对学术型人才的过分推崇对高考改革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障碍。而传统观念的改变需要社会现实的支撑。只有高职院校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真正咸鱼翻身,上升通道明朗,才能吸引人才。而这种职业地位的提升需要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效果通常具有迟滞性。从改革措施出台到效果开始显现之间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能否挺过“黑箱期”对改革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中观层面的职业教育系统,为应对高考改革需要重新制定招生方案,多元化的招生方式将导致招生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高等职业院校在实施综合评价招生、自主招生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等新招考办法的过程中可能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一旦发现问题学校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承受重大的声誉损失。即便是完全公正的招考结果也有可能因为与统一纸笔测验的结果不一致而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需要院校与考生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以及时应对质疑并作出解释。此外,“双轨制高考”实施后,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普通高中学生选择参加职业轨高考,对于中学来说,现行的培养方案有必要进行调整,对这部分学生的培养应与学术类考生有所区别。
微观层面落实到个体,目前在中学阶段,教师和学生均处于应试压力之下,无暇顾及学生个体的兴趣和特长,多数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感到迷茫。因此,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挖掘自我潜质,进入适合他们的发展轨道。在新的招考制度下,学生也需要改变以往“紧盯书本”的学习策略,提升自我的综合能力。
总之,本文仅从信号理论这一个维度来分析“双轨制高考”改革,显然存在局限性,但不失为高考改革研究的一个有益视角。“双轨制高考”改革的帷幕才刚刚拉开,真实的效果令人期待,希望牵涉千万家庭利益的高考能越来越接近她的理想状态——每所院校都招收到合适的学生,每个学生都进入适合自己的院校。
参考文献:
[1]双轨制高考,几家欢喜几家愁[EB/OL].[2014-08-13].http://edu.people.com.cn/n/2014/0401/c1053-24794477.html.
[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曼昆.微观经济学[M]. 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90-492.
[4]王定华.美国大学招生制度与公平性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03(9):44-46.
[5]刘合行.美国职业教育开放性办学的研究与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6):89-93.
[6]沈纯道.德国高等专科学校及其基本走向——“职教高移化”与“高教职业化”的典型范例[J].比较教育研究,1995(5):24-28.
[7]中国台湾“教育部”综合规划司.技职教育现况介绍[EB/OL].[2014-08-13].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4053
0154917/8.%E6%8A%80%E8%81%B7%E6%95%99%E8%82%B2.pdf.
[8]吴维宁.新课程学生学业评价的理论与实践[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72.
[9]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74-102.
[10]刘海峰.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2007(11):19-24.
(责任编辑蔡宗模)
Logic on the Reform of Double-track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GAO Fangyi, DONG Xiangyu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ly proves the rationality of reform of double-track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The new assessment approach is beneficial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alents to ‘signal’ to suitable colleges, which has been testified b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o accomplish the effect of reform,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ppraisal scheme that is equipped with the function of screening, which is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diverse abilities through pluralism of evaluation subject, evaluation content and evaluation mod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form result is dependent on the social acceptance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lthough it is a complex social project. Finally, it is a fact that the reform of double-track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still facing with challenges at macro-, meso-and micro-level.
Key words:double-track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logic
引用格式:唐世纲.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J].重庆高教研究,2015(1):36-40.
Citation format:TANG Shigang.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5(1):36-40.
■ 教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