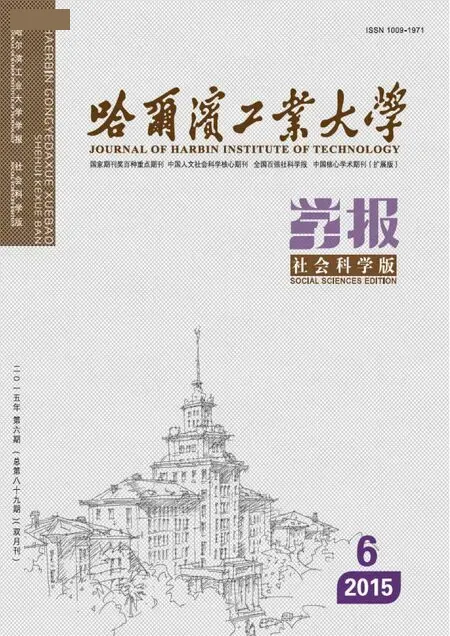重大事件电视直播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陈致烽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文法学院,福州350300)
人类社会已经历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早期的氏族和部落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同一个氏族或部落生活的地域相对狭小。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社会成员之间不仅受到血缘关系的制约,而且受到地缘关系的制约。同时,随着人们生活地域的扩大,如何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跨度大,生活习俗、文化、血缘、语言等都有较大的差异。海峡对岸的台湾同胞,由于长时间的分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两岸人民的认同度存在减弱的趋势,还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华民族儿女,如何维系他们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进而对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母国产生认同,这都是当下我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传播的时代,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古老部族和亲族体系来说是基础的那种人类社群感,已让位给人类传播和相互作用的日益人为和具有社会性的手段”,大众媒体“在整个社会内维持了某种社群和亲族感”[1]。本文讨论的就是如何利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对重大事件的直播来加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促进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一、电视媒体与拟态环境
1922年,美国著名大众传播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观点。他认为,大众传播建构的其实是一种虚拟环境,这一虚拟环境有别于人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但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见解。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普通大众由于自身的实际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对整个外部世界和众多事物保持直接的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受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了解,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变化着的客观环境的反应,而成为对大众传播媒介建构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因此,在公众观点的形成上,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担负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
李普曼所论及的“大众传播媒介”,当时主要指的是报纸媒介。他的观点是否适合后来兴起的电视媒介呢?电视诞生之初,大都是采用直播的方式,后来随着储存技术的发展,录播的方式渐渐成为主流。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通讯卫星的广泛使用,电视直播车已成为各个电视台的基本配置,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可以快速地通过卫星向全球进行直播,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视了解到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从大型的体育赛事、国际国内会议到各种突发性的事件,电视直播为人们提供了实时了解重大事件的重要窗口,也最大可能地向人们提供了新闻现场的真实信息。直播完美地实现了电视的含义,即“远程实时观看”。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说过:“现场直播把观众带进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一事件只有明天才能搬上银幕,后天才能成为文学、戏剧和绘画的主题。”[2]电视现场直播营造出“天涯共此时”的景象,让围坐在电视荧屏前的观众有浓浓的现场感,仿佛自己就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仿佛自己就是各种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那么,在电视直播日益常态化的传播语境中,李普曼所言的“拟态环境”是否已经淡化、甚至消解?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信息环境是否等同于真实的客观环境呢?无论是各种事件的新闻报道还是各种活动的现场直播,呈现真实的环境和传递真实的信息都是电视媒体的首要功能和应尽义务,然而,任何媒体传递的信息其实都经过一定的选择和加工,电视媒体所呈现和营造的世界仍逃脱不出李普曼所言的那种“拟态环境”。继李普曼之后,20世纪80年代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又提出“拟像”之说,他更激进地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由符号和编码支配的模拟时代,电视媒体是主要拟像机器之一,电视不再是再现现实世界,而是建构一个让人信以为真的媒体世界。
对于波德里亚的观点,人们可能并不完全认同。然而,电视直播在给观众带来很强的现场感的同时,其营造的世界仍然是与真实的客观环境有着一定落差的“拟态环境”,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通过对画面、声音和文字的组合运用,电视在二维的平面上展现立体的三维空间,这个空间必然包含一定的虚拟性,电视传播者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重新组织事实,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并非就是完全的客观事实,如李普曼在谈到新闻媒介机构时指出:“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不可能凭着一个一个插曲、一个一个事件、一个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去治理社会。”[3]259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的人的因素,从现场的摄像人员、导播到后期的编导、总编都在对直播进行层层把关,同一个现场直播,在欧美的观众看到的和在中国看到的、在非洲看到的,也许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直播,国内大部分看到的是央视版的直播,中国主场、中华元素让中国人感觉亲近,而同时直播的美国NBC版,面向西方观众,他们对开幕式的报道则是好奇地、旁窥式地引领西方观众观看,缺少一些情景交融的心理体会。
由此可见,电视直播的事件并非完全等同于现场发生的事件,坐在电视前围观的观众所看到的或多或少是经过电视媒体过滤的内容,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很鲜明的文化特性,各国的传媒机构会从自己的视角去直播重大的事件,电视直播在传递资讯的同时传播着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对内加强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对外则能扩大其他民族的认知。美国民族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运作的空间,首先是安德森所提到的小说和报纸等大众媒介为“民族的想象”提供了一个平台,接着是电视等电子媒介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电视媒体对重大事件从来都不会缺席,电视直播把身处世界不同地点的民族成员带到了“现场”,一同见证他们所关注的事件的进展,在他们的心中确立了共同存在、共同经历的同族人,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言:“媒体的故事和图像提供了象征、神话和资源等,它们参与形成某种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4]电视媒体的真实性与拟态性具有一种辩证关系,我们既不能因其拟态性而放弃对真实性的追求,也不可因其真实性而无视拟态性的存在。我们只能遵守、不能改变电视直播的重大事件的真实性,却可以利用拟态性为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服务。在这一方面,确如李普曼所言,大众传播担负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
二、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对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其实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由一种特定的文化所建构的。他对民族的定义是:“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5]
塔尔德在《传播与社会影响》一书也提到,在最低等的社会中,组合首先是物种的组合,沿着生命之树往上走,社会关系的精神性质越来越明显。但是,社会成员的分离超过了一定的时间,他们就不再是一个组合。谈到连接分散在各地的成员的纽带,他认为,纽带关系“存在于他们同步的信念和激情之中,存在于同时与许多人共享一个思想或愿望之中。即使不可见别人,只要了解到这样的共同之处,一个人就可以受到公众的影响”[6]。
这些学者都论述了共同的意象和共同的纽带对于建构、连接和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成员往往分居各地,流动性增大,覆盖全球的大众媒介就成为维系各个成员之间关系、保持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安德森尤其认识到并论证了大众媒介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小说、报纸、收音机和电视这些大众媒介能传播将民族成员相互联结的共同意象和共同想象,尽管这些民族成员散布在不同地区,相互之间从未谋面,素不相识,而共同的想象和共同的意象像一根纽带,将他们形成一个共同体。
如今,电视的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尤其是现场直播已成为常态,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观众可以通过电视实时地关注到,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已然实现[7]。电视媒体特有的现场感,把分处各地的民族成员聚拢在一起,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发生之际,散居在各地的民族成员围坐在电视机前,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形成一种“围观”与“想象”的氛围和效果,围观是对事件的关注,而想象是其他民族成员的关注,这种围观与想象有利于凝聚一个民族共同体。
我国中央电视台每年的除夕春节晚会,就在围观与想象的层次上起到了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作用。从1983年创办,春节晚会至今已持续30多个年头,它已经超越了一场晚会的范畴,已然成为一种民族仪式、一种民族认同符号,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春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除夕夜的北京时间晚八点整,世界各地的中华民族成员期盼着热烈的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开始,相伴四个小时,期待着新年零点时刻的到来,张张笑脸伴随着钟声、欢呼声,我们一起走进了新的一年,此时此刻,在围观与想象中,相隔千里万里、可能互不相识的我们却深深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因此,戴维·莫利认为,把看电视理解为是一种仪式,其功能是构建家庭生活,并且提供参与到民族共同体中的符号模式以及消费和生产的行动模式中去。电视作为一种仪式,具有提供参与到民族共同体中的符号模式的功能,在构建“民族家庭”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戴扬和卡茨在评价媒介事件的效果时曾提出,媒介庆典(一种显在的媒介仪式)能促进社会的“机械的团结”[9]。电视对重大事件的直播,是一种重大的媒介事件。电视传播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声情并茂,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随着事件直播的深入,观众会不知不觉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引发自身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想象,促进一个民族成员之间的团结。
1997年7月1日零时前后,中英两国将进行香港主权的交接仪式,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也是举世瞩目的重要时刻,这一刻也是中央电视台72小时持续直播过程的焦点,前期的直播都是在铺垫,受尽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儿女都在翘首以待,期待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交接仪式开始,代表英国移交主权的是查尔斯王子,导播不时地给予特写,镜头里的他失落、伤感之情溢于言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领导人的自信、满怀喜悦之情。一种自豪的情感在所有的中华儿女的心中激荡,十多亿的中华民族成员虽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但电视把他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让他们穿越了荧屏,心中都同时涌起了关于你我他的民族想象,产生了同属一家人的共同联想。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央电视台临时中断预定播出的节目,连续十余天不间断多频道直播报道汶川的地震救灾现场情况,这也是新中国电视史上连续直播时间最长、内容最全面、影响面最广的一次直播。如果说在地震刚刚发生的一周,电视着重报道的是实时的灾情和救灾的情况,我们称之为突发性事件直播,那么对哀悼日的直播就是精心设置的,电视媒介强大的积极引导、凝聚共识、建构民族共同体的功能就凸显出来。2008年5月19日14点28分,国家用全国范围国旗下半旗的形式,对四川汶川重大地震灾害中伤亡的同胞们进行了哀悼。哀悼仪式因为有电视的介入传播而广为关注。在这三分钟里,电视逐次呈现中华各地的哀悼现场,让各地的人们想象自己也处在哀悼的现场,处在同一个氛围中。电视直播不仅让人们围观,而且让人们联想,电视聚拢了各地中华儿女,消解了民族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面对巨大的灾难,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李普曼说过:“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3]10三分钟哀悼结束,镜头回到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的群众,手里拿着国旗和标语齐声高呼着“中国万岁”、“汉川加油”,特写画面表现悲伤中充满着坚毅的张张面孔,电视直播融汇了各地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中国”等这些带有凝聚力的认同性话语被反复传播,庄严的归属感在参与现场集会的成员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之间不断地融通强化,逐步在每个成员的内心积淀,形成共同体的意象与意识,此时,“用最庄严的举哀,凝聚民族的力量”的评论员评论更是激发了所有中华民族成员内心升华出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自豪感。
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重要的是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也就是安德森所说的“意象”、塔尔德所说的“共享思想”,而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有利于广泛传播这种民族认同。上文论及的春晚、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和汶川大地震即因传播了民族的认同而受到广泛的关注,也因受到广泛的关注而普及了民族的认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目前还存在海峡两岸分治和港澳“一国两制”的特定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增强民族认同,如何建构民族共同体,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而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首先,电视可以通过在传播的内容中引进民族元素,让人们在观看时与民族元素相认同,从而增强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这是一种自我认同。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之说提醒大众传播者注意自身的责任,一方面应避免“歪曲环境”,另一方面可引导观众。事实上,传播者采取的传播导向和传播策略必然影响到观众的感知和认识。例如上一节论及的汶川大地震的哀悼仪式,三分钟的画面所呈现的各地哀悼现场建立起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的形象,假如这三分钟的哀悼画面只停留在汶川当地的现场,就不会产生同样的传播效果,同时,评论员的评论突出的也是“凝聚民族的力量”,假如将“民族的力量”换成“国家的力量”,也可能减弱全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由此可见,电视传播采取适当的策略,就可以对民族认同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方面,电视对重大事件的直播尤其能获得积极的效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现场直播就有意识地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元素,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借助这一国际体育盛会,通过卫星直播,不仅是中国观众,而且是全世界观众都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一个具有传统文化,同时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神奇的方块字、激扬的击鼓声、古老的活字印刷、神秘的八卦阵等,张艺谋导演借此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充满活力的现况,让全球华人感到亲切又充满期望,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油然而生。这种以民族符号为载体的电视传播方式更能培育全民族的认同感。民族认同感有利于对国家的认同,如贺金瑞和燕继荣所言:“民族认同一方面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受国家认同的认可和保护,公民国家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国家认同。”[10]
其次,电视在培育一个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让其他民族接受的问题,这涉及他者认同。我们已处在一个全球传播的时代。全球传播是一个开放的传播,每时每刻通过通讯卫星的转播,全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可以收看到成百上千个电视频道,我国中央电视台已覆盖了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传媒的触角也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中国的形象随处可见,中国的声音也响彻全球,每一次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的受众可能都是全球性的,所以,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在传播策略的运用上,需要全面考虑,既要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也应避免伤害其他民族的情感。2006年第18届世界杯足球赛八分之一决赛有一场是意大利队对澳大利亚队,央视体育频道进行了现场直播,由当时著名体育评论员黄健翔担任解说,比赛达到最后关头,意大利队凭借一个点球战胜了澳大利亚队,这时黄健翔忘记了自己央视评论员的身份,他带有个人情绪的解说明显伤害了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情感,引
三、电视直播与民族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
发澳大利亚人的不满,也招致众多球迷的不满,黄健翔在公开道歉后不得不引咎辞职。尽管此举只是黄健翔一时的个人行为,也不涉及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但是央视体育频道代表的是国家和国家形象,这一案例应让人们引以为戒。
每一次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都为传播民族认同、加强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也为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11]。近年来我国政府从国家层面有计划地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如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制作国家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积极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不少学者也从理论层面开展国家形象传播的研究。我们认为,借助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以民族元素、民族符号为载体的传播方式,显得更加软性,更有亲和力。首先重大事件必然会引来国内外众多人群的关注,其次民族元素和民族符号的渗透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应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的同时,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他者认同问题,这既有丰富的理论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民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共同体,通常也是一种心理概念。电视在对重大事件直播时,采取适当的策略就能有利于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对自身的民族共同体产生想象,进而形成凝聚力和实现自我认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华民族,其成员广居世界各地,作为主要聚居地的大陆地区,通过大众媒介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民族的形象,传送富有中华民族元素的影像符号,以此可以维系和促进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同时,采用世界的视角,让其他民族也能接受和理解中华民族,实现他者的认同,这对于中国形象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这方面,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能起到独特的作用。
[1][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M].周传基,周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10.
[2]任金洲,程鹤麟,张绍刚.电视策划新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56.
[3][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
[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
[6][法]塔尔德,[美]克拉克.传播与社会影响[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4.
[7][美]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51-384.
[8][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37.
[9][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30.
[10]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12.
[11]天静.想象的共同体:电视、体育与民族身份认同[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