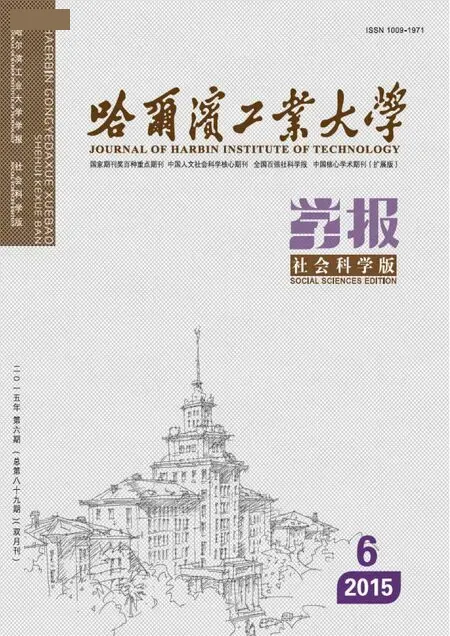殖民的伤痕:战后沦陷区作家的生存环境及其创作、生存策略
陈 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北京100191)
一、日本战败后来自沦陷区作家的历史境况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惩治汉奸条例》五条(1937年8月23日)、《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理罪法》(1937年9月4日)、《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4月)、《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8月15日),只是由于国民党在沦陷区的政权已经被架空,这些条例法则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抗战胜利之后,重庆的《新华日报》陆续公布《南京伪组织汉奸名录》《上海文化汉奸名录》《北平文化汉奸名录》《新闻界汉奸名录》《汉奸群丑脸谱》等等,多次发表严惩卖国汉奸的社论,揭露汉奸卖国罪行,公布通敌罪状,号召人民起来揭发、检举汉奸。作为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如何制裁汉奸直接关系到国民党政府的威信与政权的赓续这样的大问题。共产党政权在惩处汉奸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很积极,其原因在于:一是借铲除日伪残余势力打击政敌;一是通过动员群众而获得他们的支持,扩大统治基础。对汉奸的处理成了两党争夺政权的一项资本。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有效地惩奸,结果不但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资本,而且使民众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遗政敌以口实。曾有台湾法律界人士将国民党败走大陆归因于政府未能秉持公正原则处理汉奸问题[1]。美国学者胡素珊也指出,国民党在对日占区接受过程中惩奸不利和对一般民众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战后普通城市民众反叛国民党的第一个转折点[2]。事实上两党对“汉奸”都缺乏明确的定义,对其解释都有扩大化倾向。比如国民党政府接收沦陷区所在的大学,并对大学和中学的师生进行“甄审”,对“伪教授”不予续聘,责令“伪学生”进入政府设立的“学习班”学习一年,“清洗思想污点”后方可拿到毕业证书;生活在沦陷区的老百姓被视为“伪民”,那么沦陷区作家自然就成了“汉奸文人”。共产党政府在《新华日报》上公布的文化汉奸名单,就把陈大悲、包天笑、徐卓呆、平襟亚、袁殊、鲁风、王则等人员也列了进去。这些文人虽然生活在沦陷区,但基本与日伪政权保持疏离态度,他们也没有创作过所谓的“汉奸文学”,如袁殊、鲁风等还是奉命打入日伪政权内从事抗战工作的。此外,共产党的“汉奸”名单中还包括一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地主、恶霸等,包罗甚广。
来自不同区域的作家都对日本战败后新的历史丕变充满期待和向往,但沦陷区作家同时还承受着无法摆脱的恐惧和忧虑。连日本作家都对沦陷区作家、特别是那些与日本人往来密切的作家的命运有了预感。堀田善卫后来回忆说:“战败时我正在上海。当我在印刷所听到天皇的投降诏书时,马上想到柳雨生、陶亢德等参加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文人们的命运。他们究竟会怎样呢?他们是早有预感呢,还是意想不到呢,也许有所准备吧。不只他们二人,我们相识的所有中国人,必得走上我们所意想不到的难行之路。”[3]553“中国的正统文学史,恐怕要给他们打上向敌人出卖灵魂的叛徒文人的印记吧,或许由于战时倥偬,他们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根本无视他们的存在吧。”[3]554如果说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家对未来政权的更迭尚有表达自己思想脉动的权力的话,沦陷区作家的表达空间则狭小逼仄。他们预料到自己将受到审判,于是纷纷自谋出路。有些文人先后迁移至海外,如柳雨生、梁盛志、纪弦、胡兰成、张爱玲等,他们或者在大学任教,或者选择继续做职业作家,成为仍然有影响力的学者、诗人和作家。留在大陆沦陷区的作家不久即被卷入政治运动,他们几乎无一逃脱被现任政权怀疑和整肃的命运,于是纷纷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
二、沦陷区作家的自我保护策略
沦陷区作家对自己最直接的保护,就是隐姓埋名。周作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约稿单位要求用“启明”、“周启明”等;袁犀被要求放弃使用该名字,后来袁犀以“李克异”作为笔名;其余的还有古丁(后改名徐汲平)、山丁(后改名邓立)、田兵(后改名金汤)、柳雨生(后改名柳存仁)、文载道(后改名金性尧)、路易士(后改名纪弦)、金音(后改名马寻)、田瑯(后改名白拓方)、成弦(后改名成骏)、疑迟(后改名刘迟)、杜白雨(后改名李民)、梅娘(后改名孙敏子、孙加瑞)、丁谛(后改为吴调公)等等,不一一列举。主动改名者,试图抹掉过去的历史,以新的名字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如战后逃往台湾的路易士,以“纪弦”示人。被动改名者,是因为被视为“汉奸文人”的他们的文章确实写得好、受欢迎,日本战败后,其作品依然有读者,采用他们稿件的编辑部或杂志社以劝其更改姓名作为采用稿件的前提条件。苏青就因为拒绝改名而与约请她文稿的编辑产生龃龉。张资平对他投稿的报纸提出直接署“张资平”这个名字的要求,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曾经给他带来荣耀的名字,也想以此试探一下读书市场对他的接纳程度。结果表明,他的作品依然有市场,但报社依然不断收到读者的投诉信件,要求报社拒绝刊登汉奸的文章。一位名为沈立行的编辑对张资平说:“阁下的大名臭了,不能再用了,但是你的文章,还是有读者的。”[4]后来张资平化名“秉声”,仍然因其显著的创作风格而被认出来,报社的编辑担忧给报社招惹是非,不再刊用张资平的稿件。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他们的署名权有时是被任意剥夺的。著名作家、翻译家文洁若在回忆钱稻孙时说:“不同于周作人的是,以上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发表钱稻孙的译作时,从未要求他改用笔名。然而1962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是钱稻孙翻译的,书中却根本没署上译者的名字。仅由欧阳予倩在《叙言》中交代了一句:‘我就请人代为翻译’。拿到赠书后,钱稻孙托我给楼适夷社长带去一本,他苦笑着对我说:‘谁叫我犯有前科呢!’”[5]
其次,沦陷区作家积极拥抱新政权,以寻求政治安全感。如袁犀一心追随共产党,却始终被排斥在新政权行列之外。他多次要求入党,1949年1月30日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他因此说:“这是我获得新生的一天”[6]40。1952年,因他的“历史问题不清”停止他的候补期,他说,“感受如被宣判死刑”[6]42。他兢兢业业于党分配的每个工作岗位,但在生前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被内定为“控制使用”的人。在日伪统治时期,袁犀几乎不说日语,战后从事日本文学翻译,被暗示自己是“汉奸作家”[6]44,他执着于文学创作,在创作中表达对新政权及其带来的新生活的热爱,这样的作品被看成是射向党和人民的“毒箭”。日本战败后,山丁说,入党就入共产党。他不仅自己多次申请入党,而且要求子女要入共产党[7]。在谈到自己沦陷时期的作品《绿色的谷》时,他说:“我愿继续写出《绿色的谷》续篇《灰色的城》《红色的草原》,把站起来的中国农民性格、形象写出来,用我的笔报答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关怀。”[8]沈启无在文革期间交代说:“是毛主席共产党拯救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罪恶,对自己这些罪恶的历史,我是认罪的,这笔账也是应该算清的,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处理。”[9]72“解放后我的生活是安定的,不像在过去旧社会那样,常为生活失业而恐慌忧虑,又看到祖国日益强大,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自己也愿把晚年精力毫无保留地为党工作。”[9]751949年底,苏青在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社会活动家、作家吴藻溪(1904—1979年)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周作人也曾热情拥抱新政权。他将新旧政权做了对比,感慨道:
民国以前,消防都是民办的,各水龙会并无统一的指挥,通信机关也不完备,可是有了火警,铜锣一敲,水龙毕集,会员如不亲去,只须交纳工资一角,成绩也相当不错。后来社会事业悉由公家办理,水龙会自然消灭,改为消防队了,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与民众利害关系最是密切的机构也一样的腐化堕落,失火人家的四邻如不先讲条子,不但难受保护,还不免要被毁坏,这足以证明蒋朝政治之腐败,远在满清时代之上了。
现今各级政府致力于为人民服务,民间生活日益安全幸福了,从前办善举的精神和力量,正可以复活过来,转向正当方向,自动地出钱出力,做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我想这正是极可能也应当的吧。[10]
被新政权承认,是他们的全部慰藉,多次申请入党却通不过,直接原因就是其出身背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继续追随新政权。他们明白,惟其如此,才能摆脱内心的恐惧。当然,对新政权的拥护并非纯粹为了自保,国民党政权的贪腐混乱让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共产党政权上。
再次,创作适应社会需要的作品以及歌颂抗日战争的作品。沦陷区作家几乎放弃了个性色彩,他们试图通过贴近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和政权,来确立自己的政治身份乃至生命价值。以苏青为例。解放初期,政府欲对戏曲进行改革,需要有一批自己的戏曲管理干部与编导,以备不时之需。苏青参加越剧《兰娘》的创作小组,该剧内容讲述的是一个古代女子大义灭亲惩治内奸的故事,是为了配合“镇反”运动。据悉,苏青“一向不看地方戏”,也不懂,她觉得组织上能让她进学习班,并没有因为她的过去而嫌弃她,她隐约看到自己在新社会的前途,产生了要为戏曲改革做出努力的愿望。①有关苏青的战后转变,笔者参考了王一心著的《苏青传》第250-25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袁犀的写作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部分地放弃小说创作,选取自己难以驾驭的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电影剧本和豫剧等,以自觉地融入为政治服务的话语秩序中。其夫人姚锦这样描述道:“他不断地熟习掌握,交相采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愿它能为党、为人民所需要。”[11]
最后,修改沦陷时期的作品,以表明自己当时的抗日意志。1980年代以来,山丁在“满洲国”文坛和北京文坛都很活跃,他是“满洲国”“文丛派”的健将,是“乡土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满洲国”“文艺家协会”的委员。到了北京后,他主编过《中国文学》、《民众报》的“副刊”“文学十日”、“创作连丛”及“中华周报”,曾出席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官方场合,他也说过迎合时局的话。《绿色的谷》是山丁的代表作,当时连载于《大同报》1942年5月1日至1942年年底,1987年5月,《绿色的谷》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再版时,作者做了一些改动,如将主人公林彪的名字改为小彪,将“满洲事变”改为“九·一八事变”,将“满洲的乡村”改为“所有的乡村”,将“满洲的发达史”改为“张作霖的发达史”,等等。“满洲”是日本殖民的产物,使用“满洲”并不表明作者就承认满洲国;在战后保持作品的原貌可以让后人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1980年代以来,梅娘对其沦陷时期的原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却忘记了,其作品中的空隙和省略所表现出来的张力,本文不再赘述。
三、结 语
日本战败后的时代和社会对于沦陷区作家而言是陌生的和疏远的,他们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不安境地:由于主体认同无法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实现,他们感到一种主体感坍塌的焦虑和疑惑。他们自觉地检查和监督自己,努力地斩断与既有的表达习惯的联系,把听命于政治书写看成是必由的救赎之路,以此确认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安全感。他们的政治热情与民族情感有关:一方面,强调民族主义和共同的抗战历史,努力补救被疑似为“汉奸作家”的身份;然而同时由于民族情感过于强烈,不仅损伤了文学创作在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弱化了文学创作书写历史的价值。特殊的政治氛围造成了知识人的集体迷失。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留在大陆的沦陷区作家,个别人除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外,还受到咒骂、流言蜚语和白眼等最常用的公众制裁形式。为了作政治性的自我表白,他们用艰苦的劳动(如按政府的要求从事翻译、写作等活动、或是劳动管制等等)来“赎罪”,主动坦白、检讨,甚至发动家人来帮助自新。在文学活动中,他们则通过改姓名、贴近执政政权、创作歌颂抗日的作品、修改沦陷时期的作品来进行自我保护。这种种自虐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他们所期待的政治效果,都是值得怀疑的,但对他们来说又必不可少,是他们抵抗公众制裁和维持自我想象的手段。吊诡的是,文革结束后,新时期以来,活着的沦陷区作家一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自虐式行为,很少有坦然地面对那段历史的。他们开始辩诬和言不由衷地对外言说。即使对自己附逆行为表示忏悔的,也都很隐晦,并且大多发生在私人场合。这说明,出于对政权的恐惧而“坦白”更多地出于保全性命的考虑,它并不触及灵魂的伤痛,因此无法达到自我否定的效果。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殖民留下的伤痕。
[1]李模.奇缘此生[M].台北:商周文化出版社,1993:127-129.
[2][美]胡素珊.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G]//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启蒙编译所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9.
[3]樱庭弓子.苏青导论[G]//东洋文论.吴俊,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沈立行.“三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的结局[J].海上文坛,1997,(11):125.
[5]文洁若.我所知道的钱稻孙[G]//翻译新论集.刘靖之主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79.
[6]李士非.李克异研究资料[G].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7]金河.关东老橡树——梁山丁纪事[G]//梁山丁研究资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35.
[8]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重版琐记[G]//梁山丁研究资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205.
[9]黄开发,沈启无.沈启无自述[J].新文学史料,2006,(1).
[10]周作人.水龙会[N].亦报,1951-02-10.
[11]姚锦.晚晴集·后记.晚晴集——李克异作品选[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