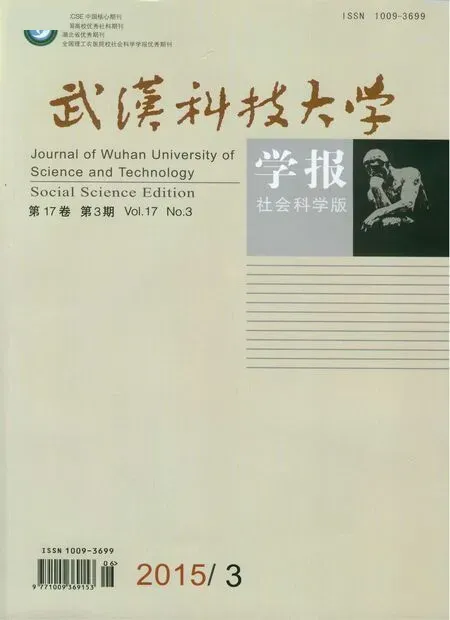奥斯维辛之后艺术的困境
陈 旭 东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奥斯维辛之后艺术的困境
陈 旭 东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主要是提醒我们,艺术表现自身的暴力难以避免,我们需要承认其不可能充分表现罪恶与苦难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始终面临这种两难境地:奥斯维辛之后生者有写诗的责任,但又难以摆脱写诗的野蛮性,艺术只能以分裂和矛盾的形式来表达罪恶与苦难。
阿多诺;奥斯维辛;艺术;文明与野蛮;罪恶;苦难;困境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据说这是针对保罗·策兰的著名诗歌《死亡赋格》(Todesfuge)而说的,面对这样的责难,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对阿多诺的回应非常到位:“我觉得他可能是位犹太人。”可见,作为诗人的策兰同样理解并同意阿多诺对写诗的指控。二战后60多年来德国对奥斯维辛的反思经历了许多反复与曲折,不仅许多血债累累的纳粹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纳粹主义也一直在社会中有复兴迹象,虽然出现了不少可圈可点的反思行为,但整个世界包括德国都远未达到彻底的水平。无论是通过沉默或遗忘来尽快地甩掉历史包袱,还是用解放纪念日或商品化等手段好好利用这个包袱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过去,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来理解,奥斯维辛的悲剧仍然会重演。要理解为什么写诗是野蛮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阿多诺提出的文明与野蛮的辩证关系。
一、文明与野蛮的辩证关系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没有步入真正的人性状况,反而倒退为野蛮?启蒙关于人类进步的话语无法解释启蒙之后人类向野蛮倒退的现象。虽然流亡美国的阿多诺在写作《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时未必知道奥斯维辛的详情,但他已经意识到一场空前野蛮的灾难逼近了:“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1]25我们都会惊诧德国这样一个产生过康德、贝多芬、歌德的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却可以如此野蛮,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尖锐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个人可能在晚上阅读歌德或里尔克,弹奏巴赫与舒伯特,然后早上继续到奥斯维辛工作。”[2]ix
阿多诺敏锐地指出,奥斯维辛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恶魔或一个文明的例外,而是从文明内部自然产生的野蛮,因为人类支配自然的方式与大屠杀对待异类的方式并无多少质的差异。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阿多诺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反文明趋势,文明内部包含着黑暗空洞的一面,文明一开始就包含有倒退的萌芽,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野蛮同时不断强化。我们早就想摆脱野蛮,结果在野蛮中越陷越深,自我毁灭的趋势没有逆转过,只是有时极端有时隐蔽罢了。
针对这一文明与野蛮的空前交织状态,阿多诺痛斥说,在这个非人的世界里,所有文化都是垃圾,包括对其的批评,都是野蛮主义的一部分。道德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失败了,因为它不能提供对极权主义任何有效的抵抗。不仅文化与道德没有提供对纳粹主义的有效抵抗,而且提供了催生纳粹的土壤。文明的面具可以被轻易撕破,一个文明人可以在体制安排下转变为一个杀人的工具,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文化,整个社会充满着善的扭曲,我们无法确知什么是绝对的善与好,无法从现实世界中认识善与好,包括我们的概念框架都与之同谋,甚至想象力也被极度破坏,不能获得正确的观念[3]352。可惜的是,哲人直面痛苦的呐喊总是很容易被乐观的喧哗所淹没,在意识形态的盛行与思想能力缺乏的现实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过于轻松的解脱,在文化工业的熏陶下我们乐于当下的舒适而回避任何过去的痛苦,我们被劝导积极向上而不是消极悲观。所以,每年全世界各种组织与机构都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庆祝奥斯维辛解放纪念日的活动,这样纳粹屠杀就被转化为同盟国所代表的善最终战胜法西斯之恶的巨大成果。我们不禁要问,被救出的仅仅是几百万中的7000人,这几百万的死者如何解放?即使对幸存下来的那批人来说,他们的身心创伤就能在胜利的欢呼中愈合吗?这些个体的命运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历史前进的步伐所埋葬吗?
正是“文明与野蛮之辩证的最后阶段”这个社会的总体状况使得写诗成为野蛮。在阿多诺看来,这个绝对异化的社会是理性化的手段与非理性目的的奇怪混合。甚至原本应该有一定独立性的艺术与文化都被统一,无法从这种异化状态中完全分离出来,思想与文化都被吸收进总体受管制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一座“露天监狱”。我们找不到一个外在于这种总体异化状态的立足点,没有清白与安全的领域,艺术属于产生了大屠杀的文明机制的一部分,它与野蛮具有某种共谋关系。
对此,阿多诺异常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的总体性程度越高,物化意识就越严重,而试图通过自身来逃离物化的尝试就越显得矛盾。即使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可能会堕落为闲聊。文化批评发现自身面对着文明与野蛮最后阶段的辩证关系。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腐蚀了当今为什么不能写诗的理解。”[4]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诗人还能写诗来称赞这个世界的美好,那将是一种不诚实,当然是野蛮的。“奥斯维辛之后所有的文化,包括对奥斯维辛急切的批判,都是垃圾”[3]367。不过阿多诺始终站在辩证的立场上看问题,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文明,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一文中他指出,对文明的辩证批判必须同时参与和拒绝这种文明。因为文明既代表着自由的可能与希望,又是现存社会控制关系的体现。
写诗当然是广义上的,它可以包括一切艺术实践,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所代表的文化工业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其导演斯皮尔伯格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家,但仍然难逃野蛮的嫌疑。作为上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的奥斯卡大片,《辛德勒的名单》曾经使纳粹大屠杀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它似乎以积极正面的形式描述了这场灾难,而且要告诉我们在纳粹屠杀的残酷中仍有着人性的闪光。片中主角辛德勒起初只是一个发战争财的投机商,后来却变成倾家荡产来拯救犹太人的义士,这种带着缺点的英雄似乎比较可信与动人。作为反面人物,残酷、冷血、暴力、血腥的德国军官高夫也保留着一丝人性,不完全是杀人魔王,但仔细看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该片依旧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产物。其中有一个体现整部电影风格的场面:一群妇女被错误地送往奥斯维辛,赤身裸体地被赶进一间浴室。灯突然灭了,响起了惊恐的尖叫声,她们盯着头顶上的莲蓬头等待着毒气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清水代替了毒气倾泻而下,妇女们捧喝着清水,哭中带笑。撇开对毒气室描写的历史真实性不论,清水取代毒气暗含着把纳粹屠杀戏剧化,以起到娱乐效果,这是好莱坞大片一贯风格。影片似乎用黑白的写实风格再现了集中营的恐怖,但大屠杀的恐怖只是作为背景来衬托英雄的拯救,依旧是英雄与坏蛋对手戏的套路,正义与邪恶还是那么分明。
这正是阿多诺批评的典型的文化工业,其典型特征就是每一个镜头都蕴含着效果的计算(calculating of effect)以便掌控观众的反应。再比如结尾时,辛德勒指着手上的戒指后悔地说:“我可以用戒指再多救一个人。”这体现了《塔木德智慧全书:像犹太人一样处世和经商》“救赎一人,即救赎全世界”的崇高意义,让观众感动不已。这种苦情戏的常见套路使我们爽快地释放了黑暗面前的压抑,只剩下了感动。如同凯尔泰斯曾指出的,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画面由集中营时期的黑白转至结束时出现彩色的胜利人群,暗示着人们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人类跨越了恐怖,过去被抛到了身后,原来的道德理想得以安然无恙地长存下去[5]。电影娴熟的技巧使观众轻易地接受它所营造的一切,观众很轻松地理解了历史。大屠杀虽然很残酷,但痛苦只是暂时的点缀,黑暗是遮不住光明的。就这样斯皮尔伯格帮我们卸掉了面对历史时的重负,我们可以用不着直面大屠杀的恐怖就轻松地避开人性的黑暗。影片里高尚的人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掏空了我们追问大屠杀的苦难与反思自身处境的潜力。英国的黑格尔主义者罗斯说,《辛德勒的名单》让观众可以一直处于道德安全的位置,在党卫军司令戈特不断的施虐中分享无条件的厌恶,对辛德勒出世般的正义充满敬畏和惊奇。处于一种地位优越者的感伤,沉默地目击他人的暴力,免除对自己暴力的反思,处于这种非反思的优越位置就可以避免正视尖锐的问题:我会这么做吗?[6]导演与观众似乎有某种默契,都满足于善良战胜邪恶的快慰,都满足于“不管如何,世界总是美好的”的辩证法。我们都喜欢关注英雄、拯救、奇迹这些例外,而不是大规模的死亡本身。我们不应该忘记阿多诺的警告,对千千万万的死难者来说,这种把苦难浪漫化,从集中营囚犯的悲惨中获得赏心悦目的审美乐趣不是一种野蛮吗?
还有电影《美丽人生》也逃不脱文化工业的摆布,它创造了一个逃避黑暗的世界,以为靠想象就能创造出一个美丽的人生,假装集中营是个游戏就能在现实中躲过。其实无论哪个父母或英雄都不能在集中营里救出孩子,但这类电影的受欢迎显示有大量情愿相信这些童话的观众。真实的苦难与恐怖不能被涂脂抹粉,集中营里无法提炼出美感。对于这种文化工业,阿多诺批评说,文化成为一种娱乐,满足就是点头称是,娱乐代表了一种错误的幸福观,以标准化的方式来适应轻松消费,压制了反思,掩盖了我们无力的处境与地位。文化工业的力量甚至使得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名言成为口号,成为一句抽象空洞的道德命令,甚至成为阿多诺所痛恨的大众文化的消费品,当然难逃被严重误解的厄运。对此阿多诺早有先见之明:“口号令人怀疑不仅是因为它们把思想贬低为反面,口号本身就是非真理的标志。”[7]
二、艺术再现的困境
其实,阿多诺并不否认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必要性,因为苦难要求写诗来表达,艺术有见证罪恶与苦难的道德责任。但这种艺术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它既不能是亚里士多德眼里的起教育与愉悦作用的艺术,也不能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判断。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一种无功利的快乐,如果我们以旁观者的姿态对苦难保持审美距离,以超然的距离欣赏苦难、消费苦难,那么就可以获得超然物外、冷漠的审美满足,从而将痛苦审美化、娱乐化。阿多诺拒绝以任何审美化的方式对待罪恶,以艺术欣赏的姿态来玩味痛苦。艺术甚至会再生出一种它所试图克服的恶,正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所说,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8]。这些都是阿多诺所批判的野蛮的艺术。
从更深层次来说,阿多诺谴责一切试图书写奥斯维辛的艺术都是野蛮的。现实的恐怖与黑暗超出通常艺术与语言力所能及之范围,艺术家会意识到这种责任的不可能性,写诗始终处于内疚状态。阿多诺还反对同一性哲学企图进行整全式把握苦难的专横,也拒绝黑格尔把艺术定义为美的感性显现的美学辩证法:“所谓的对被枪托打趴下而造成的赤裸裸身体痛苦的艺术加工,包含着从中挤出快感的可能,无论它有多么遥远。通过审美风格的原则,受害者不可想象的命运就会看起来有了某种意义,它会变得理想化,恐怖被软化,仅此一点就会造成对受害者的巨大不公平。”[9]88艺术在结构与形式上总是具有某种条理及内在一致性,所以,即使主题是苦难,这种审美形式赋予了苦难某种意义,无意义的大规模死亡仍然难逃变成某种自我疗伤的精神胜利法。
阿多诺强调,艺术试图从这些完全无意义的事件中挤出些意义,比如苦难可以磨练人的灵魂这类道德说教。当我们用任何积极性、拯救、历史意义等肯定全能上帝的神学残余话语来安慰众人时,艺术带来的审美快感就会使得苦难被合法化,这些空洞的希望都是对死者的不公正。所以说,在所发生的苦难现实面前,写诗始终是一种冒犯。在奥斯维辛之后,艺术面临的困境在于,它既要表达苦难,又无法真正表达苦难。乔治·斯坦纳也指出了审美与野蛮的联系,他说,道德上的想象力能够被快速地吸收进虚构作品,所以诗歌当中的痛哭可能比街头的哭声更大声、更紧急、更现实;小说中的死亡比隔壁的死亡更能感动我们,所以在审美修养的培养与个体非人性的可能之间有着隐蔽的联系[2]61。在这里,艺术的表达很容易转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对高级看客来说,现实中的苦难恰好是提供精神创作的最佳养料,这种痛苦的极乐不也是一种高级的野蛮吗?
比如马丁·吉伯特的纪录片《大屠杀:犹太人的悲剧》(The Holocaust)就非常有雄心地展现了众多受害者的声音,该片在补偿性的叙述框架中展开,最终以回归正常、庆祝人类精神的胜利历史结束。有学者指出片中关于集中营的解放、以色列的建国、幸存者定居美国等叙述都属于一种救世神学[10]。埃利·韦塞尔也批评说:“(该片)是虚假的、伤害人的、廉价的,是对那些已经死去或存活下来的人的一种侮辱。它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事件转化为肥皂剧, 我们看到犹太人排成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队伍走向巴比山谷,我们看到倒在血泊中的裸体死尸。……可这一切都是假的……大家会说,同样的技巧也运用于战争电影和历史娱乐中。但大屠杀是独特的,而不是另一个事件。……这部片子将大屠杀处理为另一个事件而已。奥斯维辛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也是无法得到形象化的。大屠杀超越了历史……死去的人握有的秘密,是我们活着的人不配,也无法找回的。”[11]这正是文化工业的常见做法,它把纳粹屠杀当作仅仅是历史上的另外一个事件来处理。其实死者拥有的秘密是活着的人没有能力揭开的,大屠杀作为终极的事件与终极的神秘,永远无法被理解与传递。
阿多诺还批判了让-保罗·萨特与贝尔托·布莱希特所代表的使命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它提倡一种政治化的艺术,强调文学应该直接干预现实。他担心这种使命文学会成为宣传工具,从而失去自主性。阿多诺指出:“布莱希特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反而减轻了其罪行,使得纳粹不再是社会权力集中的产物,而更像是一个事故、不幸或罪行,以致真正的恐怖被消解。”[9]83无论布莱希特等艺术家的本意如何,这类艺术难免有试图从灾难中挤出意义的嫌疑,所谓负责任的艺术其实是在利用苦难,把苦难工具化。他们强加给苦难以某种意义,赋予苦难唯一整全的意义,于是苦难就成为榨取文化意义的对象。同样,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使得大屠杀的恐怖转变为对人之本真性的肯定,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处境下,仍然可以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而使真正的冲突不那么尖锐与震惊。
三、沉默与言说的张力
既然写诗注定是野蛮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对之保持沉默呢?一些人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缄默是一个选择。乔治·斯坦纳就认为奥斯维辛的世界处于语言与理性之外[2]101。大屠杀留下了一个不可愈合的伤口,这使我们处于失语状态,对这个伤口唯一可能的反应是沉默。德语已经被纳粹毁灭,再也无法维持作为表达理性与真理的功能。语言是一种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第三帝国的统治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当这个关系的基础已被摧毁,原来的语言也无法继续下去,社会生活中的扭曲与谎言都会被语言吸收。
阿多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现在每一种表达行为都在歪曲真理,出卖真理,同时,无论用语言做什么都会遭受这种悖论之苦。”[3]41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任何表达都可能沦为对死难者不尊敬的野蛮行为,俗套的话语在灾难面前总显得无力。任何一种幸存者的代言都可能是对无法言说者的背叛,他们可能利用受害者作为素材产生的审美快感,语言自身的有限性不足以表达这种灾难。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不可言说的只有保持沉默。当大屠杀的暴行超出语言的表达能力与范围后,最恰当的反应就是沉默,即保持对不可言说的沉默。奥斯维辛的不可言说性只有通过沉重的沉默来纪念,默哀仪式就是恰当的一种表达,只有沉默才属于死者。“艺术的真正语言是沉默”[12]112,这种沉默提供了超越自己经验并进行反省的媒介。
但是,沉默本身在灾难面前也具有悖论性,沉默可能意味着纳粹野蛮主义的胜利。因为对罪行保持沉默正是纳粹企图实现的结果,他们不仅使集中营隐蔽起来,而且毁灭了见证者。艺术的表达可能陷入对灾难受害者的不敬,而沉默又会让人误解为纳粹野蛮主义在精神上取得了胜利。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对此评论说:“我经常感到只有退入沉默才行,我认为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有诗时也是这样想的。但如果保持沉默的话,我们正好做了纳粹想要的:像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行事。如果保持沉默,我们就允许错误表达近来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篇章。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防止这些再次发生?有思想的人就会无法获得这些洞见。”[13]面对奥斯维辛,言说是有风险的。它太容易使我们用人性中已有的东西去猜度他人,结果阻碍我们对造成奥斯维辛历史条件的洞察。
通过对这些张力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不是以一句谴责写诗的野蛮就结束了反思,因为彻底的反思将不断指向自身,包括沉默。“为维持这种有罪的与破烂的文化辩护的人都是其帮凶,而拒绝文化的人直接加深了文化显示的野蛮主义。甚至沉默都不能摆脱这个循环,因为在沉默中我们简单地用客观真理的状态来合理化我们的主观无能,从而再一次使得真理沦为谎言”[3]367。奥斯维辛后的一切文化都难逃脱帮凶的嫌疑,即使是批评者也要提醒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野蛮文化的帮凶,因为无论如何言说,都很难走出导致奥斯维辛得以可能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即使是彻底批判也只能在原有的逻辑方式和话语系统内进行,它潜在着相当强大的消解力量,随时都可能将批判重新纳入一个环节而消解批判。这里需要区分两种野蛮,我们不得不坚持一种蕴含着野蛮的文化而不是退回到赤裸裸的野蛮状态,所以我们并不能完全放弃艺术。
应该说,阿多诺对轻松言说灾难的警惕受到了犹太教的禁止偶像崇拜的启发,犹太教禁止为上帝造偶像,不许为上帝命名的诫律也就禁止了具体的未来图像。这些诫律证明了上帝的崇高,上帝是不受限于图像和语词的,对于他的存在我们只能间接地来探究与接近。阿多诺还解释说,具象思维没有反思性,只有在具象的缺席中才能把握客体。图像的神学禁止的世俗形式就是不允许对乌托邦作肯定意义上的描述[3]207。犹太教的教义不允许减轻所有关于有限性的绝望的语言。它的希望仅仅在于禁止召唤虚假的上帝,禁止偶像崇拜就是禁止用任何有限的语言来代表无限,且通过不断地否定虚假之物来表达无限。
阿多诺一直强调忘记苦难的危险性,他认为对过去苦难历史的压制与冷漠会丧失对痛苦的敏感与知觉,从而泯灭我们的良知。“极端的苦难不能容忍遗忘。这种苦难需要它所禁止的艺术的存在。只有艺术才能让苦难得到表达而不会立即背叛”,但这也并不是说对记忆的高调呼吁就是解决之道,似乎有了记忆就可以防止大屠杀永不发生,这是企图在记忆与美好的未来、遗忘与恶的回归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只有通过艺术的表达,苦难才可以不受扭曲地再现。“在不可理解的恐怖时代,黑格尔的原则‘真理是具体的’可能只对艺术适用。黑格尔所认为的艺术是对苦难的意识得到了远超过他所能设想的证实”[12]18。艺术成为唯一有可能表达真理的媒介,艺术可以再现产生苦难的社会条件及相应的文明与价值体系。阿多诺认为艺术具有双重作用,相对于资本社会,艺术是自律的,恰恰是这种自律性给了它社会功能与价值,这种社会性使它具有了他律性。艺术的自律性并不意味着艺术就不需要对现实负责了,阿多诺同样认为,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似乎有自主性,但它追求纯粹的快乐,否认与现实有关,结果在现实面前失去了力量。所以阿多诺并不同意艺术可以与现实无关,艺术可以通过与现实保持距离来批评现实,并且显示意识形态隐藏的内容。艺术必须保持这种张力,它必须不断地反对自己,包括艺术的形式与概念。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必须保持其否定性与批判性。阿多诺一直到晚年还强调说:“我并不希望缓和我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它以否定形式表达了激发承诺文学的冲动。恩斯伯格的反驳也仍然是正确的,文学必须抵抗这个判决,换句话说,奥斯维辛之后艺术的存在不能向犬儒主义投降。”[9]88
具体来说,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可以恰当地表达这种苦难。现代艺术可以通过碎片化、分离性的表现手段来提供反表达的内容,以防止任何有意义总体的生成。比如卡夫卡的作品就可以显示社会在个体身上留下的伤口,但又避免产生某种意义,拒绝满足读者的任何期待心理。这种艺术要求推倒现存的秩序,使我们感觉到应该有不一样的现实。同时它不排除拯救的可能,虽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图像,但又可以激发对他者的一种想象。这种艺术上的效果是借助身体性的力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概念,它告诉我们的身体而不是诉诸理性。这种艺术不是试图去产生某种意义,而是让我们体会某种经验,这不是愉快、安慰、有序的经验,而是否定性的经验,比如恐怖感、主体受到伤害的经验。在奥斯维辛之后,甚至某些古典音乐都显得怪诞和可疑了,策兰的诗《死亡赋格》揭露了这一点。策兰的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它拒绝升华或美化这些否定性的经验,完成了没有诗意的诗歌。
四、结语
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言说理性不可言说的内容,但艺术表现自身的暴力也难以避免,我们需要承认其不可能充分表现罪恶与苦难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始终面临着这种两难,奥斯维辛之后生者有写诗的责任,但又难以摆脱写诗的野蛮性。毫无疑问,阿多诺对于艺术的暴力困境的思考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阿多诺似乎过于强调了艺术所可能具有的暴力与野蛮,我们如果害怕艺术具有的问题而裹足不前的话,反而使得历史上的苦难没有机会言说与表现,暴力就会更加嚣张。而且,阿多诺的论断有其特定语境,它针对的是当时西方用艺术来消费苦难的现象而发出的警告。对于经历过种种深重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艺术在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伤害面前的失语与沉默,而非过早地奢谈艺术的暴力与野蛮。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但我们的艺术并没有拿出与苦难相匹配的有份量的作品。为此,我们需要超越阿多诺口号式的论断,深入到其富于内在张力的思辨中寻求更多的启示,以勇敢地承担起艺术在邪恶与苦难面前的责任。
[1]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George Steiner. 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3]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M].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4] Theodor W Adorno. Prims[M]. Cambridge: MIT Press,1981:34.
[5] 凯尔泰斯.谁的奥斯维辛[EB/OL].[2014-09-02].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5747010005d8.html.
[6] Gillian Rose. Judaism and modernity:philosophical essays[M].Oxford: Blackwell, 1993:35.
[7] Theodor W Adorno. Critical models: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41.
[8]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04.
[9] TheodorWAdorno.Notestoliterature:Volumetwo[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Robert Fine, Charles Turner. Social theory after the holocaust[M].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223.
[11]Elie Wiesel. Trivializing the holocaust[J]. New York Times, 1978(16):2.
[12]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3]Bruno Bettelheim. 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79:97.
[责任编辑 彭国庆]
2014-10-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编号:13YJC720005).
陈旭东,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106;G206.3
A
1009-3699(2015)03-0339-06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